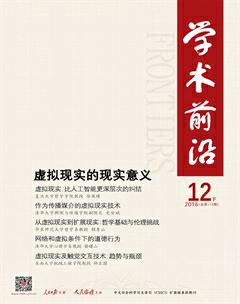作为传播媒介的虚拟现实技术
【摘要】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自上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以其独有的“复现真实、临场体感”的优势而备受推崇,近两年来其影响拓展到新闻业、传媒业、文化创意产业和娱乐业等多个领域。本文从传播理论和媒介史入手,发掘VR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必然性,梳理和分析在VR影响和带动下新闻传媒业、文创产业和娱乐业所发生的多维转向,并结合批判理论阐发其对人类传播和媒介生态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和隐含的风险。
【关键词】 虚拟现实 新闻业 传媒业 文化创意产业 技术批判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4.002
媒介之于人类传播行为的重要性,可以用麦克卢汉那句被广泛引证的“媒介即信息”的经典论断来加以概括和阐发。纵观学术界迄今为解析人类传播而形成的诸种“传播模式”,我们便可发现,无论它们的宏观方向、中观构型、微观单元如何嬗变,“渠道”(Channel)亦或“媒介”(Medium)都始终居于各类传播过程之中枢,而技术革新则又是驱动媒介生态变迁的根本动力,也是带动社会建构、发展、转型的重要动因。作为当前最前卫、最受关注的新兴传播媒介,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的理念肇始自上世纪6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跳跃”式发展和“降槛”式演进,从尖端科学领域拓展至人类日常体验,成为“人人皆可用”的大众化传播媒介。对于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而言,VR所独有的“复现真实、临场体感”的优势也逐渐被发掘出来,为叙事者提供了又一描摹和体验世界的强力工具。2012年,美国新闻记者诺尼·德拉佩纳(Nonny de la Pena)首次运用VR技术拍摄深度报道纪录片《饥饿洛杉矶》(Hunger In Los Angles)自此以后,各大媒体机构纷纷斥资试水,短短几年间,以360度全景图片、VR纪录片为主的新闻佳作层出不穷,全行业都被卷入了以VR媒介为核心的内容创制、生产和分销的热潮中。①
与业界的探索和试验相匹配,中外新闻传播学界有关VR媒介的研究亦如汗牛充栋。笔者在2016年初发表的论文中,较早向国内受众引介和分析了VR作为新闻叙事工具的潜质,以及在其影响下传统新闻业在内容、业态和样式上出现的多重转向。②其他学者也从观念、技术等不同角度切入,聚焦于VR在各大传媒的具体应用与未来前景。总的来看,国内学界仍倾向于将VR技术同特定媒体的专业化新闻实践牢牢绑定,从具体案例入手剖析其利弊,问题导向和针对性较强,但视野却不免被拘束在传媒一隅,往往忽视了VR媒介在广义的文化范畴中,传播主体可倚仗其完美再现真实情境的能力,辅以VR器械的多重感知模拟,营建出跨越时空的“临场感”,以驱动受众“共情效应”,显著提升客体对内容产品的体认和感知。
VR媒介的理论溯源和历史脉络
VR技术作为传播媒介最为核心的两大优势,一是在于其高度仿真现实情境的“复现”能力,二是其借助器械模拟人体感官,使受众仿佛“沉浸”于新闻现场或故事情境之中的“临场”效果。③从媒介发展史的宏观视域看,上述两个特征恰好耦合传播媒介技术演进的两大基本趋势,即“现实化”(Actualization)趋势与“人性化”(Anthropotropic)趋势。
“现实化”。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为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不断改进媒介技术,提升传播能力,以克服时空所限,最大限度地复现或还原所处世界的全景样貌,从而拓展自身的有限“感知阈”。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始终处于探索无限世界与自身有限感官的固有矛盾之中,特别是对于那些相隔遥远时空距离的客观世界,常常是“心向往之,然不能至”。麦克卢汉精辟地指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类感觉能力的扩展或延伸”④。他所创立的经典媒介理论体现了人类试图借助媒介技术以期完全掌控客观世界运动、存续、变化的永恒追求。早期出现的各类媒介形态——口语、文字、图画等,由于本身特性所致,不仅难以兼顾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之间的平衡,且因符号抽象,对真实的表征往往间接而含蓄,而非直观反映,由此产生“传播的偏向”。简言之,以麦克卢汉等传播理论家设定的标准来衡量现有的各种传播媒介,无论在其还原真实的能力上,亦或在其复现世界的程度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书籍报刊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拥有了专门化、机制化、大众化的、对外部世界进行摹画与传播的媒介。印刷媒介可以用抽象的文字配合静态直观的图片,对发生在不同时空界面的世界进行视觉上的精准复现。相对而言,广播媒介则更专注于开发听觉要素,但却丧失了对视觉要素的含括。电视媒介声画同步,视听兼有,用声音和影像的水乳交融来表意情境。互联网则融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于一炉,以多媒体形式多侧面映射世界。简言之,媒介对于现实世界的表现和还原能力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渐变提升的。然而,事实上,仅凭如上所述的诸种媒介,无论它们运用多么凝练的文字辞藻、何等华丽的声光图像,其对客观真实的表征依然是不完美的,“现实化”过程中仍会面临沃尔特·李普曼所指的信息衰减境遇——即对“意义”的损害。⑤以此脉络来衡量,虚拟现实技术则可近乎完美地复现真实世界,且因其以建构虚拟空间来复现真实,不受时空所限。简言之,VR媒介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复现与体验无限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媒介“现实化”趋势的终极形态。
“人性化”。莱文森在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经典论断的基础上,强调了媒介演进过程中凸显的“人性化”趋势。他精辟地指出,“兴盛的媒介技术只是复制、对应、调适和再现了生物学传播中的某些重要方面与方式……人类在早期的媒介延伸中,可能已经失去了某些生物学的传播成分,而我们则是想要重新捕捉它们,渴望回到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⑥
麦克卢汉就曾将人类最为原始的“口语”视作最为优质的媒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口语传播中,人的五官皆可受到刺激,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且拥有极强的互动性。以报纸为主的印刷媒介过分专注于单一视觉感官,而其后出现的广播、电视与近期兴盛起来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则是不同程度地“补偿”并“再现”了“口语”这一最人性化的、基于互动交流这一原初本能的传播形态。上述的媒介演进过程也符合笔者在探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演进时所概括的从“吾牠关系”(I-It Relationship)到“吾汝关系”(I-Thou Relationship)、从“客观新闻学”到“对话新闻学”的历史脉络。前者强调“传者中心”的单向灌输,且普遍“物化”“降贬”受众,禁绝交流,将其隔离媒介叙事之外,只能被动接受传者所阐释的意义;而后者则将先前被“物化”的受众升华为“人性化”主体,其与传者地位均等,双方皆可阐释文本,于协商交流中角力意义。⑦
与之相应,VR媒介另一显著优势则在于其赋予了受众自行探索意义的无限潜能,且在传播过程中以高仿真的传感技术使受众在虚拟环境中的本能活动基本契合现实所为,进而达到以假乱真、身临其境的效果。一方面,VR媒介在叙事上消解了横亘于“传者”和“受众”之间的无形障壁——即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所指的“第四堵墙”。⑧传播媒介的“受众”类似戏剧中的“观众”,被观众席和舞台间的一面无形之墙相隔,只可远观;而VR技术则可破除此壁,让受众以第一人称“浸入”故事中,“观众”被带入了“表演”,其不再拘泥于单线叙事结构,而拥有了穿越时空的多维体验空间;另一方面,VR媒介采用“多通道感觉输入”(Mutimodal Sensory Input)系统,使虚拟环境中的行为以较高的质量响应和匹配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类似境遇下的本能感官需求与身体动作,一举一动皆如现实,仿佛真如临场。⑨综合来看,VR媒介充分考量了受众的“人性化”需求,无论是给予其参与叙事的主观能动,亦或是对其生物感官的仿真、模拟、迎合,都达到了现存各种媒介技术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数字化时代新兴的“融媒”与“浸媒”的典型代表。从本文所做的理论溯源来看,VR成为传播媒介基本契合于人类传播和媒介生态演进的历史脉络,因而可以成为今后人类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VR媒介的传播效果
从广义上看,只要传播主体是通过一定的“仿真”“模拟”手段,制造出一个“类现实”的复合世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用户进行互动,实时化、动态化地响应用户输入的各类指令,满足如上条件的则都可以被称之为VR媒介。⑩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更替,VR技术本身的实现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当今,根据其“仿真”“模拟”类现实、构建虚拟世界的方式差异,VR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模式。一是以3D建模(3D Modeling)和“计算机合成图像”(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简称CGI)为基础构造世界;二是凭靠近年研毕的“360度全景立体式照/摄像机”复现现实情境,以此建构“拟态真实”。?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实时的“互动”以至于更高级的“沉浸”,指令输入—传感系统也在经历不断的改进,从早期依靠屏幕、键盘、鼠标、耳机等辅助工具进行抽象性地指令输入与初级的感觉输出,到后来更为直观本能,可追踪头部移动的VR一体机与头显。上述两个标准相互配合和交叠,共同构成了VR发展的两个世代。
早期的VR技术世代,亦称VR1.0时代,以3D模型与CGI构造世界,受众以电脑、手机、电视等为载体,施行指令输入响应(例如,鼠标点击、滑动;键盘控制;手柄操作;手指滑动)和初步感觉输出(例如,借助于电子屏幕传输视觉;借助于耳机等传输听觉)。在其后的VR2.0世代,技术人员在进一步完善3D与CGI技术细节的基础上,附加了借助全景照摄器械记录现实情境的全新“仿真”手段。同时,技术人员还改善了1.0世代间接的、以键盘、鼠标等为主的“指令输入—响应”系统和以屏幕、耳机为媒的低级“感官输入”系统,而是替换以模拟现实动作、更人性化的“传感系统”(如头部追踪、眼球追踪、声音方位转换、手部触觉模拟),以直接加深沉浸体验。VR1.0的世代模式在近20年出现的各类经典3D游戏中表现最为突出,且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运作机制;而VR2.0世代的辅助科技还在快速更新之中,并未出现模式化的产业构型,换言之仍处于“创新扩散”阶段。有鉴于此,本文选择VR1.0世代的相关3D游戏案例,解析VR媒介所具有的最为突出也是最为独特的传播效果——即从“驯化时空”到“身份代入”。
保罗·莱文森认为,人类拓展传播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认知渴求。?人类对于未知的世界总是有着无限的好奇,然则因自身生物性所限,只能依靠媒介协助体认无穷尽的现实,且因在现实时空中受限于各类规则的条条框框,很多个人化的欲求与梦想通常难以实现。VR1.0世代出现的3D游戏,特别是角色扮演类(Role-playing game,简称RPG)作品,便成为了很多人梦想成真、规避现实的“伊甸园”。它们依靠3D建模和CGI技术“驯化”时空,虚构出一个个融古典与现代、真实与魔幻于一炉的“仿真”世界,无论是中世纪的帝都罗马,亦或现代的花都巴黎,还是宏大的艾泽拉斯大陆,皆可“现实化”为玩家触手可及的情境。现实中的草根网民可以化身为反恐精英、中世纪战士等,在各类虚拟空间中遨游探索,收获在未知遥远世界的难得体验。
另一方面,作为传播媒介的VR技术通过“驯化”时空还可以实现对用户的情感代入,这一目标的实现与“沉浸”感亦或“临场”感的多少直接挂钩。有学者提出了“如真反应”(RAIR:Response As If Real)的概念来衡量VR媒介的传播效果。“如真反应”的产生主要系于三个变量:现场拟真度、事件合理性与第一人称视角。?由此可见,“仿真”技术的完美与否,决定了受众使用VR媒介的满意度。响应传感系统的舒适度也是构建“拟真度”的重要方面,一般说来,VR媒介响应传感系统的设计愈契合于人类的生物本能,则用户的沉浸感和临场感愈强。事件合理性即为虚拟情境中发生的各类动态事件,其结果应符合现实常理,否则会让受众产生极大的“违和感”,削弱传播效果。第一人称视角则是人类的本能视角。如上所述的所有目的则都是为了达成所谓的“人性化”目标,即让受众脱离“旁观者”,产生将自己“代入”到游戏角色的“沉浸”感,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高层次互动中,最终达成“感他人所感,想他人所想”的“共情效应”(empathy)。
美国暴雪公司(Blizzard)2004年出品的经典3D RPG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the Warcraft),无论在驯化时空还是情感代入上都堪称VR媒介产品的范例,在国内外历经十多年而不衰。以其中的经典角色“纳兹戈林将军”为例,他是一直跟随部落玩家征战的NPC(非玩家控制角色),在多年的游戏时间中,他与玩家一起成长,从游戏早期的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最后的部落将军,后来却因秉持理念不同与玩家刀剑相向。在最终的战斗中,多年的沉浸式游戏体验使很多玩家与自身的虚拟角色产生“共情”效应,仿佛这位虚拟的、曾经与角色对话、一同战斗的“将军”真的就是和自己有着深厚友谊的老朋友。即使战斗结束,有些玩家也还纠结不已,纷纷各处撰文纪念这位NPC,赞扬他对部落荣耀与信念的坚持。这样的例子在《魔兽世界》等一批3D游戏中比比皆是,很多虚拟的角色以及他们身上所带有的特质、传承的精神都在玩家的游戏情节体验中,经由潜在的情感代入机制深深成为脑海中的回忆,这种无形的“情怀”效应不仅为其培养了庞大的“死忠粉丝”群体,也在之后不断转化为有形的经济利益。2016年6月上映的《魔兽》电影,便在国内掀起了观影热潮,累计总票房14.7亿元,而其中的大部分观众都是当年的游戏玩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VR作为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情感代入效应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开掘,还会迸发出巨大的经济乃至政治方面的转化潜力。
VR媒介重塑新闻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指出,当今社会承载各种文化内容的“象征形式”——例如,语言叙事、艺术作品等,其制作、接收与传输越来越多地通过技术化的媒介平台来完成。由于文化一词本身包罗万象、纷繁芜杂,仅凭一己之力往往难以把控宏观图景。借助体制化的媒介技术来认识文化,尤其是能够很容易感知到处于遥远时空之外、平日难以触及的异质文化,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经验。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介力量建构了受众对特定文化的“解释框架”,这就是汤普森所谓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过程。?从这个意义看,媒介作为支撑这一解释体系的基础性工具,其发展变化会对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即“传播革命”引发“文化革命”。本文试以VR媒介为中心,归纳和解析在其影响下新闻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生的诸多变化。
三方转向:VR媒介的应用与传统新闻业的嬗变。作为新型的传播介质,VR的形态和属性与传统媒介大相径庭,加之传媒业是由诸多异质要素融合而成的“非稳定结构”,故VR的深度介入势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业内各种结构性力量的转型、调适与重组。具体而言,VR媒介的广泛应用对传统新闻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容转向”——从浅层叙事到深度内容。严格来看,这一转向恰好映射了前文所述的媒介演进的“现实化”趋势——即对客观现实的无限追求。前文中已多次提及,人类对未知世界存在着无限的好奇,媒介的产生即为人类感知和探索世界之延伸,而新闻业作为最为机制化、体系化、规模化的大众传媒机构,自然也对“复现真实”存在着永恒不懈的追求。
受限于传统媒介之物理特性及其表征符号的固有抽象性(如文字),即便是再全面、再优质的新闻报道,它所提供的也只是有限、浅层的“片面真实”,许多存在于“客观语境”中的细枝末节因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被删减与过滤,大大降低了受众对客观真实的体知与把握。相比之下,VR媒介却可近乎完美地“仿真”现场,特别是在VR2.0世代出现的“全景照/摄像机”的辅助下,这一优势则更为突出,360度的全景式信息呈现于受众眼前,虽然它仍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画复现”,但其承载的信息量相比于传统媒介而言大大提升。显而易见,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背景、细节愈多,其表征真实的能力也就愈强。另一方面,时间与空间的“障壁”往往是妨碍新闻报道复现真实的掣肘。传统媒体要想复现遥远时空离距外的真实世界,通常要耗费巨量的资源与精力,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真实。而VR媒介则可轻松穿越和切换时空,可利用3D和CGI建构、仿真乃至复原诸般特殊新闻场景,尤其是历史事件、灾害现场、机密违禁区域等,也可借助全景设备直接截取新闻现场情境,既能有效节省机构资源,又可确保新闻叙事质量。综合来看,在VR技术的辅助下,新闻业的内容产制将由原初的“浅层片面”转向“深度全面”,再现和还原新闻现场的能力有了本质上的提升。
第二,“业态转向”——从各自为战到跨界融合。美国皮尤(Pew)中心发布的“新闻卓越计划”报告显示,传统媒体已经难以引领数字革命潮流。相反,数字化时代的媒体创新都是在新闻机构以外的领域产生,以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新闻的未来。?不容否认的是,当下的传媒业在跟进尖端技术潮流上常态性地落后于各大高科技公司。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公司对于新闻叙事潜能的发掘能力也极为有限。事实上,如果传统媒介能够发挥其叙事经验、品牌效应和公信力,能够与紧密追踪尖端技术的高科技公司实现有效融合,而非各自为战,权威内容与尖端科技的强强联手将很容易形成“爆点合力”,从而吸引大量受众。
VR新闻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实践者诺尼·德拉佩纳是美国《新闻周刊》的前记者,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墨客”。她在2012年与加州大学学生、VR“极客”帕尔默·洛基(Palmer Luckey)合作,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VR深度报道纪录片《饥饿洛杉矶》,并在当年的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一炮打响,首次向世人展现了VR强大的新闻叙事潜力。有趣的是,帕尔默·洛基也在其后声名鹊起,以辍学生的身份获得25万美元的众筹投资,并于一年后推出了革命性的VR头显(Oculus Rift),成为硅谷最为年轻的亿万富翁。由此可见,“硅谷”与“舰队街”“墨客”与“极客”之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融合,将会是后VR时代的新闻传媒业主流。?
第三,“模态转向”——从被动旁观到本能体验。这一层面的转向回应了上文提出的媒介演进“人性化”趋势,在VR媒介的新闻叙事结构中,受众参与新闻叙事的方式相较之前出现革命性转变:VR借由对构成“如真反应”(RAIR)的多个要素的共时性满足,让受众产生了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临场感”,受众成为了舞台上的“演员”——即新闻现场的一份子。因此,受众便从传统新闻业中被动的、被叙事结构所挟制的“旁观者”转化为了主动的、基于生物感官本能的“体验者”,由无足轻重的“物化”客体升格为同等重要的“人性化”主体。VR叙事将“外化叙述”转变为“内化情境”,打破了传统的基于叙事者的、固化的单线结构,进而转变为基于受众的、动态且自由的主动体验模态。借助于VR媒介,尤其是在VR2.0世代越来越精确的仿真手段、愈来愈先进的基于人类生物本能的感官模拟系统,用户“沉浸”感显著提升。受众被“代入”新闻现场后,很难发现自己身处幻境,虚拟的现实成了真正的现实,在此般“共情效应”和“多感官刺激”下,用户对特定故事与主题的认知和体验也随之提升。
四维趋变:VR媒介与文创产业的联动。VR技术——特别是以“全景照摄”为仿真载体的2.0世代技术——历经数年的实践打磨,与新闻传媒业产生了深度的“化学反应”。由于传媒业是文化的主要表征与传播手段,其所发生的三方转向也会带动其所属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发生“连结性转向”。总的来看,VR媒介与文创产业的联动及合作的未来前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受众年轻化”。游戏业作为VR1.0世代技术应用最为成功的旗舰领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凭借其独特的驾驭时空、策动情感的运作机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受众基础,而这一批年轻的游戏受众也成为了现今VR2.0世代技术创新扩散的第一批“创新者”(Innovator)和“早期使用者”(Early Adopters)。GWI(Global Web Index)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大约有39%的人群对VR的未来应用较感兴趣,这对VR2.0的技术普及来说应是较大利好,已基本覆盖了“创新扩散”理论中界定的“早期多数”(Early Majority)——即主动“拥抱”新技术的青年人群。其中,近半数的16~34岁的年轻人对VR应用持欢迎态度,而到35~44岁人群中就下降到40%,45岁以上人群则跌至20%上下,可见愈年轻的受众对VR的好感度越高。?由此来看,对于一些主打传统、经典和高端内容的文创产业领域,如博物馆、戏曲、曲艺等,以VR为媒介对内容进行重新包装,不仅能够借助其媒介特质助力内容产制,还能凭其新颖、独特的操作体验将那些已与传统媒体“割裂”的、沉浸于社交媒体和新式设备的年轻人重新“拉回”到自己的受众群体中。
第二,“传播无界化”。媒介传播中最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便是汤普森所强调的“时空离距”。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往往很难跨越国与国的边界,即便是对互联网这样的“全球媒体”而言,仅仅依靠镜头拼接和文字组合难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换言之,传统媒体对远在异国他乡或时间久远的目标文化难以进行完整、全面的呈现,时常会由于“传播偏见”和“文化折扣”而加剧误解和隔膜,从而导致文明的冲突甚至于血腥的战争。
而人们借助于VR媒介则可以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播“无界化”,即对空间和时间边界近乎完美的驾驭。VR2.0世代的“全景照摄”技术,可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位于世界任何地点的真实情境。虽然一些“认知死角”仍然在所难免,但人们能够借助VR媒介实现对物理意义上的“时空离距”的超越。对于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文明形态或文化现象,则可借助3D建模和CGI进行拟态复现,完成对“时空离距”的征服。这也就是说,用户足不出户,便可借助于VR媒体到达空间各地,横亘时间各点,且能高效体认目标地域或特定时间段的现实情境,这有助于生活在不同地区和社群的人们实现高质量的跨文化传播或对历史传统的高保真体验。
第三,“教育互动化”。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宝贵财富,对其的保存、传承、发扬一直是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图书档案、音像、文化培训等,都是教化人类的主要方式。然而,严格来看,这一类的教育模式普遍都是单向的灌输,受众本身还是作为“被启蒙者”而存在,从整体来看缺乏互动手段和交流动力。VR媒介的一大特质,便在于其赋予受众探索未知世界的强大主观能动性。在VR1.0世代的一款经典3D RPG游戏《刺客信条》中,我们就能窥见VR作为教育工具的潜能。这款游戏的每个版本都会以3D模型与CGI高度还原1~2个存在于历史上的城市: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等等。制作团队会赋予历史知识与特定地点的联结,比如玩家走到巴黎圣母院,游戏中就会跳出对这个建筑的介绍;历史上的很多名人,也会出现在游戏中,与玩家进行对话,共同经历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相较于枯燥的阅读、听讲、参观,显然是这类“寓教于乐”的游戏式的动态沉浸体验更能吸引受众的参与。一家市场调查公司(QUID)于2016年初调研了454家VR技术公司,结果显示,“教育+游戏”与“硬件产销”“现实应用”构成了VR产业的三个支柱领域。?这体现出VR媒介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即整合了“教育”和“游戏”这两个在传统媒体时代相互掣肘的领域,让学习真正成为以“快乐体验”为特征的生活方式。
第四,“娱乐纵深化”。VR技术最早吸引人们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其就是凭借驯化时空、建构虚拟世界的“数字化迷思”来激发用户的视听体验,其后通过各式传感系统模拟现实动作,将本能感官体验放大到极致,给予人们前所未有的震撼。VR1.0世代3D游戏产业的大繁荣,充分展示了VR在娱乐产业方面的巨大潜能,这还只是在模拟传感系统和现实建构方式皆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准下达到的传播效果。步入VR2.0世代后,屏幕载体被支持头部、眼球动能追踪的VR一体机与头显替代,配合手柄触觉模拟、声音方位转换等高科技传感系统,附带可以抓取实景的“全景照摄”技术,让用户的沉浸感进一步提高,这使得娱乐产品原本仅满足于感官刺激的浅表体验向着更为纵深的“全息体认”层面拓展。
VR媒介的广泛使用也催生了“VR电影”这一新品类。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VR电影+VR游戏”的复合版。其将精心制作的全景电影与第一人称参与冒险的游戏元素相结合,玩家能够沉浸虚拟世界中,无需依靠导演的“蒙太奇”剪辑来为观众“展开”剧情,转而依靠旁白或场景提示以第一人称视角主动探索故事进展,在多重感官模拟之下,代入剧情角色之中,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主人公”体验。
此外,借助VR媒介,受众还可以“到达”许多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亲至的娱乐场所,比如虚拟地“浸入”某巨星的演唱会、体育比赛现场,感受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氛围,相较于传统的电影、视频转播,VR媒介所能为受众提供的娱乐体验会有质的飞跃。在此影响下,娱乐产业的内容制作、渠道分销、业态构成将会出现重大转变,从而推动文创产业向着更加“娱乐化”“游戏化”“体验化”的趋势发展。
VR热媒介的冷思考
美国传媒业巨子沃尔特·安南伯格(Walter Annenberg)有句名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倒退皆因传播而起。”纵观人类历史,传播媒介在整合社会“众意”,形成宏观“公意”,进而动员民众方面拥有着其它技术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当VR由相对冷门的尖端技术演进为炙手可热的传播媒介之后,对其进行推广、宣传与应用的尝试则更须严格和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界有必要从技术批判的角度入手,发掘隐藏在VR媒介华丽包装之下的诸般隐忧,以期更为全面地把握其媒介特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视觉圣化”是美国学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将法国符号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理论与后现代文化语境相结合后所提出的批判性概念。杰伊认为,身处“后现代”的人们对视觉化影像的沉迷和膜拜,导致了媒介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吊诡的趋向:“虚拟的‘仿像是如此之真实,以至于完全征服了其旨在表征之物。”?这一观点虽原本被用来批判媒介的“商品化”趋向,但也是对当今众多沉浸于VR媒介的忠实用户发出的警世恒言。VR媒介所营造和传播的虚拟情境,与现实世界存在极高的拟真度,用户在其中的一举一动皆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复现,甚至还能满足用户的诸般奇思妙想,最终往往使用户陷入了真假莫辨、虚实混淆的境地。VR1.0世代产生了大批沉迷于虚拟游戏的“瘾君子”,陷入了对“视觉物”——即游戏内的华美虚拟“仿像”——的盲目崇拜之中,而忘记了自身应在何处。VR媒介产品取材自现实生活,却“篡夺”了其原初表征之物的权威地位,从“虚拟现实”一跃成为受众心目中的“实质真实”。
无论虚拟世界是在VR1.0世代由3D和CGI等技术手段创制而成,抑或是2.0世代的全景照摄之物,其本质都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真实”。即便它与客观真实何其相似,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手段可以完全复制客观现实中的所有细节。即便是使用现今先进的3D和CGI技术,亦或更高级别的全景照/摄像机都无法做到,出现“信息衰变”“传播偏向”的情况仍在所难免。此外,“叙事者”这一主体在VR媒介中并未消弭,而是依然存在,其仍可有选择性地向受众“呈现”“遮蔽”现实,决定他们“看什么”,亦可通过镜头组接、叙事设置决定他们“怎么想”,只不过其剪辑、呈现的权限与自由相较传统媒体时代有所降低而已,但其内在本质却仍未变化。
VR媒介的传播主体仍不是用户本身,虽然用户可以“沉浸”在第一人称的叙事当中,但故事本身依旧是由别人撰写的,用户只能被动地进行体验。无论这种沉浸式的主动体验模式多么新颖有趣,它与UGC(用户产制内容)等模式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传播主体所具有的权力为意识形态的宰制提供了必要条件。统治者仅需掌控传播主体这一端口,便可垄断VR媒介的内容生产,使所有用户和玩家沦为意识形态主体的“玩物”。
正如影片《黑客帝国》所表现的那样,“矩阵”电脑便是统治者,用户所看到的真实只是经过改良的意识形态幻象。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VR媒介为加深“沉浸”感为用户提供了较高层次的感官模拟系统,再辅以对现实世界的高保真还原,往往会使用户受到全方位的感官冲击,其所产生的“共情效果”会减弱用户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判断。如若特定利益集团有心利用VR媒介,以此左右用户态度,控制公众舆论,将更容易。由是观之,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对电视时代所做的“娱乐至死”的预言仍然适用于VR媒介大行其道的当下。
作为新兴“融媒”“浸媒”的典型代表,VR在各个层面和维度上相较于先前的传播媒介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但技术上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合法性。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提醒我们,“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虚幻”。?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学界对VR这一“热媒介”进行必要的“冷思考”的最好注解。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耀钟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Patrick Doyle, Mitch Gelman,Sam Gill, "Viewing the future? Virtual Reality in Journalism", Knight Foundation, March 2016, p. 3.
参见史安斌、张耀钟:《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新闻记者》,2016年01期,第34~41页。
Raney Aronson-Rath, James Milward,Taylor Owen, Fergus Pitt, Virtual Reality Journalism, https://www.gitbook.com/book/towcenter/virtual-reality-journalism/detail.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ritical ed, CorteMadera, CA: Gingko Press, 2003, p. 19.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court, Brace&Co, Inc,1922, pp.65-70.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3、179页。
史安斌、钱晶晶:《从“客观新闻学”到“对话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11年12期,第67~71页。
Cuddon, J. 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Fifth Editio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 Wiley-Blackwell, 2013.
O'Brien J., Buscher M., Rodden T., & Trevor, J., Red is behind you : The experience of presence in shared virtual environments, Presentation at the Workshop on Presence in Shared Virtual Environments, 20, 1998.
Grigore Burdea, Philippe Coiffet,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EBSCO Publishing (Firm), New Jersey: J.Wiley & Sons, c2003, p. 2.
"Why newsrooms should care about virtual reality", https://www.journalism.co.uk/news/why-newsrooms-should-care-about-virtual-reality/s2/a565739/.
N.De la Pena,P.Weil, J.Llobera, B.Spanlang, D.Friedman et al,"Immersive Journalism: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for the First-Person Experience of News", Presence: Teleoperators & Virtual Environments, 2010, no.4, pp.291-301.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2~20页。
The Pew's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of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The State of News Media 2012, Overview 2012, http://www.stateofthemedia.org/overview-2012/.
史安斌、杨轶:《硅谷与舰队街:化敌为友还是亦敌亦友?》,《青年记者》,2015年8月号,第45~47页。
"Are Consumers Ready For Virtual Reality?", https://www.globalwebindex.net/blog/are-consumers-ready-for-virtual-reality.
"Report: 2016 will be critical for growth of VR in journalism", http://www.niemanlab.org/2016/03/report-2016-will-be-critical-for-growth-of-vr-in-journalism/.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 544.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