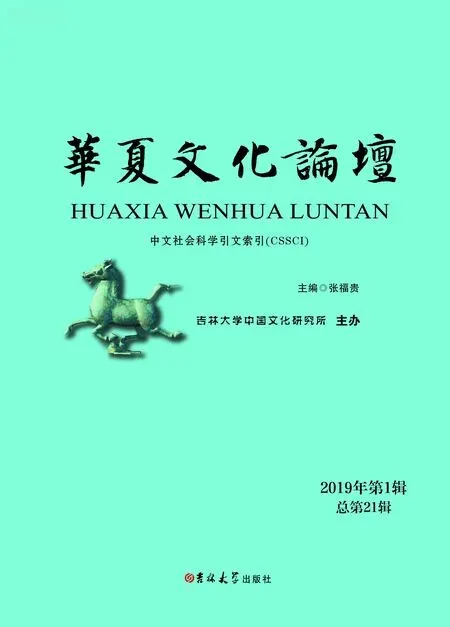苏诗唱和与物品交换
——一段关于“仇池石”的记忆
李光生
【内容提要】元祐八年(1093年),围绕苏轼“仇池石”的唱和活动,引出一段“以石易画”的故事。交易虽未果,然透露出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意识、艺术品消费与收藏的“物恋”情结、“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与哲理思考、人生出处情怀的寄托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前 言
唱和诗在苏诗中占有相当比重,学界多从诗艺角度论之,不乏卓见。然其作为文人间日常交流活动之重要方式而涉及物品交换的内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从程德孺处得到两块石头,赋《双石》诗云:“梦时良是觉时非,汲水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眼前的石头使苏轼的想象力纵横驰骋,时而把他带到太白山,时而把他带到峨眉山。诗歌最后两句聚焦于石头上的孔穴,在苏轼的想象中,双石变成了他神往已久的仇池山。也因此,苏轼把这两块石头命名为“仇池石”,迷恋之意溢于言表。翌年(1093年),苏轼返回京城,“仇池石”成为苏轼与钱勰、王钦臣、蒋之奇等友人在一段时间内唱和的主题之一。另一好友王诜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引出苏轼“以石易画”的构想。交易因王诜“难之”而未果,然围绕“仇池石”的唱和活动真实再现了宋代文人鲜活生动的生活图景。两块石头,何以引起苏轼等人如此巨大的兴趣?这其中承载了当时怎样的文化语境?“仇池”唱和传达出了宋代文人与石头(玩好之一种)之间怎样的关系?唱和本身具有怎样的文化意涵?下面就这些问题做些探讨,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仇池”唱和与“以石易画”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返回京城后,在与钱勰(字穆父)、王钦臣(字仲至)、蒋之奇(字颖叔)等友人的唱和活动中,“仇池石”成为主题之一。苏轼《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之二《见和仇池》一诗表明,先有三人对“仇池石”的唱诗,尔后苏轼和答。苏诗云:“记取和诗三益友,他年弭节过仇池”。完全可以想见,当时被誉为“元祐四友”的这几人对“仇池石”的赏玩与钟爱。钱氏诸人的唱诗其实是对苏轼《双石》诗的次韵和答。
“仇池石”因诗歌传播而为苏轼周围的文人圈所知晓(确切地说,诗歌传播只是“仇池石”被知晓的途径之一)。苏轼的老友王诜以诗相投,要求借观。王氏的索求引出了苏轼三首答复长诗中的第一首《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诗题夸大其词地把仇池石说成是“希代之宝”,这也暗示了苏轼与这两块石头之难舍难分,同时也为两个石头癖好者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搭好了舞台。诗人敏锐地察觉到,王诜醉翁之意不在借观,而在于“夺”。
苏轼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王诜(1051年—1114年至1117年之间),字晋卿,宋代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英宗驸马。苏、王二人过往甚密,相知颇深,王诜曾在乌台诗案前为苏轼通风报信而受到朝廷重罚。王诜热衷于诗文书画,是当时艺术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也是走火入魔乃至贪得无厌的古玩收藏家,常因有借无还而声名不佳。米芾《画史》对此颇多记载:“余(米芾)收易元吉逸色笔,作芦如真,上一鸜鹆活动。晋卿借去不归”“(轼)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王诜还曾借了米芾一块砚石未及时归还而毁了米芾与刘季孙的一桩交易。刘季孙收藏了大量书画,其中包括一卷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真迹。为得到这幅真迹,“(米芾)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王诜还常在别人的名贵书画上搞恶作剧,以逞作伪之才。米芾《跋快雪时晴帖》云:“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已乃翦去国老署及子美跋着于摹本,乃见还。”王诜借了米芾藏品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未经同意便擅自剪下原作的名人题跋及章署,合裱在模本后才还给米芾。王诜对艺术品的贪恋及真假参半的作伪行为在当时可谓“臭名远播”,人所共知。
对王诜的索求,苏轼自云“不敢不借”。这似乎是诗人对两人身份玩笑式的戏谑之辞,诗最后几句云:“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王诜贵族出身,驸马身份,自然是“风流贵公子”。这似乎暗示苏轼是弱势的一方,也注定苏轼最终不得不顺从王诜的请求。但与此同时,“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句,以“和氏璧”的故事暗示了弱者战胜强者的结局。“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这是苏轼提出的两个条件:第一是不得“传观”,第二是尽快归还。
苏轼与王诜围绕“仇池石”的争执,引来了第三方出面调停。这第三方便是钱穆父、王钦臣、蒋颖叔三人。尽管他们三人的诗歌现已亡佚不传,但他们的观点清晰地保留在苏轼第二首超长的诗题里:《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轼以谓晋卿岂可终闭不予者,若能以韩幹二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复次前韵》。苏轼第一首回复诗不久,所有的人似乎都达成了共识:王诜的“借观”实际上就是“夺”。苏轼似乎也占据了“得道多助”的制高点:“故人诗相戒,妙语予所伏。一篇独异论,三占从两卜”、“今朝安西守(蒋之奇),来听阳关曲,劝我留此峰,他日来不速”。同时,诗人再次表达了守护“仇池石”的决心:“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然如此的步步为营,却在诗题中早已透露出了“以石易画”的设想与准备:苏轼要用双石去换王诜收藏的韩幹的马画。
骏马画是苏轼那个时代的文人热衷的收藏品之一,尤其是那些出于8世纪画家如韦偃、曹霸、韩幹之手的作品。有一幅韩幹的马画,就在王诜手上。对于一位画家及痴迷成性的古玩收藏家而言,苏轼“以石易画”的交易构想无异于陷阱。当然,王诜的拒绝也在苏轼的意料之中。兴许,苏轼貌似合情合理的提议只是在以王诜之道还诸彼身,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果然,苏轼的交易构想被王诜所“难”无疾而终。此时,第三者再一次插足介入。钱穆父异想天开,要将石、画据为己有;蒋颖叔则走极端,建议焚画碎石。这些都体现在苏轼的第三首诗的诗题里:《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颍叔欲焚画碎石,乃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
二、宋代文人的生活本相
苏轼“以石易画”之提议因王诜“难之”而未果,然围绕“仇池石”的唱和活动真实再现了宋代文人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图景,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艺术品交换的“经济”意识
有宋一代,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商业活动日益活跃,社会出现了“贱稼穑,贵游食,皆欲货耒耜而买车舟,弃南亩而趣九市……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的重商风气。这深深影响着宋代士林,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他们普遍意识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北宋建国之初,在“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的厚禄养贤政策下,大部分士大夫犹以经商为耻,然时隔不久,皆以货殖是逐,“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从而形成“专业商贩为急务”的士林风习。
在此背景下,文人士大夫有着精打细算的“经济”意识当属情理之事。这种“经济”意识也渗透到了象征文人士大夫高雅生活情趣并俨成风尚的艺术品领域。在“仇池”唱和中,苏轼“以石易画”之提议虽存在着永久拥有仇池石策略上的嫌疑,然并不排斥出于诚心。虽然苏轼信誓旦旦地说要“完我无瑕玉”,且不会贪恋其他的“宝”,但其实已经做好了交易准备。他更切实际地给王诜还了个价,要用双石换取王诜收藏的韩幹的骏马画,这无疑是苏轼在艺术品交换中“经济”意识的流露。又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实则是对郭祥正谢诗的和答)告诉我们,苏轼为报好友郭祥正之热情好客而醉画竹石(或许苏轼本意并非如此,然竹石一旦画成,就起到了被回报的暗示与作用),郭祥正作了两首诗来答谢苏轼的绘画,苏、郭二人的你来我往事实上构成了一次交易。既然是交易,那么,彼此心中自然存有精打细算的“经济”意识,郭氏赠送的两把铜剑无疑平衡了这桩交易。郭、苏二人的唱和诗不仅记录和解释了物品的交换,还积极地参与到了这次交易过程之中。上文提及刘季孙和米芾的交易未能完成,原因仅在于米芾缺少了一块砚石的砝码。这同样也反映了刘季孙的“经济”意识。
宋代文人士夫进行艺术品交换的行为极为普遍。米芾《书史》载:“朱巨川《告颜书》,其孙灌园屡持入秀州崇徳邑中,不用为荫,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类《徐浩书》在邑人王衷处,亦巨川告也。刘泾得余颜告,背纸上有五分墨,至今装为秘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尔。王诜与余厚善,爱之笃。一日见语曰:‘固愿得之。'遂以韩马易去,马寻于刘泾处,换一石也。此书至今在王诜处。”这段文字提及了米芾以金梭换颜真卿书法真迹、王诜以韩幹马画换取了米芾收藏的一幅书法真迹、王诜以一块石头换取了刘泾的韩幹马画等交易。显然,在文化消费市场上,艺术品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的例子在宋代所在自有,甚至比比皆是。在艺术品交换中,固然不乏朋友之间“君子成人之美”的雅意,如王诜对米芾所藏书法真迹的迷恋,米芾给予成全。然即便如此,米芾在书法真迹与韩幹马画交换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意识依然清晰可见。
(二)艺术品消费与收藏的“物恋”情结
在仇池唱和中,苏轼视仇池石为“希代之宝”的略显夸张和机智护石,都表明苏轼对物的执迷。这份执迷也促使他不太恰当地把仇池石比喻为妻子。第二首诗前八句云:
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平生锦绣肠,早岁藜笕腹。纵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
诗歌提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其中一处用“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来描绘卓文君。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之后,处于“家徒四壁”的窘境之中。此处仇池石、山和“眉色如望远山”的美女这三个意象实则可以相互指代,因而产生一种暗喻性的类比:仇池石之于苏轼,如同卓文君之于司马相如。不过,苏轼把自己与仇池石的关系说成夫妻关系似乎并不恰当。在中国古代传统婚姻观念里,妻和妾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妾可以作为物品进行交换。早在西汉,刘安便有《爱妾换马》为题的乐府诗(不传),梁简文帝亦作《爱妾换马》一诗。至中唐以来,爱妾换马的故事非常流行。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裴度、白居易的诗歌唱和便导演过一出唐代版的爱妾换马故事。裴度看中了白居易的小妾青娥,欲以良马换之。裴度唱诗今只存一联附于白居易和诗前,存诗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白居易和诗《酬裴令公赠马相戏》云:“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按:白居易妾名)。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这次交易虽因白居易不舍而未果,然透露出妾作为物品可以交换的事实。张祜《爱妾换马》诗中如此写道:“一面妖桃千里蹄,娇姿骏骨价应齐。”马和姬妾被认为是功能相同的商品。同样,仇池石被女性化后,其化身更像是可以交换与转手的姬妾而非妻子。苏轼这个貌似有悖常识因而并不恰如其分的比喻实则表明苏轼对仇池石的迷恋之深。
苏轼恋石随性而投入,形诸文字,颇多趣事。其《怪石供》记述于元丰三年(1080年)在黄州发现江边多美石,“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清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苏轼恋石成痴,即便在被放逐中,亦不改本色。在谪迁惠州经过湖口时,在普通百姓李正臣家中看中一块怪石,形制宛转盘旋,如纳九华山于壶中。因南迁途中的种种不便,交易没能完成。当时苏轼能做的只是给石头取名为“壶中九华”,并为之题诗,以资纪念。题诗有云:“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苏轼念及仇池石“太孤绝”,想让“壶中九华”与之为偶,恋石之意溢于言表。
在宋人眼中,怪石是古玩艺术品之一。作为一部被誉为“鉴赏家之指南”的古玩艺术品鉴著作,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列古琴辨、古砚辨、古钟鼎彛辨、怪石辨、砚屏辨、笔格辨、水滴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石刻辨、古画辨等十类古玩,其中便有“怪石辨”。在宋代,像苏轼这样恋石的文人士大夫所在自有。仅从苏轼的诗文中,便可开出一长串恋石者的名单。据周裕锴先生统计,除上文提及的王诜、钱勰、蒋之奇、王钦臣、米芾、李正臣、郭祥正外,还有刘敞(字原父)、文同(字与可)、鲁有开(字元翰)、梅灏(字子明)、程之元(字德孺)等。这些朋友相互赠送欣赏并收藏怪石,相互唱和,形成了人文旨趣极浓的嗜好怪石的文艺圈,体现出宋人浓厚的“物恋”情结。上述“元祐四友”围绕“仇池”唱和所体现出来的对仇池石的赏玩与钟爱,王诜的“意在于夺”,钱穆父“欲兼取二物”,以八千金易得“壶中九华”的石头迷郭祥正,无不透露出这一点。米芾拜石饱含深情的癫狂,堪为宋代文人“物恋”之典型。《宋史》载:“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就仇池石而言,由于苏轼的称赞,价值倍增。在苏轼死后,仇池石为宫廷所藏。北宋王朝覆灭后,这两块仇池石和宫内收藏的其他奇石一起弃置沟渠。但很快就被赵师严取而藏之。仇池石新得其所,至少又引发了两首诗,押的是苏诗原韵。或许,连苏轼本人也不曾想到,仇池石虽然身为外物,却具有如此的神力:非但不为人所转,而且能让人为之所转。
(三)“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与哲理思考
文人恋石约始于中唐元和以后,李德裕和牛僧孺可谓开风气之先。李德裕于京师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蓧,树石幽奇”。牛僧孺在洛阳归仁里筑私第,“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牛氏酷爱怪石,初衷在于适意,然据白居易《太湖石记》载:“公于此物,独不谦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各刻于石之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独不谦让”一语及定石品级,透露出牛氏对怪石的迷恋之深及对适意初衷的背离。在这点上,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在“物恋”之余又往往能抱持一种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以达理性超脱之境。苏轼《宝绘堂记》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一件物品成为审美对象,不在于它本身的属性,而取决于人们的态度,即“寓意于物”抑或“留意于物”。“宝绘堂”乃王诜所筑,藏历代书法名画,王诜日夕观摩其间,苏轼作此记,对挚友“留意于物”不无规劝之意。
宋代文人恋石至深,却也能超然其外。在第三首仇池唱和诗中,苏轼从痴迷的当局者变成了清醒理性的旁观者。诗云:
春冰无真坚,露叶失故绿。鷃疑鹏万里,蚿笑夔一足。二豪争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镜既无台,净瓶何用蹙。盆山不可隠,画马无由牧。聊将置庭宇,何必弃沟渎。焚宝真爱宝,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贤,出语耆年伏。欲观转物妙,故以求马卜。维摩既复舍,天女还相逐。授之无尽灯,照此久幽谷。定心无一物,法乐胜五欲。三峨吾乡里,万马君部曲。卧云行归休,破贼见神速。
该诗结构较为复杂,其言说对象和言说主题具双重性,且叙述中不断穿梭于两个层面之间。当言说对象是王诜时,苏轼谈论的是仇池石和王诜马画的不济(“盆山不可隠,画马无由牧”),并以《庄子》中的典故反映小物之于大物的卑琐。如此贬损艺术品的价值,这对于作为文人画理论先驱和奇石鉴赏家的苏轼而言简直难以置信。但随着苏轼和王诜之间谈判的升级,苏轼不得不否定那些珍物的价值。而对钱穆父和蒋颖叔,苏轼解释了为何不必非要损毁或舍弃某件东西才能避免自己为物所役。“明镜既无台”用六祖慧能改神秀“心如明镜台”之偈的著名故事,说明对于一颗了悟之心而言,任何外在的实际依凭都不再需要,甚至都不用知道这些依凭的存在。不管石头或马如何“逼真”,它们和实物相比都微不足道。然苏轼刚阐明这个观点,却在下一句“净瓶何用蹙”用另一个禅宗公案予以质疑。在这个公案中,百丈、沩山和华林围绕净瓶进行机锋对答,故事的高潮是净瓶被踢倒。蒋颖叔为了标榜超然物外而采取“焚画碎石”的方式,与公案中“踢倒净瓶”一样极为幼稚,正所谓“焚宝真爱宝,碎玉未忘玉”。为占据哲理制高点,苏轼居然把曾在第二首诗中提出的交换建议重新解释为“转物妙”。“转物”之典源出《楞严经》里佛祖对阿难的布道:“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若能转物,则同如来。”“维摩既复舍,天女还相逐”句用了《维摩诘所说经》魔波旬试探维摩诘的典故。魔波旬将万二千天女交与维摩诘,维摩大士教授了她们佛法,魔波旬返回天宫时想要从维摩诘处把天女要回:
魔言:“居士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于彼者,是为菩萨。”维摩诘言:“我已舍矣!汝便将去,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
被维摩诘传授“无尽灯”后,天女们最终跟随魔波旬回了魔宫。她们身居无限幽冥之中,但心灵却保持“无上正等菩萨”。苏轼有意强调天女们仍归维摩诘所有,并未还给魔波旬。魔波旬讨要时,维摩诘说“我已舍矣”。这里的“舍”,是意念上一种不掺杂占有欲的占有状态。苏轼借此典故,意在表明,他之于那对引发了争夺的仇池石,正如维摩诘之于万二千天女,在将其送给王诜之前,已经在意念上舍掉了它们。“定心无一物”句是苏轼宣称自己达到一种理想境界的明确表达。
在苏轼看来,仇池石不过是盆景中的假山,韩幹所画之马亦非真马。在本真与模拟的对立之中,石、画都失去了价值。虽然,就佛家真义而言,即便是真山和真马也是虚幻的物象。苏轼在此诗中用了一连串佛经和高僧传里的典故,并通过对“无”这种否定性修辞的反复强调来表达心、物两分的重要性,因而具有了哲理批判的意味。苏轼的哲理批判对象并非石、画之假不如真,而是人“欲”之愚不可及。
(四)人生出处情怀的寄托
围绕仇池石的系列诗歌不仅清晰地呈现了北宋文人的“经济”意识、物恋情结、审美态度及哲理思考,事实上也寄托了苏轼本人的出处情怀。这种情怀在《双石》诗及其序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序云:“至扬州,获二石。……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序以元祐六年(1091年)知颍州时所做的一个奇怪的梦写起,梦中苏轼来到题名为“仇池”的官府,醒后则诵杜甫《秦州杂诗》“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之句。“小有天”在河南省王屋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府之一。杜甫将仇池山上的池穴设想为暗通仙境的途径。宋人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引王仲至语:“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石,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苏轼以杜诗来解释“仇池”之梦并以此为双石命名,显然带有浓厚的归隐避世的象征意味。在《双石》诗中,无论是太白还是峨眉,都是道教名山,是能使人得道成仙、躲避世俗之乱的洞天福地。然故乡既不可归,桃源也不可寻,仇池石便成为诗人日思夜梦的山林归隐的替代品,也是诗人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一种心理补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句,是自称为老人的苏轼退隐山林的明确表达。仇池山不再是具体的物象,而是苏轼心中的归隐之乡。这种归隐之思虽仅是一场“仇池”梦而已,却恰恰反映了苏轼大半生的政治浮沉与人生感喟。截至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经历了进士及第、制科高等的名震天下和任职翰林的无限荣光,也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黄州谪居的忧危惧祸,洛蜀党争后历任地方的流离漂泊,归隐还乡之念愈发渴望与强烈。“此生终安老,还轸天下半”之喟叹是苏轼半生宦海浮沉渴望归隐安顿的清晰流露。
苏轼在短暂的知颍州、扬州后,于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又被召回京城,参与郊祀大典,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其一生中最高的官位。在看似荣耀的背后,政敌依然不断地在弹劾他,使他不安于朝。事实上,此时元祐之政也已日薄西山,苏轼敏锐地觉察国事将变,政治风暴又将席卷其身。“仇池”唱和活动便发生在苏轼留在京城这差不多一年的光景中。如果说,《双石》诗中以“仇池”命名双石已明确透露出苏轼的避世之想,仇池石象征了苏轼归隐之梦的物质寄托;那么,仇池唱和中看似剑拔弩张却心澄如境的艺术品交换似可视为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对艺术的皈依,并由此达成在艺术之乡的心灵安顿。苏轼在第二首唱和诗中云:“吾今况衰病,义不忘樵牧。逝将仇池石,归溯岷山渎。”无论衰病,终不忘山林之念,且要带着仇池石同归故里。这既是仇池唱和赋予的文化意义,也是仇池石对苏轼——当然也包括在乌台诗案中义薄云天的挚友王诜——避世情怀的承载。
三、余论
唱和诗在宋代极为盛行,是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和交往的普遍方式,透露出宋人不俗的生活情趣和审美风尚。其所涉及的内容与功能极为复杂,所谓“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苏轼诸人围绕仇池石的唱和活动,把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内容升华到诗的境界,突显了以诗娱情的雅趣和诗歌的交际功能。这种文人间双向甚或多向的酬唱活动,使我们能够找寻到诗人间交相往来的线索,了解彼此因事触发的感受,真正做到知人论世。正如台湾学者梅家玲对唱和诗的精辟见解:“由于‘礼尚往来'的精神乃是赠答活动所以形成的重要基素,故透过诗作往复赠答,原就蕴含了深具社会性的‘人/我'互动。”围绕仇池石的这段记忆,通过对这种交往图式的体味,展现出了宋代文人的生活本相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文人间日趋普遍的艺术品交换反映出宋人日常生活的雅化,而交换中流露出的“经济”意识与宋代重商风气不无关联;艺术品交换作为文人间一种互动的文化消费活动,通过诗歌酬唱的形式得以呈现,与收藏风尚一起清晰地透露出宋代文人的物恋情结。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恋石成痴,却又能抱持“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与哲理思考而超然石外。围绕仇池石的系列诗歌,也寄托了苏轼本人的归隐之念与避世之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诡谲激烈的新旧党争中更接近生活本原的诗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