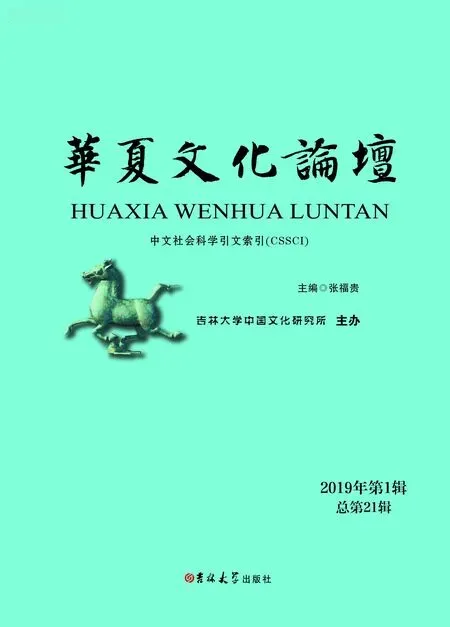明朝宫廷的耶稣会士
——文化适应策略与海外汉学的开端
福树人(Miguel Frías Hernández) 罗慧玲译
【内容提要】自从16世纪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以后,西方传教活动就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早期的耶稣会士通过实行“适应策略”,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结交儒家知识分子,并在系统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实地接触了中国社会,获得了关于这个东方大国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毫无疑问,利玛窦、谢务禄、卫匡国等传教士为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朝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欧洲早期的汉学研究殊途同源、密不可分。文化“适应策略”的初衷是基督教士们用以接近儒家精英学者的途径,但其客观结果却远超预期,耶稣会士们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为欧洲提供了有关中国的全面信息,内容涵盖地理、语言、政治、哲学、社会等各个方面,继而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巨大兴趣;同时,耶稣会士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合作与著述,也客观上促进了明朝科技的发展。可见,这些活动都给17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耶稣会士形成文化“适应策略”时, 大明朝仍处于繁荣开放、有创造力的时期,这也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和融合提供了宽松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曾德昭(Alvarez Semed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都试图通过儒家传统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结合来更好地解释基督教义。然而,这种趋势随着1644年明朝的灭亡而完全走向了衰落。
自耶稣会成立伊始,澳门便成为其修士们前往日本传教的中转地带;相比之下,前往中国内地宣教的计划却迟迟未有进展。但这种情况却在1577年得到了改变,当年东方教区视察员范礼安在到达澳门后,逐渐意识到需要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东方宣教的方式,应该采取一种适应策略,尽力寻找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这一观点是基于日本传教的经验,同时,他意识到,具体形式上也要根据天朝的情况而采取因地制宜的变通。在分析了耶稣会士们早期收集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后,范礼安意识到,如果不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策略,宣教活动将无路可走。因此,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以便更准确地传达基督教义,获得中国民众的接纳。
因此,1579年,在范礼安的指令下,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在一位中国儒生的帮助下开始刻苦学习中文。1582年起,罗明坚有了一位得力助手——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训练有素,是克拉维乌斯神父的弟子,受遣来到中国专职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他们的目标是用基督教的精神征服中国,并尽力进入北京的宫廷。罗明坚和利玛窦是第一批到达中国并持续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尤其是利玛窦,拥有“汉学之父”的美誉。他的造诣和影响甚至超过了1588年就回到了欧洲的罗明坚。利氏的出众之处在于,他不仅可以用汉语交流,而且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声望,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学习中文,不仅要做到能够用这门语言讲话,更要学会通过它来了解中国社会、倾听中国人的思想。”作为该时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葡汉词典》在一些中国基督教徒的帮助下编纂成功了。它成书于1582—1588年,是早期在华传教士们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不过,无论是在翻译活动中、还是在与中国文人最初的接触中,传教士们都很强调佛教在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由于先前在日本宣教的经验,天主教修士们在接近中国文化的初期选择了以佛教形象为工具,他们甚至着袈裟、剃发。
传教士们在不断地学习中国文化及语言。在与广州的官员们接触的过程中,罗明坚等发现,西方人接近和认识中国文化的意愿很快拉近了他们与中国官员的距离;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对西洋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种来自双方的兴趣恰恰有助于友好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得益于此,耶稣会士们于1583年得到了在中国内地肇庆居住的权利,并于1584年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会所。
鉴于中国传教形势的发展,澳门教区分设了两个教区:日本教区和中国教区。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出于推动在华传教事业发展的需要,范礼安于1588年派遣罗明坚前往罗马教廷向教皇申请设立梵蒂冈驻中国使馆,以便为传教士们在华期间提供保障和保护。但最终这一计划无果而终,且1589年,耶稣会士们从肇庆被驱逐至澳门。所幸在他们到达广东后获准居住,并于1590年建造了另一所会所。
几年来的经验使耶稣会士们对中国有了更深刻、更现实的理解,并清醒地认识到佛教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借助佛教靠近中国的方式并不可取。同时,耶稣会士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士大夫们的重要性,他们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构成了封建王朝的权力精英集团,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国的社会制度等级森严,权力集中。至此,如何了解和接近中国官吏,培养与中国知识分子们交往的能力,就成了在华耶稣会士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1594年11月,范礼安神父批准了这一在华传教的“适应策略”。至此,在华传教士们以“西士”或“西儒”的面貌出现,使用中国文人比较容易理解的“上帝”的概念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摒弃了曾经使用的僧侣的装扮,蓄发留须,并学习中国士大夫一般穿戴丝绸衣物。
1595年,利玛窦打扮成儒生的模样,意图前往北京宫廷。但到了南京后受阻,故被迫回到南昌。在此后的三年里,他继续向知识渊博的文人们学习,其儒家思想和文化知识突飞猛进。他先后用中文写作,在文化适应的策略上借助儒家思想,替代了1584年罗明坚的借用佛教思想的方式。利玛窦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里得到尊敬,1595年完成的汉语作品《西国记法》和《交友论》,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广泛赞誉。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利玛窦开始着手《天主实义》的撰写,行文中注重利用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解释基督教的理论和教义。《天主实义》无疑是一部集中反映了西方传教士们接近中国文化、进行早期汉学研究的大成之作。
作为中国教区负责人,利玛窦于1598年与郭居静一道,在南京礼部官员的帮助下前往北京,希望能够觐见大明皇帝。但恰逢明朝对朝鲜作战,因此“皇帝无心处理其他洋务”,故此行未果。随后,利氏回到了南京,并于1599年到达韶州,次年5月与耶稣会士庞迪我再次北上,最终于1601年1月到达了北京宫廷。通过宫廷内侍们进献了送给明朝皇帝的西洋礼物后,耶稣会传教士们得到了在京的居住权。此后的十年间,直到1610年去世,利玛窦都生活在北京。但事实上,耶稣会传教士们始终未能亲眼见到皇帝的“龙颜”。
在华期间,利玛窦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尊敬,这大大有利于巩固耶稣会在华的地位。徐光启、杨廷筠等中国知识分子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与耶稣会士们合作、帮助他们学习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儒生们同样比比皆是。因此,“适应策略”成为了早期在中国传教的成功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适应策略的采取,不仅仅是在宣传宗教教义,还扩展到了传统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范畴: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同时,为了引发兴趣,引起注意,利玛窦在著作中也加入了引人入胜的插图和名言警句等。正是这些精益求精的方式赢得了中国文人们的由衷敬佩。
利玛窦是“适应策略”的主要践行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也尤其值得称颂。1604年,利玛窦的作品《天主实义》问世,书中对西方哲学的理念和中国传统哲学观点进行了大量的引用和对比。此书得出的结论是,天主教和儒家思想的共同对立面是佛教或道教。通过研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德经》等其他流派哲学,利玛窦认为,基督教《圣经》的理念与中国儒家的早期思想最为接近,尽管明朝的知识分子的确对儒家思想已经有了新的解读。同时,目前流传的儒家思想,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和若干个世纪以来佛教的侵蚀,已与最初先贤们的思想相去甚远,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貌似”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很多方面是如出一辙的。在适应策略中,应该对中国的传统“礼仪”加以尊重,因为它恰恰是渗透到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在的因素。
通过与中国文人们的接触,利玛窦认识到,要达到宣传基督教义的目的,单纯的说教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在语言和知识层面制造共同点。继续着这条路线,利玛窦去世后,“适应策略”依然注重知识上的深刻交流,这也客观上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
在后期曾德昭和安文思等人的著述中可见,二位神父沿袭了利玛窦创立的交流方法。他们继续研究“四书”,对中国的社会教育和知识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也保持了接近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习惯。他们实际上代表了“适应策略”的不断进步,在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融合的前提下引入新的思想。
另外,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还对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的扩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卫匡国神父对中国的地理、历史都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成果传到欧洲,更加激起了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此前中国由于“天朝上国”“自给自足”的观念而对外封闭,而这些知识的传播则加强了双方之间的联系,同样在适应文化沟通的前提下,继而把传播福音的范围扩大到了东方世界。
综上所述,16世纪起,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耶稣会士在中国实施和发展的“适应策略”,它令神秘而遥远的东方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正是这种相互认知的需要和实践,推动了文化间的融合,也构成了早期西方汉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