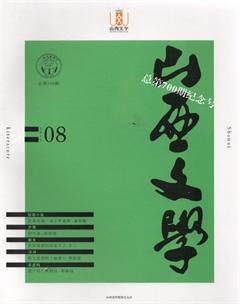散文:带着心灵热度和身体痛感的非虚构之作
谷禾
虽说也写过些长长短短的散文,但散文这门艺术之于我,仍然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文体。这里不单有从古以来灿若星辰的先贤名家,更有浩如烟海的佳作名篇。远的可追安天下之半部《论语》,900年前的一篇《岳阳楼记》,影响绵延至今,成就了一代代不同阶层人士“心忧天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也间接肯定了曹丕在《典论·论文》所言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岁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一个“无穷”,说尽了古今文章的玄妙。今人王充闾先生把自己对中国古典诗歌阅读的心得结集为《诗外文章》,我以为既是对散文这一中国特有的古老文体的回望,也是一种自然回归。在小说没有兴起之前,我们的先人除了分行的诗,但凡不分行的各种文字,落于字纸绢帛,大体都归入了文章的范畴。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是说文章是搭起事与心的桥梁。就中国古典散文来看,前至“诸子百家”、《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后到“桐城”“公安”,及流传广泛的《古文观止》等权威选本等,其丰富和包容令人惊叹,内里狭义的散文可说少之又少。从这一维度来看,今人所一直津津乐道的纯散文及其写作理念是否给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散文带上了无形的纸枷?
拉近了目光,我们还可以看到,新世纪伊始,在一时风生水起的“新散文”诸多篇章里,张锐锋、周晓枫、祝勇等人在打破散文“短小精悍”“形散神聚”等条框桎梏,引入更多小说叙事和诗性意象等表现手法之后,也鲜见进一步的开拓和创新,近年来更是趋于沉寂。换句话说,这早已不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也就不可能产生散文或者其他文体的革命性作品,如同汽车的创新,可以涉及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的电动化和自动化驾驶,四个轮子一直都是圆的却不曾改变过。各种“新散文”所追求大多是艺术表现手段的引进和尝试,参与者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在力图在纯文学范畴内把“散文”往“文章”的方向上拉一拉罢了。继之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无疑是对当下小说和散文写作文人化、精致化的反悖,也是对散文写作日益风月化和书斋化的无声抗议。它表明了读者对“读者体”鸡汤散文的兴味索然和部分散文作品缺少世道人心的深层关怀的失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散文这种文体过时了,是“扎根精神”的缺失,让我们的散文作家落伍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了。
古人讲“文以载道”,这个“道”,不该只是道理之道,更应该是道统之道,天下之道,是写作者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现实。我不反对写作者对文本价值和意义的求索,也不认为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人笔下的闲适就不是真实的个人生活,而是说散文源远流长的厚重传统积累已经表明,当代散文创作一样有能力去呈现时代和个人生命和精神的境遇。
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诗是对真理的热情追求。”我们的散文作家一样有义务走出书斋,走出故纸,去关注现实、思考现实,发出自己独特而真实的声音。我在这里反复强调的“真实”作为散文这种文体的本质和核心,既指向人物、事件、自然、社会、历史,也指向文本内的重要情节和细节以及作家的内心世界。但散文创作不是照相机的拍摄,不是照本宣科的还原和复印机式的对应,它带着作家鲜明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经过了作家心灵之光的照亮。是具备了文学审美功能的、文学意义上的艺术“真实”。它的边界又是无边无际的,是陆机所说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是最自由的,最显示作家个性和才华的现代文体。
基于对真实的个人认知,相对于当下过度专业化、文人化写作的散文写作,我更偏爱那种带着心灵热度和身体痛感的非虚构之作和田野调查式的行走之作。梁鸿在写作《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过程中,长时间的住回自己出生的村庄,挨家挨户地去走访,还无数次往返村里人不同的外出务工城市,去了解主人公们不同的生存状况,她在成文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学者自外而内和自内而外的思考,文本呈现的不仅是以梁庄为典型的中国乡村现实,更有它内部的清晰的脉络走向。雷平阳为了写作《乌蒙山记》系列散文,几乎走遍了乌蒙山的村村寨寨和山山水水,他的“乌蒙传奇”首先是活生生的乌蒙现实。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是他历尽沧桑的生命岁月的血泪记录,其字字句句都源于铭心刻骨的记忆,滚烫而疼痛。李娟为了写作《春牧场》《夏牧场》,坚持与母亲和羊群一起栉风沐雨地度过草原上每一个夜晚。从这些作家的文本中,读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作家在写作,而是一个与他们的关怀对象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在向你倾诉,与你交谈。与更多资深散文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字也许还不那么圆融,还略显匆忙和粗糙,但因为扎根于大地和众生的命运,带着作家的心灵体温,突然就有了活力、魅力和魔力,赢得了文学圈之外的众多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家也成了当下散文写作不可或缺的力量。从梁鸿、雷平阳、袁凌、黄灯、张承志、高尔泰、李修文、李娟等作家的非虚构和田野调查式的持续书写中,我清晰地看到了散文对时代和个体生命的深度介入和热情关怀。不管有多少人质疑他们书写的真实和虚构的模糊界限,我仍然認为,以真实为基础的现实重构(而非虚构),恰好呈现了散文走出美文藩篱,走向原野和大地深处的勃勃生机和无限可能性。
我所供职的《十月》杂志同事、青年批评家季亚娅在谈到自己对当下散文写作的看法时,表达了与我不同的关注。她这样说:“当代最富探索性的写作,可能在散文书写领域。我不是在美文或者抒情散文的意义上谈论散文,恰恰相反,关于散文的定见里所不能满足的阅读焦虑,在这些溢出文学、无法归类的文字中得到纾解。我希望找到最具创造性的激进文体,能越界,也能呈现不确定性的实验性文本,如果它们也提供一种叙事,那首先是一种现代博物体式的知识型叙事,学科领域的分界线被有意识地模糊,类似于知识生产的原初状态,美与智慧、词与物呈现一种元气茫茫的纠缠。它们所容纳的巨大的信息和情感含量,所提供的整合思想、叙事、行动的能力,以及或清晰或模糊的实践指向,为散文写作带来新的方法论思考。”也可以说,她对作为散文写作另一极的知识分子散文的向前走,也提供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这两极交汇起来的散文写作,近年来在《十月》这个平台上得到了立体的呈现和展示。这也是基于《十月》所一直秉承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代的发扬和拓展。
散文“怎么写”和“写什么”见仁见智,并且至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来。作为期刊同仁,我一直关注着业界资深人士的发声。《散文》主编汪惠仁提出了“有情趣、有情怀”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更多关涉作家个人素养和旨趣的主张,所指向更偏于“写什么”。作家穆涛则针对作者提出了“看清楚,想清楚、表达清楚”的三要素,看似简单,却对散文作家“怎么写”提出了极高要求。其难度在于要真正达到“看清楚、想清楚、表达清楚”的境界并不容易,甚至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
无论作为读者和文学编辑,我一直都在期待着散文对古典传统的回归和散文现代精神的张扬,在“文章”的大海里,散文理当焕然一新。
(作者:《十月》杂志事业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