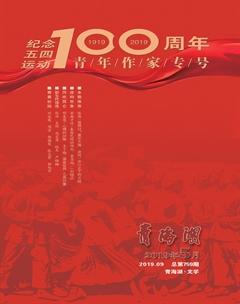故里(散文)
张立堃
宿一间老院,睡一席热炕,熬一壶茯茶,吃一块锅盔,听一阵风声。
这是我儿时在乡下姥姥家度过那几年最深的印象。
那时的天很蓝,在没有阴雨的夏天,抬头便可以看到树叶点缀中的丝毫没有被玷污的云从视野的这头慢慢飘到那头。时而飞过的鸟,不经意将视线拉远,再拉回。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和小哥哥一起爬到村子西边庄稼地后面的山上,还记得那时家里的大人总是说不能去那里,说山后的野狼专门吃不乖的小孩,可是年幼的我们好奇心总是胜过恐惧。从村子的这头走到村子的那头,穿过庄稼地的塄坎,蹚过河滩的泥洼,再爬上那座一直认为并不是高而陡的山,一直到山顶,坐下来看着这片被绿树拥抱着的村子。那时候我总喜欢在上山的时候从这块大石头跳到那块大石头,幻想着自己是最近看的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好不威风!乐此不疲地跳来跳去,哥哥总是笑着说我真是个跳腾小子。乱喊着,大笑着,看着脚下的村子和远处的河,看着对面东山山顶上的雪。
在乡下的夏天,最喜欢的是走在那条通往姥姥家的笔直得没有一点儿弯的水泥路上。那时候路的兩边除了刚进村的一片房屋,剩下的都是油油的没有一点儿掺杂的麦地,当然,最靠近路两旁的是那两行笔直、望不见树梢的大白杨,也当然,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最爱的。不知道从几岁开始,每年夏天我都喜欢从家走去姥姥家,一路上最喜欢的也是这条被白杨抱住的路。走到这里,便会听到白杨树叶在风的伴奏下低声唱着歌,虽然声音不大但能听清它唱的是支属于故乡的歌曲,是“花儿”里夹杂着方言的欢乐颂,唱给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走得有多急,走得有多慢,是开车飞驰而过,还是坐着轮椅缓缓而行,你总能听到心里,不由得想听清它唱的每一句歌词。在这二十年里我时常因为看到、听到或者想到它们而笑过,却也正如现在一样得知它们因为修路而被砍倒后含着泪水抽泣。可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在梦里走到那条路上,乘着风和歌慢慢地飞起来。
在这片如梦一般的村子里,最不缺少的便是美味了。不管是小哥哥到现在依旧心心念念的姥姥做的素炒洋芋和每年中秋蒸的大月饼,还是秋天大果园里的软梨和大姨烧的青稞,都是尝过海味珍馐后依旧放不下的“素食”。记得那时每年暮春最开心的是去离姥姥家不远的大姨家吃桑葚,这个活动从每年第一颗桑葚泛红到全树的果子掉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每次只要去了姥姥家,下一站便是大姨家,从下刘屯的杏树再爬上上刘屯的桑葚树。七八岁时矮小的我总爱和大我几岁的外家哥哥比赛,谁先爬上树顶谁就是美猴王。那时候我俩总是不分你我,最后一起靠在树干上吃着染红了嘴和小手的桑葚,看着大姨家的屋顶,看着墙后面的小麦地。这几年的假期,偶尔也会去摘几颗桑葚吃,看着有近十米高的树,佩服那时我和哥哥的胆量,只是很久再没见过他。最近的一次,也是几年前姐姐结婚时的酒席上,却也因为生疏没搭几句话就离别了。
从小到大一直没觉得故乡的冬天很冷,却记得姥爷去世的那天晚上,风是那么的凶,空气是那么的沉,就算穿上妈妈织的羊毛毛衣再套上一件大棉袄,鸡皮疙瘩却依旧像听到号角一样整齐地排列在我的皮肤上。那一晚的后半夜,我是吊在炕沿边睡着的,却睡得很死、很踏实。因为那一晚是姥爷最后一次陪我睡在他睡了一辈子的炕上。过了那晚,这炕上再也不会有他的体温;过了那晚,他再也不会因为腰疼叫醒不厌烦的我给他揉背;过了那晚,再也不会有人在我睡醒的时候捏一把酥油糌粑喂到我嘴里;过了那晚,盛夏的会场上,再也不会有一个小伙推着快要翻的轮椅载着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串走在拥挤的巷道里。
姥爷的葬礼上,我没有流下一滴泪。
故乡的记忆里有一个不怎么知名的村子,那是抚养我长大的地方。我把它叫做故里。那里有许多关于生和死的故事;那里有一本记录一群幼稚小孩从成长到衰老的语文书;那里有一所早已变成停车场和集市的小学;那里,是我这一生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