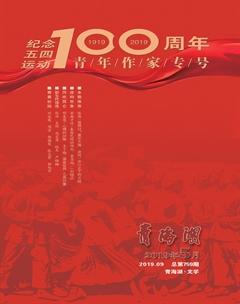在成长中带着擦伤穿过绝境(评论)
马钧
作为新千年我省崭露头角的短篇小说作者,张强(笔名央北)一直保持着稳健上升的创作力。如果省心省力地按照职业去划分,他可以顺溜地划归到石油作家这个当今文学界视为落伍、僻远、狭小、边缘的创作类别里。尽管这种老式的划分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出他在某些小说题材上的职业表达偏向——表现石油工人的生活,但它也大大局限了我们对这位80后(几乎临近90后)小说作者在虚构世界中左冲右突的创作潜力的全面考量,甚至障蔽掉他逐渐拓展着的叙事疆域。
事实上,他一直在磨刀霍霍地营造着自己的虚构天地。在我集中阅读他初具规模的短篇小说之前,坊间已经出版有他的几部传记体文字,比如《那一世,我遇见了你:仓央嘉措的今生今世》《杨绛传》《当爱已成往事:徐志摩诗传》。我还在一次他在西宁参加培训学习期间的短暂聊天中,得知他下一步的一个写作计划就是写作一部《玄奘传》。仅从他驾驭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不同人物的创作题材时的写作自由度和随性调整创作视野的开合度上,我已经嗅出他作为新生代小说作者不同于传统作家的地方。他们在写作上特能“东吃西嗅”,越界跨疆。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已经不完全是一个拘囿于轻车熟路的经验型书写者,他们相对瘠薄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尚不足以去支撑起气派恢宏的虚构殿堂,他们便采取轻轻雀跃于半空的写作法术,巧妙利用海量的各种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与自己一鳞半爪的身经目验进行榫卯和“混搭”。酷似于江南局促之地的园林营造法式,他们频频以“借景”来扩大他们虚构的格局。传统作家习惯于书写自己所腻熟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生活,而央北这一代文学新人,已不那么执着地谨守于窝边的那一丛青草,他们更乐于去“远取诸物”,尝试开辟新的领域,或者说他们更乐于神游于经验藩篱之外的各种领域,哪怕那是一片他们极不熟悉的世界,他们仍旧会带着巨大的创作激情去一试身手,哪怕是在异陌之地留下趔趔趄趄的身影。他们的知识结构、想象途径、创作的兴奋点,已然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作家。藉由这么一些资禀和异质,他们必将把一些崭新的元素注入到叙事文本当中。
之前我仅读到他的短篇小说《黑夜之光》,仅凭这一单篇孤例,我那残留的“学院派概括癖病毒”小有发作。我曾在一篇关于青海当代文学短篇小说的微型报告里,率意地把我看到的短篇小说类型,分为农村叙事、草原叙事类型,把《黑夜之光》“分拣”到一种跨界的混合类型里,鄙意以为:《黑夜之光》属于“荒原叙事”类型里蘖生的一个新类型——“荒原叙事”与“工业叙事”的嫁接。小说描写的是地处荒原的石油小镇和钻井工人孤独、寂寞的精神世界和充满疼痛感的情欲世界。在这里,“千里荒原被金色的光芒覆盖,高耸的井塔如一根根银针扎在这片荒原的血肉里”。作者所赋予小说主人公的那种既孤独又略含诗意的“空旷感”,在当代小说中已属于极为罕见的文学书写,小说中有一段令人过目入心的描述——
我跟季年的通话常常伴随着风声,那些风声嘈杂而凶猛,以致我们任何私密的话都不能说,因为听不见只能大声吼,而这座山头上打电话的男人不止我一个。
以前的时候我喜欢看荒原上的日落,那种不可逆转的宏伟感才能摧毁这片荒原的寂寥。可后来我给季年打电话的时候常常顾不得看日落了,挂掉电话一抬头就是满天星辰。荒原上除了井队上的那一点光外,再也没有光亮,星星因此格外闪亮。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舞台上,这群荒原小镇上的石油人演绎着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向往、他们的苦闷、他们的猜忌、他们内心的坚韧,还有世人难以抵达的那种荒原世界里的尖锐的疼痛感和浩茫的忧郁。在当代小说的形象画廊中,工人形象的日渐缺失和暗淡已成为当代小说创作里的一种气候和潜势力,央北的“荒原叙事”加“工业叙事”,无疑为当代小说雕塑了被遗忘的存在和一群几乎成为我们认识盲区的存在者。
时间仅仅跨过了短暂的几年,待央北把他即将付梓的短篇小说集《愿长夜可被慰藉》的电子版发到我的邮箱里,8个短篇组成的叙事版图已不复是当年《黑夜之光》所能覆盖的地盘。要想让鞋子合脚,不能再去采取削足适履的思维自残,而只能本分地去寻找合脚的鞋子。与传统作家容易钙化自己的经验、巩固自己的创作根据地相比,央北们更愿意去建立尽可能多的虚拟据点,更愿意去旁逸斜出,超越既有的创作领地。8个短篇中,除了《黑夜之光》,还有延续“荒原叙事”加“工业叙事”的新作,比如《荒原狼》。即便是《荒原狼》,也已经衍化为此种类型的叙事亚种。其更多的篇什已经“移步换景”,别开生面。我仔细寻味了一番之后,觉得可以换用“成长小说”这一更为匹配的批评框架来观察央北的短篇小说。
依据背景资料,我们知道成长小说起始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认为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始模型。成长小说进入当代中国之后,经过意识形态改造,结出本土化的果实。中国的成长小说与西方的成长小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成长小说主要是叙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他们的各种遭遇和经历,并通过巨大的精神危机长大成人的故事。而中国式的成长小说,主体积极的完型几乎未见,而逆反式的与被动式的成长叙事则显得过剩,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成长小说,常常表现为主人公成长的晚熟。及至当前的一些成长小说,摆脱了对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的依傍,而转入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对成长的磨蚀与改写。叙写“成长中”状态或“成长的破碎”状态的作品呈趋热态势。央北的小说,作为主体的叙述角色,几乎都聚焦于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身上。他们这些人中较为成熟的一些人,在故事中都扮演着对其他晚熟人物进行生活启蒙和人生向导的角色。比如《黑夜之光》中工友黑子与陪酒女辛霜之于井下工人张白穆,《荒原狼》中社会上的“混混”灰哥之于工人张鸣一,《和光同尘》的林智夏、顾远竹之于“傻丫头”李小冬,《最后的时间》中酗酒后杀了母亲的父亲顾海之于儿子顾生林,《装甲车》中的大哥李向阳之于他的三个哥们张辽北、陆宇远、宋多米,《在山不远》中李鸣鹊之于陆六,都程度不同地成为后者人生觉醒的启幕者,或者是后者人生阅历中突然打开另一面世界的人物。正是这些“启蒙人物”,或者促成被啟蒙者自天真无知至成熟的历练过程,或者引领他们进入社会吃亏吃苦,逐渐明白世途的艰难和人心的险恶,或者引领他们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他们的人生轨迹有所改变。
进一步来探讨央北的“成长小说”,我想援引作家阿城的一个说法:“不管你是古人也好,你是现在的人也好,你是未来的人也好,都会有绝境,有过不去的槛。所以我说好的作品常常是穿越这个绝境的。”我以为,这个说法可以给“成长小说”这个已初现骨质疏松端倪的概念,补充到丰肌强骨的“钙添力”。成长的最大关节点,乃是遇到“过不去的槛”,就是吃堑,就是开眼,就是见世面,就是对人生的诸般禁忌来一次次的脱敏体验。
央北的短篇小说里,设置了各式各样的“成长绝境”。
绝境之一:原本属于“荒原叙事”加“工业叙事”这一混合类型的,基本上都是描写坐落于荒原上的石油小镇——“西镇”人的生活的,他们遇到的巨大绝境就是荒原工厂生活难以消受的寂寞与无聊。因为这个绝境,老一辈石油人采取了一种燃烧式的奉献与牺牲。而小说里的年轻一代,恰恰被这个绝境导演出“一夜情”、离婚、酗酒、赌博、逃离、情感背叛等一件件事涉命运变化的事情。同时,年轻一代也借着情感背叛、逃离、赌博、酗酒、离婚、“一夜情”等方式,抵抗着他们难以排遣的无聊和寂寞。这个荒原的可怕,正像《黑夜之光》里的一句描述:“我脸贴着车窗,荒漠的黑夜像砖块一样,一块一块扎实地垒起来,这一下连过去也看不见了。”
绝境之二:年轻一代的选择自由仍旧被他们的父辈们所操控,继而埋下两代人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甚至仇隙。比如《黑夜之光》中的张白穆是被父亲强硬的态度逼回西镇的,他的相亲和提亲也都是老妈一手安排操办的;《云光》里的白乔婚姻失败是婆婆阻拦的——“她和他领了结婚证,然而在新婚不到半年的时候,遭到了婆婆的阻拦,阻拦的理由是嫌弃白乔的性格太风风火火不适合过日子。”《荒原狼》中的张鸣一是被父亲弄回石油局当采油工的;《在山不远》中的陆六所有的厄运都来自于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引人嘲谑的名字;《最后的时间》里主人公“渴望去当一名职业吉他手。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顾生林真正顾忌的不是父亲的反对而是顾生夏是否反对”。
绝境之三:婚外恋。比如《云光》里的白乔与何生之恋,《黑夜之光》里张白穆和辛霜之恋,《在山不远》里的陆六与李鸣鹊之恋。小说里的婚外恋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打破他们既有的组合而转向新的组合,而是爱过、痛过之后走向分离,走向诀别。
绝境之四:重大变故。正如《和光同尘》里作者借林智夏之口所道出的“绝境哲学”或“成长哲学”:“真正让人成长的不是时间而是事件,比如失恋,比如亲人的逝去,再比如事业的挫败。这是林智夏领悟到的道理。”如此,央北试验了诸多人生的变故形式。比如《云光》里的何生结婚后,“经济负担、女儿的病,让他没有时间再拿起吉他了。”“女儿诞生后就是肌无力患者,何生把这个错归咎于兰荣,从而丧失了爱意”,导致其最終的移情别恋;《荒原狼》中的张鸣一因为父亲烧伤毁容,逃离单位,逃离让他痛苦的家庭,在社会上赌牌失踪,最后又因父亲为营救他而偿还赌债,而自断手指;《和光同尘》中,少不更事的李小冬一是经历了爷爷去世的重大打击,二是经历了与顾远竹由一厢情愿到失恋失踪再到经历一场火灾;《最后的时间》中顾生林遭遇了骨癌和母亲被父亲因醉酒而杀害的双重极端经历;《装甲车》中的大哥李向阳经历了由截肢到自杀的绝境,而他们四人组成的哥们团队,经历了经商受到欺骗设局,大哥截肢后大家共同赡养接济的历程;《在山不远》里的李鸣鹊离婚和发生婚外情的祸端是她被医院查出双侧输卵管堵塞。
面对这些绝境,央北的小说反复强化着一个潜在的价值指向,那就是选择面对,缓释抚慰的温情,哪怕许多时候好像是在被动地躲避,逃离,出外散心,但隐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一种自我拯救的激情还是涌动在字里行间,一种人性的力量和尊严在小说文本的段落和情节中扩大着它们不可轻视的音量。这使他常常在小说的结尾,不惮于被人诟病地“拖出光明的尾巴”——
她开车前往何生家,当时是阴天,大片的乌云笼罩着天空,一缕耀眼的阳光从厚重乌云的罅隙投射下来,那个方向正好是何生家。
——《云光》
那一刻眼前汹涌的火势,李小冬并不觉得灼热。她反而觉得这像曾经看见的一片火烧云,而这夜除了这片云之外,再无黑暗。
——《和光同尘》
我个人十分喜欢他的《装甲车》,篇名与我们的阅读期待所造成的巨大反差无疑是本篇的一个亮点,但其在反抗绝境后所重铸的生命尊严,更是让我见识到央北精神世界中可贵的精神钙质,这一点尤其在他们新生代作者身上显得弥足珍贵。“他(李向阳)自己在极短的时间里,做了截肢的决定。只是以后得靠人工激素进行维持了。”“即便是腿断了,他仍旧在维护在我们中的尊严,像一个将军一样,站在猎猎风中,冲我们挥手,帮助我们实现那些微小的梦想。”“李向阳死得倔强而又残忍……”“装甲车上坏掉了轮胎,可是也要一马平川地向前走啊。”
在《最后的时间》里,兄妹原本怀着复仇之火意欲将来有一天杀掉曾经杀害了母亲的父亲,故事的结局,却走向了宽容与原谅:“顾海和顾生夏两个人各自站在顾生林病床的两边,顾生林两只手拍了拍床,示意他们都坐下来。他伸出两只手,分别抓住了顾海和顾生夏的手,他用尽全身力气把两只手放在自己胸前,顾海的手放在顾生夏手上,顾生林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盖住他们的手,他说了句,好了。这句话并没有声音,只是做出了嘴型。”这样的处理,显示出作者在人性思考上已具备了可喜的深度和温度。
央北小说在男女情爱世界的书写上,确实已经显露出与传统作家在情爱观上不一样的表达。这种表达,一是时代使然,更是其所描写的荒原地带人们情感存在的一种真实样态,它们作为一种新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存在,已经很难再被旧有的道德利刃所戗割和评判,而只能以一种人性的观照所宽宥和通融。就拿《黑夜之光》中的若干片段来管窥——“最近的一场酒宴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女伴离了婚,她说起这事的时候无惊无喜,就像是揉掉一颗隔夜的眼屎般容易”“婚姻在这里不过就是履行程序般,走一遍就好”“这里的一夜情就是每天食堂里倒掉的剩饭,吃过了就倒掉,不会再端上饭桌”。这种新的现实书写,昭示了作者直面人生的坦诚、敏锐和勇气,也隐含着这一代作者们的忧怀,爱的战栗与遗忘,对爱之崇高价值的崩解的无奈与感伤。
我特别注意到《愿长夜可被慰藉》的电子版的排版设计里,每一篇名的白底白字都被打在漆黑的页码上,像是荒原的幽暗与闪光。“黑夜”作为时间的一种形式,被央北布景似的安置在每一篇小说人物命运和生活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因而夜晚在他的小说中具有了物理时间和心理情境这两种叙事功能。这让我想起以拍摄夜景闻名于世的法国摄影家布拉塞说过的一段话:“夜晚将事物隐约地暗示出来,却从不清晰地展现它们。夜晚的怪异之处使我们感到惊奇和不安。它将我们体内那些白天被理智所控制的力量释放出来。”在央北全部的小说里,小说中的人物在夜晚展开他们欲望的另一面,也是“夜生活彻彻底底”让他笔下的人物“了解到这个活生生的戈壁”,释放出他们蛰伏的野性欲望。
与夜晚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是,央北在全部的小说里,都会在人物遇到“绝境”、遇到“过不去的槛”、遇到重大人生变故的时候,总要植入各种各样的“梦境”。这些纷杂凌乱的梦境,要么作为隐喻在暗示着人物的某种纠结、可怕的处境,要么它们就像一段闪回的记忆复制着往昔的瞬间,要么在表达着人物潜在的欲望和向往。这些梦境的穿插,使其小说形成了一定的心理维度。但总体上看,央北的梦境设计有时候显得草率,还不那么与整部小说的意蕴形成精巧无比的关联和映照,有些情节就像设置了“快进播放器”,文脉走得过快,失却了草蛇灰线般的缜密和叙事的内在张力。有些叙事破绽,暴露出央北的叙事底气尚有待充实。
央北属蛇,其前辈作家里,至少与他同一属相的格非,早年间被胡河清视为“蛇精”,富含诡秘、诡谲的寓意。大概是央北生于西北之地,生于荒原戈壁之城,我在其文字里倒没有尝出多少诡谲的味道,但能嚼出北人的倔劲和北人式的灵气。只是这灵气最害怕满世界弥散的躁气。我能体谅如今在繁琐工作之余烹文煮字的业余作者的艰难与不易;要在身心疲惫之余,在种种娱乐刺激的干扰与强劲诱惑之下,忙中偷出一小片一小片文字的光芒,这种事情,真难!唯其艰难、不易,意欲有成,非得从善始把自己一錾子一錾子,又稳又准地敲进善终里。否则前功尽弃。
我们都不具备西西弗斯反复推石上山的耐性和意志,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去趋近完美地敲打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