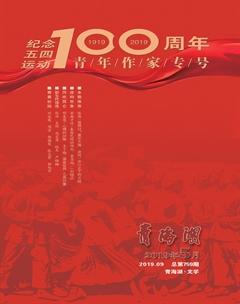秦格巴特的阳光(短篇小说)
索南才让
1
尼玛说:“明天上午9点上蓄水池,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大家都去么?”秦格巴特握住尼玛的手,让他进屋喝茶。
“都去?只有我们四个。但再不去羊就要渴死了。”
“水利局怎么回事?”
“不知道,他们在忙着填窟窿吧。”尼玛说,“不了,不进屋了,我还有事。明早我来接你。”
“需要带铁锹吗?”
“我看用不着。”尼玛把围巾拉到脸上,拧转摩托车头。他留下一股怪味乌烟和尘土,拐上混凝土路,加足油门,飞驰而去。秦格巴特抖了抖裤子,重新去仓房。他正在拌料。将玉米和麦子、麻渣以及酵母粉、盐混拌均匀。这是喂牛的饲料,牛吃得比谁都多,他现在后悔了。为了省点钱他没有买成品饲料,而是分开来买,这样确实省了点钱,但花费的力气和时间太多了,他都没有时间去干别的需要干的事情。他还没修理羊舍的采光板。因为被风刮动了一年,现在张开着一条巨大的缝隙,他得把所有板子拆卸下来,再推上去,与木头梁衔接好。要是他一个人干,那得好几天时间。但他只想一个人干。还有两个羊圈里的粪便也没清理,如果不清理,就浇上水,让羊群在上面踩踏结实了,再用铲子挖取成一块块石头一样的羊轧。可以用来取暖做饭,差不多跟煤一样耐烧而且还环保,却不用像煤一样花钱。他觉得还是不要花钱的好。他没有多少钱,能省当然要省,自己辛苦不要紧,辛苦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劳动就不会生病,很多很多病都是闲出来的。他只要小心不要受伤就好。他现在饭量大增,比以前多吃一倍,就是做饭是一件麻烦事。老婆不在家,吃饭真麻烦。除此之外,他过得一点儿也不困难。他的生活其实挺舒心的,只要他不逼自己去乱七八糟地想。他发现生活一下子简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为除了干一些零零碎碎的活计、照顾牧场上的牲畜,他一下子拥有了很多空间和时间可以用来挥霍。而且他觉得即使在干活的时候,这些空间和时间也没有被占用。他越干活,整个人就越轻盈。他打心底里喜欢上了这种生活。以前他没想过会是這个样子,现在却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按照他一贯的做派,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将拌好的饲料堆在仓房角落,另一个角落是自来水管,有一米五乘以一米五的小火炕包裹着,冬天和早春时节要煨炕以保水管不冻掉。但现在,已经两天没水了。查找原因,蓄水池里的水位很高很正常。所以明天大家伙儿要干的活儿就是找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他的羊已经两天没喝水了,马和牛也是。它们快渴死了。赖在门前的冰面上不走,一点一点地啃冰解渴。他想过赶着牛羊去公共水房饮水,但距离最近的一个水房也在10公里以外,去饮水不现实。马倒是可以去,要是明天再不来水,他就必须连牛也一块儿赶过去,虽然需要花上整整一天时间但没办法,要是水不来他必须这么做。那个当初提出拆掉他们这里的水房的家伙真是一个脑残,但大家伙儿都傻掉了?为什么要拆掉水房?难道大家都觉得一旦家里埋进自来水管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看来确实都是这般幻想的。但事实是自从埋进自来水管,一到冬天和春天,吃水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心头的大病。水管里总是没有水,总是没有水。等水来了,而且越来越充沛的时候,畜群们已经到夏牧场去了,到秋牧场去了。所以每年夏秋不需要它水管里有水的时候,就是水管里水压最大的时候,简直把人气死。
秦格巴特灰头土脸地离开仓房,忘了关门,等意识到这点跑去看,下午5点便因为口渴而早早跑回家的羊群塞满了整个仓房,将饲料糟蹋得一塌糊涂。他拳打脚踢将它们逐赶出去,还弄伤了手指,为此气得一晚上没睡好。
2
第二天秦格巴特和太阳一同起来了。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无论四季中太阳升起怎么变动,他总是和太阳一起开始一天的生活。他的卧室里的床在窗边,而窗户是朝东方的,他不用窗帘,所以每天的太阳露出脸的第一时间他就会被光线刺醒,然后起来。从来不变。
他用结有一层冰碴子的水洗脸,然后把水倒进拖地的塑料桶里。节约用水的习惯早已深嵌行动之中,不用刻意留心。他看手机时间,是7点40分。风不小,很冷。这个季节的惯用伎俩,再过两小时,太阳升高一些,风会停下来,像执勤一个晚上的巡警一样去睡觉,等太阳落山后再出来。他热了剩饭:粥和半盆土豆丝。粥是昨晚为了兼顾早饭煮的,今天要吃饱,中午肯定回不来,没地儿吃饭喝热水去,所以还要带上水。他正好有一个很漂亮的保温杯派上用场。吃饭的时候他还在哼着调子。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老婆孩子在的时候他基本上不怎么说话,有一句是一句,磕磕巴巴的,一天下来放的屁都比话多。不聊天不幽默,只要没必要,他一个字也不愿意施舍出去。有那么一段时期他甚至厌恶透了说话,浑身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合起伙来反抗说话,仿佛说话成了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但现在,当他独处,他倒闭不上嘴了,要么哼唧哼唧,要么自言自语,总之嘴巴特别愿意动弹着、吧唧着。他都觉得脸红,怎么这么犯贱呢。
他站在羊圈门口,是惩罚它们,在不给吃草还是把没有水喝当做惩罚之间纠结,最后心一软,打开圈门放出去。刚刚赶进草场,尼玛来了。他说你怎么一脸青色?你是纵欲过度。他觉得占了一个便宜,一个劲地傻笑。
“你也有自己遭罪的一天。”秦格巴特说,“而且很快就会到来。”
“秦格巴特,你这是在咒我啊。”他说。他将摩托车支好,低头一个劲儿地瞧擦得锃亮的皮鞋。这肯定是尼玛最最最舒适合脚的一双鞋子,因为一双鞋穿的时间久了,会和脚产生默契,那时候就是最好的鞋。可惜大部分鞋都到不了那个时候。尼玛自己看得满意了,这才抬起头来,“你干吗咒我,我老婆能跑哪儿去?”
“你笑话别人,殊不知同样也有人在嘲笑你。”他说。
“我才不在乎,只要不是当面嘲笑我。”尼玛满不在乎地说,“而且,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可不是真的嘲笑你,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秦格巴特说。
“好好。你准备好了没?”
“好了。”
“那走吧。”
“等我拿东西。”秦格巴特说。他拿了包和铁锹,骑到摩托车后座上。迎面而来的劲风提醒他今天保不准是一个极为恶劣的天气。阳光虽然白晃晃地照射,但作用不大,他躲在尼玛后面不出头。
他们之前已经有人到了,站在高高隆起的蓄水池边上指手画脚,仿佛在搞一场演出。更登开来了微型小货车,带来了加汽油的手拉式发电机和抽水泵。
“这些都是借来的,要是弄坏了我们都要赔。”他说。
“我们谁也不动它,你整。”尼玛说。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
“你一定行,你不行我们没人行。”
他们将发电机抬下车安顿好,把水泵扔进蓄水池里。发电机只拉了一下就响了起来,撒豆子一样的声音一下子让秦格巴特联想到那些年在这种声音的陪伴下在帐篷录像厅里看电影的往事。他看了那么多电影,几乎每部电影都看过三遍以上,除了寥寥几部,其他的都是垃圾电影,但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自己那几年几乎看完了所有已经有了的香港电影。为什么是香港电影,而不是好莱坞电影,或者内地的电影?这两者他不记得看过什么。在一个人最有活力的15至20岁这五年,电影是他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同水分一样滋养着他。他宁愿一夜接一夜地不睡觉也要骑马走两个小时去追逐流动的帐篷录像厅看电影。而且这样做的人并非他一个,很多像他一样大的小伙子都这么干。像现在的这几个,都是那时候录像厅里的常客。但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年的观影岁月并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一点痕迹。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看过很多电影的痕迹。仿佛看电影仅仅是看电影,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秦格觉得他们和他的差异太大了。自从意识到这点以后,他和他们再也不是一路人了。他是孤独的。孤独得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走神这会儿,抽水泵已经工作起来了。抽出来的水在草地上乱淌。蓄水池里的水位很高。
“这得抽到什么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来了就开始抽水,但为什么要抽水呢?“问题在里面?”他问更登。
“八九不离十。等我们的通水管一出来就知道了。”
“我估计是有什么东西堵住管口了,你说呢?”
金乾朝来路张望,“我看今天就我们几个人了。看来只有我们几个需要吃水。”
“我们四个是积极分子。”尼玛缩着小身板说。
“太阳只晒我们。”
“什么?”更登看着他。
秦格巴特只好解释,“我说太阳只会晒黑我们这样的勤快人,因为我们在太阳底下。”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他大为赞同,重复道,“太阳只晒我们。”
“太阳只爱我们。”秦格巴特故意说。他知道更登说不出口这样的话。更登有很多很多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只要稍微有点难以启齿他就说这话太肉麻了。“我可说不出口,简直会羞死我。”
“太阳只爱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勤劳而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在干吗?”
尽管抽出来的水越来越多,蓄水池里的水位下降得却很缓慢。秦格巴特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出水管在哪个位置。
“我也不知道。更登你知道。”尼玛说。
“在第十三个梯子那里。”
秦格巴特数梯子,第七个梯子正和水位持平,还有六个梯子的水位呢。他估算着怎么也要一个小时。
3
拉毛来的时候他们蹲在背风的地方抽烟。秦格巴特在思考晚上吃什么。一个人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但做饭是一件麻烦事,他不喜欢。但也不一定。他做过大拼盘,就是将土豆片、西兰花、洋葱、牛肉块、红萝卜等各种食材放在锅里煎,撒上五香粉和盐,味道好极了。他一个人将整锅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他又做了一次,这次并不如上次好,但也不错。他还是很满意地把肚子填饱了。
那天晚上他还喝了一瓶啤酒,后来11点钟看CCTV6播出的电影《大地惊雷》时还将仅有的一瓶葡萄酒也喝了。他很少喝红酒,但那瓶酒很好喝,他不知不觉间喝光了。电影在12点20分结束,是一部好电影。他在阳台上的破旧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让自己的身心松弛下来,满天星光频繁闪烁,迷人心窍。他直到脚冻麻木了才上炕睡觉。那是美好的一个夜晚。多年来最安逸宁静的一个夜晚。
尼玛在他旁边突然站起来,秦格巴特才瞧见拉毛。她那条褪色的红头巾仿佛已經和她的头发结为一体。她只露出一双正正规规的三角形的眼睛和有四条皱纹的额头。秦格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一个女人也会有男人感兴趣?他们在想什么?
他最后一个站起来。他们个个噤声不语。他们都有些怕这个女人。秦格巴特也怕。这是一个一点儿亏也不吃的女人。她来了后并不看他们。她看着淌了一大片的水。
“你们为什么把水放出来?而且还放到我的草场里?”
“我们的管子里不来水。”更登说。
“我的草要是冻住了,我的羊怎么吃草?”
“不会的,现在不会冻。不但不冻,浇了水的青草才会长得更好。”尼玛的语气好像有讨好的意味,“我们很快就修好了。”
“你不来,我们也会为你着想的。”更登跟她最近,几乎是站在一起的。他笑嘻嘻地看着她。“我心里有数,我们几个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你们不要弄了,这样不行。”她说完这句话,态度变得坚决了。
“我们家里没有水。”更登继续解释,“我们已经三天没有水了,整个水管都没有水,那么问题就只会在这个管口了。”
“我管不了。但这是我的地盘,我的草场,这里还有我的羊需要吃草。你们这样我的羊都惊吓得跑到角落去了,还怎么吃草?你们的羊春天一天不吃草行吗?”
“无论是你的羊我的羊,一天不吃草不喝水都是不行的,但我们的羊已经三天没有喝水了。大家都是心疼牲畜的人,应该都体谅体谅。”更登说的这些话让秦格巴特刮目相看,他惊奇地盯着更登。
“但是谁来体谅我?我的草场一年到头都不消停,我快操心死了但还是没用,现在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了。”她的话里有很多意思,但秦格巴特只知道她今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
“这是我的草场,你们却开车进来,碾压我的草。”她继续说,“没水你们找水利队去啊。”
“水利队?”金乾轻蔑地冷笑,“他们要是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
“总之不行,你们快走。”
“可蓄水池在这里。”金乾指出问题的关键,“而且,当初水池修在这里,可是给了你费用的。”
“就因为我没有男人挡着,所以才被欺负。”她霸气地说。
你的男人多了去了。秦格巴特心里说,数也数不清。尼玛走到井边趴下,把头伸进井里,瓮声瓮气地喊道:“出来了出来了。”
他们都暗松心神,急急忙忙地动起来。更登和金乾扶着梯子下了井。他们身上绑着绳子,秦格巴特和尼玛分别紧握一红一绿两根尼龙绳。万一他俩脚滑落水,绳子就是救命用的。
“还得等一会儿。”更登喊,“秦格,你把铁丝钩子吊下来。”
“什么钩子?”
“在我车上。”
秦格巴特在汽车后备箱里找到了用八号铁丝做的钩子。他准备得倒是充分,好像知道需要什么。
他将铁丝用绳子吊下井去。他的旁边站着拉毛,像监督人似的挑剔他们的一举一动。尼玛没话找话,问她今年的羊羔怎么样。
“还能怎样,半死不活的。就是因为这里没办法吃草,天天有人跑来折腾,这一带的草都废了。”
尼玛被戗得闭上嘴,专心致志地盯着黑黝黝的井底,颇有羞愤欲死的意思。秦格巴特想到关于她的种种传闻,紧紧地闭着嘴巴,打定主意不说一句话。赶紧干完了回家。风一直在吹,阴森森的冷。下面又在喊,但风太大,他没听见。
“我看见了。”更登将咬在嘴里的小手电筒取出来,朝上面喊,“有一团东西。”
“什么东西?果然有东西。”秦格巴特高兴地跟拉毛说。拉毛一声不吭地站着,吸了一下鼻子。
“但钩不出来。”下面说。
“拉,拉绳子。更登掉水里了。”金乾大叫起来。秦格巴特急忙往上拽绳子,只觉得手里的重量加重了十几斤的样子,他再拉了一点儿。
“好了好了。”下面说。
“怎么样?没事吧?”
“不行。他全湿透了,会冻僵的。”金乾说,“他上去,你们一个人下来。”
尼玛看着秦格巴特。“我下去吧,你的腿还没好呢。”秦格巴特说。
“小心。”尼玛说。
拉毛始终站在距离井口一米之遥的地方,既不向前探查井内也不退后离开。她古怪地站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将绳子递给拉毛。“帮着抓一会儿?”
她接过绳子,冷漠地嗯一声。秦格巴特不着痕迹地递了个眼色给尼玛,但对方面无表情,好像没懂。
更登浑身湿漉漉地上来了,冻坏了。又是缩脖子又是抖身子,连话也说不利索。秦格巴特把他扶进汽车,发动引擎。更登开始脱衣服,车上有军大衣,他脱得精光光后穿了大衣蹲在后座上。
“加油门。”他哆嗦着说。
秦格巴特连续轰了几脚大油门,温度表缓慢地向上移动着。他打开暖气,吹出来的气流逐步温热,10分钟后才变得热烘烘的。
秦格巴特回到井边,在腰上牢牢系好绳索,顺着嵌入水泥墙壁的麻花钢筋梯子下去。下面的水青幽幽的,仿佛一个无底洞。金乾在通往他们那边的出水管正前面。秦格巴特只能停在上面,他不能再往下。两个人没法并排站在这短小的梯子上。
金乾嘴里叼着手电,左手紧握梯子,右手拿着钩子在水管里拨弄,频频地将手电光对准水管里面。秦格巴特刚在梯子上站稳金乾就含含糊糊地嚷了一下。他示意将手电拿掉。
“钩到了。”金乾活动了一下有点僵硬的下颚说。
“慢点钩。”秦格巴特叫他稳住,“真幸运,居然就在管口上。能钩出来么?”
“没反应,堵得很死。”
“慢慢来。”
金乾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成功了。
“好像是布。”金乾一点一点往外抽,铁丝一寸一寸地出来。接着到了钩头,那里先是出现了被拽得快要断了的一条红布。然后红布多起来,最后卡住了。但这会儿已经不用钩子了,金乾一把攥住红布,轻而易举地拉出来了。随着他的动作,秦格巴特发现这东西不是布,是裤子。但他还要细看,金乾已经说出来了。
“你看。”他终于将这东西整个兒拿到了手里,“这是内裤吧?”
秦格巴特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盯着看,“是内裤,而且还不是一条吧?”
金乾用手臂勾住梯子,腾出双手翻动。“一条两条,三条。三条内裤,外面的这是两条线裤。”他确定地说道。
他翻动的时候,秦格巴特眼睛不受控制地明亮了,红内裤和红线裤上的斑斑驳驳花花绿绿的污浊痕迹即便长时间被水冲刷了也清晰可鉴,联想到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秦格巴特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开始头晕目眩起来。
金乾眼睁睁地看着手里的东西,突然急急忙忙地叫秦格巴特上去。
“快快快。”金乾火急火燎地往上冲,使劲地推搡他。秦格巴特一边往上爬一边道歉起来,他都不知道是为什么。金乾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催促,他手里紧握着裤头。终于他们从井口翻出来,金乾冲下小高地,仰着头一遍又一遍地深呼吸。他手里紧握着裤头。
第一个看清那东西的人是尼玛,他立刻破口大骂起来,越来越激动。他跑到金乾跟前,详细地查看。
“王八蛋王八蛋。”他又几步走到汽车那里,拉开了车门吼起来,“是裤头啊更登,是女人的脏裤头。我们喝美了……我们喝得太美了。”他几乎快要哭了。
更登蹲在后座上看着尼玛,一副面无表情的呆板模样。
“更登。”尼玛捏住更登的手臂,激动地摇晃不止。
秦格巴特就站在井边,他对自己失望极了,他用尽了所有力气,也感到难以面对这种事情,他想不到一个解救的办法。金乾还在远处,他蹲在那里。一股一股的白烟出现在他头顶。然后他站起来,一步一步走过来。他的脸色极为难看,极为苍白。他走过来后靠着汽车端详着后视镜里的自己。接着他看向井边。秦格知道他在叫他,但他踌躇地看拉毛。拉毛已经退下高地了,她似乎很想离开但不可能了,金乾在叫她。叫得很凶。秦格巴特吓一跳,但他马上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自责没工夫琢磨,现在金乾一喊他才回过神来。
“叫你呢。”他尽量不让自己发火。他盯着她。
秦格巴特让她走前面,押解犯人似的走向汽车。
更登裹着大衣坐在车里。车门大开着,他依然冻得发抖,但比起寒冷,更使他感到寒冷的是那东西。他下车检验过,脸色就和金乾一样难看,回到车上就仿佛病了一样。
大家聚在车旁,可谁也不说话。静默异常。在这种氛围中首先拉毛受不了了。“我先走了。”她一改之前的做派,小心翼翼地说:“我要去看羊群。”
“你想走?你走哪儿去?”尼玛一拳砸在车门上,他牙齿咬得下一刻就会全部碎掉似的,他用一种邪恶的眼神盯着拉毛,但他再怎么努力伪装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失落和苦痛,仿佛这件事一发生,他的精气神就被废了一半。他的样子十分惹人同情,但他自己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拉毛平静地看着尼玛,“你冲我发什么火?”
“你自己心里清楚。”金乾说,“你再清楚不过了,你这个魔鬼。”
更登用颤颤巍巍的声音也说道:“魔鬼,世上怎会有你这么绝的女人。怪不得你没有男人,活该,这就是你缺德的报应,活该!”
拉毛声音陡然尖锐刺耳,“你们这群狗毛——”她炸裂般地将身子绷直了,脸上剧烈的表情让蒙着的头巾都掉下来,露出那张不再年轻更不漂亮而且很大的红脸,还有那张极薄极薄的、宽大的嘴巴。一系列精彩的让人叹服的咒骂就从那张嘴里喷出来。他们根本无力还嘴,即便有谁见缝插针地回击也会被她新一轮更恶劣激进的咒骂弄得狼狈不堪。她一旦开始吵起架,就恢复了刚来时那股劲儿,或许更强烈了,她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难听,她没有任何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什么绝损说什么,把他们每一个都实实在在地辱骂了一遍,然后再挑选着骂。他们几乎都忍不住了。秦格巴特是第一个没能忍受的,他已忍无可忍,他几乎快要被气死了。他本来是站在金乾后面一点儿的,现在他一把推开金乾,一下子站在拉毛眼前,一拳砸在她鼻梁上。她被击中以后嘴里的骂声还没结束,但马上就接上了一声惨嚎。那声音之难听,比辱骂更令人难以接受。这回是尼玛,他大吼一声,把那叫人痛苦的惨嚎比压下去。
“别喊,你再叫我掐死你。”尼玛蹲到她近前说。
但她才不会听话,虽然声音小了但一个劲儿地嚷嚷有种就掐死她。
“你以为这样就过去了?”金乾和尼玛并排蹲在地上,他生无可恋的样子,但说话还是中气十足。“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你干的好事?你就是一个鬼。你让我们吃你下面脏东西你这个鬼……”金乾说着便挥起手臂,一巴掌扇在她左脸上。这一个巴掌打得格外响亮。干冷而有力的东风都压不过这声音。等他的手收回去,拉毛红彤彤的脸颊上四个淡白色的指印明显地留在那里。她硬生生地顶了那一巴掌,头都没晃动一下。她甚至有可能是在等着这一巴掌,因为秦格巴特一瞬间分明看到她得偿所愿的胜利神态暴露无遗。她的身体是朝着巴掌过来的这边倾斜的,就是说在金乾几乎就要发飙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了,于是做出反应。
秦格巴特确定没有看错,但其他人没看见。他们分明都是一副解气又舒畅的模样。他们一点儿也不掩饰这种神情,但拉毛看不到。拉毛不再哭喊吵闹。她用冷静的语气一字一字地说:“你们凭什么说是我的东西?你们谁看见了?”
“还用得着亲眼看见吗?你就是那样的坏。除了你还有谁?我们都知道,不就是因为你的草场经常被车碾人踩,你不高兴吗?你拿了踩踏费你还干这种丧尽天良的缺德事,你活该一个人困死你……”金乾不断地挥舞手臂,好几次就要打到她脸上和身上,每次都是巧妙地滑过去。他说得唾沫横飞,都是他们想说的话。
“草场门口有陷阱,一条木板上钉满的钉子,是你干的吧?”秦格巴特提醒大家还有这事,好多人都被扎了摩托轮胎,他们全部上过当。她把木板用一层浅浅的黄土掩盖住,骑车人没有一颗十分敏锐的警惕心便逃不过陷害。
“对,差点忘了你还干过那事,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在你的阴影下吃水生活的吗?”尼玛尖细尖细地叫嚣着,他去踢汽车前轮胎发泄,一遍遍地咒骂。但他的骂词枯燥无味翻来覆去没啥新花样,和之前拉毛的骂形成鲜明对比。他自己也似乎意识到这一点,突然间变得沮丧了。
一直静坐车中的更登摔门下车,秦格巴特他们都让开了路。更登径直走向拉毛,一脚踢去,一点儿不含糊。
“这一脚,好叫你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你挑战我们的底线了骚货。”说完他再一脚。
“你的阴險,无人能敌。”尼玛说着向前跨出一步,这样他们四个人就把拉毛严严实实地围在中间了。拉毛被踢倒后马上站起来了,但紧接又被踢倒,这回她就歪坐在地上,迅速地看了他们几个,然后迅速低下头。她被恐吓住了,不哭不喊,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你们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们凭什么?”
“你觉得我们冤枉了你?我们哪儿冤枉你了?”
“草场门口的钉子是我弄的,但井里的这个不是我。”
“你还说。”尼玛揪住她的头发,“你再说我打死你。”
她的头巾被尼玛扯掉,一扔,便被风吹走了。
“请把头巾还给我。”她无力地说道。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觉得我们奈何不了你?”金乾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现在用完了。以后,你休想我们让着你。你起来。”
“真不是我,你们会后悔的。”
“你威胁我。”更登的第三脚踢到她屁股上,发出受潮鞭炮一样沉闷的响声。
他们越打她,就越觉得不解气。秦格巴特在红头巾飞走的一刻想起那团东西,浑身都开始难受起来,他预感到自己将会大病一场,而源头无疑就是那东西,就是这幽暗的蓄水池里挖出那东西的那一刻,同样是那样一股挥之不去的气味。还有,如果不克服这个问题,以后一喝水就想起那东西,每想一次就是一次痛不欲生的灾难,那还让他怎么活?这才是让他最难以接受也是最恨拉毛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尽管令人震惊但在这会儿他已经缓过来了,他从来不会为发生过的事情费神。但这件事不一样,这件事的后续影响太深远太恐怖了,他不敢想。他的火气一直就没下去,他一直忍着。他是他们当中最不愿意动手的一个,却是第一个动手的人,也是下手最重的一个。他第二次动手,打了一拳在她头上,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他一拳接一拳地胡乱打到她身上,有十几拳。最先的几拳下去她还惨叫着,然后便没有声音了。等他们三个把他拉开时,拉毛的头上和脸上全是血。最明显的一道伤口是右眼上角的一道豁口,有四五厘米长,血正在一刻不停地流出来。
他们慌了,尼玛飞快地跑去将一百多米外被铁丝挂住的头巾捡回来帮她擦血。金乾扶着拉毛。她似乎是想晕过去。秦格巴特觉得她在装,就还想揍她,被更登又拖又拉地推开了。他们忙活了好一阵子,她的伤口不流血了。于是她被扶上车,更登和金乾送她回家去。剩下尼玛和秦格巴特。
尼玛唉声叹气地埋怨秦格巴特不应该弄出伤口。
“没有伤口、没有伤痕怎么都好说,现在好了,要是她去告状我们就完了。她肯定会去告我们的。”
“打她的人是我,是你们把我拉开的。”
“都一样,我们都动手了。”他用铁丝将那团东西挑起来放到摩托车载重盘上,用绳子绑好。“这东西不能丢,这是证据。”他说,“好了。我们走吧。”
“你走吧,我走回去。”秦格巴特说。他不会和那东西共乘一辆车的。他穿过六片草场,抄近路回家。
4
他回到家,点了炉火。他烧了茶,但马上就倒掉了。他在炉子上搭上厚厚的平底铝锅,倒了几滴菜籽油,然后将早上走之前取出冷房的牛肉切成片。一共三片,都有巴掌那么大,一个指头那么厚。他把三片牛肉都放进锅中。他本来是想腌一腌的,但切好后忘了,而放进锅就不能拿出来了。但也没事。牛肉滋滋地响起来,有牛油的部分开始渗出油水。他用木铲子将牛肉推动,在锅里滑动一圈。肉香味出来了。等煎好一面翻转到另一面,撒上一些花椒粉和辣椒粉。辣椒粉一碰到油便刺激出一股辛辣味,他打了一個喷嚏。他喜欢有辣椒粉的牛排。
几分钟后牛排煎好。他盛好牛排,找到一瓶已经打开了用来浇花的啤酒,然后欣慰地坐下。他扭头瞧一眼柜里的钟,4点50分。距离5点50分去赶牛喂牛饮水还有整整一个小时,不着急。他切开牛肉吃了一块,味道和上次略有差别。但别有一番滋味。比饭店里的好太多。他吃过西餐厅的牛排,那牛肉的味道让他恶心,软绵绵的,一点儿嚼劲都没有,仿佛在嚼一团棉花,只吃了指甲盖大的三块他的嘴巴就发酸了。于是他停下来,浪费了它。后来他又有机会吃过两次,还是那个样子,于是他确定,牛排就是那个样子。那是牛肉的问题。他用自家的牛肉自己随便做的牛排才是最好的牛排。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做牛排的功夫了,掌握了一些技巧,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的。今天的这顿又有所不同,他本来心情极差,做它的过程中缓和下来,又在吃的过程中彻底放松了,他怀着一种十分罕见的愉悦心情吃完最后一块牛肉,将碟子刀叉放进一个铁盆子里。他不想洗它们。
然后他从一个抽屉里找到香烟,找到打火机。他有一段时间每天抽一根香烟,后来觉得没意思就不抽了。现在他想抽一根。他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躺在沙发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给老婆发了一个信息:明天赶紧回来,我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