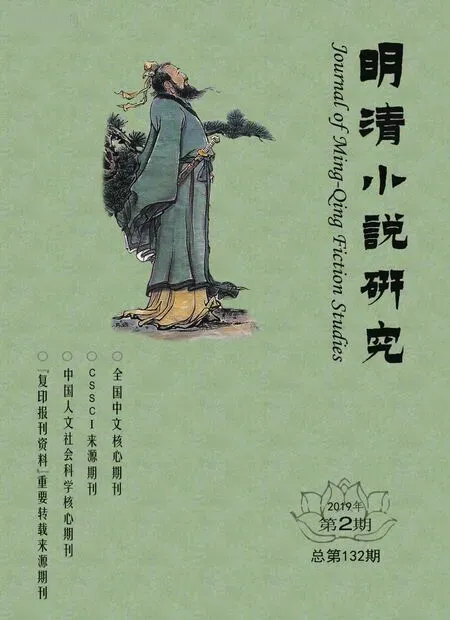论《西游记》叙事中孙悟空的能力表现矛盾∗
——以现象、成因与艺术作用为中心
·李 军 王 昊·
内容提要 世本《西游记》中孙悟空前期所向披靡,后期屡战屡败。前后叙事看似矛盾,实则自有情理。人物的前强后弱,一是受此前西游取经故事形态的影响,《取经诗话》、杂剧、平话的叙事中一直有着借助神佛力量解决困难的传统;二是与作者构思相关,前期需要突出悟空之能,后期需要突出取经之难;三是受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驱动,孙悟空后期处于武艺与法宝、法力的不平等对抗中,暴露出自身能力与性格的不足,又受到师父、师弟的掣肘,以致多次陷入困境。世本对孙悟空能力表现的书写,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立体丰满,艺术成就远超取经题材的其他文本。借助互文性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叙事面貌。
作为百回巨著,《西游记》通过异想频出的故事叙述,将主角孙悟空塑造得形象鲜明、魅力十足。曾有学人高度评价其叙事之法曰:“前呼后应,首尾联动,使整部小说既在结构上严密精细,叙述起来也巧妙灵动。”①与此同时,出于不同的阅读体验或认知角度,人们对其叙事也有一些质疑或批评,其中一个典型问题即孙悟空的能力表现问题: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角,花果山时期的齐天大圣战天斗地一往无前,为何西行取经阶段却举步维艰屡屡受挫?小说中孙的武艺、兵器、七十二般变化与筋斗云等能力(即小说所谓的“神通”)并无前后变化,前期面对的是整个天庭的神仙天将,而后期不过是地方上“割据”称王的妖魔鬼怪,但孙悟空的战斗效果却为何如此迥异?
对这一问题,梁归智先生认为西行途中孙悟空进入了“体制内”,要遵守成人世界的规则,其目标也由“做英雄”转向“做圣贤”,故“表现本领的方式也不同了”②;李天飞则从人物形象的构成来源角度进行了辨析,指出孙的形象由能力本有差别的“齐天大圣”和“猴行者”两个形象组成,故而前后有异③。除两文的已有揭示外,还有无其它因素?如何评议两文的解答?孙悟空的前后表现对小说的艺术效果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仍可探讨。本文即拟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结合史的考察进行论述,以求正于学界贤达。所引小说原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版《西游记》,该本据明世德堂百回本(即“世本”)整理出版,为通行之本,故引用时仅标出所在回目。
一、现象:能力表现的前后差异
《西游记》叙述的孙悟空故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1至7回,叙其以猴王身份从花果山发展到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经历;第13至100回,叙其以行者身份保护唐僧的西行取经过程。前后两个阶段,孙悟空面临的敌对力量在强弱、多寡上显著有别,而孙的战斗表现也大相径庭,前后不一。
(一)前期表现。孙悟空自须菩提祖师处艺成归山之后,入东海、下冥府,“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第3回回目),扰动了天庭统治下的三界秩序。随后由于不满天庭前后两次招安中的轻贤慢待,孙悟空先后反出天宫,也相应地引来了天庭的两次镇压。对此,孙悟空慨然应战,第一次,胜巨灵、伤哪吒,轻松迫使天庭承认其“齐天大圣”名号。第二次,面对十万天兵布下的天罗地网,大圣先败九曜恶星,继而又“一条棒,抵住了四大天神与李托塔、哪吒太子”(第5回)并战而胜之,三败惠岸,最后才因老君的偷袭而在二郎神、梅山六圣及哮天犬的围攻下被擒。自炼丹炉出来,又将道祖李老君“捽了个倒栽葱”,一人一棒打到灵霄宝殿,“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围攻的三十六员雷将不能近身,直打得天庭请来西天如来方得安生。这些叙述,将孙悟空塑造得英勇无比,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人心折神驰。
(二)后期表现。这一时期为小说的主体部分。第8回,压于五行山下的孙悟空经观音指点而自愿加入取经队伍。自第13回正式加入后,他一路降妖除魔,保驾护航,最后修成正果。这一阶段的主要叙事模式,就是孙悟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辅之多方求助,最终从妖魔手中解救失陷的师父。面对各路妖魔,虽然孙悟空自诩“历代驰名第一妖”(第17回),常常不忘宣扬一番昔日大闹天宫的旧事作为自己勇武难敌的注脚,但动起手来却往往陷入难局,风光不再。其过程,虽然武艺上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占据上风,但或败于对方法术、或败于对方法宝。具有对比意味的是,很多妖魔不过是天庭神仙们的僮仆乃至坐骑之流。很明显,妖魔们相较于他们的主人,是处于寡与弱的一方,但孙悟空的战斗表现却反而未能延续前期面对多而强的天庭对手时的那种所向披靡。
尽管最后孙悟空获封“斗战胜佛”,但缘由在于“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第100回),是重在降伏的结果而非战斗的过程。前后相比,西天路上孙行者较之天庭鏖战时的齐天大圣,黯然失色了许多。换句话说,小说中孙的能力被叙述得前强后弱,差距明显,简直似非一人。
二、成因: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针对上述局面,综合考虑故事面貌的历史流变和文本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小说对孙悟空能力的叙事处理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已有故事形态的制约
对小说如此叙事的内在动因,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小说的成书因素。与独立创作的现代小说写作模式相比,《西游记》是典型的世代累积性作品:世本之前,已有多个西游取经故事先后出现,借助民间传说、说话艺术、戏剧艺术甚至壁画艺术等方式广泛传播④。世本的写定者——较被接受的说法为吴承恩——是在此前已有故事形态的基础上剪裁、整合、改造、创新而定型完成的。因此,《西游记》中情节的发展与人物的行动要受到世本之前的故事形态的制约,而不完全由世本写定者本人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吴承恩在叙述、描写孙悟空的言行时,要受到彼时早被民众和自己所知悉听闻的已有形态的或显或隐的影响。
玄奘西行求法是唐初的真实事件,这一事件进入文学领域,逐步神异化为西游取经故事。叙事文学中现存最早的取经故事文本,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诗话》共18节,首节佚,“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节中,一白衣秀士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主动前来加入取经队伍,被法师(玄奘)“当便改呼为猴行者。”⑤这位连姓名都无的猴行者,“未曾大闹天宫,既没有混号齐天大圣,也没有法名孙悟空”,但他就是后世取经队伍中孙悟空的雏形⑥。《诗话》之中,猴行者在取经队伍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向导,告知前路有何妖魔险阻;而对于妖魔,取经队伍全仗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赐给法师的三宝(隐形帽、锡杖与钵盂)来解决:“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⑦行进途中队伍所遇的妖魔本就不多,猴行者除与妖人斗法一次外,降妖之战不过是化锡杖为夜叉战白虎精一次、为铁龙战馗龙一次;其余所遇自然险阻,甚至可由法师自己解决,如过长坑、灭连天野火时都是手持宝物大呼“天王”而过;所遇毒蛇猛狮,皆具佛性而遇人不害⑧。《诗话》为“晚唐、五代的俗讲底本”⑨,则取经故事早期原是为了宣扬佛教的佛法神力,以其救苦救难,本来就没有将猴行者的战斗能力作为取经之行的保障。
《诗话》之后,倚靠神佛来降妖的叙事模式贯穿于取经故事的演变中。元末明初杨景贤有《西游记杂剧》,其第八出《华光署保》叙取经之始观音就安排了包括李天王、韦陀、华光天王及其自己在内的十大保官,要保官们“都保唐僧,沿路无事”,并“写了文书,要诸天画字”,全如剧中【正宫·端正好】曲所唱:“差十大保官来,同九曜星君降。把唐僧于路堤(提)防。天佛牒玉帝敕都交往,西天路收魔障。”⑩相较于《诗话》的猴行者,杂剧第九、十出中猴王有了“通天大圣”名号,因偷仙桃、仙丹与仙衣而被李天王率那吒(哪吒)擒住,在观音的现场办公式的安排下等待加入取经队伍,并得法名“孙悟空”。从此,南方犯上作乱的猿猴精进入唐僧取经故事,并造就了取经故事体系中的猴行者自此有了“猴王”“大圣”“行者”与“悟空”等交融混用的称谓。但杂剧中孙悟空独力解决的妖怪,不过收沙和尚、除银额将军而已。其余遇红孩儿、收妖猪(八戒)、过女儿国、经火焰山,都得力于保官的保障之力,孙并未显示出有多大的本领,甚至还被女儿国一个人间婆娘按倒纠缠而未能保护住师父,挨了“奉观音法旨”前来救护的韦陀的好一顿训诫⑪。
明初至明代前期,出现了《西游记平话》一书⑫,公开印行发售。该书现已失存,幸有朝鲜半岛的《朴通事谚解》(约成于16世纪前期)留存了部分故事梗概和少量情节的转述。《谚解》概述三藏法师西天取经经历为:“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几死仅免……怪害患苦,不知其几”⑬,可知孙行者对付这些“怪物妖精”并非一战降伏,而是以绝处逢生者为多。《谚解》又云:“在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但紧接着转述的车迟国斗法故事中,孙悟空与伯眼大仙的弟子鹿皮较量油锅洗澡,还需念咒让“山神土地神鬼都来了”,使之合力将鹿皮挡在锅内烫死取胜⑭。鹿皮师徒并非法力多高明者,尚需助力,则可推测遇到其他令唐僧“几死仅免”的妖怪时,更是需要大圣去搬取救兵。所谓“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应指降妖过程中孙悟空主动担起重任,不屈不挠,奋力解决“怪害患苦”,而非像杂剧那样由保姆似的保官们不招自来,主动护佑唐僧无事。
上述内容,是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之西游故事中孙悟空能力地位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具体情节各有不同,但取经故事中一直有着依靠神佛来帮忙降妖除难的传统。《诗话》、杂剧、平话,皆根植于民间文艺,大众经过口耳相传,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情节印象与接受思维。推情度理,世本写定者在整合已有的各种遇妖情节时,因利乘便,承袭已有的情节模式,继续让孙悟空四处求援而在写作艺术上加以提升,如此则事半功倍,不至于与接受者产生龃龉。从实际来看,世本也正是如此完成的,安排大圣受挫在先、求援继后,百折不挠地完成重任。
前言李天飞有从形象生成史的角度分析孙悟空能力差距的专文,其大要为根据蔡铁鹰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孙悟空的形象源头可分南北两个故事系统:南方系为浙闽一带久有的猿猴精“某某大圣”的犯上作乱故事,北方系为流传于陕甘西域的神猴“某行者”跟随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在北方系的故事里,猴行者的身份类似一个奴仆,不大需要表现英雄气质,遇到问题用最低成本解决就行了,比如现存最早的西游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动不动就请大梵天王解围,这其实就是今本《西游记》动辄请人帮忙的嚆矢”⑮。此说除“奴仆”有所夸张外,其余精当,而其分析角度实际也是从故事形态的演变来分析的,不过是着眼于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的形态而已。稍显遗憾的是,限于篇幅,李文未就杂剧、平话中的孙悟空求助传统进行展开。
(二)作家艺术构思的需要
从前述广义的西游故事文本中的已有形态,到世本所体现的现有局面,离不开《西游记》写定者吴承恩的艺术构思与写作实践(一般认为,《西游记》版本史上的朱鼎臣本、杨致和本晚于吴承恩本)。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成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⑯1960年代后期,法国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或译“克里斯特瓦”)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说:“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⑰而我们通过对广义文本角度的《诗话》、杂剧、平话中西游故事的梳理,正可以看出世本《西游记》中蕴含了此前故事文本(“前文本”)中的“众多声音”;通过比较世本对前文本中故事情节的扬弃,则可以看出吴承恩根据创作意图与框架构思,对前文本的情节进行了裁剪与吸收,再以虚构与想象进行了转换和天才性的个人加工。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前后表现的差异,与世本写定者经过“对话”前文本之后形成的整体构思紧密关联:根据小说中心故事的需要,既要特意突出孙悟空前期的神通,又要特意增加后期的艰难险阻。
首先,从确定取经人选的角度而论,为了有效刻画孙悟空加入队伍的合理性,小说需要突出齐天大圣的威武神勇。一方面,世本之前诸文本对行者加入取经队伍的推动力量缺乏充分的铺垫,世本则明显对此进行了弥缝增补并且大肆渲染。《诗话》中猴行者不明所以地主动前来,缺乏原因的交代;杂剧中观音在那吒擒住大圣后“特来抄化这胡孙,与唐僧为弟子,西天取经去。休要杀他!”⑱平话中则是二郎神拿下大圣后,观音“上请于玉帝,免死”,安排压于花果山下等候取经之人⑲。但是,观音是西天佛教力量的代表,而天庭靠的是自家的道家神力降伏妖猴,又何以会顺从外部意愿而轻易放过上犯天条的猴王?对大圣由“闹天宫”到“取西经”的故事走向中这一关键转折,杂剧与平话都未曾拈出点明。世本则不然,小说先浓墨重彩地叙写天庭在孙悟空造反事件中的窘态难局——借第8回如来之语,即“概天神将,俱莫能降伏”“亦莫能伤损”,反而令猴王更加“扬威耀武,卖弄精神”——这些叙述有力地突出了如来参与天宫平叛的必要性。灵山佛尊出手之后,玉宇澄清,“安天大会”上天庭诸神因此由衷地赞叹如来的安天之功(第7回)。通过这样的情节设计,由佛门来决定猴王的命运就合理得多了,第7回回末诗“妖猴大胆反天宫,却被如来伏手降……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正是对全书故事由作乱到取经之关键转折的揭示。天庭的无能有力地反衬出佛门如来“法力无边”的形象来,以至于桀骜不驯的悟空西行遇妖自夸时也多次心悦诚服地提及这段经历,第17回即直言“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如来作为最高法力的存在,乃是小说叙述大圣皈依向佛、投身取经之行的内在需要;而要安排佛祖前来降妖,势必要突出大圣之能——小说也正是如此写作的,故第一阶段叙事时,将大圣的战斗能力极致化到令整个天庭颜面扫地,不得不求助西天佛力。
另一方面,各前文本对取经护法人选的过人之处并未在意,世本则有意书写了这一点。《诗话》中的猴王因偷桃而“被王母捉下”判打铁棒数千,再过王母处时望而生畏到“至今由(犹)怕”⑳,其能力与胆量俱无足观。杂剧、平话中的猴王分别在那吒、二郎神的一战之下败北,虽有能力但非超群之才,为何能被选为将要面临各色妖魔的取经队伍之护法人?似乏铺垫。世本则不然,通过对他两次大战天兵神将再到大战灵霄殿的层层推进,充分地展现了齐天大圣战天斗地的过人之处;尽管他在二郎神手下遭遇一次败绩,但那是在天罗地网、照妖镜、金刚琢和梅山众将等诸般力量之围堵合击下的失败,且自炼丹炉跳出后更是强势反击,直杀得整个天庭天仙神将们无可奈何,不得不请来佛祖如来。这样,后文佛祖所付观音的法旨——“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第8回)——中的“神通广大”方是落到实处,护法人选也就非大圣莫属了。李天飞言:“在南方系故事里,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是本土妖神,本来就是要讲一个造反捣蛋的故事。当然要突出大圣的能力了。”㉑此说实际值得商榷,前述杂剧、平话中来自南方系的“大圣”并未竖起造反大旗,更多的是偷窃仙家珍品的捣蛋行为,且一战败北,故事突出的乃是天庭仙家的威力。将大圣战天斗地能力作为正面描写对象的,是世本写定者才做到的大胆构思。而其能力作为重点谱写任务,还体现在吴承恩特地于小说开篇为猴王叙述了远涉重洋学艺、东海觅趁手武器等情节,不惮篇幅补足了取经护法人的前期经历,为此后闹天宫、取真经两项大事作了充分的铺垫(这些都是之前的故事形态所缺乏的),并将猴王的出身提到叙事的肇始。此外,杂剧、平话将大闹天宫情节设置于唐僧取经事宜启动之后,小说则安排大圣于“王莽篡汉之时”被压两界山(第14回),远远早于大唐。如此一来,关押了五百年的猴王听闻观音指点解脱之道时,即甘心情愿地加入取经队伍,“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第8回)世本如此设计情节叙事,明显高于此前的故事面貌,他的顽劣不堪、超人之威引来五百年的磨难,也有力地宣告了他就是西行降妖的不二人选。正乃《孟子·告子下》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了,这些都是世本写定者在“对话”前文本之后的创造性的构思成果。
其次,从取经历程完整性的角度,作家需要增加进程中的磨难。小说第8回叙述取经事业缘起时,如来言:“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故要找个取经人,“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这从根本上奠定了取经要历经重重磨难、步步波折的基调,是小说中佛家“经不可轻传”(第98回语)理念的直接体现。为了突出真经的神圣,需要其得之不易,故对取经团队横生考验。如平顶山降伏老君的金角、银角两童后,老君即明言:“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第35回)故西行取经的展开基调就是“师徒们魔障未完,故此百灵下界,应该受难”(第66回),所以唐僧“步步有难,处处该灾”(第31回)。至于完成取经大业需要历完的“魔障”数量,第99回叙观音将“历难簿”过目后急忙传声道:“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吴承恩是特意设定了唐僧所经磨难的总量,而可资比较的是世本之前并无九九八十一难的说法。因此可以推知吴承恩特意增加了取经的不易,其表现形式,就是唐僧之徒孙悟空不得不在数量上接受更多的任务、在难易程度上遭受更多的挫折。世本之前《诗话》中的蛇子国、狮子林的毒蛇猛兽看似险恶,实则“皆有佛性,逢人不伤,见物不害”㉒。而以最接近世本的平话为参照物,《谚解》对唐僧经历的“怪害患苦”有概述,徐朔方先生以今本《西游记》与之进行了对比:
《谚解》第267页说:“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相当于今本第七十四回)界遇猛虎毒蛇之害(今本为青毛狮子怪、黄牙老象、大鹏雕和四万八千小妖),次遇黑熊精(第十六回),黄风怪(第二十回),地涌夫人(第八十回),蜘蛛精(第七十二回),狮子怪(不止一次),多目怪(第七十三回),红孩儿怪(第四十回),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薄屎洞(第六十七回),女人国(第五十三回),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㉓
按,引文中“怪害患苦”四字总括前文所遇种种艰难,不应断开而致分属上下两句,宜从前引“怪害患苦,不知其几”的句读形式。而从徐先生的详细比勘中,可以明显看出世本设计的妖魔更多。以平话中的师陀国为例,其“难”不过是猛兽毒蛇,承袭的是《诗话》中蛇子国、狮子林的物类而删削其“佛性”特点;世本则改为“路阻狮驼、怪分三色、城里遇灾、请佛收魔”四难(第99回),将此前的猛兽改为有法力之妖魔:以普贤的长鼻似蛇的象怪代替平话中的毒蛇,以文殊的青狮为妖代替猛兽之害(这一构思还导致文殊的狮子坐骑与第39回乌鸡国狮妖重出㉔),尤其是增补的大鹏雕怪,“搧一翅就有九万里,两搧就赶过了”纵筋斗云败走的孙悟空(第77回)。大鹏的这一本领,明显借用于《庄子·逍遥游》,是作家从自身文化修养中获得的灵感并构思成文而非沿袭前人。这些不同,昭示出这部分磨难出自世本写定者的个人构思。正是在不满于平话等所设妖魔险阻份量不足的情况下,世本写定者增改生发,将妖怪的数量明显增多、能力明显增强,因此,孙悟空后期遭逢“强中更有强中手”的难局就成为必然现象了。
(三)服从艺术真实的必然
从根本上来说,小说的叙事以虚构为本,但在文字所营造的非真世界里,人物的言行与情节的发展要符合情理,小说呈现出艺术上的真实性来,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到真实而易于接受。对这一点,明末小说家就有了“事赝而理亦真”者能“触性性通,导情情出”(冯梦龙《警世通言叙》)的认识㉕。至于《西游记》在艺术真实方面虽谬而真的高超成就,《二刻拍案惊奇序》就评价说:“《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㉖文艺研究也已表明,一旦作家笔下的人物获得自己的性格、生命,就将“按着事物内在的逻辑发展,循着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行动”㉗,这种艺术真实内在需求驱动下的故事发展与人物行动,不以作者的主观愿望来扭曲,也不以读者的阅读感受而减色。从《西游记》对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写出发,我们认为,西行之途重重艰难是取经故事符合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物按照其个性行动而合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孙悟空前后期的不同表现,是小说叙事达到“幻中有真”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与典型体现。
首先,孙悟空虽然机智勇武,但却有两个一以贯之的短板。一者,怕风烟吹眼。当年被推入八卦炉中,钻身巽宫位下的他虽然避开了炉火的锻炼,“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煼红了,弄做个老害病眼”(第7回)。有此弱点,令他在黄风岭被黄风怪“劈脸喷了一口黄风,把两只火眼金睛,刮得紧紧闭合,莫能睁开,因此难使铁棒,遂败下阵来”(第21回);枯松涧遇红孩儿,首战火中无功,次战时被妖怪“将一口烟,劈脸喷来。行者急回头,煼得眼花雀乱,忍不住泪落如雨”(第41回)。因为怕烟的弱点,他在二妖手下都吃了大亏。二者,不善水战,他自言“水中之事,我去不得。……若是那般捻诀,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第49回)水中妖怪即可占据地利之便,或闭门不出,或一战即潜,故征程之初大圣即对鹰愁涧小龙无可奈何,此后流沙河对沙和尚、通天河对金鱼精、碧波潭对九头虫都是空有一身战意却无用武之地。而与后期不同的是,前期大圣抗击天庭时并无火战与水战经历,未曾暴露己短,不曾折损威风。
其次,孙悟空前后所处的斗争态势不同。我国的先民神话与外来佛教中早有或朴拙或繁复的斗法故事,神魔小说则进一步发扬光大,设定妖魔仙佛各有神通,所叙斗法斗宝,异想迭出,引人入胜——这也是神魔小说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其他类型小说形成区别的显见标志,法术法宝也会在神魔小说情节的进行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游记》中,七十二般变化是为了“躲避三灾之法”(第2回,指雷、火、风三灾),与筋斗云都属于防身法术,并非攻击法术。因此,在神魔横行、法宝争竞的世界里,大圣所具备的进攻能力竟然只是一身武艺。虽然他“身拜灵台方寸祖,学成武艺甚全周”(第67回),但与外界发生矛盾时,他的攻击力也就局限于自己的一身武力了。前期,天庭的镇压是以武力为主,如哪吒化身三头六臂后,也只是“手持着六般兵器……丫丫叉叉,扑面来打”(第4回),老君的金刚琢也是在被问及“有甚么兵器”时取出使用的(第6回),故大圣可以凭借趁手的金箍棒与超人的战斗力而大获全胜。后期,需要降妖除魔时,孙悟空第一凭借的还是其引以为傲的武艺(与对手大战后甚至会向观战者炫耀一番),但时移势易,主动要与大圣先后“比势(试)”武器、拳法的青牛精兕大王毕竟是少数(第50、51回),妖怪们所倚仗的,乃是自身的一技或数技之长的法术(如喷风喷烟的黄风怪、红孩儿),或别具威力的法宝(如青牛精的金刚琢就让孙悟空深感无奈)。拥有了这些法术法宝,强者如虎添翼,弱者防守反击,故而即使妖魔本来不过是神佛的僮仆、坐骑之流,也能抗衡甚至碾压大圣的强悍战斗力。换句话说,孙悟空的能力并未发生前后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其对抗方式:前期是武力之间的比拼,后期是以武力去进攻已超越武力层面的法术法宝,故战斗的效果前后大不相同。
顺而论之,虽然法术法宝属于想象的产物,但这些虚构物造成的难局也有解决的逻辑:法术法宝虽威力巨大,但也各有“天敌”或正主,如不能盗取以解除之,则要找到法术法宝的克制者或真实主人。故套兵器火器、拒大水金砂的青牛精在悟空找来老君后,芭蕉扇下乖乖就缚(第52回),连佛祖都吃了一亏的蝎子精在天敌昴日星君前现出原形束手待毙(第55回)。所以对依仗法术法宝横行的妖魔,小说借沙僧之口说道:“以相生相克拿他,有甚难处?”(第41回)孙的取经历程,某种意义上就是上下求索以找出相克之道的历程;降妖除魔过程,实际即斗法降法过程,所需乃以法克法而非以武克法,故孙悟空的旧有神通施展效果就大不如昔了——这是《西游记》书写超现实的神魔题材决定的,虽然小说也多处对大圣及若干对手的武艺进行了描述,但毕竟不是英雄传奇小说。而且,前期大圣斗变化受制于二郎神、赌筋斗云败于如来,也在叙事中形成前后呼应——武力克制不住妖怪(孙的前期为妖猴),法力才能克制。至于沦落到要找昔日手下败将助力,大圣也曾有动摇:“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想我闹天宫时,玉帝遣十万天兵,布天罗地网,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如今那怪物(按,指青牛精)手段又强似老孙,却怎么能彀取胜?”小说第51回特意通过这一心理描写,借许旌阳之口表达出降妖逻辑道:“此一时,彼一时,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这种“一物降一物”的思维,出自人们的生活经验总结:非其天敌则多无法克敌制胜。西方《伊索寓言》之《蚊子、狮子和蜘蛛》中,也正反映了这一点,而西行路上的孙大圣即如猛狮一样,空有武力而无奈飞蚊。故后期取经过程虽是超现实的斗法叙事,但由于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朴素逻辑之上,故孙悟空的屡战屡败并不突兀,这正是来自生活的艺术真实驱动着情节的必然发展。
再次,取经路上波折丛生,与孙悟空的性格以及取经团队中的性格冲突也有相关之处。孙争强好胜,对其武艺甚是自信,号称“棍打诸神没躲藏,天兵十万都逃窜。……全凭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第75回),故遇到妖魔时,悟空首选的降妖方式是明刀明枪以武取胜。观音所言“那猴头,专倚自强”的批评语(第15回),正是对其性格弱点的精当认识。甚至多次遭遇武力无效的经历后,孙大圣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典型事件即过狮驼岭时,他被狮魔(老魔)吞入肚后与大鹏怪(三魔)的一番对话与心理(第76回):
三魔见老魔怪他,他又作个激将法,厉声高叫道:“孙行者,闻你名如轰雷贯耳,说你在南天门外施威,灵霄殿下逞势;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缚怪,原来是个小辈的猴头!”行者道:“我何为小辈?”三怪道:“‘好汉千里客,万里去传名。’你出来,我与你赌斗,才是好汉;怎么在人肚里做勾当!非小辈而何?”行者闻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断他肠,揌破他肝,弄杀这怪,有何难哉?但真是坏了我的名头。……也罢!也罢!——你张口,我出来与你比并。”
这段激将之下舍易就难的叙述,可见孙悟空性格上自视甚高,争强好胜,心理上以英雄好汉自居,不愿以不光彩的手段取胜——这种以免“坏了”或“低了”自己名头的心理活动,在小说第18、33、72、74、76、85回中多次出现。孙的这些表现,颇有些英雄传奇小说所宣扬的江湖习气(这也应与取经故事早期在民间、市井流传有关),但在西行的神魔世界之武艺与法术法宝间的不对等战争中,无疑使孙悟空落后于敌我力量的对比,陷入被动、遭受挫折就屡屡发生了。
所言性格上冲突,主要发生于孙悟空与唐僧之间。悟空出身妖仙,熟知妖魅惑人的手段,又兼火眼金睛识得妖怪,其为人则刚烈勇猛,对谋夺师父者嫉恶如仇,故遇妖时想以先下手打杀为上;而唐僧虽为师父,但属一介凡人,本无分辨人、妖的能力,却又菩萨心肠泛滥,秉持佛家不杀生之训而近迂,所以反而对霹雳手段保护自己的徒弟常有怀嗔教训之心与避祸保身之意,加之耳根软,常听信妖怪的花言巧语或八戒的谗言唆嘴,轻信与刚愎交杂,因而加剧了对悟空的不信任,时常加以紧箍咒的威胁惩罚,形成严重的掣肘,无疑平白地增加了孙悟空除妖行动的难度与成本。这种掣肘,西行之初即已出现。白骨精是第一个蓄意要吃唐僧肉的妖魔,第三次变化相戏时,小说叙道:
行者掣出棒来,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弄个风儿;若要打他,又怕师父念那话儿咒语。”又思量道:“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还打的是!”(第27回)
此时尚在西行初期阶段,悟空已明白妖魔众多、西行不易,故斟酌犹豫,最后发动山神土地来为自己的除妖正义作证,却依然被是非不分的师父赶出取经团队。此后,这种因师父的不听劝告而被掳,让悟空“费心劳力去救他”的情形又发生多次。典型者如过号山,红孩儿的红云出现,悟空两次让师父下马防备已惹恼得师父要念紧箍咒,到见到妖魔所化吊在树上的孩童,更是引得师父一阵“全无有一些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泼行凶哩”的责骂。小说就此叙道:“大圣见师父怪下来了,却又觌面看见模样,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低着头,再也不敢回言。”其后虽明知红孩儿的谎言有诈,却不得不听从师父指令。唐僧被摄走后,孙悟空满心沮丧,说:“奈何师父不听人说。我老孙火眼金睛,认得好歹……你们不识,那师父也不识……(妖怪)想是又使解尸之法,弄阵旋风,把我师父摄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听我说,故我意懒心灰。”(第40回)等到了雷音寺之难,被捆着的唐僧向悟空承诺“向后事,但凭你处,再不强了!”(第65回)言犹在耳,黑松林中又要“善将起来,就没药医”,要救金毛白鼻鼠精变化的女子,弄得悟空无奈地说:“师父既然如此,只是这个担儿,老孙却担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劝你:劝一会,你又恼了。任你去救。”(第80回)这次不听劝告的后果,就是唐僧失陷无底洞,横生一番波折。因此,取经团队中,师父的人妖不分和八戒搬弄是非,平添了悟空的降妖阻力,使其不能攻敌不备一棒打杀,反而导致妖怪掳走唐僧之后以逸待劳,导致大圣攻守易势,不得不屡屡陷入武力与法力间注定受挫的战斗局面之中。
三、作用:情节、人物的多彩与立体
《西游记》在孙悟空的能力表现叙事上,强有强的根源,弱有弱的情理,使小说成就斐然,超越了此前文本所载的取经故事。其艺术作用,可从小说的情节与人物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这种强弱不同的叙事,造就了故事发展的一波三折、步步推进与情节的同中有异、丰富多彩。小说作为叙事文学,故事情节是作品存在与传播的基础。就前期经历的叙述而言,《西游记》补足了孙的学艺过程,又大胆地重复了两次“招安为官——反出天庭——迎战天庭”的叙事进程。具体叙述时则进程似同而情节不一:第一次是出于怀柔而招安,第二次是天庭战败而招安;第一次反出天庭是拂袖而去,第二次则搅散蟠桃与丹元大会;第一次迎战大获全胜,逼得天庭授封“齐天大圣”,第二次惜败于围攻,遭受雷击火炼。而之前的故事文本中,能见到的只是静态介绍孙悟空有铜头铁额的神通,有盗取仙丹仙酒的经历,并无过程的叙述,其所作所为也只是盗窃捣蛋,哪里可与《西游记》步步推进的情节变幻相比?至于跃出丹炉后的大圣,更是一改此前的作战模式,在天宫主动出击,孤身对抗整个天庭力量,进行了一番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大战。这是吴承恩的天才的独创,是孙悟空强悍战斗力的高光时刻,成为展现齐天大圣英雄壮举的重头戏。其精彩程度,足以震撼一代代读者的心灵,时至今日更是屡屡搬上影视屏幕。
至于后期的西行过程,小说是将玄奘西行的本事、传记及文学化了的传说、杂剧、平话中的多种相关或相近文学素材融为一体,叙述一个克服重重苦难求取真经的故事,想象着对灾难、妖魔的化解降伏和殊方异域的游历体验。它沿袭了《诗话》以来的求助传统,但大幅向前推进:不断经历“遇难——救难”的情节模式,此为叙事中的“同”;但在每一难中,会遇到不同的险阻、妖魔、仙佛与法术,每一次斗法、解难、脱困的具体过程叙述又有不同,此为“异”。在“异”的叙述中,虽然初战遇挫,但孙悟空或以智取、或以外援破解对手的法术法宝;所遇妖魔远多于《诗话》、杂剧等,给大圣造成困扰的能力也大幅提高且各不相同,手持钢叉尾藏“倒马毒”的蝎子精、肋下金光的蜈蚣精等法力与动物特征紧密结合的妖怪,让人印象深刻;在对待妖怪法术法宝的过程中,找对了人,手到擒来,找不对人,劳而无功,推动孙悟空上天入地,多方求索,极大地开拓了故事的容量;在战败求胜的过程中,书写了妖魔精怪、神仙佛道的种种异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斗法画面。这些都是此前故事面貌所未达到的境界,而这些故事情节的进步,即令是科技昌明的今天,依然可以满足读者“文似看山不喜平”的阅读期待与大开眼界的想象空间。试想一下,如果还是如大闹天宫那样让孙悟空一条铁棒势如破竹直上灵山,或是还如《诗话》那样让行者师徒不顾对手是谁而全凭锡杖、钵盂大喊“天王”来简单粗暴地过关涉险,或是如杂剧那样任由保官们主动解难而坐享其成,那么小说的叙事进程将大为简化,将一览无余而毫无意趣,怎么会有世本这样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叙事之妙,怎么拥有令读者欲罢不能的艺术魅力和阅读体验?
其次,在强与弱的不同局面下,孙悟空的形象塑造得更为丰富、立体。在表现强的一方面,《西游记》之前的取经故事文本中,展现的是孙悟空偷仙丹、盗王母仙衣等行为,虽然大胆,但更多的只是品行的不端。《西游记》则不然,他重视自己的生命,渴望自由,因而千里跋涉求仙学道;他张扬自己的价值,因天庭的轻贤而公然树起“齐天大圣”大旗,因天庭的慢待而搅散蟠桃大会,孤身杀至玉帝的灵霄宝殿后更是高倡“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奏响了造反者的最强音——“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彰显了其自信自尊的心理与桀骜不驯的个性,其境界明显高于此前故事文本中近于偷儿的猿精“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之流。
西行路上,妖魔法术法宝之前表现了悟空弱的一方面。但他虽然屡遭挫折,而其强者个性仍然一以贯之。对漫天神佛,虽多属有求于人,但他到天庭抱着的是“查勘”的姿态(如查奎星、青牛精等),遇手下为妖的老君,要追问其“钤束不严的罪名”(第35回),问弥勒佛“有个家法不谨之过”(第66回);骂借老君童子为妖考验自己师徒的观音:“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第31回)即使对法力无边的如来,也敢当面讥嘲其为“妖精的外甥”(第77回)。小说在叙其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又书写出其性格的不同侧面。对肉眼凡胎的师父一片真心,“遭魔遇苦怀三藏,着难临危虑圣僧”(第75回);对不听良言的师父自初期的磨合之后,忍辱负重,即使“身回水帘洞”,也“心逐取经僧”(第31回)。对一路的妖魔鬼怪,虽然也多次吃亏,但仍然见猎心喜,主动出击,追寻根底,除恶务尽,又对武艺高强的对手甚至不乏真心赞赏之意、惺惺相惜之情,闪耀着阳刚之美与英雄气质。他固然有很多次是靠四处搬救兵,但也有完全靠自己的机智谋变解决拥有多项宝贝妖魔的经历(如平顶山降伏拥有宝葫芦、幌金绳等宝贝的金角、银角大王)。他“是人间的喜仙”(第66回),遭受挫折时,也曾有过沮丧、委屈、心灰、恼怒等负面情绪,甚至还曾多次落泪,“但,这一哭,却把孙悟空由神、由猴更拉向了人……他哭过之后,不是从此意志消沉,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㉘西行路上他屡战屡败,但同时更是屡败屡战,智计百出,变身小虫或小妖摸清底细、解除敌方所恃法宝,力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并最终取得每一次战役的最后的胜利战果。他的“斗战胜佛”名号,即从心性、方式与结果等方面揭示出这一形象的内核与气质,远胜于平话中所封的“大力王菩萨”。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真性,取经途中的艰难为孙悟空的个性与思想的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小说也借助后期的经历将孙悟空的形象塑造得更为立体丰满。是在事件中展现人物个性,波折中全面塑造人物:他武力与智谋并用,策略共神通并行,他可以被打败,却始终不会被打倒,虽常常束手缚脚却绝不束手无策,虽屡屡受挫反而愈挫愈勇,洋溢着乐观自信、刚猛坚韧的气质,成为百折不挠、奋斗不止的典型。有学者即指出:“在孙悟空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敢于斗争、积极乐观……无疑反映了我们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蕴㉙。他的降妖除魔历程也富有了象征意义,颇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意味,深得读者的认可与喜爱。
梁归智有文解释孙悟空本领的大小之谜,选择从“体制”内外的角度切入,说:“要在体制内获得成功,主要不在个人的好勇斗狠,而在熟悉并利用规则和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有显规则,也有潜规则”,又言“对那些有后台老板的妖怪,还必须网开一面,这是潜规则”,所举例子为第52回收老君青坐骑牛精时,如来有意先败一仗㉚。但小说中孙悟空并不考虑妖怪有无后台的问题,战斗过程中何曾考虑过向妖怪示弱买好以便与其“体制”内的后台搞好关系?该回中,对如来“打狗先看主人面”式的行为,大圣连言:“可恨!可恨!如来却也闪赚老孙!”实则对此类人情世故强烈不满。小说中也多次叙述大圣对妖怪的后台毫不客气地当面讥嘲,哪有体制中人之间的虚伪谄媚或心不和而面和?梁文又言:“有没有明确的‘向善'的意义,就成了做英雄还是做圣贤的分水岭。”㉛孙进入取经队伍,虽然有了改邪归正的色彩,但并不以“向善”而改变其“专倚自强”的英雄手段和放弃除恶务尽的理念。一棒打杀妖怪的态度自不必说,就连本为人身的草寇也是打杀多次,甚至到了已近西行终点的铜台府,“行者欲将这伙强盗一棍尽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伤人性命”,这才放过害死寇员外的强盗们(第97回)。可以说,求佛目标并未改变其“霹雳手段”,既未“慈悲为怀”,更非求贤做圣。因此,无论是梁文所论的体制内外因素还是圣贤目标因素,都不是解决大圣本领大小之谜的所在。梁文在论述细节上也有值得疑议之处,如举大圣降伏层级最高的妖魔之一的例子说:“狮驼国的战斗中,孙悟空本来已经把三个妖魔全都挫败”,以此来说明孙“并不是斗不过妖魔”,“孙悟空的本领没有变小。”㉜但这个情节的转述并不准确:小说中大圣是真的斗不过大鹏怪,灵山哭诉时他捶胸自诉:“自为人以来,不曾吃亏,今番却遭这毒魔之手。”如来也道:“那妖精神通广大,你胜不得他。”(第77回)
李天飞言北方系故事里“猴行者的身份类似一个奴仆”,以最低成本解决问题㉝。世本之前的故事形态中确是如此。但世本之中,孙悟空的身份早已洗去“奴仆”色彩,是推动取经团队前进的主力(甚至还有若干提点唐僧修行的言行,具有导师身份)。吴承恩放弃前期故事形态中的最低成本解决方式,反而是不吝成本、不惮辞费,写活了积极主动的孙悟空,他按照自己的性格行动,勇谋并用,上天入地,“用尽心机……解脱三藏师徒之难”(第78回)。因此,小说的叙事内容更为丰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为成功,也无怪乎世本《西游记》出世不久即成为西游取经故事的“权威”版本而广为流传。除商业性的刊行之外,也很快进入谢肇淛、冯梦龙、凌濛初、袁于令等文艺大家的批评视野,以之作为批判的范本,就虚实、真幻、奇正等观念进行了重要的探讨㉞。甚至“自有传承渠道”的宗教领域里,民间宝卷演说的西游故事在明代时与世本多有不同,自清代中叶前后起则“其故事形态与百回本《西游记》基本一样,两者之承袭关系一目了然”,说明世本《西游记》最终影响到了“特殊的接受群体”㉟。与世本的命运不同,《诗话》、平话等前文本最终被大浪淘沙而只“存活”于专业的研究视野之中。克里斯蒂娃的丈夫、法国先锋作家索莱尔斯曾指出互文性的关键意义:“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㊱《西游记》对此前诸文本故事的更新、深化等整合作用前文已有揭示,世本取代各种前文本使之被淘汰,也正是这种“摧毁”作用的重要表现吧。
结 语
美国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叙事学词典》中曾对“互文性”下过一个清晰易懂的定义:“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㊲其对“关系”的着眼,暗合传统小说研究中对故事流变的重视。也正如学人王凌所论,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动态关联思维可以避免“结构主义封闭文本所造成的认识局限”,使我们“通过发现和建构文本之间的联系来阐释作品”㊳。同样,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文本特点及其叙事策略。通过对《西游记》的文本分析,结合其与《诗话》等各种“前文本”以及宝卷等“后文本”的互文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对《西游记》中孙悟空能力表现强弱变化叙事作一总结:《西游记》关于孙悟空的能力表现的叙事,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小说承袭了取经故事中孙悟空求助外援降妖伏魔的传统模式,又有自己的发展与创新,从注定要成为取经人选的角度在前期的叙事中突出了他的超常能力,又从取经不易的角度在后期的叙事中着重叙述他所遇到的挫折。但不论是前后哪个阶段,除个别难免有所疏漏的情况外(毕竟是百回巨著),小说都是在符合情理逻辑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而将故事叙述得波澜起伏、真实可信,将人物塑造得形象鲜明、内蕴丰富,远超此前各种文本,并影响了后世宝卷、戏曲、影视等领域的西游故事面貌。《西游记》以其变幻之奇、想象之异和人物之美,厕身于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奇书”之列,真乃实至名归。
注释:
① 张世宏《谈小说〈西游记〉的两点结构失误》,《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②㉚㉛㉜ 梁归智《孙悟空本领的大小之谜——〈西游记〉经典探秘之一》,《名作欣赏》2015年第19期。
③⑮㉑㉝ 李天飞《齐天大圣不是孙悟空》,《文汇报》2015年7月31日,第T09版。
④ 壁画艺术对取经故事的传播和对《西游记》成书的推动作用,请参霍志军《甘肃地区“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2期。
⑤⑦⑧⑩ ⑪⑬⑭⑱⑲ ⑳㉒ 朱一 玄、刘 毓 忱 编《〈西 游 记〉资 料 汇 编》,中 州 书 画社1983版,第39、41、43-45、95、105、111、112-113、97、112、50、42页。
⑥㉓ 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⑨ 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⑫ 此处据熊笃先生之说。见熊笃《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兼说〈朴通事谚解〉中所引〈西游记平话〉非元代产物》,《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⑯ 周流溪《互文与“互文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⑰㊱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㉔ 侯会先生认为乌鸡国故事是世本《西游记》刻版之后的增插情节,吴圣昔先生则逐条辨驳了侯文所列凭据,否定“增插”之说。吴文可从。详参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吴圣昔《〈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㉕㉖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228、228页。
㉗ 鲁德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艺术形态学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14页。
㉘ 曹炳建《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民族精神》,《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㉙ 周先慎《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㉞ 请参王齐洲《论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曹炳建《明人的〈西游记〉研究与明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历史演变——论“虚与实”、“幻与真”、“奇与正”三组重要小说观念》,《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
㉟ 陈洪、陈宏《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㊲[美]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p.46.转引自朱安博《朱生豪的文学翻译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㊳ 王凌《互文性视阈下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电影《邱少云》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