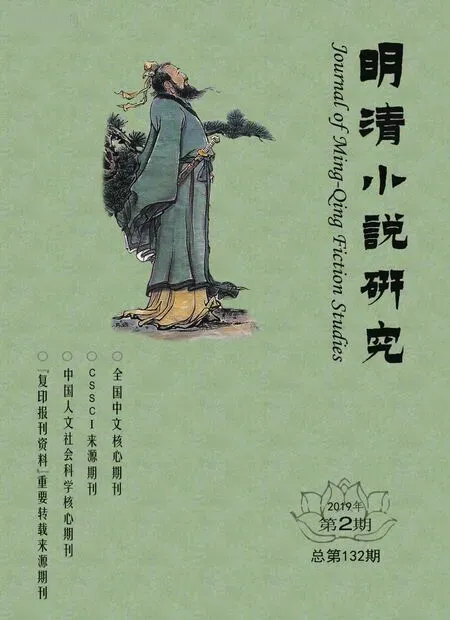试论明清神怪小说审美风格的新变∗
——以《西洋记》《飞跎全传》为中心
·王 昊·
内容提要 明代神怪小说已渐次具有了写实求证、搜奇显怪、歌颂教化三种审美风格,长篇巨制和小说发展,促成了三种审美风格在明代的交融。清代神怪小说既有因袭的承继性,更显示出自觉求新求变的审美追求,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荒诞讽刺。本文选取两部中外战争题材的神怪小说《西洋记》《飞跎全传》正代表着明清神怪小说审美风格的新变,以戏仿的视角加以解读,挖掘其成因及对神怪小说表现领域的拓宽,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中国的神怪小说起源于民俗信仰和神话传说,这使得奇幻一开始就伴随着神怪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一种情节类型和文学结构的手段,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审美风格。至明代神怪小说已经具有了写实求证、搜奇显怪、歌颂教化三种审美风格,并因长篇巨制和小说发展,实现了三种审美风格的相互交融。清代神怪小说既有着审美积习的因循延续,更在求新求变的审美追求下,孕育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荒诞讽刺。本文选取了明清时期神怪小说——晚明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后简称《西洋记》)与清中叶邹必显的《飞跎全传》来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两部小说,是因为它们属于同一题材——中外战争,虽然描写战争,但限于作者对辽阔域外世界的认识还很懵懂,所以均采取了神怪与中外战争相嫁接的方式,同时也契合普通民众的宗教心理。两部题材相同的小说,本应具有相当的承继性,但却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审美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是明代神怪小说审美风格合融性的代表,后者则成功实现了对前者的戏仿,并因此产生了荒诞讽刺的审美风格。明清时期审美风格的新变有效阻拒了审美疲劳的产生,从而展现明清两代神怪小说的特点、价值和意义。
一、合融:明代神怪小说审美风格的新变
到明代神怪小说已经渐次具有了三种审美风格。最早形成的是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写实求证的审美风格,代表作为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干宝被誉为“鬼之董狐”,曾著《晋史》,故在自序中就清晰明了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态度:“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①即在史家小说观的指引下,以亲身经历或亲耳所闻的实录方式来证明神仙五行兼及释氏之存在的真实性,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人生敬信之心。故此阶段的神怪小说是神怪理论与实例验证相结合的产物,真实性是作品最重要的标尺和最严苛的要求,作家的写作态度是极为虔诚和真诚的,并希冀因此带来受众的震动和笃信。此外郭璞通过对《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进行注解,也极力证明怪诞描写的真实可信性;南朝梁代萧绮在《拾遗记序》中亦分析、肯定了志怪小说《拾遗记》的“真实”特点,提出了“纪其实美”“考验真怪”②的主张。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③
进入唐宋,小说家们开始认识到“稽神语怪,事涉非经”④,走上了“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⑤的传奇之路,从而形成了搜奇显怪的审美风格,代表作如唐代段成式的文言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融志怪小说、传奇小说、杂事类小说于一炉。他在《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黥”中写道:“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⑥代表着当时文人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将搜奇显怪视为一种扩充视野、丰富见闻的手段。洪迈在《夷坚乙志序》也自称其创作动机是“好奇尚异”,并欲尽萃“天下之怪怪奇奇”⑦,还在《夷坚支乙集序》中再次表白:“老矣,不复著意观书,独爱奇习气犹与状矣。”⑧并对神怪小说的真实性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夷坚支丁序》中说:“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⑨转而重视其娱乐功能:“圣人所不语,扬子云所不读。有是书,不能为益毫毛;无是书,于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为验,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⑩这使得唐宋元时期的神怪小说并不着意构建婉曲摇曳的情节来感染读者,而是浓墨重彩地用力于故事情节中令人瞠目结舌的部分,以满足自我炫奇和读者好奇的心理特质。
明代,进步文人的积极倡导、小说的商品化及读者群的改变与壮大,导致了通俗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勃兴,这使得他们对神怪小说的创作态度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特别凸显神怪小说中所富含的婉曲动人、发人深省的讽喻意义,甚至在故事结尾频频用卒章显志的方式来直接宣明自己所要伸张的教化意义,从而使神怪小说具有了歌颂教化的审美风格。突出表现在明代专门为佛道人物立传的小说类型——宣教小说。代表作如朱鼎臣的《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开泰的《达摩出身传灯记》等。虽然这类小说意在传扬佛道人物对于戒律苦行奉守的坚韧不拔,显示宗教所具有的感召性和教育意义,但这些戒条往往融合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淫人妻女、贪财好利这样的丧德败行不但佛道不容,儒家亦不齿,这显示出很强的三教圆融性。
同时我们看到明代长篇小说成为创作主流,小说具有了足够饱满的叙事时空,这使得神怪小说三种审美风格开始融合。当然这种合融性更是长篇通俗小说四种题材类型相互融合在神怪小说内部的显现。元末明初产生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已经包含有“关公显圣”“九天玄女赐天书”这样的奇幻情节;世情小说的代表作晚明《金瓶梅》和清中叶的《红楼梦》都有幻境的描写,并且这些情节“往往成为寓言,暗示着天意或者命运,为小说情节埋下伏笔,在结构上蕴含着推动人事演变的深层动因”⑪;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直接推动着神怪史话小说的诞生”⑫,孙悟空成佛之路浸染着浓厚的英雄传奇的色彩,小说更是在“极幻之文中,含有极真之情;在极奇之事中,寓有极真之理”⑬。服务于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四种题材类型实现了相互交融,从而促成了神怪小说审美风格内部的汇融,下面以《西洋记》为例析之。
首先,《西洋记》原名《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不仅是命名上沿用‘演义'一词,而且在实际写作中也沿用‘演义'体例”⑭,它所描绘的是太监郑和受明成祖的派遣“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承袭了神怪小说写实求证的审美风格。从中我们能够解读出中国人对于“化外之邦”的强烈探索精神。在第九回张天师就向永乐皇帝指出:“天覆地载,日往月来,普天之下有四大部洲:一个东胜神洲,一个西牛贺洲,一个是南膳部洲,一个北俱芦洲,陛下掌管的山河,就是南膳部洲。”⑮在第十四回中又由金碧峰长老历数下西洋的路线:“南朝去到西洋并无旱路,只有水路可通……”⑯,并奉上海外地图小经折儿,“上船处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转过来就是金山”;“过了金山,就出孟河,前面就是红江口;过了红江口,前面就是白龙江;过了白龙江,前面却都是海。舟船往南行,右手下是浙江、福建一带,左手下是日本扶桑,前面就是大琉球、小琉球。过了日本、琉球,舟船往西走,右手下是两广、云贵地方,左手下是交趾”⑰。接着过“软水洋”“吸铁岭”,“软水洋以南,还是南膳部洲,软水洋以西去,却是西牛贺洲了,就却叫做西洋国。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国是一国”⑱。虽然这些地理描述还存在着很大的含混不清,但已显示出中国人对传统天地观念的突破,是对域外世界认识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小说中对郑和一行人途经的国家和地区的航海路线、风土人情、物产民风,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都做了详尽的记述。此外在小说情节内容上也具有效仿《三国演义》的“演义体”性质,构成全书主要内容的是一场场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事,全书主要人物也在征战中次第登场亮相。所以《西洋记》有很浓重的历史成分,具有“演义体”极强的实证功能。
其次,《西洋记》延续了自唐以来的搜奇显怪审美风格,集中体现在异域邦国的展现。《西洋记》恪守着古典小说两个重要的审美元素,一个是情节曲折,另一个是语言雅致。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西洋记》可谓匠心独运,新意迭出,突出表现在两点:第一是对域外光怪陆离世界的描写。作者不单写出了异域洋洋大观的进贡宝物,如西南哈失谟国的青狮子、正南真腊国的白象、西北撒马儿罕国的紫骝马等,更描写了人所罕知的异域风土人情,如三十二回的金莲宝象国,其国没有纸笔,用羊皮捶之使之薄书之。国中“若争讼有难明之事官不能决者,则令争讼二人骑水牛过鳄鱼潭,理屈者鳄鱼出而食之,理直者虽过十馀次,鱼亦不食”⑲。国中婚事,男子先入女家成亲,十日半月之后,方迎入男家;有国王当贺之日,用人胆汁沐浴,将领以下,俱献人胆汁为贺。第二是小说的情节更构筑得神乎其神,异想天开,创造出许多新鲜奇妙的小说意境,明知是虚幻,却产生了一种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艺术效果。虽然很多章节都是神妖斗宝、佛道斗法,人神斗艺的场面,但是却写得变化多端,并不雷同。最突出的就是王明盗宝,所盗之宝每次各有不同,盗法又各自相异,如此多变求新,使小说的艺术魅力增色不少。
再次,作者借助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实,融合了民间传说,用丰富大胆的想象,大量展示了异邦国度的奇风异俗,珍奇物产,让人称奇惊叹,但《西洋记》的主导情感却饱含着很强的时代性,即通过颂扬这桩王朝往昔的盛事,表达他对于国家复兴、重振朝纲的强烈心愿,高扬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华尊夷贱”观念,代表着明代神怪小说歌颂教化主要的审美风格。《尚书·禹贡》中已经有“九州”“五服”的记载,稍后的《周礼·夏官·职方氏》更将“五服”扩展为“九服”,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华尊夷贱”观念,成为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即使利玛窦带来了《舆地山海全图》,也从未动摇过国人的天下观,《西洋记》即是一个明证。作者生活的明代万历年间已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尤其是海患日烈,葡萄牙不断在广东沿海滋扰,进而强占澳门,倭寇在南方沿海的侵犯也日趋白热化,这使得寓居江南的罗懋登无时无刻不强烈地感受于心,所以在歌颂的背后更隐含着作者对海事危机的深深忧虑和对传奇英雄的极度渴慕,他既希望执政者能够在海上发愤图强,消弭海患,以此来重振国威,更呼吁像郑和、王景弘这样的勇猛将帅决胜海域,驱除外辱。虽然作者心中对此充满了极度的迷茫,在小说的末尾并没有让郑和一行找到传国玉玺,似乎隐喻着梦想难圆的无奈和悲概,但这无损整部小说的叙述重点是郑和一行过关斩将,历经三十九国磨难,一直走到了“极天之西,穷海之湄”的酆都鬼国,所遇各国均呈上降书顺表,贡献了大量异域珍宝,极大地宣扬了中华帝国的“圣教伦理”,把“抚夷取宝”的上邦情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作者不单宣扬了“皇风宣畅西夷,夷而慕华,莫大之益”⑳的思想感情,更不断地强化着“华夷之辩”的观念,这充分的表现在:“其一,地理位置中心论,即‘中国据内,为君为父;夷狄居外,为臣为子'。其二,中国民俗优越论。中国上邦,物阜民丰;蕞尔小国,野蛮贫穷。其三,中国人种优越论。”㉑以此鼓舞人心,激发斗志,弘扬天朝中心主义的盛大情结,凸显了“华贵夷贱”的思想感情。
可见随着长篇小说自明代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小说的表达空间极大扩充,题材类型相互交融,这为神怪小说的各种审美风格能够相互配合、协调统一提供了条件,并在《西洋记》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这使得《西洋记》既凸显了明代神怪小说的主要审美风格——歌颂教化,又兼容了前代神怪小说写实求证与搜奇显怪两种审美风格,并使之服务于主要审美风格,前者为小说提供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使歌颂教化具有了深厚的基壤;后者为小说织构了摇曳的故事情节,使歌颂教化不断地弥厚升华。三者共荣共存,主次鲜明。
二、荒诞讽刺:清代神怪小说审美风格的新变
进入清代,神怪小说的审美风格既得到因袭,又有了不断地创新,这既是小说作者不断追求的结果,从接受美学角度,这也符合审美积习与求新求异之间的平衡,从而在清代神怪小说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荒诞讽刺,这一审美风格突破了传统审美观和价值观,具有了“解构主义”的色彩。我们以《飞跎全传》对《西洋记》的戏仿,来解读这一审美风格。表面看来,《西洋记》与《飞跎全传》两部小说的承继性是很明显,虽然《飞跎全传》的中外战争完全出于虚构,但中华天子依然大胜海外天子,飞跎在两军阵前风光无两,最终受封跎王衣锦还乡,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皆为三教中人,共同高扬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旨趣。但细读之下,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西洋记》所恪守的传统小说两个重要的审美元素——情节曲折和语言雅致——在《飞跎全传》中全部被突破了。《西洋记》用完整清晰的故事情节、深刻生动的人物刻画、雅驯瑰丽的语言,以此照应着读者的审美期待,传达着作者热切盼望国家荣昌的思想感情,而《飞跎全传》却反其道而行之,小说通篇用扬州方言写成,甚至是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讳,加之灵活运用那些有别于故典的成语,作者将它们或赋以新意,或用其借义、转义,或望文生义,妙笔成趣,使文字分外精神,并配合运用了比喻、夸张、断取、返源、巧缀等大量的修辞手法使得作品在叙事写人时,产生新奇、滑稽、风趣的效果,常令人忍俊不禁。《飞跎全传》以异化、戏谑、对反的手法实现了对《西洋记》的整体转化,这使得两部小说呈现出了戏仿的关系,《飞跎全传》在源文本《西洋记》的基础上借助巨大的戏谑张力实现了其超文性的建构,从而将饱含在记忆文本中“华贵夷贱”大国宣言彻底抹消解构,正是这种戏谑性的仿拟是形成荒诞讽刺审美风格的根本原因和生发机制。
首先《飞跎全传》将源文体式《西洋记》中的义理赋予了另类意义,突出表现为人物形象和情节套路的义理关系的置换。作者通过对主人公飞跎的塑造,用这个表面化挫蛮敌、扬国威的故事,颠覆了英雄传奇小说的题材,诙谐地把英雄事迹和势利小人强硬地扭结在了一起,将外在的可笑与内在的可笑完美统一在了一起。看事迹,石信乃上界想空星临凡,本是一无名小辈,却在悬天上帝那里习得一身高强本领,成为两军阵前的常胜将军,直至封王拜侯,何等风光;论品行,他确实一个投机钻营、唯利是图、吝啬贪婪之徒。形容残丑的跳跎子,因吃了悬天上帝的仙丹生了肉翅,故书名又称石信为飞跎,而“飞跎”一语乃扬州土语,焦循《易余龠录》卷十八云:“凡人以虚语欺人者,谓之跳跎子;其巧甚虚甚者,则为飞跎。”㉒就是其本名作者也语多嘲讽,石信,字不透,实则是石心,隐喻其铁石心肠,石信谐音“失信”,直指其薄情寡义,人格猥琐。正如飞跎其名的涵义,这使得无论在之后的情节里面,他做出何等英雄的丰功伟绩,都跳不出小人发迹的窠臼。此外《飞跎全传》以其诙谐幽默的语言颠覆了古典章回小说所惯用的情节和题材上的模式,邹必显通过对腊君及文武百官的描写,消解了传统小说忠奸对立的情节模式。腊君及其臣僚构成了对中国帝国的明显的指代象征,这使得他们本应被塑造成为贤君能臣,光耀千古,但恰恰相反,从小说的第一回,作者就用极其龌龊的笔触彻底地瓦解了国君的威严,臣僚的贤明。国君称为“腊君”,宫殿叫做“无底殿”,喻其贪婪,其收宝物、扣殿下不耻行径被海外天子斥为“腊手太重”,这使得“腊君”其名其行很容易让人从“腊”联想到“辣”,借以揭露国君残暴无德的本性。随之作者又将其言描写为“张开臭口”,“与诸臣说难入肺腑唧唧话”,其容刻画为“头戴一顶怒发冲冠,身穿一件劫龙袍,腰系一条硬担带,足下登一双圯桥三进履,一副密脸,两道乌眉,一双推巴眼,小小的一个细闷鼻,两个软耳朵,一张油花嘴,满嘴稀面胡”㉓。这幅令人喷饭的言谈形容,足像一个跳梁小丑。常在小说中美化英雄人物的上星临凡,在小说中被作者写作屎迷星、没良星、鹦歌鼻子称钩星等一帮辅佐腊君的“穷文富武”们。作者在揶揄讽刺中将君王的崇高形象、百官的威严气势在起始处做了彻底的消解,从而使小说中失去了代表正义的国家形象,这场战争也就成为了无义之战,跳跎子所报效的不过是一个早应气数丧尽的朝廷,这使得正邪对立的中外战争在一开始就没有了意义。
其次,《飞跎全传》在义理置换的基础上,实现了极速矮化的艺术效果。在《西洋记》中无论是金碧峰长老、张天师还是永乐皇帝、郑和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圣化色彩,这些形象的神圣性也契合约定俗成的审美规范和大众心理定式,但在《飞跎全传》中所谓的君主和英雄被“瞬间抽掉了神圣脚下的崇高圣坛,从而享受急速心理落差的刺激和快感”,这就是“极速矮化”㉔的艺术效果。君与臣、神与人、师与徒之间的等级和尊严被瞬间剥离,这必然赢得自由开怀的大笑,“极速矮化”在小说中表现为到处充斥着不和谐的笑。《飞跎全传》中的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滑稽的笑,二是怪诞的笑。先看滑稽的笑,主要体现在东拼西凑、信手捏来的语言。有韵律的扬州方言使得小说充满了魔术性,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紧守的严密的语言逻辑性,让人们在阵阵讽刺的笑声中享受到了充分的自由,“胡说八道的废话歌谣和散文扩大了感觉的范围,打开了逻辑和钳制性常规之后的自由的远景”㉕。以第二回富家郎应邀至跎子府上赴宴为例,以富家郎之眼看跎子家居陈设,跎子家门名叫“半开门”,此语原有妓女之意;家中的对联分别是“门当户对”“遥遥相对”和“与你不对”,柱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桌子是“安分守几”,“几上摆了一只找金瓶,瓶内插了几枝眼前花”,椅子是“不得而椅”,堆的石头是“吃白石”,烧的炭火是“自改自炭”等等。小说中的双关也颇有意味,如哈元帅的大帐名叫“混帐”,既达到了关合的目的,又收到了异常的讽刺效果。而作者在应用词语的巧缀时,又常常把两个或多个语体风格截然不同的词语粘连起来使用,或故意运用和语境相悖的方言、俗语,造成语境和词义之间的背离,如“怕老婆的都元帅”“歪嘴经”“绕门经”“杂板令”等,既消解了描写对象的庄严性和神圣性,又达到了嘲讽揶揄的目的。此外,作家还将语言和行动的自相矛盾性极端化,突出表现在十二回至二十九回的两国大战,如当脱空祖师用愁山来压悬天上帝的时候,悬天上帝却说“我头顶磨子不觉重,头顶尿泡不觉轻”㉖,用一句俗谚轻松化解了命悬一线的紧张斗法,也在笑骂中让读者忘却了中外战争原应有的雄壮与凝重,因为滑稽,战争反倒让读者觉得亲切,闹剧般的语言已经无法引起人们对于战争特有的激荡崇高的情感。
再看《飞跎全传》怪诞的笑,如果说滑稽的笑让人感到轻松与活泼,那么怪诞的笑则带给人恐怖与痛苦。弗·施莱格尔在其《关于诗的谈话》中认为“怪诞是这样形成的,即形式和内容的尖锐对照,不同因素的随意混杂、相互矛盾(既可笑又可怕)的爆发力”㉗,所以“怪诞可以作为一种真实地表现现实世界的新方法”㉘,从而形成“矛盾性反常”㉙的艺术效果,表达出了可笑更可怕的人类生存的荒诞性。怪诞中蕴含的丑、怪、恶的成分,它的矛盾性和悖谬性使其具有了两种审美意蕴。第一种是幸灾乐祸的笑,在小说中突出表现在对飞跎畸形外貌和丑陋名字的描写上:“此人姓石,名信,字不透。娶了一房妻子混氏,小字叫个混世虫儿……这石信生来是一个钱虫,没窟窿钻蛆,忽然得了一个牙疼不是病,请了一位好好先生,叫做贾大方脉,来家医治。好好先生用了一剂蜜饯砒霜,将钱痞虽然医好,背上不觉高出一块,竟成了一块呆肉。左脚又被人弄了个二起腿,却短了三分。故此人叫他个跳跎子。”㉚《荷马史诗》中赫拉的跛儿子赫准斯托斯与赫准斯托斯发现妻子阿夫罗狄谛和战神阿瑞斯私通的两个故事,“由此诞生了两个最主要的永恒的笑的主题:生理上的缺陷和感情上的不幸”㉛。这种笑声源于我们自己的优越,“凡是我们看见或者听说别人有些微小的不幸,但非惨痛的或致命的不幸,例如,肉体的丑陋,或心灵的愚昧,只要它不是或者相信它不是在我们身上,这就会使我们愉快或者发笑了”㉜,显示出人本性中的无关与无情。
第二种是恐怖痛苦的笑,《飞跎全传》继承了搜奇显怪神怪小说带来的娱乐性,并将其极端化,使之具有了怪诞的娱乐性。阅读之下,使其感官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集中表现在将明君贤臣异化成为跳梁小丑,但笑过之后恐怖悄然滋生,在这失去了亮色的叙事中一切不复再有生机,笑过之后,感受到的却是了无希望的恐惧和痛苦,笑成为了人们无力摆脱苦难的防御。这也使得《飞跎全传》和其他的讽刺喜剧有了很大的区别,在讽刺喜剧无论作家多么无情的鞭挞社会与人性的丑恶,往往会加入一些肯定性的因素,包含着作者对人生、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但在《飞跎外传》中荒诞的笑声铺天盖地,但因失去了明暗的鲜明对比,最终却只能归于苦涩,“真正的幽默需要的就是感受性。我们将会发现,幽默与某种特殊的忧郁有关联,当然,不是指那种强烈的忧郁,而是发自忧郁的感伤与对世道堂吉诃德式的沉思默想”㉝,在笑声背后透出了时代与人生的荒芜与苍凉,“既想笑,又害怕,既惊恐万分,又忍俊不禁”㉞。怪诞的笑,也不再仅仅地指向外向性的嘲他,从小说完全取消的忠奸对立情节模式来看,这更显示出内省性的自嘲。如果说传统讽刺喜剧,是用理性来抨击非理性、反理性,那么《飞跎全传》却用荒诞、放浪的笑声,以非理性来挑战理性的缺陷与漏洞,质疑着时代和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飞跎全传》实现了对《西洋记》的“转述者变调”。《西洋记》中“华贵夷贱”大国情感与忠奸对立的情节模式已经被经典化和众所周知,邹必显却不甘如此,他用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重新诉说,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取消了中外战争中的正邪对立,跳跎子所报效的不过是一个早已气数丧尽的朝廷,也就架空和消解了《西洋记》中高扬的“华贵夷贱”的华洋观念,在“转述者变调”的状态下实现了对源文方向和语调的彻底改变,正是转述者的变调保证了戏仿的效果,使得行文中充满了“讥刺、夸张、挖苦的语调”㉟。深入时代和作者去探寻这一审美风格出现的原因,我们发现邹必显生活在文网高张的大清盛世,但却敏锐感觉到了世事殆将有变的征兆,使其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精神自觉。虽然对作者我们如今已知之甚少,但是从他嬉笑酷辣的文字,我们可以寻出他对于底层百姓生活的熟知,他的敏感与正直,他对于社会不公和人性龌蹉的深入细致的感喟与反思,深刻的社会批判显示着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的良知与担当。清政府的文化专制和政治喑哑,使得文人不能在文学世界中自由地俯仰吞吐,只能把目光投向神鬼的世界,释放自己的孤独与压抑,显示出强烈的人文精神,表达出了正直文人在一个盛衰交替之世的敏感与悲痛,在哀世中强烈困惑、怆痛、忧愤的生命体验。
这与同时代的很多有识之士形成了呼应,如龚自珍、黄景仁等。目光如炬的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借用春秋公羊学的理论,将历史分为治世、乱世和哀世三等,哀世即表面繁荣内里已经腐烂的状态,并发出了“起视其世,乱世竟不远矣”㊱的疾呼,至晚晴,残败的景象已不可收拾。正是这一前瞻和敏锐的思想,使得邹必显突破了一以贯之的华夷观念,在小说中颠覆了“中华优越论”的传统华夏观。夷族入主中原,华夷界限变得暧昧不清,这不仅在国人的心目中起了明显的变化,即使在外交方面也有显现。在清朝的宗藩关系上,能够清楚地看出明清两代之间的显著区别,如朝鲜贡使团将出使明、清两朝的记录分别命名为《朝天录》和《燕行录》,可见朝鲜只认同清帝国是“大国”,而非“天朝”㊲,从而形成了朝鲜“一边事之以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㊳两重性的对华观,这使得“明清易鼎的世变,让所谓‘天朝'名存实亡,以‘中华'为主的文化纽带就此断裂,东亚诸国不再以清帝国作为中华世界秩序体系的中心”㊴,这使得有识之士,很难把胡皇虏主奉为上国,邹必显在小说情节中将“天朝大国”的威严化为虚空成为一种必然。
三、明清神怪小说审美风格新变的意义
神怪小说自诞生走过了神怪以实、神怪以奇、神怪以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熟于魏晋南北朝的写实求证的审美风格,代表着作者和受众试图在宗教中求解脱安慰、存憧憬期待的审美体验;第二个阶段在唐宋孕育了搜奇显怪的审美风格,“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㊵;最后一个阶段则在明清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歌颂教化与荒诞讽刺。晚明的《西洋记》代表着神怪小说写实求证、搜奇显怪、歌颂教化三种审美风格交融,并凸显了明代神怪小说的歌颂教化的主导审美风格;清中叶的《飞跎全传》通过对《西洋记》的戏仿,诞生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荒诞讽刺。《飞跎全传》用放浪的笑声完全解构了《西洋记》中高扬的“华贵夷贱”中华优越论,取消了孰优孰劣的比较,帝王将相、神仙菩萨与我们已没有了心理的距离,英雄与神圣荡然无存,使得我们必须直面荒诞的存在,“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消蚀,思考回味也没有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心理距离消蚀之后,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和幻觉的原本过程便得到了重视”㊶,作者将时代中的每个人裹挟进这荒诞的世界,这使得笑声具有了自我嘲讽式的幽默,笑的底色是悲观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指向一种超脱和彻悟。这使得《飞跎全传》既不同于传统的悲剧,人们在苦难中见证着崇高,激起人们强烈的生命感,导人奋发,实现“悲剧精神的实质是悲壮而不是悲惨,是悲愤而不是悲凉,是雄伟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志消沉”㊷的审美效果。《飞跎全传》消解了悲剧精神,以直喻的方式将时代与人性直接冲入我们面前,以极端的喜剧性挖掘出巨大的悲剧内涵;也不同于传统的喜剧,它将喜剧中的非常态因素彻底化,小说中从头到尾、随处可见的是小丑式的人物,异化为非人,阅读中人们看不到任何与之对比的充满希望的人物和情节,使得这种彻底化的非常态获得了惊世骇俗的审美效果,小说中丑陋与蹩脚使我们产生了极大的间离感,阻碍了认同感的产生,初见之下不由得放声大笑,继而这笑声却透出了可悲和可怕的意味。《飞跎全传》中这种悲喜观念的交融,将之视为喜剧,它却笑中透悲,将之视为悲剧,它却悲随笑出,体现出复杂审美意味。
虽然二者审美风格大相径庭,却都饱含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神怪以实的阶段,无论歌颂教化还是荒诞讽刺的审美风格,都凸显出作者创作神怪小说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使得“不平则鸣”“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成为神怪小说创作强劲的思想动力,尤其体现在《西洋记》《飞跎全传》这类个人著述型的神怪小说中,正如汪寄《希夷梦自序》言明自己编撰该书时云:“援前证后,虚诞而不支离;进正退邪,褒贬符于经史。稀奇古怪,事之所无,而理之所有;深奸隐恶,法所不及,而情所不容。”因“凶猾为之寒心”而才“壮气”以“信腕抒怀”㊸。借神怪以言情畅怀,自我排遣成为神怪小说创作的主流思想,这标志着神怪小说创作由人被神怪所吸引过渡到了神怪为人所用的新阶段,实现了对神怪的脱冕。
同时我们注意到世情小说开山之作《金瓶梅》立意的改变是促成两种审美风格裂变的根本原因。在《金瓶梅》之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立意总在歌颂,《西洋记》正是在这样一种影响下,将思想感情定位在歌颂教化上,小说中充满着砥砺昂扬的奋发之情。《金梅瓶》则意在暴露,用冷静客观之讽刺手法,揭露人世间之假、丑、恶,这直接促成了《飞跎全传》荒诞讽刺的审美风格。但我们同时注意《飞跎外传》中的讽刺手法又与《金梅瓶》《儒林外史》决然不同,鲁迅对《飞跎外传》相类的《斩鬼录》评价为“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起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㊹,这被后代很多研究者延续。我们看到作者选择直讽首先是服务于小说巨大的喜剧效果,正如《飞跎全传》题序中所描写的作者个性:“与诸同人袭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一时闻者,无不哑然失笑。”㊺邹必显的创作意图首先指向的是这种喜剧的效果,并借助凸显其讽刺艺术;其次《飞跎全传》中的直讽较之《儒林外史》中的婉讽借助精确的白描,通过不和谐的人与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婉讽,具有直揭老底、洞穿对象恣意的讽刺效果,正是它与荒诞的完美结合,将这种借题发挥、东拉西扯却又深蕴人生失意、社会不平之气痛彻淋漓地表现出来,实现了“从神魔小说中脱胎而出的一个重要契机”㊻,使得小说呈现出“看去荒诞无稽,思来事在身边”㊼的艺术效果。
在神怪小说中荒诞与讽刺的深度结合,既使神怪小说内部实现了超越,小说家不单去除了对史话的依赖,更去除掉了对自古有之奇幻的依赖,让神怪世界成为荒诞讽刺辗转腾挪、任意挥洒的天地,荒诞讽刺成就神怪小说急速直抵生活本真的痛快淋漓,在看似毫无逻辑的荒诞世界中,讽刺指向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建构;又促使长篇通俗小说描写重心实现了再一次的变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强调情节的传奇色彩,这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西洋记》中;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描写重心则由讲故事到了写人物,在平凡和细腻中对人物进行了精雕细刻;《飞跎全传》的描写重心则是语言,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完全服务于语言的高度戏谑性和反逻辑性,将语言的滑稽和讽刺发挥到了极致,既体现了充实饱满的形式与极度空虚的内容之间的悖谬性,又借神怪世界抨击了人世和人性的假、丑、恶。《飞跎全传》中的语言堪称语言的狂欢,颠覆了语言自身的逻辑,更改着语言自身的所指方向,使其语言成为游离开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之外的纯粹的话语乐趣,只“言说”,不“说事”,语言成为小说层出不穷的笑料与润滑剂,这使得小说的叙事明显带有幼稚化的倾向,形同卡通作品,在小说伊始一切美丑爱憎就一目了然。小说的内容和主题亦呈现出简单化和程式化,却服务于凸显了戏谑性语言酣畅淋漓艺术效果的目的,使语言狂欢的魅力得以扩张和放大。这种狂欢的语言使得语言所指的鲜活性被挤压和榨干,语言的能指因此变得具有了机械性,这种机械性正使得语言获得了极具跳跃性的节奏,表现在小说中大量一次性出场的人物,如贾斯文、白赖、圆和尚、扁长老等,这样的人物形象完全被戏谑性的语言所冲淡、压倒和湮没。可见小说家所关心的不再是表达的对象是否真切,而是语言的狂欢是否达到了极致。
清代围绕着荒诞讽刺的审美风格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呼应的神怪小说,如《何典》《平鬼传》《斩鬼传》等,喜用俚言土语,热讽人情世态。“神怪小说发展到了清代,已经呈现为一种少有依傍传说,神话为基础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形态”㊽,它们继承了之前小说的神魔鬼怪,玄特奇异之事,抛弃了之前依傍历史及其传说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极大地加强了自由性,在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情景安排、象征取喻等方面突出人格化,正如鲁迅在《何典》再版的《题记》所说“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亦如古典”㊾,“五四”学者刘复亦评论:“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㊿这些小说明显的嗜好就是把人性和人世的丑陋和不堪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暴露出来,神怪已经成为这些小说的虚壳,人世和人性的写实才是这些小说的灵魂,它们意图在彼世和此世之间建立那种可怕更可笑的平行对应关系,虽然这些写实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夸张和变形,但这皆服务于小说要达到的那种诙谐大笑的艺术效果。这种喜剧式的荒诞讽刺神怪小说,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往往能容纳谴责小说、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甚至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种种因素,神怪促成着这些因素的勾连和调合,神怪的爱恨离合、欺骗和出卖亦如人世之所为,可见神怪的世界已经被人伦法理所统治和驯化。同时我们看到神怪小说审美风格的合融性在清代仍继续发展勃兴,代表作为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虽然单只短篇往往集中凸显一种审美风格,如《梦狼》,白姓老人梦中满是狼和白骨的衙门无疑具有极大的荒诞讽刺意味,但从小说集整体上来看,却显示出合融的趋势和特征。
结 语
《西洋记》中的庄严整饬、奋发向上,与《飞跎全传》中的支离破碎、狼藉一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代表着明代三种审美风格的合融与交汇,高扬着“华贵夷贱”华夏优越论;后者则体现着对传统语言观的背弃,直接放弃了语言作为传达价值的功能载体,显示出“向着早期非语言”的回归,取消了语言逻辑的严密性,从而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失去了必然的因果联系,这颠三倒四的叙事使得我们尽情的欢笑,但这笑声却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饱含着痛苦意味的幽默,这昭示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失序,已经无法衡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袭来的阵阵痛苦和恐惧之后,只能用笑来安抚受伤的灵魂,并让它去蓄积反抗和重生的能量与希望。
从合融性到荒诞讽刺,明清神怪小说审美风格的变迁,不仅是对时代巨变、作家创作心路的深刻反映,更显示了神怪小说在集大成的基础上,自觉求新求变的发展趋势,具有着时代、作家和小说史的多重意义。《飞跎全传》以群魔乱舞的视角对人性的龌龊与虚伪,人间的不公和腐败发出了阵阵讥笑,这笑代表着一种彻悟、一种禅味、一种解放和一种反抗,用荒诞的方式让人跳出思维的惯性,去破除更大的荒诞,以邹必显为代表的进步文人形而上精神上的反思与超越,这是对传统理性与封建秩序的反叛宣言,也无疑建构着一种新的理性,正是作者这种深沉的情感为晚清出现一批特立独行,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蓄积了思想的能量,为近代“现代性”的开启奠定了基础。荒诞讽刺的神怪小说,因极契合晚清的社会景状,得到继续的放大和加强,如《立宪魂》,将指斥矛头直指1906年清廷自编自导的一场立宪闹剧,以阎罗派阴间使节的海外立宪考察指斥了这场改良运动的无稽,显示着这类神怪小说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 [晋]干宝《搜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② [晋]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③㊹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98页。
④⑤ 林烨、王淑艳选编《唐传奇新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9、52页。
⑥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⑦㊵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修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187页。
⑧⑨⑩㊸ 丁锡根《中国小说序跋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96、1438页。
⑪ 陈迎辉《幻: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审美形态》,《齐鲁学刊》2014年第4期。
⑫ 林辰《神怪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⑬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⑭ 李建武、尹桂香《〈三国演义〉对〈封神演义〉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⑮⑯⑰⑱ ⑲⑳ 罗懋 登《三宝太 监下西洋记 通俗演义》,昆仑出版 社 2001 年 版,第95、147、148-149、150、335、1042页。
㉑ 沙宗平《从罗慰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看明代之中华文明中心论》,“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㉒[清]焦循《易余龠录》,江苏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874页。
㉓㉖㉚㊺[清]邹必显《飞跎全传》,《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飞跎全传》《七真祖师列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1、9、2页。
㉔ 赵宪章《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
㉕[英]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华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㉗㉘㉙[美]A·P·欣奇利夫《荒诞·怪诞·滑稽——现代主义艺术迷宫的透视》,杜争鸣、张长春、赵宁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58、175页。
㉛[法]让·诺安《笑的历史》,果永毅、许崇山译,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㉜ 阎广林《历史与形式: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喜剧、幽默和玩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㉝㉞ 孙绍振《幽默基本原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3页。
㉟[德]列欧·施皮策尔《意大利口语》,来比锡,1922年。转引自《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5页。
㊱[清]龚自珍《龚自珍文选》,谢飘云、闵定庆选注评点,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㊲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㊳[韩]李在学《燕山纪事·利》,[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9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77页。
㊴ 尤淑君《“华夷之辨”与清代朝鲜的事大政策》,《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㊶[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页。
㊷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㊻ 胡胜《从“侈谈神怪”到“揶揄世态”—钟馗系列小说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
㊼ 林辰《中国荒诞小说及其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㊽ 李保均《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㊾㊿ 张南庄《何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关于藏译名著《水浒全传》中的人物绰号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