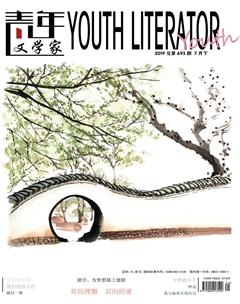欲望的尽头,是毁灭还是重生?
摘 要:渡边淳一的《失乐园》自出版以来,有过多种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源于作品自身所带来的双重话语,其中道德话语和人性话语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冲突构成一种欲望的矛盾。本文试图通过对人性和欲望的探讨,从马尔库塞新感性主义与日本耻感文化视角下去认知分析《失乐园》中关乎欲望、婚姻、爱情和性之间相互的内在联系,并对此做出自己的阐述。
关键词:失乐园;马尔库塞;耻感文化
作者简介:任程宇(1995-),男,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8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2
渡边淳一的创作极富时代特色,其作品多是介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中间小说”,他同时继承了日本情色文学传统,成为了一个“情痴主义”者。其作品在体现现代新型情感伦理的基础上回归日本传统感情文化,并将二者深刻的结合起来,极大程度上诉说了渡边淳一内心对于欲望和人性认知。
《失乐园》是渡边淳一理念阐释的代表作之一。渡边笔下的婚外情是一个看似凄美、悲凉的爱情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更是以一个全新视角在探究现代社会人生存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种种抉择。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以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为例,从马尔库塞新感性主义视角和日本耻感文化方向出发,探讨在欲望面前所展现的人性的复杂面。
一、欲望解放——人性的回归
从亚当夏娃被诱导食禁果伊始,欲望就被深刻地写入“人类”这一物种的基因代码中,作为人的本能而呈现。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的全面工业化推动人类文明到达了全新的层面,愈来愈多的思想家、人类学家致力于现代性的精神批判研究,既不断回到前现代的心灵生活开始以寻求历史性支撑,也深入到后现代的人生意义追求。马尔库塞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认为在内在精神的欲求世界中,爱欲解放可以消除文明的压抑。在他看来,爱欲是人的本质需求,而在《失乐园》中久木和凛子的爱情悲剧正是一场在本能欲望驱使下由身到心的沦陷。
久木和凛子两人最初各自背离家庭的在一起是源于欲望和性,初衷是借助欲望和刺激所带来欢愉的精神快感来暂时逃避现实中的不如意。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在欲望的等级上步步深入,精神世界与难平的欲壑世界逐渐交缠。这份欲望被不断扩大,从最初的性欲逐渐蔓延到精神层面,包括食欲、享受、占有欲等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
弗洛伊德理论中广泛提到了性欲这一概念,既指异性间对生殖至上的肉欲追求,又指人类追求快乐的力比多性质的普遍表现形式,为了区分前者,他称后者为爱欲。而马尔库塞则认为性的欲望仅是爱欲表现形式中的一部分,性的欲望的满足只能使人类在局部上获得短暂的快感,但是爱欲能够使人长时间、更加全面的陷入在快乐之中,波及到人类的一切活动。正如马尔库塞所谈到的“爱欲”本质,其作为人的生命本能,行为活动的“最高内容是在肉体范围内获得欢乐”,马尔库塞的“爱与本质论”不仅发展了弗洛依德的本我思想和性欲本能论,而且又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进一步提出了爱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理想”,在久木与凛子的关系之中,从性欲延伸到二人对于这份情感的维系,正是对于爱欲追逐的结果,这是欲求世界的一个因素,也遵循着欲求世界的满足逻辑。马尔库塞认为人的身体是快乐的工具,人的活动是追求快乐的活动,而个人在解放爱欲的过程中会获得一种持久的快感,这是一种人性的觉醒。映射于久木和凛子,在两人追求和享受快乐的过程中,这逐渐唤醒了他们在社会环境、家庭生活中被时日流经而淡化掉了的真实自我。
从本质上来说,在《失乐园》中作者将目光更多的投向对于人性的关注、认识和理解,他在小说深入解读的过程中结合了心理学、人性学、情感学等诸多方面,让读者更加思考爱情神秘、复杂、多变的特性,这是出于人性本能却又超出人类理性控制范围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然、道德、法律、伦理的规则,体现出较强的“反叛性”。但不得不承认,人的欲望确实如此强烈,在性欲地驱使下,人的真实自我人格开始觉醒,主观性意识开始萌发,导致追求真爱、追寻自我、渴求释放的思想和情感愈加強烈,这使得主人公哪怕抛弃整个世界也要为这份爱情而坚守,反过来爱情也满足了二人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在人性的探讨上,整部小说显示出了自我独特的深刻性和有效性,从反叛角度凸显爱情的本质本真。
二、欲望深渊——人生的毁灭
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首次针对日本文化提出“耻感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耻感文化”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是“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失乐园》中,在久木和凛子有过出轨的爱情之后,他们身上就既背负了日本民族与生俱来“耻”,也背负了西方文化中“罪”。这两份压力是他们在追寻欲望过程中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也迫使他们最终在欲望的尽头选择以共赴死亡旅途的方式来永存爱意。
首先,从耻感文化角度而言。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人群的思想模式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发现其民族性格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崇尚武士道文化,穷兵黩武又生性好斗;另一方面他们将“菊”作为日本皇家家徽的象征,崇尚美感又平和礼让。因此认为日本文化的社会性是以“耻辱感”为特征,日本民族将个人或社会尊严放置于生命之上,这体现在日常行为活动中,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完全将外在的他人与社会的认可作为自我行为的评定标准,这种外在的约束力包括“情义”、“义务”、“恩情”及“孝道”等道德范畴。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投放在《失乐园》之中,便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到这份压力的来源——社会。久木在职场方面因为一封寄送到常务董事办公室的举报信而掀起不小的涟漪,刚知晓时的久木心想“这会被认定为无非偷情罢了,乃是有违社会常识的极不道德的行径”,接着他被告知要求中止正在负责的出版编辑书籍工作而调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分社,这对于久木的职业生涯来说可算是不小的打击。之后他为维护自我的最后一份小小自尊而选择主动辞职,逐渐与同事疏远。凛子也因为这场爱情欲望的追逐和母亲的关系到达冰点,失去了家人温暖的后盾和港湾。久木和凛子是否在这场奋不顾身的爱情中有过后悔,衣川也曾这样问过,当时的久木心想“说不后悔是谎言,可事至如今,后悔也没用”。
久木和凛子为了自己爱的欲望而奋不顾身抛弃全部,殊不知社会因自己所有的道德规范特征也在同一刻抛弃了他们。这些似乎在他们二人眼中是“世俗之物”的一切,每一件其实都是道德范畴下的载体。集体或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认可是日本民族十分看重的衡量标准,本应在人情世界严格的自我行为规范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但现在主人公却因为欲望而打破这一规则法度,心理上的耻辱感便会悄然无声的加重加深,这使久木和凛子坠入孤独、恐惧和不被接纳的漩涡。事实上,日本民族这种重视他律的耻文化早已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为誉自尽,尤其表现在其武士道文化中,他们往往把自杀看成是消除耻辱的最好的办法。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最终久木和凛子选择共赴死亡之旅的必然性。
我们在《失乐园》中能清晰看到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作用下的人性的复杂,从追寻欲望到欲望解放再到欲望的惩罚,这场死亡旅程是具有必然性的,三岛由纪夫曾讲过“一个人的肉体只有在最痛苦、备受折磨,比如切腹那一刹那,那种极痛的状态,你才会觉得:啊,原来我的身体是存在的。”同样,久木和凛子最终的死亡也是人为了验证这样抛弃所有追逐而来的爱情欲望是否有着实在的存在感,这便是爱之极致,同时人性欲望尽头也带来了危险和惩罚。这一场爱情或者说欲望的追逐,本身便是背负着罪与耻的压力,即使具有反叛性,却也难逃现
三、结语
本文首先从爱欲解放的角度分析在久木和凛子相遇相恋过程中,从肉体欲望上升到精神心灵层面的浓郁情感,在某种层面上来说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从而对社会法则控制与操纵的产生了内在的反抗性,这是作者对于人性觉醒的探讨,也从反叛角度凸显爱情的本质本真。另一方面,爱欲解放之后环境和自我对于主人公产生了各种压力效应,强力展现了人性在欲望面前具有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于社会环境和自我道德约束在人类肉体内仍留存精神和余热,这不觉地使人类在自我解放过程中仍对罪与耻产生思考和顾虑。最终,这样一份因为爱欲解放而千难万苦获得的人生乐园,却又因为人性的复杂而最终永远的停止在极致一刻又同时失去了生机。所以,从惩罚和救赎的角度谈及二人结局,终究是在与社会抗争的同时被社会抛弃,终究是无法保持情感上的极致而走向毁灭。作者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复杂面全然尽显书中,这便是《失乐园》存在的文学意义和价值。
正如日本作曲家大岛满为同名电影创作的原声,一种深沉的悲悯在欲望的尽头反复奏响诉说:欲望的尽头,到底是重生还是毁灭?婚姻的尽头,到底是责任还是释放?义无反顾奔向纯爱之境的久木和凛子,在世俗的眼光里,他們自私,任性,毁灭自身的同时连带给别人带来无法平复的伤痛。被世俗所不容并抛弃的久木和凛子最终决定采取极端的方式乘上这趟通往终极之爱的列车,抛开沉重的道德约束,护着纯净之至的爱情向着天堂所向披靡一路飞升。凛子对久木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了感情,难道还要继续虚假地维持下去吗?容不下一丝杂质的纯澈,却也是一种让人心碎的任性。他们是被选中的绝无仅有的一对,亦是欲望尽头选择在毁灭中重生的一对。欲望看似模糊了答案,却在更有力的敲击着答案。当欲望无限膨胀的时候,走向的绝不会是真正的重生,只是虚假面具下的欣欣向荣,最终突破伦理道德底线的结果,只能是将自己与他人一步步的推向毁灭的无底深渊。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译林出版社,1987.
[2]唐铎.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及其当代价值[J].浙江师范大学,2015.
[3]渡边淳一.失乐园[M].林少华,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
[4]许兰,郝长墀:《论语》中”耻”字小议——兼论原始儒家重耻观念的现代意义[J]. 伦理学研究. 2006(1).
[5]李少伟.从《菊与刀》探析日本文化的特殊性[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