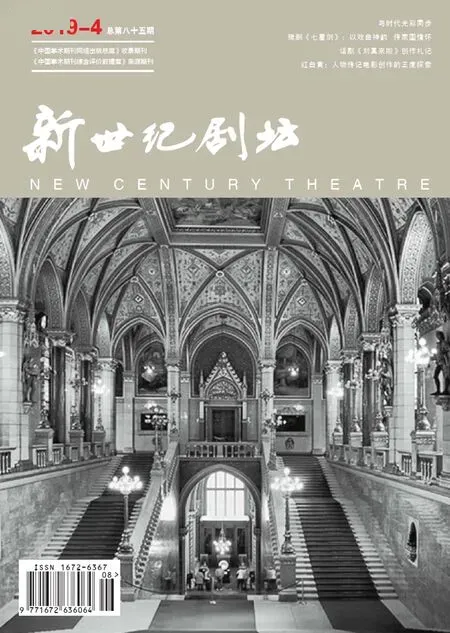浅析“津版”话剧《原野》中的“陶俑”形象
靳娟娟

“津版”话剧《原野》剧照
王延松的“津版”《原野》一亮相舞台,其中的“陶俑”形象便引来阵阵喝彩,专家和媒体纷纷叫好。但是“陶俑”这一舞台形象的运用,好究竟好在哪里?大多数评论文章都提到了创新,仅仅创新是不够的,那么“陶俑”和曹禺原著精神的契合点在哪里呢?本文试图通过再读原著,结合王延松的舞台版《原野》,对此作出回答。
一、作为歌队的陶俑形象,是《原野》悲剧力量的体现。
导演王延松活用了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让八个陶俑形象作为歌队呈现在舞台上,但不是让陶俑唱古希腊悲剧那样的酒神颂诗,而是在戏剧规定情境推进的过程中积极干预和评判。陶俑是演员,在舞台上根据剧情的需要,扮演者剧中的角色;陶俑是道具,作为舞台意象的载体,体现着苍茫的原野上生命粗粝的质感;陶俑是虚拟的幽灵,为戏剧发展推波助澜;陶俑是剧中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时刻传递欲望,拷问灵魂。
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往往是把悲剧的情感纯粹地独立起来,使悲剧的情感外化,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戏剧形式。王延松在《原野》中的舞台呈现,正是巧妙地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让一队陶俑放大人物的情感,通过陶俑粗砺的外表,木讷呆滞的行动和陶俑模拟剧中人物的心里独白,使剧中各种纠结的情感外化。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紧紧包裹在悲剧故事核心周围,在宣泄“怜悯”和“恐惧”情感的同时,又用集体理性约束个人情感,对个人情感进行理性引导,使个人情感不要过度释放,让观众通过看戏,通过戏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心理走向平和健康。“津版”话剧《原野》中的陶俑就起到了古希腊悲剧中歌队同样的作用。陶俑站在台上冷静地凝视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悲剧最终不可避免。陶俑更是象征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下的悲剧走向。因此,陶俑的运用,更加增强了曹禺原著悲剧的力量。
二、作为黑森林各种幻像的陶俑形象,是人性内部冲突力量的体现。
在曹禺原著中,作为仇虎对立面的焦阎王,早在仇虎出场前两年就已经死了,无法跟他进行正面交锋,而曹禺将焦阎王事先打入地府,也是有意而为之的。作品不直接表现焦阎王如何坑害仇虎一家的斗争场面,也不直接表现仇虎向焦阎王讨还血债、刀光剑影的复仇故事,作品没有进行这种庸俗的客观再现,没有让故事淹没人物,减少人物的外部冲突,从而腾出更多的篇幅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突出了仇虎这个人物丰富的人性。
曹禺原著里的“原野”昏暗、沉郁、诡秘,是花金子充满压抑的焦家老黑屋,是仇虎愤恨难平、冤屈难鸣的黑林子。所以,曹禺写的是复仇的母题,但《原野》不止于复仇。王延松在他的《原野》导演手记中说:“在我看来,原野上的人一出现便够‘恶’的,以至令人不安到最后。剧作者似乎不要求观众与剧中人的命运同呼吸,也不期待观者与剧中人的情感同步卷入。那么,这种戏剧是怎样满足观众的呢?”[1]通过深读《原野》,王延松运用陶俑对剧中人物进行追问,让陶俑去追思、去反省、去应答。“津版”《原野》在舞台呈现的外形上似乎是和原著脱了形骸,但在精神的本质追求上是一致的。原著的核心不是重在讨论仇虎复仇是否合理,而是重在讨论仇虎背负着“父仇子报”这样一个古老的合乎情理的家族使命却如何难以实施,一颗原本赤诚的善良的火热的心在走向复仇之路时迷失自我,进入了走火入魔的非人状态。
曹禺原著第三幕黑森林有许多不说话的幻像登台表演,如洪老、仇父、仇虎妹妹、焦阎王、赛张飞、囚犯、狱警、牛头、马面、判官、小鬼、阎罗王等。而王延松把第三幕中登场的很多幻像删去了,仅留下了仇虎的亲人和仇人、牛头马面、小鬼阎罗。导演运用陶俑扮演幻像,使仇虎的内心冲突外化,突出了这种内部力量的强大,更说明悲剧的不可避免。
三、作为象征生命样式的陶俑形象,是经典在今天力量的体现。
原著《原野》的序幕里有一段舞台提示是这样的:“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芽,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罗米休士,羁绊在石岩上……”[2]沉郁的大地蕴藏着野性的生命的力量,带着泥土散着香暗暗滋长,秋蝉的有气无力和巨树乱发着枝芽蓬勃的生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腐朽和崭新形成对比,压抑和滋长形成对比,这一切都是苍苍莽莽的原野意象。诸如此类的舞台提示在第三幕中还有,从中无论“巨树”还是“禾根”等意象都在昭示着生命,而原野是这些生命的载体,人是这个载体上最活跃的生灵。
王延松曾说:“古陶,原野大地里的一种生命样式。”其实,形态各异的陶俑正象征着人类,他们冷静的站在台上审视着正在演出的《原野》。当台下的观众看到陶俑,又何尝不是看到人类自身,我们人类究竟还有多少恶的种子在播撒,还有多少狭隘的思想在萌芽,还有多少纠结的爱恨情仇在延续,还有多少被不死的灵魂捆绑的肉身?……生命在延续,这一切还在轮回。那么就让一首《安魂曲》来慰藉在世的苦难的心灵和在天的不安的魂灵吧!导演王延松深深地把握住了曹禺原著对人性的悲悯情怀,剧作家曹禺是多么渴望人世间能多份祥和安宁,人性多一份善良的天性。《原野》诞生的那一年,有多少纷乱挣扎,有多少仇恨在相互戕害,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个人魂与灵的对抗,这是一个“恶”的世界,《原野》正是盛开在苍茫大地上的“恶之花”。剧作家曹禺从内心感受出发,把外围环境熔炉进去,提炼出来《原野》这么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没有直面战争,直面当时的军阀混乱,也没有直面阶级压迫与斗争,时过境迁,时代痕迹很浓的作品会尾随历史流去,而把这一切包融在内,提炼出“人性”中“复仇”这一永恒的主题,并赋予作品极其深远的追思的力量,为什么这种“力量”还在轮回,这就是经典为什么在当下还具有价值的原因所在。
《安魂曲》正是剧作家曹禺剧中的书写,心中所歌,这也是导演借助“陶俑”形象和莫扎特的名曲来对曹禺的深度读解,王延松又何尝不是在“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安魂曲》过后,台上和台下仅片刻宁静,这个世界各种纷乱的力量仍在广袤的原野上继续着狂乱挣扎,这是曹禺的忧思所在,也是导演王延松借助名著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诗意表达。
的确,陶俑把曹禺原著意到笔不到的内涵深蕴挖掘了出来,《安魂曲》在这里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原野》从诞生开始,舞台上不知被多少导演创作出了多少个版本,它的价值恒久远。原因正如王延松所言:“我排《原野》因为我身在其中,你演《原野》因为你身在其中,他看《原野》因为他身在其中。”[3]再读原著,再看“津版”《原野》,也是因为笔者身在其中。陶俑的出现让人更清晰地洞见藏匿于内心的最原始的力量,看着舞台上呈现的幻象,拷问人性,拷问自己的灵魂究竟有没有迷失在“黑森林”中。
注释:
[1]王延松《原野》导演手记,http://yule.sohu.com/20060127/n227741316.shtml
[2]曹禺《原野》序幕
[3]王延松《原野》导演手记,http://yule.sohu.com/20060127/n2277413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