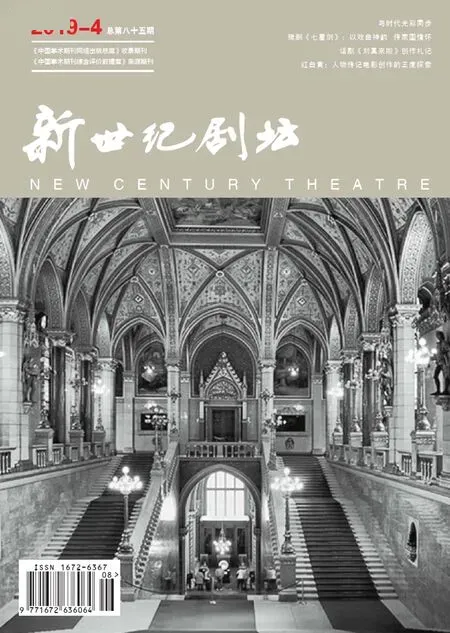红白黄:人物传记电影创作的三度探索
宁敬武

电影《为了这片土地》剧照
近年,我创作了以辽宁当代英模人物为主人公的三部传记电影,分别是:《为了这片土地》《毛丰美》《黄玫瑰》。
三部传记电影的传主都是平民英雄,北镇市正二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桂兰,凤城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毛丰美,抚顺市传染病医院防治艾滋病医生邹笑春。他们都没有传奇跌宕的人生故事,作为人物传记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另外一个维度的难度是在大家对“主旋律电影”诟病的背景下,在商业片占据市场主流的产业环境下,如何完成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突破?现在看来我们基本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为了这片土地》获得了第10届巴黎中国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宁敬武)、最佳女演员奖(陶红)、最佳男演员奖(郑昊);《毛丰美》获得第17届华表奖优秀影片提名奖,获得第3届中国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宁敬武)、最佳女配角奖(梁林琳);《黄玫瑰》入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并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姜宏波)。这三部电影都有一个色彩标签:《为了这片土地》的红,来自盘锦的红海滩,在影片中是王桂兰“出生地”的象征。《毛丰美》的白,来自大梨树村漫天梨花的洁白,凝结了主人公对故乡贫穷记忆的恨和爱。《黄玫瑰》的黄,是主人公对这首自我勉励的歌曲的共鸣,也是主人公和时间赛跑燃烧生命的颜色。
三部曲之红白黄,也是创作者在艺术化塑造英雄银幕形象的色谱中苦旅探索的“三基色”。
一、放到中国传记电影的大背景下,人物塑造的高度也能匹配这个时代。
人物传记电影在电影文化中有着比其他类型更独特的文化意义,是以电影的形式在给这个民族立传。中国电影史早期及新时期以来都涌现出多部传记电影杰作,如《武训传》《聂耳》《孙中山》等。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观众审美水平快速提高,中国电影艺术和制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中国电影已融入世界电影产业的大版图,中国电影也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人形象的文化命题和使命。在这种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中国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会发现创作和制作上存在严重的困境或瓶颈,亟需突破,否则无法匹配中国电影产业的体量和文化地位,更是在世界电影文化版图中的缺位和失语。
主旋律人物传记电影是传记电影的主流或重要组成部分。当下传记电影的创作困境第一当属画地为牢,对“主旋律”的狭隘化误读。主旋律传记电影因为大都是以英模人物为主人公,由政府或宣传部门策划推动,狭隘的创作者很容易落入图解、宣教的创作窠臼,最后观众反感、市场抵触。在恶性循环之下,观众对“主旋律电影”标签化,致使主旋律电影面临“信任危机”。其实,主旋律电影的提法只是针对商业化电影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对电影传播正能量的一个引导。电影作为一个大众艺术当然要传播正能量,主旋律电影更多是对电影策划的一个引导,在电影创作上,主旋律电影要有更高的艺术性、观赏性才能传达出主旋律的思想内涵。否则连一部合格的电影都不是,更何谈是传播正能量的主旋律电影?
在部分创作者、制作人狭隘化制作的同时,国际影坛的人物传记电影在向着“更个性化、更人性化、更灵魂化”的传记电影方向发展,表现丘吉尔在民族危亡关头艰难抉择的《至暗时刻》,描写一代总统内心幽暗的《林肯》,都在践行传记电影一以贯之对人的灵魂和人性更深刻的探索。在传记电影的类型里,中国传记电影和国外传记电影的差距在加大,这和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社会经历如此巨变,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部饱含酸甜苦辣、悲喜交集的长篇小说,观众有读解这四十年涌现出的时代英杰的需求。在这些主人公身上,观众不只看到英雄,也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好的人物传记电影也是观众对身处时代的重温式观影体验。电影市场到了一个风雨四十年登高回望的节点。关键是选取什么样的传主?用什么样的艺术态度来创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营销成“感动中国”的现象级大片?总之,不论在策划、创作、营销哪个环节,都要剥去对主旋律狭隘化的理解,深耕出观众内心深处对主旋律题材的需求,以优秀的电影作品呼应这种需求。
对主旋律人物电影的狭隘化理解,除了电影观念的因素外,文化的障碍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中国文化里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把强者神化,二是把逝者美化。这一点对于传记创作来说,不管是传记文学还是传记电影,无疑是一个灾难。把强者神化,牺牲的是真实性和人性;把逝者美化,损失真实性、个性化不说了,损失更大的是传记作品的基础价值,损失观众的代入感。观众之所以看传记电影,是基于一个逻辑:我们同样是人,为何这个人如此不同?我的人生是否可受此人的启发?代入感的损失会削弱传记电影的一个重要价值——励志价值。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为尊者讳一定要在传记创作中得到重视,创作者应该要有自省意识,否则很难还原出传主的伟大,更难以提炼出传主的个性和风采。
主旋律传记电影的第二大创作瓶颈是人物塑造的平面化。由于主旋律传记电影往往选取英模人物为传主,而这些英模在电影拍摄之前已经有广泛传播的英模事迹,所以电影很容易沦为这些英模事迹新闻报道文本的“二度创作”。由于这些英模事迹在采写过程中有未必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提炼”,比如“拔高”、“无私”、“无条件奉公”、“神圣化”等,所以如果以英模事迹的新闻文本为蓝本,无论怎样编剧都不会刻画出一个真实可信又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在过去主旋律传记电影创作中,有一些优秀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但时代在进步,以今天的文艺观念看,我们还不能说这些形象非常好地完成了真实化、个性化、立体化的艺术塑造。由于这些作品曾经被高度肯定,无形中成为后来创作者的范本,也成为制片方的策划榜样。在众多英模人物电影中,剧情往往由“政绩陈列”+“不徇私情”+“与病魔抗争”等板块组成,影片模式化,说教意味浓,很难满足今天互联网时代观众的电影审美。
人物传记电影创作可以依托一个大事件,也可以连缀一生中的多个事件,但都是要完成人物的塑造。而人物的塑造一定是立体的、多维度的,而不是平面的。以英模人物为例,人物塑造的多维度包括:人生的样本价值及差异性;行为的个性化及个性化的形成过程;人物魅力;独有的内心世界或精神境界;人物如何伟大及由来等……当然不限这些。这些维度不展现,所塑造的人物就不可信,观众不会触动,当然观众也没必要花两小时看一部和新闻通讯报道一样信息量的“电影”。在传记电影创作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创作者没必要进行解释。一部电影是一个封闭性的独立存在视听世界,观众要以自己普通人的生存经验可以理解传记主人之非凡人生才行,不管他是国王还是歌手,否则观众无法投射情感,也不会跟进传主的命运。
二、以真实性突破主旋律的模式化,完成从生活人物向艺术形象的升华。
真实性既是人物传记电影的铁律,也是打破模式化主旋律窠臼的突破口。在接到《为了这片土地》创作邀请时,我第一时间想到合作了三部电影的编剧搭档李铭,他的家乡朝阳离北镇非常近。但是,创作之初我和李铭即约法三章,不过度依赖之前的生活经验,以深度采访为手段,深度挖掘、发现真实的王桂兰为目的,更不是简单地构建辽西风情画。明确目标:塑造不出王桂兰的个性就是失败。一部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一定来自于生活。王桂兰的电影一定来自于真实的王桂兰的生活以及正二村的喜怒哀乐,而不是我们的想像,甚至不在我们以前的创作储备中。
合作很顺利,在初步了解了王桂兰的故事后,我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好奇心,一是她拥有强大的精神能量。她对一个城乡结合部曾经落后的正二村的治理,既敢对地痞流氓叫板,又能柔肠寸断到外乡接回赌气出走的老人,又扛着白血病从容笑对人生。没有一个强大而慈爱的内心世界是无法二三十年如一日受到村民的拥戴。还有一点非常突出,她身上传递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宝贵却又日益稀薄的内容,如“仁爱”。过去说县官是父母官,王桂兰这个村官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官”。谁家的房子漏雨,谁家做小生意本钱不够,谁家孩子上学有困难,这本账都记在她的心中。做一年容易,做三年也不难,二三十年一直做着这个仁爱之心的“母亲官”就是了不起。特别是在这个“母亲官”的字典里,有着当下稀缺的“公平”、“互助”等理念。我们默契的剧本创作从采访入手,向生活深处扎,泥土的气息、内心的细小逻辑、出人意料的细节越来越多,建立在深度理解主人公基础上的塑造才成为可能,也才真正开始。
在这个层面其实还不够,还必须找到她这一切行动最源头的那个驱动力,我把它叫做人物的“种子”。寻找个性产生的“种子”依然是高难度的挑战。王桂兰的事迹已有大量的报道,她本人在全国各地也巡回报告多场,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常态,然而,找到人物最真实的内心和个性的种子恰恰不在这些通常的新闻报道的层面。我们要找的是那种成为朋友之后的真心话,是面对女儿抱怨时的窘迫,是酒过三巡之后的无意之言。所以这个寻找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自己的小家到一个村庄的大家,六十年的人生,至今还拖着病体奔波在正二村的王桂兰是东北人的“脊梁”,也是当代中国的“脊梁”。她来自辽西一个贫困的大家庭,父亲是最能卖力干农活的,“累死了”。四个弟弟口粮不够吃,被村民取笑将来肯定“打光棍”。“长子若父”的命运降临到王桂兰身上,一个要强的、不屈服命运的东北女性成为王桂兰从小家走向大家的命运线。我们找到王桂兰成为王桂兰的“种子”了吗?也许找到了,也许还要继续找。
王桂兰“嫁”在正二村,也就是说她的丈夫是“倒插门”在正二村的。这意味着正二村是她的出生地,也是终老之地,王桂兰对正二村是责无旁贷的,甚至担当要比男人还大。王桂兰力量的源头追溯到“长女如母”,她不能让四个弟弟打光棍让人笑话;她的敢担当是从小就造就的,一步步从为小家走向为大家。“全国农民的功臣”毛丰美放弃到县里当畜牧局局长而留在村里当农民,是幼年因贫穷,父亲带着弟弟妹妹远走黑龙江烤烟叶讨生活而被抛下的“留守儿童”式心理阴影;邹笑春创建艾滋病科室为艾滋病患者撑起一片没有歧视的天空,源于要让父母不以自己上护士学校而遗憾……每个传主的内心深处的“种子”也许只是我们理解他们的众多钥匙中的一个,但解决可信性是观众愿意走近他们的第一关,也是传记电影创作的起点。

电影《毛丰美》剧照
比真实性更进一步的是对主人公的情感认同。假如能把主人公当成亲人或是挚友,那可能就成功了一半。他的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怎么捍卫他的尊严,怎么保护他的脆弱?都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直觉式判断。所以当完成电影的创作后,创作者应该和主人公本人或者家属成为“亲属团”关系,这也是检验创作的一个标尺。《为了这片土地》拍完,王桂兰本人很满意。《毛丰美》不光得到毛丰美夫人和子女的高度认同,整个大梨树的父老乡亲都很感动和满意。《黄玫瑰》也得到邹笑春家人的高度评价。
在主旋律电影中,英模人物的影片通常容易失去真实性和个性化。创作者往往急于使主人公更高大、更富党性,而忽略个性化塑造,遮蔽弱点,往往是在完成短期的宣教任务后无法使艺术生命力长久。真实,情感认同,有代入感,能让观众理解主人公为什么了不起,这才是传记电影的起跑线。

电影《黄玫瑰》剧照
三、传记电影需要艺术升华,需要导演的风格贡献。
传记电影创作需要真实性,又未必有情节片一般有丰富张力的故事做依托,所以需要有艺术升华的手段。我个人倾向于在高度真实和高度写意之间进行拼贴、对撞和淬火。真实和写意看似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方法,但其实是可以有机统一的。另外,写意的表现手法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艺术手段,甚至中国文艺的主流自古以来就是诗的方式或说写意的方式。放眼到世界电影版图,富有中国人文精神的电影诗化风格还有很多延续、显现和再创造。纵观李安导演的创作历程,都有一条东方诗意的脉络。李安是拍出“惆怅”情绪的电影大师。从《卧虎藏龙》《断臂山》到《理智与情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情境的诗意融合在庞大电影工业的支撑下展现出惊人的东方美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半部分基本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了,李安导演贡献了他富有创造性的中国美学,展示了一个印度少年所看到的天地间的大美,为世界影坛贡献了罕见的美丽瑰宝。
提到诗意、诗性,很多人想到的是MV式的风光加音乐,这个理解太狭隘了。电影的中国诗性,是中国人感知世界的方式的电影化,是对电影本体探索的东方贡献。从侯孝贤的长镜头到王家卫的旁白絮语,从李安竹林上的舞蹈到张艺谋的境州山水,中国文人感知到的拟人化的、富有情绪的世界外化为银幕上的一个个镜头。或者说是电影给中国人感知世界提供了文字和绘画之外的一个更大的艺术空间。我的感受是,在电影创作中的诗情表达是和电影叙事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彩蛋。
在《为了这片土地》的创作中,正二村作为王桂兰的出生地、奋斗之地,需要具象为一个能承载大感情的造型。于是我选择了离北镇还有一段距离的红海滩。因为红海滩的深红色太有造型表现力,年轻时的定情之地,重病后的纠结,看破生死的顿悟,都需要一个能升华成大境界的“大地”。而一望无尽的红海滩完全可以担当,是一流的电影场景。在章绍同老师的音乐下,多种复杂情感得以抒发、升华。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和王桂兰几乎并列的主角,就是“大地”。一部表现农民的电影一定离不开她脚下的大地。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王桂兰对出生地的热爱和钟情,得病之后对土地的不舍和纠结,到主动放弃骨髓移植,对丈夫的情感和丈夫故去之后的回忆与怀念,“为了这片土地”成为王桂兰发自肺腑、深入骨髓的大爱。
如何表现承载了如此情感的这片土地?我们以现代电影理念挖掘了多个维度来表现:用三个季节来拍摄,从正二村收割玉米,到冬天的大雪覆盖原野,开春的播种,到玉米高过膝盖。如果不是七一影片要上映,我们一定会继续拍摄夏天的青纱帐。在辽西满族的剪纸艺术中,我们创造性地以剪纸的大块红色来表现土地,把版画的表现力运用到电影中。我们还大量使用航拍,把大地拟人化,艺术地创作出“王桂兰为之奋斗的大地,王桂兰眷恋的大地”的大地形象。我们还不拘一格地把红海滩、芦苇地甚至黑龙江的大地雪景等有大美气质的景象来艺术地整合为影片的“这片土地”。当然,也包括我们从好莱坞请来的美国摄影师,以他的视角来发现和提炼“这片土地”之大美。
在创作《毛丰美》传记电影时,需要一个表达主人公临去世前对妻子情感的重场戏。毛丰美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农民创业者,敢为人先,妻子一辈子为他担惊受怕,感情很深。但写不好会很平庸和俗套。想了很多个方案,都不是很满意。在现实生活中,丈夫不会给妻子“跪”的,但是否可以提炼成一个电影情节呢?“跪”——这个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人文内涵的仪式性动作能否提炼成一个电影化场景?艺术还是要高于生活的,经过反复设计,终于成为影片中有份量的一场戏,当然要有富于诗性的情景创造。这当然是只属于中国导演拍中国人才有的电影化中国诗情表达:
116、病房 夜 内
夜,病房里只有丁桂霞默默陪着毛丰美。
丁桂霞:“一辈子跟着你,担惊受怕。没去县里当干部,我不后悔。我就是后悔一件事,我当初应该拿把菜刀顶住,不让你当这个村支书。”
毛丰美:“当初日子过不下去,我爸带着5个弟弟去黑龙江烤烟叶,我是老大,对着家里十几口子,怎么才能吃饱饭?我是真没辙,每天骑个二八自行车,来回骑100多里路去贩烟叶,最苦的时候,我都去东沟的山洞里放声大哭过。恨自己怎么生在了大梨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大梨树会有今天啊!”
插入闪回:十三、四岁的毛丰美骑着二八大自行车(骑大梁),脚都挨不到地上,来来回回从村口进进出出,贩卖烟叶。
毛丰美忧伤地慢慢说:“桂霞,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当兽医时家里还算小康,当了村干部反而顾不了家了,日子倒开始紧巴巴的。不过,不当村书记怎么当人大代表呢?能提案把农业税免了,农村电费降了,农民好贷款了,粮价提高了,咱一个祖祖辈辈的农民就该知足。桂霞,你是牺牲最大的人了,你让我给你赔个不是吧!”
毛丰美颤颤巍巍爬起来,竟然给丁桂霞跪下了。
丁桂霞眼泪刷地下来了,也给毛丰美跪下了,两个老人就这样跪着。
插入闪回:毛丰美骑着自行车,后座带着丁桂霞。丁桂霞围着鲜红的围巾,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
毛丰美:“桂霞,你就当把我舍了吧,权当我少活了十年,我能让人们都知道大梨树,能给八亿农民出点力,我一个农民少活几年也没什么。”
两个人抱头哭着。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际。
毛丰美的银幕塑造经受住了考验。邹笑春的塑造更难,因为邹笑春的伟大不在于惊天故事,而是更高的做人境界。《黄玫瑰》为辽宁英雄电影三部曲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让我对当代人物传记电影创作有了一些心得。《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家李敬泽写给《黄玫瑰》的一篇评论《一盏灯如何点亮》,道出了人物传记电影创作中编导者试图突破的那层屏障。
请允许我引用李敬泽先生的评论作为文章的结语:
“以明德引领风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提出的希望。《黄玫瑰》正是一部感人至深地照亮明德的影片。它的根本经验其实是朴素的:在中华民族的基本经典《大学》中,开头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大学》的论述中,追求至善的过程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正是一个人不懈追求生命的整全、不断向着更广大的世界承担责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始终举着那盏明德之灯,刚健而坚韧,深情而阔大,就像邹笑春,她走了,但她让更多的人有勇气有力量去拥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