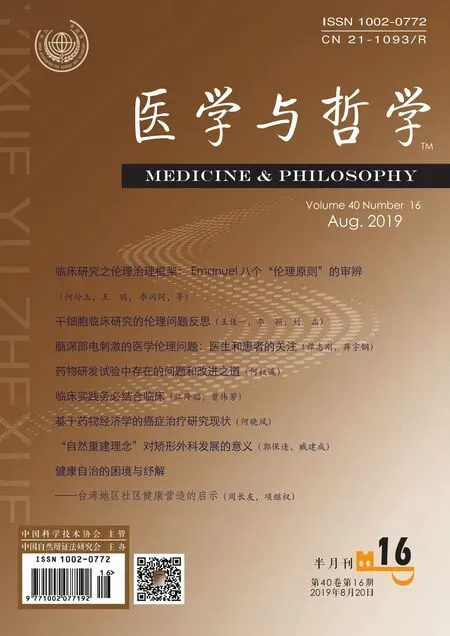国外安宁疗护领域研究热点*——PubMed数据库的共词聚类分析
罗 薇 吴红霞 赵学红 孙建萍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转变,安宁疗护已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我国将临终关怀、舒缓医疗、姑息医疗等统称为安宁疗护。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1]。随着安宁疗护内涵的外延,安宁疗护不仅仅局限于肿瘤患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痴呆症、心血管疾病(排除急性死亡)、肝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在疾病进展期或末期,均可接受安宁疗护[2]。近年来,针对安宁疗护的研究逐渐增多,安宁疗护不仅可以帮助临终患者控制症状,改善其生活质量,也可以避免过度医疗,节约医疗成本[3]。因此,了解安宁疗护的发展及其研究领域,为护理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推进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本研究从文献计量学角度,以PubMed作为数据源,对2009年1月1日~2018年6月30日安宁疗护的文献进行双向聚类分析,探讨安宁疗护领域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研究选取PubMed数据库进行检索,采用主题词检索策略,首先在《医学主题词表》(MeSH)中查找规范化的安宁疗护相关主题词,以“hospice care”、 “palliative care”和“terminal care”作为检索词运用布尔逻辑运算符构建检索式:hospice care[MeSH] or palliative care[MeSH] or terminal care[MeSH] or bereavement care[Majr] or end-of-life care [Majr] and nurs*。检索时间为2009年1月1日~2018年6月30日,文献类型不限,语言不限。共检索出7 007篇文献,通过浏览题目和摘要、阅读全文,手工剔除不相关文献,将检索记录的题录信息下载并保存为XML格式,最后纳入6 648篇文献。
1.2 分析方法
1.2.1 发展现状分析方法
采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 2.0软件,对纳入的6 648篇XML格式的文献进行提取并整理题录信息,对文献发文量情况、国家分布情况以及高频主题词分布情况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
1.2.2 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Bicomb 2.0软件对PubMed上2009年~2018年上半年安宁疗护相关文献进行词频分析,截取高频词,建立主要主题词和副主题词词篇矩阵,运用SPSS 23.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并将此矩阵导入双聚类软件gCLUTO 1.0中进行可视化分析,最后结合专业知识对结果进行判读。
2 结果
2.1 发文量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6 648篇文献,2009年发文量506篇,2009年~2015年安宁疗护研究的文献发文量逐年增加,2015年发文量最多,达722篇,2015年~2017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下降至587篇(下降18.7%)。
2.2 发文国家分布情况
安宁疗护研究主要来自于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2 321篇,占34.91%,英国2 030篇,占30.54%,累计百分比65.45%。
2.3 安宁疗护高频主题词分布情况

2.4 安宁疗护高频主题词的共词聚类分析
将主题词和副主题词词篇矩阵导入图形聚类工具包gCLUTO 1.0中进行双向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择重复二分法,相似性函数选择Cosine函数,判别函数选择I2,通过比较类内相似度(Isim)和类间相似度(Esim),形成可视化矩阵和可视化山丘图,其中矩阵可伸拉处理生成树状图,见图 1;本研究结合专业知识并通过多次对比双向聚类的山丘图,发现将主题词聚为7个聚类效果最佳。
表12009年~2018上半年PubMed安宁疗护前35位高频主题词

序号主题词出现频次百分比(%)累计百分比(%)1palliative care10363.573.572perminal care8302.866.433palliative care/methods6552.268.694terminal care/psychology5421.8710.565attitude of health personnel5371.8512.416palliative care/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4941.7014.117palliative care/psychology4751.6415.758terminal care/methods4031.3917.149caregivers/psychology3861.3318.4710attitude to death3521.2119.6811terminal care/standards3021.0420.7212terminal care/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2971.0221.7413palliative care/standards2880.9922.7314neoplasms/nursing2840.9823.7115family/psychology2840.9824.6916nurse-patient relations2730.9425.6317neoplasms/therapy2660.9226.5518nurse's role2270.7827.3319decision making2230.7728.1020neoplasms/psychology2150.7428.8421communication2030.7029.5422quality of life1900.6530.1923nursing staff, hospital/psychology1680.5830.7724nursing homes1660.5731.3425professional-family relations1540.5331.8726nurses/psychology1520.5232.3927terminal care/ethics1480.5132.9028home care services1420.4933.3929hospice care1400.4833.8730palliative care/statistics & numerical data1320.4534.3231dementia/nursing1320.4534.7732health knowledge,attitudes,practice1250.4335.2033quality of health care1210.4235.6234death1160.4036.0235spirituality1150.4036.42

图1 安宁疗护高频主题词聚类树状图
3 讨论
3.1 研究现状
文献计量的结果显示,2009年~2015年安宁疗护研究的文献发文量逐年增加,2015年发文量最多,从2015年~2017年发文量有所下降,说明这一领域研究在2015年达到高峰,2015年以后研究热度有所削减,同时也说明了国外安宁疗护的进程较国内快,能够给予国内研究较多的建议及启发。
3.2 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高频主题词聚类树状图及文献评阅,并结合专业知识,分析出关于安宁疗护文献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7个方面。
3.2.1 聚类0类:安宁疗护的实践标准
主题词包括34(death)、33(quality of health care)、11(terminal care/standards)、13(palliative care/standards)。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对于不同疾病、不同人群给予最佳的安宁疗护实践有着不同做法。严重的脑卒中患者接受安宁疗护服务时往往已经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因此,对于不可逆的脑卒中患者来说,与患者及其家属尽早沟通,及时转介安宁疗护病房是十分有必要的。加拿大学者Blacquiere等[5]对哈利法克斯QEⅡ健康科学中心急性卒中单元应用当地制定的姑息照护指南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使用规范的姑息照护流程能够在相对冲突较少的情况下帮助家属和患者及时做出临终关怀的决定,但仍需进一步解决其具体问题。高质量的死亡质量对于安宁疗护来说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涵义,因为安宁疗护的最终目的是让患者平静、安详、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帮助其家属尽快走出悲伤,继续生活。日本学者Hirooka等[6]通过调查接受居家姑息照护癌症患者的丧亲家属以探索死亡质量、沉思与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的关系,PTG是指创伤后生活事件后的积极人格变化,结果表明死亡质量与PTG有着直接关系,二者之间的间接途径为去世后不久和近期的蓄意沉思[7],因此,在提供高质量的临终照护的同时,要做好丧亲家属的心理疏导。2017年2月9日,我国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8],其标志着我国安宁疗护事业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3.2.2 聚类1类:姑息照护或临终关怀机构的质量管理
主题词包括6(palliative care/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12(terminal care/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18(nurse's role)、27(terminal care/ethics)。随着照护机构逐渐增多,探索其机制、监测和管理其质量对于促进安宁疗护的事业有重要意义。2010年,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提出了一项立法框架,以保障临终时的尊严和临终阶段的护理质量,Sepulveda等[9]对西班牙的一家急诊医院在提出立法框架前后进行横断面分析,来确定卫生专业人员是否已将这项立法的要求纳入其临床实践以及在医院死亡质量的决策程序方面是否有改进,结果该框架实施一年后的最小变化表明改良及优化临终决策服务程序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单靠法律是无法实现的。美国学者Hall等[10]以姑息照护发展中心(Center to Advance Palliative Care,CAPC)提出的推荐为评估框架,对纽约布法罗的7家医院的姑息照护计划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在这7个姑息照护计划中有22项符合CAPC标准。目前我国对安宁疗护的机构质量管理的研究较少,杨洪菊等[11]通过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一套肿瘤患者临终关怀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6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但未经临床应用,还需进一步验证。因此,尽快开展安宁疗护机构质量管理的相关研究对促进其服务质量改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3.2.3 聚类2类: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的研究
主题词包括15(family/psychology)、9(caregivers/psychology)、7(palliative care/psychology)、20(neoplasms/psychology)、14(neoplasms/nursing)。主要的研究内容有心理健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和精神的实质、需求、现况调查及干预等。对于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患者来说,不仅要遭受身上的痛苦,更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甚至,对家属的精神健康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心理照护是安宁疗护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研究表明,对于临终患者来说,平静的感觉以及认为生活充满意义比身体舒适更为重要,精神健康对患者的总体生活质量有积极而较为深远的影响,反过来,精神上的痛苦对生活质量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12]。美国耶鲁大学的Bai等[13]运用系统评价的方法探索癌症成年患者精神健康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精神幸福感与生活质量存在独立关联,应强调精神健康在提高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性。安宁疗护的“心理照护”中的“心理”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健康,而更多指的是“灵性”。对于“灵性”,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解读,杨克平[14]将其解读为:“人在生命中所体现的不断超越自我的行为,可借由个人与自我关系、他人关系及其他的关系之交流,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美国学者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来探究临终阶段患者、照顾者以及家属灵性的本质属性,结果显示,灵性在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灵性主要有五个属性,分别为意义、信仰、联系、自我超越和价值。博茨瓦纳共和国学者Philips等[15]采用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查该国国内临终患者及其照顾者的情绪和精神健康状况,结果发现,患者及其照顾者在患者临终时情感和精神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且去世患者的总体生活质量很差。安宁疗护的最终目的是让死者善终,让生者善别,但在安宁疗护服务开展的比较好的日本,仍然存在20%的临终患者及其家属面对死亡,感到绝望或者尚未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16]。有研究表明,“精神支持”干预(spiritual support invention)护理实践有助于帮助患者及家属应对及接受即将去世的现实[17]。国内在这一层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薛丽娜等[18]和赵越[19]通过问卷的方式分别调查肿瘤患者的灵性需求,结果均表明肿瘤患者灵性的需求程度高。单逸凡[20]采用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5位癌症居家患者进行访谈,发现他们的灵性困扰和需求均分为4类,灵性困扰分别是沉浸在痛苦与自责中无法自拔、对医疗或神灵感到失望、无法平安面对死亡、因癌症怀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灵性需求分别是原谅自我与原谅他人、增强对医疗或神灵的信心、平安面对死亡以及体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明晰患者的灵性困扰与需求之后,应该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灵性困扰,有研究者提出,对于中国无神论者的临终灵性关怀,应该围绕患者生命意义的适当评价和家庭生命接力和接代的主题进行,通过人生回顾、亲朋好友评论、家属承诺等方式进行临终灵性关怀[21]。
3.2.4 聚类3类:安宁疗护中与沟通相关的内容及其对应的关系
主题词包括2(terminal care)、19(decision making)、21(communication)、25(professional-family relations)、16(nurse-patient relations)。研究内容是探讨安宁疗护团队与患者及其家属在沟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及关系,主要谈论有关临终决策的内容,如生前预嘱(living will)、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生命支持治疗(life-sustaining treatments,LSTs)、拒绝心肺复苏(do not resuscitate,DNR)、代理医疗决策者(surrogate healthcare decision-maker,SDM)等。安宁疗护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临终决策,其目的是改善患者临终生活质量以及维护患者尊严,帮助家属留有时间和空间与患者道别,不留遗憾。沟通的过程即建立关系的过程,当患者和安宁疗护团队在同情、希望、人际关系、超个人关系和个人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关系时,患者会感到心灵上的舒适[22],可能助其找到生命的意义,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临终患者认为理想的护患关系中最重要的四要素是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处足够的时间,希望护士把他们视做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病人”[23]。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临终决策的主导者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护士,甚至可以是心理学家,沟通内容因医生、护士和心理学家所讨论的各种临终问题以及个人(患者或家属)问题而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医生与家属的交流多于与患者的交流;而心理学家则更多倾向于与患者交流;护士对患者和家属的沟通行为基本相同[24]。澳大利亚学者Sinclair等[25]对严重呼吸疾病患者的(临终决策)偏好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试验组给予由护士主导的ACP干预,即该护士促使医生和患者及其家属共同讨论ACP,协助参与人员指定一名SDM和制定预先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结果表明,在干预6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对ACP的接受度更高,对ACP的讨论频率更高;而试验组在干预前后相比,对ACP的接受度更高且其中对ACP有强烈偏好的人更愿意签署正式文件,由此看来,由护士主导的ACP干预能够有效增加有关ACP的讨论以及进一步促成正式文件的制定。在国内,在这一层面还停留在现况调查阶段和初期研究阶段,患者方面,晚期癌症患者对生前预嘱等知识普遍了解尚浅[26],DNR签署率偏低[27];护士方面,缪佳芮等[28]对7名肿瘤科医务人员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炼出ACP的三个主题,分别为态度、沟通要素及阻碍因素,为临床上ACP沟通提供了指引。
3.2.5 聚类4类:护士及其他专业人员的心理状态或灵性
主题词包括35(spirituality)、26(nurses/psychology)、5(attitude of health personnel)、23(nursing staff, hospital/psychology)、4(terminal care/psychology)、10(attitude to death)。研究内容是探讨护士和其他专业人员在安宁疗护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以及对其进行干预等。作为安宁疗护团队中重要的成员,与患者及其家属接触较多,常常会面对患者的逝世,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遭受到冲击,长此以往,参与照顾末期患者的护士可能会感到无助和情绪上的压力,对护士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严重者可导致焦虑、抑郁等[29]。另外,在病人离世时,护士不能表现出悲伤,尤其是在病故者家属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而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护士必须坚强,还要将患者去世的痛苦划分开来[30]。有研究表明,安宁疗护护士的精神视角对精神关怀护理实践有影响,培养护士早期的精神关怀意识,加强对精神关怀的表述和记录,可以提高护士的精神关怀实践水平[31]。瑞典学者Udo等[32]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对外科护士进行由讲座和反思性讨论组成的干预,干预的主题是生命与死亡、自由、交往与孤独、意义等与存在相关的内容,结果表明干预6个月后护士在护理临终患者时可显著增强信心和价值感的同时减少沟通无力感,另外,由于意识的增强和反思的增加,对患者的理解先于交流态度的改变。由此来看,护士的心理状态或灵性与临床关怀实践的水平密切相关,对关怀过程影响更甚。我国台湾学者林承霈[33]通过问卷调查成功大学附设医院照顾过生命末期癌症患者的133名护理人员以探索照顾临终患者的护士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知识与技能层面(临床决策知识、临床处置行为、濒死症状知识)有着显著的改变,对于情意层面(信念、正向态度与意愿)几乎无差异,由此可见情意上的培养远比技能知识的建立更加困难,未来应加强情意方面的训练。国内对安宁疗护护士或其他专业人员的心理状态研究较少,未来应关注护士的心理健康状态以提供最佳的安宁疗护服务。
3.2.6 聚类5类:安宁疗护的形式、方法及策略
主题词包括30(palliative care/statistics & numerical data)、22(quality of life)、17(neoplasms/therapy)、3(palliative care/methods)、8(terminal care/methods)。尽管各个国家都有其对应的安宁疗护指南,但在现实情况中,执行的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国情下,安宁疗护的形式及策略都不尽相同。通过该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安宁疗护的形式、方法及策略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居家安宁疗护相比于医院、机构的安宁疗护深受患者喜爱[34],多学科医疗团队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可能改善了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且对于家属而言,负担较轻,价格相对低廉[35]。另一方面居家安宁疗护能够有效地减少住院人数,缓解就诊压力,节约医疗资源[36]。居家安宁疗护是较为理想的安宁疗护模式,虽然实现起来较为困难且条件较为严苛,但未来的趋势是向其靠拢。瑞士学者Furst等[37]提出临终基础药物包可为居家安宁疗护提供最适当的药物,减少痛苦和住院需要,从而提高护理质量。美国学者Meier等[38]概述了国家安宁疗护策略的必要性,回顾了其他国家的策略,提出了美国国家卫生倡议,可为该策略的实施提供信息。国内对于安宁疗护的形式、方法及策略研究的较少,刘梦婕[39]初步构建了ICU患者生命末期姑息照护模式的理论模型框架,但需验证该模式运用的效果。彭小兵等[40]基于重庆市及长沙市儿童临终关怀服务的实地考察情况,提出搭建以“情境理论”为理论视角,以患儿为中心的个体增能、家庭增能、照护专业增能和社会资源链接的儿童临终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由此来看,我国安宁疗护事业的进程还在起步阶段,未来应加大其研究力度,为其更好的发展指明道路。
3.2.7 聚类6类:安宁疗护的知信行相关研究
主题词包括31(dementia/nursing)、24(nursing homes)、32(health knowledge,attitudes,practice)、29(hospice care)、28(home care services)、1(palliative care)。研究人群覆盖了患者、亲属、照护者和管理者,研究内容涉及长期照护人员对姑息照护的知识与态度、亲属对疗养院临终关怀的看法、护士对居家姑息照护的技术观等。我国台湾安宁疗护发展也比较好,如台湾学者Chen等[41]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了解长期照护机构中的护理人员(包括护士和护理助理)对老年痴呆症安宁疗护的知识与态度,结果表明护理人员对晚期痴呆的安宁疗护缺乏足够的知识,其态度为中性至积极,而护理人员对安宁疗护的知识与态度可能会影响晚期痴呆患者的临终关怀,未来应增加对该护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这对于促进晚期痴呆的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安宁疗护十分重要。美国学者Flock等[42]采用描述性研究调查位于马萨诸塞州中部三所养老院中亲属对临终关怀的看法,发现养老院患者的丧亲家属认为临终关怀和一般护理相比,在护理和服务、疼痛和症状处理、关于患者护理的沟通和预先指示等方面是相似的;对于接受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症状管理并不比那些接受养老院护理的患者更好。因此,在养老院的发展方面可借鉴美国养老院的模式,使更多的老年人从中受益。瑞典学者Munck等[43]采用现象学方法调查地区护士(district nurses,DNs)对居家安宁疗护的医疗技术观,结果表明,当更多的患者带着医疗设备回家时,地区护士的工作环境会因为需求的增加而变得艰难,再加上缺乏时间和连续性,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危及患者的安全,但这种不确定性可通过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支持性管理人员以及与安宁疗护团队的合作来减少。我国对安宁疗护的知信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况调查阶段,且局限于护士、护生、患者及其家属等,护士存在知信分离、知行分离及信行分离的现象[44];王丽萍[45]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广东、江西、海南、陕西、安徽共8所高校的1 150名实习护生中,超过半数表示不愿意照护临终患者;周雯等[46]调查并分析了武汉市2所三甲医院的242对晚期肿瘤患者及家属对预先指示态度的一致性,结果显示,超过一半患者愿意制定预先指示,大部分家属愿意遵循患者的意愿,但患者及家属对生命支持性治疗的一致性较弱。总体来说,国内对安宁疗护的知识掌握较少,态度较消极,执行力度较弱,未来加大国民对于安宁疗护的知识普及,从根源上消除安宁疗护推广的阻碍,是很有必要的。
4 结语
本研究的结果基于文献计量学和内容分析法,运用高频主题词的共词双向聚类分析,并结合具体文献和专业知识对结果进行判读而得出,为我国研究学者了解2009年~2018年上半年国外文献中安宁疗护的研究热点提供了线索、启发及借鉴。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资源限制等原因,数据库只选择了PubMed数据库,未能获得全面的国外安宁疗护的研究成果,未来可扩大检索数据库或范围,以获得更为严谨、完整而全面的安宁疗护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