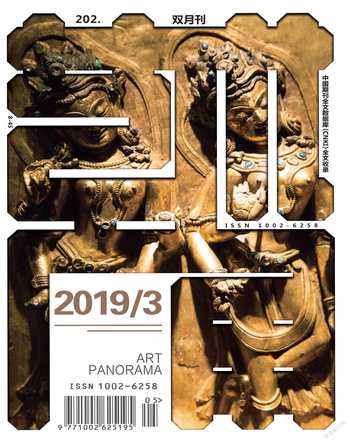译制片配音的技术内涵与美学意蕴
张联
匈牙利的贝拉·巴拉兹身处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期,他曾批评追捧、滥用声音的技术主义倾向,认为声音让电影给观众带来了新的生活奇观,却伤害了演员的表演,嘴巴沦为单纯的发声工具,演员表演能不大打折扣吗?由于最初录音技术不完善,缺失艺术美感,让人感到荒谬厌倦,默片时代的艺术大师卓别林、爱森斯坦等也纷纷表达了贬斥的态度。巴拉兹认为有声电影的任务是展示我们周围声音环境,人类除了语言之外,一切东西都能说话,并且不断影响支配我们的思想感情。他把语言隔阂未免看得过重了,拙劣的译制片造成语言和手势之间出现可笑的矛盾,他在1952年于伦敦出版的最后一本理论著作中,认定“有声电影文化的大大提高,结果竟使配音译制变成了不可能的事。”[1]无独有偶,进入20世纪70年代,法国电影评论家马塞尔·马尔丹在其代表作《电影语言》里,仍断定译制片在艺术上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援引导演雷诺阿喜欢说的一句话作为立论的注脚:“那些搞译制片的人如果是生活在中世纪,那就得被杀死,因为他将某个人的声音给了另一个人。”[2]不同民族的精神产品之间果真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互相交流?既然人类将感觉和知觉诉诸艺术,影视中凝聚的特定民族身上的文化色彩和气息,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和理解呢?
长期以来,影视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始终重画面轻声音,这一点对译制片的危害最大。当年有声片一经出现,其本身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使各种担心和不安接连不断。因为它动摇了视觉形象的首要地位,跃出了那个时代对电影精神的普遍理解——影像本身已是一门完美的艺术,声音充其量不过是从属和陪衬。语言是“自古以来对人的束缚”,语言会取消摄影机的运动。爱因汉姆甚至认为“对话本身不是一个艺术品,不是一个独立的、连续不断的东西。连续不断的对话必然要把可见的动作局限在说话者的特写镜头里,这就会使表演呆板化。因此在画面和声音之间就不可能有融合,因为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元素之间是不能设想有均衡的。”[3]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一面寄希望于语言“把无声片从字幕和‘解释性画面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又害怕对话成为“影片主要含义的传达者”。[4]英国电影理论家林格伦在20世纪60年代仍抱定这样的信念:“画面和声响不是同等重要的。通常有声电影中的视觉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总的说来,它表现更多的东西。”[5]安德列·巴赞等人倡导,不要分什么主要次要,电影就是一门视听结合的艺术。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于某种精神意志,而不是历史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巴拉兹也曾说过,“声音将不仅是画面的必然产物,它将成为主题,成为动作的泉源和成因。”[6]布莱松根据自己制作电影的体会,甚至认为“声音永远能召唤出一个画面,而画面则召唤不出声音来。”[7]只可惜他们的声音太弱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两者截然对立的美学观点逐渐瓦解。事实上,语言、音乐、音响三者密不可分,在影视中的地位作用丝毫也不亚于画面,有些时候不仅比画面更为重要,而且无可替代,实在是不应小觑。
有了这一认识,肯定会将影视片的译制过程视作艺术的再创造,种种后期制作说,录音棚里对口型的简单定性,当然灰飞烟灭、不攻自破。难堪的是,确实有一些译制片忽视配音这一中心环节,没有把它放到应有的正确位置,调动所有力量为之效劳,因而大大降低了其应有的技术标准,丧失了许多富于审美意义的东西。例证易寻,而且这种现象大有越来越蔓延的趋势,导致译制水平的徘徊不前,甚至出现质量的滑坡下降。毋庸质疑,配音中许多最常见情况的处理,不仅牵扯着技术因素,还关联着敏感的美学问题。
一
影视艺术中没有了声音,简直无异于死亡。
即使早期电影,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声音的,人们希望电影能够同时带来听觉的冲击和感染。1896年,当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上映时,已经请钢琴师在现场即兴弹奏流行歌曲,后来又相继引入了留声机、管弦乐队等。只不过这时的声音从形式到实质,都外在于电影的画面,影片的感光胶片上没有如今的声带。有声片最初诞生时,唱片或胶片上的声带放出的低水平录音,不知要比默片时乐队的现场演奏逊色多少,这恐怕也是观众和批评家们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声音的发展也确实逐渐从自然的还原上升到完美的创造。现在一部成功的影片,其多声道数字立体声必须融高度的技术性与艺术性于一体。“有声电影不应当仅仅给无声电影添些声音,使之更加逼真,它应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表现现实生活,应當开发出一个全新的人类经验的宝库……我们最感兴趣的并不在于它怎样发声,而在于它利用声音的表现力给电影带来了什么。”[8]译制片在再创作时,对原片的声音,尤其是语言处理中,时刻不能放松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统一的美学追求,否则,传达原作的效果时就要不伦不类,大打折扣,更休谈什么准确忠实、更胜一筹之类。
配音的出现是由于在录制同期声时,许多难以克服的实际问题所造成的。后期配音让人们迅速克服了棘手的难处,带去了便捷,摄影机又恢复了活动能力,片子可以做得更加细致精到。尽管各种高科技手段,诸如“智能化”拾音器材已然出现和运用,但对录音环节来说,声音技巧追求的最高境界仍然是真实。译制配音也不例外,首当其冲的,便是真实感的营造和真实美的欣赏。
录音和还音设备的升级改进,视频和音频装置的复杂配合,势必引起信号的延迟。积累起来,容易导致声音与图像不同步、口型对不准,影响译制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人们的操作技巧日益自由完善,如果自信无所不能,套用普多夫金的一句话,把谁都能够听见的东西表现出来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表现。观众接受的毕竟是经过主观选择的“声音影子”,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到回放的你的声音时,你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我的嗓音与自己听到的不同?按照好莱坞语言教师和声音教练纳尔逊·沃恩博士的说法,当我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时,我们还“有一条贯穿一系列身体器官,主要靠液体传播的体内听力通道”。[9]自己的声音尚且如此,何况别人的、异域的声音呢!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声音真实性的美学追求永远不会有尽头。二度创作的配音,作为对原片声音艺术真实的再现,理当更加小心翼翼,谨慎从事才行。虽然原片的音响构成方案是固定的,但在平衡声音比例关系、加工演员声音本身、调节音乐伴奏、音响烘托等方面,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
其中第二个需要导演和录音师通力合作的步骤,便是对声音造型的观照,由此使译制片声音的造型美得以凸现出来,创造出与画面有机融合的声音形象,而不是简单相加。对译制片来说,它需要充分发挥声音的物理、时空、生理心理因素,丰富立体地展现语言、音乐和音响,恰当地协调声音与画面的关系。事先构思好的声音结构可以决定某些视觉成分,有时甚至超出画面的功能,能够代替画面。声音的重叠、有意的含糊、局部的失真,成为配音艺术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声音的造型性质可以脱离其真实性的基础,这一点是迥异于戏剧的。
各种语言的词序、语调、重音都不相同,其韵律和节奏的变化,绝非以长度来简单匹配就算完事大吉。潜在的内心动作、特殊的情绪效果、独到的弦外之音,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声音的造型特征应该强化语言的这种渗透力。每个角色的嗓音基调,应在试音中反复权衡比较后才能确定。如《教父》中马龙·白兰度那种沙哑、喉音极重的嗓音;李扬为唐老鸭设计的特有味道,都使片子生辉添彩。
译制片配音还应把握好原片的声音动态变化,让观众在画面的变幻中体会到声音的运动美。影视片中的一切,都可理解为动作的一种成分,声音也不例外。配音中声音的连接、混合,需要将其距离感和运动感表现出来,无论是切入切出、淡入淡出,还是转场延续、噪声铺垫,都应最大限度避免录音间单调乏味的缺陷,力求生动地保持原有的整体性,传递声音的空间特质和对比关系。
仅以演员的对白为例,声音的强弱虚实,应随镜头的远近变化而变化;每个角色音型的固定,并不能代替在情节的推进中起伏跌宕的具体不同。特定的情境对话、动效的烘托,使人物的性格、事件的发展,从起点走向终点。孙道临与邱岳峰在《王子复仇记》中的迂回斗智,在《基督山伯爵》中的唇枪舌剑,分寸得当,激动人心。篇幅较长、人物众多的连续剧、系列剧的声音,更应着力驾驭,把握全剧的调子有序衔接,以免前后不一致、互相抵触。配音过程中不引人注意的静默之处,往往“此时无声胜有声”,多种多样的作用寄寓于此,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译制片尽管是在处理原片的声音,但不能将此作为唯一最高的任务,走到另一极端。不能忽略让画面与配音和谐相融,一味强调配音的技巧,使其成为决定一切的主导,干扰观众对镜头的鉴赏。声音叙事方式满负荷地运转,视觉形象叙事则被搁置一边,无暇顾及两者的统一,如此构思下去,两个层面恐难浑然天成。声音,尤其是对话,分散了人们的审美注意,画面游离其外,托不住声音。过分推崇对话的主体地位,必然突出影视的戏剧化特征;反之,减弱些语气和音量,松弛会使对话更自然更富弹性,更接近生活,更符合影视的本性。想赋予原片以新的灵魂,机械的复制是没有前途的,不具备犀利的美学眼光,是提不出各种可能的具体方案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艺术个性。阿瑟·米勒指导中国演员表演其《推销员之死》时直言:“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行为举止怎样才能像美国人。回答很简单,根本不要故意装成美国人的模样。要把这出戏演得美国味十足,办法就是把他演得中国味十足。你们真正进入了角色,表面上那点风土人情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先做到浑身没戏,再臻于浑身是戏,表演境界的玄妙之道自然领悟在心了。配音表演也是如此,只盯着人物说什么,对上口型成为压倒一切的标准,简洁倒是简洁,丢掉了生气贯注的为什么说、怎样说、与环境怎样合拍,“迫使語言形象跟着如实的画面形象走,就会限制或者歪曲语言”,引起“视觉形象意义含糊或者误解”。[10]如若再囿于琐细的技术分寸,那么配音一定会变成流水线上模式化的“替声”,从中难以展现自己的艺术创造。
也难怪,回顾一下译制片的产生情形,我们便会得知其浓厚的商业色彩的出身。“美国之所以迟迟不拍有声片,与其说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全部有对白的影片将妨碍好莱坞影片在国外的销路。”“好莱坞为了扼杀各国民族电影的复兴,开始利用外国演员来摄制外语版的影片,而在限制影片进口或完全实行影片定额输入制的国家里,则采取就地摄制影片的办法。随着技术的进步,美国掌握了一张最大的王牌,那就是一个不懂外国语言的演员可以用别人的声音来代替他说话。‘配音译制’使美国又收回那些已经失去了的市场。输入美国配音译制的影片,在华盛顿签订的通商条约中成了一项正式的条款”。[11]译制片可以自由进入任一民族的文化空间,而不被视作“异己”,“其他国家的电影也被迫接受‘对话的专制统治’”。[12]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是1948年1月大上海电影院公映的《一舞难忘》。悲伤的意大利爱情故事,外国明星开口说起了中国话,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德沃金在为刘易斯·雅各布斯的书所撰的题为《民族形象和国际文化》的前言中,分析为什么“更多的观众愿看本国语言配音的影片”,谈及了三个要素,实在是切中肯綮,应该在配音中时刻遵循。这里将其顺序颠倒一下,这便是“原作形象具有的沟通人们思想感情的魅力”“实质正确性”和“美学完整性”。[13]遵循这样的标准,应当可以有效减少译制配音中的粗制滥造,远离平庸,多出精品。
二
成功的配音环节背后,需要一系列的努力,翻译、校译、编辑、导演、录音合成、剪辑等等,都必须有上乘的水准才行。“声的世界是人们能够立即相信的世界;景的世界是人们能够立即理解的世界。这两种世界都不要求想象力。”因而“我们才肯接受电影对我们注意力的绝对控制”。[14]乔姆斯基称语言是一种“心理器官”,将语言行为与身体成长联系起来。事实上,说话在书写之前,语言不依赖于文字而口耳相传的历史,是所有语言发展的共同传统。正是这些所谓的“特点”,给影视翻译以施展的天地,构成其美学表现的各个元素。翻译编辑过程中许多技术处理和艺术把握,能够弥补原作的不足,甚至超越原著的品位。优秀的翻译,应该从影片中重新塑造影片,使译制片的前世与今生同也不同,像也不像,学也不学,引导观众感知原片的声音和意图,保留异域情趣和美感,重现其神韵灵魂。翻译水平的高超,才能合乎影视翻译的规律,把国外影视片的精髓介绍进来,把我们优秀的国产片推向世界,让相互认可的文化遭逢相会,提升影视海外影响力,竖立起通天的人类影视语言巴别塔。
导演的中心地位同样适用于译制片,导演需要组织有关人员共同攻下配音关。大量的案头工作有助于演员把握角色、服从调度、观摩原片时的阐述、挑选演员试声、现场与翻译对译本的修改,与录音师对声音的艺术处理等等,导演事必躬亲,身体力行。在配音中,导演要提醒演员注意台词的双重作用,既要推进情节,还要传达说话人的个性,让他们成为言语的主人。导演对译制过程中的沟通屏障需要保持清醒认识,语言稳定的字面意义之下,流动着变化的意思,如何确定特殊语境,瞄准思维与言语间的过渡,将隐藏着的潜台词所寄寓之意思与字面意义联手协同增效的复合意味传达到位?潜台词的波动与表达,大有文章可做,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在动作领域里称之为贯串动作的东西,在语言领域里我们就称之为潜台词。”[15]斯氏看重演员的想象和灵感,谈及表演技巧,他常说的箴言是:“通过有意识性达到无意识性。”不关注无意识性,不激发潜意识,实际上抛弃了“角色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本质”。其实“话语的重要性更多是表现在话语所反映的变化上,而不是表现在话语本身”。对话的作用,是“使讲话的人物和听话的人物性格化。”[16]互相的冲突才能避免声音的相似。陈陈相因的译制腔矫揉造作,毫无生动可言。在差异中丰富形象个性,而不是拘泥于人物的外在特征。苏联著名导演罗姆在讲述如何指导演员时,这样告诫过我们:“只是在准备自己的台词,就不是在倾听对手说话,就不是在同他进行交流。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准确地再现思想,因为准确地再现思想只有在思想进行斗争时才会出现。”[17]倚仗可塑性强,先入为主,与原来人物貌合神离,观众便不会认可你的“做戏”。与片中人物融为一体,深入其内心,把脉其性格感情,不是背词,而是配戏,和角色、对手以及自己全方位交流,语言的再度居留,更是合作的产物,否则,不足以再现具体、完整的语言环境,难免出现刻板呆滞、机械模仿等弊病,破坏译制片的整体美感。
三
译制片配音中的重头戏是演员的表演。这种表演的特殊性对译制片的影响至关重要。它不仅要求演员具备舞台语言的基本功,将吐字归音、重音强调、换气方式烂熟于心,还要恰如其分地运用内外部技巧,如声音的高低长短、自我感觉的捕捉、对动作和潜台词的准确把握、互相衔接的快慢疏密。所有这一切,应该以原片为依据,在忠实原来风貌的前提下,重新塑造出为本民族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异域人物形象。使“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在广泛传播中造成一种共同的归属感……民族特性的内部因素就是这样每日每地、不知不觉地反复复制出来。”冯宪珍在话剧表演和影视配音中对俄苏作品的把握,堪称“传神”。童自荣演绎法国影星阿兰·德隆的形象,有声有色。高仓健作为日本观众眼中数一数二的男明星,外表冷峻、内含热情的表演特点,被毕克展现无遗,成为其中国的代言人,以至于毕克去世时,高仓健发来唁电,请人带来冥香献于知音的灵前。[18]
演员在译制片配音中的创作程序,包括三个步骤——观摩分析原片、初对和实录。只有掌握了剧本的精神内容,才能掌握台词和外在形式,这一点不言而喻。初对时,将原片的声音关掉,演员沉浸在塑造的角色中,按照设计好的基调,找好长短不一的气口,妥当处理重音、停顿,掌握好节奏,数准、装好口型,看原片人物说话的时间长短,开合状态,肌肉松紧程度,找准原片演员的呼吸节奏,跟着其呼吸节奏走,收放自如,说话时和人家拍戏的感觉一样,自然去接他的话,录制下来口型就肯定没错儿。声音不仅要和原片的视觉形象贴切,还应适合配音同行之间的交流分寸。所有这些,都必须将原片的画面铭记在心,尤其是外部动作的细微变化。我们都有这种体验,不说话的时候,人的面部表情反而鲜明生动。口型技术固然重要,但配音如果只盯着嘴,手中不离台词本,本身即是对表演的抵制,肯定会造成与表情、动作的不合拍或满拧。克拉考尔将它上升为理论的概括:“只有当话语的含义是我们所捉摸不到的,只有当我们能从讲话者的形象来把握一切的时候,话语才是最电影化的。”[19]有时需要明白准确,有时含混不清则成为上好的标准。只有充分调动视觉的所有潜能,才能与声音配合默契,这里可以引用奥勃莱恩的一句话:“你必须瞧进其他演员的眼睛里并与他发生联系,而不是只对他正在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20]一个演员在配音时,其他人精神集中在彼此关系上,才不至于忽略自身的特点,方能在录制中将栩栩如生的形象通过声音还原出来,形象才会在充盈的声音中,让人感到分外的魅力。
数口型可以长达一个半月,从背词到改词、对词,与原片人物融为一体,既配音又配戏,才能深入内心,把性格和感情配出来,念台词三五十遍是常事,甚至六七十遍,曹雷等演员的回忆为我们留存了这样的记录。仅有正规严格的训练和雷打不动的程序仍然远远不够,如今声画不同步、口型不对等明显的失误已越来越少,但在欣赏译制片的配音中,感觉演员往往技巧有余,沉湎在框子中自蹈窠臼,甚至为了迁就口型,违反习惯重音,拖延间隔,“洋腔洋调”削足适履,而激情冲动、情境想象,生活中的自然天成明显不足。需要说明的是,内在的激情冲动绝不是肤浅意义上的带有夸张成分的“过度反应”和配音腔;与原片特定情境赋予的意义、情绪和潜台词相吻合,也并不意味着将生活中有机一体的感觉搞得支离破碎。戏剧演出中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为代表的体验派和表现派,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美学体系,两者是从不同方面解析演员与观众的相互作用,目的都在于解决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基本美学问题。斯氏强调演员“自由解放自己”的训练,因为演员比谁都更了解自己,在研究剧本、感受和分析角色方面比导演、作者和评论家更胜一筹。现实中与之背道而驰的是,因为急于求成不甘示弱,演员凭借声音化妆技巧,一个人同时扮演两个或更多角色,这种省时省力的救急方法,实际上不宜于大面积推广。至于抱定一种音色,以不变应万变,矢志不渝地“表演自己”“张扬自我个性”的做法,更是不堪效仿。
当然,成功的配音艺术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如李梓在《巴黎圣母院》《简爱》《叶塞尼娅》《恶梦》等片中,调动各个音区,或装饰或渲染,将声音的高低、强弱、宽窄、明暗运用自如,为不同的人物改变音色和讲话方式,以刻画出人物不同的内心世界。李梓体会在原片演员基础上的再创作,要适应角色需求,跟着人物感情走,抓住人物性格,通过气息运用来掌握、调节,使声音听来真实可信,最关键是和原片人物贴合,把原片说的外国话变成中国话。[21]说到配音演员的贴合功夫,研究者认为从口型起始,直到性格呈现为止,还要经过动作、表意重点、情绪、身份、语调等一系列贴合。52集动画片《狮子王》,抛弃用大量女声模拟童音,可爱的小狮子、小鹿、小蜜蜂等都由少年朋友配音,充满童真稚趣,乔榛、丁建华等人则甘当配角。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的导演艾·梁赞诺夫,在中国访问期间偶然看到该片的重播,惊喜地鼓掌、狂呼:“太好了!太好了!……看过这部片子,我懂中国话了!”更有极致者,甚至认为邱岳峰为《简爱》中罗切斯特的配音,“粗一听,同斯考特(饰演巴顿将军的乔治·斯考特,在《简爱》中演罗切斯特)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可多听听就能听出差别了。斯考特的声音干、粗、直,比邱岳峰少了许多的韵味和内涵。”[22]痴迷邱岳峰玉振金声的追星族,覺得他的声音比原来的演员更丰富、成熟,有魅力,比外国人更像外国人。“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这是陈丹青的评价。译制配音的再造点染之功,可以将普通片子改造成杰作。“观众硬是在没有绅士的时代,在没有绅士的国度,通过一种特殊的媒体,在心中创造了绅士。说到底,这个绅士只是我们借以摆脱粗俗现实的代偿品。”[23]邱岳峰声音里蕴含的高贵气质,诱发刺激着观众的想象。他们创造出的银幕情境,满足了观众的审美认同。大概这一点,与钱钟书先生“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愿意读哈罗德的原文”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原文“明爽轻快”,“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颇有些进入“化境”的味道。[24]
影视表演中的对话之难和不易把握,可以从卓别林身上找到例证。直到有声片诞生12年以后,他才拍出有对白的《大独裁者》。他先运用音乐,继而又采纳了音响,最后才引入对白。“如果我想扮演说话的角色,那么,我就要改变我所创造的形象”。[25]可见创造说话的形象有多么复杂。“一思考一呼吸,”英国皇家戏剧学院训练演员台词功夫时,将此作为首要原则,对白的生动简洁、紧凑精准,充满可能性与想象力,深意存焉。演员的配音同其他表演一样,“基本上是零星进行的,所以他很难把所扮演的角色当作一个整体来想象或感觉。”[26]而观众的欣赏过程却是连续不断的,这也是配音时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在译制配音中,我们常常发现原片导演和演员的许多即兴创作,台词与提供的本子有很多出入,因为事先准备好的某些自然假定一到临场,可能会显得不自然,有时甚至可能放手让演员发挥。即兴的调整往往很生活化,也很符合对话的真正实质。配音时,演员的心态主动积极,而不是被动迎合,鲜活的形象自然呼之欲出。
演员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观众,要以他们的观点审视自我塑造的形象。同时投身角色之中,又不能丧失自我。伯格曼说得好,“演员必须无条件地同他的角色合二为一。这种合一必须就像披上一件戏装那样容易。长时间精神集中、连续不断控制感情和高度紧张的工作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演员必须能够通过纯粹的技巧随时进出他所扮演的角色。”[27]诚哉斯言。配音演员在表演全程沉浸在总体创作意图中,“给自己的心灵‘化装和穿服装’,以便创造出角色的‘人的精神生活’”[28],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语言活灵活现地附着在原片人物身上。
记得二三十年前,在大学生的文艺晚会上,一些人竞相表演译制片的配音片断,作为自己的拿手好戏。也许我们不应仅仅陶醉于目前引进数量的突飞猛进和观看体验的完美享受,不忘昔日的故事和情怀,才会使影视译制的天地再创辉煌。“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先生的宣言,声犹在耳。正如技术的潜力是无限的,译制片配音中的美学追求同样没有止境。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英汉翻译与比较文学相关性研究”(L17BWW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6][8]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第185页,第182-183页。
[2]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150页。
[3]转引自亨·阿杰尔:《电影美学概述》,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4][19]转引自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132页,第136页。
[5][26]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第155页。
[7]转引自诺埃尔·伯奇:《电影实践理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9]转引自斯蒂芬·胡安:《奇特的人体》,《中外书摘》,2003年9期。
[10]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
[11]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第281-282页。
[12]约翰·霍华德·劳逊:《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13]转引自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14]斯坦利·卡维尔:《看见的世界》,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171页。
[15]苏丽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1页。
[16]米歇尔·西翁:《影视剧作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7]米哈伊尔·罗姆:《电影创作津梁》,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18]苏秀:《我的配音生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20]玛丽·奥勃莱恩:《电影表演》,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1]转引自徐燕主编:《银幕传情:与中国当代译制片配音演员对话》,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22]严锋:《好音》,《万象》,2001年6期。
[23]张稼峰:《那些难忘的声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50頁。
[24]钱锺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269页。
[25]库卡尔金:《卓别林评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27]转引自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28]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