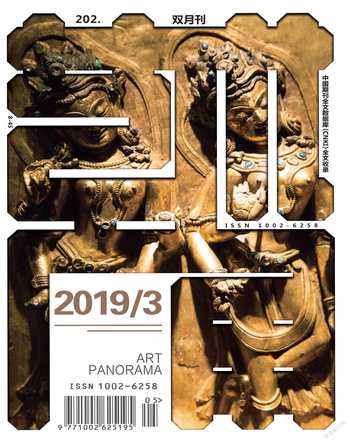中国广场舞的学理性透视
刘建 孙慧佳 沈雨潇
与“中国大妈”紧密相连的广场舞,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研究对象,惊动了舞蹈圈内外众多专家学者。这很像一个滑稽故事,但我们面临的对象所涉及的问题却一点也不滑稽,因为大妈们不仅让中国广场舞填满了中国城市适合跳舞和不适合跳舞的公共区域,而且把它们带进了意大利的都灵广场、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广场,让老外瞠目结舌……对中国广场舞蹈的基础理论研究,迫在眉睫,同时也是一个非技术性单一视角的论题,很冷峻,我们就谈谈它。
一、中国广场舞的概念与关注视角
概念的界定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否则便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乱谈”。中国广场舞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大中城市为引领的城市市民阶层在城市公共区域自发的舞蹈活动。“改革开放”是时间界定:中国广场舞不是汉代广场上的乐舞百戏,不是刚刚解放时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街道广场上表演的大秧歌,其时间是1978年以后到当下。“城市公共区域”是空间界定:从公园到社区休闲场所,从立交桥下的空场到社区篮球场,中国广场舞几乎空间无禁忌——从实地空间到音响空间,甚至为争夺空间把篮球场上的小伙子们打得头破血流,引发《新闻联播》也介入其中。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过快过猛,城市市民阶层瞬时变得非常复杂,原有人口向社区外部迁移,外来人口向城市中心聚集,这就决定了中国广场舞舞者身份的混杂:不同民族的、不同区域的、不同身份的、不同职业的人都来跳舞,非职业舞者的巨大人群中还夹杂着不同舞种的职业舞者,由此,分化出不同人群不同舞蹈类型的广场舞,包括自我区分出的“雅俗之辨”。但无论哪一类人群,哪一类舞蹈,其舞蹈都是在城市区域内自发的陌生人群聚集之舞。它们可能产生聚合力,也可能产生破坏力。
今天,这种力量已经是以原子裂变的方式向外扩散,由中国大中城市扩散到三线小城市,由中国城市扩散到从北美到欧洲的外国城市,有如“洪水猛兽”而引发关注。不久前,山西省临汾西关小学校长张鹏飞(广场舞成员)以中国广场舞的“鬼步舞”取代课间操,成为舆论焦点。在英国有网友就将其描述为:“这位四十多岁的校长,将中国音乐和爵士、街舞舞步相结合,带领学校师生开创了新的课间娱乐项目”……关注要有视角,学理的视角就是各类一级学科的方法论。无论如何中国广场舞是在用自然的身体跳舞,应该属于舞蹈学范畴;舞蹈学上位概念是艺术学,包括各门类艺术;艺术学的上位概念是文艺学,包含文学与艺术;这一概念的再上位概念是人文科学,包括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伦理学,等等;与人文科学并列的是更接近实用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人口学,等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合起来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与其并列的还有自然科学,包括生态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等;当然还有交叉科学,像与自然的身体相关的人类学的一支——生物人类学,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这样中国广场舞学理的讨论就“由点而线而面”地扩大开来。如下面所示:
非学科的中国广场舞<舞蹈学<艺术学<文艺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
二、对主流舞蹈的反动
主流舞蹈又可以稱作艺术舞蹈、职业舞蹈、精英舞蹈、学院派舞蹈,与中国广场舞的生活舞蹈、非职业舞蹈、群众舞蹈、自发舞蹈正好相反。在古今中外的舞蹈中,二者本是互为一体的:楚汉战争中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和乐舞百戏中职业俳优的“跳丸弄剑”是血肉相连的;今天阿根廷街道广场上的探戈和国家探戈舞蹈团是同根共源的;中国青海玉树学校广播体操的“卓”舞和玉树歌舞团的“卓”舞是无甚差别的;法国孩子们学习的芭蕾和芭蕾歌剧院退休演员教授的芭蕾是标准统一的……中国大妈们的广场舞可不管这一套,自由自在,特立独行,对主流舞蹈视若无睹:“拿来”的“水兵舞”“肚皮舞”“交谊舞”,自创的“僵尸舞”“手套舞”,继承的“花棍”、“耍长绸”、汉族伞头秧歌的“唱时不扭,扭时不唱”,等等。此外,还有亦舞蹈亦体育的“健身球舞”“巴山健身舞”……
那么,互为一体的主流舞蹈的引领作用何在?答曰:自身尚一头雾水。今天中国主流舞蹈构成大致如下:芭蕾舞,西洋来的;现代舞,西洋来的;国标舞,西洋来的;爵士舞,西洋来的;韩国舞,东洋来的;缅甸长甲舞,南洋来的……它们均有舞种属性,有技术套路。相比之下,占据主位主流的中国古典舞一直不清不白,难以成为“国舞”标识。中国民间舞被挂上了概念混乱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后也是混混沌沌,一会儿要搞职业化的“元素化”创编,把蒙古族贵族古典的《顶碗舞》搬上舞台;一会儿要北京舞蹈学院的《沉香》去做“非遗”民间舞节目,让职业民间舞者去复现藏族寺庙的“羌姆”。而今,一个《黄河》交响乐,芭蕾舞跳,中国古典舞跳,中国民间舞跳(《东方红》),中国现代舞跳(《我们看见了河岸》),国标舞跳,街舞也跳(且获得国家“荷花杯”金奖),不知谁是老大?在“中国舞蹈最高学府”的北京舞蹈学院,又成立了“街舞”和“冰舞”研发基地……“战罢玉龙三百万,残鳞败甲满天飞”,我们拿什么引领中国大妈们?
于是,非主流舞蹈造反了,起义了,从孩子到老人,五花八门的培训班、舞蹈队、舞蹈比赛风起云涌——你敢三百万“玉龙”,我就敢三百万“土龙”。其中最浩大的一支队伍就是中国广场舞。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广场舞参与人数已达1.5亿之众。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分为两个类型:其一是具有较明确的族群身份或区域身份舞者参与的广场舞,它们多驻足在三线小城市中,像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市广场上的“巴山健身舞”(原型为土家族“撒叶尔荷”),又像山西省临县广场上的“伞头秧歌”。这支队伍的广场舞多以传统舞蹈中的民间舞为基础,舞种属性相对清楚,男女老少均有介入,像临县“伞头秧歌”的“伞头”多为中年男性。其二是无族群身份、无区域身份舞者参与的广场舞,跳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人数众多,成分复杂,除了“拿来”的舞蹈,这支队伍的广场舞多数没有舞蹈的舞种属性,自编自创、五花八门。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广场舞主要是这支庞大队伍的手舞足蹈。由这两支队伍汇合而成的中国广场舞是一面镜子,反射出舞种属性杂糅的中国主流舞蹈现状的同时,也开始显现出“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的自我镜像塑造,使主流舞蹈和非主流舞蹈呈现出越来越大的撕裂状态。
放眼世界,广场舞并非中国独有,巴西的桑巴舞、阿根廷的探戈舞、日本“花祭”时跳在广场上的日本民俗舞、匈牙利喜庆场合跳在广场上的匈牙利民间舞……它们都保有各自与主流舞蹈对应的舞种属性,用以形成一种身体文化凝聚力。与此同时,中国主流舞蹈其实面对一个非常尖锐的命题:我们是否确立了中国舞蹈文化与审美的身体母语,并以此对非主流舞蹈施加影响,以形成主流舞蹈与非主流舞蹈共在于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舞蹈语库中?如果不能,中国大妈们就要进行阿Q式的舞蹈革命,在无标识的语境中创建自己的舞蹈。这是舞蹈学领域的问题,是本体的问题。
三、亚艺术与去人文化
如果舞蹈学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么紧接而来的便是艺术学、文艺学、人文科学诸学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像艺术院校的国标舞经常在体育节目中亮相一样,中国广场舞更多得到的是中国体育界的关注,成为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着眼点,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艺术属性,成为挂着“舞蹈”字样的亚艺术。
艺术学的关键词之一是“风格”,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当土家族的“撒叶尔荷”被抽去了男性“跳丧”的内容而变异为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的“巴山健身舞”时,它便失去了内容;同样,当戏曲中衍生的中国古典舞的“小射燕”和蒙古族的“鸿雁”舞的揉臂重组在一起时,它便失去了形式。至于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背景下的“水兵舞”和“交谊舞”,则形成了阿恩海姆所说的“艺术与视知觉”的“分裂”……我们可以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来称呼这种亚艺术,但无论如何,它们很难归属“美学”的研究范畴。
从形而上的哲学来讲,儒家礼乐的身体哲学讲究“不争、不怨、不乖”(《礼记·乐记》)。中国广场舞的大妈们不大理会这一套,不仅要争夺跳舞的生存空间,而且自身还有“雅俗”之争以及“水兵舞”“健身舞”的争先感。此外,彝族“千人跳菜”广场舞、黎族“千人竹竿舞”广场舞以及一些广场舞大赛,更是显示出“争”之气息。就“怨”而言,中国广场舞在总体上遵循了民间舞的“快乐原则”,但这种“快乐”不同于乡土民间舞的快乐——以之获取生存的力量,它还潜藏着某种城市平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感,因而形成非理性表达的泛滥——无限的身体空间占有,巨大的音响噪音播放,隐忍的软弱个人的积怨获得了群体性释放。这其中,也不排除像“僵尸舞”所潜藏的“怨”;另有“手套舞”白花花的视觉冲击,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接受的。由此,一些舞蹈乖张的形式就凸显出来,它们其实不适于在公共空间表演。从哲学降至文化学,“交谊舞”“肚皮舞”等不属于中国舞蹈文化,“僵尸舞”也没有身体文化记忆;即使汉族的大妈们跳“锅庄”和“赛乃姆”,那也是藏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体文化记忆和技艺,并非本有之身体母语,这就又涉及到民族学和人类学。
人类学中有一种“逆向人类学”的方法,比如某些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可能会问汉族的广场舞者:你们为什么跳我们的舞蹈?你们没有自己的舞蹈吗?其实是有的,至少有“北方的秧歌南方的灯”,还能从北方的秧歌中细化出山东秧歌、河北秧歌、东北秧歌;山东的秧歌中又可以分支出海阳秧歌、胶州秧歌、鼓子秧歌。就是北京市,也还有“太平鼓”“打花棍”这些民俗舞的记忆与技艺。凡此,足以让不同区域不同广场上的汉族舞者“各美其美”。
身体的记忆与技艺是历史学问题。山东商河地区的鼓子秧歌明代既已存在,以男子左手持鼓、右手持牛肩胛骨击鼓祭天为主体。今天商河地区广场上的鼓子秧歌多已改换成大妈们的集体舞,有时为了比赛还女扮男装,在性别上已经是非历史化了。类似情况非常普遍,像湖北“巴山健身舞”的广场舞,也是转换为女性主体,废止了“男跳发,女跳塌”(男人跳就會发达,女人跳就要倒霉)的历史规约。“中国广场舞”又称“中国大妈舞”的原因大约就基于此。
身体历史学的失忆,必然带来身体美学的失准、身体语言学的失语和身体伦理学的失范。“水兵舞”和“肚皮舞”带着某些独特的美,但不是中国的;“僵尸舞”和“手套舞”是中国大妈独创的,但不美。即使扭中国民间的大秧歌,其手中折扇的举扇敬天、落扇敬地、齐眉扇敬人的“天地人合”的身体语言,也随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消失而消失。但不能由此断定中国广场舞没有语言性,只是其身体语言极为简单——“我快乐”“我健康”“我任性”,类似于体操演员所表达的“我健美”“我灵巧”“我技艺高超”。于此之中,身体伦理学的个人伦理叙事取代社会伦理规约,继而引发出社会科学问题和是否真“健康”的自然科学问题。
四、社会科学的焦虑和自然科学的悬疑
美国人雷·哈奇森主编的《城市研究百科全书》道出了现代城市种种重要话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叉关系。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渐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型社会向以非农业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二○一二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这一进程所带来的问题包含众多研究领域,而每个研究领域又包含着许多分支学科。世界上没有中国这种作为城市现象的广场舞,所以没有“城市舞蹈学”,但我们却回避不开中国城市产生的这个重要现象。
作为一种身体姿态,中国广场舞宣泄了诸多不良情绪,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我很快乐”、“我很健康”、“我很任性”乃至“我很青春”。中国广场舞构成了生活的“彗星的尾巴”,使劳累一天的人们用以消磨业余时光。而对那些退休的大妈来说,它即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身体多余的能量被消耗在舞蹈活动当中,形成一种临时的非熟人社会的和谐。但这种能量发散到社会学视角中城市公共空间的不同区域时,社会问题与冲突也暴露出来,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都面临着压力和挑战,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放的为争夺舞蹈场地而发生的流血冲突。
这些问题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引发的,即广场舞的成本和公共资源的争夺问题。在日本,每年一度的“花祭”也算是一种广场舞:以神社为中心的广场,由地方政府投资装饰,身穿节日服装的日本男女老少以民俗舞蹈来欢度节日。太阳出来时先由孩子们跳,之后是年轻人、中年人,一直跳到日落时老人们出场,满目花海与人海,井然有序。在巴西,还有耗资更大的广场舞——“狂欢节”的桑巴舞。与之相比,中国广场舞既是最低成本的大规模舞蹈活动,也是最低成本的个人健身体育活动,对于参与者来说几乎不需要成本。如此热闹和廉价,广大低收入市民便自然而然地加入到这种几乎无成本的娱乐健身活动中。而这种活动一旦被要求加入成本(如为避免噪音要佩戴耳麦)和限定跳舞场合(比如离家最近的社区休闲场所、公园、球场等),问题和冲突就会发生。两个实际的例子是:在北方长春市的净月公园,因为收取门票,所以公园内安安静静,没有广场舞;在南方,浙江温州丽水市政府为市民修建了一条长8000米的宽阔塑胶步行大道,旁边绿树成荫,大道上市民跑步和行走,自然地取代了广场舞。
除外部原因,中国广场舞问题的冲突和产生还与舞者的教育密切相关,不仅是思想道德教育,而且是舞蹈本体教育,它直接关系到国人的身体伦理养成,也是一种文化政治姿态。从教育对象看,中国广场舞是目前最大人群的身体教育方式,关系到舞者自身,也关系到观舞者:你扭秧歌,你就感受到秧歌的律动,观者亦感受到秧歌文化;你跳“水兵舞”,你就自认为是俄罗斯水兵,观者就像看俄罗斯芭蕾舞一样旁观异质身体文化;你跳“肚皮舞”,你会感受到一种乖张的“S”型,观者也会看到一种怪异的城市身体文化……换言之,中国广场舞巨大的身体教育平台既可以给中国舞蹈的普及带来文化与审美的福音,也可以带来负资产。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中国大妈们带来的孙子孙女在手舞足蹈地模仿她们时,这种对未来的焦虑便油然而生。正是基于此,诸多专业人士已经着手编写广场舞教材,但其前提应该是在主流舞蹈的建设思想厘清之后。
最后,我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谈谈中国广场舞。宏观地看,这里面有一个生态学问题。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城市生态到舞蹈生态,它是一个循环系统。如果一边是“我快乐”“我健康”“我任性”的狂歌劲舞,一边是公共领域被侵占(包括视觉、听觉和实体的物理空间的侵占)和不断的社会冲突,这就不是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微观地看,中国广场舞所带来的心理学、生理学、运动力学、运动医学等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今天,中国广场舞已经纳入了某种竞赛机制,赛场上的评委俨然分成两类——舞蹈的专业人士和体育的专业人士,前者以“美学”来判断,后者以“训练学”来判断,“任性”而为的舞蹈可能会产生某种“快乐”的生活美,但它未必是“健康”的……
总之,中國广场舞蹈的学理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如果只片面强调其中的一个视角,就会产生偏差,难以提供全面认知和对策。用哈奇森《城市研究百科全书》的话来讲,中国广场舞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城市地理学、城市历史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等认知类的学科,加上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管理学、城市防灾学等操作类学科,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学科集成。这个学科集成应该寻找到相应的学理,为中国广场舞提供合理操作规范,以缓冲它与诸学科范畴的紧张性,这或许才是中国广场舞的出路。
结语
应当看到,“中国广场舞”和“社区文化”中的社区舞蹈远不是一个概念:以世界舞蹈为坐标,前者庞杂模糊,后者应该较为具体清晰。比如美国华盛顿东区(黑人区)的社区舞蹈,有专门的非露天的舞蹈场(里面有相应设施以及黑人舞蹈的照片与舞蹈文化资料),有专门的社区舞蹈教师(或专职或兼职),有专门的舞种传授(诸如南非黑人传统的“战斗舞”“矿工舞”等),有专门的学习或表演时间,并有专门的舞蹈群体。与移民国度的美国不同,日本的社区舞蹈则呈现出单一民族的多元一体。在北上市,广场、街道、寺院和百货公司前常有规定日期的“鬼剑舞”表演,涵盖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和成年市民,也有各地的鬼剑舞团体。“以鬼剑舞为荣耀,以鬼剑舞为使命”使得北上市儿童从小就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广场及主干道鬼剑舞的表演期间,几乎全城市民都参与其中,他们大半都身着传统和服或浴袍,根据规定的步伐和动作在大街上游行,热闹非凡。在公演中,又有东京鬼剑舞、京都鬼剑舞、函馆鬼剑舞、滑田鬼剑舞、岩崎鬼剑舞、北藤根鬼剑舞、谷地鬼剑舞等多地区的表演,每个地区的鬼剑舞总体风格相同,但编排和表演水平各有千秋。[1]由此形成一种舞蹈学、艺术学、文艺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视域内可以整合的个案。
中国广场舞的前途,应该是走向社区舞蹈,其前提条件是:第一,重建公共领域及公共意识,允许并保障在公共性问题上的“理性的公开使用”,以理性、平和、负责的态度对待公共资源,淘汰极端的、激情式的、不负责任的占有方式。第二,发展并强化各种位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社群和组织(社区),使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个体重新嵌入社会、防止城市个人的原子化、游民化。如涂尔干所说:“如果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他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2]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才可能达到,因为与破坏相比,重建一种舞蹈文化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广场舞蹈与社区文化建设研究”(17ZD04)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张军、王雪:《日本鬼剑舞文化探微》,《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2]王小章:《群氓是怎样炼成的》,《读书》,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