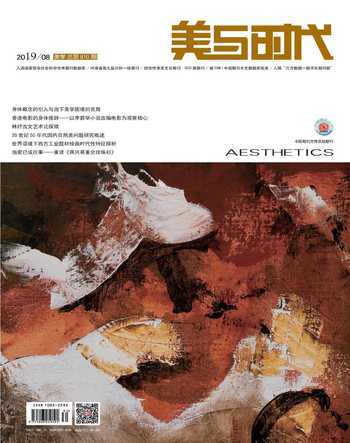当爱已成往事
摘 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文是《喻世明言》的开卷之作,该小说迭出的巧合稍显虚假,但其叙述的夫妻因缘和爱恨纷争古今一理。解读人物心理、剖析复杂人性、展示可贵真情并以之观照当下的现实也可作为一个批评切入角度。
关键词:古典白话小说;《喻世明言》;夏志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古典白话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完满结局让人心悦,无论是“因果有报无虚谬”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终归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一夫二妇,团圆到老”,好不叫人欢喜。这部小说是《喻世明言》的开卷之作,也是冯梦龙所辑《古今小说》的头篇,由此可见作者对它的看重。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舐犊情深无可厚非,但评论者则大可不必,总还是要本着客观的态度有甚说甚,绝不能一味戴高帽捧臭脚。评论界向来就有“吹嘘派”,见东说东好、见西说西好,这些“好好先生”并不见得能够识得好东西。
别人做“好好先生”也就罢了,毕竟这世上爱讨乖巧的俗人居多,可是搞中国现代小说史评论的学者夏志清竟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视为“明代最伟大的作品”,这显得有失水准,叫人大跌眼镜。从形式与内容两点论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文在艺术层面是可以称道的,其语言流畅、构思奇巧、情节曲折,但若从思想内涵层面和现实观照层面观之,夏先生的论断却大可商榷。
一、巧合迭出 稍显虚假
“巧合情节的设立,是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是我国小说创作叙事结构的典型代表。我国古代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都讲究一个‘巧’,即说书、唱戏,无巧不成。它是我国叙事文学创作中作者的基本结构思路,反映了我國读者或听众对传统叙事文学作品审美心理的思维定势。”明代白话小说为了迎合读者猎奇的审美心理需要,非常重视情节的设置,产生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巧合成了结构小说屡试不爽的叙事策略。
让我们且看这个巧合迭出的故事:蒋兴哥和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婚后四年,蒋兴哥为了广东的生意便要外出经营,他和三巧约定“好歹一年便回”。假如蒋兴哥按时回家也就没什么事了,可他偏偏在广东得了一场病,一年头上回去不成。三巧听信卖卦先生丈夫月尽月初必然回家的话,便时常向前楼走动并在帘内东张西望。陈大郎偶然一日进城,穿戴打扮恰与蒋兴哥平昔相像,三巧远远瞧见以为是丈夫回了于是定睛而看。此时此刻,陈大郎也偏偏抬头望见了楼上目不转睛的美妇人,于是一片精魂便被摄了上去,作为一个外乡人,本应人生地不熟的陈大郎恰想起与他做过珠子生意的薛婆,于是乎薛婆和陈大郎为“买卖珠子”故意喧嚷,三巧也就偏偏欲买珠子,便唤那薛婆入室……
陈大郎奸骗了三巧,这一事件又是怎样暴露的呢?小说作者没有采用蒋兴哥怎样觉察、捉奸和冲突等俗套,而仍然设置了偶然性的巧合:陈大郎在苏州赴同乡人的酒席,席上巧遇蒋兴哥。这本是生活中的偶然相遇,谁知两人竟因年相若貌相似成了知已。蒋兴哥在回乡之前到陈大郎处作别。酒席之上陈大郎若不解衣也就没什么事了,可他偏偏解衣饮酒,解出了蒋门祖传之物珍珠衫。兴哥本来已经心中骇异,陈大郎又恃了相知把和三巧相好之情诉了一遍。后来,兴哥忍痛休了三巧,假如三巧悬梁自尽,故事也就结束,可她偏偏被母亲王婆看见救得下来。再后来,陈大郎生意本钱全被劫去,病死在枣阳,妾子平氏偏偏就嫁给了蒋兴哥。蒋兴哥再去广东做生意吃了人命官司,又偏偏告到三巧后来的老公吴县主手里。吴县主灯下阅状,三巧偏偏在旁边看见,被告罗德正是前夫蒋兴哥。
但是,小说中并非所有的巧合都合乎情理,符合生活逻辑,文中有些巧合就稍显牵强。在此略举三例:其一,陈大郎诱奸了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后,蒋兴哥休了王三巧,但续娶的恰好是陈大郎的妻子平氏,这个安排出人意料但难以令人信服。更多的是作者从惩恶扬善的道德说教角度对因果报应的自圆其说。其二,蒋兴哥陷入人命官司,断案的恰好是王三巧的丈夫吴杰,并且案卷恰好被王三巧看到,蒋兴哥由此死里逃生,王三巧这个角色经过了一连串的波折最终又回到了蒋兴哥身边,这也是作者为了因果轮回而有意设置的巧合。其三,最让人难以信服的是小说故事的结尾——蒋兴哥和王三巧重新结合,要知道吴县主娶王三巧是“看了多少女子,心不中忿。闻得枣阳县王公之女,大有颜色”,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才选中的美妾,他岂能因一时心善就把三巧送还蒋兴哥呢?这可真是为追求奇巧情节,表达因果报应的编排。它离开了真实的世俗生活,显得无比虚假。
二、事出有因 古今一理
事实上,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反而削弱了小说的味道及其应有的艺术魅力。巧合源于生活,社会生活是产生巧合的基础,但巧合不是故弄玄虚和荒诞离奇,当巧合与想当然的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违背生活逻辑并损坏文本真实。无可否认,巧合的运用确实为小说增色不少,情节的曲折带给我们新鲜的感官体验和情感共鸣,但如果只以因果轮回和道德说教为目的去设置巧合情节、忽略小说的艺术效果与思想意义,就不免把真实流于虚假。
重读文本,应该重新审视这个故事重现的可能性。回到最初,故事起因是蒋兴哥离家经商,这个支点撬起了一部大戏。于是王三巧的出轨就有了一个特定的情境:配偶失位。其实在任何时代,这种情况是缺免不了的,即使在今天也是正常,求学、入伍、出国、他乡买卖、异地供职等都是鸳鸯两处的原因。事实上,“与君生别离”是对夫妻感情和婚姻坚固度的另一种考验。如果故事仅停留在怨妇思夫日日苦等夜夜思念之上就没了嚼头,于是作者让第三者陈大郎出场了。抛却了王三巧错认为夫的因素,她与陈某就是孤男和怨女的“一见钟情”。
道理很简单,纵观人的一生,一个男的不可能只钟爱一个女的,反之亦然。但为什么不可以见色起心、见异思迁,那是因为道德、风俗、伦理等因素的制约。如果说三巧与大郎在古时的“多看你一眼”是出于巧合,那么放眼今日,这样的机会就非常多了,更何况有现代化的聊天社交软件专门为素不相识的人提供这种便利。陈大郎没有手机或者网络,薛婆就成了他渔色猎艳的媒介,“套耗子还得个油灯焾儿”,陈大郎预付下的本钱就是百两白银和十两金子,真可谓“决心可嘉”。干薛婆这种营生的,其实是最缺阳德损阴德的——撩动妇人春心、破坏他人家庭,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现身说法,真是“合当拉来这老厮,剥其皮、寝其骨,但不食其肉,免得脏了胃口”。可叹的是,人类走到今天,我们自己就在科技飞速发展之下造设出了各种“薛婆”。小说里的薛婆是人,可打可骂,更可罚惩教育。但今天的“薛婆”——无形的网络、媒体,有形的手机、电脑,我们是该打还是该摔?
三、理解万岁 真情可贵
“世间只有虔婆嘴,哄动多多少少人”“排成窃玉偷香阵,费尽携云握雨心”。陈大郎没有看错人,薛婆也真不是吃白食不管事的,你看她步步为营逐渐靠近了目标,一点点打消了王三巧的戒心,最后二人竟成忘年闺蜜同寝同睡。火候已到时局已成,这薛婆巧用乾坤大挪移之法狸猫换太子,把赤条条的陈大郎送到了三巧儿的床上遂了雇主心愿。书中交代,干柴烈火好事做成原因有二,“一则多了杯酒,醉眼朦胧”,我认为这只是为三巧开脱之辞,实非主要原因。一赤身男子入于被里,感觉再迟钝的女子也不会丝毫没有察觉,况且大郎此时的身子又非比寻常。事实上,第二条说王三巧“被婆子挑拨春心飘荡,到此不暇致详,凭他轻薄”,这才是关键所在——此时的王三巧绝对是情欲胜过理智,早已想不得太多。怎么说呢?人从根本上讲还是动物,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或不乱坐怀的男女还真是稀缺,毕竟大家都是俗人。别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相貌堂堂的某些大学者不也是衣冠其外、禽兽其里吗?弄得人家“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尘雨打萍”。与这些“叫兽”相比,三巧儿毕竟是“守寡”多时,这次只是没硬撑过去罢了。即使如此,委身之后的三巧还是担心满怀,“万一我丈夫知觉,怎么好?”薛婆不是吃素的,立马晓以宽慰安抚其心。没拿到台面上的罪恶都不是罪恶,被突破第一层防线的三巧儿“也顾不得许多了”“又狂荡起来”。婚外情从古到今都不是甚稀奇之事,只是曝于阳光下或藏于被窝里之区别罢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固然是美好的,但美好往往易碎,在庸常的消磨之下感情最不靠谱。不想庸碌麻木、郁郁终身的人便把眼光抛向别处,这很难一言以蔽之为败德恶行。人生苦短,全得看一己的世界观。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陈大郎也要离去,但这露水夫妻却不肯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反而是倍加眷恋,王三巧竟要卷钱与这郎私奔。也难怪作者不无慨叹:“堪恨妇人多水性,招来野鸟胜文鸾。”事未遂愿,妇人就把珍珠衫儿亲手与汉子穿下,“再三珍重而别”。无巧不成书,商旅途中陈大郎竟与三巧丈夫相遇。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说蒋兴哥的肚里能撑得下宰相。按理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让人不共戴天的,即便是今人的捉奸在床,最可能的场面也是打作一团,可他知了这等羞事竟兀自忍了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孰也可忍,实在让人敬佩。对待出轨妻子,蒋兴哥的做法足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大气!虽然“气得面如土色,说不得,话不得,死不得,活不得”,但他没有像《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那样将偷情的妻子开膛剖腹,更没有揭露她的隐私,而是巧妙地保存了妻子的颜面。后来三巧儿再嫁,他也“并不阻当。临嫁之夜,顾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她新夫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陪嫁”,这样的伟丈夫真是难得。话说此人之善举可否重现在今日?想必绝不可能。今人是讲实际讲效益讲投入产出性价比的,若有离异,女方早已忙于分房索銀弄家产不迭,根本不用好心的蒋兄施舍,自会把一切料理妥当。
作者有心设计三巧儿再嫁吴杰进士,为最后的破镜重圆埋下伏笔,最后大团圆众心欢喜。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巧合的夸张性前文已有阐述,但在这里,我们也能体味到一些别样的东西:当今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但走出围城之后,许多人也实际上未能得到想要的美好,于是,追悔前情自责不已。其实一日夫妻百日恩,若不能在他处寻得幸福,回头路也不是不可考虑,要知道:好马亦食回头草。但两个前提条件必不可少:其一,彼此生命还有交集。蒋若不遇官司,也不会再捧美人归;其二,彼此心里有爱存在。蒋与王两人一见便“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就是哭爹喊娘,从没见这般哀惨”即为证。
四、结语
世间之事,大抵不过男人的事、女人的事,还有男人和女人的事,能不费心于是乎?文学即人学,当我们重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之后还是要明白,作者只是为你我叙述了个故事罢了:在爱已成往事的时候,生活还是要与艺术分开的,不然生活会乱,人自己也会乱。
参考文献:
[1]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M].陈熙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2]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胡益民,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范正声.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J].东岳论丛,2003(2):123-126.
作者简介:张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法理论和现代汉语语法,兼及修辞学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