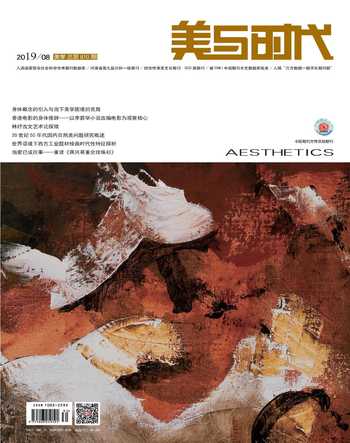圣人的无与空
摘 要:《甘泽谣》为唐朝袁郊撰写的传奇小说集,其中《懒残》一篇流传甚广,颇为后人赞誉。该篇围绕李泌、懒残和尚二人的传奇故事进行叙述,阐释了道家的飘逸之美与禅宗的空灵之美,行文精妙,寓意深刻,是唐朝文学的吉光片羽。
关键词:甘泽谣;李泌;懒残;无;空
佛、道二教对唐朝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就《甘泽谣》而言,主要体现在《圆观》《红线》与《懒残》诸篇。《懒残》一篇中,李泌的道,明瓒的禅,相辅相成,向我们诠释了何为圣人之美。故事层层递进,扣人心弦,让人回味无穷。
一、李泌的道
天宝初年,李泌隐居于衡岳寺。寺中有僧明瓒[1],号“懒残”。懒残者,性懒而食残也。《甘泽谣》所注懒残传奇不过三则,一为食芋和预言李泌拜相,二为踏巨石以开山路,三为除虎豹。其中第一、三则尚有记载,第二则暂无考据。除此三则之外,另有德宗召懒残出山被辞一说,原典未曾提及,因昭宗在位时,袁郊出任翰林学士,著文谨慎之故。
李泌自幼好讀《易经》,擅黄老之术。肃宗在位时,李泌为平安史之乱出谋划策,“权逾宰相”,遭到崔圆、李辅国等要臣妒忌。直至收复两京,李泌飞遁离俗,隐于衡山修道。帝念其功绩,遂“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①李泌此举颇有张良、范蠡之情操,可谓“谦退”②。《易经》六十四卦载,只有谦卦,六爻皆吉。不贪功劳,不与权臣争斗,有道家风骨,体现了“游”的精神境界。“游”,一指精神的自由超脱,二指人与大自然的生命融为一体[2]。李泌退而致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醉心衡岳山水,砥志研思易老之学。若非后来从代宗诏命还京,衡岳寺即为李泌安享晚年之所。
宋人周密《齐东野话》卷五云:“李泌在衡岳,有僧明赞,号懒残。泌察其非凡,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拔火中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
“是日,李泌闻懒残吟诵梵呗之音,中夜谒见,却得懒残诟骂。”《齐东野话》略去此事,稍有欠妥。懒残初识李泌,尚不知其根本,恐出言不逊,惹李公震怒而问罪,危及隐世生活。然李泌“愈加谨敬,惟拜而已”,能够放下姿态,难能可贵。懒残一诟,昭示了他不拘礼教、不涉尘世的圣人气概,李泌一拜,彰显了他不矜不伐,移樽就教的阔达胸襟。李泌拜“良久”后,懒残才令之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懒残或已领会李泌持之以恒、虚心求教的态度。授之以芋,可表认同之意。当时懒残正于牛棚之下,以牛粪火煨芋,环境定不如室内,李泌仍然席地而坐,“奉承③就食而谢”,没有为官自傲。懒残视而谓之曰:“昚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后世皆以道家预知未来祸福之术称颂懒残道行高深。然设身处地,眼前跪拜之人既是当朝“权逾宰相”的大人物,又降尊临卑,屈高就下,虚心问理,如何不令人动容?与其说是僧人以易经之学、相面之术卜其仕途,不如说是识人之明、赏其品学推而得之。
有关食芋轶闻,千古流芳。后人谈及此事,或以自况,或以赠勉。据《〈甘泽谣〉评注》所载,由宋至清,各朝咏懒残者不可胜数,但咏李泌求教一事者鲜矣。宋有孙觌《再过天长寺》“芋火鹑衣对懒残,铜瓶泣雨又更阑”;范成大《题查山林氏庵》“山僧见客如枯木,疑是懒残南岳师”;元有陆文圭《送北禅释天泉长老入燕》“君不见懒残昔住衡山峰,使者召之终不从,天寒垂泣石窟中”;明有李昌祺《寄定岩戒上人》“拟拨懒残煨芋火,蒲团分宵话声尘”云云。至于清代遗作较少,大抵是与文字狱有关。
颂李泌之诗文,内容以其赞为官之道居多。如,徐钧《李泌》:“衣白山人再造唐,谋家议国虑深长。功成拂袖还归去,高节依稀汉子房。”沈鼎科《容台集后序》:“嗣是,若唐之李邺侯④,……庶几帝师之选乎。……朝披一品衣,夜抱九仙骨,如李邺侯而善藏其用。”
就此章而言,李泌请教懒残所为何事,不可得知。懒残既发李泌拜相之语,若非空穴来风,李公必有问其为政为官之道,方可引出前言。为政时鞠躬尽瘁,淡泊明志;归隐时独善其身,心系朝政。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李泌说懒残“非凡物也”,只有同属“非凡”,才可相互赏识,心有灵犀。儒生有云:“才德全尽谓之圣人”⑤。李泌专《易经》,擅黄老,博涉经史,著有《养和篇》《明心论》(已佚),其诗收录于《全唐诗》,不可谓无才。上谋政理,三朝立功,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下通仙道,宁静致远,掷胸怀于大好河山之间,不可谓无德。才德全尽,李泌可谓圣人也。
二、懒残的禅
懒残擅梵呗。梵呗,是和尚吟诵经文的形式,相传由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陈思王曹植游鱼山,有感而创,故又称鱼山梵呗。魏晋时期,佛学东渐,佛教音乐也随之而来。隋唐时期,得益于西域交通的发展与唐乐府的采用,梵呗得到了广泛普及,中国梵呗进入了辉煌时期。《甘泽谣》对懒残梵呗之音的刻画仅以“响彻山林”一笔带过,但李泌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坠之人,时将去矣。’”
梵呗旋律优美,节奏沉稳,由于它的艺术性主要服务于宗教,所以其演唱形式较为固定。在这固定的形式中蕴涵了禅宗的“空灵”之美。《古尊宿语录》有言:“闻声悟道,见色明心。”[3]李泌在懒残的经声中听到了悲喜,在刹那中体悟到永恒的情感,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是一种形而上的愉悦。
履石而动一说,后世鲜有考证。十牛及数百人尚不可移,仅凭一人之力投机取巧遂开山石,不可尽信也。若仅论其艺术手法,袁郊此处的悬念布置可谓匠心独具。前提有三:其一为“刺史祭岳”。古人对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解释,对山岳的崇高感到敬畏和恐惧,于是产生了这些现象都是由山神主宰的观念,将山岳神化并对其崇拜。在《山海经·山经》和殷《卜辞》中都对祭岳有明确记录,祈祷山神以求风调雨顺,保一方平安。此乃国之大事,不可拖延;其二为“修道甚严”。“严”字在此作“紧急”义。祭祀日期愈近,则工期愈紧。慌忙之中,补给、规划不足,并无应对突发事项的准备;其三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仅此一路至山巅,没有再开一路的条件。三则前提决定移石迫在眉睫,设下悬念。然十牛縻绊不可挽,百人鼓噪不可推,开路之举,实属不易。此类铺陈,皆为反衬懒残履石而动的高明。
巨石动,山路开,众僧五体投地,刺史奉之如神,“皆呼至圣”。懒残此举,不仅使僧侣众人信服,也使刺史免遭朝廷问罪,但却令他悄然自悲: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去”的意思,解释为“离开衡岳寺”更加恰当。前文写李泌请教懒残,懒残发怒唾骂,可见懒残并不想与俗世有染。一人如此,更何况百余人顶礼膜拜,岂能不怒?因功而怒,不合常理。情绪无法发泄,怒而生悲,遂想告退。日后懒残美名远扬,对他而言却是无法潜心隐遁的负担。离开衡岳寺,云游四海,不被俗人纠扰,更能表现懒残的“去意”,以示其隐逸之风。
在驱虎豹之前还有一段插曲,《甘泽谣》中并无记载,后世有诗文叙之。正值秋冬时节,天气寒冷,被德宗派来召懒残进京的使者,看见懒残鼻涕一直垂到胸口,形貌邋遢。使者笑而令其拭之,懒残答曰:“哪有闲工夫为俗人擦拭鼻涕?”使者不悦,进京一事就此作罢。宋何师韫赏其避世精神,作《自题懒愚室》诗以自况:“君不见南岳懒残师,佯狂啖残食。鼻涕任垂颐,懒为俗人拭。……二子真吾师,欲见不可得。”师韫返璞归真,守愚守拙,潜心浮图之学,颇有懒残风骨。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云:“衡山大明寺虎豹成群伤人,懒残以荆条授僧,命蹑而逐之,虎豹绝迹。”此处记载与原著大相径庭,《甘泽谣》有云:“(懒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后,虎豹亦绝踪迹。”履石和除虎豹二事考证较少,至于后者,原著更能彰显懒残的崇高形象。虎豹伤人数日且无由禁止一句,暗示已有猎户尝试除虎却无功而返。猎户且如此,更何况一僧侣呢?懒残持荆条出门时,早已自明。懒残去,虎豹遁。懒残的献身精神值得称颂。古有曾子谓子襄曰:“……虽千万人,吾往矣。”⑥今有懒残面对虎豹面无惧色,以小我之牺牲换大我之安宁,彰显了崇高的灵魂美。这种美是生命的奉献,是心灵的净化,超越了渺小,使灵魂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驱虎一事,亦可作此解。正如懒残献身以保一方安定,李泌的隐居又何尝不是一种献身——以朝内权臣争斗为轻,以平息安史之乱为重。一语双关,可见袁公功力之深,行文之妙。
懒残鲜有著作流传后世,一篇《懒残和尚歌》足矣:“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列其数语,以参其境。“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禅者在刹那间顿悟永恒的意义。世事短暂,沧海桑田,唯有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之外”,坐忘心斋,不闻俗世,不忌生死,方可获得永恒的自由,以悟至圣。
三、佛道交织下的晚唐思潮与三教合一
晚唐以来,三教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三教一家、三教归一,成为社会风尚。尤其是三教中力量最弱的道教,积极倡导三教合一。《甘泽谣》的三教合一,体现在从相互关系的和谐中提倡三教一家。
佛、道二家高唱三教一家,其目的在于通過强调三教地位平等、提倡三教团结,避免他家的排击,营造适合于自家的生存环境。受正统思想儒家排击的佛、道二教,尤其是实际上地位较低、力量最弱的道教,更须防范儒家、佛教之攻击,有利于三教关系的和谐,故三教一家的口号喊得最为响亮,这也是诱引人信其教的手段。元刘谧《三教平心论》卷上站在佛教的立场说:“谓佛教与道教同,则庶不启道教之争,谓三教可合而为一,则若儒若道,皆可诱而进之于佛。”
道教讲三教一家、道与儒佛一致,当然更是如此。儒、释、道三家,源远流长,各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各有各的特长和用处,自汉末以来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儒家一直作为统治思想的轴心,佛、道两家与儒家相辅相成,组成中国封建社会三元共轭的文化结构,因此儒佛道三元一体文化结构具有稳定性,是社会秩序的思想保障。
四、结语
总而言之,《甘泽谣》以玄言轶闻的形式讲述了诸多深刻的故事,其主旨无不与儒佛道紧密相连。李泌的道家风骨、懒残的释家灵逸相互交织,将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活饱满,同时也衬托出佛道交融的内涵。反映在社会问题上,三教合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适应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旨归在于和谐三教关系从而和谐整个社会秩序。从《甘泽谣》中不难看出,三教合一已开始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这为处理唐以后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出自《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八十》,第1051页。
②《史记·乐书》:“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③按《太平广记》,作“捧承”。
④邺侯:德宗在位,李泌入朝拜相,封邺县侯。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
⑥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参考文献:
[1]李军.“甘泽谣”评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1.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81.
[3]张节末.禅宗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0.
[4]邹燕凌.中国汉传佛教梵呗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5]段晓明.中国山岳崇拜信仰[J].艺海,2012(2):130-131.
作者简介:李宏垣,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