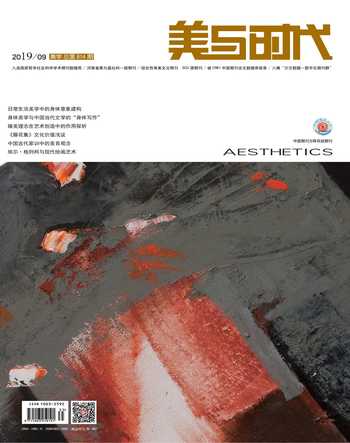2014年以来大陆犯罪片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 要:自2014年的《白日焰火》一片以来,大陆犯罪片呈现出新的创作模式,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是其最大的特色以及成功的要素,人性的挖掘则是其一贯主题,人物的吸引力提到了与叙事并肩的高度。犯罪片作为一个极具市场潜力的类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面向市场时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对《白日焰火》《心迷宫》《暴雪将至》《爆裂无声》四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梳理,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女性:被利用的女性、贤妻良母式女性以及被污名化的女性。这三类型女性中,一方面,有着电影中对女性的传统表达,另一方面,女性人物的反抗,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自我要求、自我认识、自我独立的女性意识的生长。这些影片在保持其深刻的人性挖掘主题不变的基础上,呼唤着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形象的继续书写,也呼唤着更丰富的女性形象的表达。
关键词:类型电影;大陆犯罪片;女性形象
2014年,《白日焰火》一片摘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员两个大奖,成为当年的话题性电影,奖项的助力加上适当的营销,使这部文艺气质浓厚的影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自此之后,涌现了一批融合作者思考和商业色彩的犯罪片。与《盲山》《盲井》这一类借助犯罪事件深挖社会黑暗现实的影片不同,新的犯罪片侧重表现个体在极端环境中的煎熬与自我反思,直指人性的幽微之处。这类犯罪片主要以男性为主人公,女性大多作为男性的对立面或附庸出现。
一、 被利用的女性
在犯罪片中,有一类女性是长期的书写对象,她们外表美丽,兼之强大的性吸引力,往往作为欲望客体出现在银幕上,成为男性的凝视对象。这类女性的代表人物有《白日焰火》的吴志贞和《暴雪将至》的燕子。
《白日焰火》的女主人公吴志贞周旋于多个男性之间,与男性角色的关系揭示了她作为欲望客体的悲惨命运。男主人公张自力接近吴志贞,一方面有着“破案-人生成功”的动机,另一方面源于对神秘有魅力的吴志贞的探究欲和征服欲。劳拉·穆尔维指出,在两性尚未实现真正平等的社会语境下,男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掌控电影的生产与接受过程,从而创造出各种女性形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无意识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被处理成了一种符码,在银幕上成为“被看”的对象。在看与被看的“权利-欲望”关系中,张自力与吴志贞分别处在看与被看的位置,影片中多次表现张自力对于吴志贞主动的“看”。吴志贞第一次出现在镜头中时,并未直接展示她的面部,而是运用了一个对裸露腿部的摇拍,既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主义,又将女性的身体奇观化。直到张自力介入吴志贞的生活、投射出凝视的目光时,观众才第一次看清这个女人的面庞。在接下来过肩拍摄张自力背部的镜头中,张自力成为画面的前景,吴志贞背对着画面的身体成为后景,这个镜头连结了银幕上的男性与银幕前观众的视线,确立了张自力观看的主动权,同时提醒着银幕下观众的视线投射。
影片中,吴志贞两次反抗过张自力的跟踪行为,第一次,吴志贞偷偷递给张自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再跟着我”,张自力不以为然;第二次,吴志贞遭到洗衣店老板的猥亵,张自力将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件事成为吴志贞内心防线的第一个突破口,张自力得到接近她的机会,车站前吴志贞又一次对张自力说“别再跟着我了”,这一次张自力同样无视了她的要求,转而向她提出邀请,而实际上他正密谋着如何利用吴志贞。吴志贞的两次反抗都带着无法自我说服的无力感,与其说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行为,毋宁说是弱者形象的深化。在与张自力的交往中,吴志贞从抗拒到接受再到信任依靠,展现了一个女性从无望的反抗中最终走向失败的过程。
洗衣店老板与吴志贞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和影片中流浪汉与他收留的马形成对照,收留与被收留之中,主被动关系一目了然,这意味着吴志贞必须常年忍受老板的猥亵,才能使自己免于被丢弃的困境。洗衣店老板作为一个性无能的人,是男权社会的他者,他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快感,被他欺辱而无力反抗的女性因此显得更加悲惨。
活死人丈夫梁志军与吴志贞,他们之间呈现占有与逃离的对抗。梁志军的社会身份已经不存在,这令吴志贞脱离了“梁志军妻子”这个身份,语言上的解脱并没有为吴志贞带来实际的自由,梁志军强烈的占有欲促使他杀死一个个接近她的男人,也将危机加诸于她。背叛梁志军使吴志贞完成了一次逃离,不过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逃离,不久她又陷入了张自力的掌控与背叛之中。在片中,皮氅这一反复出现的物象,直指男性对吴志贞的控制,这件象征着男性权利与金钱社会的皮氅,先后经过白日焰火夜总会老板和张自力的手,正是掌握了这件东西,这两个男人逼迫她做出了献身。吴志贞作为欲望客体,在对三个男性的绝望反抗中走向失败。
《暴雪将至》的燕子,特殊的装扮和霓虹灯闪烁的空间暗示了她的妓女身份,这一社会身份加诸于她的是“不纯洁”“低贱”等词汇,因此,她成为了余国伟抓捕针对女性犯罪的嫌疑人的诱饵。燕子是一个想象视域中的受害者形象,始终处在余国伟、想象中的犯罪者和观众的三重视线之下。
对于燕子的分析也可以引入关于黑色电影中蛇蝎美人的描述,大部分黑色电影和犯罪片对蛇蝎美人身体的展现是充满窥视欲的“奇观化”审美,劳拉·穆尔维把这称为男性视角对女性身体的“恋物癖”式的表现方式。男性对女性的恋物倾向,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玩偶之家》式的,将女性变成父权或夫权的漂亮玩偶。另一种是狭义“恋物癖”式的,男人们对女人飘逸的金发、性感的红唇、时尚的皮鞋、闪亮的珠宝都有着火热的激情。燕子經常以红唇形象示人,再加上红色皮衣和皮裙,构成了片中男性的恋物实体,强化了“恋物癖”式的男性窥视的目光,在不断重复的化妆动作中,一个潜在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就出现在余国伟和银幕前的观众面前。
片中总是利用物像的并置暗示燕子的命运,燕子贴在墙上的照片是余国伟将她当成诱饵的开端,在这个场景中,燕子贴在墙上的照片和警察局墙上的女性受害者的照片相对照,燕子第一次与那些女性受害者建立了联系。在燕子发现真相的段落中,她的照片与那些受害者裸露的身体的照片放在一起,燕子等于受害者的结论更加清晰。
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女都是这样的女性:有着独立的意识,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对片中的男性发出冲击,但是她们往往在与男性的交往中产生真情,而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与这类女性有相似之处,燕子尽管干着看不到明天的工作,但一直坚持着去香港的梦想。她爱上了余国伟,但当她发现余国伟并不爱她而是把她当成诱饵时,她说“好像做了一场梦,忽然间一切都不真实了”,爱的梦破碎了,她纵身一跃,以悲痛的方式反抗了余国伟的利用和“背叛”。吴志贞和燕子代表着被男性观看、被男性利用的一类女性,她们也曾有反抗的意识,但反抗行为总是和失败并存。
二、贤妻良母式的女性
这一类女性在影片中的身份通常设定为母亲或妻子,其形象与中国传统的富于母性的女性形象一脉相承,其关键词可以是含辛茹苦的、相夫教子的、维系家庭的,她们认同男权社会的运行方式,是男权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这一类女性包括《心迷宫》中肖卫国的妻子,《暴裂无声》中张保民的妻子,她们成为片中男性的抚慰力量,并不构成叙事的动力。
《心迷宫》中的母亲这一角色,作为肖卫国的妻子,肖宗耀的母亲,是两父子紧张关系的调停者。在可见的场景中,她都与厨房和家务事联系在一起,苦口婆心地劝导儿子听从父亲的安排,尽管如此,肖宗耀真正理解、接纳父亲却是在自身陷入杀人案之后,母亲的意志在本片中是被忽视的。这类女性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她们并不参与到男性的话语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男性的主导地位。
《暴裂无声》中男主角张保民的妻子翠霞是另一典型人物,她总是和许多药瓶处于同一画面中,这直接宣告了她身体的脆弱,腿上的疾病使她丧失了行动力,最常见的动作是几乎静止地坐在炕上,不多见的行动中也总是佝偻着肩背,摇摇欲坠。尽管翠霞自身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不吝惜对张保民的维护,当张保民的母亲忍不住抱怨张保民之前的冲动行为时,她站出来维护了张保民的尊严。
这一类女性并不参与到影片的主要叙事进程中,她们是失意男性的抚慰者。
三、被污名化的女性
这一类女性总是受到男权社会评判标准的压迫,她们生活在男权社会之下,只要违反了男性主导社会之下的女性标准,总会受到男性角色的言语侮辱。这类女性包括《心迷宫》中的黄欢和丽琴。
在《心迷宫》的第一条叙事线中,王宝山在流水席上见到黄欢,两人因王宝山表弟的死发生冲突,王宝山将表弟的意外死亡归咎于黄欢,斥责黄欢是贱货,这一情节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将错误推到女性身上的习惯性做法,而男性在这一行为中得到想象性解脱。黄欢在片中的主要身份是肖宗耀的女朋友,除爱情之外,肖宗耀选择黄欢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被他当做反抗父权的工具。黄欢是肖宗耀反抗父权的一个牺牲品,正是因为在恋爱中处于弱势地位,她需要用孩子来稳固恋情,从肖宗耀的话语中,也直接将她与传宗接代的工具挂钩。《心迷宫》中的农村社会,即使在新的时代,也将父系宗法制贯彻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女性受制于它,也认同它。
《心迷宫》中的另一个女性丽琴是第二条叙事线的主要人物,她也属于男权规范下被污名化的女性。丽琴年轻时与王宝山的恋情遭到男方家庭的反对,遭到拋弃的丽琴被村里人唾弃,导致她只能嫁给现在的瘸子丈夫,受到丈夫毒打后,她只能将痛苦转化为对丈夫的背叛。在情人王宝山被当成杀人犯之后,王宝山为证清白不惜牺牲她的名节,在众多男人面前,她冷静地否定了昨晚与王宝山在一起的事实,“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做法为这个人物添上了无情的色彩,也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在男权格外稳固的农村社会,妇女的名声就是一切。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返还给男性个体以灾难,不得不说这是对男权社会的讽刺。
丽琴这个角色是有着反抗色彩的,早年的经历为她带了污名,使她陷入困境。但是伴之而生的潜意识下的反抗精神,虽然并没有将杀夫的意图付诸实践,然而将丈夫的骨灰与拐杖一起埋葬正是她获得新生的体现。与王宝山断绝关系,拒绝心仪她愿意为她杀人的大壮,都代表着受到男性伤害和男权社会压迫的她认清了事实,并主动断绝了这种不对等的关系。
在这一类女性身上体现了一个事实:男权社会形成了诸多女性规范,女性或遵循这一规范,或违反规范以致被污名化处理;而男性总是将过错推到女性身上,幻想在对女性的污名化中脱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白日焰火》《心迷宫》《暴雪将至》《爆裂无声》四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梳理,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女性:被利用的女性、贤妻良母式女性以及被污名化的女性。这三类型女性中,一方面,有着电影中对女性的传统表达:女性的地位始终次于男性,或是欲望客体,或是抚慰男性的角色,这是女性形象塑造中不变的一面;另一方面,女性人物的反抗,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自我要求、自我认识、自我独立的女性意识的生长,这是变的一面。犯罪片作为一个极具市场潜力的类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面向市场时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保持其深刻的人性挖掘主题不变的基础上,呼唤着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形象的继续书写,也呼唤着更丰富的女性形象的表达。
参考文献:
[1]周宪,主编.视觉文化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宋鑫,朱洁.2014年以来大陆犯罪题材电影的创作转向探析[J].文教资料,2017(32):204-206.
[3]祖纪妍.简述蛇蝎美人的历史溯源与发展变迁[J].当代电影,2015(4):68-72.
[4]吴洪娣,管仁福.论我国百年电影女性形象的嬗变[J].电影文学,2007(21):19-20.
[5]张艺凡,陈富为.《心迷宫》的叙事结构和人性主题解析[J].大众文艺,2016(19):188.
作者简介:张莉,上海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