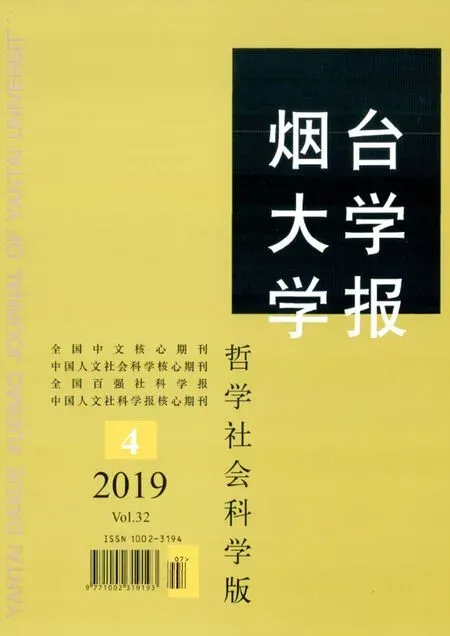“东不过江黄”:晚商周初王朝东界及其政治地理格局
刘佳琳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商周政治地理格局,特别是中央王朝统治四至,是学界密切关注的传统课题。当时疆域形态大体上是多种族属与政治实体插花式交错分布,虽不必有国界的概念,王玉哲先生指出,商代国界或边界概念还没有产生的可能,另有不少学者认为疆域式国家是东周时才开始出现。见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林沄:《商史三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第46页。笔者认为,晚商时期边界的一般概念似已经形成。但诸多文化单元在事实上形成了交界面,也即边界。边界作为具有一定宽度的地带,本文所探讨的边界,并非现代线性边界,正如拉铁摩尔所强调,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地带,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不同文化在此纠葛、交融,其多元与动态的特性相较于中心地域似乎更为突出。因此探讨商周统治边界,不仅仅是为了考察早期国家空间发展的最大限度,边界地带本身的政治地理态势同样值得关注。
《汉书·贾捐之传》所载“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之语,因可信度较高,[注]李民:《〈汉书·贾捐之传〉所见商代疆域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往往被视为探讨晚商周初四方边界的重要参照。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中异地同名、族迁地随等复杂现象普遍存在,学界对“江、黄”地望之认识尚有分歧,[注]孙淼:《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79、380页;周书灿:《殷周“地东不过江黄”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李民:《商王朝疆域探索》,《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不免影响对商周东界政治地理形势的认知。
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贤时彦研究基础上,梳理不同时空范围中江、黄地望,明确晚商周初王朝东界大致所在,进而以江、黄地名变迁为线索,探讨江、黄等族群的流播情况,勾勒这一边缘地带可能存在的族群迁徙线路。
一、淮水之江、黄与商周东域
商周统治东界的确定,除考察考古学文化分布外,对文献中记载的江、黄也应予以足够重视。春秋时期淮水流域恰有江、黄,不少学者以为此即《贾捐之传》之江、黄。[注]孙淼:《夏商史稿》,第379、380页;李民:《商王朝疆域探索》,《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李民:《〈汉书·贾捐之传〉所见商代疆域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但从二国方位、时代及族姓等方面来看,此说恐怕尚有商榷的余地,试分析如下。
春秋时期淮浦江、黄的地望较为明确。江在息县西南、正阳县东南,[注]徐少华:《江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考辨》,《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黄在今潢川县西北十二里,[注]在信阳潢川、光山一带,曾多次出土春秋时期黄国器物,并且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春秋黄国故城。参见信阳地区文管会、潢川县文化馆:《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杨履选、杨国善:《春秋黄国古城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81年第1期。皆在今豫南信阳市境内。但目前尚无考古学证据表明东周之前江、黄即在此地,其早期居址或另有他处。商周时期,随着地理知识的积累与交通发展,先民已有十分明确的四方观念。[注]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而今息县、潢川一带,无论于安阳抑或洛阳,恐怕很难谓之“东”。[注]周书灿:《殷周“地东不过江黄”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更何况《贾捐之传》对疆域南界有“不过荆蛮”的描述,江、黄地域与荆蛮相近,若为东部边界,着实令人不解。
另一方面,江、黄皆为嬴姓。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黄氏、江氏……蜚廉氏、秦氏……”[注]《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1册,第277页。黄为嬴姓之族,也得到出土铜器材料的印证,如黄君簋(《集成》4039,西周晚期)铭文作“黄君作季嬴稻媵簋”;黄大子伯克盘(《集成》10162,春秋早期)也有相似记载。另有湖北随县所出黄季鼎(《集成》2565,春秋早期),其铭文作“黄季作季嬴宝鼎”,有可能是黄季为季嬴所做媵器。[注]李学勤:《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嬴是东夷的主要族姓,少昊氏之后。少昊之墟在曲阜,嬴姓集团本聚居于山东地区。因此,春秋淮域之江、黄极有可能由海岱地区迁徙而来。
以上种种,皆表明将春秋时期淮域江、黄视为商周王朝东界标志恐有不妥。商周统治东界必然应在当时东域范围内找寻。我们首先来看卜辞反映的商王朝的东土:
(1)甲午卜,亘贞:翌乙未易日。王占曰:“有求,丙其有来艰。”三日丙申,允有来艰自东,画告曰:“兒……” (《合集》1075正,宾组)
(2)……东,画告曰:“兒伯……” (《合集》3397,宾组)
两条卜辞或为同一事所卜,是说甲午日亘贞问之后,商王亲自占卜,认为丙日有灾祸,第三日丙申果然在东边有灾祸,画来报告说兒伯如何。其中画是卜辞中常见国族,一般认为即“孟子去画”之画。[注]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页;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史记·田单列传》记载燕师破齐,乐毅令“环画邑三十里无入”,裴骃集解引刘熙说,以“画”为“齐西南近邑”。[注]《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第8册,第2977-2978页。《水经注·淄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澅中也。”[注]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01页。赵庆淼先生考证甲骨刻辞中兒与春秋齐国郳邑是一非二,似应位于临淄西南、淄水上游谷地的今淄川区淄河镇一带。[注]赵庆淼:《齐国“迁莱于郳”与卜辞兒地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等编:《历史地理》第3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页。画、兒与商王朝的关系可能并不相同,但同处淄博一带。另外,商王曾派小臣醜到东对去代理统治:
(3)辛卯……小臣醜其作圉于东对。王占曰:大[吉]。(《合集》36419,黄组)
李学勤先生指出,“圉”意为疆垂,益都苏埠屯亚醜大墓即是小臣醜作圉于东的考古学证明。[注]李学勤:《重论夷方》,《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2页。说明今青州附近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统治据点。上揭卜辞与考古证据皆表明,殷商时期商王朝势力已达潍淄流域。
而金文中“东域”亦不鲜见,且常与东夷联系在一起。东夷是活动于今山东及淮河以北的非华夏族群,其聚居地域一定程度上指示出东域的大体范围。另外西周时期有不少发生在东域的战事,所涉国族多在淄、汶流域。陈絜等学者据此指出,西周王朝东域的主体无疑是今山东地区,南不过淮水。[注]具体论述可参看陈絜、刘洋:《宜侯吴簋与宜地地望》,《中原文物》2018年第3期;强晨:《由西周“东国”看宜侯吴簋中宜地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0期。因而标识商周统治东界的江、黄,似应在海岱地区探寻。
二、东域之江、黄与夷夏分布界限
石泉先生曾指出,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山海经·东山经》有言曰:“又南三百里,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泰山以东的“江”,即今鲁东南之沂河。[注]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1页。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山东沂水即“东不过江、黄”之“江”。[注]周书灿:《殷周“地东不过江黄”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两说皆颇有启发,在此略作补充。
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戉(越)命(令)尹宋盟,述(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逗(属)至北海。晋幽公立四年,赵狗率师与戉(越)公株句伐齐,晋师长城句俞之门,戉(越)公、宋公败齐师于襄坪。至今晋戉(越)以为好。(简111-113)
春秋时期齐、鲁间也有地名黄。根据《春秋》宣公八年记载,“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桓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杜注“黄”为“齐地”,清儒江永认为“是黄为鲁至齐所由之地”[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杨伯峻先生亦认为与宣公八年的“黄”是一地,为由鲁至齐所经之地[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7、693页。。由此可知,黄位于齐鲁交通线上。《水经注·瓠子河》载,昌国县有黄山、黄阜[注]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553页。,杨伯峻先生据以指出齐鲁之间的黄地在山东省淄川镇之东北[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7页。。当时齐鲁南北往来确存在一条“中路”,[注]王京龙:《长峪道:一条新发现的古代齐鲁大道》,《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郝导华等:《试论齐国的交通》,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54页;庞小霞:《先秦时期齐鲁交通的考古学观察》,《管子学刊》2018年第3期。故杨说可从。
沂水与淄水上游的黄山黄阜,大致可视为晚商周初统治东界所在。当时王朝东界所区分的文化族属,无疑应是中原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因此这一界限也基本符合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夷夏分布。
鲁中泰沂山脉将海岱地区天然地分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江、黄所在的沂沭流域与潍淄流域,恰皆可视为晚商周初夷夏势力的交界地带。鲁北潍淄流域基本是山前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史前及商周遗址颇为丰富。一般认为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分界即在此一带,但具体看法尚有细微区分,有观点认为以白浪河[注]栾丰实:《商时期鲁北地区的夷人遗存》,《三代文明研究》编委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弥河[注]任相宏:《泰沂山脉北侧商文化遗存之管见》,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编:《夏商周文明研究:’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54页。为界,亦有学者主张商周文化已越过潍河直到胶莱平原[注]张国硕:《商王伐东夷事件之考古学佐证》,《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4日;邵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燕京学报》2001年第2期。。考古遗存揭示潍淄流域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来自中原的商周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交织,力量对比随时空不同而发生变化,足见夷夏双方在此地带的角力与拉锯。故而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不可能用一条线简单地区分开来,而必然存在一个碰撞与缓冲的地带。曹艳芳等学者以淄川区北沈马遗址和潍坊会泉庄遗址为界点画出这一地带的范围,即商末周初典型商文化东界在淄河西岸,商文化东进的东界在潍河西岸,向东没有越过潍河;单纯的东夷文化主要在潍河以东胶莱平原和胶东半岛地区,夷文化的西界亦在淄河西岸。[注]曹艳芳、尹锋超:《淄潍河流域商末周初考古遗存研究》,任相宏等编:《淄川考古:北沈马遗址发掘报告暨淄川考古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71页。分析详实,颇可信据。至西周分封,太公吕望分封至齐,“营丘边莱”(《史记·齐太公世家》),尚有莱夷与之争边。因此,“黄”作为晚商周初王朝的东部界点,地望在淄博淄川区一带应不至大谬。
而江所在的鲁东南沂水流域,同样是一个夷夏文化的交界地带。通过考古遗存分布,可清晰看出商文化向鲁东南地区推进的两条路径。其一是浚河河谷,据调查,沿浚河分布的商文化遗址约有20余处。[注]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54页。而沿尼山东南麓分布的商文化遗址带,则指示出商文化自滕州前掌大沿尼山山前地带东进的另一路线。但目前看来,沂河干流基本未见典型商代遗址,可见商文化东进止步于沂水西侧的丘陵地带。至西周初年,鲁东南地区仍有夷族踪迹。《书序》言:“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可见周初有夷人在曲阜以东地带。《诗·鲁颂·閟宫》描述更加具体:“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峄,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诗文是说,鲁人经过龟山和蒙山就到达淮夷地区,经过凫山和峄山则是徐夷领地。当然,这里淮夷可能是东夷之误称,[注]鄢国盛:《西周淮夷综考》,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第14页。但总归反映出周代在龟蒙以东地区有夷族聚居,徐夷则在鲁东南,正是沂水流域。因此,“江”作为商周文化东界的另一界标,位于沂水附近也十分符合当时夷夏分布情况。
三、晚商周初王朝东界的夷族分衍与迁徙
商周时期的地名并非是单纯的地理要素,往往与之承载的国族名有密切联系,体现为族名与其居地名称的普遍重合。并且“一个民族每迁至一地,往往即以他们的旧居地名名此新土”[注]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8页。,这也即所谓的“族迁地随”。通过剖析地名变迁的历史过程,无疑可以窥探其背后蕴含的族群活动史迹。故而不同时空范围的江、黄,恐怕是相同族群分衍、迁徙所遗留的痕迹。淮浦江、黄为嬴姓,因此江、黄当是东夷族群。以江、黄为线索,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晚商周初王朝东界夷夏关系的认知。
……王卜,在……今日……彝(?) (《合集》36567,黄组)

(5)黄[其]弜[田]


除此之外,黄与宁地的关系亦十分密切:

就目前材料而言,早期江、黄应该活动于泰山南麓汶水北岸。东周时期沂水、淄水流域与淮水北岸的两组“江”“黄”,无疑是相应国族分衍、迁徙的结果。这一历史过程的复原,须综合相关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加以分析。
随着商民族的征伐,中原文化强势推进,夷人原有的文化格局被打破。相应文化面貌的更替,在考古工作中有充分揭示。例如泗水尹家城与天齐庙遗址,商文化陶器特征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而和之前岳石文化陶器彼此相去甚远,可见土著文化被商文化所取代。[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编:《泗水尹家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09页;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泗水天齐庙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4年第12期。考古学者指出,这是商人东征史事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体现出中原地区商人势力的扩张与东方夷人的退缩。[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编:《泗水尹家城》,第309页。不少学者认为商人在鲁中南地区采取的统治方式,是对土著部族大加驱逐。[注]徐基:《大辛庄遗址及其出土刻辞甲骨的研究价值》,《文史哲》2003年第4期;朱继平:《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在此大背景下,江人恐怕也难以幸免。根据鲁中南山地的地理形势,蒙山之阴有沂水支流东汶河、蒙河二水,形成宽阔的河谷走廊,江最有可能就近由此天然通道进入鲁东南,因此东周时期沂水流域的地名仍留有“江”的痕迹。

事实上,在政权鼎革、时局动荡的年代,部族往往流离四散。因此,另有部分江、黄族众继续南下,至春秋时已迁居淮水北岸。而素为学人熟知的东夷南下淮域,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沂水这一交通线路实现的。鲁东南沂水流域应是夷族主要的聚居地域,徐、江等族即曾活动于此一带。东周时期这里为嬴姓大国莒国的领地,莒是少昊之后,为东夷之国。[注]《左传》隐公二年孔疏引《氏族谱》云:“莒,嬴姓,少昊之后……《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材料表明,早已迁居淮水建国的江、黄皆与莒国有往来。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村莒国墓葬,曾出土春秋时期黄大子伯克盆(《集成》10338)。[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2012年山东沂水县纪王崮1号春秋墓出土君季盂,时代大约为春秋中期,其铭文作:“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邛伯厚之孙君季自作滥盂,用祀用飨,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是尚。”[注]郝导华等:《山东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考古》2013年第7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纪王崮一号春秋墓及车马坑》,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96页。释文见林沄:《华孟子鼎等两器部分铭文重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页。黄太子与江国贵族所作器物出现在莒国墓中,无疑是二国与莒交往的见证。要之,族姓与故土的向心力,维系着淮水江、黄与海岱地区的联系。另外,陈大丧史仲高铃钟、徐子汆鼎、吴王剑、越戈等器物在莒国出土,[注]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心健、家骥:《山东费县发现东周铜器》,《考古》1983年第2期;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工王青铜剑》,《文物》1983年第12期;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战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9期。也昭示了鲁东南与江淮地区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族群往来交流的情形据此得以显现。
综上所述,《汉书·贾捐之传》所言“地东不过江、黄”,江在鲁东南沂水流域,黄位于原山以北、淄水上游,族属性质及其活动地域使江、黄成为晚商周初王朝东界的地理坐标。随着商周民族东拓,中原文化强势推进,东夷国族原有文化格局被打破,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纷纷东退山东半岛或南下淮水流域。晚商时期聚居于泰山南麓的江、黄之族在此时代背景下流离四散,东周沂、淄之江、黄与淮水北岸的江、黄,正是民族分衍迁徙的结果。沂水在鲁东南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沟通鲁北淄潍二水、鲁西南汶泗地区与淮水流域,在族群迁徙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交通作用。
淄水、沂水一线作为商周统治的东部边界,中原文化与东夷族群在此地带相互纠葛,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族群之分化与迁徙,都十分活跃,政治地理格局颇富动态性与立体性。事实上,四方边界的空间尺度、时间跨度、边疆形态以及与中心区域的互动,各具历史地理特性。从边界的视角重新审视上古历史,或许会得到更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