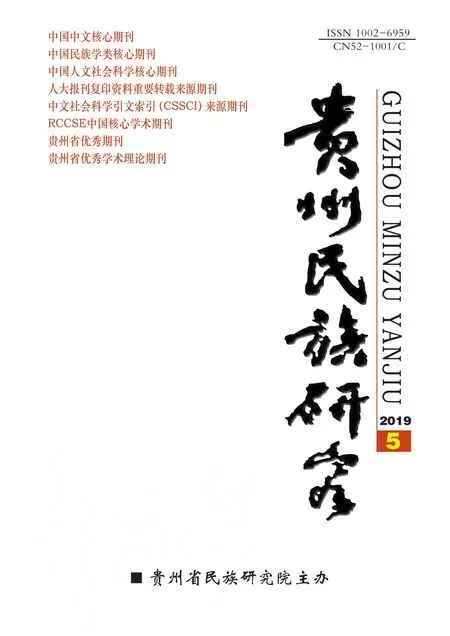“宗教—信仰”维度视野下的藏族民居研究
杨宇亮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500)
一、引言
近代科学勃兴以来,理性光辉将未知世界逐渐祛魅,科学精神渐成主流,以理性为途径寻找确定性答案,成为人类认知范畴中的显学。理性精神作为现代建筑的思想起源之一,使功能导向在现代建筑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形成一种强调“科学—理性”、以物质决定论为主的学科研究范式。学科意义的建筑学在中国是“舶来品”,却又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后者具有重现实、尚事功、对超越性精神匮乏的世俗性特征,成为“科学—理性”范式被迅速接受的土壤,加剧了民居研究中显著的物质决定论倾向,能够给予以庇护为根本的物理功能以很好的解释力。
然而,民居又决非物质决定论所能涵盖。为此,拉普卜特针对气候与庇护、材料与技术、场地与防卫、经济条件等物质因素决定民居的解释,逐一反驳,民居“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建筑,而且是一种组织形态的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于一整套复杂的目的和信念……其构成形态与和组织方式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从一开始,住房“功能”的概念就要比物质和实用的范畴大得多,奠基、起屋和入住的各个过程总是与已有的宗教仪典伴随始终。假定提供庇护是住房的“消极”功能,那么其“积极”功能就是为某一人群的生活方式创造最为适宜的环境,换言之,就是构成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社会单元”[1],拉普卜特开拓了民居研究的人类学广阔视野,宗教作为其核心概念,影响不可或缺。
二、宗教对民居的影响
以探寻“人—神”关系为指向的宗教是所有民族混沌之初的精神主体,这一超验性的认知方式一度成为解读世界的权威,其本体论思想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起点。近代以来,随着理性光环的扩展,信仰的立足之地从自然科学领域退缩,却从未在人类的认知范畴缺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将自然界交给了科学,却在人的内心世界为信仰留下了地盘,成为道德生活的重要支柱。施莱尔马赫认为,信仰领域既不属于知识,也不属于道德,而是属于情感,信仰的存在源于人心中的绝对依赖感。
传统民居历经漫长岁月“层累”而成,实用固然重要,但诉诸信仰的宗教,无论是在时间尺度,还是影响程度,都有实用所不能承担的功能。正如拉普卜特强调的,仅以气候和庇护的观点解释民居是不够的,应探讨文化在聚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民间的盖房习惯则下意识地把文化需求与价值,以及愿望、梦想和人的情感转化为物质形式”[1],无论是“文化需求与价值”,或是“愿望、梦想和人的情感”,并非来自于理性权衡,而是来自信仰。
宗教与聚落、民居方面的研究,国外开展较早,伊里亚德认为,宗教信仰者的空间图式和不信教者并不相同,以超凡的空间地点设立秩序,建立“世界中心”,世界才成为可理解的宇宙,这一主题反映在人居环境中,使“每一个结构和创造都有一种宇宙起源作为它的范式”[2],这显然并非“科学—理性”范式。德方丹认为宗教对于地景与聚落有决定影响[3],芒福德认为,人类能够创制符号的时间比制造工具的时间要早,相比形成宗教、仪式方面的专门化程度与复杂性,产生物质工具的专门化程度与复杂性的时间都要更晚[1]。
与此相关的国内研究并不多。在建筑学视野下,常青对建筑人类学的背景和学科边界进行阐释,重点分析了建筑作为制度、习俗、场景和身体感知对象的人类学属性[4],邵陆则以习俗与建筑的关系切入,尝试回答若干建筑疑问[5],蒋高宸对云南民居也涉及了人类学的视角[6]。宗教社会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稍多,张雪梅探讨了藏族传统聚落与藏传佛教的世界观[7]、聚落形态、住屋方式与宗教的关系[8],郑莉、陈昌文等认为,藏族牧民民居是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9]。总体而言,宗教隐藏着人类尝试解释世界的冲动,在民居中投射出厚重的影响痕迹,在既有研究中,宗教与民居、尤其是民居空间的关系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三、藏族民居:隐藏在世俗中的神圣世界
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一个巨型构造地貌单元,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四周群山环绕,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10]。藏族民居就位于这个全球最高、独一无二的环境中,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极限状态的人类聚居行为,藏族民居的研究因此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宗教对民居的影响在此也表现得最为典型。
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严苛,藏民自出生起就要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严寒、雪灾、高海拔等,无一不是每个人切实需要面对的生活。而游牧生活的特点又很难组织起体系完备、功能复杂的大聚落,匮乏的社会关系与人际交流使每一个人都要更多地面对与生俱来的孤寂感与焦虑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苯教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这一与高原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系统,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四谛”“六道轮回”等主要内容否定物质与现实世界,而关注冥冥高天之上的极乐世界。彼岸性宗教的介入,对个体的精神生活是莫大的宽慰,甚至成为支撑现世生活的唯一途径。因此,藏族信教人员较多,成为我国具有宗教信仰传统的代表性民族,社会成员依靠宗教关系凝聚成为一个典型的非世俗社会,拥有以藏传佛教为导向的独特价值观[11],这一点不仅与汉族迥然相异,就是在少数民族中也颇为独特。
(一)理性的困惑
藏族民居属于“邛笼”系民居,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数丈,为邛笼”,其典型特征是内部的承重体系与外部的围护体系分离,承重体系为木结构,围护结构以石砌或夯土而成,厚重朴实;屋顶或为平顶,或为坡顶。
以香格里拉一带的藏族民居为例,房屋平面规整呈矩形,厚重的夯土墙体三面围合,有明显的保暖防寒作用,开窗小而少。剩下一面多向东南以争取日照,一层部分架空,二层有宽大前廊,以木板墙为室内外分隔。从功能而言,一层多为牲口圈,二层以堂屋为主,周围有经堂、厨房、卧室等。典型平面如香格里拉县小中甸乡期学谷村江育新家(图1)。
1.何以为大

图1 小中甸乡江育新家(测绘:高端阳 李翔宇 迟辛安)
藏族民居以“大”著称,包含两点:建筑面积大、建筑构件的尺度大。江育新家的总建筑面积540m2,堂屋面积约70余平米,在当地仅属于普通规模。若从功能需求而言,大尺度空间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在建筑热环境中为其所累。李莉萍对小中甸藏族民居热工性能的研究表明,堂屋作为唯一直接采暖的房间(火塘采暖),其空气平均温度仅比室外高3.4℃[12],考虑到该地的高寒气候特征,这种室内物理环境显然不能使人舒适,大空间的热工性能是非常不利的。
大尺度还体现在以柱子为主的建筑构件本身,如二层的普通柱子直径约在450mm,中柱的直径更是达到750mm,大大超出了结构受力所需。
2.何以为多
藏族民居的承重体系多为木结构,却颇有值得留意之处。香格里拉地区并不乏成熟的榫卯结构体系,但几乎在所有的传统民居中,榫卯连接都只是部分使用,一般用于二层,以及一层的外檐柱部分,换言之,即人居住、使用的空间才用榫卯结构,如图2(b)、(d)、(e)。在图2(b)中,檐柱使用了榫卯,柱础也颇为考究,而退在后面的柱子就直接顶在梁上,柱础也很马虎。而一层内部的牲畜圈中,所有梁柱节点都不使用榫卯结构,也是以柱头直接顶住横梁。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屋顶夹层,屋顶仅用大小、高度均不等木架或短柱支撑,非常随意,如图2(a)、(c)。

图2 吾日村孙诺家宅的梁柱节点
相比之下,藏族居民的家中一般都有经堂,经堂中的梁柱联接点在结构体系中使用榫卯,但在经堂中央立一对或两对纯为装饰而设立的梁柱,却非榫卯连接,而是在柱头伸出梁枋,承托上方的梁,更富有装饰性。经堂所有的梁柱都雕梁画栋,极尽华丽,见图3。

图3 翁水村某民居中的梁柱节点
同一房屋中的梁柱节点处理呈现出三种方式,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二)信仰的超越
民居在起源之初,都具有非实用性特征,宇宙幻化形成的神圣空间对于情感的满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藏族民居中,非世俗化的宗教色彩仍然有大量遗存,虽然民居的世俗性不可避免,不过在藏民眼中的重要性,却大大地退居在后。也就是说,看起来功能多样的民居,在藏民心中就只有两类: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二者的差异就是佛教教义中彼岸与此岸的差异,充满了异质性。
1.神圣空间一:经堂
经堂无疑是最纯粹的神圣世界,以金碧辉煌、满室生辉建构了异质性。藏民家中的财富积累很少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宁愿斥资装饰经堂,使这一象征性的彼岸世界极尽华美。一般而言,经堂的层高最高,在外立面上最易分辨;开窗最大,并在外立面饰以精美的窗套;内部的梁柱雕饰最精美,最重要的是供奉的佛像、两侧的经书,以及专供僧人睡觉的床,构成佛教三宝——佛法僧的专属空间。经堂作为专职的信仰空间,相当于安置于家中的寺庙,一旦信徒涉足至此,一个足以召唤宗教情感的场景就将俗世尘嚣屏蔽在外。
因各种原因,藏民建房有时周期较长,会先建好部分房间入住,以后逐渐完工。即便如此,也必先设置临时空间作经堂之用,纵然临时,也足见其精心;有时预留适合的房间先作经堂的必要布置,待有所积累后,再将经堂装饰至富丽堂皇,由此可见经堂在藏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图4)。
2.神圣空间二:堂屋

图4 神圣空间——经堂
相较而言,堂屋是藏民日常活动最重要的聚集地。以江育新家为例,70余平米的堂屋正中有一根中柱,火塘布置在靠墙的一边,另一面墙上常设置一个嵌入式的木柜,内置大铜缸,盛洁净的生活用水,谓之水亭。这一看起来宏大而平淡的空间中,日常活动主要是围绕火塘会客、吃饭、聊天、喝酥油茶,在节日中则会围绕中柱跳锅庄舞,看似一个充溢着世俗活动的空间场所。然而,世俗活动仅仅是表象,堂屋中更有不显见的宗教内涵,以容纳兼职神圣之物的宏大空间,及在其中的仪式性行为,建构了异质性,是一个兼职性的信仰空间(图5)。
(1)中柱:宇宙的中心

图5 神圣空间——堂屋(冯晓波提供)
在藏传佛教的的宇宙图式中,至高无上的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四周为四大洲、八小洲、日月星辰[10],而宇宙本体与包罗万象的现象界是合二为一的。在被融入至藏传佛教的苯教传说中,天梯“具有宇宙论的功能,它像一根世界之轴连接天地”,被称为“天墀七王”的七位赞普就是顺着天梯回归天界,“另一方面,它在宇宙——住所——人体的一本同源的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
“宇宙——住所——人体的一本同源是一个远古概念,在亚洲流传甚广”。浩瀚的宇宙是人类认知的外部世界中最为宏大的体系,在人类仰望星空之时,寻求宇宙与自身之间的联系,是合乎逻辑的,从而在微观居住环境中有意识地对宇宙图式模仿[8],从而达成与理想世界的同构。中柱可能就是须弥山或天梯的意象,这一点可以从唐卡中得以印证,见图6(a)。缘于这一独有的宗教内涵,中柱一般都异常粗壮,柱头常有梁枋伸出,雕饰精美,柱上部常附有松枝或哈达等,而受力结构作用反而弱化为附属功能,也因为如此,柱子尺度的增大,却没有带来梁的尺度增加。
在藏族神话中,猕猴菩萨与罗刹女结合后繁衍五百小猴,观音就在须弥山取天生五谷,众猴子食用后成为藏族先民,也就是说,藏民是对自身有神性认同的,见图6(b)。日常生活中,藏民常围绕中柱诵经;在节日的喜庆时刻,藏民都要围绕着象征须弥山的中柱跳锅庄舞,在看似欢乐的世俗节庆中,生命的神圣向度得到了恢复,使参与者体验到人作为神圣创造物的神性,见图6(c)。
(2)火塘:天地的中介

图6 须弥山与中柱
柱子旁的墙边是火塘,其重要性可从藏民早期游牧生活的帐篷中窥见一斑。火塘是帐篷布局的基本空间参照,其上方为天窗,袅袅轻烟自此达上天,天窗非雨雪时节不得关闭,否则视为对天神不敬;前方为入口,后面有佛台,供奉佛像、经书,面对火塘的左侧空间供女子使用,右侧空间供男子使用。火塘的右方有一黑色火塘石,上方或涂抹酥油,或置香炉,以供奉火神。在此,所有物事因为火塘的存在获得了空间意义。在定居化之后,火塘后方设神龛,屋顶的对应位置设天窗,都与帐篷布局如出一辙。藏传佛教也信奉苯教的火神,藏民认为火神是家庭的守护神,火塘作为火神的栖息之地,终年不息,尊贵而神圣[14],见图7。

图7 火塘

图8 水亭
(3)水亭:圣湖的投影
水亭是一个位于堂屋中的靠墙体的一个嵌入式的木柜,水亭内置大铜缸,内盛洁净的水备生活之用。柜子上方开口,悬挂大小不一的若干铜瓢,以方便取水。柜楣上面雕刻佛像,喻示着洁净之水的宗教意味。青藏高原湖泊众多,藏传佛教吸收了苯教中历史悠久的自然崇拜,并将神湖赋予新的意义,使其成为藏民祭祀膜拜的佛教圣地。在藏民的传统观念中,对洁净的水极为重视,洁净观在各宗教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作为笃信宗教的民族,凡具备神圣色彩的事物,均是洁净的,如溢满洁净之水的圣湖。在民居之中,盛满洁净之水的水亭,就是圣湖的微观投影。有的人家开始用新的水亭之时,还要请喇嘛举行专门的仪式,足以彰显出其宗教性(图8)。
(三)异质两分的世界
经堂与堂屋作为神圣空间,具有相当突出的宗教职能,只不过前者容易被识别,而后者却往往被隐藏。在一个全民信教的文化传统中,外人看来的世俗场景其实更是一幕宗教场景,中柱、火塘与水亭都可以转换成“中断”世俗性的信仰空间,其器物形态往往是“反”物理功能的。
与此相对,厨房、卧室、牲口圈则属于世俗空间。以卧室为典型,藏族民居的卧室简陋之极,四壁空空,杂物堆砌,床具简朴(图9)。世俗空间的草率性,是与藏传佛教否认现世生活的教义一致的。卧室位置多远离火塘这一唯一的热源,紧邻二楼外廊的墙面仅以薄木板为壁,保暖性能极差,唯有附设在经堂的床条件较好,但仅供请喇嘛到家中做佛事使用,恰恰映衬了经堂中的床是属于神圣空间的。
总体而言,藏族民居中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差别,“俨然迥然不同的世界”,对前者的处理极尽华美,而对后者的处理极为草率。理解了这一点,前述的“何以为大”“何以为多”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即凡属神圣空间的部分,或高大(堂屋的面积与层高),或华美(经堂中的梁柱、堂屋的中柱),或精细(榫卯结构);凡属世俗空间的部分,则完全与之相反。

图9 典型世俗空间——卧室
宗教是藏文化的核心,以世俗与神圣的两分视角看待藏族民居,世俗空间以生产与居住为目的,神圣空间以信仰为目的,二者的共融,恰恰是理性与信仰在认知体系中互补的最好诠释。
四、结论与讨论

图10 藏族民居中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
(一)民居研究中的“宗教—信仰”维度
涂尔干认为,宗教现象的真实特征是将宇宙分为无所不包、相互排斥的两大体系——即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神圣之物与世俗之物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异质性,俨然迥然不同的世界[15]。米尔恰·伊利亚德认为,神圣与世俗是这个世界的两种存在模式,居住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人类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模仿与圣化这一物质空间,通过神圣化的方式摆脱混沌,求得某种与宇宙一致的秩序,使居所与身体均成为一个微观的宇宙,形成“身体——居所——宇宙”的对应结构[2]。
藏传佛教在藏民的精神生活中的意义重大,形成了自宏观宇宙直达微观居所的信仰体系,影响深远。在民居研究中,“科学—理性”只能解决庇护这一物理问题,但对于人类而言,居住行为还具有心理与情感意义,这种意义具有终极命题的意味,其答案在理性边界之外,只有基于信仰维度的宗教才能给予。宗教对民居的影响是具有普遍性的,如中柱崇拜在傣族、普米族、彝族等民居中普遍存在,傣族民居中的中柱分为男柱、女柱,是傣族造屋始祖桑木底与妻子的化身,被赋予了家神的意义;彝族古歌描绘到:“居木吾吾阿,竖起铜铁柱,通到天上去”,将中柱看作通往天界的通道;火塘崇拜在彝族、独龙族、纳西族、摩梭人等民居中也很常见。因此,就神的宇宙被幻化成人的居所这一点,“人—居所—宇宙”的同构性在不同民居具有普遍性[6],印证着宗教对民居的深刻影响。
拉普卜特在引用德方坦的观点时说,“大多数原始社会,甚至包括前工业社会的人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强调宗教,其程度远甚于对物质和舒适的关注”[1]。宗教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在代代相传中形成具有惯性与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在民居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持续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二)讨论:人类认知的双重范式
作为唯一有灵性的动物,人类具有源于人性深处、与生俱来的认知天赋。罗素说,“在我们沉思的一瞬间,我们就超脱了动物的生命,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了将人从野蛮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的伟大目标”[16]。理性与信仰相互补充,构成人类对世界的完整认知体系。诉诸理性,人类可以得到具有确定性答案的科学,以及具有非确定性答案的哲学,但理性边界之外的广袤与宏大,才能够容纳人类追寻无限未知的心灵;只有诉诸信仰,人类得到的是具有终极意味、非确定性的答案——宗教,因为“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答案”[16]。
柯布西耶作为现代建筑运动的奠基人,曾提出“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著名论断,是理性精神在建筑思想中登堂入室的重要标志。然而,在柯布西耶的晚年,早先的技术与理性被神秘与混沌所替代,其作品也从明朗走向神秘、从瞻前走向顾后、从理性走向非理性[17],这决非理性可以概括。民居同样隐含着建筑语义的多意性与复杂性,具备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异质两分,深刻反映了人类认知体系中的两种范式:“科学—理性”范式与“宗教—信仰”范式。前者提供以庇护为目的的物理功能已成共识,而后者提供以情感为依托的心理功能,具有普遍意义与源远流长的持续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正如科学与宗教在学科轴中各安其位,“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应该成为民居研究中秉持的基本范式,不能相互替代(图11)。

图11 学科、认知与建筑功能关系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