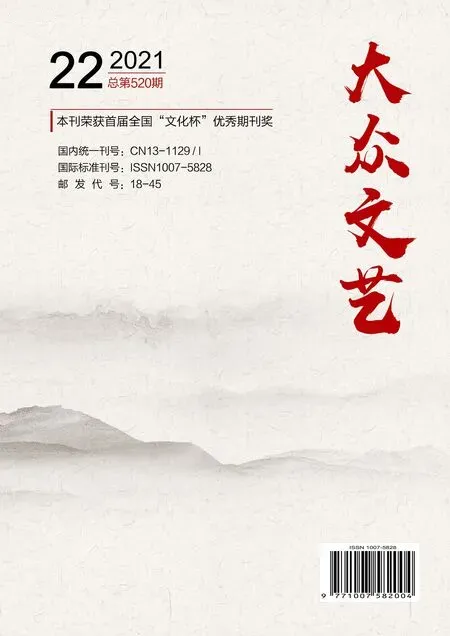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真”的审美“蔓延”
——论本雅明“Aura”观与王夫之“现量”说的会通
张 羽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00)
作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本雅明提出的“Aura”观与我国明末清初儒学大家王夫之所倡导的诗论“现量”说都涉及了“真”这个内涵。“Aura”源于拉丁语词,原意是“光环、气(风)”,它被本雅明借用到其论述中试图表达一种19世纪前西方传统艺术所具有的难以用具体概念捕捉的特性;“现量”本是佛学术语,中国明末思想家王夫之首次将其引入美学领域。与本雅明的“Aura”之“真”对西方传统艺术核心精神的揭示相比,王夫之的“现量”之“真”不仅代表其自身的文艺审美取向,也表达了中国传统文艺求“真”的审美诉求。
一、“真”的时空与情理的“蔓延”
(一)“Aura”之“真”的时空“蔓延”
本雅明关于“Aura”的形容,最早出现在其1931年的《摄影小史》中:“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象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Aura’。”在之后写成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本雅明又对“Aura”作出了解释:“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与此同时,“真”这个特性也在“Aura”的阐述中被提及:“一旦真实性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的生产,整个艺术的功能也就天翻地覆。”,“真”在这里主要指艺术作品的原创性,来自原作与真品的不可复制性。它要求“此时此地”以确保“原真性(Echtheit)”,就是强调一种当下“所在”,但又要求“真”应从当下的时空中解放出来,以物理距离与历史的见证扩展了想象的空间,这是“所思”;除此之外还要求“真”要具有相对场域中的绝对话语权,就是要具有“权威性”。可见,在本雅明的“Aura”中,“真”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涵:第一,原作本“真”:与仿品、赝品及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诸如相片、摄影等有所区别;第二,审美感受的“真”:即是心物交融所产生的想象空间下一切自然视观所忽视的层面;第三,确保审美场域中话语权的“真”,即植根于宗教仪式衍生出的“权威性”。“真”中“即时即地”的要求极为自然地涉及了时空观,即是对时空的把控,它看似固定了“真”的时空,实则是要让观者体会审美时空的“蔓延”,何谓“蔓延”?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弥散感,以中心原点向四周扩展。时空的“蔓延”在“Aura”之“真”里的运作至少包含着两层:首先,时空的原点代表着事物与观者之间的在场性,在场性使得主客之间得以建立联系,也使得“显象”得以开始和完成。其次,物理距离与历史见证增加的审美心灵意识展开的想象空间造成了所谓社会和艺术时空的“蔓延”。具体来看,就是从审美在场性向审美心理距离的“蔓延”,共同构成了“真”的美感经验。
“Aura”之“真”的时空可分为自然时空、社会时空与艺术时空。关于“Aura”的场景性描述恰好就是自然时空“蔓延”的证明,描述先从“夏日正午”、远处“地平线”、“一截树枝”的投影的时空点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地平线并非当前所处空间,而是距离很远但又看起来很近之物;树枝的倒影也并非真的树枝本身,而是对树枝的一种投射。我们可以从这个场景描述中看到空间的发散性,而“沿着”、“顺着”两词又证明了时间的流动性,审美时空并不机械固定在一点,而是“蔓延”到达“此时此刻”的显象之中才结束。另一种社会时空的“蔓延”是着重在历史见证上,“事物的原真性是其从起源时起可流传部分的所有本质:从物质方面到它的历史见证力都属之”,“历史的见证力”代表着社会时空不断更迭,只有通过历史风云变幻的检验,从而不被当时时代的“话语”裹挟,也因此显现出传统艺术最本质的状态,所以本雅明说:“事实上,中世纪的圣母像在创作的时代还谈不上‘真实’与否,是后来数百年才变成真实的。”这种“真实”来源于历史更替过程中艺术品经历的时空以及背后所包含的事件,它使得社会的“真实”附着于某件艺术品之上,从此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权威感。而在艺术时空的“蔓延”上,本雅明主要是从绘画与摄影作品的区别展开讨论的:“画家对景作画,隔着一段自然距离来观察所欲描绘的实景,反之摄影师直接深入实景的脉络中。所得的图像两者也截然不同。画家所绘的图像是完整的,而摄影师拍的影像却分割成许多片段,每个部分又自成一格。”绘画图像与摄影图像相通之处在哪里?那就是图像所表现的事物虽看起来是远处之物但却能将远处之物人为地拉近到二维平面之内,它们都具有“虽远、尤近在眼前”之感,但为何现代摄影作品相比传统绘画,最关键的“Aura”之“真”还是消失了呢?实际上这里还涉及到想象空间的问题,正如本雅明所说,绘画作品的图像由于隔着一段距离更见其完整,而影像却被画面切割成局部,这里“完整”所指涉的真实并非只是物理上的完整,而更多是想象空间延伸的完整,比如《摄影小史》中提到的早期人像摄影还保有微弱“Aura”的原因大概就在于其历史见证力与其在光影斑驳的模糊色块中,展现人像面部瞬间表情所扩展开的想象空间有关,摄影作品因为缺乏时空的“蔓延”破坏了想象空间,所以也破坏了图像真实的完整性,消解了“Aura”之“真”在人心中的神秘感和权威性。
(二)“现量”之“真”的心目“蔓延”
在《相宗络索·三量》中,王夫之认为“现量”有三层义:“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其中,“显现真实”实则包含三方面的内涵:第一,物本“真”,即事物本身固有之美;第二,审美感受的“真”,即是“心目”在场,用情感的“真”和景、物的“真”构建独特的审美体验;第三,真实地反映,即追寻物背后完整鲜活的“神理”。实际上,“显现真实”义是建立在对“现在”的时空把控以及“现成”义的直觉体验的基础上,“现在”意即注重当下,不被过去的固有经验所影响当下的直觉判断和感受,而“现成”义则是追求一种“心目合一”以求“神理”的状态,只有通过“现在”与“现成”才能达到“显现真实”之境,前两者是以“真”为旨归。可见,“真”触及了“现量”所提及的审美状态的命门。
王夫之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以心目相取”、“心目为政”,正如他在《古诗评选》中所云:“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心目一词,表面上看是王夫之提倡的审美感受方式,实则包含王夫之对“真”的层次化推演,那就是心目在横向与纵向的“蔓延”。横向上,以心目为基础,向内求情,向外周理;纵向上,寻求心目合一的“神理”,在情理表达的基础上跳出情理桎梏,寻求完整的审美经验。
首先是横向上的“蔓延”,王夫之认为“心”作为统领“五官”之要,实则是“目”等五官的内化:“一身之要,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是故心者即目之内景,耳之内牖,貌之内镜,言之内钥”。这里“目”也并非简单指目视,而是代指身体感官获取审美材料的方式,《相宗络索》中说:“前五识:眼,九缘生。耳,八缘生,不择明暗,故不缘明缘。鼻舌身三,聚七缘;香、味、触俱合境方取,不缘空缘”可见“目”相较于其他感官所囊括获取的信息最多。显然,“目”所指代的就是在向外寻求“身历目见”的审美在场体验基础上寻求真实的“物理”,如果只寻求“物态”(外在形貌),而不求“物理”(内在审美特性),就不足以构成审美体验真实,故王夫之在《诗译》中引用了苏子瞻对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评语:“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当‘沃若’,固也”的评语,并得出“然得物态,未得物理”之感。在王夫之看来,“物态”变化多端具有迷惑性,并不是把握审美材料的关键,反之追寻“物理”才是对于审美对象最为真实的把握。那么“物理”该如何获取?这就需要直观的“目击”式体验,而非用以往的经验蒙蔽此刻的体会,即是“不缘过去作影”,这样才能直观万物最本真部分。与“目”的向外求“物理”相比,“心”则是在“目”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向内寻求情感完整性,也即是寻求“诚”的境界。这种情感完整性集中体现在“心”作为介质作用于情与景物之中,针对心目先后的问题,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凝而睇之然后得其真,密而之然后得其情。劳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于目,而后目往交于彼。”他认为,心不应先注与目,而是要先把“目”与景物的体验自然纳入心中,“目”所进行的审美体验就是要将物与审美主体和谐统一,才能得其真情、真景物。所以,这个“目”是一种综合性的审美体验,它既包含由“目”为代表的身体感官之体验,又包含着“心”与之一同灌注的超越生理身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因此,“现量”之“真”在横向上的“蔓延”是从由目及心的感知出发,超越景、先前经验对于审美的把控,追求一种至纯之“情”,所求的正是情感完整性之“真”。
其次是心目纵向上的“蔓延”,“心目相取”意在追寻物背后完整鲜活的“神理”。何为“神理”?叶朗先生认为是在妙悟的基础上寻求“物理”,《姜斋诗话》中船山用“神理”评诗:“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神理”在一远一近、一虚一实之间,如“气”般缥缈,“自然恰得”说明审美时心目虽在情景交融中又不被情景所缚,情感有所表达又有所控制,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宣泄,颇有儒家“中和”美之感。此外,“神理”要求审美在“远近之间”,即是说心目在时空远近之间穿梭,自动与先前经验拉开距离,不迷失于过往的一切,注重当下审美体验,寻求的是由此在之“物”向身后“情”、“理”的突围。因为天地之物的美本就完整,不能因人的主观感受强加于物,就要超脱出人所赋予的语言、概念、文化、政治意图以及过往经验等外在枷锁,做到“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缘物而起又不为物所滞碍,广大无量而又非虚空”,以纯粹之心感受审美本“真”。
二、思维差异及其原因
(一)思维层面的差异
不论是“Aura”还是“现量”,它们的审美起点无一例外都提到了“眼睛(目)”的作用,可最终却走向不同审美追求:前者指向“相”,后者指向“道”。
自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始,“光”寻求真理世界的种子便在西方审美中生根发芽,人们追求的是“相”这种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是超越了时空限制的“非时空”存在。中世纪时期,这种“相”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权威,并且又与仪式和宗教不可分割。因而,西方传统的审美时空意识也具有崇拜“权威性”的取向。“Aura”中“光”的意涵,就是一种追求实“相”的权威性存在。以西方19世纪前人物肖像油画为例,画作中的光线运用一直被艺术家看重,这集中体现在人物肖像的塑形上,光线使得画作中的人像蒙上一层神秘而安详的色彩,这种色彩毫无疑问来自于宗教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画作中的人像神,神像人,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不必说的绘画准则,宗教中的神与凡间的人通过这种独特的光线得以沟通。一方面,光线运用使得“眼睛-对象”间形成长久的“凝视”意味,而“凝视”过程中想象空间又被无限扩展延伸,直通宗教的神秘境地。另一方面,“凝视”传统也使得西方人对于事物肌理的追寻显得格外执着,从而追求视觉可触碰的“实相”,即是“相”之真。摄影出现时,本雅明认为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人物肖像画,因为摄影对于光的运用不似油画,它以科学展现物理细部的方式将人之为人的物质实体性最大化揭示出来,而将人对于宗教的神秘幻想和对于“实相”的追寻完全替代了,宗教原有的权威性也沦为人性;同时,摄影所展现的对象因缺乏绘画那种整体上的把握,想象空间也被压缩替换成单纯的记录,这一记录通常还伴有人为扮演的痕迹,缺乏了“即时即地”的“原真性”所带来的时空蔓延,这些共同造成传统画作中“Aura”的消失。
相比西方传统对“相”的追寻,中国审美传统则是指向万物身后所隐藏的“道”,“现量”实质上是一种“目击道存”的审美方式。如果说“Aura”在时空的蔓延中检验美的真,那么“现量”则是在“心目”的蔓延中用“意”构建美的真,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写意”审美方式上,“写意”就是“道”的表现方式之一。本雅明说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综合性思维方式和试图寻找相似性的方式感到很不可思议,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一文中对中国画及中国艺术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事实上,这些相似性之间彼此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交织缠绕,形成一个召唤思想的整体,正如轻纱引风。中国人称这种描写为“写意”,真是特具意义。形象就其本质,即包含某种永恒。”形象包含着本质的“写意”,是中国古人在综合感知的审美体验后对真美的构建。关于“意”,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实则一脉相承的诗论观点,那就是“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意”与情景的关系密切相关,“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不虚景,景总含情”,“真”情中必定有景,而“真”景中也必定含情,情景交融得以产生了“意”,这时的审美是“俱以意为主”;但审美不以情感局限于这一隅的景物中,而后跳脱出思维理念束缚,更不可用主观之“志”强加于此情此景,不涉理路,这时才到达“俱不在意”的境界。王夫之因此说:“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以意为主之说,真腐儒也。诗言志,岂志即诗乎?”。可见,“意”本是诗中不可少的部分,可一旦刻意寻“意”,便会使诗歌流于板滞,所以应跳出“意”的束缚,以“心目”寻“神理”之真,也即是寻求“道”。
总之,就追寻的审美意义而言,“Aura”之“真”指向实在之“相”,是一种沟通人神的宗教权威的存在形式,而“现量”之“真”指向“道”,体现了“心目相取”、虚实互补之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产生差异的原因
造就上诉这种思维差异的原因实际上是两者文化根源上审美认知的不同:西方传统审美时空观与生命观彼此分离,更多与审美形式方面相关;而中国传统审美观,主要持一种“道”因“气”而生的时空观和生命观。换言之,在审美认知上,“Aura”注重的是审美的时空观,而“现量”注重的是审美时空观与生命观的结合,即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对于美的生命体验。
在西方传统的审美中,无论是最初原始人在洞穴画上企图让神灵看见的壁画,还是中世纪对于宗教肖像的崇拜,亦或是文艺复兴后对于美的人文崇拜,都使得审美仪式成为了传达“真”之美的载体。审美时空观造就了西方注重逻辑和实在形式的思维特点,所以他们的传统诗歌通常是叙事诗而少见哲理诗更难见到如中国古代那样颇具画面感的意象性诗歌,至于画作就多具有了祭祀、宗教等的实用价值。本雅明在其著述中说:“‘真实’艺术作品的独一性价值是筑基于仪式之上,而最初原有的实用价值也表现在仪式中。”显然,复制品虽能复制真品“物性”的实用价值,但却不能复制真品“事性”的审美价值,这个“事性”就是把艺术品置于时空之中,把它当作一种事件去对待。作为艺术“事性”的载体——审美仪式对时空的把控极为严格,这种时空必须要经过历史进程的检验,还要增加审美的想象空间,并且必须拥有某个审美场域中的绝对话语权。审美时空最开始被祭祀宗教氛围所笼罩,艺术作品因此注重崇拜仪式价值,当艺术从祭祀典礼功能中出来,审美时空的展览价值开始被强化,对于艺术品的观赏使得人们主动去构建人文的审美时空,并从中找寻真实的理念世界。“Aura”之“真”的时空观就是要保证在一定时空距离之外窥见审美对象整体,以便把握事物实在形式,试图追寻审美形式背后的理念世界。
中国审美传统中,“气”本就是时空与生命的结合,如同自然界中的“气”蒸腾而上的形象那般,代表一种生生不息的向上状态,同时也暗含一种原始神秘的生命力量,成为孕育天地万物的本源。以“气”为主的审美不仅是展现审美对象的形式层面,还着重在此基础上追求精神层面,以求沟通天人。中国传统的诗歌与画作因审美生命观和时空观的注入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写意传统。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解释坤卦时说:“阴阳二气絪緼于宇宙,融结于万汇”,他认为宇宙由“气”所组成,“气”之阴阳互相交杂在天地间形成万物。在王夫之看来,“阴阳二气”具有浓厚的生命色彩,参与审美活动的万物背后都有“阴阳二气”牵制。另一方面,“气”的生命观还体现在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所拥有的的“气”最为“灵秀”,《四书训义》中说:“阴阳五行之气化生为万物,其秀而最灵者为人”,人具有独特的灵秀之心,此心应物斯感,具有专属于人的生命意识,审美因此具有“人”的生命体验。《读四大全书说》中船山进一步提到“阴阳二气”的显隐:“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周易内传》中对“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解释是:“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隐矣,乃必有其形,而后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谓之形而上,而不离乎形。道与器不相离”,可见,形而上的“道”必须通过形而下的万物才可将万物的“显”、“隐”把握,才可得世间万物之真谛,而“道器不相离”的观点,表明船山将世界看作整体的审美时空观。以“气”为主的审美时空观与生命观恰好也体现在王夫之“现量”之“真”中,正因为人的感知认识能力有限,想在审美活动中直寻万物之“道”就必须借助感官对于形而下的万物的把握,不脱离于对景物的感受,才能做到情物交融、心目合一,使审美对象“显现真实”,展现出完整意义的真美。
三、结语
综上,通过“Aura”之“真”和“现量”之“真”的梳理,并对二者审美内涵背后所存的中西审美文化及审美认知源头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产生语境方面,二者相同之处是都与人的审美感受密切相关,都以“眼睛(目)”作为审美感受的开端,具有心物交融的独特体验。而两者的不同在于:首先在审美方式上,“Aura”之“真”从凝视切入,更偏重从视觉寻求宗教权威式的人神沟通,而“现量”之“真”则注重一种由目入心、“目击道存”的综合性审美感受;其次,在审美认知方面,“Aura”之“真”是追求实“相”的审美时空观主导,“现量”之“真”则是“气”生万物的审美时空观与生命观的统一,这些特征上的差异使得东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审美感受也有所不同。
当今社会,人们过着机械重复的快节奏生活,早已没有悠闲的灵魂去体味经典艺术,在精神方面向内回归的生活也愈加贫乏。对传统艺术的复归,对"现量"、“Aura”的重新召唤或许有助于以—种更辩证的视角看待今天艺术和各种技术的关系,避免简单地被置于商业追逐的系统之中,以艺术之“真”和生命之“诚”延续审美的终极关怀意义。
——本雅明流寓海外初探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