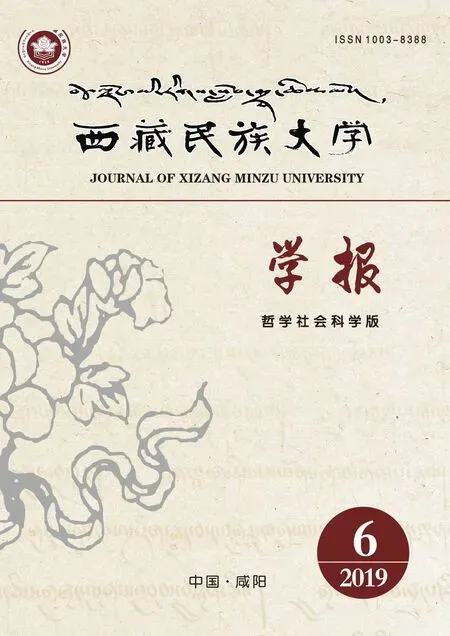汉学家博晨光(L.C.Porter)生平学术札记
王启龙,贾诚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无疑发挥过重要的作用。①1928年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对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中国近现代人文学术发展功不可没。而后来任教于该校并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总干事的汉学家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今天学界知之甚少,下文将就其学术生平之点滴做一简要介绍。
一、博晨光生平简介
博晨光,美国传教士,著名学者,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等职。1880年10月31日出生于中国天津,父母均为来华传教士,父亲博恒理(Henry Dwight Porter)是由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来中国传教的外科医生,母亲是美国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首任校长Aaron Lucius Chapin的女儿,随夫在天津传教。博恒理与明恩溥②于1882年在山东德州旁庄村建立传教点,博晨光便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这段时间他在父母帮助下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1897年回到美国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为止。1901年从伯洛伊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神学院读书,1906年获神学学士学位[1]。在其成长阶段,他称自己为“边缘人”,生活在三种文化之间:童年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租界的英国文化和北京的外国文化;在家乡和接受正规教育时的美国传教士文化[2]。但是在他看来,没有哪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越,这三种文化都是一样的自然、美好[3](P28)。
1908年5月16日,博晨光在美国与拉克罗斯县的高中老师Lillian Lee Dudley完婚[4](P455)。同年,受美国公理会差会指派,前往中国通州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教授心理学和哲学[5](P1821)。该校在1916年变成了燕京大学的组成部分。他还在柏林、马尔堡、耶路撒冷以及纽约协和神学院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过,并于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1917至1919年任华北公理会(North China Kung Li Hui)总干事[6](P544)。
1921至1926年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邀请创建燕京大学哲学系,担任首任系主任。1926年2月,冯友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博晨光此前曾在哥大作丁龙讲座教授[7],教授中文,与冯友兰相识,故聘请冯友兰作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在任期两年半的时间里(1926年2月-1928年8月),讲授中国哲学史。除此之外,博晨光还介绍冯友兰为当时在北平的外国人讲授《庄子》,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英译本《庄子》,其中“天下篇”就是由冯友兰与博晨光共同完成④。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博晨光任学社北平办事处首任总干事一职,史静寰教授评价他为“唯一一位从燕大成立之初到1949年撤销之时一直任职于此的西方人”[2]。同时,哈佛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为本科生讲授为期一年的中国概况课程——《汉语12:中国思想概论》(Chinese 12:Sur⁃vey of Chinese Thought)[8]。
日本侵华期间,他也一直在中国教书、传教,1935年在四川的一个大学教书,1937至1939年掌管美国公理会差会在山西的财产。1943年被日特当局逮捕,但他为了再次入职燕大,拒绝被遣送回国。休假期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1924)、哈佛大学(1928-1929,1931-1932)、克莱蒙特大学(1938)以及伯洛伊特学院(1940-1941)任客座讲师,通过学术和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国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合作和欣赏,并取得伯洛伊特学院神学博士和纽约大学文学博士荣誉学位[6]。1950年回到美国,担任伯洛伊特人权委员会主席。1958年9月7日心脏病发作不幸过世[5]。

博晨光(L.C.Porter,1880-1958)⑤
博晨光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有《中国哲学研究辅助》(Aid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4);1925年5月28日在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发表演讲“Plans and Dreams of 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1939年出版Tao in the Lun Yü(《论语》中的道)。博晨光虽著述寥寥,但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推进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功不可没。他信仰自由派基督教,反对教条主义,倡导尊重中国文化才是正确了解中国的出发点[9],始终致力于将西方的基督教,哲学观和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青年,并向美国人讲授丰富的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人生观[10],是中国教会大学里的代表人物。
二、博晨光与钢和泰的交往
民国时期,博晨光与胡适、顾颉刚、冯友兰,司徒雷登等学者都来往密切,而与同是“异乡客”,来自俄罗斯、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和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的钢和泰男爵更是交情甚笃。
钢和泰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同时又多少有些神秘的名字[11]。他出生在爱沙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熟悉梵语、婆罗门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并精通俄语,法语,英语,德语等西方语言[12],是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梵语学者和佛学专家。1917年,钢和泰为了查找有关“迦腻色伽”的资料,研究藏文和蒙文文献而来到中国。后来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等原因滞留北京,从此便久居北京,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梵文,古印度宗教史和印度宗教哲学史[13]。大约从1927年起,他在北京创办了中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⑥。中国藏学和佛学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不仅出版了《犍椎梵讃》《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藏汉对照)》等著作,还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林藜光,黄树因,于道泉等从事佛教文献研究的国内学者[14]。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钢和泰与伯希和(Paul Pelliot),博晨光,洪煨莲(William Hung,1893-1980)⑦一起,被邀请成为哈佛1928-1929学年的客座教授[15]。1929年,钢和泰正式受聘为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与此同时,他在北京创办的中印研究所变成了哈佛燕京学社设在北京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为哈佛燕京学社购买研究资料,实施教学科研计划,以培训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并给他们提供学术上的指导,出版有关文献材料和研究成果,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等[16](P222)。中印研究所的运行经费由哈佛燕京学社负责,并通过其设于燕京大学的北平办事处划拨并由后者监管,于是,作为哈佛燕京学社首任总干事(1932-1939)的博晨光,自然在中印研究所的日常管理、财务报账等方面与钢和泰多有来往。两人的关系从他们相互的书信往来里可见一斑,从1926-1936年间,可查到的两人书信往来80余封,讨论的内容从生活,学术到中印研究所的工作等方面,无一不全。
在生活方面,两人可谓是至交好友,关爱彼此家人,互帮互助。钢和泰得知博晨光的儿子沃尔科特(Wolcotto)喜欢集邮,便经常寄邮票给他;博晨光得知钢和泰的妻儿生病住院,便不断写信问候,比如:
1931年1月19日,博晨光在写给钢和泰的信中开头便提到:“我真心希望令郎的健康有所好转,病已痊愈。”
1931年1月22日,钢和泰回信道:“万分感谢阁下善意的短信。犬子已经出院,大家似乎都好起来了。”
1933年7月19日,博晨光给钢和泰的信中写道:“阁下还记得沃尔科特对邮票着迷,您真是太好了!您真的给了他一些非常罕见的邮票,其中一些他连样本都没有。我们都非常感谢您。代我向男爵夫人问好,真希望令郎已经完全康复。”
1933年12月,博晨光写信给钢和泰:“感谢您一直记得沃尔科特喜欢集邮这件事,没有什么比邮票更让他高兴的了。”
1933年12月24日,钢和泰致信博晨光:“我最近收到了很多信件,您的小儿子可能会对信封上的邮票很感兴趣。可否麻烦您把信封交给他?”
1933年12月28日,博晨光回复道:“您可真是我们家那位小小‘集邮者’的好朋友,如此慷慨地送给他这么多礼物。您真应该看看他当时看到您送来那个大信封时的眼神,简直是飞跑着奔过去的呢,直接就开始贴邮票了。我们父子二人对您的好意感激不尽。”
1935年12月24日,钢和泰写给博晨光夫人的信函中说:“希望随函附寄的邮票能让令郎感兴趣。他已经熟悉了这个小小集邮册里所有国家的邮资,也就只有其中一两个的面额对他来说可能有些陌生。犬子仍在住院,但是他的体温恢复正常已经三周了。”⑧
可见博晨光和钢和泰不仅在工作上有关系,在家庭生活中也是相互关心,彼此照顾。
除此之外,博晨光写给钢和泰的信中,总是称呼他“我亲爱的男爵”“亲爱的钢男爵”,以示友好;钢和泰则称呼博晨光为“尊敬的教授先生”“亲爱的博晨光博士”,以示敬重。两人在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彼此的关心,如若遇到困难,另一方则全力相助。比如博晨光在1934年12月14日给钢和泰的回信中写道,“随函附给您一张金额为5,831.31美金的支票,请您查收。去年春天在紧急情况下,您如此慷慨地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这是我们的还款金额。谨允许我代表斯图雷登校长和燕京大学对您雪中送炭,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做法表示衷心的感谢。”钢和泰中印研究所的资金并非十分宽裕,但在博晨光遇到困难时,还是倾囊相助,足以见得二者相交之深。
在学术上,钢和泰对博晨光在佛教研究上也有帮助。1934年2月3日,博晨光致信钢和泰,请求他推荐一些有关印度和佛教哲学的最佳书单,还表示想参加钢和泰的梵文学习班,从最基础的学起。博晨光也曾帮钢和泰校对他在上海出版的佛教的序言部分(第5,6,13页),这在1926年2月钢和泰给博晨光的去信中有所提及。不仅如此,他还帮钢和泰争取基金,包括来自帮助中国学者的基金和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enheim Foundation),来支持中印研究所的工作,钢和泰在回信中表示感激又开心。
两人的关系还可从《钢和泰学术评传》中得到印证,书中所言:“钢和泰在他的中印研究所接待过的著名学者数不胜数,其中与钢和泰有长期交往和深厚交情的,如胡适,陈寅恪,博晨光,洪煨莲,李华德等”[16](P224)。博晨光的名字赫然在列。
三、博晨光与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成立于1928年1月4日,由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联合建立,是美国较早的正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该学社的成立源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他将三分之一的遗产用来建立“霍尔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al Fund),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支持或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美国或英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17],在司徒雷登,路思义,洪煨莲,博晨光等人的不懈争取下,哈佛最终选择与燕京大学合作办学。学社的目的在于保证在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北京的中国学者,为传播与保存中国文化而进行研究[18]。学社成立之初,其负责人由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历史学家乔治·蔡斯(George Chase)教授兼任,1934-1935年间改由学社首任主任、法籍俄国东方学者叶理绥(Serge Elisseeff)直接负责,学社的首任执行干事便是博晨光。除此之外,博晨光还担任《燕京学报》⑨的编委并参与学报编辑工作。1930年6月6日,博晨光曾去信钢和泰,邀请他担任该报的名誉主编,并希望他能够在《燕京学报》的汉学研究栏目上发表文章,帮助他们的学报在海外推广。钢和泰欣然接受。
博晨光与钢和泰书信往来中,提及最多的便是关于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印研究所的财务问题。哈佛燕京学社的财务制度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专项基金制的研究机构。根据霍尔遗产董事会对霍尔教育基金的分配,燕京哈佛学社最初共获得640万美元,分为两类进行管理:(1)非限制性基金(A General Fund)共计450万美元,用于学社的一般项目,支付学社在研究和行政上的日常经费;(2)限制性基金(A Restricted Fund)共计190万美元,将其利息收入分为19份,按指定比例每年分4个季度拨给中国的6所教会大学和1所印度农业研究所(燕京大学5/19、岭南大学3/19、金陵大学3/19、华西协和大学3/19、齐鲁大学2/19、福建协和大学2/19、印度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1/19)[17],其中燕京大学配额最高。由于这两种资金的资助对象和资助范围均有所限制,因此能对各教会大学的研究起到良好的支持作用。比如实力最为雄厚的燕京大学,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干事,陈观胜⑩曾回忆说,“燕京大学对中国文化研究方面,能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中居于领导地位,哈佛燕京学社赋予该校充分经济后盾,实为主要原因之一。”[19](P53)
第二,严整规范的管理体系。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起初由哈佛大学司库代为掌管,后成立学社董事会,每笔资助的资金都受到董事会监管。每年6月1日各大学必须提交详细的报告,对过去一年资助资金进行说明,作为下一年度的拨款依据[20]。而钢和泰的中印研究所成立后,由于经济窘迫和研究所发展受限,1929年被哈佛燕京学社“收编”,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的单独拨款,受其监管,并按时向其提交财务计划和财务报告[16](P191)。从两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出,钢和泰向博晨光申请基金,博晨光请示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和哈佛共同商讨制定年度预算和发展规划。1930年1月9日博晨光给钢和泰的信中写道,“我一直在等您寄来上一季度研究所工作人员的经费开支情况。我们已将帕拉托夫先生的支票直接寄给他了,其他需要按季度支付工资的‘代表’的支票也已寄给阁下。但对于研究所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不作说明。我想阁下应该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先寄来一份账目说明让我分析,再上报给财务部门登记,这样我们的财务人员就会寄给您一张支票,上面是需要偿还给阁下的总金额。我已将上一季的账目分类处理妥当,这样每一项的分类就十分简单明了。”由此可以看出,受哈佛燕京学社管辖的中印研究所需要每季度寄给博晨光一份账目说明,分析审核过后上报财务部门登记,财务人员才会将所需金额的支票寄出。但可能由于钢和泰凡事缠身,过于忙碌,他经常不能将账目说明及时寄出,博晨光会在信中委婉表示只要钢和泰寄出账目说明,他立即就能收到支票。除此之外,哈佛燕京学社的所有报销账目,须有收据才可,1930年4月27日钢和泰写给博晨光的信中就提到,他买的很多书都只得自己掏腰包,因为日本的书商没有给他开收据,是从日本转寄而来以货到付款的形式签收。正是这种层层递进的财务审核制度,严谨规范的管理体系,使得哈佛燕京学社运转独立,少有纰漏。
结语
博晨光出生于中国天津,尽管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教育,但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使他对中国社会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租界的英国文化和北京的外国文化、美国传教士文化等多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2]他认为,文化间不存在高低之分,这些文化都是一样的自然、美好。[3](P28)这种客观、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对他后来学术人生影响至深,并在他长期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得以践行。
客观地说,他虽然深谙中西文化,并长期在华工作,但他留下的学术著作并不算多,现在人们能够记得住的大概只有他的《中国哲学研究辅助》(Aid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为数聊聊的著述了。但作为学术活动家或者学术组织者,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作为燕京大学的首任哲学系主任,他对燕大哲学学科发展、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做出过奠基性贡献,比如冯友兰等就是他的大力推介而加盟燕京大学的。博晨光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将西方基督教、哲学和科学传播给中国青年,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向美国人译介中国哲学(包括风水思想等)。
其次,作为哈佛燕京学社初创时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担任了学社北平办事处首任总干事,在学社的成立、运营、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曾为学社购买了大批中国地方志、丛书,欧洲中国学著作,欧洲著作等[21]。正是由于这些努力,学社成立之初,他便受邀参加了第17届国际东方文化研究会,这表明当时的国学研究已在全世界引起注意[22]。在华四十余年里,他一直为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传统国学的发展和传播竭尽全力。他对燕大之热爱,从一点可以得到旁证,据说今天作为北大地标的博雅塔就是博晨光当年在燕京大学时直接参与建造的。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在他被日伪当局逮捕之后,为了出狱后能继续在中国燕京大学任教,他拒绝被遣送回国。
作为生活中的朋友,他对人真诚热情,待人诚恳,从上文所述他与钢和泰书信往来中所体现的真挚情感和互帮互助,我们不由得会联想到鲁迅与瞿秋白之间“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23]的深厚情谊。
[注释]
①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1916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等四个基督教教会联合将北京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华北协和女子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通州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等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初名北京大学,后更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任首任校长。参阅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等著述。
②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又作明恩普,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到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882年与博晨光之父博恒理在山东德州旁庄村建立传教点。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下,美国1908年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给中国,后成为清华建校之初的主要经费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明恩溥返回美国。著有Chinese Civilization(1885),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China in Convulsion(2 vols,1901),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1902)等。
③纽约协和神学院:20世纪初,由于美国各大专院校海外传教热情高涨,“北美宣教预备董事会”(the Board of Mis⁃sionary Preparation for North America)和美国宣教界头面人物,均力主在当时全美150所神学院校各设一宣教学教授讲席,并在北美大专院校和神学院中成立七所培训海外传教士中心,纽约协和神学院便是此七大中心之一。在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中,已在中国或预备去中国服务的传教士占较高比例,博晨光便是其中一员。(《纽约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徐以骅)
④彭靖(?):《冯友兰在燕京大学鲜为人知的往事》,载上海《联合时报》,时间不详。
⑤照片源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6%99%A8%E5%85%89/7655771?fr=aladdin。
⑥关于中印研究所,请参阅WANG Qilong.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and His Sino-Indian Institute.China Tibetolo⁃gy,2014,No.1.
⑦洪煨莲(1893-1980),原名业,字鹿岑,谱名正继,号煨莲,英文学名William。福建侯官(今闽侯)人。著名历史学家。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士学位。1923年起受聘于燕京大学,除行政事务外,任历史系教授。他在燕京大学执教23年,历任文理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1928)、国学研究所所长兼导师(1930)等,并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总编辑20多年。1933、1940年先后获得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名誉神学博士。1937年获巴黎茹理安(儒莲)奖金。1941年12月与陆志韦、赵紫宸、邓之诚等人被日军逮捕入狱,次年出狱后拒绝为日伪工作。1945年燕京复校,仍任历史系教授。1946年赴哈佛大学讲学,1947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1947-1948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1948年起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58年兼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73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倡导者奖状”。1980年12月23日,病逝于美国。主要著述有:《引得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史通点烦篇臆补》《再论杜甫》(英文)等。著作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英文专著)、《洪业论学集》等。
⑧本文引述的博晨光与钢和泰往来书信,现均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⑨《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同被誉为我国四大国学刊物,蜚声海内外学术、教育、文化界。担任其编委并参与学报编辑工作的都是大学者和学术大家,如许地山,陈桓,博晨光,冯友兰,冰心,张星烺,王克私(Philp de Vargas)等。(《燕京学报》的今昔(上),丁磐石)
⑩陈观胜(Kenneth Chen,Kuan-sheng),美籍华裔。1931年获夏威夷大学学士,1934年获燕京大学硕士,194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专长佛教史。著有《南诏时期反佛教的宣传》,《中国佛教在会昌遭到镇压的背景》等,一度担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干事。(《哈佛燕京学社》,张寄谦)
——《外国语学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