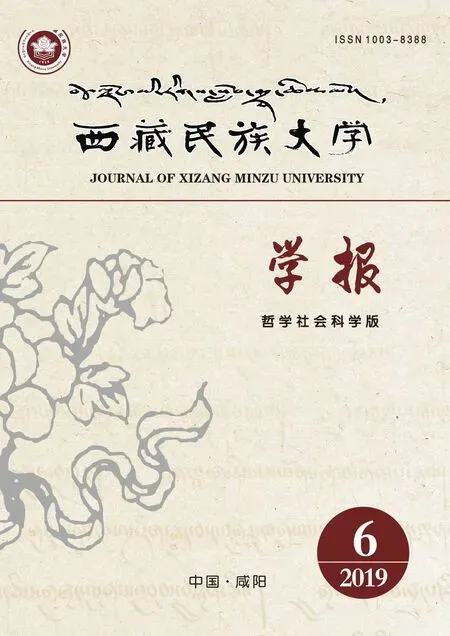再读《元史·阿尼哥传》
——以阿尼哥为中心的相关研究
严祥海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 陕西咸阳 712082)
一、问题的提出
阿尼哥是中尼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元史》专门为其作了传记,但传记内容过于简略,为全面了解阿尼哥生平事迹带来不小的困难。
之前大部分学者对阿尼哥(arniko)研究,仅局限在汉文史料或藏文史料中,囿于一隅,难窥全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以下几篇:1、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1],文章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考察了自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到明清以来,关于尼泊尔的历史文献记载,其所用文献之多、视角之宏大令人折服;2、熊文彬《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上、下),两篇文章细致地梳理了“西天梵相”的源头以及在汉地的传播,尤其是对“西天梵相”在汉地传播有深入地探讨;3、米夏埃尔·汉斯《萨迦-元时期尼藏和藏汉金属造像存在阿尼哥风格吗?》[2],这篇文章从佛教造像的角度考察阿尼哥的历史,大量汲取了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具有洞见性的观点。
本文以《元史·阿尼哥传》为中心,通过对文本逐条注释和考证,拟提出和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元史》载:“中统元年(1260),命帝师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3](P2885)根据藏文史料记载,1260-1264年,帝师八思巴不在萨迦寺,那么帝师八思巴又如何能见到阿尼哥呢?
第二,“命帝师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那么阿尼哥何时入藏以及在藏所修何塔?
第三,阿尼哥所传“西天梵相”之源头以及艺术特点为何?
第四,尼泊尔与元朝的关系为何?
二、《元史·阿尼哥传》注释及史料来源
《元史·卷203·列传第90·方技》载[3](P2885):
阿尼哥①,尼波罗国②人也,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③。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④,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⑤,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巴⑥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为弟子。从帝师入见。帝视之久,问曰:“汝来大国,得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以心为师,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宣抚王楫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镔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⑦。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⑧,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子六人,长阿僧哥⑨,授大司徒;次阿述腊⑩,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程钜夫的《雪楼集》是研究元代中前期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笔者将《元史·阿尼哥传》与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慧敏公神道碑》进行文本对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慧敏公神道碑》中对阿尼哥记述较为详细,而《元史·阿尼哥传》较为简略。《元史》由明代宋濂编撰,而《雪楼集·卷七·凉国慧敏公神道碑》现世于元代中后期,程钜夫为当时元朝士大夫。《凉国慧敏公神道碑》先于《元史》现世,《元史》无疑是在《凉国慧敏公神道碑》基础之上整理、加工而成。
三、阿尼哥何时入藏以及在藏造塔事迹
(一)对帝师八思巴的汉、藏史料考察
欲弄清阿尼哥入藏时间和在藏造塔事迹,帝师八思巴是关键性的参照人物。帝师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元大都,他对元朝和萨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搞清楚了萨迦何时修塔、由何人主持以及何时完成修塔这三个问题,则阿尼哥何时入藏以及在藏所修何塔将会迎刃而解。
《元史·卷202·列传第89·释老》为“帝师八思巴”作了传记[3](P2867-2868):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Khubilai Khan)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号大宝法王”,汉、藏文史料记载完全一致。无论是《汉藏史籍》[4](P372)还是《萨迦世系史》或是《青史》,对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以后的四年间(1260-1264)记载甚为详细。在此四年期间,八思巴一直在元大都(今北京)活动。然《元史·阿尼哥传》讲道:“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藏文史料表明,在1260-1264年间,帝师八思巴不在萨迦,既然帝师八思巴不在萨迦,那又如何得见阿尼哥呢?
为了搞清楚此问题,不妨通过萨迦寺的建造历史来理解阿尼哥与帝师八思巴见面的时间问题。关于萨迦寺(sa skya dgon)的修建事迹,《萨迦世系史》十分明确记载道:
其后,在八思巴二十八岁之时,他派人给萨迦送去许多财宝,由本钦释迦桑布于大屋顶旧殿之西面兴建了大金顶殿。后来,八思巴于三十一岁的阴木牛年返回具吉祥萨迦寺,在大金顶殿修建了几座金刚界诸天神之吉祥果芒塔,并为7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建立了伞盖、金铜合金筑成的法轮,还特为各灵塔建了金顶。
帝师八思巴28岁,即公元1262年,依藏历推算该年为水狗阳年(chu pho khyi lo),31岁为藏历的木牛阴年(shing mo klang lo),即公元1265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敦请八思巴入朝廷面圣。此处引出一个问题,帝师八思巴是1267年到达元大都还是从萨迦开始动身呢?通过《萨迦世系》的记载,帝师八思巴是在1267年(藏历为火兔阴年)开始从萨迦动身前往元大都。
《元史·阿尼哥传》讲道:“造塔吐蕃,二载而成”和“帝师一见...命监其役”以及“从帝师入见”,若要三者同时成立,则要通过藏、汉文史料比勘互证而得知。因此,八思巴最早也要在1265年间见到阿尼哥。在1260-1264年间,帝师八思巴在元大都,无法见到阿尼哥,因此在1264年或者1264年之前见到阿尼哥是不可能的。
那么“命其监役”,那么所监何役呢?根据藏文史料《萨迦世系》记载:“八思巴于三十一岁的阴木牛年(1265)返回具吉祥萨迦寺,在大金顶殿(gser thog)修建了几座金刚界诸天神之吉祥果芒塔,并为纪念前辈教主的七座灵塔建立了伞盖、金铜合金筑成的法轮,还特为各灵塔建了金顶。”
通过藏、汉文献的互证,可以推知阿尼哥“所监之役”:(1)修建金刚界诸天神之吉祥果芒塔(rdor dbyings kyi lha tshogs bzhugs pa’i bkra shis sgo mang rin po che);(2)为七座前辈教主(rje btsun gong ma)的灵塔(phyi rten sku‘bum)建立了伞盖(gdugs)(3)金铜合金筑成的法轮(chos‘khor gser zangs las grub);(4)金顶(gser thog)。吉祥果芒塔(bkra shis sgo mang rin po che)和萨迦七座教主灵塔(phyi rten sku‘bum bdun)均在萨迦北寺。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疏于修葺,这几座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元史·阿尼哥传》中又讲道:“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为弟子。从帝师入见。”[3](P2885)说明阿尼哥“所监之役”用了两年时间完成,此正好和后面见元世祖时所言“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完全相吻合。由此也就可以回答前面“所修何塔”之问题,《元史》所谓“建黄金塔于吐蕃”之“黄金塔”即为吉祥果芒塔、萨迦历代教主灵塔、合金法轮和金顶等建筑。
修塔完成后,帝师八思巴进一步认识到阿尼哥超凡的才华,勉励他入朝觐见以获得元世祖的赏识和重用。1267年,帝师八思巴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敦请前往大都。阿尼哥“从帝师入见”之举也应该在1267年年末或者之后。然在《元史·阿尼哥传》中讲道:“中统元年(1260),命帝师八合斯巴(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3](P2885),此又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建黄金塔”,但是工程浩大以至于工期较长或者1260年并不具备这样的财力,致使建造事宜推迟延缓;二是《凉国慧敏公神道碑》对“建黄金塔于吐蕃”的时间混淆。限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笔者更倾向于前者。
因此,阿尼哥入藏应在1264年间,阿尼哥则生于1247年。在1265年间,八思巴返回萨迦寺修塔之时,阿尼哥与帝师八思巴两人相见。1267年,阿尼哥随帝师八思巴前往元大都见到元世祖忽必烈。
(二)藏文史料对阿尼哥的记载
在藏文史料中,关于“阿尼哥”的记载仅能在《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中找到,在《汉藏史集·上部》的《大蒙古世系》(hor chen po rgyal rabs)中,简略地讲到了阿尼哥的事迹。有学者指出,《汉藏史集》关于阿尼哥的记载源自汉文历史的记载[5],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核查和证实。笔者将《汉藏史集》的这段藏文记述转写成拉丁文并翻译出来,以兹考校分析[4](P281-282):
维利转写:
gsungs nas bsdad yod pa’i skabs/khong ba yan dang/Au lug gnyis/gcig las gcig bzang pa’i blon po gnyis yod pa’i dus der/yang rgyal pos/bla ma la/da ba yan‘di/sman tshe’i phyogs su btang na gsung pas/des pher bar‘dug nged kyi don grub pa’i thabs dang/rten‘brel byed gsungs nas/bal po Ae ner dga’/sprul pa’i lha bzo lta bu la zhal ta mdzad/dzu chur lha khang dang/chos skyongs mahākāla’i sku‘khor dang bcaspa bzhengs/rab gnas/bla ma rang gis mdzad/mgon po’i zhal/sman tshe’i phyogs la gzigs pa mdzad/slob dpon dam pa kun dga’chos skyong/der bsgrub pa mdzad pa la bkos/ba yan la/ching sang gi ming dang/
拙译:
从在位之时谈起,伯颜(ba yan)和耶律(Au lug)二人,在这个时期连续有两个贤能的宰相。复次,皇上对上师说:“现在,伯颜去了汉地(sman tshe),故有很多成功的办法和机缘。”尼泊尔人阿尼哥(Ae ner dga’),有神变画塑之能。他建造了楚曲神殿(dzu chur)和护法大黑天(mahākāla)之塑像,上师开光以示现怙主之面,在汉地建造了瞻台和阿阇梨丹巴贡噶护法,此乃建立功业之事迹。伯颜乃一丞相之名。
藏汉词语对照:
伯颜ba yan 耶律Au lug
汉地sman tshe 阿尼哥Ae ner dga’
楚曲神殿dzu chur lha khang
大黑天mahākāla 丞相ching sang
阿阇梨丹巴贡噶护法slob dpon dam pa kun dga’chos skyong
通过以上材料来看,阿尼哥来到元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后,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此时正值应该伯颜当丞相期间。在伯颜征战南宋期间(公元1274-1279年),由于阿尼哥卓越的建造技术受到忽必烈赏识,委任阿尼哥建塔造寺等,为国家祈福禳灾。本材料并不与前面之推断和论证相抵牾,前后逻辑通畅。依此而论,此亦能佐证前面的推断和论证成立。
四、阿尼哥所传的“西天梵相”
(一)阿尼哥所传之“西天梵相”之学及其源头
阿尼哥之历史功绩在于造塔、建寺,其所建造之塔寺风格与汉地固有风格迥异,在当时的社会有不小的影响,《凉国公神道碑》这样评价道:“又蒙恩建碑焉,惟公生自金方,虽智由天性。然所知不出其本及逢圣人之与,不间万里来归于廷观。”[6]《凉国慧敏公神道碑》简明扼要总结了他一生的功业:“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因此,《元史·阿尼哥传》才讲道:“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图画弗及也”,那么阿尼哥学问的源头为何呢?
为了厘清阿尼哥所传造塔寺学问之源头,我们不妨可以先从阿尼哥之弟子刘元开始追溯。《元史·卷203·列传第90方技》载[3](P2885):
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搏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
根据《元史》对阿尼哥弟子刘元的记载,可以得出:(1)阿尼哥所传之学被称作“西天梵相”;(2)“西天梵相”与“西番佛像”同出一源;(3)与汉地风格迥异,“人罕得见者”,当时在汉地尚未传播。海德格尔说:“伟大的事件总有伟大的开端”,一门学问总有其源头,阿尼哥所传的“西天梵相”之学也不例外。《元史·阿尼哥传》中讲道:“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由此可知,在当时尼泊尔,《尺寸经》是“绘画妆塑业”的根本经典。换句话说,《尺寸经》是阿尼哥所传的“西天梵相”之学的根本经典。
《尺寸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经典?《元史·刘元传》载:“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3](P2886),《尺寸经》自然也就不为汉地之人所知晓。由于《元史》对《尺寸经》介绍得太过简略,因此笔者只能从现存的汉、藏文献中进行尝试性探寻。
(二)《尺寸经》文本的尝试性探寻
遍查《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关于佛教造像的经典屈指可数。《汉文大藏经》中的造像经典更是寥若晨星,笔者仅找到了一部以造像命名的经典。在《藏文大藏经》中,笔者查到四部与佛教造像有关的经典,一般称之为“三经一疏”。现将汉、藏文经典名列举如下:
汉文类:
(1)唐·于阗三藏提云般若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一卷),收录在《大正藏》十六册。该部经典是讲如何让信众增信,而非讲造像尺寸,与《元史·阿尼哥传》讲的《尺寸经》旨趣相去甚远。
藏文类:
(1)《造像度量经》(das'atāla nyagrodhaparimaṇd.ala budhapratimālaks.aṇa,sku gzugs kyi tshad gyi mt⁃shan nyid),亦称《身影量像相》,NO.5804(gzo rig pasna tshogs ngo)。《造像度量经》的梵名为das'atāla nyagrodhaparimaṇd.ala budhapratimālaks.aṇa,直译为《如尼拘卢陀树纵围十搩手之佛身影量像相》。有学者考证,该经典藏译时间最迟在公元14世纪初[7]。该经汉译本由工布查于1742年从藏文本译出[8]。
(2)《佛说造像度量经疏》(saṃbuddhābhas.ita pratimālaks.aṇa vivaraṇa,rdzogs pa’i sangs rgyas gyis sku gzugs gyi tshad gyi rnam‘grel),亦称《等觉佛所说身影量释》,NO.5805。《佛说造像度量经疏》是对《造像度量经》的解释。
(3)《画法论》(citralaks.aṇa,ri mo mtshan nyid),NO.5806。该经典在造像方面有着极高的地位,受到历代高僧和藏族工匠重视。该经典是一部婆罗门的造像经典,目前尚未发现完整的梵文本,但被佛教徒保存并流传下来[9]。
(4)《身影像量相》(pratimālaks.aṇa,sku gzugs kyi tshad kyi mtshan nyid ces bya ba)NO.5808。
以上列举了有关佛教造像经典的名称,但并不能确定以上何者即是《元史·阿尼哥传》中的《尺寸经》,或者根本不在以上列举之列。因此,《尺寸经》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富有挑战的研究工作,希冀通过藏文、梵文、汉文等多语本文献对勘的途径来解决。
(三)“西天梵相”的艺术特点
元朝以前,汉地佛教艺术主要以唐代佛教艺术风格为其典型。唐代佛教艺术风格即是糅合了印度犍陀罗艺术与汉地固有建筑艺术风格而成,此种风格并不称为“西天梵相”。《元史·阿尼哥传》中所指的“西天梵相”,是指以印度-或尼泊尔和西藏造像风格传播到汉地后形成的佛教建筑艺术风格,将其称之为“西天梵相”,以有别于汉地固有的佛教建筑艺术风格。
“西天梵相”的艺术源头来自印度-尼泊尔,后传播到藏地进一步吸收融合藏地建筑艺术,再传播到汉地的佛教艺术风格。为了理解“西天梵相”的艺术特征和在汉地的流传,阿尼哥弟子刘元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元史·卷203·列传第90·方技》载[3](P2886):
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征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大夫观者,咸叹异焉。
由上可知:(1)刘元乃元朝皇家御用“工程师”,其造像水平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2)他精通汉地传统的建筑艺术,所造的道教神像及侍臣像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而他受到汉人士大夫的赞扬和叹服;(3)他巧妙且成功地融合了汉地建筑艺术风格。
因此,阿尼哥所传的“西天梵相”源头是印度-尼泊尔佛教建筑艺术,经过逐步吸收和融合藏地和汉地的建筑艺术风格,随后在汉地形成独具一格的佛教建筑艺术风格[2]。
五、尼泊尔与元朝的关系
尼泊尔与中国官方往来始于唐代。元朝西南边疆直抵喜马拉雅雪山。那么,尼泊尔与元朝的关系怎么样呢?《元史·阿尼哥传》讲道:“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和“奉命造塔吐蕃”[3](P2885)云云,究竟奉谁之命以及为何要奉命?1274年3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招抚尼泊尔。《元史·卷第八·本纪第八·世祖五》载:“遣要速木、咱兴憨失招谕八鲁国(bal/pala)。”[3](P97)尼泊尔是元朝的藩属国之一,因此才有元世祖忽必烈之问和阿尼哥“奉命”之答。
藏文史书《贤者喜宴/mkhas pa’i dga’ston》载[10](P1423):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王室就确立了进攻印度的目标,到元朝时忽必烈也不例外,据说他曾“打算道经吐蕃向尼婆罗和印度进兵,多次派遣金字使者前来察看道路。上师郭仓巴,大成就者噶玛巴的弟子部坚巴以广大佛法满足金字使者的愿望,为取悦皇帝编写了赞颂皇帝的颂辞,让使者们亲眼观看河流的流向,劝阻不要打开去尼婆罗印度之路,写了河流之流向如此,贤明之王亦应如何之流向的话,进呈历代皇帝,阻止了进兵,使印度、尼婆罗和吐蕃避免了战争的恐怖。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尼泊尔的地缘价值,遣使招抚尼泊尔,将尼泊尔纳入元朝的外藩,也是情理中之事。明朝前期延续了尼泊尔与元朝友好的藩属关系,《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九·西域三》载[11](P5755):
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二十三年再贡,加赐玉图书、红罗伞。终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涌塔王可般。明年遣使来贡。封沙的新葛为尼八剌国王,赐诰及镀金银印。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锦、纟宁丝,地涌塔王如之。自后,贡使不复至。
明朝继承了尼泊尔与元朝的藩属关系。明朝前期,尼泊尔和明朝两国的官方使者经由西藏往来十分频繁。尼泊尔与明朝的藩属关系直至1427年才中断。
六、小结
阿尼哥作为中尼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尼泊尔与元朝的宗藩关系自然而然地投射在阿尼哥的生平事迹中。弄清元代的中尼关系对我们理解和践行今天的中尼关系具有启示意义,这将有助于推进“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释]
①阿尼哥,在程钜夫《雪楼集》作“阿尔尼格”,拉丁文拼写一般采用arniko;《汉藏史籍》(藏文)的拼写为aenerdga’。关于阿尼哥生平,大多根据《元史》记载,认为其生于公元1244年;但根据藏文文献的记述和相关问题的推断,汉、藏文献在时间上不一致。笔者经研究认为,阿尼哥生于1247年。
②尼婆罗,梵文Nepāla或Nevāla,现在尼泊尔语转写为Nepala,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均有专门的记载,二者记载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同点,二者均提到了其手工艺十分发达。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七》中用佛教徒的视角,记载了当时尼泊尔的地理、人文、风俗及宗教状况。
③八鲁布,为藏文bal po之对音,意为“羊毛”。在诸多清代文献中,将尼泊尔称为“巴勒布”,如《卫藏通志》载:“西南接布鲁克巴、巴勒布(bal po),通西洋等处。”参见松筠.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8。
④“凡儿,稍长,诵习佛书”,足以说明元代尼泊尔依然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直到明朝前期,佛教依然在尼泊尔流传,《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九·西域三》载:“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
⑤何谓《尺寸经》?《元史》对此并没有过多的细节交待,但从上下文之语境(context)来看,《尺寸经》当为一部如何造佛像和佛塔尺寸的经典。
⑥八合斯巴(公元1235-1280)系八思巴(’phags pa),原名为洛追坚赞(blo gros rgyal mtshan),藏文意为“圣者”。因其聪明神异而得名,《元史·卷202·列传第89·释老》载:“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萨迦世系》(sa skya gdung rabs)中说“咏《本生经》(jātaka,skyes pa’i rabs)),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paṇd.ita之对音-引者注)。”
⑦“为七宝镔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这表明元世祖忽必烈以佛教的意识形态来塑造自己王统的合法性,这和《蒙古源流》和八思巴所造的《彰所知论》(shes bya rab gsal)的讲述相吻合,将其塑造为“转轮圣王(cakravarati)”。
⑧“初服”取自屈原《离骚》:“进不以离尤兮,退将吾修初服”,此处意为“养老、退休”之意。
⑨“阿僧哥”为梵文asañga之对音。
⑩“阿述腊”为梵文asura之对音,意为“非天非人”,是佛教术语“阿修罗”之异译;在程钜夫《雪楼集》中作“阿卓勒”,其对应为梵文ajuna,为印度神话的主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