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外两篇)
☉刘星
治理社会无非有三种形式:法治、人治和无为而治。一般认为洋人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洋人在观念上都是喜欢法治的。这种说法只能说是部分正确。翻翻西洋历史,你不仅可以发现人治的痕迹,而且可以看到鼓吹人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哲人贤达(如柏拉图)。为什么有人喜欢人治?这恐怕与法律的缺陷有关。
先看一个小例子。数十年前,英国审理了一个颇为棘手的刑事案。案情是这样的:一天,一名叫乔治的小伙子在家里闲得无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看看飞机日常训练。他轻手轻脚地爬过机场旁边的铁丝网和障碍物,坐在机场跑道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天上的飞机。这时,一架飞机打算降落。正当慢慢降落时,飞行员发现跑道上坐着人,不得不将飞机再次拉起飞向天空。虽然乔治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警察还是将他带走了,并于几天后把他送上了法庭。
当时审理此案的法官叫帕克。在开庭那天,帕克一手拿着一部叫做《官方机密条例》的法律,一手翻阅着案件调查的情况说明。当检控官陈述完起诉状后,帕克法官问乔治还有什么可说的。乔治回答说,他甘愿受罚,谁让自己这样无聊地惹事呢。可是,乔治的辩护律师却说,乔治不应受罚,因为他没有违反《官方机密条例》的规定。
律师让帕克法官仔细阅读该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上面写着:“不得在禁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律师巧辩道,虽然军用机场毫无疑问是个“禁区”,乔治也妨碍了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但是,他不是在“禁区附近”而是在“禁区里”做的事。条例第三条只规定了“在……附近”,没有规定“在……里”,所以依据这条规定是不能处罚乔治的。律师还提醒帕克法官注意,英国是个法治国家,法无明文是不为罪的。这样,帕克法官还真是为难了。
大家都说,法律的优点在于它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可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正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所以遇到特殊情况便无法随机调整;正是因为它具有明确性,不能模棱两可,所以遇到未曾遇见过的情形,便难以灵活处置。而人的智慧就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处断。在上面那个案件中,假设没有法律在旁边,帕克仅用自己的智慧来断案,可能就不存在为难的问题了。如果再加上人的自觉自律,那么在治国上能说人治不如法治吗?
当然,尽管西洋历史出现过人治,有人根据上面所述理由赞同过人治,洋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法治。不过,最后的选择并不表明法律没有了缺陷,也不表明法律完全可以顶替人的智慧的灵活性。其实,法律的缺陷是法律本身固有和无法消除的。洋人最终选择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觉得法律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仅仅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
法律的条文与目的
当今,我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法治。
法治有许多要求,其中一条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难理解,如果法律制定出来了,文字是清清楚楚的,那么便不能有个什么“灵活”问题。假如可以“灵活”,今天你灵活,明天他灵活,严格依法办事自然要大打折扣,法治似乎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假设严格依法办事就是严格照法律条文办事,我们有时就会发现,这本身可能就是不大合乎理性的。
我们从西方人那里借个例子来说明。
有那么一个市政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有关市区城管的法律条令。里面讲,在市区公园内不得通过或停放任何机动车辆。条令颁布后,各公园都严格执行,绝不让各种车辆进入。一天,某军人团体将一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使用的军用吉普车开进了市中心公园。当时,公园管理人员说不行,可这个军人团体非要将车开进去。团体的代表说,这辆车非同一般,它象征着国家军队在战争中的艰辛与光荣,将车摆在公园里,是为了让人们在公园享受幸福欢乐的时候不忘这些东西来之不易。就这样,车硬被放在公园的中心草坪上。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军人走到哪里都备受人们尊敬。他们把车放在公园以作纪念。管理人员也没觉得有啥不好。可是市政委员会有令在先,管理人员又总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是,他们找到军人团体代表商议,劝其将车拉走。但军人团体毫无退让之意。
公园管理人员无奈,只得告到法院。公园一方说,法律条文清清楚楚,没办法,被告只能将车拉走。但被告说,这车放在公园不是随意的,它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战争与军人。法院首先明确了几个问题:第一,条令很清楚,任何机动车辆不得停放在公园里;第二,军用吉普车绝对属于机动车辆;第三,按条文字句看,吉普车当属禁止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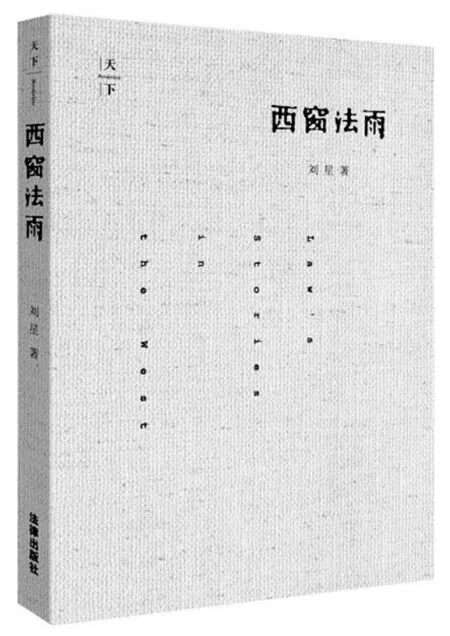
然而,法院又在想另一个问题:市政委员会颁布这条法令是为了什么?换个问法,为什么机动车辆不能停放在公园里?想来想去,法院得出了结论:禁止停放是为了让公园避免不安全噪声和污染的“侵害”。如果车辆可以停放在公园里,就意味着车辆老要进进出出,老是进进出出,当然会有不安全、噪声和污染。而按照这个结论,上述吉普车放在公园里并不与市政委员会立法的目的相矛盾,因为它不会产生不安全、噪声和污染。既然停放吉普车没有违反法律的目的,为什么要禁止呢?显然,禁止是不合理的。最后,法院认为可以停放。
所有的法律都有自己的目的,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立法者在立法时不知为了什么,那么我们会说他是非理性的。同样,如果司法者在司法时不知法律条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会说他是非理性的。所以,有的西方人认为,法律不仅是条文,它还包括目的;司法时不仅要看条文,而且要想目的。
依此之见,严格依法办事就不应该处处唯条文是举。将目的视为法律的一部分,法治可能才会更具有理性。
法律形式上的正义
说一部法律好不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看它的内容如何,二是看它的形式如何。不过,长久以来,人们总是从内容上来谈法律的好坏,像纳粹德国时期的有关杀害犹太人的法律,二十来年前的南非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法律,我们都会说它们的内容是不好的、非正义的。
现在,西方人倒是常常谈论法律的形式问题。法律的形式涉及这样的问题:1.规定的内容是否清楚;2.是否可行;3.是否也管过去发生的事情;4.是否公开等等。西方人说,如果法律在形式上不好(如内容不清、秘密实施),则它也是非正义的;而如果在形式上都是非正义的,就要在其身上打个问号,问它是不是法律。
1943年,纳粹德国在那些纳粹分子之中传达了许多秘密的“法律”文件,其中之一是有关宣扬对德国领袖不敬言辞的人如何处置的内容。当时,一般老百姓对此无一知晓。
1944年,有个叫冯·伦徳的新闻记者,看到第三帝国的昔日辉煌不再,日渐对希特勒和戈培尔等人产生不满。他觉得,德国的衰落,纯粹是因为希特勒和戈培尔之流的疯狂弄权。在报社,冯·伦德有时见人就发牢骚,甚至指名道姓说希特勒尤其是戈培尔的蛊惑言论将德国人引入死亡之路。没过多久,冯·伦德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盖世太保的“政治危险”人物花名册上找到了冯·伦德的名字,而且,在他的名字下面注有一行说明:“依有关秘密法律处决。”
对纳粹德国时期的法律,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它肯定是邪恶的。但如果都是邪恶的、非正义的,还能不能叫法律?在大战刚刚结束的那些日子里,不少人毫不犹豫地认为它不是法律,许多西德法院的法官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案件时都是这么说的。
可是有些西方人倒是挺“小心”的,他们认为,从内容的角度来说一个规则不是法律可能有失慎重。因为,对实体内容的评判,完全依赖我们的道德观念。对纳粹,我们可以有相当一致的道德判断,但对许多其他问题如堕胎,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看法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论,如果因为对其有道德上的不满,能否直说允许堕胎之类的法律不是法律?如果能说,社会的法律秩序岂不时常要受到威胁?
然而,这些西方人却明确地讲,一个规则在形式上出现了毛病,则可以大胆地说它不是法律。法律必须公开,必须清楚,必须不溯及既往,从而让人们知道怎样行为。这样的话,即使其内容是邪恶的,人们也还能在知道的情况下躲避它的魔爪,冯·伦德也不至于连死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也算是给人们留下一个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权利。另外,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形式,只有公开地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才能谈到法律的治理。所以,不仅存在形式正义的问题,而且它是法律的最基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