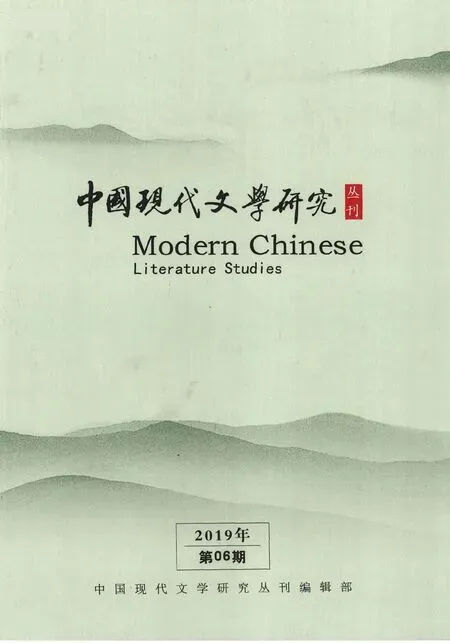鲁迅、周作人失和与羽太信子的“癔症”※
马春花
内容提要:关于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委,之前的诸多研究,屡屡归因于羽太信子的“癔症”发作,但这种说法多有纰漏,存在诸多可疑之处。因此,有必要从考证羽太信子的“癔症”入手,勾勒“癔症说”得以形成的历史谱系,分析各种“二周失和”叙事对于羽太信子再现政治,进而说明羽太信子是如何被生产为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与此同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亦可以发现作为“她者”的羽太信子的某种历史能动性,她通过“癔症”进行权力表征,终而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话语策略,完成了自我的主体建构。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与坊间乐道的话题。“经济矛盾”与“思想分歧”的“正传”,与“听窗”“偷窥”“无法言说的爱情”等“稗史”,纠结一气,成为盘桓不去的“幽灵”,构成了鲁迅研究以及周作人研究中,难以回避的历史“症结”。许久以来,对于“二周失和”事件的探究,往往以指认一个有罪他者——羽太信子而告终。似乎兄弟二人反目成仇、隔如参商,皆源自这个日本女人的“谎言”。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者在论及“二周失和”事件时,多愿意以癔症患者贬斥羽太信子,以为只要落实她的“歇斯底里”,尤其是事发之时有癔症发作,“兄弟失和”的公案便可迎刃而解。
不过,有关羽太信子癔症的论述其实多有纰漏,存在诸多可疑之处。譬如,羽太信子的癔症始于何时,由何而来?周氏兄弟失和冲突的当下,羽太信子是否真的癔症暴发?羽太信子的癔症除造成“二周失和”的后果外,可否有别样的阐释层面?基于上述问题,有必要从考证羽太信子的癔症入手,勾勒其“癔症说”得以形成的历史谱系,分析各种“二周失和”叙事对于羽太信子癔症的再现政治,在探看羽太信子是如何被生产为一个“无声他者”抑或“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同时,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阐明这个出身卑微的日本女性,如何利用间接的发声方式——身体扭曲与话语疯癫——癔症,来进行权力表征,并终而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话语策略,完成了自身的主体建构。
一
最早将“二周失和”与羽太信子的癔症联系起来的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中,许寿裳认为:“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许文将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性与“内怀忮忌”联系在一起。“忮忌”即嫉妒。羽太信子是一妇人,鲁迅的弟媳,她嫉妒鲁迅什么?当然只能是鲁迅的家长身份。一个女人,却觊觎一家之长的地位,当然是不可理喻的歇斯底里。许文中的歇斯底里,暗示的是羽太信子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不该有的野心。至于羽太信子歇斯底里的病理学症状、发作肇因,就像许寿裳曾言及的令周作人“轻信”的“妇人之言”一样,语焉不详。
关于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症,周氏家族成员的回忆要详细些。很有可能亲历过羽太信子癔症发作的周建人回忆道: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住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根据周建人的记忆,羽太信子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可上推到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夫妇暂居绍兴时期。羽太信子歇斯底里在彼时的发作,被描述为羽太信子一家“欺凌和虐待”周作人的手段之一。这种歇斯底里症候几乎是家族性的,因为周作人的郎舅和小姨的“破口大骂”,在一定程度来说,也是近乎“歇斯底里”的。而且,夫妻家庭/家族内的“欺凌和虐待”,最后被上升到种族欺凌的政治高度,日本使馆在家庭纠纷场景中的出现,其实就是将家庭矛盾上升为国族矛盾的叙事策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周作人的郎舅与小姨,亦是周建人的郎舅羽太重九和妻子羽太芳子,周建人与羽太芳子1914年成婚于绍兴。
至于没有亲历过羽太信子癔症的许广平和周海婴,则往往转述他人的说法。许广平的记述“可能”来自鲁迅,她“复述”鲁迅的言语道:
信子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还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撒起泼来,顶多只是装死晕倒,没有别的花招。但有一回,这一花招却被她的弟弟重九看见了,就说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家里人长久以来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
在许广平的记叙中,羽太信子“撒泼”“装死晕倒”等歇斯底里症,不过是“花招”和“戏法”而已,而且被自己的弟弟羽太重久拆穿。当然,许广平的复述同样遵循着国族政治的原则,在叙述羽太信子歇斯底里症之前,不忘交代绍兴是没有“日本领事馆”的,失去政治庇护的歇斯底里花招,于是只能被“拆穿”而已。不过,周建人笔下与羽太信子沆瀣一气的羽太重久,却被赋予了拆穿羽太信子“花招”的作用,其见怪不怪的反应,则暗示了羽太信子之歇斯底里的惯常性。周海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暗示,他引用鲁老太太和邻居俞芳的谈话说:
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
周海婴将羽太信子的癔症发作,由绍兴时期、北京时期,一直上推到日本东京,且“时有发作”,可见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症并非新疾,乃是顽症。
从周建人、许广平到周海婴,叙述立场大体一致,对羽太信子其人、其“病”的厌弃溢于言表,而“日本使馆”“日本领事馆”等词汇在各种表述中的频频在场,则是一种以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叙事的策略。令人遗憾的是,叙述者一方面指出羽太信子的确患有歇斯底里症,然而另一方面,却缺乏对病患者的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与同情。相对来说,俞芳转述的鲁老太太的说法,似乎更合乎人情:
信子初到绍兴时,不懂我们的话,事事都得老二翻译,可是老二每天要到学校去教书。每当老二不在家时,看到信子一个人孤孤单单,怪可怜的,但也没有办法为她解决困难。不料,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
初入异国他乡的一个大家族之中,语言不通,孤单一人,在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时发病,也算是情有可原。对信子癔症的发作,鲁老太太其实抱有很大的同情心,认为羽太信子“怪可怜的,但也没有办法为她解决困难”。而老人家叙述中的“大哭”“昏厥”等症状,比起前者叙述中的“装死晕倒”等主观性说辞,显然更为客观中立。
许寿裳、周建人、许广平、周海婴等人近乎一致,强调的是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病症中隐含的野心、霸道,甚至是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霸权。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鲁迅被赶出八道湾的根源所在。不过,指认羽太信子存在歇斯底里症,并继而营造周作人惧内的叙事,并不能证明“二周失和”的根源,就在于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症”。与周氏家族成员侧重建构羽太信子强势的日本女人形象有所不同,后来研究者更喜欢用癔症,而不是“歇斯底里症”来指认羽太信子。实际上,歇斯底里就是癔症,癔症就是歇斯底里,但由于偏重在“癔”上,羽太信子的“秽语”“妇人之言”则只是一人之臆想、臆念而已。于是,羽太信子这个女人不过是在有意(癔)无意(癔)间,向周作人以及大家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因为她“富于幻想”、“易受暗示及自我暗示”、而又“缺乏理智的分析”,所以她才会对鲁迅对其妻子的异常“冷漠”表现,对她自己的异常“亲热”表现发生种种联想,产生错误的领会与错误的判断,认为鲁迅对她及孩子们的种种关怀与爱护的举动,是在传递性爱的信息,暗含猥亵的心怀,并且深信不疑。因此,“1923年7月14日,当信子以鲁迅对她有‘失敬’举止而引起双方冲突时,羽太信子当即癔病发作。周作人日记十七日记有‘池上来诊’的记载,说明信子病情严重,但她未把发病的原因立即告诉自己的丈夫。”
周作人对大哥的分开自吃诘问信子,诱发了信子的癔症,信子在丈夫的诘问前以1921年鲁迅欲“失敬”的猜忌应对丈夫。周作人信以为真。
为了证明“二周失和”事件发生时,羽太信子的确癔症发作,诸多学者多引用周作人晚年日记所记信子“易作”频仍之事。而“易作”频仍的原因,却又肇源于信子怀疑周作人甲戌年(1934)东游日本时有外遇。羽太信子亦忌讳于周氏兄弟皆“多妻”(鲁迅于朱安夫人之外有许广平,周建人于羽太芳子之外有王蕴如),既然周家的老大和老三都多妻,老二想来也不会例外。这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羽太信子可以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周作人身上,会不会也同样加诸鲁迅身上呢?而且在“二周失和”事件发生之前,周作人日记中确有“池上来诊”的记载。于是,钱理群便谨慎推测:“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朱正则根据信子晚年“易作”频频的缘由,结合当年周作人日记中的“池上来诊”的记载,进一步推断周作人日记中被剪去的约十个字,可能是“易作,如谵如呓”,并认为周作人把信子的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是“昏”的表现。
在诸多后来研究者看来,既然羽太信子因为妄断周作人外遇而“易作”频频,那么若能坐实“二周失和”事件发生时,羽太信子也是癔症发作,便能证明所谓“不敬说”自然也是子虚乌有。那么,根据周作人1923年7月17日“池上来诊”的日记,能否推断其时羽太信子确实癔症发生呢?应该不能。在1923年7月15日的日记中,周作人记载“7月15日,玛利子病,池上来诊”,玛利子即是周建人之女周鞠子,对照周作人日记中凡有人新病,必有人名记录的惯例,1923年7月17日的“池上来诊”,应为继续诊治玛利子之病,而不是羽太信子。中岛长文也曾分析:“她若照例出现歇斯底里,也许事情会是另一种情况,但她没有发作。”晚年羽太信子“易作”频频,周作人似乎不堪其扰,颇有怨辞,在其日记中也多有记载。然而,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现实的困窘、政治的压抑、疾病的折磨,或者才是羽太信子发病频频、周作人不堪其扰的原因。
关于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症,除鲁老太太外,周氏家人皆强调其“悍”的一面,“大哭”“吵闹”“装死”“晕倒”等,皆是泼妇的“花招”,而“民族主义”叙述,显然又暗示了其“悍”的殖民/帝国主义根源。后来的研究者则强调羽太信子“癔”的一面,“如谵如呓”,妄想症而已,就像她无端怀疑周作人外遇一样,她自然也可能凭空“臆造”鲁迅的“不敬”抑或“偷窥”。“悍”与“癔”彼此交叉强化,呈现了一个非理性的失常者形象,一个理应驱逐的疯癫他者。而在相关叙述中的周作人,既“弱”且“昏”,最终受制于歇斯底里的他者,造成兄弟失和的“一生的大损失”,致使“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
二
关于羽太信子的癔症,鲁迅从未涉及只言片语。而在周作人的日记中,他对羽太信子的日常行状,包括生病时的病因、诊治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羽太信子癔症发作的具体情况,在目前可查阅的周作人日记中,1920年之前的居绍兴时期并无记录,而1920年代居北京时期约有五次,1930年代一次:
1920年5月26日,上午重君来云小儿危笃,信子携若子(日语)去,下午八时后回昏晕招山本来。
1920年8月1日,下午信子因与重九论争又发病,晚请山本来诊。
1922年4月24日,信子病山本来诊。25日,山本来诊。26日,山本来诊。
1922年8月31日,晚池上来诊,信子发病注射二次,夜睡不足。
1923年1月7日,信子发病,池上来诊。.
1933年7月16日,丰一又发热,吾(?)语违忤,信子发病语利。7月17日,信子不食,晚又发热,语不通。7月18日,上午招盐池来诊信子病。
周作人日记对全家病症的记录一般较为详细,惟这几处,羽太信子的病症仅简略记为“发病”“昏晕”,“发病”“昏晕”的记录,或可推测为癔症发作。但是,这与其晚年直接记录羽太信子“易作”以及他“甚不快”的表述完全不同。其时,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彼此融洽,并无多少冲突、困扰,因此对其发病未见微辞。1951年开始,周作人的日记里开始出现“不快”的记载。除“1951年5月1日,信子为丰一夫妇移居事发病,特请东邻梁大夫来诊”直接说明“发病”外,其余一般未予说明。如:
1951年3月18日:甚不愉快。
1954年1月3日:夜睡不安,因此亦思长眠之乐。4月30日:下午觉不快不工作。6月2日:晚极不快,睡不足。6月25日:下午不快,止工作。8月31日:晚雨,极不快。
此后时断时续,1956年、1958年都有或长或短的“不快”记载。1960年后,周作人记录的信子“易作”开始频繁,周作人不堪其扰,“不快”日甚。
1960年5月25日,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7月1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7月3日,今日又不快,未工作。7月9日,晨,极不快,拟译书遂止……晚不快,至十时后,犹独语不已。7月10日,上午困倦不作事,仍大不快。7月11日,拟工作而精神动摇,暂不从事,下午出,不快问题似仍未了也。.7月12日,终日不快。7月26日,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又不得工作矣、前得和解才有12日耳,殆亦业也。……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7月28日,时雨时霁,仍又不快。7月29日,下午又复不快……但苦不能耳根清静,得以自迁,待死耳。7月31日,午前入浴,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污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8月14日,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9月13日,虽有不快,仍得六纸,盖所谓死物狂也。11月13日,上午大不快,似狂癔发。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11月28日,又复不快,似旧疾复作,虽暂平愈亦只一时而,一叹。12月10日,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12月11日,拟译书,因不快而止。12月31日,一年倏已了矣,唯愿明年有平静的一年,得以安静的工作耳。
1961年,信子“易作”更频,几乎每日如是,发怒呓语,周作人动辄得咎,故说信子是恶魔、鬼祟附体。
1961年1月5日,因不慎言又引起大不快,此疾恐终不能愈,亦属命运也。1月18日,上午不快余波未了。1月24日,上午又不快,似每日应时发也。2月10日,上午即不快。.3月2日,上午不快。.3月11日,上午略不快,似病又发作矣。3月27日,上午又稍不快,所谓转喉触讳也。3月28日,上午又复不快,殆古人所谓冤孽也,只可以迷信之说解了,说是前世事亦大可怜矣,日日记此亦复可笑。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4月24日,上午又不快。4月29日,不适亦不快。5月29日,上午甚不快。.5月30日,又不快。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6月16日,上午又易作,乃至不知话言,甚感不快,只默尔而止耳。.6月17日,上午不快,无因而至。6月26日,又易作,甚不快。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8月7日,似又疾作,甚不快而止。.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9月1日,晚大不快,幸即了矣。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9月22日,无事易作,不快殊甚。.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10月20日,又易作,梦呓不止。.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10月27日,易仍时作,以呓语相苦,诚可谓冤业。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獬犬。.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11月13日,上午仍不快。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周作人本拟不再记录“不快”之事,然而不久,又记录3次。
1962年1月4日,下午关于不快的事,今年已决定不再记矣。2月24日,易作,殊甚不快。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入院,8日病故。.....
新中国成立后,羽太信子“易作”频频,学者多以此来证明她的无由妄想,并因此给周作人造成巨大痛苦,而不愿涉及羽太信子“易作”频繁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生活困窘、政治压抑等原因之外,羽太信子身体状况的恶化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羽太信子患有糖尿病,腰腿有病,不能下地行走,卧床数年。。且在1960—1962年间,食物、药品匮乏,身体愈益衰弱,再加病入膏肓、思乡日苦,心情不佳,癔病发作,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周作人在日日“甚殊不快”的同时,仍能“兴师动众,远及数千里外的友人为办差使”,购买盐煎饼、味之素、栗馒头、海苔等日本食物,“徒为病人口腹之欲”,以慰其思乡之苦。羽太信子过世后,更是感念良久,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反复提及:
4月8日信:内人不幸于四月八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化去,或者稍得安慰欤。
4月17日信:老妻去世,于生活上稍感寂寞,唯此渐以习惯,因情绪紧张,血压不免略高。
4月27日信:内人去世,虽房中少了讲话的一个人,未免寂寞一点,但是习惯了也好,因为精神上少了一重负担,可以安心的工作,说工作现在也没能开始,希望到五月中旬当可渐渐安静下来吧?
虽然羽太信子“易作”频仍,但夫妻情谊仍笃。在其发怒、昏呓时,周作人写道:“临老老吵架,俾死后免得相念,大是好事。”(1960年10月9日)1962年4月6日,信子被送入医院,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4月15日又写:“距信子之殁已整七日矣,念之慨然。”一年以后再写:“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一九〇八)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四月八日也。”虽每每吵闹不快,却仍心念旧情,令人唏嘘。
因为关乎“二周失和”的原委,羽太信子的癔症在1947年即被许寿裳提及,之后更是被周氏家族成员以及众多研究者屡屡叙述。也许是“先见之明”于信子的“易作”有可能被“误读”,周作人干脆于日记中加以说明。他在1963年2月20日的日记背面写道: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
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至于歇斯底里症,周作人亦多有阐释,曾在《亦报》上发表《精神病问题》(1950年4月26日)和《歇斯的里症》(1951年3月18日)二文。《歇斯的里症》讽刺了犯歇斯底里症者多为妇人的说法,并指出“最特别的是,这在女人是个别的发作,在男子则有时为集体的,发作时更是可怕”。由此可知,周作人对于动辄指认女性的歇斯底里,是相当地不以为然。实际上,周作人对歇斯底里的分析,已经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理论再生产有内在相通之处了。
三
歇斯底里(癔症)一直被建构为“女性疾病”。“歇斯底里”一词源自古希腊,意为子宫。西方古典医学认为癔症是由子宫闲置、游走引起的。柏拉图指认子宫是一个渴望生育的动物,若迟迟无法受孕,子宫将苦恼不安、游走体内,切断呼吸道,引发疾病。而治疗歇斯底里的方式不外乎两种:结婚和怀孕。意即只要女性臣服于男性/阳具,扮演好其性/别角色,癔症即愈。中国古代也有类似说法。在《歇斯底里症》一文中,周作人引用张仲景的《金匮方论》中记载:妇人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身。《金匮要略编》注云:子宫血虚,受风化热者。“可见所谓藏乃子藏,即子宫,谓其藏躁扰,乃致精神紊乱也。”近代以来,歇斯底里逐渐被纳入精神疾病领域。虽然歇斯底里挣脱了女性子宫迷走的神话,但是其作为一种“女性疾病”的意识形态建构依然如故。女性被断定“肌体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所有的妇女都有歇斯底里,都携带着歇斯底里的种子,歇斯底里成为女性“非理性本质的表征”。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源于被动的经验,女性在性方面天然的被动性,说明了她们何以比较容易变得歇斯底里。颓废善变的歇斯底里的欲望,是女性特有的欲望。
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有关歇斯底里的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不变的是,歇斯底里是女性的自然本性。不管是子宫,还是被动的女性气质,皆凸显了女性歇斯底里的本质性,歇斯底里是一种“女性疾病”。不过,伴随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高涨,作为“女性疾病”的歇斯底里,开始受到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其通常被视为一种反女性的病理学修辞。女性主义者重估了歇斯底里的建构史,她们认为不是女性器官或气质,而是女性之“第二性”的社会地位导致了女性的歇斯底里。在《歇斯底里超越弗洛伊德》一书中,主编者指出:“对女性的限制与压迫是造成女性歇斯底里身体病症的罪魁祸首。”而在其中的《歇斯底里、女性主义、性别》一文中,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歇斯底里被看成是通往女性主义的第一步,是言说和反抗父权制的特别的女性病理学。对于其他人来说,19世纪的那些有名的歇斯底里的妇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女性压抑的缩影。”
颇有意味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导致“二周失和”的羽太信子,大约也算是一位有名的歇斯底里妇女,成为诸多周氏兄弟研究者难以回避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她面目不清却影响巨大,不曾谋面却时刻在场。人们难以将其从周氏兄弟的历史中清除出去,因为由她而起的“兄弟失和”的风波,对二者的文学创作、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影响深远,甚或超过了宏观历史境遇对于周氏兄弟之人生轨迹的规定。鲁迅将“兄弟失和”的遭际称为“寇劫”,而其辛苦营建的“八道湾寓所”亦被称为“盗窟”。至于而后的南迁广东、上海,以及小说集《彷徨》诸文之沉郁风格的形成,抑或与此有所关联。
周作人亦终生不能忘怀“兄弟失和”之精神创伤,在《抱犊崮通信》等文中,屡用曲笔铺陈出许多“救恕神话”,在声言恕道的同时,却绑定了女性的“性原罪”。而他日后的附逆失节,也时常被人与“兄弟失和”风波联系起来。当然,分别通过对于一个歇斯底里的她者——羽太信子的建构,鲁迅想象了“宴之敖”者的主体自我,一个“自拟其头”的复仇者。周作人则实现了对于兄/父的无意识叛逆,成就了基督般的自我认同,一个自钉于十字架的赎罪者。晚年周作人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羽太信子“易作”频仍、自己不堪其扰的经历,或者依然是早年在《抱犊崮通信》等文中以“圣徒”自诩的无意识延续。羽太信子的“易作”频频,则不过是“圣徒”为成就自己,而不得不承担的“宿业”罢了。
无论周氏家族成员以及后续研究者为祛除鲁迅生命中的“莫须有”的污斑,而将羽太信子塑造为一个癔症患者,还是周作人为自我想象为“苦雨斋”中的“圣徒”,而将羽太信子的“易作”建构为需时时克服的业障,二者目的有异,却策略相同——那就是将羽太信子及其“歇斯底里”式言语,摈除在理性的、可理解的范畴之外,无视进而消除其歇斯底里式的发声中蕴含的意义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构成了某种不可测的风险。因为,无论是在传统的古典医学还是现代的精神分析中,一个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发生,往往与性、身体和欲望相关,任何与之关联的个体,都难以摆脱与“性”相关的污名化嫌疑,而人们往往又通过建构某种言语是否“歇斯底里”,来形成一种对于一件事物是真实抑或谎言的判断。在“二周失和”事件中,恰恰就是周作人“相信”了羽太信子的“疯言癔语”,从而导致了鲁迅被驱逐出八道湾的风波。而站在鲁迅一方的人们,则往往以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症”的存在,而以为其言语断不可信。至于“歇斯底里”与“谎言”之间是否存在着客观的因果逻辑,并不曾做任何探究,女性的多谎、善变,似乎天然建立在女性之歇斯底里的本质之上。
于是在各样的叙事中,羽太信子的癔症被不断引申强化,而癔症背后所隐含的“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的性别偏见,则是诸多叙事都试图达到的意识形态效果。然而,就像鲁迅曾经批判过的:“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依照鲁迅的逻辑推演,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女人歇斯底里要比男人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歇斯底里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实际上,歇斯底里作为一种本质化的“女性疾病”,大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关于羽太信子的癔症的话语建构,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以歇斯底里抑或癔症为名,羽太信子不曾被客观记录下只言片语。她在“二周失和”事件的诸多言语,一言以蔽之以“多秽语”而已,至于“易作”频仍时的“疯言疯语”,当然也被概之以“如谵如呓”或“如遇獬犬”,她终而被湮灭并塑造为“沉默无语”的“空白之页”。然而,无论在“二周失和”事件的当下,甚或在周氏家族的日常生活之中,羽太信子以其歇斯底里式的言语,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并实际上证明了自己不能被取消的历史在场性。谁能够忽视这个深刻地嵌入周氏兄弟的生命史和创作史的女性呢,即便她表征的是一种近乎“毁灭性”的魔力。实际上,羽太信子的癔症并非偶然,其应当是诸多创伤体验、权力欲望叠加的后果。或者说,其作为一种症候,既掩盖又表征了存在于羽太信子身上的各种创伤经验及主体欲望。
其一,癔症首先是对于女性性别压抑的“反映与抗拒”,父权社会既不断生产出女性的歇斯底里,又需不断承受其带来的质疑、挑衅与抗争。
其二,羽太信子出身贫寒,“一看就有些好胜”,而底层民众改变身份、地位的欲望,其表征/发作起来,往往极为“歇斯底里”。
其三,羽太信子不得不面对异国婚姻以及传统中国家族政治带来的困境,其进入周氏大家族而招致的窘况,想来并不令人愉快。语言隔阂或者还有国族歧视带来的压抑,使其不得不通过歇斯底里表达自己。鲁老太太曾回忆:
对于这桩婚事,亲戚本家中,有说的,也有不赞成的。因为这在绍兴是新鲜事,免不了人家有议论。
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曾提及绍兴当地人对于羽太信子的歧见:
其时小儿刚生还不到一周岁,我同了我的妻以及妻妹,抱了小儿到后街咸欢河沿去散步。那时妇女天足还很少,看见者不免少见多怪。在那里一家门口,有两个少女在那里私语,半大声的说道:“你看,尼姑婆来了。”
其四,歇斯底里是女性由被动的客体状态转换为主动的主体状态的话语策略,“外表恭顺”的羽太信子通过歇斯底里得以表达“内心忮忌”,从而一举由客居的从属的他者,转变为“君临”八道湾的主体。
歇斯底里不仅是压抑的结果,也是反抗的表征。在由性别、阶级、族群、知识、语言等区隔构成的权力网络中,他者作为权力的对象、知识的客体,被禁锢于象征秩序的牢笼之中。在象征秩序之内,他者只能被动地应承询唤。也许,唯有通过歇斯底里,才能超越象征秩序的语言结构,发出某种被认为是错乱“谎言”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注定不能被理解、记录并诠释,因其根本就在所谓理性的知识体系之外。女性主义者赋予歇斯底里症的意义,或者可以运用于理解羽太信子的癔症:女性身体是会演/说的女体,常常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来表演或诉说女性的故事。而这种故事只可意(癔)会,不能言(验)传。
余 论
晚年的羽太信子沉疴日久,而周作人亦因所谓附逆历史而风光不再,羽太信子即便强悍如斯,却也抵不过时间流转、世事迁变的巨大能量。她再也不能跟随周作人,一道购物、出游、访友、收薪水了。终日卧病在床的羽太信子,只能时时凝视着周作人,维系/坚持着自己作为爱情抑或家庭的“主人/主体”位置。在《周作人与儿孙》一文中,文洁若曾回忆道:
周作人的老妻羽太信子卧病后,为了便于照顾,为她在堂屋尽头安置了一张床,让她睡在上面。右手光线充足的一间,是周作人的书房,书桌就摆在窗下。……堂屋和书房之间没有隔断,羽太信子躺在床上,便可以看见工作中的老伴儿。
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晚年羽太信子癔症频发,几如狂易。实际上,周作人的记述中隐含着一种性别凝视的权力关系,这种凝视在临床治疗中具有仪式性的内涵,理性的男性医生处于观察/判断的主体位置,非理性的女性病人完全处于被凝视/诊断的客体位置,男性主体做出“诊断”并“记录”下来,作为女性患者的“病历”。这“是一界定性别差异的机制,也是父权用以支配、掌控女体的手段。在这身体剧场里,女体是成就医学主体知识的‘她者’”。
然而,文洁若的叙事却反转了周作人的记述。在她的文本中,卧床不起的羽太信子目不转睛,时刻凝视着写作状态中的周作人。这可以看成“抵抗隐性消声”的行为,这一刻,羽太信子全然不是周作人日记中的那个需不时“诊断/证实”的癔症她者,当然也不是诸多“二周失和”叙事中所呈示的那个歇斯底里她者。羽太信子有如一个幽灵,不仅每时每刻凝视着周作人,也凝视着后来的每一个周氏兄弟的研究者。正是以这种偏执到歇斯底里的凝视/发声方式,作为“空白之页”的羽太信子,将自己深刻地嵌入了男性主导、书写的历史中,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的“主体/她者”。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