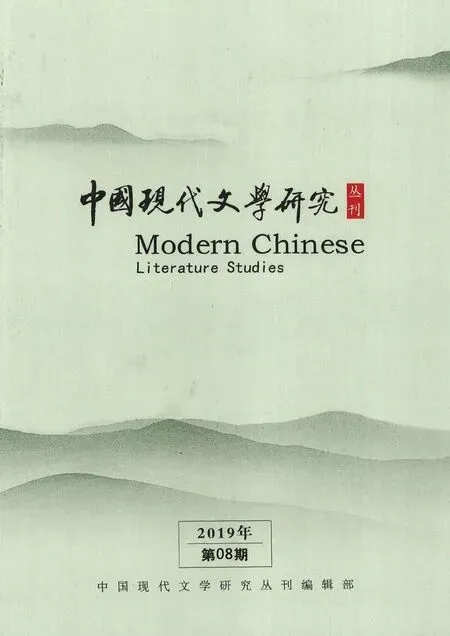在历史中溯源
——“70后”小说创作的隐秘路径
张晓琴
内容提要:近年来,“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日益丰厚,有关其研究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综观“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其内部虽然千差万别,但却呈现出一条隐秘的共同路径,即在历史中进行精神上的寻亲与溯源。寻父是“70后”作家小说中一个较为普遍的主题,也是创作的一个支点,其内在的精神性和象征性较为复杂。书写大的时代变迁与历史沉浮中的平凡个人心灵史是“70后”作家精神上的另一种寻亲。与此同时,他们探寻历史中的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思考时间中的存在意义,由此实现历史与时光深处的精神溯源。“70后”作家在这条路上以自己的方式挑战已有的文学规范,完成小说创作上的创新与突破。
提到任何一个以代际命名的作家群体时,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代群作家的共同特征是什么?“70后”作家也不例外,他们除了出生的年代相同之外,共性到底何在?作为一个代群,“70后”作家被命名至今已经二十余年①,其间创作日趋丰厚,对其代群的共性研究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在逐步发展。20世纪末,文坛对“70后”作家的认识并不全面,彼时“70后”作家中引人瞩目的大多是女作家。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此举在文坛产生的影响较大。1999年,卫慧小说《上海宝贝》出版,“70后”作家影响进一步扩大,但当时也产生了一种“70后”作家等同于身体写作的错觉。新世纪以来,更多的“70后”作家登上文坛,他们的创作姿态各异,日趋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有关“70后”作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饶有意味的是,虽然代群称谓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一开始论及“70后”作家时,对其代群困境的论证成为其共同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70后”作家被看作是夹在“50后”传统精英写作的高峰和“80后”网络时代时尚写作的高峰之间的低谷的一代②,是被遮蔽的一代,“如果说遮蔽,所有他们之前的好作家都构成对他们的遮蔽,脱颖而出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作品说话,用作品完成个性的超越”③。甚至是“落荒而走的一代”,“他们在夹缝中求生,这是他们的宿命,但未尝不是机遇”④。事实上,对“70后”作家来说,机遇一直就在那里,他们并未沉默,他们已经在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以此来冲破被遮蔽的状态。“70后”作家面对的文学环境比较复杂,他们很难在某种共同的明晰文学规范下写作,也没有清晰的群体性行动,作为个体的“70后”作家需要实现突破,单个作家的突破路径和力量皆不相同。然而,综观“70后”的小说创作,仍可以发现一条共同的隐秘路径,那就是在历史中寻亲溯源,这是“70后”作家共同的精神特质之一。在当前文学整体常态化的表层之下,他们提供了一种新鲜质素,正因为此,我们尤其需要关注这一隐秘路径上的文学行动。
一 寻父:“70后”写作的一个支点
“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先锋文学有着复杂的关联。一些“70后”作家在起步之初曾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但在后来的创作中只有少数坚持先锋的道路,更多的则改走他路。无论是否坚持先锋文学的道路,“70后”作家在书写父亲时大都与先锋作家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先锋作家的小说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审父,乃至弑父意识,而在“70后”作家这里,父亲的形象显得更为复杂。虽然也有个别作家表现出弑父意识,但父亲在更大程度上是被寻找的对象,父亲是一个人,更是一代人,“70后”作家写下的是父亲这一代人的集体命运,一代人的爱和怕,一代人在时代中的命运浮沉。同时,“70后”作家笔下的父亲更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象征性存在。
李浩的创作姿态在“70后”作家中堪称先锋,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在“70后”作家书写父亲的作品中尤为独特。他那先锋的叙事风格对一些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他心知肚明却依然我行我素。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就是写给理想读者的,也是写给他想象的读者的:“我想象的读者远高于我,无论在哪一方面。”⑤值得注意的是,李浩想象的读者中有莫言、余华等先锋作家,他在一些创作谈中不止一次提到先锋作家余华。《镜子里的父亲》塑造了一个既具象又有象征性的父亲,这个父亲形象与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或知识分子形象完全不一样,父亲的一生是通过无数个镜子完成的,这使得父亲的形象有多种可能,也具有了某种不确定性。李浩完成了一次对父亲的寻找与重构,同时,他将父亲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书写,这个父亲形象就包含了历史文化思考。李浩也是“70后”作家中唯一反复书写父亲形象的作家,他写过《父亲树》《父亲的奔逃》《会飞的父亲》《父亲的七十二变》《蹲在鸡舍里的父亲》《父亲,猫和老鼠》等作品,李浩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和生活中的父亲会有部分重合,当然,更多的属于作家的虚构。他说:“父亲,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象征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而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愿意对父亲言说,我愿意让父亲承载——当然,有这一意愿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人数众多。”⑥的确,有这一意愿的除了李浩,还有更多的“70后”作家。寻父在很大程度上是“70后”作家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路径。⑦正是这样的一代人才比其他人更需要寻找父亲,也就不难理解“70后”作家创作中的寻父主题非常普遍的原因了。
弋舟认为,世界的本初就是建立在寓言之上的,“我等都是寓言的主角”⑧。这样的创作观念让弋舟的许多作品拥有较强的寓言品格。《谁是拉飞驰》就是一篇有寓言特点的小说。少年的父亲于十年前失踪,他母亲要他去寻找父亲,他不愿意,甚至对此有些厌倦。他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和父亲相遇,但是到后来他已经无法想象。一开始,读者以为这仅仅是个寻父的小说,但后来才明白母亲让少年走是因为少年杀了一个叫拉飞驰的人。少年身上和网吧里的血迹是真实的,少年杀人的记忆也是真实的,但是少年不知道谁是拉飞驰,他不断追问究竟谁是拉飞驰,但没有人能告诉他,包括警察。大家担心警察来抓少年,可是警察并没有抓他,反而质问少年谁是拉飞驰,认为少年在捣乱。“少年支吾着挤出了人群,他努力憋着气,走出很远了才抑制不住地笑起来。但是笑着笑着,他就抖了起来。那种巨大的恐惧再一次淹没了他。他从那个警察的语言中,回味出了一种可怕的逻辑。当他意识到自己终将面临这种逻辑的堵截时,那种巨大的恐惧就扑面而来。少年因此一下子虚弱下去了,那股兴致勃勃的劲头荡然无存。”⑨小说最后,拉飞驰竟然活着出现了,他抢了少年的钱并杀死了少年。拉飞驰似乎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但也只是在少年心中,他们的彼此战斗与死亡都是在内心完成的。这篇小说具有先锋气质,在悖论中蕴含着哲理思考。在弋舟这里,父亲显然已经不是个体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象征,他象征着信仰、逻辑、理性、秩序,也是母亲心目中唯一可以拯救少年的人。然而,父亲失踪了,只留下一张与狮子亲密无间合影的照片。少年扔掉了父亲的照片,被拉飞驰杀死。这意味着,父亲根本不能拯救少年,少年的寻父也只是一个说辞而已。
有不少“70后”女作家同样在写父亲的缺席,总体来说显得更为敏感细腻,当然,她们的书写态度与方式并不一致。鲁敏的中篇小说《墙上的父亲》通过对一个父亲离开人世后其亲人生活的书写展开对一个缺席的父亲的寻找。小说中的父亲在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因车祸离开了人世,他出车祸是因为和一个不知名的女性私会。母女三人在父亲走后过得并不如意,母亲为了生计和一些男人发生过暧昧,但并未改嫁。大女儿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小女儿心理出现严重问题。两个女儿只能看着挂在墙上照片中“相当文艺”的父亲,这个“相当文艺”的父亲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小说侧重书写大女儿王蔷的心理,她在成年后常常会想起父亲死前的夜场电影,想象当时的情景与父亲的心理。每想到最后,都会想到父亲对现实的逃避,想到他是甘愿变成照片挂在墙上的。这样的绝望心理让两个女儿活在自卑中,她们的寻父显然是没有结局的。小说结尾处,梦中的王蔷“摘下尘灰满面的父亲,捧在手上——父亲可真轻啊,她托都托不起来的轻”⑩。父亲成了女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魏微的中篇小说《家道》开篇就写:“父亲出事以后,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⑪父亲原本是一位好老师,也是城里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了市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又当上了当地财政局长,父亲的升迁给整个家族带来了荣光,母亲和“我”也随之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然而生活突然逆转,父亲因为行贿受贿入狱,母亲和“我”跌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小说写得最为出彩的地方是家道败落后母亲和“我”的生活,经历了艰辛劳苦,体味了世态炎凉后,“我们”又回到了“富裕阶层”,却不再有欣喜,只记住了劳苦,有时更觉委顿。这篇小说最引人注意的是对人际关系与世事人心的书写,其中的父亲缺席与其所带来的影响则是“70后”作家共同的写作特征之一。乔叶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的父亲,乃至祖父都是缺席的。父亲一生对祖母言听计从,离开人世较早,在“我”的心中,他更像一个兄长,而不是父亲。祖父也在战争中过早离开人世,这其实也是一个缺席的父亲。在祖母的葬礼上,祖父年轻的照片和祖母年迈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仿佛也成了祖母的一个孩子⑫。这样的父亲不仅是缺席的,而且是永远不成熟的。
“70后”作家在书写父亲时仅仅集中在精神寻父的层面,父亲也可以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甚至是暴力与罪恶的来源,于是,弑父在“70后”作家笔下出现就不足为奇了。金仁顺的短篇小说《盘瑟俚》让人难忘。盘瑟俚是朝鲜族的一种说唱曲艺,小说以此为名讲述了一个弑父的故事。太姜的父亲是一个贵族,他把倾城倾国的太姜母亲从花阁买回家,但是因为嗜酒而家道败落,他强迫太姜母亲重操旧业。母亲不堪身心折磨发疯而死,他竟然让女儿卖身换酒。金仁顺在写这样残忍的故事时笔调异常沉静,更加显现出了命运之残酷。太姜结婚后,丈夫发现她非处子身,将她逐出家门。父亲却用太姜的嫁妆换回两大缸米酒,愤怒至极的太姜将父亲淹死在酒缸中。太姜被定罪并行刑时,年老的盘瑟俚艺人玉花闯法场,她说唱的故事感人肺腑,包括太姜在内的全场人都被玉花的盘瑟俚感动流泪,太姜重获自由,最终成了一名盘瑟俚艺人。这种弑父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寻父的起点。长篇小说《春香》⑬中,金仁顺又一次写下一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人物——春香,她有奇异的禀赋,但最后仍然沦落红尘。值得注意的是,太姜在《春香》中又一次出现了,她已经是一个失明且年迈的盘瑟俚艺人了,春香的故事真真假假,被她在《春香歌》中说唱。小说中的书生玉树原本看不起靠写异闻传记维生的书生,但被太姜的故事镇住了,开始写起了异闻传记。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和虚构掺杂着的,春香故事的真假连春香自己都难以分辨。金仁顺在《盘瑟俚》中写道:“我既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同时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人”⑭,这是金仁顺写作姿态的呈现,也是“70后”作家写作姿态的一种呈现。
任何一代作家要发现世界,发现自我,探寻历史,首先要从探寻自身的血脉开始。“70后”作家也不例外,他们以复杂多元的方式寻父,并赋予父亲以多重复杂内蕴。寻父是“70后”诸多作家追问历史的聚焦点所在,也是他们写作的支点所在,“70后”作家由此走向更深层次的寻亲和溯源。
二 寻亲,建构个人的心灵史
不难想象,“70后”作家面对的经典作品与规范性的力量有多强大,他们想让一部作品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并不容易,但在某些情况下,反常规、越界,对已有的规范进行挑战,恰恰可能成为他们赋予文本新鲜质素的一种途径。总体看来,“70后”作家在书写时代变迁中的个人心灵史方面形成了共性,他们更关注时代中的个体存在,而不追求时代与历史的宏大叙事。
任晓雯写过系列短篇小说《浮生》,每一篇记录一个平凡人一生的故事,这些人都浮在尘世,浮在时代的浪潮中,很难抵挡大时代的浪奔浪涌,也很容易失去建立自身主体性的能力,但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尽管这人生并不完满。宋没用是《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任晓雯觉得两千字意犹未尽,便写成了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宋没用是在上海生活了一生的苏北女人,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她生活的这大半个世纪中,上海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小说中均有涉及,但都是作为小说人物生活必不可缺的背景出现的。任晓雯将笔力放在宋没用这样一个极为平凡的女性身上,以一种朴素口语化却有古典意味的语言把宋没用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呈现出来,这一个个节点貌似平淡,却又构成了平凡个体生命的结实密度,揭示出个人的心灵史。
任晓雯自云上一部较为满意的长篇是《她们》,写20世纪的男男女女众生相,试图表述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她承认自己的这种写作是缘于某种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叙事传统,要求宏大、厚重,有史诗性的品质。然而,大的历史书写往往造成了对个人的遮蔽,个人的重要性在其中被弱化。任晓雯探寻其原因,发现或许并不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他们”与“我们”,因为人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人构成生活,众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构成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从《她们》到《好人宋没用》,任晓雯的写作发生了从“她们”到“她”的本质变化。宋没用仿佛是一个没用的人,但她经历着生存的巨大艰难与活着的诸多苦难,她对世界、人生从来都是隐忍的态度。她只是中国传统妇女中的一员,并不典型,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任晓雯在写宋没用时,显然带着一种精神上寻亲的想法,她说:“多年来,一位老太太在我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执拗、敏感、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太年轻,没能怀着体恤之心去爱她。我虚构了宋没用,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⑮宋没用希望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她把自己名字中的“没”改成了梅花的“梅”,但她过完六十三岁生日,儿子杨平生陪她去派出所办身份证时,才知道自己仍然是没用的“没”。她想改过来,却遭到了杨平生的坚决拒绝。杨平生根本不理解自己的母亲,他与妻子廖文娟闲聊时说不知道老娘一辈子活着到底有啥意义。文娟说:“她养大了三个儿子,这就是她的意义。”⑯儿媳反而成了最理解宋没用的人。文娟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作者的关怀,普通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好人宋没用》将思考的终极指向了信仰与死亡。小说中宋没用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普通的中国女性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对信仰和死亡思考的一个谱系。她们都有自己的信仰,或隐约不明,或信仰宗教,或以家国为信仰,但最终都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宋没用在她们面前反而显得比较迷离,她仰望她们,试图理解她们,但始终在她们的信仰之外。有一天,宋没用以烧锡箔纸元宝的方式来祭祀死者。她意识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因而落了单。死亡缓慢侵蚀她的身体,它耐心等待着,要对她做出最后一击。任晓雯在小说结尾处写道:“七十四岁的宋没用,回到了最初之地。”⑰这部小说有个附注,任晓雯在附注中强调,本书所有历史细节都已经过本人考证,若有疏忽和错误,欢迎读者指正。这表明任晓雯的一个态度,即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都是有据可考的,这确保了一种真实性,但它们并非小说的重心,而是宋没用这样的小人物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任晓雯实现了她的初衷,即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
去书写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成为一些“70后”作家的新路径。乔叶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呈现出祖母漫长坚韧的一生。“我”从小在精神上与祖母有着莫名的对峙,成长过程中的叛逆也都指向祖母,但最终与祖母和解。祖母年轻时就开始守寡,拉扯儿子成人后又带大孙子孙女,始终活在一种“怕”中,“我”终于懂事并理解祖母后,发现祖母一生的不易,这是一个平凡个体在历史浪潮中的不易。“我”发现父亲像长兄,母亲像长姐,因为祖母太像母亲了。在祖母的葬礼上,“我”发现祖父与祖母的照片放在一起不像夫妻,更像母子。甚至于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揭开那些形式的浅表,“我”与祖母竟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小说结尾,作者写道:“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⑱这是乔叶经过寻亲后得到的一种生活观,也是一种写作观。小说不单告诉我们活着之慢,还告诉我们这慢给生命带来的一切,这让“70后”女作家在寻亲的路上多了一份深沉与从容。
希尔斯·米勒说:“文学作品的形式有着潜在的多样性,这一假设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它可使读者做好心理准备来正视一部特定小说中的种种奇特古怪之处,正视其中不‘得体’的因素。”⑲某些作家试图开辟新的路径,并对此前的文学规范进行冒犯,他们的文本特征可能会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不“得体”,甚至是异常的、“出格”的因素。“70后”作家中,石一枫的部分作品在这种挑战性和语言风格上让人想起当年的王朔,但石一枫对普通个体精神的发掘与书写与他的同代作家更为相似,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中。杨麦童年时曾受到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姨妈的照顾,后来失去联系,但杨麦一直对大姨妈念念不忘,也走上了一条寻亲的道路。终于有一天,当杨麦找到她时,她却成了一名传销人员,后来又在信仰的路上迷途。大姨妈信教后,觉得自己以前信别的都信错了,“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就是为了绕到这条大道上来”。杨麦问:“所以您信了?”大姨妈并未确认,她眼睛亮晶晶地回望杨麦,“好像点了点头,又好像摇了摇头”。杨麦再次发问:“所以您决定信了?”“大姨妈没再说话,又看了看四周,仿佛漫天飞雪已经替她作了回答。”⑳可见大姨妈并未真正信教。杨麦的寻亲之路其实也是大姨妈的一条寻找信仰之路,大姨妈不停地寻找信仰,最终没有找到就离开了人世。小说的“附录”明确告诉读者,杨麦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心灵外史》的语言是戏谑的、反讽式的,但其中的思考是严肃沉重的。作品的名称显然有针对性,指向曾经名动一时的张承志的《心灵史》,张承志写的是哲合忍耶教派的坚定信仰史,而石一枫写下的是个体信仰迷失的心灵外史,是大姨妈和“我”两代人精神的迷茫与失落,以及追寻道路上的彻败。
梁鸿的《梁光正的光》也是一部以平凡个体为重心的长篇小说。梁光正是一位父亲,终其一生都在寻亲。他第一次寻亲是十五岁,主动承担了寻找自己母亲娘家人的重任。寻亲工程浩大,但父亲以此为乐,六十五岁以后更加热衷,先是寻他的舅舅和外婆们,然后寻远亲,寻恩亲,再后来,寻找年轻时和自己一起生活过的无名无分的女人。他的四个儿女也被迫跟着一起寻亲,梁光正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寻亲路也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荒诞。梁光正在他不圆满的寻亲路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梁光正的光》与之前梳理的寻父类作品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梁鸿也是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来实现精神上的寻父。梁鸿发现,父亲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太过庞杂,她无法完全明白。梁鸿说:“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㉑小说中的父亲与现实中的父亲并不一致,唯一未经虚构的是那件闪着光的白衬衫。梁光正是一个农民,要干很多农活,却永远穿着雪白的衬衫,这像是个奇迹。同时,他又有很不卫生的一面,典型的行为是随地吐痰。这两个细节似乎构成了一个矛盾体,却又是如此贴切地糅合在一个农民身上。他固执保守,甚至是偏执,但渴望融入这个时代,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为了改变家境,他一次次地规划宏伟蓝图,然而这些蓝图却是镜花水月。梁光正与此前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梁光正的光》是一部当代农民的个人心灵史。
“70后”作家在大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的寻亲,呈现出从宏大历史叙事到个体心灵史书写的转变,使得当前文学在个体心灵的呈现上更为丰富与厚重。
三 溯源,在历史与时光深处
“70后”作家登上文坛之初似乎更偏向于书写个体成长与生命经验,但他们在关注自我的成长与精神的同时用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建立起与时代心理意识的关联。
“70后”作家在精神溯源方面的相似之处可谓不少。徐则臣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就呈现出深厚的溯源意识。小说中的初平阳是一个“70后”,他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主题是“我们这一代”,他每天都在琢磨这拨同龄人,更盯着自己看,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问题,看一天到晚忙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焦虑的是什么。因为这个专栏,他被“意义”追着跑。初平阳和他的同龄人最大的想法是“到世界去”,初平阳想去的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象征,它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这宗教与信仰最终要成就于我们的,是一个欢欣的世界。在教堂里,在那些出入于教堂的乡村人身上,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词,它与‘生命’一样是我们文学的最重要的关键词,这个词是‘众生’。”㉒当然,徐则臣同时运用理性思考来面对这个世界,初平阳明知道耶路撒冷有战争,政治和宗教在那里纠缠不清,那里并不太平,但在他看来,耶路撒冷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那里的人对他来说没有区别,甚至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由此,徐则臣的写作呈现出,向人类的存在之初与精神出路溯源。如舍斯托夫所说,“耶路撒冷和雅典,宗教与理性哲学,一直都能和平共处,于是,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便可以看到为自己的那些珍贵的、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幻想而提供的保障”㉓。
《北上》也是颇值得讨论的一部长篇小说。徐则臣在这部作品中以大运河为主线,写出与运河有关的中西人物及家族的人生遭际与命运,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对话意识。小说以“过去—现在”的交叉式叙述呈现出这一切,结构精致而复杂。意大利人马费德因为迷恋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来到中国,成为八国联军队伍中的一名军人。1901年,其兄小波罗租船沿大运河北上,名为考察运河,实为寻找失去音讯的兄弟。与他同船北上的有清廷官员、船家、脚夫各色人等。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当时中国人民对“洋人”非常排斥,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小波罗在途中受伤,没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亡,船上的人四散而去。马费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福德,以西北骆驼客的身份与自己心爱的中国女孩过着贫苦的生活。日本人入侵时他已经年老,妻子被日军的军犬咬死,他拿出多年前的枪愤而反击后被日本人杀死。时间推移到新世纪,曾经在小波罗那条船上一起漂游过的人的后人又因大运河相识相交,马福德的后代意识到自己的血脉中流淌着异族的血液。一个叫《大河谭》的记录大运河的大型节目经过艰难曲折后也得以顺利启动。对运河上生活过的人来说,运河就是他们的生命所在,小说中邵秉义说:“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㉔《北上》中的人物命运均与大运河相关,也与这一个多世纪的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徐则臣对大运河的特殊情怀,小说的勃勃生机与深长韵味也正来源于此。
《北上》从小波罗的寻亲,到新世纪一群人的寻亲,无不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溯源意识。时间是作品的另一个溯源方向,所有人都与1901年北上的那只船一样溯向河流的源头。近则这一个多世纪的人事,远则龚定庵的诗,更远处则是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当然,最远处是大运河自身的历史。过去与现在,在小说中被并置于同一时间之河,所有的人与事在这里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那条大运河。
与《北上》较为相似的是,南京是葛亮小说《朱雀》的主人公。葛亮在《朱雀》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朱树桢教授。”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很符合现实主义的历史叙事,以时势变迁为宏阔幕布,以一个手工艺品朱雀为线索,写出一个家族三代人的人生与命运。细读之后,却发现葛亮的重心不在这个家族三代人本身,而在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厚重,在葛亮看来,“南京与历史间的相濡以沫,其实有些不由衷。就因为这不由衷,倒让这城市没了‘较真’的兴致,无可无不可,成就了豁朗的性情。所以,你细细地看,会发觉这城市的气质,并非一脉相承,内里是颇无规矩的”㉕。葛亮的写作,也是在南京的“常”与“变”的暗涌下悄然进行的,他敬畏于这城市背景中的丰盛与厚重。
朱雀是小说名,小说中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朱雀,几经辗转到了它最初的主人手中,主人剥去朱雀眼睛上的铜屑,它的一对血红色的眼睛见了天日,放射着璀璨的光。朱雀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中国古人认为朱雀是神鸟,代表火与南方。小说中的朱雀象征着南京,南京的朱雀桥极富盛名。南京拥有盛大的气象,这气象中有没落而绵延的东西。葛亮试图拨开历史的风尘,让南京这座城池散发出光芒。这自然也是为一座城市溯源。小说共十六章,最后一章内容很短,以几百字为小说收尾。时间是千禧年到来的前一天,是世纪之末,也是千年之末,许廷迈从国外回到南京,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却又似乎是命中注定。王德威认为,“南京的故事未完,也因此,《朱雀》不代表葛亮南京书写的结束,而是开始”㉖。
到了《北鸢》,葛亮由南及北,转而讲述北方城市几个大家庭的兴衰,其中仍然有关于南京的书写,却是从侧面进入的。《北鸢》无论对“70后”作家还是对葛亮来说,都是一部重要作品。《北鸢》的叙述视野宏阔,在民国的多元背景下,展开几个家族与个体命运的变化。小说一开始写卢文笙莫名出现在大街上被昭如收养,小说结尾处则是卢文笙与冯仁桢收养秀芬的遗孤。这意味着《北鸢》表面写几个大家族的故事,实际上想抛开家族记忆与血缘关系的局限。葛亮关注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中个人的动与静。在大时代中,个人的动静之辨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北鸢》所写,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静一动,都出自本性,在某种程度上,动静一源。不论是何种身份的人,在历史的大浪与时间的河流中渐渐认清自己,“兼济天下”难,“独善其身”同样不易。小说中昭如说给姐姐昭德的话意味深长,昭德问:“你说我这辈子,算不算是独乐?”昭如回答:“今日那大师的话,我倒觉得,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意思,姐姐太认真了。”㉗昭德最终精神失常,在关键时刻清醒过来,与土匪同归于尽。在乱世,“独乐”何其难哉,所谓“独乐”不过一个象征罢了。
葛亮在《北鸢》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这与《朱雀》扉页上的内容有一种明显的精神上的延续性,从母亲到祖父,从南方的朱雀到北方的纸鸢,葛亮将自己的溯源之路继续向历史纵深处迈进。葛亮多次提到祖父,认为“祖父的时代,人大都纯粹,对人对己皆有责任感。投射至家庭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沉的君子之道。所谓家国,心脉相连”㉘。他“本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㉙。本身就是精神上的寻亲,但在这个过程中葛亮发现了历史的藏匿,这就让他到达了另一层境地,那就是探寻历史大浪后的人的本质。在世事飘摇的动荡时代,普通个体有所坚持,有所不为,这种君子之道是牵动一个国家之鸢的“线”。小说中的卢文笙在课堂上画了一个大风筝,取名“命悬一线”,毛克俞则改为“一线生机”。这是一个暗喻,民国这个大风筝在时代的风雨中飘摇,最终陷于失败。冯仁桢参加反对内战的请愿活动,在南京被警察打伤,这时的南京已经站在了爱国青年的对立面。从创作手法上看,葛亮以《北鸢》向《红楼梦》致敬,小说名为《北鸢》,出自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葛亮从中汲取的是久藏的民间精神,其写法更重于家族日常生活细节的呈现,堪称一部民国野史。“这也是典型的《红楼梦》的写法。真实的历史悼亡被隐去,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㉚从《朱雀》到《北鸢》,葛亮由南至北,由南京及北中国,完成了一次历史深处的寻亲与溯源。
“70后”作家中,以地理为坐标展开精神溯源的还有朱文颖,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以南方为底色,以“我”为叙述视角,将目光投向大时代的小人生。莉莉姨妈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宏大的时代,然而,她始终活在时代之外,活在自己的“细小南方”。小说的背景是1950年代到新世纪初十年的中国,此间经历的大事件小说中均有涉及,但小说重心并不在呈示历史与时代的大的变迁,而是时代中个人的生命与心灵。“我”外公出生于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的一艘木船上,成年后突发奇想跟着评弹团从运河上漂游而去。莉莉姨妈一生中和同一个男人三次结婚又离婚。“我”也有着不安稳的内心。三代人虽然所经历的时代不同,但都是具有戏剧性的人生,内心深处都异常丰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拍案惊奇、黯然神伤,我们说,这个世界真是戏剧性呵。”“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为命运。”㉛朱文颖以独特的方式让历史与时代实现了内心化和精神化。“我”想寻找并感受前两代人在运河上的体验而未果,因为“我”一站在游船上就开始吐了。小说中充盈着南方气息,南方的植物、雨水、青石板路、雾中的大运河,运河上弹琵琶或三弦的游船等,一切都呈现出向南方文化深处溯源的探索。
站在时间的长河之岸溯源,通过某个人或某种器物从细微处出发探寻生命经验与精神体验,这是“70后”作家所擅长的。乔叶的长篇小说《藏珠记》㉜以一颗神奇的可让人永生的珠子为线索,写一个千年少女因爱发生奇迹,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生活的故事。但它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穿越小说并不相同。乔叶将时间推回至唐代,让人物从历史中走来,不时对历史中的事件与人发出感叹,在岁月的磨砺中,人世不过是一场虚妄。作者用一颗包容的心理解人性,以善意体谅人世间的一切。小说叙述中涉及《独异志》《广异记》《资治通鉴》等古典文本,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溯源。于晓威的《圆形精灵》篇幅虽短,却是一次时间和历史的深度探寻。小说以一枚小铜板三百五十年的经历为线,发掘出与其相关的历史与人物。三百余年诸多人物的命运浮沉都通过这个小小的圆形精灵得以呈现。最后,这枚铜板流落至于晓威朋友之手,成为他手中的占卜工具。当然,这个于晓威是作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出现的:“从古到今,我不知道有几亿或几十亿圆形的钱币,它们连带了怎样无以计数的故事和命运。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我以上叙述的将同它不谋而合。”㉝于晓威让生命在时间之河中不断地寻找,这枚铜板和它牵涉的人物都是时间之河中被抛的此在,它存在于历史性和时间性之中。因为此在“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相反,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㉞。
当前“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无疑呈现出多维度的追求与个性,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差异带来的,更是多元时代的一种文学呈现。总体看来,在历史中寻亲溯源是当前“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既是对自身存在与精神血脉的探寻,也是对历史时间中个体与家国命运的思考,更是一种存在之思。这是当前“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共性所在,他们由此实现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思考与追问。当我们一再地为“70后”作家“被遮蔽”和“低谷”的处境忧心忡忡时,我们看到了“70后”作家的可贵努力和探索,他们的创作中当然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但他们很少为自己的代群辩护,其实也无须辩护。在这样一个时代,“70后”作家开辟出属于自己这一代的文学路径,历史中的寻亲溯源就是其中一条,这条路径虽然比较隐秘,但必然会在当代文学繁盛杂乱的现实中坚韧地延伸下去。
注释:
① 1996年《小说界》推出“70年代以后”栏目,其后,《钟山》《花城》《大家》《山花》等刊物也相继刊发“70后”作家作品。
② ⑦ 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③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下)》,孔范今、施战军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
④ 陈晓明:《70代,向后看,向前看,看透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⑤ 李浩:《代后记:我和我想象的读者》,《镜子里的父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⑥ 李浩:《父亲,父亲们》,《艺术广角》2013年第4期。
⑧ 弋舟:《后记:我等都是寓言的主角》,《所有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⑨ 弋舟:《谁是拉飞驰》,《山花》2007年第6期。
⑩ 鲁敏:《墙上的父亲》,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⑪ 魏微:《家道》,《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2期。
⑫ ⑱ 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收获》2008第3期。
⑬ 金仁顺:《春香》,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⑭ 金仁顺:《盘瑟俚》,《作家》2000年第7期。
⑮ ⑯ ⑰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16、500、514页。
⑲ 希尔斯·米勒:《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⑳ 石一枫:《心灵外史》,《收获》2017年第3期。
㉑ 梁鸿:《后记:白如暗夜》,《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㉒ 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㉓ 列夫·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㉔ 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㉕ 葛亮:《后记:我们的城池》,《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7~378页。
㉖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㉗ 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㉘ 葛亮:《自序:一封信》,《小山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㉙ 葛亮:《自序:时间煮海》,《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Ⅲ页。
㉚ 陈思和:《序:此情可待成追忆》,《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Ⅱ页。
㉛ 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㉜ 乔叶:《藏珠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㉝ 于晓威:《圆形精灵》,《收获》2005年第1期。
㉞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3页。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