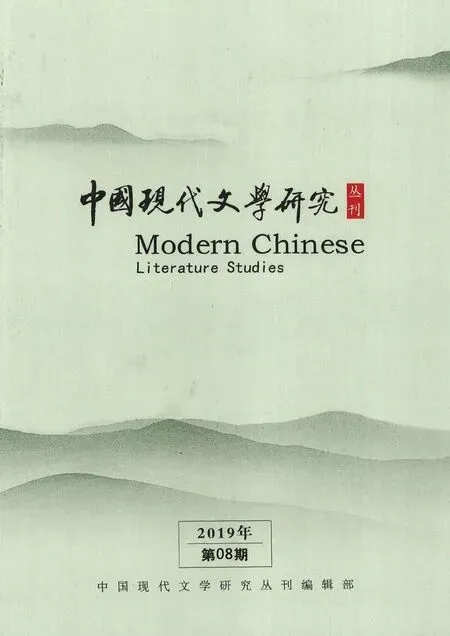旧学新义:后期陈三立诗学的现代观
潘建伟
内容提要:陈三立的诗学大致可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分成前后两期,从早期在创作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但并不稳定的诗思在后期逐渐得到凝定与升华。后期陈三立的诗论集中体现于他的《顾印伯诗集序》一文提出的“约旨敛气”“洗汰常语”“综贯故实”与“色采丰缛”四个方面,这些主张虽与早期新诗理论截然相对,却与1930年代现代派的诗学观点极相吻合。由于后期陈三立处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总结、归纳他的诗论,比较分析他与现代派诗人在论诗主张上的相通相应,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新旧诗学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认识他对于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意义。
一
陈三立的诗学大致可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他主要以创作为主,诗论并不太多;后期他在诗文中表达了大量的论诗主张,从早期在创作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但并不稳定的诗思在后期逐渐得到凝定与升华。①由于后期的陈三立处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总结、归纳他的诗论,比较分析其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学的相通相应,可以让我们从他的旧诗学中发现许多新的意义。②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章直接批判了陈三立的诗,认为其病根是“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抄胥奴婢”,又说“《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③。胡适的语气极为严厉,而陈氏没有任何回应。不回应,并不代表没有意见。恰恰相反,后期陈三立在给师友所作的大量的序中隐晦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与胡适等新文化人构成一种“潜对话”的关系。比如他的《朱鄂生真斋诗存序》提到:“邪说充塞,蹄迹纵横,莽莽非人世,其狂逞几欲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④显然这针对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反传统,不但颠覆了传统的纶纪道德,也摧毁了传统的典籍文字。他的《十六观斋遗集序》又提到:“瑰宝杂陈,其光气已自不可泯灭,敢取证蒿庵、倦知二叟,以谓中国效古之文字苟终不为持异说者所胜,固无忧其覆瓿也。”⑤所谓“持异说者”毫无疑问是指推动白话文之新文化人,他坚持“效古之文字”自有其价值,绝不会为白话文所掩。陈三立认为,文学一方面会因时代之变而变;另一方面在变化中仍存在某种不变的因素:“天地之变无穷,文章之变亦与之无穷。然而非变也,变而通其同异,而后能维百世之不变者欤?”⑥这与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主张同中有异:所同者为“文变染乎世情”,即时代境遇之于文学的影响;所异者是陈三立除了强调文章随时代变之外,还坚持变中有不变之理。这“不变”之理,就诗而论,极为鲜明地体现于《顾印伯诗集序》(1932)中的一句话:
务约旨敛气,洗汰常语,一归于新隽密栗,综贯故实,色采丰缛,中藏余味孤韵,别成其体。⑦
陈三立写这篇序言离其逝世只有五年多时间,可看成是其在诗论上的成熟思考,虽是揄扬顾印愚的诗,却无一不是自己的主张。“约旨敛气”即约束主旨、节制情感,“洗汰常语”即不作习见语,“综贯故实”即融汇典故,“色采丰缛”即讲究语言的色彩,如此才能使诗“归于新隽密栗”“中藏余味孤韵”。
“约旨敛气”“洗汰常语”“综贯故实”“色采丰缛”的提出,无一不与早期新诗主张截然相反,而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论相融相契。“约旨敛气”针对的是早期新诗的词肥义瘠、放纵感情,“洗汰常语”针对的是早期新诗的用语鄙俗,“综贯故实”针对的是早期新诗的反对用典,“色采丰缛”针对的是早期新诗的排斥想象。而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及批评家反思早期新诗创作时所提出的诗学观点,正与陈三立的这四条主张极相吻合。
二
首先是“约旨敛气”。“约旨”指约束主旨,勿使直露,跟诗的思想相关。“敛气”指收敛习气,可理解成节制感情,与诗的情感相关。“约旨”与“敛气”密切联系,不能分作两截看:能够“约旨”,必然“敛气”;做得到“敛气”,也必然会于“约旨”处下功夫。
陈三立早期的诗在这方面就已经有所体现了。比如《与纯常相见之明日,遂偕寻莫愁湖,至则楼观荡没巨浸中,仅存败屋数椽而已,怅然有作》一诗感慨戊戌变法失败,维新同志被杀,光绪皇帝被囚,国事益不可为,诗中“崎岖九死复相见,惊看各扪头颅在。旋出涕泪说家国,倔强世间欲何待”等都是诗人痛苦心情的体现。但是诗却并未继续直抒痛苦,而是通过叙写莫愁湖边烟沙漠漠、巨浸汗漫、颓墙朽树等来借景抒情。诗人最后写道:
千龄万劫须臾耳,吾心哀乐乃如此。起趁寒乌啼入城,回头世外一杯水。⑧
前两句意谓:倘以佛教关于世界之成、住、坏、空的时间观来看,“千龄万劫”都不过是须臾之事,何况自己所生之时代呢,“吾心”如此哀伤(引诗第二句中的“哀乐”乃偏义复词,偏重于“哀”),是很可笑的。后两句意谓:赶趁寒乌的啼声回到城里,再看莫愁湖,也正像世外的一杯水而已。这种情感的表现方式,可谓是以极为超脱的外表来掩盖极其沉痛的内心,如此,抚今追昔的主旨才表现得格外深刻。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陈三立对这一创作律令明显更加自觉。他的《书善化瞿文慎公手写诗卷后》称赞瞿鸿机虽然愤时伤乱,其诗却仍然“蕴藉而锋芒内敛”⑨;《苍虬阁诗序》称赞陈曾寿“中极沉郁而澹远温邃自掩其迹”⑩;《沧趣廔诗集序》说陈宝琛即便经历了“万变袭撼,寤寐交瘁”“纯忠苦志、幽忧隐痛”,“所为诗终始不失温柔敦厚之教,感物造端,蕴藉绵邈,风度绝世”。⑪表彰他人的诗风特色,即是表达自己的诗论主张,这一点殆无可疑。陈三立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也可与之相印证。比如《写怀次闲止疴韵》,诗云:
往时初脱九秋疴,诗兴曾联水部何。弹指黍离迎暮景,牵肠桃梗废酣歌。尧年历历苍天死,禹甸茫茫白骨多。拟拨烽烟追谢客,登山心迹托颐阿。⑫
此诗的主旨一样是表现忧患。首联诗人自注:“谓居湘时患痢病,与塾师何璞元相酬唱。”⑬因何璞元与何逊同姓,故以“水部何”代称之。颔联以“黍离”对“桃梗”,前者代指辛亥国变,后者代指人生漂泊。意谓从辛亥至如今,弹指一挥,而自己晚景堪伤。颈联以“苍天”对“白骨”,意谓国家战乱,百姓涂炭。尾联的“拟拨烽烟”承前一联语意而来,在战乱中苟存如此不易,而“拟拨”二字说得如此轻松,用他的《读仁先和章感题》一诗所云,真是“弥天忧患藏襟袖”⑭。“谢客”指谢灵运,“颐阿”典出谢氏《登永嘉绿嶂山》的“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意谓拨开烽烟,追随谢客,在沉寂的自然中保持一己的本真。⑮该诗表现的忧患如此之深重,抒情却如此有节制。
新诗运动开展初期无论在创作中,还是诗论上,都相当轻视“约旨敛气”。胡适强调作诗要“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⑯,直接将作诗等同于说话。俞平伯则说:“我们就自认做的是散文,不是诗,也没什么要紧,我们只把要说的话说了。”⑰又将作诗看成了写散文。1920年代中期开始,闻一多、徐志摩提倡“新格律体”,逐渐对新诗的抒情问题有所自觉。李健吾《新诗的演变》认为徐志摩“已经过了那热烈的内心的激荡的时期。他渐渐在凝定,在摆脱夸张的词藻,走进(正如某先生所谓)一种克腊西克的节制。这几乎是每一个天才者必经的路程,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⑱。这种具有“克腊西克的节制”,就类似陈三立说的“约旨敛气”。如果分而论之,“渐渐在凝定,在摆脱夸张的词藻”,相当于“约旨”;“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相当于“敛气”。不过徐志摩在1931年不幸因空难去世,闻一多也早在1928年后就基本转向学术研究,真正在诗学上对这一主张有所推进的则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深切影响的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及批评家。梁宗岱引《棕榈》(Palme)一诗赞赏瓦雷里在创作之前,“是用了极端的忍耐去守候,极敏捷的手腕去捕住那微妙而悠忽之顷刻”⑲。同样秉承瓦雷里诗教的卞之琳则说自己:“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⑳诗旨在淘洗、提炼中得到提升,诗情在克制、结晶中变得深蕴。现代派诗人中戴望舒多怀浪漫主义情愫,但他也最为推崇瓦雷里“对于思想和情性的流露都操作有度”㉑。瓦雷里的名作《海滨墓园》(Le Cimeti re marin)起笔就展开了一片扬波复起的大海,接着经过了一系列关于静与动、生与死、古与今的思考,充满着对话、辩驳、冥想,同时又以丰富秾丽的的感性质实来加以表现,最后以汹涌滔天的波浪作结,呼应开篇。该诗本旨是“从自我中心出发,以求达到‘无我’的境界,用了那么大思想感情,回环往复”㉒。这类作品才是钱锺书心中的“佳作”,即“能呼起(stimulate)读者之嗜欲情感而复能满足之者也,能摇荡读者之精神魂魄,而复能抚之使静,安之使定者也”㉓。从感情的兴发到情志的自持,正好成为一个循环,读者不需要再从诗外寻求慰藉与满足。
所以“约旨敛气”,从渊源上来说,其实是中国古代“诗者,持也”诗教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相应地,西方经过19世纪感情不加自控的浪漫主义诗学阶段,也逐步对收敛习气、节制感情有了高度的体认。㉔正是由于这一主张是中西方共有的特点,卞之琳才会很自然地说:“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㉕固然现代派诗歌表现方式更为复杂(比如戏剧化等手法的广泛运用),但在感情“不能自已”之时,“倾向于克制”,与陈三立主张的“约旨敛气”正是同一种思路。
三
陈三立《顾印伯诗集序》中的第二、三条主张是“洗汰常语”与“综贯故实”,这两者关系极为密切。所谓“洗汰常语”,用陈衍的话来说,就是“不肯作一习见语”“避俗避熟”。㉖后期的陈三立对此反复进行申说。比如他1934年为胡先骕诗集作的《忏庵诗稿题识》第一则就提到:“摆落浮俗,往往能骋才思于古人清深之境。”㉗淘洗涤汰浅近浮俗的语言与情感,往往能在古人清雅精深的境界中发挥自己的才思,这是对胡先骕诗的一种期望,也是自己论诗主张的表达。他的《再次和伯夔生日自寿专言诗事以祝之》又以“论诗诗”的形式来陈述这一主张:
昔贤句法高天下,遗响都非众所云。徒掇毛皮应笑我,能雕肝肾一逢君。陆离奇景辉孤梦,冥漠空霄写大云。五十诗人起高适,还如雾豹泽其文。㉘
首联谈古人诗能流传下来者均非庸碌之人所能为。颔联先自嘲己之学古是徒掇皮毛,接着反用韩愈“不用雕琢愁肝肾”(《赠崔立之评事》)之意,进一步表现了他“不肯作一习见语”的风格。颈联两句以“陆离奇景”“冥漠空霄”谈诗要开辟独特的境界。尾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旧唐书》所谓高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二是《古列女传·贤明传》中陶荅子妻所言“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陈三立用此二典意在说明需要经营诗什、泽润文章,而不能跅弛不羁,诗作虽戢戢多如束筍,却无一流传。
那么,如何能“洗汰常语”“摆落浮俗”?途径有很多,在陈三立看来,最重要的就是“综贯故实”。所谓“综贯故实”,简单说来,就是用典,包括融贯典籍中的故事与成辞。他一直强调“古事”与“今情”可以对接,“古事今情满孤抱,天涯岁暮共悲风”㉙。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写的《夜坐》一诗中又说:“古事今情吞咽尽,欲劙肝膈补霜痕。”㉚同光派另一位诗人陈衍虽然不反对用典,但他对用典有很多批评,甚至认为诗以不用典为上品,用典不管如何精要,都只能落入二、三层了。㉛陈三立对于用典却几乎都为肯定,在他看来,并非要不要用典的问题,而是如何贯通运用典故。他的《忏庵诗稿题识》第三则赞赏胡先骕戊午(1918)以后的诗“本学识以抒胸臆”,故能“高掌远蹠,磊砢不群”㉜。在《不匮室诗钞题辞》第二则中,他更是指出“依故实而抒胸臆寓识解”对于达到“蕴藉俶傥,别辟一境”的重要意义。㉝不依托“故实”,就往往会无法突破个人生活的限制,得因濡染于习气过深导致在诗中也对此种经验作了透明的表现,语言因此淡乎寡味,诗境因此流于常俗。陈三立不喜张之洞所主张的“清切”诗风,正是由于其诗“念念不忘在督部”“语语不离节镇”㉞。自我经验色彩太过浓厚,从而使张氏的诗染上了“纱帽气”。而“综贯故实”不但能避免个人经验的习气,更能够借此与古人精神遥相呼应。袁思亮《沧江诗集序》记载陈三立之言:
古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废者,必各有其精神气体,以与后人相接,后之人亦各因其才与性之所近,从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其同异而穷其变,然后可即于成。㉟
除了能洗汰常语、避免滑字率句之外,更重要的是,用典能寓过去于现在,将新的情绪与旧的古典对接,使得新旧文本具有共时性的对话。不妨以他的《更生翁既相过不遇,复馈盆菊池鱼,媵以三绝句,率和报谢》其三为例:
出网双鱼带笑看,不忘老秃佐加餐。深惭亦饱姜侯德,罢向灵岩斩钓竿。㊱
佛教典籍中,常将鱼之逃脱罗网比作人之逃离尘世,顿悟解脱。《杂阿含经》卷四十九记载佛陀的话:“彼当到彼岸,如鱼決其网;禅定具足住,心常致喜乐。”㊲诗的第一句写“出网双鱼带笑看”,“双鱼”出离罗网,观者心致喜乐,似觉它们带着笑容。第二句笔锋一转,“双鱼”的“出网”是要为“老秃”(诗人自己)当作加餐菜肴,于是接着说“深惭亦饱姜侯德”。这里的“姜侯德”是用杜甫《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中的“新欢便饱姜侯德”,借此感谢康有为之馈赠池鱼。既饱转而“深惭”:原本“带笑看”之双鱼已成自己腹中之物,心情从欢娱跌落到了惭愧的深渊。此处又隐含地用了杜甫《观打鱼歌》中的一句:“既饱欢娱亦萧瑟”,语意转折一脉相承。最后一句“罢向灵岩斩钓竿”,“灵岩”指灵岩寺,“斩钓竿”表示向佛忏悔,今后不再垂钓。在这二十八个字中,诗情跌宕起伏,诗思遥接千载,最后仁心及鱼,充满着悲悯众生之情。如果像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的那样,不用典故来写,可以写得很容易,比如:“出网双鱼美可观,不忘老秃佐加餐。深惭亦饱更生德,从此决心斩钓竿。”表意没有太多损失,声律也一仍其旧,诗却因此索然寡味了。
强调用典,注重学古,并非否定独创。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引述陈三立之诗论:
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㊳
胡适强调“惟作我自己的诗”㊴,陈三立主张“应存己”,可见,要求创造是新派旧派的一致要求。两者的区别在于,胡适的“作我自己的诗”是没有依傍的创造,陈三立的“存己”是有所依傍的创造,是“入唐宋之堂奥”而后“超乎唐宋之藩篱”的创造,是学习唐宋而自成一家。杨声昭《读散原诗漫记》对陈三立这一思想有很好的概括:“古今文人,未有无才者,而学为尤要。无书卷,不足以言学,有书卷而不极锻炼之工,仍不足以言学。知此,乃可与论散原之诗。”㊵才华是作为文人的前提,学养却并非文人均能兼备,才学俱足再加锻炼之工,才有可能做到梁启超所说的,“每翻陈语愈清新”㊶。
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及批评家在反思、批判胡适的新诗理论时,对于用典的积极意义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戴望舒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的情绪的时候。”㊷废名说:“作文叙事抒情有时有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这样的用典故最见作者思想的高下。”㊸由叶公超着力推动、卞之琳着手翻译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是现代派诗人倚重的理论文献,该文特别强调要发展一种“历史的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共时的存在”㊹。艾略特所谓的“历史的意识”,用叶公超的话来说,正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㊺。而这不即为陈三立主张的,“古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废者,必各有其精神气体,以与后人相接,后之人亦各因其才与性之所近,从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其同异而穷其变”吗?可见,1930年代中国诗坛介绍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其思想精神早就在陈三立那里有了相应体现。
四
如果说“约旨敛气”“洗汰常语”“综贯故实”是一般诗人的基本要求,那么“色采丰缛”才是优秀诗人的品质保证。“色”是指颜色,“采”是指辞采,“丰缛”即是丰富,故所谓“色采丰缛”,即强调诗要有丰富的色彩,或者要求诗须有丰富的意象。色彩原属视觉艺术的范畴,尤其是绘画艺术之能事。狄德罗说:“在一幅画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颜色的真实。”㊻弗莱也强调,画家“要发现怎样安排形式与色彩,才能给予视觉以刺激,从而最深刻地激发想像力”㊼。诗是语言的艺术,一般来说,在言志叙事上独擅胜场,在描景状物上却不如绘画。画会向往诗的气韵生动,诗则希望具备画的传移摹写。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初次发表时的结论部分曾有过一段关于诗画艺术相互借鉴的评述:
每一种艺术,总要用材料或介体(Medium)来表现。介体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止。于是最进步的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止,不受介体的束缚,能使介体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譬如画的介体是颜色和线条,可以表示具体的迹象,诗的介体是文字,可以传达意思情感。可是大画家偏偏不刻画迹象而用画来“写意”;大诗人偏不甘专事“写意”,而要使诗有具体的感觉,兼图画的作用。……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㊽
优秀的诗人总努力要超越语言的限制,摹写精微的物象,表现切实的感觉,产生一种“如画”(picturesque)而不限于画的视觉效果。故而黄侃说:“诗不能写景,必不能成家。”㊾贺拉斯则承认自己离真正的诗人还有距离,“因为他缺乏才能或巧智去把握住他所称的colores operum(作品的色彩)”㊿。
陈三立早年的诗就善于表现意象,如《雪中携叔澥由甫次申饮酒楼》颔联云:
瓦鳞新雪生春艳,旗角寒云捲雁高。
前一句中,“瓦鳞”,如鱼鳞铺迭之屋瓦也;“新雪”,新年初降之雪也;“春艳”,春色之明艳也。以瓦鳞上之新雪,预见出整个春天之明艳,比“一叶落知天下秋”更富意味。后一句中,并不一定都是眼见之实景。“旗角”即旌旗,因其多为四方形或三角形,故称;“寒云”承前一句的“新雪”,“捲雁高”说明风急,可以想象仍然春寒料峭。短短十四个字,既有“瓦鳞”“寒云”“雁”这样色彩黯淡的意象,又有“新雪”这样明朗的意象,还有“春”这样通过预测的明艳的意象,很好地描绘出了一幅春寒未消、春意渐萌的图景。再如常被引用的《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其二,诗云: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前三句连续用了六个意象:“露气”“微虫”“卧牛”“波势”“明月”及“茧素”。“露气如微虫”,言其触觉,冬月的露气已颇有凉意,仿佛是细小的虫子在皮肤上爬;“波势如卧牛”,言其视觉,波浪就像一排排卧着的水牛,可见风并不大;“明月如茧素”,似只言视觉,但接着一句“裹我江上舟”,实是视触二觉并用,而且化静为动:原本宁谧的月色,就像布满江天的蚕丝,包裹着行进的小舟,吉川幸次郎从中读出了“苦闷”与“抗拒”。
后期陈三立也极为重视意象的丰富,如《望落日有感》首二句:
落照衔须对黯然,红飞海色到尊前。
这两句诗中意象色彩的对比极为明显:“落照”是红色,是暖色调,引出后一句的“红飞”;“黯然”是心情,是冷色调,又与后一句的“海色”相接。再如《山中又雪感赋》:
雨尽依然雪满山,琼楼玉宇挂其间。老人坐啸迎龙战,白骨如麻自闭关。
相异于早春留不住、积不起的“新雪”,这里是雪压空山。“雪满山”“琼楼玉宇”虽是陈词,却是为了后二句作铺垫:由雪满山原而想起蛟龙鏖战、玉鳞纷飞,由龙战鳞飞而想起人间白骨如麻,自己面对秩序崩解有抗拒,有苦闷,而终究无奈(“自闭关”)。这首诗只有一种色调,却至少有五种意象:白色的积雪、白色的琼楼、白色的玉宇、白色的龙鳞,最后是白色的尸骨,将人生的惨淡、气氛的阴森,全部都烘托出来了。再如《中秋夕山居看月》的颈联:
一生阅世丹心破,万里传辉白骨残。
由雪景能联系白骨,从月色依然能牵连到白骨。这联诗与前一首有所不同的是,以“丹心”对“白骨”,以红色对白色,一热烈,一惨淡;一象征生命的活力,一代表死亡的寂静。这两首诗中,雪景、月光是实景,丹心是情感,战龙、白骨是想象。之所以在山间看雪、中秋赏月这样闲适的场景中不断地会联想起“白骨”这样的死亡意象,固然是由于在陈三立心中对人间灾难有一种极深的同情,但更重要的在于他自觉的诗观与精研的诗艺。
陈延杰的《现代诗学之趋势》对陈三立这种写诗方式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代表了“现代诗学”的趋势:
唯默察现代诗学,似已专趋写实派一途,散原先生即开写实派之一人,颇足吾辈师法。所谓写实派者,不用古典,不尚词藻堆砌,全在写实境,凡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以及风物情事,皆依样写出,然此偏于客观,是死法,与照相机无异。现在写实派,当重主观,凡写景物必参己意,譬如山本无树,而意外写一树,水本无舟而意外造一舟,此即诗人所谓造境也。
陈延杰所说陈三立的“写实”风格已不是写实主义式的写实,而是一种加入想象的写实,即“凡写景物必参己意”,用刘勰的话说,就是“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与此相对的,则是胡适坚持的“客观的”写实。胡适总是强调要在诗中表现“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这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写作取材。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以胡先骕的《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为例,批评此词中所写的内容都是生活中没有的东西:“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胡适不知道古人就有“飞霜”的用法,鲍照《侍宴覆舟山二首》其二更是直接说:“繁霜飞玉闼,爱景丽皇州。”“意象”一词原本就是由胡适引入中国的,可是他太偏爱“客观的”写实了,仅满足于写当下生活中亲见、亲闻、亲历之事物,排斥了想象,如陈延杰所说的,只是一种“与照相机无异”的写作方式。
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批评家的创作主张却完全不同于胡适的看法。戴望舒说:“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扼要地表达了外在的客观真实与内在的主观想象于诗的世界中的统一。他又说:“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也即诗情需要有某种物象(“一种东西”)相对应。这种物象可以是写实,也可以是想象,可以是竹头木屑、牛溲马勃,也可以是罗绮锦绣、贝玉金珠,总而言之,需要以巧妙的笔触描写出来,让诗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生物”),一座“七宝楼台”。很显然,这一主张背后有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的影子,尽管戴望舒自己的诗并不同于1920年代英国现代主义的“智性”风格。
现代派诗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诗有丰富的色彩或丰富的意象。虽然闻一多早在1926年发表的《诗的格律》已经对诗的色彩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并未着重去阐述它。真正在理论上对之进行深入探讨的仍是现代派诗人、批评家。施蛰存特别强调诗不是将景物、动作、心理“描成一幅图画”,而是“必须要从景物中表现出作者对于其所描写景物的情绪,或说感应”,并认为:“诗决不仅仅是一幅文字的图画,诗是比图画更有反射性的。”所谓“比图画更有反射性”,也就是说诗的意象比画的图像更能在人的情绪上得到感应。梁宗岱在1930年代力主“纯诗”(Poésie pure),写了如《象征主义》《释〈象征主义〉》《论诗》《谈诗》等一系列文章。他批判了客观的写实,也否定了感伤的情绪,强调诗要纯粹凭借“音乐和色彩”,“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李健吾则从意象“烘托”人生真理的角度认为:一行美丽的诗永久要在读者心头重生,它需要“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现代派诗人及批评家对意象表现的论述极为深广,他们的新诗在“意象抒情”上也比同时代的旧诗更为繁复、远奥,但其基本义旨仍可以归结为陈三立这个精简的短语:色采丰缛。
五
到了1930年代,陈三立已进入暮年,对诗坛的这些新气象,不会再有太多关注。倘若他读到现代派诗人及批评家的诗论与诗作,应该不会反对,或许还会有所欣赏的吧。这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从陈三立对卞之琳的老师徐志摩的诗之褒扬中也能窥见他的诗体观绝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顽固不化。钱锺书的《围城》中董斜川引陈三立的话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董斜川的原型是冒孝鲁,现在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虽然是小说家言,但这一说法肯定属实。赵杏根曾在苏州大学听过冒孝鲁的讲座,冒氏就透露道:“陈散原常看徐志摩的诗。”此外,方玮德也说陈三立对当时新诗并不多过目,却觉徐志摩诗“似颇有线装书气味”。所谓“有线装书气味”也就是指徐诗能够“约旨敛气”,可以“综贯故实”。
欣赏徐志摩的新诗,又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学如此接近,正能说明陈三立其实与新诗运动并非截然对立,他只是反对早期新诗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鄙俗、感情放纵、形式混乱、想象消泯,而并非反对新诗本身。他反对的其实不是新诗,而是“非诗”。朱湘的一段话通透地道出了新旧文学之间存在一贯性:
新文学与旧文学,在当初看来,虽然是势不两立;在现在看来,它们之间,却也未尝没有一贯的道理。新文学不过是我国文学的最后一个浪头罢了。只是因为它来得剧烈许多又加之我们是身临其境的人,于是,在我们看来,它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与旧文学内任何潮流是迥不相同的文学潮流了。
这段话正说明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对立只是看似“迥不相同”,“却也未尝没有一贯的道理”。1930年代新诗坛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新旧之争了,而是未来的新诗该如何继承中国诗歌传统的问题。新诗理论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还是回到了陈三立的观点。
由此可见,陈三立与新诗运动之间的对立其实是基于“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生的,不是就诗艺本身而言的。1930年代新诗坛反思、批判的并非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派诗人,恰正是当初高举“文学改良”旗帜的胡适一派。胡适与现代派诗人虽同属新诗阵营,在创作主张上却截然相反;而被认为是旧派的陈三立却与现代派诗人有着如此相近的见解。研究新文化运动以来陈三立的诗学,比较分析他与现代派诗人在论诗主张上的相通相应,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新旧诗学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认识他对于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意义。
注释:
① 李开军点校的《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中的诗文基本上由陈三立本人自选自定,且几乎均为光绪辛丑年(1901)以后的作品,故而将1901年至1917年作为陈三立诗学的前期,1917年至1937年作为后期,从时间段上来说也是合适的。潘益民、李开军有《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增补了陈三立1901年以前的不少诗文。如果算上补编的内容,那么则可将陈三立的诗学划分为早期(1901年之前)、中期(1901—1917)与后期(1917—1937)三个阶段。
② “现代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大致指上承新月派、早期象征派,下启九叶诗人,活跃于1930年代,追求“纯诗”的新诗流派。这一诗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转益多师,代表人物有戴望舒、施蛰存、梁宗岱、卞之琳、李健吾、废名等诗人及批评家。
④ ⑤ ⑥ ⑦ ⑨ ⑪ ⑫ ⑬ ⑭ ㉗ ㉜ ㉝ ㉟ ㊱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9、1024、950、1091、949、1113、635、635、688、1138、1138、1147、1269、634、711、691、714页。
⑩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点校,第1139页。按,标点略有调整。
⑮ 关于“颐阿竟何端”,黄节解释“颐”为语气助词,认为“阿”出自《老子》第二十章的“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但并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叶嘉莹则认为“阿”为否定语气词,与“唯”作为肯定语气词相对。分别见谢灵运著、黄节注《谢康乐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0页;叶嘉莹著《古诗词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4页。
⑯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沈寂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页。
⑰ 俞平伯:《诗底自由和普遍》,《俞平伯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
⑱ 李健吾著、李维永编《李健吾文集·文论卷》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 26页。
⑲ 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诗与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⑳ ㉕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江弱水、青乔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445页。
㉑ 戴望舒:《诗人梵乐希逝世》,《戴望舒全集·散文卷》,王文彬、金石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㉒ 卞之琳:《新译保尔·瓦雷里晚期诗四首引言》,《卞之琳译文集》中卷,江弱水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㉓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7页。
㉔ 最典型的就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提出的:“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见江弱水编《卞之琳译文集》中卷,第 283页。
㉖ 二语分别见陈衍编《近代诗钞》中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4页;陈衍著《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第1卷,张寅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㉘ 陈三立著、李开军点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660页。按,马卫中、董俊珏编此诗于1926年10月。见所著《陈三立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6页。
㉛ 陈衍说过:“大概作诗不用典,其上也;用典而变化用之,次也;明用一典,以求切题,风斯下矣。”见所著《石遗室诗话续编》,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486页。
㉞ 两句话分别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27页;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㊲ 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第3册,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4页。
㊳ 载《国史馆馆刊》1947年12月创刊号,第101页。
㊴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沈寂编,第22页。
㊵ 载《青鹤》1935年第5卷第14期,第2页。
㊶ 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㊸ 废名:《再谈用典故》,《废名集》第3卷,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6页。
㊹ T.S.艾略特著、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文集》中卷,江弱水、青乔编,第276页。
㊺ 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叶公超批评文集》,陈子善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㊻ 狄德罗:《画论》,《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徐继曾、宋国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㊼ 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㊽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国师季刊》1940年第6期,第7页。
㊾ 黄侃:《黄侃日记》中卷,黄延祖重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0页。
㊿ 引自维柯《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