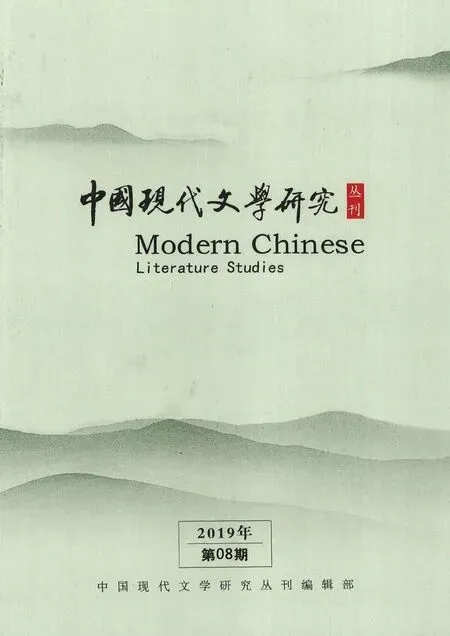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历史化”: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研讨会
郑 扬 吴舒倩
“历史化”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话题,不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也充满分歧与争议。2019年3月29 —31日,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协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台北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当代作家评论》《东吴学术》等全国知名学术期刊社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莅临会议。在会议中,不同代际的专家学者就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分为开幕式、主题发言、专题发言、闭幕式四个部分。30日上午,斯炎伟(杭州师范大学)主持会议开幕式,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致欢迎词,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主持主题发言环节,洪子诚(北京大学)和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作主题报告。
洪子诚通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动物凶猛》三部作品文本内部形态变化的分析,指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不仅涉及对文学生产方式的考察,也包含文学文本的“历史化”,即关注某一时期文学形式的取向、基调、模式、惯例等文学形态的问题。除了文学对象的“历史化”,洪子诚也十分强调主体的“历史化”,认为阐释主体要认识到自己的相对性,对自我的确定性保持某种怀疑,不应将对命题、现象、文本的“历史化”结果与对它们的价值认定混为一谈。程光炜则提出了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这一概念。他认为,七十年的历史长度已经开始使当代文学由批评状态“下沉”到了可以做历史研究的状态。他进而指出,“十七年”文学可以作为“下沉期”的研究对象,1980年代文学和一些已故作家可以作为“半下沉期”的研究对象,而那些创作上已取得瞩目成绩且现在仍新作不断的作家则可以作为“半半下沉期”的研究对象。其中对“半半下沉期”对象的研究,可以采取分期的方法。最后,通过对路遥招工问题的考证,他进一步阐释了所谓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会议专题发言共计三场,与会者分别从理论、现象及实践三个层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就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理论建构问题,吴秀明(浙江大学)提出了“知识历史化”和“思想历史化”两种向度。“知识历史化”强调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化”时,要体现出“知识”的眼光,并将其转化为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知识言说”;“思想历史化”是指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上,对曾经用来当作批判武器的“思想”进行再解读。而无论是“知识历史化”还是“思想历史化”,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主体意识的调整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调整知识结构、提高史学素养、加强理论辩证等“主体历史化”的可能方法。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则提示我们,“历史化”可能是一个虚妄的文学史方案。他重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现在对于历史的讲述也应是“历史化”的一部分,历史永远处在“历史化”的过程中,这将是一项永远未竟的方案。他继而指出,每个历史语境都有着不确定性和非封闭性,处在连续变化中,难以被真正“重返”或“语境化”。最后,他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这一行为背后潜藏着建构“共识”文学史叙述的冲动,而这种无法达成的“共识”,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历史化”的虚妄。姚晓雷(浙江大学)提出“历史化”具有双重目标。一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即用历史上一些经典的审美对象为参照,来衡量当代的文学审美现象;二是“让未来告诉历史”,即要在一种发展的视野下,研究新的审美经验给历史上的审美秩序带来的改变。他进一步指出两种目标存在内在悖论:一方面“让历史告诉未来”需要将过去的审美经验和文学秩序固定化,另一方面“让未来告诉历史”又不断显示出过去的经验和秩序的不可靠性。张均(中山大学)和郭洪雷(杭州师范大学)都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张均指出,对某些当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运用本事批评“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的方法。当然,新的本事批评必须要走出传统本事批评“有考无释”或“考多释少”的窠臼,完成自身的理论化。具体而言,新的本事批评是以本事为基础,通过考察从本事到故事的变异与重构,揭示其中内含的主体创作心理与文本生产机制。郭洪雷指出,当代作家的“阅读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创作的可能,因此可把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放置在“阅读—创作”这一框架中,通过辨读和比对作家的“阅读”和“创作”,考察作家的精神谱系和心理发育过程,并归纳总结出当代作家个人阅读经验向审美创造转换的规律、路径和模式。这不仅能够提高批评的“硬度”,也能有效突破以往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的“瓶颈”。罗长青(贵州师范大学)对“历史化”概念做了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他注意到不同学者对“历史化”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存在着差异,它既可以指向文学创作中的“历史”题材和“新历史主义”手法,也可以指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还可以指向学科教育的“史学化”与“学科化”等。不同的“历史化”概念背后有着不同的学术诉求,如何理解分歧,面对争议,处理好当代与历史、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思考。朱羽(上海大学)同样注意到了“历史化”内涵的多义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史观方面的分歧,对此他提出了两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概念:“难题”和“潜能”。一方面,作为“难题”的“历史化”能打通文学研究与其他研究;另一方面,作为“潜能”的“历史化”则能激活历史的辨证连续性,敞开历史的未来指向。
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历史化”问题已然渗透到了整个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之中,并成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意识。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认为,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已从“政治化”走向了“学科化”,但却又陷入了“行政化”和“学科意识形态”的泥淖。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他呼吁当代文学学科应重建“个体化”的研究维度。陈培浩(韩山师范学院)则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等重要的命名论争进行了“历史化”。他指出,对文学史学科的重新命名并非完全基于学科内部的学术冲动,其背后隐藏着研究者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文化逻辑,因而对学科命名的“历史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将特定时代匿名消失或被强行消失的部分重新挖掘出来。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王光东(上海市社科院)就进化的文学史观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方面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写作特别是新文学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本质化的文学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因此他指出,当代文学史写作要充分意识到当代文学形态存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更为开放的观念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武新军(河南大学)结合自己编撰年谱的经历,对当代作家年谱编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作家年谱的评传化倾向十分明显,而要想提高年谱编写质量,就必须对年谱的性质与功能,年谱的结构、条目和语言,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刘艳(《文学评论》)认为“史学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代文学史书写对作家作品艺术分析的维度,因此,她提出当代文学史书写应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有机结合,重建“史家”眼光下的作家作品艺术分析维度。朱文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则对“新移民文学”是否应该进入当代文学史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仅海外文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合法性仍然存疑,新移民作家也大多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因此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必过分着急将新移民文学纳入其中。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科幻文学这一文类应该进入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视野。她以当代中国赛博格科幻小说中的阶层叙事为例,探讨了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想象如何在21世纪为文学创作提供新的价值维度,如何将未来照进现实,并参与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与其争论“历史化”的概念内涵,不如将其作为一种学术意识,以此打开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维度。韩春燕(《当代作家评论》)就认为“历史化”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一种学术意识。她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为例,指出了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历史化”进程中的作用,并认为一切当代文学研究实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张曦(《学术月刊》)也认同这一观点。她认为当代文学的史料是“无限”的,但研究是“有限”的,因此只有通过“历史化”才能对当代文学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杨位俭(上海大学)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问题。他认为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世界史和世界文学紧密相关,因此当代文学研究应打开国际视野,发掘当代文学与世界历史的呼应关系,并以足够的世界意识,参与重构新的世界文学。刘复生(海南大学)则表达了对“历史化”意识的某种疑虑。他认为,虽然“历史化”似乎使当代文学获得了更为正统的学科地位,但它隐含着将文学对象从“当代”脱离出来而成为史学对象的意图,这种把对象“隔离”后所获得的“中立”或“静观”,恰恰因其脱离了历史的联系而可能存在“危险”。他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应该强调与现实对接的能力,尤其是在复杂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关系中理解现实的能力。
呼应着理论和现象层面的思考,不少研究者从实践方面入手,通过对具体事件、思潮、作家作品或某一现象的“历史化”,考察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及话语建构。黄平(华东师范大学)结合新的史料,指出“新时期文学”真正历史性的起源乃源自1978年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现代化”作为“新时期总任务”中的核心概念,由此被合理编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内涵之中。他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考释,不仅涉及对“新时期”这一提法的重新理解,也关乎对文学“现代化”起源的追溯。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不单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还考验着文学能否有效地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中我们的生命体验。王秀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则以华乐戏院到大众戏院的剧场改革为例,通过细致考察两者之间的转换情景,发掘了其时社会主义剧场新秩序重建的依据与逻辑。他认为,从华乐戏院到大众剧场的转变,其间的斗争、变化可谓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乃至社会改造的缩影,它既涉及根本的制度变革,也涉及一般艺人、职工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日常行为方式的变革。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通过新旧版《心灵史》的对读,并结合作家1990年代以来的各类文学创作,从激情的消退、宗教观念以及思想道路三个维度,分析了张承志创作思想的演变轨迹,并将这种思想演变放置在近三十年全球政治经济变局中加以认识,进一步阐释了其改写的价值意义。李润霞(南开大学)在文学史层面上综合考察了海子“被经典化”的过程。通过对“海子神话”的“历史化”,揭示了文学史写作与文化制度、文学批评话语模式、图书出版发行、读者接受等文学生产体制之间的关系。李建立(广州大学)对《今天》创刊号“致读者”的手稿和正式发表的版本进行了对读,指出前者侧重于自由与艺术,后者侧重于政治与文坛。他认为我们应以“历史化”的眼光看待这种版本辑校问题,即不去追溯到底哪个版本更接近历史“真实”,而去考察这种差异化的版本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袁洪权(西南科技大学)通过对“新月派”的“历史化”,指出文学史对“新月派”的叙述及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权力话语的规约。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新月派”的叙述主线应以徐志摩还是闻一多为主,这关乎对“新月派”的评价,而此种现象无疑显示着政治话语对文学流派命运浮沉的潜在影响。斯炎伟(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化”往往受到了某些观念或话语的钳制。他指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步性“历史化”充满着“定性”与“占位”的焦虑,后“历史化”则因其占据着某种“立场高地”而实际上造成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话语压制”,同时历史情境的“消隐状态”又给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化”制造了诸多盲点。钟怡雯(台湾元智大学)则从命名、土地认同和宗教文化等角度,对“新疆汉语文学”作了一种“历史化”的表述。她通过对王族、李娟、张承志、黄毅等作家个案的分析,发掘了“新疆汉语文学”的诸多质素,并由此认为“新疆汉语文学”可以从“西部文学”中剥离出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
吴秀明在闭幕式上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历史化”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代文学研究所应具备的必要心态。当代文学的研究要秉持一种贴着事实、贴着文献、贴着文本说话的心态,以更为开放、辩证的眼光去进行和拓展,警惕“短时段”视野可能带来的主体意识和思维理念的狭窄、紧箍与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