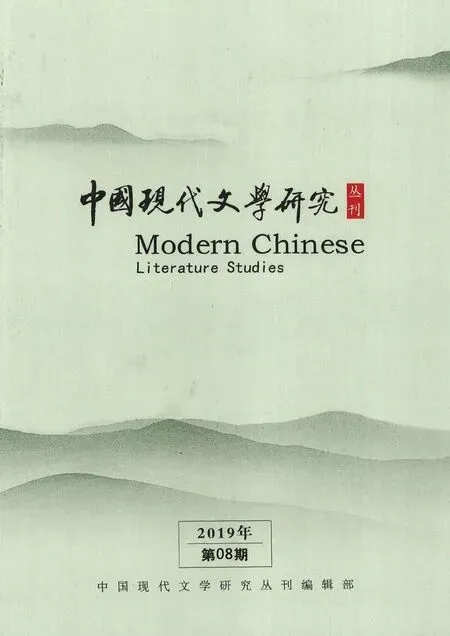文化史的观照与文学研究的另一学术进路※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
郑珊珊
近年来,社会巨大变革和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要求,引发了许多学者对文学研究路径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在这一趋势下,“大文学”渐成热点。杨义从《周易》的“物相杂,故曰文”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出发,提出“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文学观就是一种大文化史观,文学应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历史,面向所有的文化存在。早在1996年,杨义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图志》②,以图出史,以史统图,通过一百零九个文学主题和五百多幅图编撰“文学图志”,这可谓是其大文化史观的早期实践。时至今日,提倡大文化史观,兼容文学的多样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尤其是在近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③。近年来的许多优秀成果,基本都呈现了这般丰富多维的研究思路。新近出版的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④(以下简称《左》),更可谓是典型。
陈平原关于晚清画报的研究早已超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范畴,兼及社会史、新闻报刊史、城市史、艺术史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历史文化现象。1998年,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时曾提及研究目标:“描述晚清画报之‘前世今生’,呈现其‘风情万种’,探究此‘五彩缤纷’背后蕴藏着的历史文化内涵。”(第487页)可见其当时就已不局限于一般的文学研究,而是关注更广阔、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十年后,他将该书增补了一倍的篇幅,又调整了章节结构,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左》。这是陈平原二十一年来关于晚清画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⑤,从一百二十种晚清画报中精心拣选了三十种,通过探索其中文字与图像两种介质的功能互补与互动,重新体认晚清画报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建构。以“左图右史”为研究方法,是《左》最大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是对图像学的借鉴与超越,“一方面重视吸收西方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努力发掘中国文化自身的理论潜力”⑥,将晚清画报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都进行深入的观照,进而对近现代文学研究和大文化观的建构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发。
一 以图像学介入晚清画报研究
“左图右史”一词出自《新唐书·杨绾传》:杨绾“性沈靖,独处一室,左右图史,凝尘满席,澹如也”。⑦此词原用以形容藏书极多,嗜好读书。后来词义发生了衍化,也可表示“一种有插图的读物”⑧。而《左》书名中的“左图右史”可谓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指晚清画报的图文并茂;另一方面也指该书使用的方法,是将画报中的图像、文字与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图像学原是西方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19世纪,是关于图像的阐释和研究。近年来,西方图像学的影响和图像化时代的到来,使国内图像研究日趋兴盛。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宋代学者郑樵的一段论述: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⑨
这段话既指出古之学者早已有“左图右史”的阅读传统和研究传统,也道明了图与书相结合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左》中也分析了郑樵以及中国古代的图像观:“郑樵……特别强调图谱对于经世致用的意义”(第177页)和“‘图’‘书’携手的重要性,并对时人之轻视图谱表示大不以为然”(第176页)。遗憾的是,虽然郑樵如此推崇图像,而且中华图像传统源远流长,“中国曾有过书图并举的时代”,可是“国人‘以图叙事’的传统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即便让今人赞叹不已的绣像小说戏曲,其中的图像仍然是文字的附庸,而不曾独立承担书写历史或讲述故事的责任”。(第178~179页)
正是因为中国重文字而轻图像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所以晚清画报“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策略和“图配文”的形式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画报“有意让图像成为记录时事、传播新知的主角”(第179页),在画报这一媒介上,图像的重要性首次超过了文字。而这一变革凸显了图像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突出了画师的重要地位,进而影响了中国绘画领域的革新。可以说,这是技术革新、媒介革新与时代思潮推动的重大文化变革,在新闻史、美术史与文化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以图像学介入晚清画报研究,无疑十分必要。
受传统观念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对文字的重视远甚于图像,相当多的学者缺乏以图像透视历史、解读历史的自觉意识。近年来国内图像研究兴起后,还显露一些问题:“有的图像被过分还原为文字,研究者注意到它的叙述内容,却不注意图像的形式意味,于是图像还原成了文献,像近年各国学者对《点石斋画报》的一些精彩研究,可是这里的内容如西风东渐,如社会风俗,只是作为社会史的资料被使用。”⑩基于此,图像学理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就显得颇为重要。
著名的图像学学者欧文·潘诺夫斯基曾把图像研究的主题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第一性或自然的主题,正确鉴别图像上可识别的事物即艺术母题;二是第二性或程式主题,关注艺术母题与艺术母题的组合(构图),与主题或概念联系在一起,对图像、故事和寓意进行认定和正确分析;三是内在意义或内容,发现和解释图像的象征价值,对“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宗教或一种哲学学说的基本态度”加以确定。⑪潘诺夫斯基坚持“图像是整体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解释图像中的信息,必须熟悉文化密码”。⑫贡布里希认为,图像有三种功能:一是再现功能,再现了可见世界中的某物;二是象征功能,象征了某种理念;三是与艺术家个人有关的象征,通过这种象征,一个图像可以变成艺术家意识或无意识心理的表现。这三种功能可能同时表现在一幅具体图像中,而我们对图像的看法与我们的宇宙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⑬葛兆光曾指出:“图像不仅用模拟表达着取向,以位置传递着评价,以比例暗示着观念,更以变异凸显着想象。”⑭《左》虽然没有引用图像学家的观点,但其中的图像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无疑吸收了这些方法论。书中截取一幅幅画报图像,“讨论晚清画报中的宗教、科技、儿童、教育、女性、帝京、胜景、民俗等……借助这些五光十色的历史画面的钩稽与阐释,进入那段早已消逝的历史”(第31页)。
《左》力避宏大叙事的疏漏,通过对史料的精细处理,深入发掘晚清真实的社会场景和历史细节,进而论述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以《左》第七章“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为例,可以发现该书图像研究的严谨和深广。女学的发展是晚清最引人注目的新气象之一,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本就有以女性为观赏对象的一面,因此,女学成为晚清画报的一大内容,备受当时社会的关注,也引起当今学界的关注。画报为通俗读物,又有销售压力,其报道难免流于迎合大众。也正因为如此,画报基于大众趣味对妇女日常生活和女学的报道,展现了当时女学真正的发展情况与社会反响。《左》“试图以画报的图文来钩稽北京女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以女学的眼光,来审视画报的性别意识”(第297页)。虽然以北京女学和北京画报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作者又将风气更加开放的上海与之对比,借此映衬不同政治气氛、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下的社会心态,“把‘皇太后懿旨’拿来当提倡女学的令箭,这是上海的革命家所不能接受的”(第296页);还将画报图像与晚清小说对比,“画报的作者会注意女学生走路的姿态以及公众的目光,女子服饰的变化,女子上街可能碰到的骚扰,女学堂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是兴女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画报’中的‘女学’,更为真实可感”(第307页)。此外,还将不同画报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进行对比,将报道与历史记载进行对比。这样“广征博引”的对比,避免了碎片化和片面化,扩大了晚清画报女性图像的观照面,充分还原了晚清女学的历史现场。客观来说,画报所报道的晚清女学必然无法全面,必定受到报刊定位和编者个人趣味的影响。因此,《左》虽然以画报为主要研究基石,但是对画报图像的解读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结合大量历史资料进行辨析,由此开掘出其潜藏的历史信息。如作者敏锐地发现,晚清报刊上提倡女学的文字大多出自男性之手,但也有不少女性的声音;而画报的女学报道全部来自男性,“必须意识到其中很可能存在着某种焦虑、盲点乃至陷阱”(第313页)。还有,官方关于女学越来越细致具体的规定,画报关于女学或保守或进步的言论,反映了新的社会思潮对传统造成了有力冲击,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秩序从此失去控制——这才是朝廷以及卫道士们最为担忧的”(第335页)。此外,作者还从艺术学的角度分析画报中女性图像,有仕女画和新闻画,以及仕女画传统改造的新闻画。这隐约透露出画家和读者的传统男性的赏玩趣味,说明了晚清画报“既包含‘启蒙’的宏大目标,也不无鉴赏女性的潜在欲望”(第347页)。虽然研究的是“画报中的女学”,可作者直面的“除了具体的图像资料,还包括凝视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以及凝视本身的历史性”(第348页)。
《左》中的图像研究莫不如此,层层深入,通过图像与其他历史资料的互动,在跨学科语境中辨析图像,从而开掘出丰富的深层历史价值。以这种方式传递知识、表达立场,超越了一般个案研究的细碎,也避开了宏大叙事的空疏,体现了作者严谨的研究方法、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入论述的能力。同时,也为当前图像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图像呈现的是画家眼中的事物,不可避免带有画家主观性,未必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但这种主观也是一种历史真实,代表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图像被制作出来,是带有功能性和目的性的,往往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建构中发挥了作用;图像是静态的,表现的是某个时间断面的事物,却蕴含了丰富的动态的历史信息;要从生产和接受两个角度去考察图像,作为艺术品的图像和作为商品的图像在本质上有着许多差异,前者主要表现画家的艺术性,后者主要是迎合大众的兴趣。这些启发仅仅是笔者一些简单的思考,无论如何,图像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坚持全局的视野,运用强大的综合解读能力,去解读图像的里里外外。
二 以图文对峙建构晚清:超越图像学
《左》的研究不止于研究图像本身,作者更关注的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图像为主体所进行的叙事,与以文字为媒介所进行的叙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是否可以互相沟通与补充”(第487页)。这可谓是借鉴叙事学理论,对图像学的超越。其实早在三十年前,陈平原就曾进行“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⑮。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张力,也是基于这种沟通内外的模式。
“晚清画报的最大特点是图像优先;但这不等于说文字可有可无。没有文字的铺张扬厉、拾遗补阙,乃至画龙点睛,则‘新闻’过于单薄,‘纪事’难得诱人。某种意义上,晚清画报中图像与文字之间的‘悲欢离合’,既充满戏剧性,也是其独特魅力所在。”(第47页)图像中的文字一般简短平实,作为对图像的简单说明,以往常常被学者所忽略。而陈平原指出:“图像中的文字,如果并非只是简单的标识,而已经成为画面整体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就有必要追究画家如此构图意义何在,以及文字本身是否具有独立价值。”(第189页)确实,这些文字不见得有很大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难以进行深刻的文本分析,但它们也具有叙事功能,承载了一定的思想。《左》从文人画题跋追溯“图中文”的渊源和传统,再与民间版刻图像和文人画跋进行对比,通过纵向与横向的对比研究,说明了晚清画报图像中的文字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叙事和文化评论功能。画报的图像优先是一重大变革,是受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影响,为传播新知而产生的策略。但文字作为画报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与图像实为一个整体。“图文并茂”的出版方式创新了图文关系,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是对中国书画传统的继承和变革。
这是一种高度动态的研究,“因其充分重视历史语境,既避免陷入‘以图证史’或‘以史证图’的纠葛,避免传统二元论的僵化,更有一种新的历史建构的追求暗含其中”⑯。这种新的历史建构,就是以“左图右史”建构晚清的“西学东渐”。众所周知,晚清面临着中华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科技文化对中国造成了全面的冲击。画报本身就是“舶来品”,“正是因为石印术,图像制作速度大为提升,画报之与新闻结盟,方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第10页)。画报的生产和传播,内容和形式无不体现了西方科技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左》以画报中的图文对峙切入,试图勾勒晚清大变局的一个侧面。在《左》的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和第十章中,作者都有对图文对峙展开探讨。如果将这些内容系统串联起来,再结合其他章节的有关论述与案例,这种历史建构会更加清晰。
《左》在开篇即确定,“晚清画报‘图文并茂’的工作目标,是借助‘以新闻纪事为主干,以绘画技巧为卖点’来完成的”(第47页)。正因为画报的媒体属性,画报图像中的文字更多地属于新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新闻的叙事形态比文学要简单得多,新闻叙事是以再现事实为目的,而文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作家的艺术表达,而非事实。可是,图像中的文字表达空间有限,要以简短的文字清楚说明时事,又要引发读者的兴趣,必须兼具文采,因而画报的文字作者一般有较高文学修养,他们在创作时不免流露了自己的风格和思想。《左》注意到画报中的文字往往并非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介于记者的报道和文人的文章之间:比前者多一些铺陈,比后者又多一些事实。不只是叙事,往往还夹杂一点文化评论”(第48页)。更有甚者,如《时事画报》的一些文字作者,摆脱了“图中文”的框框,采用“图外文”的形式,自由发挥,单独撰文,与配合的图像各具独立叙事功能(第49页)。当然,这与报刊的定位有关,《时事画报》的宗旨不仅仅是报道时事、传播新学,它还有鼓吹革命的政治理想。这样一来,图像叙事就显得有所不足,需要辅以文字加强渲染,并加强思想深度。如《时事画报》在描绘俄国革命博物馆的图像上大发议论:“二十世纪,一革命之时代也。革命风潮,淹及全世界。”(第260页)这样高调而充满激情的议论文字,已经远远超出图像的叙事能力,不仅仅是图像的补充说明,而且具有比图像更突出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背后的报人对于办报的宗旨、定位和目的,都与同时的画报不太相同:他们办报不仅仅是为了启蒙,而是意图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因此他们不考虑商业因素,不考虑大众趣味,甚至对政治环境毫无忌惮,直接对抗朝廷。这类画报的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都极富个人风格,充满先锋意识和昂扬斗志,格调高出同时期的大多数画报。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对画报中的图文就能进行更多有趣的解读。如《开通画报》刊出的《花界热心》(第336页),文字在正面表扬妓女们为江北难民募捐演说的热心慈善,而图像却在一派踊跃募捐的感人场景一角,画了一个举着望远镜窥视妓女表演的猥琐男子。即便这图像源自真实场景,但也显示了文字作者和画师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文字作者集中笔墨正面突出真善美,排除了一切偏离主题的内容;而画师则意图在歌颂之外,穿插市俗的趣味。也有文人比画师更为保守传统的,如《花条马》,图像在山前草地上画了两大一小三只斑马,颇为写生;而文字作者在记录了游人的评价——北京万牲园中许多国外的珍禽异兽里数斑马格外出奇后,从中国古代相马角度认为,斑马只是徒有好看的皮毛,胆量甚小,“窃恐伯乐复生,斯马必无取焉”(第384页)。图像中的斑马颇为生动,画家的技法和构图有西洋画的特点;而文字作者的道德化解读就显得迂腐不堪,大煞风景。这些文化表达的差异反映出的是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下每个人具体而微的差异,晚清新旧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交错杂陈,投射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最终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庞杂纷乱。画报中的图文对峙,其实就是晚清社会激烈剧变在文化领域的投影。
彼得·伯格曾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图像学,但也必须超越图像学,“要使用更加系统的方式去实践图像学”,“借鉴心理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借鉴结构主义和符号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借鉴艺术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所有这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中找到对应的研究方法”。⑰这说明图像学本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在米歇尔那里,图像学所研究的形象更是涵盖了广大事物,“图画、雕像、视觉幻象、地图、树图、梦、幻象、景象、投射、诗歌、图案、记忆,甚至作为形象的思想”,并以“图像、视觉、感知、精神、词语”进行分类为形象家族建构谱系。⑱以此来看,《左》所研究的画报图像属于图画形象。米歇尔曾认为,关于图画形象的讨论“倾向于艺术史的褊狭主义,因而失去了与更广泛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史的联系”⑲。但《左》关于图文关系的研究却突破了米歇尔的观点,它超越了图像学,超越了一般的艺术史研究,对晚清画报的广泛钩稽、整理与研究,不但展现了晚清画报发展史,也展现了晚清新闻史、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这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学建构。
三 大文化史:文学研究的另一学术进路
以惯常的学科视角来看,文字并不居于主导地位的晚清画报似乎不属于文学研究的对象。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选题恰恰是文学研究者所忽略的一块宝地。早在195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就曾指出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在几个世纪里,而且直到现在,文学史还是过多地局限在研究人和作品(风趣的作家生平及文本评注)上,而把集体背景看作是一种装饰和点缀,留给政治编年史作为趣闻轶事的材料。”⑳因此,有必要让文学研究回到历史文化现场,对文学事实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1980年代以来开始重建和转型,学界日益重视“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学史观”,现代文学学科空间不断扩张,“将更多的文学形态和现象纳入到视野中”㉑。晚清报刊就在这种研究趋势下被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之一。
陈平原曾强调:“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学界关于报刊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已硕果累累,“相对而言,政论包括最受关注,文学杂志其次,至于通俗画报,只是偶尔被提及”(第1页)。画报的通俗性令其难登大雅之堂,其文献价值也远不如“正史”,故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冷落。然而陈平原却发现了画报的特殊价值:“谈论晚清画报不仅仅是以图证史;其中蕴含的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图像与文字的互动,西学东渐的步伐,东方情调的新变,以及平民趣味的呈现等,同样值得重视。”(第3页)显然,这样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传统文学、史学和新闻出版学的范畴,融合了社会学、艺术学,呈现出更广阔的大文化史视角。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角来看,画报的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是当时重要一环,其对于晚清民俗风情、社会场景和日常生活的精细呈现,为今天的研究者进入历史“现场”,体验当时的文化氛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由此看来,将晚清画报纳入文学考察范围深具意义。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与以文字为主的报刊同为文化产品,图像与文字同为传播和叙事的工具。国家和社会思想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画报与文学都发生了变革,也都与时代的思维逻辑产生互动影响。
画报与文学的许多勾连之处,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深入。如此一来,多视角、多学科的多元研究必然给予文学更多新发现,进而丰富了文学的学科面貌。如今,这一跨界研究的方法与模式已是不少文学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路径。以陈平原为例,除了研究画报的系列成果以外,他还介入了声音研究、饮食研究、城市史研究、教育史研究等,这些宽广而深刻的研究呈现出了文化史建构的大视野。这样广泛的涉猎源于陈平原对于文学的开放性认识:“‘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㉒认识到文学的开放性,才能在宽阔的学科地带“大展身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学科特性非常适合跨界研究:“文学具有融入其他文化形态中的间性特质。”“正像文学已日渐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和领域,成为其赖以融合或粘合的融合剂一样,中文学科正起着重新向各门学科的深处渗透或交融的突出作用。”㉓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跨界研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无边界的扩大化和泛化,而是从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去重新审视文学的意义,“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空间中勘定和阐释”㉔文学的价值。通过多学科的渗透交融,展现丰富多元的文学事实,重新激发文学的新鲜活力。近些年文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就展现了文学多维度的学术活力。
余 论
陈平原在后记中提到,《左》仍有一些遗憾,“如何处理晚清画报中日渐增加的漫画(谐画、喻画、滑稽画)”和“关于‘高调启蒙’与‘低调启蒙’的辨析,以及各自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两个问题未及深入展开。其实,个别话题的探讨程度对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无影响。就全书结构而言,十章内容基本上是独立成文,各自围绕主题集中论述,解决了不少深刻的学术问题,虽然章节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但晚清画报的整体历时性发展脉络就难以彰显了。当然,基于陈平原曾经大力反省“文学史”迷思,《左》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论述而不以发展史来谋篇布局,应该是有意为之。本书的排版与书名的“左图右史”呼应,展示了三百多幅晚清画报中的精美图像,图文并茂,可惜并无图像目录,使得读者难以“按图索骥”。
注释:
① 杨义:《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 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中国新文学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㉔ 李怡:《大文学视野下的近现代中国文学》,《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
④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文中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均只随文括注页码。
⑤ 如果视香港三联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为此次三联版《左》的前身而不计入在内的话,陈平原关于晚清画报研究的著作还有《点石斋画报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2014年版)、《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与夏晓红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006年版,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
⑥ 王风:《陈平原先生旁论——代主持人语》,《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
⑦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列传第六十七“杨绾”,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64页。
⑧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第965页。
⑨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略》,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25页。
⑩ ⑭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74、78页。
⑪ 参见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页。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⑫ ⑰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2、243页。
⑬ 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象征的哲学及其对艺术的影响》,《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编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⑮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第2页。
⑯ 卫纯:《从图像研究看文化史建构的一种可能——以三联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为例》,《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
⑱ ⑲ W.J.T.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2页。
⑳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㉑ 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㉒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重建文学史(代序)”第11页。
㉓ 王一川:《迈向间性特质的建构之旅——改革开放40年中文学科位移及其启示》,《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