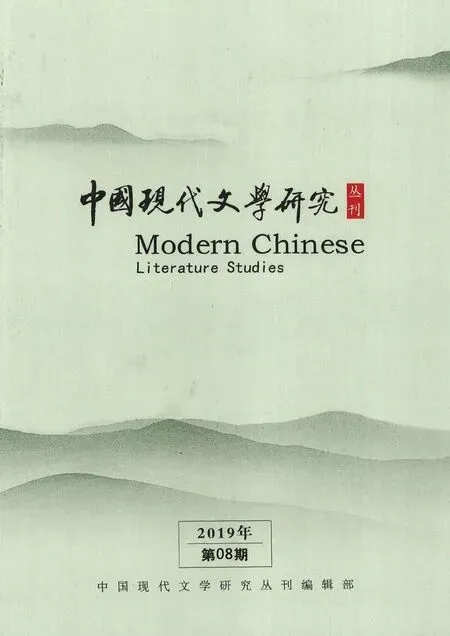汉语新诗的“百年滋味”
——以来自旧体诗词的责难为讨论背景
朱钦运
内容提要:自新诗在百年前诞生起,它与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不断被提及而从未有定论的话题。无论是用古典诗词的美学标准或历史成就来衡量、校准新诗,还是以旧诗创作的“道统未绝”来反向证成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甚或认为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诞生夺取了文学的主流地位而挤压了旧诗的生存空间——这些命题都如话语幽灵般缠绕在关于新诗的认知上,同时也构成了人们看待旧诗在当代的生存处境的一大迷思。本文拟从以上命题出发,针对已满百年的新诗历史,基于古典传统及当代诗词对新诗在普遍意义上的责难,再行讨论这种“新”与“旧”之间的纠葛。
一
盛行于晚清的“同光体”,常被视为汉语古典诗之夜空最后的耀眼星团。这个群体的诗人们承接宋诗余绪,在汉语诗歌庞大而辉煌的历史性累积面前,依然踏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种独特性,还体现于这群诗人所处的时代。如果说前期多少沾染着所谓“同治中兴”的气象,那么接踵而来的光绪年间的时代变革,足以让所有人猝不及防。那无疑是一个令人惶然的“末世”,古典诗造极于斯,宛如熟透了的果实,而又面临着来自新时代的“严霜”的考验——当然,构成这种考验的因素相当复杂,这与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一百年间景况,有着极强的同构性。
作为“同光体”殿军,诗人陈曾寿(1878—1949)送给友人的诗里说:“一夕相思减明月,百年滋味话深灯。”①前一句属于个体友谊呈现的惯常表达,后一句则未尝不能让我们读出那基于特殊时代氛围的绵长思绪——过去一百年的“滋味”在浓重的灯影下,经由言谈而遭徐徐披露,关乎知识人的忧患愁思及对时代变化所能做出的反应。据陈曾寿诗集的编年,这两句诗的创作时间当在1919年前后。他的写作或许与彼时勃兴的“白话诗”运动毫无关涉,却从一个颇有意味的角度,隐喻了未来一百年汉语诗歌的命运。这位古典诗的收梢型人物,根据其生活于世的时间表来看,已能亲身见证新诗(白话诗)的开端、确立与初步经典化。他可能对此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但新趋势一往无前,犹如时代盛衰消长的不可控制。
陈曾寿在新旧政权更迭之前的一个月离开了人世,彻底将自己的身影保留在了那个“旧的时代”。即便如此,在他生命最后三十年的岁月里,“诗国”并不再如以前那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于语言和意识两个方面,“诗”的里头似乎都混入了“杂质”。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仅凭一个简单的修辞术,就已将过去时代的痕迹一并扫除而“重开天地”:诗叫“新诗”,诗人叫“新诗人”,甚至在他身后建立起的政权,也名为“新中国”而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线。这种修辞术作用起来的方式,无疑是诗的方式。他不知道的是,又一个百年的到来,能给操持这种修辞术的人们以怎样的心态和方式,来谈论新一轮的自我焦虑与自我确认。
面对古典传统时不断产生的这种自我焦虑与自我确认,贯穿于包括新世纪诗歌在内的汉语新诗“有史以来”的始终。在学界就此问题的最新探讨中,冷霜《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贡献了一个新思路——这个思路在小范围的诗人与批评家群体内已是共识,但值得被普遍地重视。
冷霜认为,“传统”并非自明性概念而是一个现代性的“认识装置”,相比横贯在新、旧之间的思维迷障,“更值得考察的问题”应该是“诗人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征用、转化、改写古典诗歌中的文学、美学和技艺资源”,“新诗在寻求自身出路、方向时,如何借助对新诗与旧诗关系的诠释来展开自我想象”以及“不同时期浮现的对旧诗‘传统’的话语利用是在何种文化、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了其效力的”等一系列问题。②本文的任务则是,在认同此文贡献的这一类颇有价值的宏观讨论,以及它们提供的认知框架的前提之下,就新诗在其发生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自古典传统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两个领域(约定俗成地合称为“旧体诗词”)而来的普遍意义上的责难,进行一种较为宽泛和宏观的“辨认”和“辩护”。
二
诗是声音和文字的“寺庙”,有着无比古老的血统、尊贵的出身,支配着语言的祭司。同时,它却自立艰难,哪怕是古典诗自身,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责难。最大也最原始的对手是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希腊大哲柏拉图挑起了这个争端,他在教化和德性养成上,选择了戏剧而丢下了诗。孔子则将先民活泼泼的心声,经过删改和驯服,纳入/收编到自己学说的轨道上来。但诗歌之流依旧奔腾,大家在警惕它对“德性”的败坏的同时,享受着它,或试图改造它。直到16世纪,在欧罗巴大陆,锡德尼以及更为晚近的雪莱都声称要为之辩护。而在稍后的17世纪,东方人叶燮给出了他的“谅解方案”,由诗教、诗法而审美,重启了一条诗的“独立”之路。因为无时无刻面临的责难,以及因责难而起的合法性危机,部分人“为诗一辩”的努力,遂成人类文明史的一大景观。这也算得上是“意外收获”——虽然他们辩护的是具有整体意义和文化判断的“诗”,而不是“具体的诗”。
这种颇具张力的对峙情况,似乎在近世得到了缓和。旧日被视为“不入流”的小说的地位开始变得显赫,而一直处于危机中、同时又获得了危机间接给予的重要地位的“诗”,也水涨船高,哪怕有些稍稍的“门庭冷落”,却依然犹如一位容颜不老、风韵犹存的名姬。更加残酷的事实是:在汉语诗歌的历史上,在诗的内部,一种诗体对另一种诗体的责难从来没有停止过——雅俗之争,正淫之论,高卑之分,古近之别,几乎构成了半部以上的诗学观念史。随后,所有的内部争议又都可以搁置到一边,因为这个半老的“徐娘”居然“无玷受胎”,诞下了“新诗”这么一个“宁馨儿”③。更严重的是,自一百年前汉语新诗诞生以来,它几乎以一身之力,集结了人类的诗史上所能面临的所有批评和责难。古典诗内部曾经分散了的矛盾调转枪头,开始一致对外。这使得新诗的境遇变得格外诡异:这个新生儿,只是一个假的“宁馨儿”,实际上面临着真正的窘境——缔造艰难,守成不易,合法性危机无时或离。
朱自清在1935年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撰写的《导言》中,提到过催生新诗的两种影响源,即清末的“诗界革命”于观念上的推动,以及对西方诗歌的译介。④这体现着当时的“新诗人”在新诗自我经典化早期阶段的普遍看法:它固然是舶来之物,却并非与汉语诗的既有传统全无关联,某种程度上而言,它甚至是古典诗内部自我变革的产物。邵洵美则认为,直至徐志摩的作品出现以前,胡适等人的早期白话诗,无非是文化革新潮流——具体到语言上则是白话文运动——的孳息,只是从一个方面辅助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在文学上“不过是尽了提示的责任”而已,并认为新诗的渊源与西方诗的关系更深。⑤邵洵美的说法正本清源,明确了新诗在“诗体”上的真正出身,是一种从形式到文化基因皆与古典诗截然有别的舶来诗体。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同为“韵文”——自由体诗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韵文”都不能算,欧美诗在诗体上呈现出的面貌,和汉语古典诗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更何况,新诗在西方诗体的基础上又多增加了一道历经“翻译”而需借由现代汉语来呈现的曲折历程——现代汉语本身又混杂着多重的面貌。
笔者曾在一篇旧文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Poetry或Poem这样的词汇与中国既有传统中的“诗歌”并不完全等同,缘何到了汉语的疆域内,便被自然而然翻译成了“诗歌”而不是其他特殊或专门的名称?为何不该被看作两种不同的文类?将之翻译成“诗歌”的做法一旦成为事实,那么汉语古典传统中“诗歌”以及关于这类诗歌的既有观念和审美系统,便不可能不对之施加干扰。⑥这种干扰,几乎见诸新诗面临的所有来自旧体诗词领域的攻击。更严重的是,哪怕新诗早期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也难以避免这种干扰的侵蚀,甚至他们未必意识到,这种下意识的参照对新诗的“诗体自立”的负面作用。譬如,胡适给汪静之的诗集写序时,便不自觉地说“五六年前提倡作新诗时”,众人的作品“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并且在评价汪诗之“露”时,拿来参照和举例的也是李商隐和吴文英这两位极具风格性的古典诗人。⑦这种下意识的比附,难道不正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曝其短”,不自觉地置于古典传统的压力和阴影之下吗?那么,当代旧体诗词的作者将之用来作为攻击新诗“诗味不足”的口实,不“正也其宜”吗?
当然,胡适的贡献本不在新诗的“诗体”建设方面,提倡“白话诗”的深心也并不需要从诗学内部来看。荣光启在其专著《“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中,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解释。荣著认为,胡适之所以提倡“白话诗”,目的在于探索一种新的言说方式,选择从诗这种汉语最坚固的“壁垒”入手,“改变的不仅是诗歌的语言形态,而是突破了汉语的传统的‘文法’”,使得这种新的文法能够为“在历史转型期如何接通现代性的思想、文化,成为现代性的便利通道,知识分子言说方式的现代转型”提供契机。⑧
这或许可以视为前文所引的邵洵美说法的更具学理化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本人在新诗创作上的“浅陋”,或者他们那代人在为新诗辩护时,于言说和参照系选择方面的粗疏,并不是重点所在。换句话说,来自古典传统/旧体诗词的对新诗的批评,专注胡适们的立场、言论和作品作为切入点,就“击打效果”而言固然颇有奇效,但实在是有点没找准命门。
问题的实质是,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误会和模糊之处,但相对于汉语古典诗歌及富有活力的当代诗词创作而言,新诗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不是从旧体诗词中分离出来的支流或“叛逆”——虽然两者之间依旧充满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基于古典诗传统的审美和判断系统加之于新诗的创作和批评,看上去固然威猛无俦,事实上不免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另外,有了百年间在观念、修辞和风气方面的变化,也并不是所有的新诗作者都如早期的缔造者们那样,将旧体诗词作为一个天然的对立面来看待——虽然并不将它们视为有紧密关联的门类。
众多的批评和误会其实来自双方的不了解和缺乏沟通,来自诸多偏见。就旧体诗词与新诗之间的纠葛而言,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的言论虽然不具体针对此话题而发,但未必不能将之解读为对此的一份很好的辩护,在“要把诗做得不像诗”⑨这句话中,第一个“诗”自然是指闻一多等人为之努力建设与创作的“新诗”体,第二个“诗”则不妨将之视为古典诗或时人依然在创作的旧体诗词。哪怕兼事古典诗的研究,对于闻一多而言,新诗之为“新”,或许类同于邵洵美式的看法,即它从一开始就应被视为和古典诗/旧体诗词不一样的艺术体裁,作为一种新样式来被创作、辨认、鉴赏与批评。这就是所谓“洗心革面,重新做起”的内涵。极端点说,套用闻一多的说法,我们未尝不可将新诗当作一种特殊的戏剧或小说,为什么非得要将之纠葛在传统诗学的框架下呢?
当代不少旧体诗词作者对新诗所获得的文学“主流”地位愤愤不平——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借由新的权力和话语格局,借由特殊时势而来的。抛去其中明显的偏见不论,就观点论观点的话,这不正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让“(新)诗做得像(旧)诗”,下意识地觉得新诗不是古典诗的“逆子”就是它的“异端”吗?在闻一多式说法的语境下,倘若真要为旧体诗词争主流和地位的话,矛头应该指向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小说甚至电影艺术才对。把新诗当作一个天然的假想敌,和新诗早期的开创者策略性或实质上的把古典诗歌当成“靶子”或“造反对象”一样,未免有点浪费注意力。
新诗面临的第二个“窘境”是,时至今日,它都没有像古典诗那样,造就足够具有说服力的经典。或者干脆就说,新诗要么失之浅陋,要么就是“深奥”得令人费解。类似的质疑,从新诗诞生开始就从未断过——这种质疑本身,以及在质疑中的自立努力,已经成为新诗自身小传统的组成部分了。
哪怕是新诗作者,譬如于赓虞这样的早期诗人,也说过“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美的诗篇”⑩这样的话。写出《野草》这样被视为汉语现代性开端的散文诗的鲁迅(正是因为《野草》,他被众多诗人和学者,譬如张枣,视为比胡适更为合适的“新诗鼻祖”),在1936年5月与埃德加·斯诺的访谈中,还对当时已发展了二十年的新诗嗤之以鼻⑪,在此前的1934年,他给友人的信中也认为新诗“还是在交倒霉运”⑫。作为“九叶派”成员的诗人郑敏,新诗史上早已被经典化而尚在人世的“活化石”,对新诗的批评尤为致命。⑬堡垒似乎正在从内部被攻破,而不及等待外部的责难。
作为兼事新旧两种诗体创作、同时从事新诗史和当代诗研究的人,我非常理解新诗面临的这种窘迫的状况,明白为何就连新诗领域内的“自己人”,都会发出如此动摇根基的质疑——这其实是民族文化心理模式使然。新诗是一种充满活力而富有开创性的文体,与极具文化向心力的旧体诗词系统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新而未稳”的艺术形态,尚未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意识中。另外,甫满百年的汉语新诗,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文体,由于现代汉语和近世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从它内部尚未生长出一种高度成熟的意识形态来与整个大的文化系统进行对话,它的作者也难以从中获得依托于大的文化系统的安慰。它可谓是得之于“新”,失之于“新”——富有进取的青年人一旦进入暮年,创造力衰退后,精神上守成有余又足以在强大的古典传统中获得慰藉的前辈,如果不能抛弃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的话,自然容易倒向旧体诗词的“阵营”⑭。
新诗和旧体诗词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如此二元对立吗?一颗曾向最新鲜的文体敞开过的心灵,为何最终依然拜伏于我们的传统之力?一方面,或许是有人停止了对新诗内部更新鲜力量的观察,停止了跟进它的动态,由于缺乏了解、理解而导致误解,从而损伤了自己曾为之努力过的精神事业;另一方面,我们似乎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何谓新诗的“经典作品”这个问题——它的参照系如果还是古典诗词所缔造的审美标准和样态的话,是不是恰恰可以说明新诗的“新”是不彻底的呢?事实上,至少在1930—194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到新世纪,新诗中都不乏有足够说服力的“经典”作品出现,只不过,这种“经典”并不是既有理解范式下的“经典”,而是配合着新诗之“新”而成就的“经典”。我们为什么不拿拉斐尔前派的标准来衡量抽象主义绘画呢?这之间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觉得新诗尚未有足够说服力的作品出现,不过是因为,大家还是在拿古典传统的美学标准来衡量新诗的成就罢了,或干脆是对新诗领域缺乏真正内行的了解——总不能拿那些司空见惯、被大众接受得最广泛的新诗“代表作”视为它最高成就的代表吧?如果是那样,那么来自当代旧体诗词界的批评,其实和真正内行、专业的新诗现场毫无关系。
对于新诗的创作、阅读、鉴赏和批评,以及因此形成的理解模式,其实和我们对古典传统以及当代人创作的旧体诗词的理解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最好的新诗的创作与批评,已经是一种专业或近乎专业的行为,和旧体诗词在文化系统中的被接受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一种天然容易适应普通人理解力的艺术样式,而需要专业的训练才能进入。我们现有的教育系统,给予了古典诗最基础的理解训练,我们的民族文化生态对古典诗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但它并没给予新诗足够多的机会,让专业的理解训练得以进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态当中。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当代新诗的形象,往往是歪曲的,话题性的,很多时候是“新诗文化”中的糟粕而非精华。但是外部对新诗的批评往往揪住了它被歪曲的那部分,这也实在够冤枉。我们弄不懂“相对论”,却能对它抱有起码的敬畏,那么又为何总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视野和理解力,因着对旧体诗词的专业认识,便足够两相参照、对通过一般领域而非专业了解到的“新诗”发起“致命的”批评呢?
新诗的第三个“窘境”则来自当代文化的刺激,包括大众对新诗的漠视和“费解”的指责,也包括加速变化的当代社会对人类思想(及其产物)所提出的挑战。新诗诞生于汉语世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拐点,复因其欧风美雨的出身,而天然需要面对现代性这个当代世界最为核心的命题——但这也是新诗的历史性契机。借用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里头的说法:
在我们当今的文化体系中从事创作的诗人们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的文化体系包含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诗人精细的情感上起了作用,必然产生多样的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⑮
那么,这种对语言本身的复杂作用,是在具有相当稳固性的文言系统中更容易得到匹配,还是在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与活力的现代汉语中更具实现性呢?是抒情言志、连贯表意和具有说教色彩的古典传统更能具备对这个复杂纪元的理解力,还是一切并无定论、充溢着可能性的新诗更能包容如此异质多元的现代经验呢?阿多诺在《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中,借由评论里尔克的《拜物狂》,谈了现代诗(新诗的实质是现代诗)和古典时代诗歌作品的根本不同之处。他提及的过去的诗与现代诗固然都是西方传统中的产物,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毕竟不是一句空话:
里尔克的《拜物狂》在审美意义上看是贫弱的,它具有一种诡秘的味道,把宗教与艺术杂揉在一起,但同时它也显示了物化世界的真正压力。没有任何抒情诗的神力能够赞美这种物化世界,使之重新变得有意义。⑯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一个田园牧歌的时代了,而是真正的、比里尔克所处的时代更甚的“物化世界”,像旧体诗词那种类型的传统抒情诗,能够赋予它如它所自处的古典时代所拥有的那种稳固意义吗?遭遇到当代文化的刺激、大众传媒的娱乐图景,荷“诗”之戟而独彷徨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三
从新诗和旧体诗词面临的当代文化的挑战说开去,实质上我们能看到,两者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只不过,诗词文化在面对这种时代境况的时候,在态度方面,可能比新诗更为消极一些。这当然和它们所植根的话语形态有关。⑰传统诗词从精神实质和文化样态的各方面,都与古典时代的社会和人事结成了稳固关联,它们是文化精英的教养的自然延伸,是他们心智流露的产物,而古典时代(尤其是近古)也是以文化精英为核心构建的社会,两者之间体现着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那种“语言的统一性”,他说“语言的统一性是古典时期的一个信条”⑱,而旧体诗词所根植的古典语境(哪怕当代社会已不具备这种语境了),正依赖于建立在语言之上的统一性。它所依凭的文言话语,是一个对文化精英开放、对大众进行教化的循环系统,精英内部的审美共识即意味着大众在文化上接受的全面驯化。
但新诗不是这样。它既不是文化精英的文体,也不是大众的话语,类似于当代艺术,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知识”⑲,俨然如同一种专业话语。当然,这也是一些来自旧体诗词领域的当代作者用以批评新诗的一个口实,认为它占据了学院研究的主流系统,排挤了当代诗词应有的位置。事实上,这是由新诗自身的话语形态所决定的。新诗最好的那部分(同时也是最艰深的那部分)只有在学院中尚得容身之地。因为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旧体诗词虽然不再居庙堂之高,却依然能处江湖之远,有特定的生态圈子足以构成一个丰富的共同体,而最前沿而又无法为大众文化理解吸收的那部分新诗只能处学院之深,进行一个相对合理的循环。这种“各得其所”的方案,时时遇到“友军”的责难。事实上,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在学院中的不受待见,固然有新诗占位的因素,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君不见,小说研究乃至电影艺术,才是这个时代学院系统的真正主流。没有新诗的占位,当代诗词的创作就能从古典诗研究的既有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杀出一条血路?
植根于精英文化的旧体诗词,和植根于专业话语的新诗,在我们这个属于大众文化的时代,都不可能如大家所愿的那样跻身于真正的主流,更不可能复制诗歌在过去时代的荣光。所以(无论新旧)诗人们的失落是必然的。但意义自在其中。这也是诗人之所以愿意兢兢业业为之开垦的原因,因为这两种独特的艺术样态都有它相当的迷人之处。譬如旧体诗词,它自始至终便不是一种自外于生命本身的东西,而是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然延伸,无论言志抒情,还是教养使然,或者涵咏自娱,都无不合适。严肃的现代诗则像悬隔了生命涵咏的受造物,是人类在古典整全性、神性自世上消隐之后,自我确立起来的一个“新神”,一个需要人类创造力不断充盈进去、不断灌注意义的外壳。对于汉语新诗在下一个百年的“再出发”而言,它所面临的质疑和危机还将继续下去。不过,有了过去积累的经验——基于这一百年来在新诗文化、批评生态和个体创作等方面营造出的整体阐释情境,对于新诗这个“无玷受胎的宁馨儿”来说,于赓虞在《诗之艺术》中的另一句话,或许最契合用以期待它的美妙前景:“自来伟大的艺术由受胎至完成都经过长久时间抚育的苦心。”⑳
注释:
① 陈曾寿:《赠石禅》,《苍虬阁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② 冷霜:《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③ 闻一多就曾期许新诗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选集》第1、2卷,林平兰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④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导言”部分,第1~2页。
⑤ 邵洵美:《诗二十五首》,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自序”部分,第3页。
⑥ 茱萸:《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当代诗II》,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⑦ 汪静之:《蕙的风》,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胡序”部分,第5~8、3页。
⑧ 荣光启:《“现代汉诗”的发生: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⑨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当代评论》第4卷第1期。
⑩ 于赓虞:《诗之艺术》,《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据书内编者按,此文于1929年间分别以四部分、两部分的方式刊载于《河北民国日报副刊·鸮》和《华严》月刊,而以最精之《华严》刊本为底本校出整理。陈仲义就新诗百年写作的文章中亦曾引用到于赓虞这句话作为“新诗人”当时对新诗相对低的自我评价的例证,不过将“完美”误引作“完整”,参陈仲义《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人民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14版。事实上,就《诗之艺术》全文而言,及结合作者同集中收录的《诗之诤言》等文论来看,于赓虞对新诗在整体上还是采取积极维护态度的。
⑪ 斯诺对鲁迅访谈的相关内容,参阅安危(整理、翻译)《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问题单》《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等文献,刊《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⑫ 鲁迅:《致窦隐夫》,《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页。
⑬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当然,郑敏基于新诗的问题和“问题史”的批评,自有其合理性和复杂性。此处不赘。
⑭ 闻一多却是一个反例。他在1925年二十六七岁时,于留学纽约学习美术期间,在新诗革命发生六年后居然发生了“勒马回缰作旧诗”(《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的新情况。但十八年后,发表《文学的历史动向》时,显然比当初这种回趋于保守的情况更为激进,并未因年纪渐长而“倒戈”。
⑮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
⑯ 阿多诺:《文学笔记》第1卷,蒋芒据U. Heise编《文艺理论读本》1977年德文版译出。
⑰ 在白话文运动背景下诞生的汉语新诗,以及关于它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结合这个背景来理解。对白话文运动及其危机的讨论,可参阅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该作对此的探讨,也能够为认识新诗自诞生起所面临的处境和远景提供启示。
⑱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院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5页。
⑲ 臧棣:《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⑳ 于赓虞:《诗之艺术》,《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编校,第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