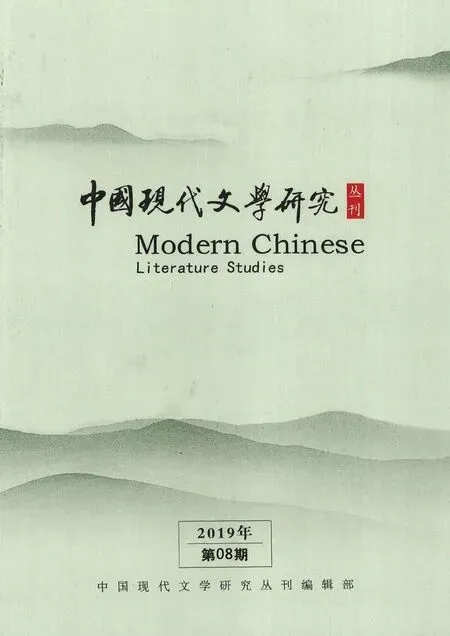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花月痕》之“痕”
——兼论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
张 蕾
内容提要:把《花月痕》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源头是有据可循的,鸳蝴派小说的哀情叙事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的开端。《花月痕》开篇第一句“情之所钟,端在我辈”抒情意味浓厚,在鸳蝴派作家中产生共鸣。内在于其中的主观、自我、悲剧等意涵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抒情表述,在李定夷等人的创作与观念中有具体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花月痕》描述的“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的情形在清末以后的文人身上更为普遍。就《九尾龟》《人间地狱》《春明外史》等小说而言,如果考虑到主人公的冶游身份和他们的情感取向,那么从《花月痕》引发出的失意文人的狭邪故事,可以成为追踪传统文人如何应对现代生活的一条线索。
创作于咸丰、同治年间,初刊于1888年的《花月痕》对现代小说影响显在。有学者论道:“在中国近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其他作品像《花月痕》那样,曾经在中国小说界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一度是小说家创作的楷模,开创了一种小说创作的风气。”①可作进一步探讨的是,作为传统小说的《花月痕》和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及牵涉到的更为深层的文学史意涵。《花月痕》叙述了困顿才子韦痴珠和青楼名妓刘秋痕的悲剧故事,寄托了作者魏秀仁(1818—1873)真实的情感经历。小说结构冲破了古代才子佳人的理想模式,表现出的士人对自身的伤痛叙事与抒情传统相关联,值得特别注意。有学者从“抒情传统与古今演变”的角度提出从冯梦龙“情教”到徐枕亚《玉梨魂》是中国文学写“情”的一条线索,②但在这条线索中却遗漏了《花月痕》的重要位置。《花月痕》作为典型的抒情叙事文本,直接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传统。
一 《花月痕》与“鸳鸯蝴蝶派”的缘起
《花月痕》初刊时名为“花月痕全传”,上海国光书局1920年10月亦出版《花月痕全传》,署“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十六卷,五十二回。正文前录有眠鹤主人的《花月痕前序》《后序》,栖霞居士、谢枚如等人的《题词》,符雪樵的《评语》及定香主人的《栖梧花史小传》。书中印有眉批、回评,基本遵循初刊本格式。另商务印书馆、上海会文书局、上海新文化书社等都出版过《花月痕》。
1915年墨泪词人编写的《花月痕传奇》③是对《花月痕》的戏曲改编。《花月痕》第五十一回叙道:“荷生低徊往事,追忆旧游,恍惚如烟,迷离似梦,编出十二出传奇,名为《花月痕》。”④第五十二回写梦中之戏,演的是《菊宴》一出。不但在结构、辞令、情意上对传统戏曲有所借鉴,还以戏入小说,这不仅是《花月痕》的重要特征,也关系到传统小说的渊源流脉。“在白话小说回目形成的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是最早产生回目的几部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元杂剧中大量的情节成为这些作品产生的故事原型,在输出情节的同时,题目正名作为一种遗传信息也会相应地沉积在章回小说的回目中。”⑤戏曲对回目制成型具有重要影响。清末民初,《玉梨魂》等小说表现出章回小说现代化的一种形态。“在回目的字数上”,“作者不再用七字或八字对,而是改用两字对”。“这种联对方式很可能与受明清传奇的影响相关,因为传奇作品每一出的标题大多数是两个字……民国章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也用二字作回目,更可见这种回目形式的影响。”⑥如果说元杂剧的题目助成了章回小说的回目,那么民初小说的标目则是有意借鉴了明清传奇。
《长生殿》《桃花扇》等明清传奇融言情于时事之中,充满寄托与哀怨。《花月痕》的故事构架明显受到这种影响,并及于《玉梨魂》等民初小说。明清传奇词曲之雅正也可在《花月痕》之后的小说中得到映现。文人写曲,俗曲雅化,这是明清传奇的一种趋向,作为传统小说后期代表的《花月痕》,文人写作的特征更为明显。和《水浒传》等小说起自民间说话不同,《花月痕》饱含了作者魏秀仁浓郁的文人情调,小说语言雅化,特别是常常可见的典丽四六文,充分显示出文人才情,并在民初小说中得到明显回应。
民初小说以诗化文言写长篇,在中国小说传统中不多见。文言小说中,清代乾嘉年间屠绅的《蟫史》和陈球的《燕山外史》颇值得关注,但这两部小说在晚清以后的影响远不及《花月痕》。李定夷回忆道:“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赡,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的牙慧。《燕山外史》句句排偶,通体骈词,有时失诸滞笨,不及《花月痕》的生动流畅。《玉梨魂》羼入许多诗词,也可说是学步《花月痕》。”李定夷和徐枕亚在《民权报》编辑部是“一案相对”的同事。李定夷见徐枕亚写《玉梨魂》:“案头置酒一壶,干果两色,边写边喝,信笔拈来”,“天天写上八九百字”,“谁料及后来一纸风行,为人侧目呢?”⑦同为民初小说家,李定夷对《玉梨魂》及《花月痕》的评论,可以见出民初文坛的状况。
无论《燕山外史》还是《花月痕》《玉梨魂》,都可归入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流脉中。现代学者概括道:“才子佳人小说之含义极为单纯……这种小说起源于明末及清顺治间,极盛于雍正、乾隆,终清之世不绝;到民国初元才一变而为鸳鸯蝴蝶派之香艳小说。”⑧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故事,而写才子佳人故事的也是文人才子。作者与小说故事的这种密切关系,正是“鸳鸯蝴蝶派”的显著特色。
在平襟亚叙述的1920年某日的聚会故事中,提到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不是没有出典的。《花月痕》第三十一回,荷生写信给痴珠,痴珠念荷生诗,感叹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不仅叹荷生和采秋,也叹自己和秋痕。“鸳鸯”“蝴蝶”就此意指带有无限哀怨的有情男女。《花月痕》谈及“鸳鸯”“蝴蝶”的不止这一处。第十六回有“化为蝴蝶,窃比鸳鸯”,第二十六回有“散为蝴蝶,五花八门;团作鸳鸯,春云秋月”……《花月痕》中的“鸳鸯”“蝴蝶”比比皆是。民初小说受到《花月痕》的深刻影响,把《花月痕》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源头有据可循。
吴小如说:“顾名思义,属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主要是指爱情小说。如果我们不上溯志怪、传奇和话本,只从清代章回小说算起,那么《花月痕》可以说是这一派作品的老祖宗至少也是属于这一范畴里面的一部代表作。到了清末民初,亦即‘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或概念形成之际,比较典型的作品应推徐枕亚的《玉梨魂》。”⑨作为继《花月痕》之后又一部大量穿插诗文的爱情小说,《玉梨魂》中也多有“鸳鸯”“蝴蝶”的文句。第十五章云“梦为蝴蝶身何在,魂傍鸳鸯死亦痴”⑩,第二十六章云“茫茫后果,鸳鸯空祝长生,负负前缘,蝴蝶遽醒短梦”……这些“鸳鸯”“蝴蝶”和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命运相映衬,可以明显见出《花月痕》影响的痕迹。
徐枕亚把自己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这和《花月痕》的自叙写法十分类似。因为是亲身经历,所以写来情感深切,直入人心。《玉梨魂》发表于1912年《民权报》的副刊上,甫一刊出,便风行一时。作为民初最早的产生很大影响的小说,《玉梨魂》被看成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是有理由的。郑逸梅在1940年代谈徐枕亚时说:“徐枕亚著《玉梨魂》《雪鸿泪史》,新文坛诸子以鸳鸯蝴蝶派诋之,实则作品随风尚而变迁,要亦不失为民初之代表物也。”⑪1924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把小说拍成电影上映,一位署名为“冰心”的观众写有影评《〈玉梨魂〉之评论观》,认为:“此片虽没有直接说出‘寡妇再嫁之可能’,但在寡妇不得再醮惨状的描写内,及旧礼教的吃人力量的暗示内,已把‘寡妇不得再醮’的恶制度攻击,间接的提倡与鼓吹‘寡妇再嫁’的可能了……此种主义,合于新伦理,合于新潮流,合于人道的。”⑫这位“冰心”虽不是“五四”女作家谢冰心,但能够把《玉梨魂》的故事诉诸一个“五四”式的话题,恰可以解释郑逸梅说的“作品随风尚而变迁”之意。
《〈玉梨魂〉之评论观》还说道:“故我以《玉梨魂》一片,宜于摄制,不过以成绩而论,关于情的表演,未能全部彻底表出罢了。”影片《玉梨魂》“未能全部彻底表出”情,这是观影感受,也是阅读小说的感受,电影未能“彻底表出”小说的情感。小说《玉梨魂》通篇抒情,主人公的浓情哀怨是被周作人等新文学家诟病的主因,但影评作者反而认为“情”需“彻底表出”。这种见解与1920年代以后文学的发展有关,“情”也融入了新文学的肌理之中。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哀情叙事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的开端。
二 “情之所钟,端在我辈”
《玉梨魂》是一部抒情小说,吴双热为《玉梨魂》写《序》道:“嗟嗟!情种都成眷属,问阿谁如愿以偿?”⑬作为徐枕亚的同乡、同事和好友,吴双热对《玉梨魂》的感叹也可用于他情动于衷的小说创作上。吴双热的代表作《孽冤镜》开首处道:“情天苍苍,情海茫茫,几多情种,以戴以航。嗟嗟!”⑭开篇写情,一往情深,无限伤怀,这于民初小说十分常见。和徐枕亚、吴双热鼎足而三的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李定夷,其代表作《霣玉怨》开篇同样在抒情:“夫人非木石,谁能无情。情也者,固吾人天赋之特点也……情因恨果,演成悲剧,则或赉恨终身,抑且甘以七尺肉躯,牺牲于是,多情如此,转不如太上忘情。”⑮这是叙述者也是作者的抒情,于篇首直接向读者表明心迹,小说的写作意图由此显现。
开篇抒情即便成为一种写作模式,也依然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真诚,只有经历切身之痛才会选择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如果追溯这种写法的来源,中国古典小说于开篇处发议论、明宗旨的比比皆是,但在开篇对“情”有专门言说的,还推《花月痕》。《花月痕》第一回开首道:“情之所钟,端在我辈……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花月痕》开篇描述了何谓“情种”,以对抗“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的世风。这是魏秀仁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小说主人公韦痴珠正是这样的“情种”。魏秀仁把自己的生世情感投注在韦痴珠身上,开篇第一句“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内涵之意深长,抒情之味浓厚。
关于“抒情”,海外汉学家已有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论述。陈世骧主要在中国古典诗学的脉络中发明抒情传统,普实克则把这一传统引向现代文学。普实克在他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中说道:“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形式和主题层面,在不同的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了清代文人文学的传统,即受过教育的中国统治阶层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抒情性和主观性”,“抒情性在旧文人的文学作品都占据了首要的位置”。普实克认为现代文学继承发扬抒情传统,表现为“对自我及其存在与意义的觉醒”,“对生活悲剧性的感受”。“对存在的这种悲剧性感受——在旧文学中发展很不充分,甚至完全没有——实际上是现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⑯主观、自我、悲剧于是成为抒情传统的现代显现。
王德威对“抒情”下了一个定义:“抒情的定义可以从一个文类开始,作为我们看待诗歌,尤其是西方定义下的,以发挥个人主体情性是尚的诗歌这种文类的特别指称,但是它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至于最重要也最具有争议性的,一种政治想象或政治对话的可能。”就此视点,王德威认为从晚清开始,对抒情的讨论已得到展开。王国维、鲁迅有学理的探讨,刘鹗、吴趼人则用作品来呈现。吴趼人在《恨海》开篇对“写情小说”有一个十分宽泛的解释,和王德威“推而广之”的“抒情”正相合。王德威认为:“在以《恨海》为坐标的抒情的叙述里面,我们也可以往回看晚清魏子安写作的《花月痕》(1858)。这部小说标榜‘才子落魄,佳人蒙尘’,反省或解构才子佳人的神话,也因此凸显晚清作家处理情和史的方法。我们不曾忘记《花月痕》的背景是太平天国时代。或者我们以《恨海》作为坐标点再往后看,像是在191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玉梨魂》。这个作品是以晚清覆亡、辛亥革命为背景,讲寡妇恋爱的问题,再一次写出情的多重条件性,还有情面对史时的无从实践。”⑰由《恨海》回溯至《花月痕》再及于民初小说《玉梨魂》,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就《花月痕》,王德威有过专门论述:“魏子安由是暗示出一种情的愿景,不再循回再生,而是空虚寂灭:情之为物,不在(像《牡丹亭》那样)自我完成,而在其余恨悠悠(residue)。这是‘衍生的美学’的极致了。”“residue”也即“痕”的意思,故事虽完但情意绵长,可在以后继续衍绎。在《玉梨魂》等民初小说中,“余恨悠悠”的“衍生的美学”有更为集中和突出的表现。王德威引用夏志清的观点,同样强调了“《花月痕》对中国现代的浪漫叙事传统,从徐枕亚(1889—1937)的畅销之作《玉梨魂》(1912)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浪漫风格,形成巨大影响”⑱。但是在王德威具体论述的抒情叙事传统中,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位置并不显著,而晚清《恨海》之类的小说,至多只是“写”情,并不“抒”情。王德威的论述从晚清直达“五四”,跳过了民初“哀情”的时代。
回到《花月痕》开篇“情之所钟,端在我辈”,此语典出《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伤逝”篇第四则道:“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⑲这则故事所言之“情”是父子之情,属于吴趼人和王德威所说的广义之情,但魏子安运用此语有其针对性。小说第一回,一名学究和叙述者“小子”有一番对话,“小子”确信:“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花月痕》所言“情之所钟,端在我辈”特指情之“最真者”,这比王德威论述的“情”的范围要窄,却是王德威不曾具体述及的民初鸳蝴派小说最动情之处。
三 从《花月痕考》到“李十种”
民初鸳蝴派作家李定夷特别维护言情小说的写作。针对时人批评言情小说,李定夷写了《论小说》一文进行反驳:“教育家某君之言曰:学校十年培养学子之功,不敌一部言情小说之害。其于言情小说,可谓深恶而痛绝矣。”“然而不然。情之为情,为人生之特性,自呱呱堕地时,即随之而来”,“使性灵不能泯灭,则用情亦无从禁。既用情矣,则当绳之以专,毋使之滥。言情小说中之主人翁,什九专而勿滥,一言之诺,至死不渝。此正足为青年用情者之好模范,乌得遽加贬辞于言情小说乎!”⑳和吴趼人的思路类似,李定夷也从与生俱来之情入手,却特别强调了言情积极的一面。民初言情小说叙述“至死不渝”的专情故事,正可以引导道德情感规范。
《论小说》刊于《中华编译社社刊》上,李定夷和中华编译社有较多往来,他的《小说学讲义》就是为中华编译社办的函授班所撰。李定夷受到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小说观念的影响,推崇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他对小说理论的阐述十分系统,《小说学讲义》可以代表民初小说家对小说的理论认识。《讲义》第二编第三章谈历史、政治等不同题材类型的小说,其中一类是言情。李定夷特别强调言情小说的“狭义”所指,他说:“言情小说之所谓情者,乃狭义的情,而非广义的情。所谓狭义的情者,只就男女之情言之。男女之情,即夫妇之情所由生也。”“二三年前,哀情小说尝执小说界之牛耳,欢娱之词难好,穷苦之音易工,实为断然之理。”㉑李定夷自己创作的小说以“哀情”居多,也有写欢情的,例如《伉俪福》。《伉俪福》叙述朱蓉华和江济和的美满婚姻。小说开篇之前有李定夷写的一篇小文《伉俪福旨趣》,表明写作宗旨:“自由之化行,夫妇之道苦。离婚之说行,夫妇之道尤苦。青年男女偶被欧风,动言恋爱,濮上之歌,终风之赋,视为当然。始乱之,终弃之,行固可诛……因有是书之作,虽属闺房细语,实为苦口婆心。窃愿世间伉俪,尽如吾书之主人翁,宜家宜室,亦唱亦随,则吾书不虚作矣。”㉒言情小说“欢娱之词难好”,但李定夷写来却声色俱佳。一是因为他希图以美好情感来匡正世风,其中包含鸳蝴派小说家维护旧道德的努力;二是因为小说独到的叙事手法。小说从女主人公的角度用第一人称“余”来叙事,绮丽故事遂笼罩上了委婉抒情的格调。第一人称叙事在清末民初的白话小说中不多见,但运用于文言小说却显得十分自然,这是传统散文渗透至小说的一种表现。
《伉俪福》销量很好,李定夷于是续写小说,重名《同命鸟》,让丈夫染病死去,妻子殉情而终,欢情遂转成哀情。小说第十章叙写朱蓉华饲养的一对鸳鸯死了,这是小说的一个关键隐喻。与“鸳鸯”有关的记述,在小说中还有重要一处。朱蓉华坐船回乡奔母丧,途中阅读小说《鸳湖潮》。《鸳湖潮》也是李定夷创作的一部哀情小说。1915年上海国华书局为《鸳湖潮》做广告说:“是书为定夷先生杰作,结构纯用倒提法,一洗平铺直叙之窠臼。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结局各异,尤特色者,书中主人疑死复生,将圆忽蚀,出神入鬼,一面缘悭……业已四版,销数之广,近日出版界无出其右,足以见社会欢迎之意矣。”㉓李定夷在《同命鸟》中借主人公谈论《鸳湖潮》,既是互文,也是“广告”。“鸳湖潮”与“同命鸟”相衬,虽然“穷苦之音易工”,但哀情之作更适宜表现时代情绪,也更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情感传统相承续。
1915年3月《小说新报》创刊,国华书局邀请李定夷担任《小说新报》主编。李定夷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道:“辞则传情,可醒酣梦。纵豆棚瓜架,小儿女闲话之资,实警世觉民,有心人寄情之作也……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使竹林游歇,尚识黄公之炉,山阳室空,犹听邻家之笛。”㉔这篇辞章小文有不小影响。李定夷回忆说,《发刊词》中有“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等语,“后来这些人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可能与此有关”㉕。在鸳蝴派作家的写作中,“鸳鸯”“蝴蝶”既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李定夷受《花月痕》影响颇深。他撰有《花月痕考》一文,文中道:“余生平极爱读《花月痕》,以其事则缠绵尽致,文则哀感顽艳,而人物之吐属名隽,尤为他书所不及,不愧名人手笔。今人之作,往往附丽古籍,其实去古远矣。此书向无作者姓名,仅署眠鹤主人一外号耳。”㉖李定夷引用谢章铤《课馀续录》原文,来说明《花月痕》成书的缘起。《课馀续录》记述了魏子安在山西太守家任西席,课暇时作《花月痕》,太守见之喜,督促《花月痕》成书,明示出《花月痕》的作者就是魏子安。李定夷的《花月痕考》是为“此书向无作者姓名”作一考证。
《花月痕》的考证研究如从1918年蒋瑞藻、孟洁连载于《东方杂志》上的《小说考证卷八》之《花月痕弟一百七十七》算起,那么李定夷对《花月痕》的研究关注也是较早的。《花月痕弟一百七十七》,录有《雷颠随笔》和《小奢摩馆脞录》两则材料。㉗前者主要记述《花月痕》成书的经过,后者主要记述魏子安生平和《花月痕》著书原因。蒋瑞藻《小说考证》中的材料成为现代人谈论《花月痕》的基础,但其中所述颇有不确,为研究者所校订。容肇祖在《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中就指出《雷颠随笔》所记魏秀仁的籍贯是错误的,《小奢摩馆脞录》中说魏秀仁“折节学道,治程朱学最邃”也没有根据。㉘容肇祖参照了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五中的《魏子安墓志铭》。铭文道:“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其言绝沉痛,阅者讶之。”㉙先于容肇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经引用了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课馀续录》的史料。对这些史料的发掘和校订,使《花月痕》成为一部人多知之的作品。民初作家李定夷对《花月痕》的关注也可归入其中。
李定夷生于1892年,《花月痕》的阅读可谓与民初作家的成长相伴。李定夷把自己的代表作归为“李十种”。“这十种是《霣玉怨》、《鸳湖潮》、《红粉劫》、《茜窗泪影》、《千金骨》、《昙花影》、《辽西梦》、《伉俪福》、《同命鸟》、《双缢记》。”㉚这些小说取鉴《花月痕》,仿照的痕迹与影响的焦虑都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昙花影》,初名《潘郎怨》,《小说丛报》1914年第1期开始连载,上海国华书局1915年12月初版,文字方面较连载版有改动,增添了刘裴村的回评,并改题名为《昙花影》,共二十回。小说用白话写成,叙述吴英仲和江筠秋从相识、相恋、成婚到死别的故事。第一回末刘裴村的回评道:“故太上忘情,次则莫如下焉者之不及情。情多恨多,无情无恨,如是或可不至蹈入恨海,便见是书功效。”㉛回评表明了小说题旨。“太上忘情”之句出自《世说新语》。小说第十九回开首云:“情之所钟,端在我辈。从来才子佳人,莫不富于爱情,又莫有圆满结果,真令人大惑不解。像吴江两人的故事,真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此处没有用《世说新语》中的原句,而是直接引用了《花月痕》的第一句话。“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同样是小说叙述者的感慨。《昙花影》开首和结尾处对“情”的讨论和《花月痕》有极大关系,或者说《昙花影》所谈之“情”源自《花月痕》。
《昙花影》是白话小说,男女主人公都上新式学堂,他们互通的书信、写的诗文却都是文言。第六回筠秋写成《四季歌》,是四首古体诗,第十九回筠秋死后,英仲写的文言祭文和十四首悼亡诗,情深意切。文言诗文的抒情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白话,而把文言诗文穿插在小说的白话叙事中,是《花月痕》典型的文体特征。《昙花影》对这一文体特征有直接承袭,并且“昙花影”之意不无对“花月痕”的仿照。花月不圆而痕长在,昙花易谢而影留心。
白话擅长叙事,文言更宜抒情。明清白话小说的兴盛,和语体本身的功能是相关的。民初哀情小说构成一股潮流,也和语体有关。哀情小说家并不太看重叙事,他们的哀情故事基本不离一定的模式。人物不多,情节不复杂,所重者只在一“情”字。普实克把“悲剧”看成是“抒情”的重要构成部分,王德威把“政治”理解为“抒情”的用途之一,这些都能呈现民初鸳蝴派小说的品貌特征,而文言则是民初小说更独具的形态,能以更直接的方式来抒发情动于衷的无限感伤。李定夷创作的多数哀情小说都是文言作品,《千金骨》第四回开首道:“情之所钟,端在我辈。人类不绝,情根不灭……情之为情,如洪水然,不动则已,及其动也,大荡横决,靡所底止。”㉜此处又直接引用《花月痕》原句,文言的四字句表情有力。
文言小说《千金骨》1916年初版,1936年第9版,1947年又版,共二十回。小说主人公狄青和碧英少小同窗,情深意笃,后各自颠沛流离,终不能聚首。碧英身死,狄青饮恨。单行本归之为“惨情小说”,比“哀情”程度更深。第十一回叙述碧英之歌,便是一种抒情。歌停,一恩客曰:“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玉如,汝诚有难言之痛欤?昔人评刘梧仙曰:‘善为宛转凄楚之音。尝于酒酣耳热,笑语襟沓之际,听梧仙一奏,令人悄然。’今可移赠玉如矣。虽然,以玉如之一尘不染,又恐非梧仙所及。”“言次,浮一大白。”玉如是碧英入妓籍的名字,刘梧仙就是《花月痕》中的刘秋痕。所引“昔人评刘梧仙”的话出自《花月痕》第七回,韩荷生《重订并门花谱》把秋痕放在第一位,并写了一篇小传:“梧仙姓刘氏……尤善为宛转凄楚之音。尝于酒酣耳热笑语杂沓之际,听梧仙一奏,令人悄然。盖其志趣与境遇,有难言者矣!”小说第六回,秋痕登场,落落寡欢,一曲《长生殿·补恨》赢得韩荷生青眼,荷生评道:“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我要浮一大白了!”文字互照,《千金骨》写碧英青楼唱曲一节,明显引用了《花月痕》对秋痕的描述。
狄青的形象如《花月痕》中的韦痴珠,才华满腹,乱世飘零。狄青和碧英的故事是由“隐红”发掘出来的。隐红在小说“楔子”部分悲叹:“予也,别无所忧,惟是历落他乡,寒暑几经,上有老亲,下有弱息,显扬既不能,事蓄又不足。每念身世,辄为忧形于色耳。”隐红的悲叹不仅可以观照小说主人公狄青的遭遇,更于《花月痕》开首处“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已经表明。韦痴珠如此、隐红如此、狄青如此,李定夷未尝不如此。这是自古读书人的一种悲哀。在鸳蝴派小说中,韦痴珠式的形象有正统的继承者。
四 文人的狭邪游
1908年《中外小说林》杂志刊载了一篇“近事小说”《花月痕》㉝。这是一篇文言小说,叙述一个名叫“饶于情”的青楼女子,考验洪生,最终两人喜结白首。这篇小说和魏秀仁的《花月痕》几乎没有关系,只是题目一样。为何也叫“花月痕”?魏秀仁谈过此三字的命意:“夫所谓痕者,花有之,花不得而有之;月有之,月不得而有之者也。何谓不得而有之也?开而必落者,花之质固然也,自人有不欲落之之心,而花之痕遂长在矣;圆而必缺者,月之体亦固然也,自人有不欲缺之之心,而月之痕遂长在矣。”㉞“花月痕”是花月在人心中被向往的印象。即使现实中月缺花残,念想中依然可以团圆美满。以此来看“近事小说”《花月痕》,便可理解作者为何用一个美满的故事来映照小说的标题。不过,这篇小说在题材方面还是追随了魏秀仁的《花月痕》。鲁迅把《花月痕》归为“狭邪小说”,而“近事小说”《花月痕》叙述的青楼艳迹又是晚清以降街头巷尾的重要话题。事关“花月”便可成“痕”。《花月痕》留给现代小说的既是诗意的抒情叙事,也是题材的浓厚兴味。
鲁迅谈狭邪小说时追溯了过往的一种风习:“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㉟文人冶游,自唐而盛。后来学者对此也有描述:“举人们一心希望金榜题名,从此跻身仕途,光宗耀祖。来到长安,烟花柳巷就是必游之地,来客无论贫富,都会去享受一下京城的艳福。”㊱冶游成了文人的一种生活样态,他们不但与青楼女子相识相恋,还写下诗文记录自己的情感经历。在鲁迅列出的狭邪小说中,《青楼梦》加了“游仙”成分,故事圆满,不关悲情,《海上花列传》中的恩客多为商人。文人写作的文人狭邪游故事,在古代还当《花月痕》最典型。
清末文人仕途不济,不得不走出书斋,在公共空间寻找安身立命之地。《花月痕》描述的“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的情形在清末以后的文人身上更为普遍。而一旦进入公共空间,歌楼楚馆又是社交谋生的一种功能性存在。鲁迅说:“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㊲写法的变化与作者或文人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有关,也与时代观念、历史变迁有关。但大变化不等于全然改变,文人诗酒风流的传统,对于“一往情深”本身的迷恋,使他们在与妓女的关系中,总有浪漫存在。如果说处于“溢美”阶段的《花月痕》因融入了作者的身世经历而显得“近真”,那么处于“溢恶”阶段的《九尾龟》也因叙述了作者的经验而几近于写实。
《九尾龟》在鲁迅、胡适等现代学者的眼中是被否定的一部作品。胡适说:“《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㊳如果搁置小说的“价值”,仅看小说写了什么,“嫖界指南”的批评是有些苛刻的。《海上繁华梦》叙写两个读书人谢幼安和杜少牧在上海游历的故事。谢幼安结识青楼女子桂天香,桂天香被小说写得风雅多情,谢幼安娶了桂天香,桂天香为护理谢幼安,自己染上喉痧而身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作者孙玉声写这个故事,寄托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孙玉声名之为“退醒庐伤心史”:“至苏氏为余侍疾,及祷天代死事实,余适著《海上繁华梦》说部,为之详细采入。即书中之桂天香是。”㊴如此感伤的文人情事,不当以“指南书”简单论之。《九尾龟》对狭邪故事的描述要比《海上繁华梦》更为“溢恶”。小说主人公章秋谷在欢场无往不利,他能文能武,只是时运不济,娶的夫人又很平庸。郑逸梅说:“书中主人章秋谷,即作者影子也。”㊵更确切说,章秋谷是作者张春帆理想自我的投影。小说第七回叙述章秋谷谈《花月痕》:“‘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接着说道:‘这是《花月痕》中韦痴珠的牢骚气派,我年纪虽不逮痴珠,然而天壤茫茫,置身荆棘,其遇合也就相等的了。’”“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出自《花月痕》第十九回,痴珠听荷生谈军务,十分丧气,便吟出这两句诗,抒发对时事的悲愤之情。秋谷引用此诗,认为自己的境遇和痴珠是一样的。小说要突出秋谷才气,熟知《花月痕》、同情韦痴珠便是重要表征。小说第十二回回末诗道:“一双蝴蝶,可怜同命之虫;卅六鸳鸯,妒煞双飞之鸟。”㊶更可见出对《花月痕》的自然化用。《九尾龟》是狭邪小说,《神州画报》(1916)连载本、尚友山房(1917)单行本、三友书社(1925)单行本,都标“醒世小说”,从其与《花月痕》的关系来看,用“嫖界指南”来概括《九尾龟》未免粗率。如果考虑到冶游者的身份和他们的情感取向,那么从《花月痕》引发出的失意文人的爱情故事,或许可以成为追踪传统文人如何应对现代生活的一条线索。
从《花月痕》到《九尾龟》再至民初及二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说,文人狎妓的故事在反复叙述,只不过具体到不同文本,狎妓故事呈现出的现实价值、主体观念、情感程度都会有所差别。这与作为文人的作者是有关系的。1920年代毕倚虹、包天笑合著的《人间地狱》是一部专写文人狭邪游的小说。袁寒云说:“《人间地狱》,多述其经行事,间及交游嘉话,其结构衍叙有《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红楼梦》、《花月痕》四书之长。”㊷比起《花月痕》的悲剧,《人间地狱》是在日常现实中沉淀人生。毕倚虹说:“余撰人狱之旨,自信无多寄托,特以年来所闻见者,笔之于篇,留一少年时代梦痕而已。”㊸这一“梦痕”是过去人生的印迹,和“花月痕”的意思一样。
《人间地狱》的主人公柯莲荪、姚啸秋等映照出作者毕倚虹、包天笑及他们的朋友姚鹓雏等人的一段岁月故事,能够见出1920年代文人的情感生活。包天笑谈毕倚虹的情事道:“乐第诚如曼殊所说的,有娇憨活泼之致……谁知这一个娃娃,竟支配了倚虹半生的命运,这真是佛家所谓孽了。”㊹包天笑和毕倚虹是上海《时报》馆的同事,常相邀吃酒,出入花丛。《人间地狱》记述了以毕倚虹为原型的柯莲荪的一段“孽缘”。包天笑给《人间地狱》作序道:“抑知哀乐中年,不堪回首。我心之衰,惟自知耳。”㊺写这些话时,包天笑四十八岁,毕倚虹三十二岁,正是“哀乐中年”的时候。两年之后,即1926年,毕倚虹去世,《时报》《紫罗兰》《上海画报》等刊物纷纷发文纪念他,包天笑则为好友续写出《人间地狱》后二十回。毕倚虹的结局投射在小说主人公柯莲荪身上,代表了现代文人的一种归宿。
当《人间地狱》在上海引起反响的时候,《春明外史》在北京一炮打红。毕倚虹去世,张恨水写了《哀海上小说家毕倚虹》一文。文中道:“海上小说家,汗牛充栋,予恒少许可。其文始终如一,令予心折者,仅二三人,毕倚虹其一也。”“《人间地狱》一书,予尤悦之。”㊻《春明外史》在写法上有借鉴《人间地狱》之处。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请张恨水协助,《春明外史》于是随着《世界晚报》的出刊而连载。小说主人公杨杏园和柯莲荪一样,也是报馆文人,杨杏园则带有张恨水的影子。小说主体故事是杨杏园的两段悲剧的爱情经历,第一段经历完全符合文人狭邪游的题材。杨杏园初涉花丛,认识了雏妓梨云,两人一见倾心,难分难舍。杨杏园无力为梨云赎身,梨云郁郁病亡,杨杏园市骨埋葬梨云。如果联系到民初哀情小说,“梨云”和李定夷《千金骨》中的主人公“梨云”同名。徐枕亚《玉梨魂》结尾词道:“老去秋娘还在,总是一般沦落,薄命同看。怜我怜卿,相见太无端。痴情此日浑难忏,恐一枕梨云梦易残。算眼前无恙,夕阳楼阁,明月阑干。”㊼“梨云”的名字即使与这首词无关,但小说中梨云的故事和这首词的意境十分贴合。张恨水非常关注《玉梨魂》,他写过《〈玉梨魂〉价值坠落之原因》分析《玉梨魂》轰动的盛况为何会烟消云散。“十年前,二十岁以下之青年”无人不读《玉梨魂》,而“今日新出刊物,如鲁迅、张资平诸人所作,均不能望其项背”㊽。非身历其境者,当不能有此感慨。非受其影响者,亦当不能有此挂念。
张恨水是在民初哀情小说的氛围中初试笔墨的,他早期的小说《青衫泪》《紫玉成烟》等不脱鸳鸯蝴蝶派的味道。张恨水谈《青衫泪》道:“我简直模仿《花月痕》的套子,每回里都插些词章。”在张恨水的阅读经验中《花月痕》占了重要位置:“我另赏识了一部词章小说《花月痕》。”“我幼稚万分,偶用几个典,也无非是填海补天,耳熟能详的字句,把这种诗去学《花月痕》作者魏子安,可说初生犊儿不怕虎。”㊾《花月痕》的辞章之美,吸引了张恨水,成了他学习的范本。在创作《春明外史》阶段,张恨水的才子气被有意彰显出来。《春明外史》不但注重回目的设计,叙事间也随处安插诗词。第二十回叙道:“果然有张诗稿,那上头写道:‘读花月痕,见韦痴珠本事诗,和张问陶梅花诗原韵,心窃好之,亦次其韵。’这下面就是诗。”㊿《花月痕》第三十一回叙述韩荷生作《春镜楼本事诗》八首,和《梅花》诗原韵,寄给韦痴珠,请他评阅和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就出自这一回,这是《花月痕》中较著名的篇章。杨杏园写的“读花月痕,见韦痴珠本事诗”就指此事,不过本事诗是韩荷生写自己和杜采秋的。杨杏园读《花月痕》引发他的诗兴,这就是“才子气”。
《春明外史》第二十九回又提到《花月痕》和本事诗。杨杏园吟道:“七千里纪鼓邮程,家山何处?一百六禁烟时节,野祭堪怜。”他对何剑尘说:“《花月痕》上双鸳祠的碑文,你怎样不记得?说起《花月痕》我又想起来了,我那和张船山梅花诗的八首本事诗,我完全是仿《花月痕》的意思,你为什么告诉密斯李?”《花月痕》第五回叙韦痴珠梦见来到双鸳祠,醒来后把梦中的碑文记了出来,其中几句即是“七千里纪鼓邮程,家山何处;一百六禁烟时节,野祭堪怜”。第十九回又提到双鸳祠碑文,第五十一回韦公祠碑记中也有“双鸳祠”,所以“双鸳祠”是《花月痕》的一个重要关目。杨杏园提及双鸳祠及其碑文,也是借《花月痕》表达出的暗示。张友鸾谈《春明外史》道:“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春明外史》之后,张恨水小说中才子佳人式的文人狎妓故事越来越少,他甚至写了《公园驱娼运动》等文,抵制娼妓现象。张恨水创作的转变,也意味着《花月痕》的影响在1930年代以后渐趋消散。
可在1939年,当张恨水在战时的重庆继续他的编报生涯和小说写作的时候,他又想起了《花月痕》。他写了一篇小文《哀〈花月痕〉作者》,文中道:“魏秀仁以满怀忧国忧时之志,无由发泄,愤而作《花月痕》。”“故其书开宗明义,即云:‘不愿闻者闻之,不愿见者见之。’千古来屈子沉江,长沙痛哭,何莫由此。”张恨水认为魏秀仁写《花月痕》别有寄托。《花月痕》开首言“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被张恨水概括为“不愿闻者闻之,不愿见者见之”,这是文人身处乱世的悲哀。战乱时期的1940年代和清咸丰、同治年间或可相互体察。张恨水辗转重庆,忆及他早年欣赏的作家、熟稔的作品,才子气节、人生感慨,今之尤昔。
注释:
① 袁进:《浮沉在社会历史大潮中——论〈花月痕〉的影响》,《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② 陈建华:《抒情传统与古今演变——从冯梦龙“情教”到徐枕亚〈玉梨魂〉》,《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③ 墨泪词人:《花月痕传奇》,《妇女杂志》1915年第1卷第10号开始连载,至1916年第2卷第7期,未完。
④ 魏秀仁:《花月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54页。以下《花月痕》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
⑤ 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⑥ 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⑦ ㉕ ㉛ 李健青(李定夷):《民初上海文坛》,《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208、217、216页。
⑧ 郭昌鹤:《佳人才子小说研究》(上),《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⑨ 吴小如:《“鸳鸯蝴蝶派”今昔》,《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1期。
⑩ 徐枕亚:《玉梨魂》,民权出版部1913年版,第26页。以下《玉梨魂》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
⑪ 郑逸梅:《徐枕亚之诗》,《读者文摘》1941年第1期。
⑫ 冰心:《〈玉梨魂〉之评论观》,《电影杂志》1924年第2期。
⑬ 双热:《序》《玉梨魂》,徐枕亚著,民权出版部1913年版,第1页。
⑭ 吴双热:《孽冤镜》,民权出版部1915年版,第1页。
⑮ 李定夷:《霣玉怨》,国华书局1914年版,第2页。
⑯ [捷克]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2页。
⑰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72、86~87页。
⑱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86页。
⑲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详解》(下),(南朝梁)刘孝标注,朱碧莲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
⑳ 李定夷:《论小说》,《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7期。
㉑ 李定夷:《小说学讲义》,《文学讲义》1918年第3期。
㉒ 李定夷:《伉俪福旨趣》,《伉俪福》,国华书局1921年版,第1页。
㉓ 《李定夷著哀情小说鸳湖潮》,见《昙花影》,国华书局1915年版,书尾广告。
㉔ 李定夷:《发刊词三》,《小说新报》1915年第1期。
㉖ 李定夷:《花月痕考》,《定夷说集后编》,国华书局1919年版,第78页。
㉗ 蒋瑞藻、孟洁:《小说考证卷八》,《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11号。
㉘ 容肇祖:《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卷第2期。
㉙ 陈庆元主编《谢章铤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㉚ 李定夷:《昙花影》,国华书局1915年版,第12页。以下《昙花影》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
㉜ 李定夷:《千金骨》,国华书局1936年版,第25页。以下《千金骨》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
㉝ 凿:《花月痕》,《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2卷第7期。
㉞ 眠鹤道人:《花月痕后序》,《花月痕》,魏秀仁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3页。
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㊱ [法]埃迪特·于热:《青楼小史》,马源菖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㊲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㊳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737页。
㊴ 孙玉声:《退醒庐笔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146页。
㊵ 郑逸梅:《张春帆》,《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63页。
㊶ 漱六山房:《九尾龟初集》,尚友山房1917年版,第47、80页。
㊷ 寒云:《人间地狱序一》,《人间地狱》(第一集),娑婆生著,自由杂志社1924年版,第1页。
㊸ 娑婆生:《著者赘言》,《人间地狱》(第一集),自由杂志社1924年版,第1页。
㊹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48、49页。
㊺ 天笑:《人间地狱序二》,《人间地狱》(第一集),娑婆生著,自由杂志社1924年版,第1页。
㊻ 恨水:《哀海上小说家毕倚虹》,《世界晚报·夜光》1926年5月29日。
㊼ 徐枕亚:《玉梨魂》,民权出版部1913年版,第169页。
㊽ 水:《〈玉梨魂〉价值坠落之原因》,《世界日报·明珠》1929年7月9日。
㊾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研究资料》,张占国、魏守忠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7、23页。
㊿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