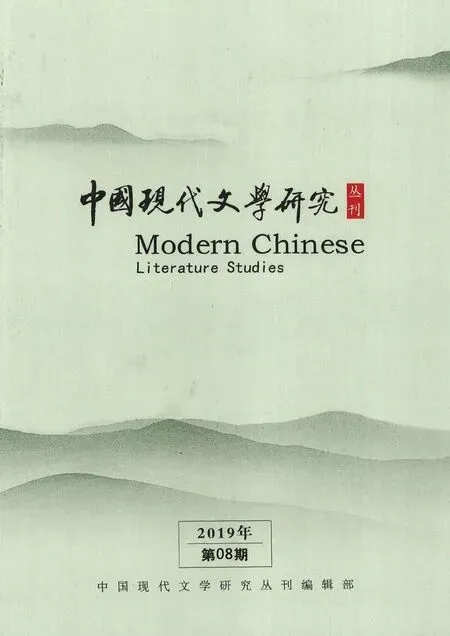从复古到反复古:钱玄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王本朝
内容提要: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他走了一条从复古到反复古之路。从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到主张思想革命和汉字革命,积极反孔教,反儒道学说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倡导国语统一和思想自由。无论是他的复古还是反复古,都与特定的社会情势变化有关,历史事件将他带入思想的现实,也与他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拥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开放性眼光和现代化诉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拥有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双向目标,选取批判与重释、拒斥与吸纳等不同路径和方式实现传统的转化和价值的创造,可以说是“破”与“立”相统一。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偏向于思想启蒙,重“破”弱“立”,走了一条从复古到反复古之路,彰显着持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
一 复古:钱玄同的民族意识
钱玄同曾这样描述他个人思想的前世:“我在1903年以前,曾经做过八股,策论,试帖诗;戴过顶座,提过考监;默过粪学结晶体的什么‘圣谕广训’,写过什么避讳的缺笔字”,还“骂过康梁变法,曾经骂过章邹革命;曾经相信过拳匪真会扶清灭洋;曾经相信过《推背图》《烧饼歌》确有灵验。就是从1904到1915(民国四年),这十二年间,虽然自以为比1903年以前荒谬程度略略减少,却又曾经提倡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做过写古体字的怪文章;并且点过半部《文选》;在中学校里讲过什么桐城义法。”①钱玄同曾是一个复古派,信奉国学(后来被他称为“粪学”),提倡国粹,从思想到行为一个劲儿地崇古复古。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复古经历和身份,而作多次表述,意思大都比较相近。他在1917年元旦的“日记”里也写道:“余自1907年(丁未)以来,持保存国粹文论,盖当时从太炎问学,师邃于国学,又丁满洲政府伪言维新改革之时,举国不见汉仪,满街尽是洋奴,师因昌明国粹之说,冀国人发思古之幽情,振大汉之天声,光复旧物。”②在这里,他提到了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和当时维新改革的社会现实。他是章太炎的弟子,曾跟随其学习传统小学,那时的章太炎也是一个国粹主义者,以国粹之学振兴大汉民族,其学问拥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特点。1924年,钱玄同又提起这些过往经历,说到1906年秋去日本留学,“我那时对于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的,觉得他真是我们的模范,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真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太炎先生对于国故,实在是想利用它来发扬种性以光复旧物,并非以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复活的。而我则不然,老实说罢,我那时的思想,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之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③。章太炎以保存国粹“发扬种性”,“种性”即汉族属性,钱玄同接受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只是更为偏激,有汉族至上意识,不仅在思想文化复古,还要包括仪文政制,都回到夏商周三代去。至于如何回得去,他也没有深入思考,只是在行为上改名为“夏”,于所习文字学,认为“字音应该照顾亭林的主张,依三代古音去读;字体应该照江艮庭的主张,依古文籀篆去写,在普通应用上,则废除楷书,采用草体,以期便于书写”④。在思想上,“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为同样之仇视”⑤。并且,辛亥革命后,他还做了一套“深衣”,后被同事传为笑柄。由此可见,钱玄同的复古有些依葫芦画瓢,比老师走得更远。他的认识总体上比较模糊,主要出自汉族身份意识的强烈认同,并无多少独特的思想和看法。后来,他的民族意识有所调整,将满人和满清帝制分开,“1912年2月12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的仇敌”,在这以后,他把满人当作了朋友,却依然把溥仪等遗老看作是自己的仇敌。⑥实际上,他对皇帝一直持极端排斥态度,即使留学日本期间,“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⑦。
甲午之战的失败,戊戌维新的流产以及庚子之难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发生,使清朝政府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也引发了排满思潮的酝酿和推进,在海外留学生和青年军人群体中更为明目张胆,如陶成章所说:“留学生中之有知识者,知满汉二族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满人不可,由是汉满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之风潮起矣。”⑧排满思潮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有西方影响,也有现实背景,其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梁启超还有大小民族主义之说,他认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而他则是“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⑨。小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汉族中心的“排满”思潮,大民族主义则指各民族联合起来抵御外侮,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当时主张排满最力的则为章大炎,他理解的民族主义是人之种族“根性”,为“生民之良知本能”,自古就有,“远至今日,乃始发达”,“必不可破”⑩,所以,他“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族为断”⑪,汉族之外的“其种族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⑫。这以血统和种族作区分,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显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章太炎的思想显然会影响到他的弟子们,何况“极端地崇拜”他的钱玄同。当时的邹容、孙中山等都曾有过这样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邹容认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⑬孙中山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⑭后来孙中山调整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念,将满族人与满清政权区分开,他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族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族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⑮于是提出了“五族共和”政治理念,抛弃了狭隘的“贵中华而贱夷狄”思想,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⑯。在这样的时代情势里,钱玄同的民族认知自有其必然性和代表性。应该说,除科学主义之外,民族主义是晚清以降所引进西方思想中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它激活了人们的文化记忆,推进了民族国家整合,有助于社会的近代化变革。章太炎和钱玄同的民族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其背后也不无争民权、促变革的价值取向。
钱玄同早年的复古出自师门,诱于国粹,委于时势,成于自知。这段复古经历也为日后的反复古提供了可能。至于其原因,周作人说是他“走不通”,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来自社会时代的变迁。周作人说他入章门,研习国学,“是他复古思想的第一步”⑰,在文字上琢磨“怎样复古”,“光复旧物”⑱,“发思古之幽情,追溯汉唐文明之盛”,“凡字必须求其‘本字’”,推崇小篆。后来,他又走向了疑古,主张破坏,把线装书扔进茅厕,四十岁的人就应该枪毙。对复古本身也有自醒,因为“复古愈彻底,就愈明白这条路之走不通,所以弄到底只好拐弯,而这条拐弯的机会也就快到来了”,1915年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⑲。钱玄同自己也承认,1910年回国以后,“祖国腐败空气久,谬见渐生,什么读经、尊孔,中国伦理超越世界种种荒谬之谈,余当时亦颇以为然”⑳。但他对共和政体却多有推崇,哪怕是在日期间,也倾向“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㉑。这也为他转向民国认同提供了基础,毕竟势大于人。
二 反复古:钱玄同的国家认同
辛亥革命和《新青年》的创办为钱玄同的思想变化提供了现实契机,从此,他走向了反复古和国家共和的认同之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也是重要因素。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转变:“从12岁起到29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㉒采用“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的说法,近似鲁迅《狂人日记》开篇的“狂人”之语:“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只不过鲁迅使用的小说笔法,而钱玄同则是陈述事实,从梦中醒过来成了“中华民国的新国民”,这是钱玄同的新身份,也是他反复古的现实支撑和价值参照。
可以说,钱玄同对“民国”的想象和认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热诚而执着,他经历过满清帝制,向往着民主共和,所以,在他看来,“民国与帝国,虽然只差一个字,可是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它们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们不但相差太远,简直是背道而驰。帝国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国的政治是国民相互的一种组织,帝国的法律是拥护君上而钳制臣下的,民国的法律是保障全体平民的”,“帝国的文章是贵族的装饰品”,“民国的文章是平民抒情达意的工具,应该贵活泼,尚自由”,“帝国民国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说是无不相反”,“要民国,惟有将帝国的一切扔下毛厕;要帝国,惟有将民国的一切打下死牢:这才是很干脆很正当的办法”㉓。他比较了民国和帝国的政治形态,一共和一专制,这可说是它们最大的不同,于是,他呼吁:“要中华民国,要认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则请赶快将国粹和东方文化扔下毛厕”㉔,并大胆直白地表态:“我是民国的国民,我自然希望民国国体巩固,不希望有人来捣乱,再闹复辟的把戏。”㉕并且,他希望“中华民国的国民”应“做一个二十世纪的文明人”,不做过去时代的“野蛮人”㉖。在钱玄同眼里,社会已进入民国时代,新时代应有新目标,“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㉗,共和国与帝制应是完全对立的。当社会现实中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以及其他种种死灰复燃的景象时,他就会产生愤懑情绪,而深恶痛绝。“自1913年袁皇帝专政以来,复古潮流一日千里;今距袁皇帝之死已两年有余,而复古之风犹未有艾”,“清末亡时,国人尚有革新之思想;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㉘。尽管帝制复辟都以失败告终,但也给钱玄同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如同幽灵一般让他深感恐惧,甚至怒不可遏。1917年,天津发大水,“日本租界涨至五尺,外人均竭力谋泄水救灾,而督军曹锟犹往所谓‘太乙庙’者(蛇精)三跪九叩祈祷。此种野蛮原人,居然在二十世纪时代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畜生事业。唉!夫复何言?”㉙1919年年初,陈衍、林纾要求徐世昌干涉,整顿文科,“这几天徐世昌在那里下什么‘祈天永命’,什么‘股肱以膂’,什么‘吏治’,什么‘孔道’的狗屁上谕!这才是你们的原形真相呢?”㉚钱玄同特别痛恨祭孔拜神,在他眼里,“到了民国时代,还要祀什么孔,祭什么天,还要说什么纲常明教,还要垂辫裹脚,还要打拱磕头,甚而至于还要保存讲什么忠孝节义的旧戏,保存可以‘载’什么‘道’的古文,讲求什么八卦拳,讲求什么丹田。你想,现在是什么时世了?人家是坐了飞行机直进,我们极少数的人踱着方步的向前跟进”㉛。“现在是什么时世了?”这既是对社会的反问也是质问,时代虽变了,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还停留在帝制时代,这让钱玄同既愤怒又悲凉。民国时代虽是他的标准和尺度,但社会现实却没有出现。“二千年前‘宗法’社会里的把戏,现在既称为民国,是早已进入国家社会,当然不能再玩这宗法社会的把戏。”㉜这也应该看作是他的理想,在他的思维逻辑里,既然进入了新的民国,为何还在玩宗法游戏?于是他想不通,看不惯。特别是在他眼里,孔教及儒家思想与民国的民主平等观念也是相矛盾的,社会虽“早为共和国”了,但人们依然“尊孔子”,且“似专一崇拜此点”㉝,而“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只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㉞。虽然孔教及儒家思想与此相反,但社会现实中却处处存在帝制思想。
因为钱玄同对民国和国民有着高度的认知及身份认同,那么,他对孔教及儒家传统采取了决绝的否定态度,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其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㉟对共和国而言,它“以民为主体”,它的法律也“是国民自己定的,没有什么‘君’可以来‘出’令,没有什么‘圣王’可以来‘行吾教’,更没有对于‘不率吾教’的人可以‘从而刑之’的道理。国民定了法律以后,大家互相遵守;国民所‘志’凡在法律范围以内,都是正当的,断断没有别人可以来‘定民志’或‘收逸志’”㊱。于是,他有了这样的主张:“凡与中华民国国体政体和一切组织抵触的,都是‘国贼’,都应该‘除’它,而且‘除恶务尽’!”如“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礼教德治”“文以载道”“安分守己”“乐天知命”“不问政治”等“种种屁话”,都应该在民国元年那天“执行枪决”,以它们是“专制帝国的保镖者,而绝对与共和民国相抵触故,只因当时任它们逍遥法外,以致十四年来所谓中华民国也者,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大多数的国人都是死守帝国遗奴的本分,不能超升为民国的国民:够得上算民国国民的,只有那极少数的几个觉醒者”㊲。虽然,钱玄同把话说得比较极端,但“民国”及“国民”在他看来是一种身份标识,它具有不同于传统道德礼教的现代观念和世界眼光。
在这方面,钱玄同自己真正称得上是民国国民典范和斗士。他曾立下豪言壮语:“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㊳,一辈子“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㊴。他称国学为粪学,比喻为如同昨天所吃饭菜的糟粕,其营养已被人体吸收,剩下的只是排泄物。钱玄同的反传统主要集中在孔教及封建宗法制度,因为在他看来,“大抵中国人脑筋,二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哪怕是孔子,他虽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但他的“‘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㊵。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在他眼里,“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㊶。由此,他坚决反对国粹,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因为在国粹里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有相氏苗裔的“‘脸谱’戏”,有“三纲五伦的孔教”,即使“到了共和时代,国会里选出的总统,曾想由‘国民公仆’晋封为‘天下共主’;垂辫的匪徒,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闹大逆不道的什么‘复辟’把戏”,如果“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出于文明人之外”㊷,“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㊸就是汉字,在他眼里,也是“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是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㊹。于是,他也有了这样的判决:“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㊺并且,汉字与“现代世界文化”也“格格不入”,它只是儒道思想学说的载体,“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㊻。如果要使中国人都接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㊼,那么,汉字就是“一种障碍物”㊽和“野蛮的文字”,因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㊾。因此,他主张废除汉字,“把它们撕毁,践踏,而改用通顺的白话文和文明的拼音字”㊿。当然,在对世界文明的接受过程中,传统文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其文化载体——汉字并非是阻碍的因素,更不是野蛮文字。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汉字是其文明内容的载体形式,但符号本身并无显明的价值负面性,如果将汉字作为内容本身,就会有本末倒置之嫌疑。当然,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主张主要是为了反对礼教,因为汉字里存有儒道思想。作为五四时期反传统最为决绝的钱玄同,有着这样的思维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周作人所评价的那样,“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最激烈者”也可能就是最极端化的人,在他倒脏水的时候,不但会把婴儿倒出去,也可能把装婴儿的盆子一起拋掉了。
三 西方即世界:钱玄同的现代立场
无论是复古还是反复古,钱玄同都采取了极端化方式,复古时想回到远古,对一切“欧化”都持拒绝态度;反复古时又极力反对国粹,推崇欧化和世界化。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社会情势变化大以及他拥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世界视野。有关复古和反复古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关系已作讨论。他之决绝地反复古,不仅基于历史进化论的民国立场,而且还来自他的现代思想。
钱玄同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进化的,断没有永久不变的”事物,民国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应该极力给予维护和坚守。但是,作为政体的民国的创建也曾经是一个空壳,它主要体现于政治体制上的意义,而疏于思想文化的开掘。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思想文化的支持,并为钱玄同的反复古提供了现代思想资源。钱玄同重新解释了“西方”与“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西方”代表了世界,就是现代文化发展方向,不存在所谓文化的“东方化”和“西方化”,“赛先生”也绝对不为西洋“所私有”,而是“全世界人类所公有之物”,是“世界文化”。所谓“欧化”也“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所以,他主张应积极向西方学习。1916年夏秋之后,钱玄同放弃了保存国粹的主张,将创造中国文化的方向转向了学习西方。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本国学问之观察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自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此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以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固闭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一句话,学习西方是为了有“参照”,为了发展“本国”,目的还是中国自身。学习西方,就必须先开放自己,必须自感其不足,这样才有学习的动力。于是,他反对种种阿Q式的“先前阔”自大现象,“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附会”可笑,“自大”更是可耻。即使“先进”的东西曾是我们的,但我们也没有守住并发展它们。若反观社会现实,那更是不值一驳。如果“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部,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什么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晚清以来的连连败绩也说明西方优于传统,因此,他主张应该大胆彻底地向西方学习,因为“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应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20世纪,做一个文明人”,“人家的学问、道德、智识都是现代的”,而“我们实在太古了”。他曾经是以古为荣,向古而生,现在却惭愧自己的“古”。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社会时代发生变化了,钱玄同也从民族自救转向了国家认同,有了世界眼光和现代立场。
钱玄同反对中西调和,认为:“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制度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全身动摇也。我以为真应该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才是。”这是非常极端化的说法。但对钱玄同而言,采用绝对化和偏激性的表达,才能表示他的决绝立场,这似乎也是他在五四时期常用的语言方式。如他说:“我坚决地相信社会是进化的,人们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而前进的,应该努力前进,决不反顾,才对。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各国文化,不问其中国的,欧洲的,印度的,日本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应该弃之若敝履。我对于它们,只有充分厌恶之心,绝无丝毫留恋之想。”这里的“坚决地相信”“决不反顾”“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充分厌恶”“绝无丝毫”,等等,都是表示程度的副词,表明他把话说得很满,表达的意思也比较极端,不想留余地,不为自己留后路。后来,钱玄同又对自己的说法做出反思和调整,认为如“发现了外国人的铁床上有了臭虫”,“我们决不该效尤”,更不能主张“我们木床上发现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将铁床上的臭虫捉来放在木床上”,外国女人穿了锐头高跟的鞋子,中国女子“并非不可穿宽头平底的鞋子”。在中外之间不能全部照搬,一一模仿。所谓“欧化”主要还是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
不但对西方文化,就是对传统文化,钱玄同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极端化策略,而认识到“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研究孔教个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他几乎是步步退让了,至少是进两步退一步了,承认了对方的合理性。他甚至对梁漱溟和梁启超等提倡的“孔家生活”,也“以为极是”,陈独秀和胡适诸人“排斥孔氏太过”了。在1921年1月1日的日记里,他反思自己,“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近来觉得不对。杀机一启,决无好理”,应知“统一于三纲五伦固谬,即统一于安那其、宝雪维兹也是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对于旧人,只因诱之改良,不可逼他没路走。如彼迷信孝,则当由孝而引之于爱,不当一味排斥”,就是“清代朴学者,亦自有其价值,下焉者其白首勤劬之业,亦有裨于整理国故也。至若纳妾、复辟,此则有害于全社会,自必屏斥之,但设法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就行了,终日恨恨仇视之,于彼无益,而有损于我之精神”。钱玄同在不断做出调整,表面上是自我退让,实际上更近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钱玄同自己也承认,他的一生也走了一条不断自我否定之路,“二十年来思想见解变迁得很多,梁任公所谓:‘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我比他有时还要厉害,而且前后往往成极端的反背”,如曾“尊清”后又“排满”;主张复古音,写篆字,后又主张用破体小写;主张保存汉字,排斥拼音之说,后又主张国语非改用拼音不可,极端排斥汉字保存论;主张恢复汉族古衣冠,后又主张改穿西装;主张尊修古礼,后又主张拨弃古礼。表面上有些反复无常,但总的趋势还是从复古到反复古,好在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当然,即使有矛盾也不能否定他思想认识的进步,并且,他自己也发现,每当出现反对现象时,新事物却发展了。“复古”让“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袁世凯称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钉牢了一点;张勋干了一次复辟的事,中华民国的国基就加了一层巩固”,“满清政府杀了谭嗣同等六人,便促进了变法的事业,它又杀了徐锡麟诸人,便促进了革命的行动”。任何事物的进步都伴随反动的力量,不会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但最终却也推进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周作人曾评价钱玄同,“所主张常设两极端,因为求彻底,故不免发生障碍,犹之直站不动与两脚并跳,济不得事,欲前进还只有用两脚前后走动。他的言行因此不免有些矛盾的地方”。生活中的钱玄同却是一个好玩的人,他的“思想显得‘过激’,往往有人误解”,但在生活中对人却“十分和平,总是笑嘻嘻的”,“最通人情世故”,是“朋友间不可多得的人”。他的文章也曾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认为:“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最大。”显然,鲁迅所说主要是他曾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肯定了钱玄同白话文产生的社会效果,并非是他的文章和思想本身。
注释:
① ㉒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81页。
④ 钱玄同:《亡友单不庵》,《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⑧ 陶成章:《浙案纪闻》,《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⑨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9页。
⑩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4页。
⑪ ⑫ 章太炎:《訄书·原人》,《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1页。
⑬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75页。
⑭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
⑮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⑯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5页。
㉓ ㉔ 钱玄同:《赋得国庆》,《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213页。
㉕ 钱玄同:《告遗老》,《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㉖ 钱玄同:《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㉗ ㉞ 钱玄同:《随感录·二八》,《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㉘ 钱玄同:《“黑幕”书》,《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㉛ 钱玄同:《答彝铭氏论新旧改革》,《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㉜ ㉟ ㊱ 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6、317页。
㉝ ㊵ 钱玄同:《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3页。
㊲ 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㊴ 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㊷ ㊸ 钱玄同:《答姚寄人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267页。
㊹ ㊺ ㊻ ㊾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6~167、166、166页。
㊼ ㊽ 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79页。
㊿ 钱玄同:《吉林的反国语运动(一)》,《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