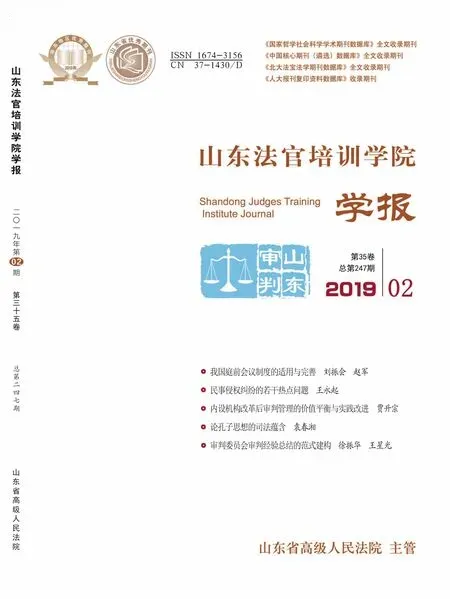陪审员事实认定的障碍突破
——兼论陪审员事实审对罪刑体系之修正构想
李茜
陪审制是司法裁判史上最为古老而又长青的制度。陪审员群体因在生活场域富集的智识,而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具有天然优势,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群体智识内生性的视域限制,陪审员在司法“小前提”的获取过程中也衍生了多重障碍。本文以威格莫尔的证明机理理论为切入视角,探究IBE(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最佳解释推理)图示证明对陪审员事实认定的障碍突破,提出辅助制度建构及罪刑体系修正之构想,以期增益群体智识之运用,助力事实认定过程臻于完善。
一、心智的疆域:陪审制历久弥新之缘由追问
追溯历史,古希腊501名陪审团公民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审判,开创了陪审团认定案件事实的先河。抚去陪审制在历史海潮中绵延承继的溢美流砂,笔者仅从心智界域与权重的角度去管窥其沉浮千年而光彩依旧之缘由。
(一)博识之界:纵深与广博的立体知识建构
法官好似法律帝国的勇士,在规范与判例的崇山峻岭中奋力攀岩,其知识向度是以封闭而整齐的法律规范为界,不断纵向且深邃地拓进。陪审员群体恰如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常识与经验的烟海中破浪远航,其知识向度则是以生活场域为圆心,不断横向且宽广地延伸。面对纷繁复杂的实践挑战,审判知识应当也必须是专识与博识纵横耦合的立体建构。
(二)说服之异:规范与质朴的伦理平衡互通
法官是博学勤练的“人为理性”之个体代表,①[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陪审员则是舞蹈在朴素正义之音中的众生影像;因此,控辩双方倾向于向法官陈述规范性的法则,而向陪审员传递道德伦理、公序良俗等价值性判断。但一场公正的庭审除需俘获法官的内心共振,还更需博得民众广泛的情感认同;而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除需赢得控辩双方胜败皆服,更应期获民众普遍的信仰遵从。
(三)证明之度:真理验证的心灵判断同质性
真理或许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验证并接受真理的过程却需要最广大民众的参与。案件事实在证据锁链的环扣建构过程,亦即真理在法庭上的验证呈现过程。真理的验证若离开了群体智识的参与,显然是不坚实且也不完整的;特别是在内心确信的程度衡量上,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员,其对证据证成与否的内心感知相差无异,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的认定本就是心灵的权重问题。②Wilson, Nigel,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or J.H. Wigmore on evidence law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 Proof, 2015, Vol. 19 Issue 1, p31。
二、庭审的质询:事实认定障碍之聚焦与透析
陪审制度改革以来,多地试点法院均在探索建立由3名以上陪审员和2名法官组成的5人以上大合议庭审理机制,河南、河北等地法院更是采用了人民观审团等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模式,但在中国现行审判模式中,陪审员依然是以个体姿态参与庭审,其经验、常识甚至特定场合的语境知识,不仅与群体智识的理论预设存在巨大差距,且还不足以应对庭审冲突的艰难质询。①[美]保罗·伯格曼、迈克尔·艾斯默:《影像中的正义:从电影故事看美国法律文化》,朱靖江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一)检索:事实认定障碍之成像
Y市L区法院抽取了该院近3年来陪审员参与的1000件刑事普通程序案件进行调研,通过聚焦分析部分典型案例,检索出陪审员群体事实认定的主要知识障碍:
障碍一:故事情节的过分依赖。案例1(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邓氏父子于2010年注册经营了某保健酒业公司,并陆续在其生产的某男性护理酒中添加非食品原料西地那非,进行了少量散售,牟利近万元。
陪审员1(初中语文教师):被告人的辩解虽然言语朴实,但至少是有情节、有故事的;但是公诉人所描述的案件事实过于抽象和离散,只在不断强调牟利、连续犯等专业术语,也未对被告人的故事进行有效回应。
障碍二:生活实例的类比干扰。案例2(非法经营罪):吕氏夫妇经营一家副食店,二人在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套用蒋某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进购香烟并销售,经营数额近6万元。
陪审员2(街道办事处干部):辩方律师提出二被告人系借用蒋某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进货并在自家店铺销售的借证经营,此观点虽有诡辩但不无道理,若二被告人是蒋某的雇工,为蒋进货并销售就不构成犯罪,但若在自家的店铺销售,则构成犯罪的界限很难把握。
障碍三:常识惯性的偏见预设。案例3(诈骗罪):被告人吕某虚构了与某锰业公司总裁交好、具备采锰优势条件的事实,与受害人蒋某约定采取打洞炸挖的形式赴该公司采锰,并先后收取蒋某4万元投资款用以挥霍,且面对蒋某的疑虑又假借各种原由阻止蒋某现场查看。
陪审员3(收藏家协会会员):据我对锰矿行业的了解,采锰需经正规审批程序且使用机械开采,本案中吕某所称采取打洞炸挖的形式显然是在偷锰,而蒋某对偷锰的做法应当也是明知,那么吕某对违法承诺的不履行也不应受到刑罚非难。
障碍四:朴素情感的煽情唤醒。案例4(贪污罪):2004年,工行某支行会计李某利用职务之便,采取空头汇款的手段成功套取银行资金38万元,并携带柜台现金4万元潜逃,后于2015年主动投案自首并退还赃款,另有立功情节。
陪审员4(水利局工程师):被告人的庭审忏悔让我特别动容。被告人的10年潜逃本是一种心灵的折磨,自首、立功和退赃更是其自我救赎的表现,因此我更倾向于从轻、减轻的处罚意见。
障碍五:事实构建的涵摄欠缺。案例5(合同诈骗罪):荣某采用汽车租赁的方式,两次租赁高级轿车,并使用伪造证件将车迅速典当,套现20余万元用以经营挥霍,两车市值共计42万余元。
陪审员5(团区委干事):我的本科曾是法律专业,对要件事实的涵摄归纳相对容易,但由于现有职业与所学专业的疏离,如再独立地整合证据、推导出要件事实,确实比较困难。
障碍六:羊群效应的从众心理。案例6(寻衅滋事罪):苟某因怀疑有人对其跟踪、监视,遂手持铁锹砸向其居住酒店前停放的汽车,共损坏3辆汽车,损失达1万余元,但未造成车内人员损伤。案发当天苟某尿液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明阳性。后经司法鉴定,苟某被诊断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陪审员6(某乡镇村民):我是一个普通农民,也不懂什么专业性的知识,法官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阐释,让我又开拓了视野,我很赞同承办法官的看法,也很珍惜每一次庭审学习、进步的机会。
(二)汇集:障碍分布之表征
结合Y市L区法院对该院85名男性陪审员和23名女性陪审员事实认定的障碍统计,笔者发现了以下现象:
现象一:陪审员的性别、年龄或学历差异并不是障碍形成及差别化的缘由,尽管陪审员个体化差异下的起伏性趋同,但障碍曲线的波折起伏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现象二:不论何种性别、年龄、学历、任期的陪审员,都难以摆脱其生活经历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或偏见,这些干扰性因素在合议中并未得到有效抑制或剔除,甚至会因对纠偏的逆反心理而进一步加深。
现象三:辩方援引生活实例、社会贡献等进行出入罪行的类比或罪轻辩护,会对陪审员产生较大触动,部分男性陪审员甚至更倾向于站在人才培养、社会贡献和个人价值等角度去作出罪轻的意见。
现象四:据L区法院抽取的十二类多发刑事案件的障碍汇集统计显示,陪审员对如故意伤害等常见的自然犯罪不乏涵摄思维,只当涉及专业领域的法定犯罪或法律拟制等情况时,陪审员的涵摄思维欠缺才与故事情节依赖呈正相关,并常陷入彼此互促的恶性循环。
(三)透视:事实迷影叠嶂之成因
通过L区法院对陪审员事实认定的障碍调研,笔者发现障碍成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成因一:说服对象与故事构建的差异。陪审员的优势在于运用其逻辑、经验等语境知识对现有证据搭建最合理的事实或者选择最佳故事。由于陪审员在我国当下的庭审模式中依然以个体姿态出现,加之法官负责对事实的共同认定及规则的单独适用,故公诉人说服的对象更偏重于法官,起诉书中所构建的故事也往往打破了时空顺序,以犯罪构成要件的形式呈现在法庭之上。
成因二:生活实例与罪刑法定的偏离。如果说法典是法官裁判的依据,那么生活则是陪审员认定事实的圣经。陪审员本是源自平凡生活的普通民众,其知识视野无法跳脱生活的参照系;但对专业的法官而言,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罪的先决条件在于是否罪刑法定、是否合乎犯罪构成要件。
成因三:认知惯性与法律逻辑的冲突。生活中的思维定势或常识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陪审员对事实认定的偏见。案例3中,陪审员暗藏了一个并非正确但却为大众接受的认知,即不履行违法的行为值得鼓励。这种思维定势虽能契合大众认知,却忽视了对违法事实的虚构也是诈骗手段的一种。
成因四:合理同情与平等裁判的博弈。对抗制庭审模式中的陪审团模式,对事实的认定充满了戏剧性的意味。经验化的律师往往能利用陪审团成员们的同情心与怜悯心去为被告人争取较轻的处罚,或通过公众舆论向法庭施压。然而,法官不仅要考虑社会民众朴素的情感,更需要关注法定量刑情节以及类似案件中刑罚的均衡程度,故而对刑罚的运用会更为冷静与克制。
成因五: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距离。相较于普通民众尊崇的“5W式”叙事模式,法官另有一套专业的逻辑思维,如基于刑事审判的要件理论或民事审判的请求权思维,去完成事实的重构。故而陪审员或普通民众在庭审中所听到的故事,与法官最终记录于心的故事存在明显的差距。
成因六:小众话语与沉默螺旋的结局。陪审员存在着人生经历、知识视野、经验常识等多重个体差异,因此在案件合议中,相对专业的言论更能受到追捧而形成代表性话语;而一些少数派观念持有者,往往出于节约人际成本和风险共担等心理而在循环讨论中沉默发声。
三、实践的证成:证明机理与群体智识的合鸣
美国证据法学家约翰·威格莫尔在《司法证明机理》一书中首创了“证明机理”(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of)理论,该理论系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一般经验、叙事修辞等基础上的司法证明科学。“证明机理”理论不仅完美地证成了陪审制对事实认定的天然性优势与制度正当性,同时也为破解陪审员事实认定障碍指明了方向。
(一)心灵论证的群体智识依赖
证明机理是指控辩审三方共同遵照证据推理的内在规律、经验习惯、叙事修辞等而合力建构语言性事实文本的过程。①张保生:《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庭审中的证据展现,经历了从开放到闭合的推演及从“原子”到“整体”的质构,所有反向信息的疑点和矛盾在控辩审三角交互中达成合理共识。②[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简单的说,司法证明的过程,就是通过证据与证据、证据与事实的逻辑关联,将“证据碎片”拼图成为“事实画卷”的心灵判断过程。③封利强:《司法证明机理: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威格莫尔认为,证明机理“主要关注争论性说服的推理过程,心灵对着心灵,律师对着法官或者陪审员,每一方当事人都力求打动裁判庭的内心。”④John Henry Wigmore, Th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of, William S. Hein & Co., Inc. Buffalo, New York,2000,p.1。陪审团模式是心智汇集的强大机制,它通过“跨领域代表”的“集体审议”,反映社会之多元价值,⑤黄国昌:《美国陪审制度之规范与实证》,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7期。并达成事实认定之共识正义。⑥陈卫东、陆而启:《打开陪审团暗箱:事实认定的法庭结构理论分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尤其在面对“应注意”与“能注意”、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等事实分歧时,“社会中一般行为方式之普遍持有的观念的巨大知识库”,以及直觉甚至是主观感觉,⑦Peter Tillers, David Schum, Charting New Territory in Judicial Proof: Beyond Wigmore, Cardozo Law Review, 1987, p.913。更能指引事实认定的方向,因为“任何一个具体推论的强度都取决于被探索主题上的经验,而非逻辑。”⑧[英]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莫尔》,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证明机理理论既论证了群体智识认定事实之“正当目的”,又横跨了不同法系之结界,为破解陪审员知识障碍提供了“实践方法”。在此,笔者援引了一份对多维知识综合运用程度较高的实践案例,⑨参见马晓宇、杨蜜、李国平:《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住所查获毒品的认定》,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7期。结合威格莫尔发明的叙事法与图式法之两大“内心证明方程式”,⑩William Twining, Theories of Evidence: Bentham and Wigmo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1。从逻辑建构、心理经验、叙事修辞等多维知识视角,全方面展示证明机理对陪审员智识提升的实践图景。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涵摄
1.叙事法:要件事实的初步搭建
叙事法将所有的证据资料按一定的逻辑框架重新整排,对证据性事实的每一主张及该主张所依赖的次终待证事实进行叙述;并以一个叙事性概论来总结最终待证事实。①[英]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莫尔》,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笔者运用叙事法援引该案例,并涵摄描述出符合犯罪要件的基本贩毒事实:
2014年5月12日22时许,被告人潘某在北京市东城区天桥商场门前,通过被告人高某向购毒人员梁某贩卖了甲基苯丙胺(以下以“冰毒”称)1包,重约5克,并由高某收取毒资1700元。后潘某安排高某再次购入毒品用于共同吸食。潘、高二人于2014年5月13日在二人的暂住地被民警抓获,其中潘某暂住地被起获冰毒0.1克,高某暂住地被起获冰毒6.12克。
上述基本事实的叙述在构成要件范围内展示了犯罪主体、贩毒时间、地点、查获毒品数目、毒资收取等情况,但因叙述的情节较为简单,陪审员仅能初步建立对事实的窥见洞视,却难以决断从潘、高二人住所查获毒品的是否应计入贩毒数量,而后者的思量,则需要通过逻辑结构更为清晰的图式法加以完成。
2.图式法:要件事实的逻辑整合
图式法主要表现为关键事项表(key-list)及图表(chart)的科学运用。“关键事项表”包含所有证据性事实及推论性事实,这些事实命题被以一定逻辑顺序整理编排,用以削弱或支持最终待证事实。“图表”则是描绘上述事实命题的逻辑关系,制图者通过列举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或反对最终结论,并建构一个连贯的结构以叙述对立的论证。②Terence Anderson, David Schum, William Twining, Analysis of Evid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second edition, p.123。首先我们将上述案情以更为详细的key-list阐明案发过程:
(1)E1:通话记录等证据→F1:潘某在东城区天桥商场门前临时回应梁某的购毒请求→G1:潘某产生贩毒故意。
(2)E2:潘某供述、安某证言等证据→F2:潘某临时从其毒品来源的上家安某处购入5克冰毒→G2:潘某为贩毒准备货源。
(3)E3:二被告人供述、通话记录等书证→F3:潘某安排高某向梁某送货→G3:高某产生贩毒合意。
(4)E4:二被告人供述、梁某证言→F4:高某送货完毕后,将收取的毒资1700元交予潘某→G4:潘某、高某共同实施了贩毒行为,且行为既遂。
(5)E5:二被告人供述、安某证言→F5:潘某收到1700元后,临时付给高某1600元让高某再行购入毒品用于共同吸食→G5:潘某、高某实施了毒资的处理行为,再次购毒。
(6)E6:现场检测报告、毒品成瘾认定书→F6:潘某、高某系吸毒人员,且吸毒成瘾严重。
(7)E7:抓获经过、现场称重记录等证据→F7:潘某暂住地被起获冰毒0.1克,高某暂住地被起获冰毒6.12克→G?暂住地查货的6.22克毒品是否应推定为二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总量?
(8)E8:抓获经过、二被告人供述等证据→F8:前1-5项的案发时间均集中在2014年5月12日22时许,第7项毒品缴获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
此份关于潘、高二人贩毒案的key-list,包含了案件组成一系列证据性事实命题(E)、8个推定性事实命题(F)及5个要素性事实命题(G),其中1个推定性命题还待合议庭做出合理解释。该份key-list好似一列以时间为轴序的列车,每个车厢中都搭载了主要事实情节或推断,而时间维度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事实发生与否的原因①Peter Tillers, David Schum, Charting New Territory in Judicial Proof: Beyond Wigmore, Cardozo Law Review, 1987, p.955。。key-list不仅清晰地展示了潘、高二人进行5克毒品的交易过程,还直观地引出了本案审理的焦点,即潘、高二人住处收缴的毒品是否应计入贩毒数量。基于审理焦点还涉及到运用心理学及一般经验对潘、高二人行为的合理解释,故下文待集中认定后再建构犯罪行为图表(chart)。
(三)证据矛盾聚焦与合理解释
威格莫尔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源于经验,经验为所有事件真相的信念形成提供了终结标准。面对事实认定的正反交叉口,与其陷入人为制造的各种证据规则寻求答案,不如依靠最广泛的一般理性、经验常识及心理反映等,去推进事实推导的自然心灵进程。
针对潘、高二人住处收缴的6.22克毒品是否应计入贩毒数量的问题,现有的关联性或可采性的证据规则无法提供任何指导,而《大连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②根据《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其住所、车辆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对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以其购买的毒品认定贩卖数量,确有证据证实购买部分并非用于贩卖的除外。也只是提供了事实认定完结时的裁判路径。本案中,合议庭以潘、高二人购入毒品的时间差、批次差,第二次购毒的临时起意及毒瘾人员心态探究等为关键因素,综合运用常理经验、心理推定及事件发展一般进程等知识,对潘、高二人的贩毒数目做出了慎重评价,最终将二人住处收缴的6.22克毒品排除在贩毒数目之外。
(四)案件事实构建的IBE模式
裁判事实的唯一性,要求裁判者对庭审中所呈现诸多事实版本择一选择或建构,这种最佳故事建构过程在实践中被称为最佳解释推理模式(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IBE模式要求证明主体从已知结果出发来推导关联性解释,③Lipton.P., What Good is an Explanation? , G.hon、S.S.Rakover: Explann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Explanations, 2002, p.12。并从众多相关解释的开放性选择中找寻对案件事实唯一性、连贯性和完整性地最佳故事叙述。①Allan.R.,The Best Explanation: Criteria for Theory Choi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9。
案件事实的建构在庭审中多以言辞形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就是修辞,“裁判凭藉判决修辞而获得形式正当性并能为公众接受。”②胡学军、涂书田:《司法裁判中的隐性知识论纲》,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陪审员在解释—推理—叙事的螺旋上升式的IBE机制中,③[挪威]戴维·布德里特:《论解释的局限及理解之条件的解释学循环》,载拉尔森《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进行了常情、常理与朴素正义等多维析辨,排除了“情怀”“贡献”“荣誉”等情感因素的不当干扰,完成了对证据资料、生活经验、逻辑推理、语法修辞、司法“前见”、常识习俗等隐形知识的“视域融合”。
根据key-list和事实认定的IBE,我们终能以打破时空三维间距的逻辑图式去构建潘、高二人贩卖毒品的案件事实。从图2可知,完整的图式法为陪审员提供了一份打破时空疆域的事实探秘地图。通过对逻辑学、心理学、一般经验、叙事修辞等多维知识的视阈融合,图式法将证据推理的多重姿态涵摄剪裁成规范要件的简明文图,而图式本身就是知识最完美的形态。④Bruce L. Hay, Les Demoiselles D'Evanston: 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Wigmore Char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8, p211-224。
综上,威格莫尔的理论为陪审员事实认定之障碍突破开辟了一道直观而又形象的训练机制。或许即便是最为严谨的法官,威格莫尔的严密的图式推理也未必能见诸其文案记录,但其脑海中关于事实搭建的图式已默然形成,而这却是对陪审员知识完善的最严谨有效的路径选择。当然,陪审员知识素养的蕴涵提升,需要依靠其内在修为,以经验知识强化推理知识,以推理知识推展经验知识,并配以心理学、修辞学等语境知识,在生活的点滴磨练中不断萃取升华。
四、制度的辅助:多维聚力的机制构建之设想
即使是最富经验的陪审员,以最合情理的语境知识去推断事实,都难以避免意识中潜在的惯性及偏见。因此,外部机制的辅助建构是防止陪审员事实认定无形偏离的重要保障。
(一)证据能力的庭前筛查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①[英]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莫尔》,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由于控辩双方会在证据资料的解释描述中加入品格、前科、动因等细节性评价,或通过其他变量对陪审员施加非直接影响,进而动摇陪审员的心理认知,甚至让陪审团的最终裁决变成了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操纵,而非对被告人行为的公正评价。②Dam Simon, A Third View of the Black Box: Cognitive Coherence in Legal Decision Ma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4,p.514。因此,在陪审员认定证据之前,必须对证据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相应的证据审查规则包括以下内容:
1.证据资格审查。凡涉及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所有证据资料必先经过证据资格的审查,合议庭可通过庭前会议等形式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及说明,并审查证据资格,与案件无关联的证据不得纳入庭审调查。
2.召集主体。庭前会议的主持人可由承办法官或审判长担任。陪审员不得参与庭前会议中证据资格审查部分,以防止其在庭前接触到证据实质内容,形成内心预判。
3.审查主体。为保障庭前证据能力排查和庭审中证明力判定的主体分离,形式上的证据能力筛选可以交法官助理进行,对争议性较大或复杂的证据资格审查可交由承办法官或审判长认定。
(二)法律规范的初步释义
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陪审员法律问题适用的指导,往往被放置在事实认定之后,待到法官正式释法时,陪审员已对案件事实形成了一种多点互联的认知网络;而在对事实进行法律涵摄拼接过程中,陪审员又要将牢固成形的知识网撕裂,以完成与犯罪构成要件或法律关系的最佳投影,在此情况下,陪审员重构的案件事实未必比先前更优越。①William L. Dwyer, In the Hands of People: the Trial Jury’s Origins, Triumphs,Troubles,and Future in American Democracy, St.Martin’s press, 2002, p170。专业的法官尚且需将目光来回流转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又何必对陪审员的事实构建进行阶段性的非难呢?
此时需要建立法律释明规则:一是法律规范释明。承办法官或审判长应在庭审前向陪审员通俗化介绍犯罪构成要件或民事请求权等规范含义,以减少陪审员在处理证据信息时的盲目性记忆,增强其对核心证据的合理关注。二是特别规定释明。诸如刑责转化、法律拟制等特别规定,承办法官或审判长应在庭前向陪审员特别说明,确保陪审员能理解特别规定之内核,以达对事实的精确认定。
(三)案情述证的IBE模式
庭审实践中,民事案件当事人对证据罗列多带有随意性,而刑事案件控方的证据罗列,往往严格遵照物证、书证等证据种类的划分列举,从而增加了陪审员形成最佳案情叙述的难度。笔者建议控辩审三方可结合剧场化的司法叙事要素,如主题(theme)、故事(story)、法理(theory)、情境(situation)、场景(scene)、效应(thelema)及剧情说明(scenario)等,打造故事叙述与事实构建的IBE模式。合议庭应引导当事人结合案件的自然发展顺序,以“故事构建”模式列举证据,并说明证据间的因果关系等。对叙事中的矛盾部分,当事人应向合议庭作出合理解释及论证。
五、体系的修正:罪刑体系与审判主体之契合
在刑事司法领域,不论事实认定抑或法律适用,都是围绕着犯罪构成体系而展开,②吴宏耀:《诉讼认识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而案件的待证事实更是通过犯罪构成要件的形式表现。一国罪刑体系的建构只当真正契合于该国审判主体之实践特征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的价值与功效。
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模式绵延承继,除对群体智识的珍视与渴求外,其平面化的“双层次”体系也为陪审团的存续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撑;同时在实体法的犯罪要素描述方面,英美法系往往提供了从“规范性”向“描述性”的技术过渡,特别是法官对陪审团指示中,犯罪要素往往表现为个案的、描述性的判断,陪审团的责任“非仅及于事实认定,还包括将认定之事实涵摄于法律之‘适用法律’在内。”③张永宏:《论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制度设计上的几个课题》,载《军法专刊》第59卷第2期。
德日法系的“三阶层”体系,亦是一种开放、递进、归类的证明模式,既保证了对个体证据的单独审查,将犯罪概念具像化,又通过对个案要素和生活进程的归纳淬炼,将散落的证据碎片逻辑串联,完成了从事实类型到法律类型的过渡建构。在“三阶层”体系中,证据锁链形成于庭审之中,而非开庭之前,故证据间的疑点和矛盾更易被发觉;控辩审三方基于交互理性而达成最终事实认定,①封利强:《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是实质性证明的偶然所得,而非形式化庭审的预先设定。
反观我国平面耦合式“四要件”体系,虽以“事实特征”的形式“模拟”了犯罪事实的结构,为陪审员搭建了相对完整的叙事框架;但构成要件间所特有的闭合共生的依存关系,不仅捆绑了静态的罪刑评价,还束缚了动态的证明进程——囿于对要件概念的解释和提炼,陪审员对事实构建和知识生产总是朝向入罪的单一闭合形式,最终的结论也是“非黑即白”的判断,而不含“或多或少”之可能。
“四要件”体系的最大缺憾在于,事实的认定依赖于证据间相互印证的整体推导。证据锁链自侦查伊始即以整体形式传递之模式,不仅使审判机关向侦查机关让渡了部分审核证据、认定事实的权力,还让庭审演变成为对侦查结论的审核与确认。实践中“三家合作”的证明模式,忽视了正向信息在证明力射程之外的模糊边界,亦排除了反向信息聚合矛盾进而出罪的可能,不但使辩方难以通过个体证据击破耦合整体,也让裁判文书得以避重就轻的仅对证据锁链的完整性予以论证,而对证据间的矛盾疑点一笔带过。“四要件”看似严密的形式反使实质错误易于淹埋,故而难以约束刑罚权的正当行使。②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8页。
威格莫尔的“案件事实IBE模式”,不仅结合了对证据的经验常识判断,还遵循了故事建构的方式及知识,通过以证据建构故事、故事解释证据的双向互动,实现故事模型与裁判类型之契合。①Richard Lempert, Telling Tales in Court: Trial Procedure and the Story Model, Cardozo Law Review,1991,p559。IBE模式作为事实认定的通律,横跨了英美、日德两大法系之间峡谷差异,其方法之精义也应纳入我国陪审员对事实认定的司法证明过程。
同时,为弥补“四要件”体系对事实认定的单向闭合与法律适用的粗泛笼统,笔者建议将德日犯罪阶层中对犯罪事实不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吸纳至我国现有的罪刑体系中,在对事实认定的步骤方面,先进行“立证不法”的罪体核定,再进行“阻却不法”的责任排查。同时还应创建法官对陪审员认定的事实进行回应的阶段,即审查“罪体”是否存在,是否属于“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并通过法官对“罪体”审查完成对被告人和犯罪人的同一性补强。②党建军、杨立新:《死刑案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
“裁判之品质与判决之正确性息息相关。”③何赖杰:《从德国参审制谈司法院人民观审制》,载《台大法学论丛》2012年第41卷特刊。将我国现行的罪行体系改造成要素描述性罗列的“事实面”,再融以德日法系阶层体系的“规范面”,能够有力推进陪审员事实审改革的顺利实施。
结语:打破事实认定之障碍
陪审员参与司法决策的过程,是群体智识认定事实、验证真理的过程。借助于威格莫尔的证明机理的逻辑、心理、经验、修辞等多维视角,辅以外力制度构建和罪刑体系修正,我们可以帮助这群平民英雄打破其事实认定的障碍,令其以平凡却又广博的智识视域,去分析剥离证据的重重迷雾,探求法律事实的IBE图式建构,从而真正实现陪审制度对公平正义之推动和为民司法之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