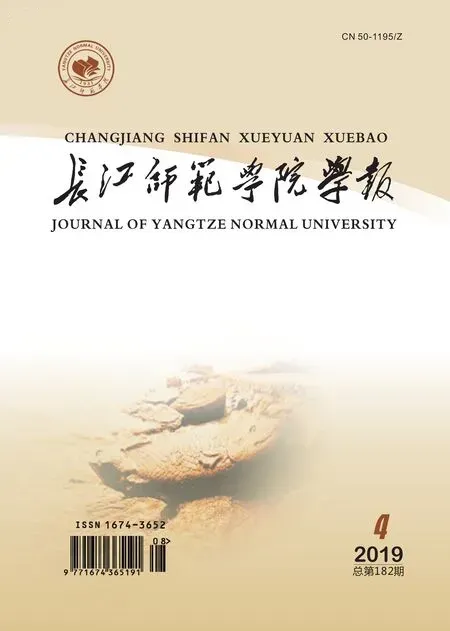散杂居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经验的视角
高 峰,刘 彦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步强化对我国散杂居民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而初步奠定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基本学术架构[1]。王俊从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政策法规、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等不同角度综述了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散居民族研究的相关论著[2];许宪隆、陈锦均认为新时代的散杂居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要关注农村散杂居民族的民生问题,对居住在“老、边、山、穷”地区的大多数农村散居少数民族要在经济上真扶贫,扶真贫[3];在引介国外族群研究理论和运用族群理论解释我国多民族格局的历史演进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现状方面,王希辉认为,现有研究的缺憾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我国多民族国家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散杂居民族[4],当前散杂居民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略显不够,对散杂居民族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关注不足[5]。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上述学者对我国30多年来散杂居民族研究成果的系统回顾、反思与展望,无疑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同于聚居民族,散杂居民族是我国民族分布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许宪隆认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广、多、杂、散、偏、弱等特点[6]。正因如此,农村散杂居少数民族往往受限于较为苛刻的生存环境,贫困发生率高。对于这些居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且远离主体民族分布的散杂居群体而言,如何实现继承民族文化与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即着眼于散杂居民族的现实发展问题,通过对地处“老、少、边、穷”武陵山区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的田野考察,试图探究桑植散杂居白族在族群认同意识下的文化再造过程;借助农耕文化节这一具体个案窥视桑植白族族群认同、文化再造和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尝试提炼类型学意义上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经验。
二、桑植散杂居白族的基本概况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民族,其先民是曾经活跃在中国西南边疆历史舞台上的滇僰、叟、爨等族群。在不同朝代的史籍中,人们对白族先民有不同的称呼,如秦汉称“滇僰”,魏晋南北朝称“叟”“爨”,隋唐称“西爨白蛮”“白蛮”“河蛮”,宋元称“白人”“僰人”“爨僰”,明清称“白爨”“白人”“民家”等[7]。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其族称为“白族”,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白族”这一称呼才正式出现。
(一)桑植白族族源和文化特性
桑植白族祖居云南大理,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蒙古侵宋,大理白族先民终因战争之故落脚于桑植县内繁衍生息。1984年6月27日,桑植县“民家人”被正式确认为白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南境内的白族有115 678人①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网页版,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除云南泛洱海白族聚集区之外,武陵山脉湖南西部境内的张家界市、怀化市沅陵县等地区成为白族的一大聚居区,尤以桑植县最为集中[8],主要分布于桑植县洪家关、芙蓉桥、刘家坪、马合口、走马坪5个白族乡(1984年为7个白族乡,2016年合并为5个白族乡)。
桑植县所处的武陵山区本身也是土家族、苗族等主体民族广泛分布的多民族地区,桑植白族在与这些主体民族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不仅吸收、接纳和融合了桑植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文化特点,也顽强地保护并传承了大理白族文化的部分内涵,表现出文化复兴与再造的过程。桑植白族文化既鲜明体现了立足于桑植本土的“地域性”,又彰显了共享白族身份的“族群性”。自桑植白族确认民族身份以来,在族群认同意识下渐渐产生的文化自觉使其不断加强与大理白族的联系,通过缔结姊妹县、乡、村的方式,桑植白族在大理姊妹村的帮助下开始对失去的白族传统文化进行复兴与再造,借以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实现脱贫致富。例如,合群村连续两年开展了以白族栽秧会为载体的农耕文化节。
(二)族群认同下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的亲情往来
1984年6月27日,桑植“民家人”被最终认定为白族。在族群认同的亲缘关系纽带下,桑植白族与云南大理州白族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与亲密互动。回顾35年间双方的互动事迹,笔者认为有四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的亲情交往主要体现在每逢重大活动时互派祝贺团、捐款援助、文化扶持、缔结姊妹关系四大方面,交往主体仍以地方政府及桑植县、张家界市白族学会为主,两地白族百姓之间的民间交往相对较少;第二,“民家人”被识别为白族之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大理州积极帮助桑植白族发展经济,使后者得以摆脱相对落后的发展困境,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桑植县开始回馈大理州;第三,文化是根,是串联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有力纽带,作为脱离白族聚居主体区的散杂居群体,桑植白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有所缺失,大理州援助桑植白族复兴白族建筑、语言、民俗节庆等传统文化,力图将白族文化不断传承下去;第四,缔结姊妹亲缘关系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借助与大理周城村结为姊妹村的关系,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得以与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遮哈村结为姊妹村,使其姊妹关系进一步扩大,同时扩充了桑植白族的友谊圈,为村际之间的相互学习、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35年间,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并不因时空的距离而使彼此情感疏离,反而在一件件事件的共同参与与见证下强化着彼此的交流与联系,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
(三)田野调查地介绍
合群村位于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境内,距离县城18公里,官瑞公路穿境而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为湖南白族聚居的核心村,于2013年与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结为姊妹村。全村现辖12个村民小组,268户共1 254人,土地总面积5.34平方公里。村民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作物有稻谷、玉米、油菜、红薯和大豆。2011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980元,2013年全村人均收入为1 900元,2017年全村人均年收入3 200元。总体而言,合群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群众生活较为贫困,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没有集体产业,是国家级贫困村。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合群村在帮扶单位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离退休人员党总支等多家机构的帮助下,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泉河坝渠道的治理及国土整治项目,并发展出古方峪黑山羊、优质稻种植、黄桃种植、丑柑种植四大产业。同时,合群村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小组阵地组织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狠抓白族文化和品牌文化,推行“党支部+党小组+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当下,全村村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①资料来源:根据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委会及合群村脱贫攻坚宣传栏所获资料整理,整理日期为2018年6月2日。。
三、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村农耕文化节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族群对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之所以能够产生持久而稳定的影响,根源在于文化,文化认同是个核心问题[9]。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因而应不断对自身进行更新、改造,以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这种过程可以称为文化再造,而再造后的传统文化是“被发明的传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编著的《传统的发明》一书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他强调从仪式和象征特性、通过重复来灌输价值和行为准则、暗含与过去的联系等方面对“被发明的传统”进行界定[10]。任何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发明”的成分尤其明显,既然是“发明”,它已经最大限度地超越了“传统”的限制,表现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鲜事物[11]。可以说,文化再造既体现出与传统的连续性,也表现出与传统的断裂性。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始终都是同人的生存需要、生存能力、生存状况以及生存意向密切联系的[12]。因此,尽管与传统的“连续”以及与传统的“断裂”看似矛盾,但从根本上说,这种新旧交织是基于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即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延续人类文明。
桑植白族的文化再造是在强化对白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对本族群文化事象内的一些要素进行改造,或者创造出新的文化事象的一种行为。一方面,桑植白族的文化再造,是为了展现散杂居民族的地方文化魅力,实现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以文化促发展,从而实现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桑植白族的文化再造,既坚持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其通过不断“发明”形成以栽秧会为主体的农耕文化节等独具特色的桑植白族文化。
(一)栽秧为媒迎新生:桑植合群村白族的栽秧会
作为稻作栽培的农耕民族,白族历来重视稻作的生产,自然也就把栽秧作为生产劳动中最关键的一环,“栽秧会”成为白族人别开生面的生产节日,也是白族最富有民族传统的农事节日[13]。《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记载栽秧会既是劳动组织,又是与劳动相结合的带有娱乐性的活动[14]222。桑植白族的栽秧会来源于大理周城,根据程志君的相关研究,大理周城村的栽秧会实则也经历了一个从“鼎盛到停办再到复兴”的演变过程[15],其演变过程恰也折射出对传统的发明与重建。2017年,大理白族栽秧会被列入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①资料来源:http://www.dali.gov.cn/dlzwz/5116378348250988544/20170615/315912.html。。
2013年5月,合群村与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结为姊妹村。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主要得益于姊妹村这一亲缘纽带,栽秧会才在一步步磋商往来中被推上议程。2017年6月5日,合群村在多方主体的帮助下举办了第一届以白族栽秧为主体的农耕文化节。2018年6月4日—5日,湖南合群第二届农耕文化节隆重举办,笔者全程参与了此次农耕文化节,活动安排集中在6月4日,主要流程如表1所示:

表1 6月4日农耕文化节的活动安排
在第二届农耕文化节上,周城村党总支张书记带领“白族栽秧会传承团”一行60多人再次来到合群村,“传承白族农耕文化,增进亲人间的往来,互帮互助,共谋发展”,是张书记一直以来的朴实想法。
杨姓秧官是大理白族栽秧会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栽秧会前一天,他带领男性传承团成员到村委会前广场上“扎秧旗”,为次日的栽秧会祭祀仪式做准备。在首次举办农耕文化节时,他便收了合群村村主任等两人为徒弟,传授给他们栽秧会祭祀仪式的流程知识,今年他仍身体力行地讲解、演示。他向笔者表示,“明年就可以让徒弟直接上手了,自己在旁边指导就好了”。“扎秧旗”活动由传承团里有经验的男性成员按照传统习俗把4根(取双数)秧旗包扎好,然后进行简单祭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准备,4根秧旗依次被众人抬起在空中挥舞几下,然后立起来靠在屋檐上。随后,秧官口中念念有词,招呼传承团的人和徒弟在摆放贡品的桌子前跪拜。跪拜结束后,筹备工作也就结束了,秧官向徒弟交代秧旗不能倒,不要淋雨等注意事项,之后便和传承团成员离开了村委会。
6月4日,栽秧会正式举行。一大早来自四面八方的村民已经将广场团团包围起来。简单准备后,只见秧旗旗头一端被横着摆放在广场中心有贡品的桌子上,另一端被架了起来。接着,法师宣布合群村2018年栽秧会祭旗仪式开始。仪式主要包括宣读祭旗文,村委领导与高寿者分别祭旗,村委领导给秧旗挂红,村委领导向秧官授令旗、令锣等环节。在仪式举行过程中,伴有鸣炮、发鼓、鸣啰、周德会奏《南清宫》、唢呐细乐的衔接,传承团成员对次数与吹奏时间点的把握都有法师和秧官的指引。最后,秧官激情洋溢地独唱完一段说辞后,鸣啰三声,大声向众人高呼“起旗,栽秧会开始啰”。随即,秧旗在一片应和声中被高高抬起。伴随着打击乐队的一路奏乐,由抬秧旗队、舞龙队、霸王鞭队、挑秧队、男女摇钱树、背秧队、莲池诵经队、村民等组成的栽秧队伍,在秧官的带领下,载歌载舞,浩浩荡荡地巡游到搭建了舞台和农产品品鉴认购会展台的农耕文化节主会场。栽秧队伍到达会场后,栽秧会成员在田间牢固地竖起秧旗。会场内外早已聚集了千余名周边村民与游客。在芙蓉桥白族乡党委书记宣布“2018湖南合群第二届农耕文化节开幕”后,交织着现代元素与少数民族风情的文艺节目便轮番登台表演。文艺汇演结束后,气氛热烈的栽秧比赛开始。栽秧活动刚结束,旁边由游客和村民组成的代表队又开始了紧张有趣的田间拔河比赛。午饭过后,在合群村村两委的组织下,受邀出席农村党支部书记论坛的代表和大理白族群众代表一起参观了合群村特色产业,参加了五省农村党支部书记论坛。晚餐过后,合群村民和大理白族群众还举办了精彩热闹的篝火晚会。
(二)合群白族栽秧会再造的特征
在合群村农耕文化节的非遗“栽秧”祭祀仪式上,来自大理周城村的白族村民始终充当着合群村栽秧会的主体,从前一天的准备工作到第二天的祭祀仪式,再到文艺汇演时的节目、栽秧比赛,大理白族主导着这个过程。秧官不但以师徒制方式传授技巧,而且协助正式举办活动,以合群村村委会成员为代表的桑植白族村民更像是接收者与配合者,合群村民不断“学习”着栽秧会上环环相扣的仪式流程。桑植散杂居白族的栽秧会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别开生面、妙趣横生的生产劳动与娱乐活动,在周城村白族的帮助下,桑植白族已将栽秧会发展为农耕文化节。除了表达对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祈盼外,农耕文化节已然发展再造了许多新元素:
第一,内容外拓,受众增加。桑植白族的栽秧会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节日,而是将文艺汇演、栽秧比赛、拔河比赛等众多活动融合而组成了“农耕文化节”,栽秧会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了扩展。从参与者来看,传统的栽秧会参与人员一般以村民为主,但2018年合群村农耕文化节的参与者除了村民外还有芙蓉桥白族乡、桑植县、张家界市甚至省外等地的人。同时,合群村村委会当天还邀请了桑植县、张家界市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拍摄、现场采访。媒体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使栽秧会成为了一场被众人观看的“表演”,不仅被当天的参加者聚众观看,还通过传播媒介被“不在场”的更多人所了解。
第二,传统栽秧会的功能发生流变,富有时代气息的表演被催生。传统栽秧会在劳动、娱乐功能之外还有表达农业信仰的宗教祭祀功能。在合群村农耕文化节会场上,组织者为当天的节目编排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文艺汇演及栽秧、拔河比赛成为了最受观众欢迎的部分,而一旁大理周城村白族村民举行的与祭祀相关的祈福活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经过再造后的栽秧会实则已经发生了功能的流变,各种祭祀程序至少部分失去了应有的内涵,村民对农业信仰的虔诚态度也已经淡漠许多,取而代之的是组织者为满足受众趣味而安排的各种富有时代气息的表演活动。
第三,传承白族农耕文化的“栽秧会”,对外展示白族发展优势的“农耕文化节”。合群村通过连续举办两届栽秧会,既表达了传承白族农耕文化的决心,也彰显了散杂居民族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归属。对于合群村村委会及相关政府部门而言,以栽秧会为载体的农耕文化节是合群村对外凸显白族文化优势和自身发展优势的优质平台。通过单独设立“合群农产品品鉴认购会”,以及文艺汇演节目中不断插播的实时交易额,合群村将农耕文化节打造成宣传“七眼泉”优质稻米、黑山羊、土山鸡、黄桃等极具合群特色生态农产品的推介平台,在展示合群散杂居白族自身发展优势的同时给这个传统节日注入了新的现实意义。
四、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的“合群经验”
文化常常被认为是社会的既定资源禀赋,在群体中习得并被传承下来,同一群体的人因拥有相同的文化因素而具有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不过在主观性的族群认同背景下,人们可以依照主观的族群认同意愿,发明或者创造出某种文化来标明自己的族群身份[16]。作为散杂居民族,桑植白族立足于发展的实情,通过与大理白族的情感联系,依靠族群认同下不断萌发的文化自觉意识再造了以栽秧会为载体的农耕文化节。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识别合群白族栽秧会再造的动因,进一步尝试提炼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的“合群经验”。
(一)合群白族栽秧会再造的动因分析
散杂居背景下的桑植白族远离大理白族主体700余年,由于历史、地理等诸方面的原因,桑植白族的传统风俗发生了变迁,栽秧会这个节日也逐渐消亡,成为了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当发展变为首要问题被提出时,行为本身便更多地附着了经济理性与利益追求。在和大理周城村结为姊妹村后,桑植白族栽秧会的复兴成为族群认同意识与现实发展需要的产物。在得知周城村一年一度热闹非凡的栽秧会后,合群村村委会开始构想恢复同为白族的这一传统农耕文化活动,并将其与自身发展结合起来,以彰显白族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更希望借助栽秧会这一载体向外界展示桑植白族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体验,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同时传承白族特色文化,为脱贫攻坚出谋划策。
(二)“合群经验”的可能性
麻国庆曾调查闽北樟湖镇民间信仰仪式农历七月初七的“赛蛇神”活动,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仍在举办,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被停办。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政府的介入下这一传统的文化仪式得以复活,并提出“文化的生产”概念,政府希望借助这一民俗文化活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旅游业的发展,使其固有的文化传统打上市场和资本的烙印。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化仪式由纯粹地方性的文化范畴,被纳入到更为广泛的武夷山大文化之中,这一文化消费成为地方性认同和地方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17]。通过更为细致的田野调查可发现,合群村栽秧会的恢复同样呈现出与麻国庆研究的共性所在。合群村栽秧会在政府的介入下得以复活,政府希望借助这一民俗文化活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旅游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压力下,农耕文化节应运而生,认购会的实时交易被打上了市场和资本的烙印。在此,笔者认为,合群村的发展经验包括:
第一,文化的内核。农耕文化节是白族民族文化的一个展演舞台,白族文化是其基本内核。无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栽秧会”本身,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桑植白族仗鼓舞等民俗表演,都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极为有力的展演与表达,其他文化行为的建设都基于这一文化内核。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与机遇。
第二,官方行政化的主导。合群村作为国家级贫困村有挂钩帮扶单位的支持,此次活动便由合群村支部委员会和合群村村民委员会主办,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离退休人员党总支、张家界市住建局、张家界市直机关工委和民盟张家界市委协办,上述机构提供的财力支持是活动得以成功举办的一大重要因素。合群村栽秧会活动的具体实施并非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是政府积极依托自身传统优势文化造势宣传,以此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行政行为,从内容安排到形式上都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从连续举办两届的农耕文化节来看,合群村村委会所代表的地方政府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蕴涵的发展理念也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
第三,凝聚内部发展共同体,拓展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合群村连续举办了两届农耕文化节,不断向外推介桑植白族文化,使其走向更大的舞台,在几年时间内就实现了经济大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生活面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合群村积极汇聚内外部力量紧密相关。从内部看,合群村的发展得益于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即由村干部、党员和地方精英共同引领。在钟姓支书的不懈努力下,合群村得到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离退休人员党总支的有力帮扶,在基础设施建设,如农田水利设施等方面不断完善,这为发展生态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得益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离退休人员党总支的撮合,湖南省山东商会等省内各大爱心企业不断对合群村进行真情帮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合群村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同时,通过党员领导示范的产业发展模式,建立有效奖励机制,吸引地方精英回乡,合群村的内部实则形成了一个发展共同体,汇聚了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将内部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到最大程度。
第四,融入外部发展共同体,吸收先进的宝贵经验与发展理念。此次农耕文化节,除了邀请云南大理周城村的白族人民之外,还邀请了和周城村结为姊妹村的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遮哈村的傣族群众,这无疑使得桑植白族的关系网络进一步扩大。同时,在芙蓉桥白族乡党委书记主持的五省农村党支部书记论坛上,来自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北京市大兴区留民营村等党支部书记各自分享村庄发展的先进经验,并为合群村的发展“号脉诊断”。在论坛上,合群村委会班子成员悉数到场,积极聆听、吸收其他村的发展经验,虚心求教。在周城村的帮助下,合群村不断走出去,和更多的中国农村形成一个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过程既是其文化自信的彰显,更是其在发展考验面前的奋发之举。
基于族群认同的归属感,合群村积极挖掘、传承白族农耕文化,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前,将发展的刚性需求整合进传统栽秧会的内涵之中,赋予了合群村栽秧会新的功能,复兴再造了以新的“栽秧会”为载体的农耕文化节。随后,依托前期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淀,合群村村干部、党员、地方精英、村民凝聚成一个发展共同体,将农耕文化节作为向外界展示的平台,将自身的优势向外界推介,使自己不断走出去,融入一个更大的农村发展共同体的格局中。合群村栽秧会文化再造的过程有着其自身“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具体表现在独一无二的桑植白族文化优势,适合发展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土壤、水源等优势条件,周城村作为姊妹村的倾力相助,这些最终使得合群村农耕文化节当下的局面向好发展。
五、结语
700多年前,桑植白族的先民以外来者身份来到桑植,长期与桑植境内其他民族交往互动。虽然“外来者”的身份迫使桑植白族改变了原有文化,以适应当地生产生活的需要,但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改变桑植散杂居白族对于本族群的认同。在未被认定为白族前,桑植白族对族群的集体记忆还停留在精神层面;1984年,桑植“民家人”正式被识别为白族后,桑植白族的族群认同越发明显,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使他们的族群认同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上。
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身处贫困中的合群村积极利用与大理周城村的姊妹亲缘关系,在族群认同意识和现实发展需要的双重动因下再造了桑植白族的栽秧会,并以此为依托连续两年举办了农耕文化节。当前的栽秧会实际上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形式的“被发明”的现代栽秧会。在这个文化再造的过程中,合群村向外彰显了对白族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展现了桑植白族独具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体验,将农耕文化节打造为一个对外推介的文化平台和展示窗口,将极具合群特色的生态农产品最大程度地向外推送,为自己开出了一剂脱贫攻坚的良方。纵观合群村白族以栽秧会为载体的农耕文化节,在类型学意义上合群经验的可能性或许在于其“以文化为内核、以官方行政化为主导、凝聚内部发展共同体、融入外部发展共同体”的精彩实践。这是当下合群村特色经济发展的个体经验,也是本文尝试提炼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的“合群经验”,“合群经验”未来如何演进,值得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以传承人向佐绒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