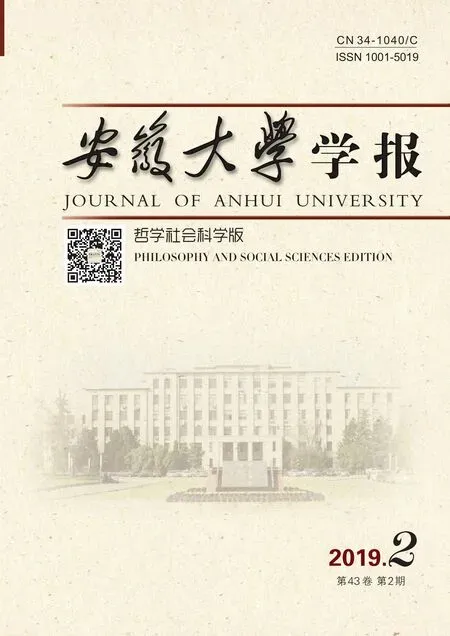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卞 利
宋代以来,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不断成功、宗族社会的渐次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至明代中叶,整个徽州社会出现了“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哉”[注]万历《歙志·考》卷5《风土》。的局面。与此同时,徽州知识和文化精英也开始从各个不同方面与视角,对徽州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并由此拉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大幕。其中,对徽州人群祖先中原身份及其血缘谱系认同的建构,是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性环节和重要内容之一。
一、三次移民徽州运动与祖先中原身份认同的建构
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即从徽州人群来源于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故事拟构入手,开始了对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延至南宋、元、明时期,徽州宗族群体移民自中原和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在一批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的考证和各大地域名门望族纂修的谱牒中,逐渐取得认知上的一致,达成广泛共识。
早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即在《许氏宗谱序》中,对歙县许村许氏宗族五代之初由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迁徙徽州的历史进行了追溯,云:“天宝之乱,[许]敬宗有孙曰远,与张巡以睢阳抗贼,自以不及巡,推巡为守而为之下。久之,食乏无助,煮茶、纸以食,犹坚守。贼所以南向,以睢阳蔽其锋也。卒与俱死,皆天下豪杰义士云。唐亡,远孙儒不义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隐居歙之黄墩,终身不出焉。”[注]隆庆《新安歙北许村许氏东支世谱》卷首《王荆公撰许氏宗谱序》。按,王安石为歙县《许氏宗谱》所撰之《序》,不见收于各种王安石文集,但目前所见包括歙县在内的明清徽州各地许氏谱牒中,均收录了该序,且皇祐二年(1050)以发运使职而被特赐进士出身的歙县许村人许元与王安石交好,许元在自撰的《祖宗世次图序》中专门交代了王安石为许氏谱牒撰序文之由来,故可认定该谱序确为王安石所撰。熙宁四年,詹济亦认定婺源庆源詹氏始迁祖徙自河南南阳[注](宋)詹济:《庆源詹氏谱系序》,弘治《休宁流塘詹氏宗谱》卷1《旧序录》。。号称“新安多望族,程氏最盛”[注](清)王步青:《大呈村程氏续修支谱序》,乾隆《歙县大程村程氏支谱》卷首。的程氏宗族,据传,远在唐代即有程淘纂修的《程氏世谱》,冯剑辉在对程淘所撰《程氏世谱序》考证后,认为其基本可信[注]冯剑辉:《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21页。。但该谱序虽将徽州程氏始迁祖追溯至南朝梁陈时的程灵洗,并未述及其祖先中原的历史。直至庆历三年(1043),歙县人程承议纂修的《程氏世录》序文,才明确将徽州程氏的始迁祖考订为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在这部早于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和苏洵《苏氏族谱》的《程氏世录》序文中,程承议指出:“程氏自晋新安太守元谭公留居郡城,历唐迄梁,代有显者,谱牒相传,灿如日星。……幼尝闻诸大父曰:[程]洎与[程]淘为同产,唐末归黄墩,最长于诸房,因悉召父兄子弟共饮,遂言:我姓来江东将五百年,支派散漫,布满南国。”[注](宋)程承议:《程氏世录序》,隆庆《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卷首。至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程祈父子经过实地调查与走访,结合传说,针对各家“谱牒散漫无纪”的状况,进一步对程氏宗族的迁徙历史和传承谱系进行建构,重新厘定、编纂族谱。在《程氏世谱序》中,程祈写道:
程氏望出广平郡,其上世盖帝高阳之诸孙也。在五帝世,为火正黎,为祝融,为和仲、和叔。逮及周成康之际,始受封为程国。由周而下,世有闻人,见于传记,皆有可考。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吾闻之先府君,以为吾家盛德之后,盖重安忠壮公之系姓也。其后,家君为和州历阳县尉,故吴明光禄帅洪道过南豫,从容谓家君曰:“吾姓同出黄墩,而谱书不传,意其遗落民间,尚未泯坠。吾曹游宦,先至歙郡,当力求之,毋忘以完本相寄也。”熙宁十年春,家君由小著得请知歙之婺源。明年,岁在戊午,实元丰元年正月之九日,于歙县得程氏数十家于黄墩。其豪曰志忠,率诸族父子兄弟迎谒道左。虽然少学,亦颇知礼,盖有衣冠遗风焉。从而询之,乃出其家谱一卷,祖孙相传,多历年数,文字漫灭,世次不明。又得所谓相公墓及宅基、射蜃湖、浴马池等处。里民谈忠壮公遗事,历历可听。其盛德在民,岁时相与祀事不绝。家君既拜墓下,又从歙令张世望借取《图经》,因以考实所闻,盖皆符合。居无几,海宁族人程立亦献其所藏《世次》一卷。两家谱叙,仅足以相补,词多鄙野,不成句读。或传歙县程璇家有善本,会其家有回禄之变,并以亡失。……于是,家君悉以所得程氏谱书付祈曰:“汝当论次。吾读旧谱,至荆州骠骑,有三世不修谱之戒。诚哉,是言也!且忠壮公英灵精爽,死且不朽,殆神有意嘱汝于梦寐,吾滋异之。”祈奉命,不自揆度,实始载其事于心,由是稽考史传,以相证佐,一代定著为一谱,以开元谱为第一。其后十年,调补玉溪掾,其书粗成,然犹未敢以为是也。……元祐间,祈掌教卫学,暇日,复加诠择,铅堑编简,不去几案者垂又五年,乃能讫事。因窃叹曰:“程氏谱牒散漫无纪久矣,凡我同姓,宜所共惜。今以祈之固陋,其所论次,大惧不文,不足以发扬万分之一,然其世序条例颇用史法,井井条理,不为不备也。”[注](宋)程祈:《程氏世谱序》,景泰《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首。
综上所述,如果说北宋时期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对祖先源于中原的建构尚处于初始阶段,那么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第三次移民徽州高峰的完成,特别是徽州经济的深度开发和教育、科第的勃兴,激起了徽州宗族追本报远、敬宗睦族的思绪,一些名门望族为证明自身尊贵的血统身份,纷纷以纂修谱牒的方式,通过对始祖和始迁祖谱系的拟构,建构祖先来自中原的移民故事,并最终使其中原世家大族血统成为徽州宗族与社会的一种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陈之茂在为休宁县《藤溪陈氏图谱》所撰的序文中,借用该族陈质夫之语,开宗明义地指明藤溪陈氏之源于中原及辗转由桐庐徙至藤溪的历程,云:“吾祖,有妫氏之苗裔,三代、秦汉以来,显晦不一,支离蔓衍,吾故不能狥迂儒之见,以强索系谱。自唐末[黄]巢寇扰攘,乃携家去故国桐庐郡,溯流而上,直指新安之城西百余里,得乡曰藤溪。”[注](宋)陈之茂:《藤溪陈氏图谱序》,康熙《藤溪陈氏宗谱》卷7《附录》。绍兴七年(1137),休宁县博村范天民也对徽州范氏宗族的历史进行追溯,并借此建构中原移民谱系,曰:“吾家系出黄唐,至晋武子,始以封邑姓范,世将中军。贞定王十一年,为智韩赵魏所并,子孙散处梁魏。献之子曰蠡,居邓州,师计然,用其术,相越伐吴,浮海出齐,止于定陶。至汉,龙舒侯讳显始居河内,其子滂仕汉为清诏使。滂又十七传曰履冰,唐高宗永徽七年,登进士第,垂拱中,拜相,载初元年,坐举逆人被杀。有子冬芬宣州刺史,生十公,讳惀,为户部员外郎。天宝兵变,复居于邓。其第三子讳传正,贞元十年登第,授集贤殿校书,历殿中侍御史、水部员外郎,出为歙州刺史,始为汪公华奏议立祠。转苏、湖二州,复擢宣歙观察使,历职江南甚久,殊勋美政,见白居易草制。公自吴元济乱后,无意北归,寻以风痹谢政,且爱新安山水,遂择里于休宁之博村而定居焉。”[注]万历《休宁范氏族谱》谱序第二《旧谱序文》。
从以上明清徽州族谱收录的较为可信的两宋徽州族谱序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截止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徽州宗族对祖先源自中原的历史建构并不都是真实的客观事实,且前后多有矛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徽州宗族血缘群体关于祖先源于中原和谱系拟构的认识。这种拟构的徽州人祖先徙自中原的移民故事,终于在淳熙初年获得官方的支持。由徽州著名学者罗愿撰修、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的《新安志》,将徽州人祖先中原的故事收录其中,云:“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注]淳熙《新安志》卷1《州郡·风俗》。从而使半实半虚的徽州人祖先源自中原故事正式转变为一种历史的事实,私家修谱拟构的宗族群体记忆亦由此演变成为徽州地域社会和文化的集体记忆,实现了血缘身份和地缘文化的整合与认同。罗愿在《新安志》中仅就其所知史实,审慎地将中原衣冠避乱移民徽州的历史时间界定为“黄巢之乱”,为徽州大姓望族建构祖先移民自中原的故事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官方依据。此后,几乎每一部徽州大族的谱牒都或多或少地将始祖或始迁祖拟构为中原地区世家大族的移民,并在“黄巢之乱”这一时间节点上进一步向前上溯或向后延伸,先后建构出“永嘉之乱”和“宋室南渡”两个时间维度,从而使得徽州人祖先中原世家大族的血缘身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徐彬和祝虻把徽州家谱中的中原认同时间确定为明清时期[注]徐彬、祝虻:《历史与文化认同:明清徽州家谱中的中原认同现象考察》,《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显然是不妥的。《新安志》刊刻传播以后,徽州各大宗族所纂修的族谱,几乎都将族源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如三皇五帝及其后裔子孙,这亦正是徽州宗族一再强调的“一本万殊”[注]嘉靖《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卷首《凡例》。观念的直接体现。
尽管罗愿经过认真考订,得出“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的结论,但实际上,还在北宋时期,徽州就有西晋“永嘉之乱”甚至王莽篡权时期中原地区世家大族移民徽州的文字记录了。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方仕燮在《方氏家谱序》中云:“余暇日留岩溪,会宗人以《续修族谱》一编来示,征言以识其端,溯自太子雷公,食采于方邑,为吾宗得姓之始。厥后,云仍蕃衍,蔓衍硕大。至汉丹阳令纮公,值王莽篡逆,避地江南。孙储公聪明颖悟,精通神术,有驾鹤乘空之异,为洛阳令,忠义凛然,遭诬而殁,追封黟侯,侪、俨皆其兄弟,咸有令名。储公生三子:观之、赞之、弘之,世其家而丕大。传三十四世,至于念五公高,始迁寒山,子孙蕃盛,绳继引翼,延其休祚,而家声日振。……以时考之,则江淮以南方氏之宗,往往多出于是。但开元而下,子孙或遭世微弱,或流寓他邦,支分派别,盛衰存亡,概难悉考,是以后世多阙略焉。”[注](宋)方仕燮:《方氏家谱序》,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历代谱牒序》。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方愚亦云:“我祖宗本方山帝胄,将相传家。汉元始间,避地江左,于是桑梓歙之东乡,今称南路是也,衣冠相继数千年,为新安之望族。”[注](宋)方愚:《方氏谱系序》,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历代谱牒序》。进一步坐实了徽州方氏祖先源于中原帝胄之裔的建构。而影响更大的理学之集大成者、新安理学的开山祖朱熹,更是在淳熙十年(1183)五月为《茶院朱氏世谱》撰写的《后序》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旧谱云:长春乡呈坎人)。相传望出吴郡,秋祭率用鱼鳖(旧谱云:有讳介者,世数不可考矣。又按奉使公《聘游集目》云:系出金陵,盖唐孝友先生之后。考之《唐书》,孝友先生讳仁轨,自为丹阳朱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义世被旌赏,一门方阅相望,而非吴郡之族。……)唐天祐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注](宋)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明)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18,何庆善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26页。罗愿不仅在其撰修的《新安志》中提出徽州“十姓九汪”的概念,而且对汪氏的祖源也进行了精密考证。针对汪氏是源于汪芒氏还是“鲁成公支子,食采于汪,因氏焉”的疑问,罗愿得出“汪氏为诸侯之裔,似稍近人情”的结论。接着,罗愿根据宋哲宗时文士胡伸所作之《唐越国汪公华行状》等文献资料,对汪氏在徽州的“州望”进行考订,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云:“《行状》称:汉建安三年,龙骧将军文和为会稽令,因世乱避地,家于新安。文和之名,他书无所见,沈约《宋书》云: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则自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近世临川邓名世作《姓氏辨证》,言王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后也。又云:陈稷州刺史汪纲,陈亡,自歙州徙河间,故又有河间汪氏。按,纲之由新安徙,既在陈时,则汪氏之居此旧矣,岂得言自王始乎?太平兴国中,有为《王庙记》者,言王乃隋将宝欢之族子,或谓陈、隋以上始处此邪。本之龙骧,则荒远;就王为说,则简陋,俱未适中,故内翰至此略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则可尔。”[注]淳熙《新安志》卷1《州郡·祠庙附汪王庙考实》。显然,罗愿并不认同徽州汪氏源于东汉建安年间汪文和避乱而南迁至徽州的说法。这或许就是其仅在《新安志》中提及“俞待制献可,字昌言,歙县人,其先居河间,晋永嘉之乱,徙新安”[注]淳熙《新安志》卷6《先达》。,而并未将东汉末年至西晋永嘉之乱作为第一次中原地区世家大族移民徽州的原因。至于两宋之际第三次中原地区移民徽州的历史,则因罗愿《新安志》之后移民者自身的记录而变得真实起来。也就是说,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以降,徽州宗族和文化精英建构徽州人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除唐末“避黄巢乱”和“两宋之际”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之外,第一次中原世家大族移民徽州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慰藉,而非全部的历史真实。但问题在于,在中国历史上,自东汉末年以来至西晋“永嘉之乱”,乃至东晋南渡及南朝时期,为躲避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确有大量北人南迁,加之徽州被孙吴国征服史实的客观存在,因此,第一次中原地区世家大族移民徽州亦并不能说全是一种虚拟的建构。
在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时期,不少徽州大族成员被征佥至淮河南岸戍守。为逃避被征发戍守淮甸的命运,徽州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世世分析”的现象。对此,康熙休宁县《藤溪陈氏宗谱》云:“百六公出自尧仁公次子僎公之后,古城百五公出自尧仁公长子俊之后,盖从兄弟也,皆属文韶公之苗裔,二支皆淮役而归。是时,丁宋之际,南国以淮为边徼,宋元累岁兵争,民多遣戍。其云迁淮者,讳之也。自淮归者,兵息而返役也。且其时,人丁蕃聚者,不免于简点,故世世分析而居,以祈侥免耳。”[注]康熙《藤溪陈氏宗谱》卷2《本宗系牒第十五》。这种被征发戍守的痛苦,加上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剥削,使得徽州人在享受山区深度开发成果的同时,更增添了国难家仇的愤懑。又因新安理学家们的大力倡导,追怀祖先,建构中原世家大族尊贵血统的移民故事,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徽州宗族来源于三次中原地区移民的故事,经过徽州各地大姓望族精英的努力,终于在宋末元初得到了系统建构:“盖江北、中土始以三国之争,继以五胡之乱,重之以五季,宋南渡之余,中原板荡,十室九空,其族无噍类者盖多矣。”[注]程荀轩:《书婺源龙陂程氏谱》,(明)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23,何庆善等点校,第518页。明嘉靖中纂修刊刻的《新安名族志》,全面接受了徽州大姓名族源自中国历史上三次中原地区移民的观点,并以此为依据来记录各大名族的祖源、迁徙与分布,从而完成了徽州人祖先中原的移民史建构过程。对此,嘉靖三十年(1551)四川道监察御史胡晓在其所撰《新安名族志序》中云:徽州“山峭水厉,燹火弗惊,巨室名族,或晋唐封勋,或宦游宣化,览形胜而居者恒多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具在”[注](明)戴廷明、程尚宽等辑:《新安名族志》卷首《胡晓序》,朱万曙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页。。至明万历时,《歙志》亦记录和叙述了三次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为避乱等原因而迁入徽州的历史,指出:“邑自汉唐以来,兵燹不加,人多安土。虽舒、聂浸衰,然而婚姻谱牒,动皆千祀。溯之厥始,昭然可据。其或山水留人,宦游兴寓公之想;乱离避地,保家怀屯聚之谋;抑或遗骨莫返,羁旅忘归;又或间关跋涉,弗惮转徙,则以此中无硕鼠之侵,而彼土多猛虎之惨耳!”[注]万历《歙志·考》卷5《氏族》。尽管歙县各大姓望族大多来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三次大规模移民,但移民又不仅仅限于中原地区,且并非全部皆因躲避兵燹和战乱,其中既有避乱而徙者即避地者,也有遗孤者、羁旅者,更有辗转迁徙而来者。故至民国时期,许承尧在其所撰之《歙县志》中,对宋代以来徽州徙自中原地区的移民故事进行了总结性概述,从而完成了三次移民徽州运动与徽州祖先中原身份认同的建构,云:“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忠壮、越国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而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期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注]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
从罗愿、程荀轩至戴廷明、程尚宽、赵吉士,再到许承尧,经过徽州精英人物的不懈努力,最终完成了对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三次移民徽州运动与徽州祖先中原身份认同的建构,但这种移民故事的建构逻辑并非没有漏洞、无懈可击,相反,恰恰是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历史上徽州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程氏和汪氏宗族,对其祖先迁徙与宗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自相矛盾,进而导致族内纠纷和族外争议不断,就很能说明问题。
以汪氏宗族为例,目前所知最早对汪氏宗族迁徙徽州历史进行建构的是北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被称为“江南二宝”[注](明)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略上》,何庆善等点校,第12页。之一的婺源考水人胡伸。他在《唐越国汪公华行状》中,对汪氏的祖源进行了钩沉,云:“公姓汪氏,讳华,新安人。其先汪芒氏之后,或曰鲁成公支子,食采于汪,因氏焉。哀公时,童踦其孙也。汉建安中,龙骧将军文和为会稽令,避地始迁新安。”[注](宋)胡伸:《唐越国汪公华行状》,(明)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61,何庆善等点校,第1455~1456页。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至少在北宋末年,有关汪氏宗族的祖源就有两种不同说法,即江南的汪芒氏和鲁成公支子。两种说法,孰是孰非?罗愿在引述胡伸《唐越国汪公华行状》并进行分析后,以“似稍近人情”,得出了“汪氏为诸侯之裔”的结论。罗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奈地以“稍近人情”和“以新安之族由[汪华]王而望始著”作为自己模棱两可的理由。实际上,在孙吴时贺齐、诸葛恪次第平定徽州土著山越人金奇、毛甘、陈仆和祖山等发动的叛乱后,山越人便消失在徽州历代文献的记录之中。那么,是不是徽州土著居民山越人完全被融合与同化了呢?或者说,作为“十姓九汪”的徽州,汪氏族群究竟是山越土著汪芒氏的后裔,还是春秋时期鲁成公后裔汪文和徙居徽州后蕃衍的苗裔?这在宋代以来包括族谱在内的徽州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有的依然持汪芒氏后裔之说,如汪高梧于咸淳二年(1266)撰写的《新安汪氏族谱序》曰:“吾鱼龙汪氏由人皇之世以迄于今,聚族新安数千年矣,非平阳、颍川二望所来也。汪芒氏再得国于斯,显圣王复开国于此,以成武之功,勋德之裔,绵绵不绝。”[注](宋)汪高梧:《新安汪氏族谱序》,后至元《新安汪氏族谱》。但更多的还是坚持鲁成公支子后裔汪文和始迁徽州的说法,分歧也不过是颍川汪氏还是平阳汪氏而已。直到近代,陈去病经过认真考证,才郑重地将徽州汪氏之祖源确定为汪芒氏后裔之说,云:“汪氏源出汪芒之后,昔禹会诸侯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之。其骨专车,盖即汪芒也,其国在今湖州山中。楚灭于越,遗黎四窜,汪芒氏入歙,当在斯时,故时号歙曰山越。及秦立鄣郡(故城在今湖州鄣山),彼土日辟。汪芒益有所逼迫,而不得不西窜于歙,居今绩溪境内(因其时,吴越皆开辟,惟歙县初立,可匿迹)。递嬗至孙吴,山越殆灭(孙权使贺齐讨黝歙,分为新都郡),而汪芒之裔,遂列于编氓,然其时当群聚绩溪也。及越国公华,起自澄源(绩溪乡名),保障六州,卒归命唐室,受国殊封,子姓济济,咸在朝列,由是而汪芒氏苗裔,日益繁衍遍歙郡矣。”[注](民国)陈去病:《五石脂》,载《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2~323页。针对汪道昆《太函集》称“吾宗得姓,自鲁颍川侯始。汉建安二年,龙骧将军讳文和为会稽令,始渡江南,于时郡新都而治始新。公迁始新,因而占籍。其后始新入歙州,公卒,与夫人孙合葬郡邵石山。胄子弭寇将军讳轸卒,与夫人李合葬都督山。后世附葬邵石山者墓二十五,附都督山者六,而公实江南汪氏始祖也”[注](明)汪道昆:《太函集》卷70《始祖龙骧将军墓域碑阴》,胡益民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451~1452页。,民国歙县学者许承尧以按语和引注的形式,认定汪氏源于徽州土著即山越人,云:“汪氏在歙占族为最古,以汉末时来也。汪注:先公考汪氏为新安土著,有《汪氏原姓篇》,非迁江南也。”[注](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汪氏迁江南始祖为汪文和》,李明回等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150页。
由此可见,宋至民国时期徽州知识和文化精英们所建构的三次中原地区世家大族南迁徽州故事和徽州人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并非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认知与认同。
二、族谱纂修与宗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建构
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以降,徽州社会逐渐成为一个聚族而居、相对稳定的宗族社会,“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注](清)程且硕:《春帆纪程》,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本。。作为宗族社会标志的族谱、祠堂和祖墓,在徽州更是屡屡重修,以致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点的徽州宗族文化。尤其是族谱,在宗族成员的心目中,更被视为“尊祖、敬宗、收族”的工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由于南宋以来徽州科第的勃兴和徽州人大规模外出经商与致富,大量徽商的资本和利润回流徽州本土,成为纂修和刊刻、印刷族谱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撑,“文人发起,商人助资”[注]民国《龙川胡氏支派宗谱》卷首章献琳《序》。亦因此成为徽州族谱纂修的基本模式。这是徽州族谱纂修能够始终保持绵延不断传统的智力支持和经济保障。而徽州本土以及周边地区发达的文房四宝业特别是造纸业和刻书业,又为徽州族谱的印刷和出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为宗族集体记忆和血缘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徽州的族谱纂修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尽管唐宋徽州族谱原本现已无一遗存,但我们依然可从宋代以来名人文集和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纂修的徽州族谱留存的序文中,了解徽州族谱纂修的一般情况。不过,与唐代官修和私纂族谱不同的是,创新和转型时期的宋元族谱,是在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官修谱牒废绝和唐末五代各类谱牒因战火而荡然无存等背景下兴起的,无论是纂修宗旨、形式、谱图之法,还是族谱内容和续修时间上,都因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特征[注]王鹤鸣:《宋代谱学的创新》,《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中国家谱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7~144页。。其纂修宗旨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区分士族门第、身份地望和婚姻仕宦,所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注](宋)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54页。,转变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注](宋)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8页。的“尊祖、敬宗、收族”,以及“序昭穆、别尊卑、严内外”的工具。在理学家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等的倡导下,宋元以至明清和民国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颁布《敕文武群臣修家谱诏》之后,徽州程氏宗族即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纂修了《程氏世录》[注](宋)程承议:《程氏世录序》,隆庆《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卷首。。随后,欧阳修和苏洵相继纂修了各自的族谱《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分别创造了“以线图系”的五世一提的谱图法和“以格列名”的谱法谱例。但不管是哪一种谱法和谱例,目的都是为了尊祖敬宗即尊尊亲亲、统宗收族。在他们的示范效应带动下,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的大姓名族纷纷掀起纂修族谱之风,“欧、苏二子亦尝作为家谱以统族属。由是,海内之士闻其风而兴起焉者,莫不家有祠以祀其先祖,族有谱以别其尊卑”[注](明)俞芳:《集成会通谱序》(弘治辛酉),弘治《新安黄氏会通谱》卷首。,徽州地区几乎每一个宗族都在此后至南宋时期,仿照欧、苏族谱体例,或融合两种修谱之法,各自纂修了本宗族的谱牒,不少宗族甚至连续性续修,徽州亦因此跃升为当时中国谱牒纂修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限于宋代徽州族谱无一遗存的现状,我们无法具体得知两宋时期徽州族谱纂修的总数,但根据程孟纂修的景泰《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等谱牒文献统计,宋代歙县槐塘,休宁县率滨、会里、汊口、芳干、山斗,婺源县长径、城东、城西冲山、龙首山、环溪、彰睦、龙陂,祁门县善和,黟县南山,绩溪县仁里等程氏宗族,总计纂修了15种族谱[注]景泰《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首《总目迁居地》。。又据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等谱牒统计,北宋仁宗嘉祐八年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063—1258),徽州各地方氏也先后纂修了11种各类谱牒[注]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各派族谱序跋记考》。。这些谱牒以尊祖敬宗、叙亲亲之道和重建宗法秩序为宗旨,从祖先的溯源和重构宗族谱系入手,初步建构起了徽州各大宗族人群的集体记忆。正如熙宁四年(1071)王汝舟在《庆源詹氏谱序》中所云:

以上文字,反映了北宋时期徽州关于祖先记忆建构和族谱纂修的基本状况。作为徽州地区现存最早一部郡志《新安志》的撰著者,罗愿在为本宗族纂修的歙县呈坎《罗氏宗谱》所作的序文中,亦以较大篇幅,对呈坎罗氏宗族祖源和谱系进行了详尽考证与阐述,从而完整地建构了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云:“新安城西四十里,曰歙呈坎,罗氏倚山环溪而居,族属蕃蔓,可无谱以志其源流乎?”于是,罗愿根据《世略》记载,不厌其烦地考订本族源流:始祖君用曾任武陵令,君用子珠世居长沙并辗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直至33世秋隐公和文昌公分别徙入呈坎,成为呈坎后罗和前罗的始迁祖[注](宋)罗愿:《罗氏宗谱序》,载(清)罗斗等《潨川足征录》卷7《序》。。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罗愿撰写的《罗氏宗谱序》对呈坎罗氏宗族的由来、迁徙及其宗族谱系等宗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尽管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订,但与其所撰备受赞誉的《新安志》相比,其中祖先学道等传说故事,显然是极不严谨的,这也反映两宋时期谱牒纂修者们在宗族谱系建构和集体记忆建构中普遍存在的通病。正如林济所言,宋元徽州谱系的构造,“体现了宋元时期徽州姓族企图在王朝历史中说明自身,在地方社会中展现其优越性与主导地位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包括族谱纂修者在内的徽州知识和文化精英,试图将虚构的宗族祖先与谱系传说故事历史化,并在历史化中使“神明祖先成为历史祖先”[注]林济:《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进而在宗族成员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认同,形成一种并非皆为历史真实的宗族集体记忆。
元朝是徽州族谱纂修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宋代业已纂修族谱的各大宗族继续修纂,以程氏宗族为例,元代续修或纂修了各种族谱达16种之多[注]景泰《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首《迁居郡地》。。徽州元代族谱尚有《新安胡氏历代报功图》《新安汪氏族谱》《新安旌城汪氏家录》和休宁县藤溪《陈氏谱略》等6种遗存至今。与两宋时期谱牒纂修宗旨、内容和形式的转型相比,元代徽州的族谱纂修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聚居徽州各地的程、汪等大族连续不断地纂修和续修各自的族谱,为跨地域的宗族联宗纂修统宗谱,扩张本族的势力范围,建构跨地域的血缘和身份认同创造了最基本条件。其中,纂修于泰定三年(1326)和后至元三年(1337)的《汪氏渊源录》与《新安王氏族谱》,即为具有了跨地域会通统宗谱性质的汪氏统宗谱雏形。也就是说,元代徽州宗族“一本”或“一气”观念为中心的血缘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进一步扩大,“君子修身,必本于孝,孝莫大于敬亲。自吾推而至于高、曾,同此一气,下而及乎曾、玄,传此一气也。……自高、曾至于吾身几世矣,由吾身而及乎曾、玄,又不知几世矣。传愈久,支愈远,厥宗纪系,此家谱所由作也”[注](元)舒:《素贞斋集》卷2《戴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577页。。但元代徽州族谱也更注重求真求实,对“妄取前代名公卿以为上世”的攀援现象多有批评。对此,著名理学家郑玉在《方氏族谱序》中即曾指出:“自宗法废,而先王所以睦族之意竟不可见,独赖谱系之存,世数犹可考也。然非大家宦姓,声势足以动其乡州、德泽足以及于后世者,则又不久而辄亡之。使其子孙服未尽而已为途人,岂不重可叹哉!予家来居西溪之上,今十二世,至以姓名其村,谱牒历历可考,坟墓无所遗失,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尚,而能保守不坏如此。余尝私自庆幸,以为积者深矣。及观方氏族谱,益有感焉。方在江南为大族,居睦、歙间尤盛,盖自真应黟侯在汉和帝时,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死而血食其地,故居其间者祖焉,以虚谷使君之博学多闻,亦自以为实其所出,是信不诬也。”[注](元)郑玉:《师山集·师山遗文》卷1《方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1217册,第70页。
在追溯和建构始祖或始迁祖及宗族血缘谱系的过程中,徽州各地的大姓望族内部往往会产生较大分歧,特别是程氏、汪氏、黄氏和胡氏宗族等大姓名族,在祖先及其谱系塑造和建构过程中不仅分歧较大,难以调和,个别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冲突与对立局面。唐代至北宋初,徽州程氏宗族大都以南朝梁陈时的程灵洗为始迁祖,而至北宋中叶以后,则逐渐虚拟建构出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这一历史人物,并将其作为徽州程氏的始迁祖。而汪氏的始祖也有汪芒氏和鲁成公支子之争,主张鲁成公支子者,其地望又有颍川和平阳之分。徽州黄氏宗族始迁祖,则有五代后梁时的黄叔宏和晋新安太守黄积之分。至于徽州胡氏始迁祖,也有东晋新安太守胡焱和唐末五代常侍胡与明经胡之分[注]参见冯剑辉《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以程氏宗族为例,徽州程氏宗族在祖先谱系的建构过程中,充满着分歧、矛盾、对立与冲突。除对始迁祖程元谭形象建构中引发的冲突[注]陈雪明、卞利:《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和程敏政因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引起几乎所有徽州程氏宗族的挞伐外,较大一次对立与冲突发生在明代中叶著名学者、《新安学系录》著者、休宁县富溪人程曈与同属休宁的汊口程氏支族之间。冲突缘起于程曈对汊口程梦龙(即程九桥)撰修之《十万公辨》提出不同意见,程曈认为:
伏读大笔集《十万公辨》,仰见大人编辑之有序,取舍之攸当,健羡健羡。但仆深山野人,见闻寡陋,惟知寻源究本以为心,不识事大畏天之当谨,谬曰吾家十万公与君家所谓十万公,其号虽同,而其实则不同也。吾家十万公讳渝,生于唐末,则勿斋撰《德秀行状》曰居汊口,号四门程;迁闵川,号十万程,有十万公墓在焉是也。君家之所谓十万公讳绪,生于宋,则勿斋撰《举胶楼记》曰居汊川,号四门;迁闵口,号十万;迁西郢,号京山大家者是也。[注](明)程曈:《新安学系录》卷末附录一《与九桥程秀才求免死书》,王国良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306~307页。
程曈对汊口程氏支族声称系十万公后裔的观点提出质疑,原本是出于一个学者严谨求实的考量,至于结论是否正确,程曈并无十分把握。于是,他诚恳地向率口族人程应征求证,并拟择机登门讨教于程梦龙。不料程应征擅自将程曈的意见转达于汊口程氏支族,致使程梦龙及叔父程记堂暨汊口程氏支族头面人物数十人大发雷霆,痛斥程曈之罪,并唤程曈族弟程新庭至汊口,当面持戟而叱之曰:“尔兄程象甚无道理,不识高下,乃敢驳我《十万公辨》。今当伺其出入,拦截之,羁絷之,羞辱之。一曰拔其髯,挞其背;一曰幽囚之,绝其食,使不毙于吾人之手不信也。”在汊口程氏支族的威胁与恫吓下,程曈自知惹下大祸,惊恐万分,遂修书自责,四处求饶。在托其亲、程梦龙之舅吴斯望转交的《与九桥程秀才求免死书》中,程曈心惊胆战向程梦龙自责和求饶道:
仆不胜恐惧股栗,心掉而胆落魂飞也屡日矣。于是反躬自省,徒知寻源究本以为心,实犯事大畏天之不谨,妄肆评论,委涉唐突,罪当万死,虽粉骨碎身,不足以息大人先生雷霆之怒,而逭大人先生斧钺之诛也。仆伏惟圣门有见过自讼之叹,国律有自首免罪之条。仆愿至今伊始,钤口结舌,不敢胶柱鼓瑟,复论是非,而惟尊辨之是从。曰吾祖可也,吾祖可也;曰非吾祖也实吾祖也,亦可也。伏望大人先生及令叔列位察仆自首之诚,钦遵朝廷之法,容仆肉袒负荆,诣门请罪,赦以不死,并存髭须,使他日全归得以见先人于地下,以免不孝之名,则感大人先生及令叔记堂太朝奉列位更生之慈无穷,亦可以为世之不量时势、胶柱鼓瑟、妄评是非以取辱身羞亲之患如仆者之戒也。万一仆罪重责轻,不足以息列位之怒,则仆二男一孙能负薪矣,可不能各分父祖之责哉,亦愿骈首而延颈阶下也。[注](明)程曈:《新安学系录》卷末附录一《与九桥程秀才求免死书》,王国良等点校,第307~308页。
接着,程曈继续致函程应征和孙云汀,或恳请免死,或求其从中斡旋[注](明)程曈:《新安学系录》卷末附录一《与海山程解元求救死书》《与孙云汀秀才光宇求救死书》,王国良等点校,第311~314页、315~323页。,其情其状,足见一位文弱学者在面对同族死亡威胁时的绝望无助与惶恐畏惧。程梦龙在托其舅吴斯望转答程曈的《九桥答吴斯望书》中,却对程曈的学问赞誉有加,承诺不会对其加害,但仍强调汊口程氏支族谱系建构的正确性,力斥程曈认十万公为祖之非:
今年族众以别派妄认吾祖十万公,编刻诗序,布满四方,虽曰蝉鸣蛙闹,诚恐以伪乱真。乃汇吾族先达英贤相传序记派系有关十万公者,集为一帙,以告宗亲高明,剖析真伪。……及《谱辨》刊出,散吾各派宗彦,海山观之,谓是辨虽某旧闻,实足为统宗羽翼,沮抑杂伪,特书叙其首,此固吾族幸也。不意吾宗望如令亲莪山先生者,乃不满其说而条加辩驳,故吾族众情汹汹不愤。令亲来谕书云各有十万公,吾族之所集,实宋十万公绪,固吾祖也;令亲所谓十万公渝,是令亲祖也。彼此既无相关,令亲宏博之学岂无他用,而顾屑屑吾祖辨?是驳焉,吾尝闻诸父老,令亲祖荣公葬古墓山,炳公始迁富溪。其十二世孙常元季编本宗谱,历历可考。荣乃杭公之弟,今又认十万公为祖,是如一人而认二父矣。曾谓博稽远照、究本穷源者,顾无定主若是耶?年湮世远,以伪为真,妄续宗系,……不顾本祖而妄冒之者,天下皆是也,吾果盍与之深辩邪正是非真伪杂错?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亡;四乡之传闻者,未之泯。用夏变夷,下乔入谷,惟令亲之惕然自省与夫自处何如耳?妄肆言以招祸,窃为令亲不取也。各祖其祖,又何以事为哉?若夫族众对某云云,及族众人人怀愤,疾邪害正,恶伪乱真,梦龙虽不敢必其尽无,而解怨释纷,梦龙可任其无咎。兹非他也,以斯文故也。令亲过往山乡,决不必虑。[注](明)程曈:《新安学系录》卷末附录一《九桥答吴斯望书》,王国良等点校,第308~310页。
以程曈为代表的富溪程氏和以程梦龙为代表的汊口程氏,在本支族祖先程十万公归属与何为正宗问题上,始于程曈之谱辨,终于程曈之认错求饶。徽州程氏宗族在程敏政之后,再次出现因学者求真而被攻击甚至遭到剥夺生命的威胁,这既是学者的悲哀,更是徽州宗族祖先谱系建构中血缘身份认同彻底战胜历史事实的集中反映。
三、跨地域统宗谱的修纂与血缘身份认同的扩大
延至明代中叶,随着徽州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富甲一方的徽商达到巅峰状态和科第教育的勃兴,无论在体例还是在内容上,徽州谱牒的纂修都进入一个更加完备和成熟阶段,不仅跨地域的单一姓氏的宗族血缘会通统宗谱纂修活动更加普及和频繁,而且还出现了跨地域的非血缘的徽州地域大姓名族谱,如嘉靖《新安名族志》和天启《休宁名族志》。在徽州各地,几乎每一个大姓名族都纂修出了各自的跨地域统宗谱。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祁门县王氏宗族即纂修并刊刻了《王氏统宗谱》[注](明)戴廷明、程尚宽等辑:《新安名族志》后卷《王》,朱万曙等点校,第568页。。至景泰二年(1451)、成化十八年(1482),程孟和程敏政各自完成跨地域程姓会通谱与统宗谱的纂修及刊刻。
有关会通谱和统宗谱概念之内涵,实际上是自宋代以来就已不断被强调的“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等“一本”观念之延续与扩大,是血缘身份扩大化的又一集中体现。鲍宁在景泰二年(1451)为程孟纂修的《新安程氏诸谱会通》所撰的序文中,对“会通”概念与会通谱的功能作了解释,云:“会者,会其源,万殊而归一本也;通者,通其派,一本而达之万殊。挈其要于前,诸谱之名公贤士、义夫节妇咸表而出之,仰而可法也;详其目于后,各谱之分支衍派、亲疏远近备述不遗,可考而可念也。呜呼!观是谱者,当知其规模之宏大,又当知其取舍之谨严,而于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忽者,人伦之明,风俗之厚,又岂不由于是乎?”[注]景泰《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首《序》。
统宗谱的纂修,一方面是出于跨地域联宗、扩大宗族血缘身份认同的需要,所谓“支则有本,继则有别,类则有秩,氏则有族姓,裔则有始,迁则有止,往则有归,涣则有敦,谱则有系,异则有统,附则有革,诬则有征,纵则有黜。夫岂谓人贤胥族贤,人贵胥族贵哉?贤若贵非族,以则同族,得民敬宗追祖,是谱其绪邪”[注]万历《三田李氏统宗谱》卷首《自序》。。另一方面也有纠正各地宗族在始祖或始迁祖以及祖先谱系建构中的讹误混乱,进而统一宗族思想、强化宗族控制的目的。就此而言,会通谱或统宗谱的纂修依然是“万世一身”“万殊一本”和“一气”观念的延续与发展,“谱牒之作,所以究一本之源也。夫一气之传而至于千万世,一身之传而至于千万人,非由谱牒以纪载,则一本之源又何所从而究哉?”[注]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历代谱牒序》。而纠谬订讹、统一各支族关于祖先及谱系建构中的口径,则正是程敏政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主要目的之所在。为此,程敏政以“谱系有异同者,有舛误者,悉以历代诸谱参较,不专主旧说,蹈因袭之弊;不自出意见,取傅会之讥。同者书之,正其舛;误者书之,否则辟之”[注]成化《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卷首《凡例》。为凡例之一,针对被各地程氏宗族遵奉的程祈和程孟撰修的《程氏世谱》和《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等谱中存在的舛误和作伪,程敏政以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积之二十年理淆伐舛”,撰写37条《谱辨》,如“辨祈谱世次自周秦迄五代了无一阙可疑”、“辨祈谱不知程氏初迁江南出吴都亭侯普之后误据《元和姓纂》以为出魏安乡侯昱欧阳文忠公碑铭亦从其误”、“辨祈谱书新安太守元谭以下世次绝与陈留谱不同及书忠壮公二十二子可疑”等[注]成化《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卷首《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辨》。,皆以有力的证据,力辩其非,并以程元谭为徽州程氏始迁祖,重新建构起庞大的程氏宗族主干谱系。尽管程敏政的《谱辨》论据翔实有力,但对已经接受了程祈等建构的祖先谱系和身份认同之徽州各地程氏宗族而言,在情感和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程敏政推翻程祈和程孟而重构的几乎颠覆性的徽州程氏谱系,最终导致徽州各地程氏宗族群起而围攻之的命运。尤其是程顼纂修并刊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的《新安程氏统宗列派迁徙注脚纂》,综合徽州各地程氏宗族所撰族谱对程敏政的批判,集中火力,以《辨说》八章即八个专题的方式,对程敏政纂修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进行激烈的驳斥与批判。在《统宗讹谬说章并序》中,程顼云:“《统宗[谱]》讹谬,序谱略见。若匪详悉,曷兑来议?外著《辨说》八章,用悉所以。或曰:‘续谱而讼先正之非,无乃不可乎?’曰:‘子昧矣。谱者,家乘实录,昭孝之书,圣人述经,不刊之典,毫有讹谬,污辱宗君,有杀无赦。知而蹈舛承讹,比之同科。且季世贵,贵崇名。是非不辨,《统宗[谱]》一行,大泽波颓,孰之能遏?虽有富溪莪山公之辨、龙山秋山公之议与檄,言之不行,不言何异?是故用说以弁篇端,的然从旧,而不敢从新,从是而不敢从非也,庶几哉。程氏有志氏族君子,不妨探讨二公辨议与檄,及顼所著者,增其所未备,遍告诸族,正其讹而续其支,宁不为统宗之幸,冰释后生贵、贵崇名之惑乎?’或人唯唯。”[注]嘉靖《新安程氏统宗列派迁徙注脚纂》卷首《统宗讹谬说章并序》。
从以程氏为中心的徽州宗族会通谱或统宗谱纂修宗旨、目的及纂修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宗族集体记忆和血缘身份认同中,情感和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远远超过历史真实的面目。正如常建华所云:“尽管新安程氏尊重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注]常建华:《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河北学刊》2005年第11期。
继明代嘉靖、万历徽州出现纂修统宗谱的高峰之后,至清代乾隆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和徽商的重新崛起与繁荣,徽州再度掀起续修统宗谱的热潮,诸如程氏、汪氏、琅琊王氏、济阳江氏、歙淳方氏、考川胡氏、甲道张氏等,又在明代基础上,分别续修了各自宗族的统宗谱。直至民国时期,徽州纂修统宗谱的热度依然持续不减,其中尤以江峰青联合族人,于1915年开局并历时三年纂修完成的《济阳江氏统宗谱》规模最为宏伟。这部总篇幅达80卷(不含首1卷)、刊刻装订成68巨册的《济阳江氏统宗谱》,不仅将徽州六县济阳江氏宗族悉数收入卷内,而且还跨省收录了江苏、浙江、江西和河南等地区的江氏支派的谱系,堪称一部具有全国性质的济阳江氏统宗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济阳江氏统宗谱》是在清朝统治政权瓦解、民国建立后不久、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新思想和旧观念交织的背景下纂修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正如江峰青为该谱局撰写的《甲寅邀集各派启》中所言:“我《江氏统宗谱》自同治戊辰续修后,迄今将五十年。其间,生齿蕃殖,人事变迁,又中更患难,世界改造,国是未定,礼教不修,社会无彰瘅之公,学子慕欧美之化,自由、平等之说,嗜之所脍炙;伦敦、纪饬之训,弃之如弁髦。所赖搢绅之家明长幼、别疏戚,始之于彝伦之叙,推之为比邻之洽,广之即大同之象,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然则敬宗收族之所关,岂细故哉?然则我江氏宗谱之续修又岂可缓哉?”[注]民国《济阳江氏统宗谱》卷80《杂志二·甲寅邀集各派启》。显然,由亡清进士、授荣禄大夫、召试经济特科、诏举硕学通儒、赏花翎二品顶戴一品封典政务处记名、奏充宪政馆咨议官,民国改元后任江西全省审判庭臣的江峰青发起和主持的规模庞大的《济阳江氏统宗谱》纂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依然坚持以敬宗收族为宗旨,并希冀通过对跨地域济阳江氏各地各派宗族的整合与血缘身份认同,来达到对抗新时代新思想的目的。可见,徽州统宗谱纂修和木本水源等血缘身份认同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平心而论,徽州跨地域的统宗谱纂修,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自元代开始,包括汪氏等大族相继完成了部分统宗谱的纂修。明代徽州的统宗谱纂修一度达到繁荣的巅峰,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徽州各大宗族充分利用自身的权力、身份、地位和财富等优势与人脉资源,纷纷投入本宗族统宗谱的组织与纂修之中,相继纂修并刊刻了跨越地域、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统宗谱,这其中尤以汪湘纂修、汪同文增修、隆庆四年(1570)刊刻的172卷本《汪氏统宗谱》篇帙为最。清乾隆时再度崛起的统宗谱,使得徽州大部分大姓望族又一次纂修了数量和规模庞大的统宗谱。因此,与其说这类会通谱或统宗谱的纂修是徽州宗族集体记忆和血缘身份认同在地域上不断强化扩张的产物,毋宁说是其宗族统合与控制扩张的结果。事实上,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在数次统宗谱纂修高潮中编纂和刊刻的统宗谱,不少都已超越了徽州地域的边界,成为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单一姓氏名门望族谱。也就是说,徽州宗族通过规模庞大、耗资不菲的统宗谱或会通谱的纂修与刊刻,进一步扩大了同姓同祖宗族谱系的建构,扩展和完善了本宗族的集体记忆,使得宗族血缘身份认同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内得到了有效拓展,从而强化了宗族与地方甚至中央权力的结合,加强了对宗族成员的控制。
四、结 语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知识和文化精英逐渐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从族谱纂修和中原祖先谱系拟构等不同视角,持续不断地致力于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并将其与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相连接,进而实现血缘身份认同、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目的。然而,在建构和强化徽州宗族祖源和谱系的血缘身份认同过程中,徽州知识和文化精英甚至采取了罔顾事实、攀富援贵、粗制滥造等手段,置历史事实于不顾,从而导致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撕裂,造成严重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超越于历史真实性的文化认知,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也许更加具有历史与文化的永恒价值。”[注]陈支平:《跨越地域与历史的界限来重新审视黄河文明的文化意义——以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关联性为例证》,《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