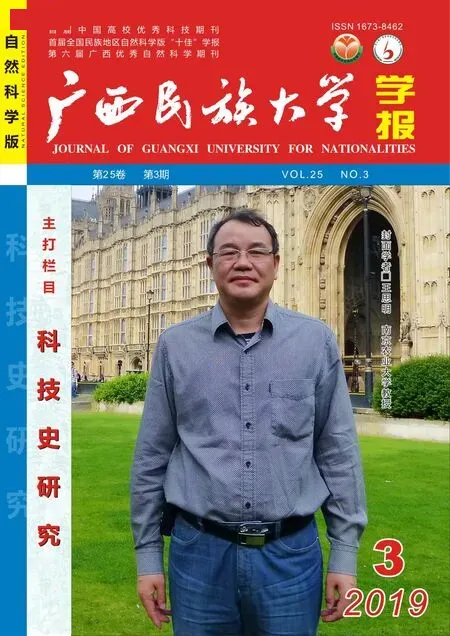汇校《九章算术》与李学勤先生*
郭书春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49)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不幸去世,我无比悲痛,立即向李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出唁电,其中说:
近40年来,我在《九章算术》版本与校勘的研究中,一直得到李先生的帮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利用与先生同住劲松三区311楼的机会,经常不揣冒昧,登门向李先生求教,大到版本与校勘的基本知识,小到一些古代字词的训解,他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诲人不倦,使我受益无穷.我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汇校《九章算术》”,[1]便是李先生提议、命名并亲自为之撰跋,予以推介.想到李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感到温暖!
在这里,我特别记述李先生在汇校《九章算术》的撰著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1 汇校《九章算术》的缘起
我是数学系出身,文史知识先天不足.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只能是边干边学.到1983年,我尽管从事《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研究已经几年了,但从未想到全面校勘《九章算术》.1982年底,我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林力娜(Karine Chemla)在中法科学合作框架内制定中法对照《九章算术》[2]的研究计划时,还明确说明以钱宝琮的校点《九章算术》(下称钱校本)[3]为底本.1983年春,严敦杰先生(1917-1988)建议我看看研究所图书馆善本库所藏清屈曾发刻豫簪堂本《九章算术》.钱老提到过这个版本,说它是微波榭本的翻刻本.待我看了豫簪堂本,发现其体例与微波榭本不同,不可能是后者的翻刻本.因而觉得钱老在版本研究上也不是尽善尽美.笔者有一癖好,发现问题后就想穷追到底,便开始一方面学习古籍版本知识,一方面以钱校本为参照,校雠了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九章算术》各种不同的版本,发现了若干重大问题.当时,我和李先生同住劲松三区311楼,什么时候与李先生相识,最初向他请教什么问题,已记不得了,应该是向他请教版本和校勘问题.1984年夏,我撰成《评戴震对<九章算术>的整理和校勘》[4]一文,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外和日本数学史代表团访华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几次报告,反响相当好.当年秋,我将此文呈吴文俊、严敦杰、李学勤、李仲钧等先生审阅.吴先生于1984年11月11日复示笔者,表示十分赞同“文末提出校勘工作方法的许多看法”,说“应该向你学习”(每个字下加了小圆圈),并“希望能发表你关于这几种版本不同处的全部对照表”.可是,《九章算术》各版本的差异太多了,得有上千条,如何发表这些版本不同处的全部对照表,我犯了难.考虑了几天,不得其法,便去请教李学勤先生.李先生说:“你可以做汇校.”我读过三会本(会校、会评、会注)《聊斋志异》,我以为是“会校”.李先生拿出纸来,写了“匯校”两个字,又写了“會校”两个字,说:“你要用‘匯校’,不要用‘會校’.”对什么是汇校,他解释说:选定一个底本,保留底本的文字,将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写入校勘记.但是我从未想过全面校勘《九章算术》,李先生看出我有畏难情绪,便鼓励我说:边做边学吧!我表示考虑一下.想来想去,不用李先生说的“汇校”,没有别的办法不辜负吴先生的希望.而且,我《评戴震关于〈九章算术〉整理和校勘》一文,已经得出自戴震整理《九章算术》的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210年间《九章算术》的版本十分混乱,《九章算术》必须重校的结论.同时,研究《九章算术》版本和校勘的这几年也试着做了某些校勘,纠正了戴震、李潢、钱宝琮的若干错校,得到李学勤先生的首肯.考虑再三,决定遵从李先生的指点,对《九章算术》做汇校.
2 李先生为汇校《九章算术》撰跋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我开始琢磨怎么汇校.首先是底本的选取.由于没有一部完整的未经戴震及后人改窜的《九章算术》传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存《九章算术》各版本中,南宋鲍澣之刻《九章算经》最早且错讹最少,然阙后四卷及刘徽序;四库本、武英殿聚珍版以及豫簪堂本、微波榭本、钱校本虽完整,但都含有戴震辑录的不少疏漏、修辞性加工及若干错校,不适宜作底本.考虑再三,只好取‘百衲本’的形式.卷一-卷五以南宋本为底本,后四卷和刘徽序采用由四库本与聚珍版对校而成的大典辑录本作底本,取两者的相同部分以及两者不同择善而从者,还有戴震按语改意见和问题.对书稿中的问题,他善于循循善诱,比如对天禄琳琅本的母本汲古阁本,我在“导言”初稿中写有“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李先生问:“你到故宫博物院看过吗?”我说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钱老书中说的.”李先生说:“那你应该写‘据钱校本说’.”回来之后我感到李先生话中有话,想再请教问题时问问.真巧,第二天收到台湾朋友寄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善本书目,其中有汲古阁本.从此,我的著述中凡是谈到我没有亲历亲见的事,都遵循李先生的教诲,说明出处.
因为我当时只是个助研,汇校《九章算术》的出版到处碰壁.最后由辽宁师范大学梁宗巨教授推荐,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拍板出版.我看到李先生对汇校《九章算术》的书稿基本满意,就冒昧提出请他为拙作撰跋,他欣然同意.他在1987年11月撰写的跋中写道:
研究《九章算术》,关键是好的本子,而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繁杂.郭书春同志对《九章》研究有年,以科学的态度,绵密的功夫,将书中多少世代积存的种种疑难,逐次梳理清楚,实在是《九章》研究的一大贡献.他的这部汇校本,确能订正异同,使读者如校雠家所说‘读此一本,无异遍读各本’,成为《九章算术》最佳本子,也给今后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蒙郭书春同志不弃,在撰着汇校本过程中,不时以其心得见示,我也有幸成此书最早读者之一.现在他要我在书末略缀数语,我深愿趁此向读者作一推荐.[5]
此时李先生已从劲松搬到昌运宫,李先生的跋实际上是对我的鞭策.中所录出的原文,以及李潢所说的几条大典本原文.我向李先生汇报了这种想法,他表示赞同.根据李先生保留底本原文的指示,我决定采用我国校勘学的传统做法:将原文中的舛误文字置于圆括号中,将校勘文字置于方括号中.同时,继续寻找、校雠《九章算术》的各种版本,特别在南京博物院发现了乾隆御览本聚珍版.到1986年完成了汇校《九章算术》初稿,以钱校本为参照,恢复被戴震、李潢、钱宝琮等学者改错的南宋本、大典本不误原文450余条,使用戴震校勘近120条,李潢、钱宝琮校勘共近140条,其余诸家近30条.重校前人校勘失当文字近70条,新校前人漏校文字近40条,存疑20余条.共得校勘记1720余条.
李先生对我的书稿审阅非常认真,提出了若干修
3 李先生为我释疑解惑
在我《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研究中李先生释疑解惑之处,不胜枚举.在此仅举几个例子.
3.1 关于《九章算术》编纂的争论
关于《九章算术》的编纂,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现有资料中最早谈到《九章算术》编纂的是三国魏时期刘徽.他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筭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6]清戴震否定刘徽的说法,他说:“今考书内有长安、上林之名.上林苑在武帝时,苍在汉初,何缘预载?知述是书者,在西汉中叶后矣.”[7]近人钱宝琮发现汉高祖时便有上林苑,推翻了“上林苑在武帝时”的论据①实际上,秦始皇时便有上林苑.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却把《九章算术》的成书推得更晚.他说:“它的编纂年代大约是在东汉初期.”[8]这种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我在研究刘徽的过程中,发现刘徽具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高贵品质,他对编纂《九章算术》这样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资料,绝不可能信口开河.我向李学勤先生谈了我的看法,他很赞同,也批评了学术界的“疑古”倾向.不久,他在为汇校《九章算术》写的跋中又说:
由于有了近年来整理大量战国秦汉简帛书籍的经验,我们认识到绝大多数古籍都不是一下子写定的.除了少数经籍有官本外,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九章算术》的源流,魏人刘徽已经作了可信的叙述.他所说《九章》本于《周礼》记载的九数,和汉末郑玄《周礼注》之说相合,而郑玄又继承着刘歆以来《周礼》家的传统.至于说汉代张苍、耿寿昌等根据旧文遗残,进行删补,更符合古籍形成过程的规律.刘徽的说法一定师传有自,综合了秦汉以来的成说.
西汉时已有传习《九章算术》的学者.《汉书·艺文志》著录《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据《广韵》载汉许商、杜忠、吴陈炽、魏王粲善《九章》术,证明许、杜所为即是《九章》术,并非别为一书.所谓《许商算术》《杜忠算术》,犹如《毛诗》《左氏春秋》之类,只是推衍《九章算术》的两家作品.
1983年12月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出土,有人根据《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说,说《算数书》是《九章算术》的前身,我不同意.又有人说张家山汉墓是张苍墓,并刊登在某大报显著位置,研究所有人打电话问我的看法,我说是无稽之谈.为慎重起见,我又给李先生电话.李先生的回答很风趣:“郭先生,有人说地心里有火,我们当然相信,因为我们知道火山爆发,会喷出火来.如果有人说地心里有馅饼,我们能信吗?”我们在电话两端都大笑起来.不久,吴文俊先生将他的一部关于机器证明的书稿寄给我,要我看看.其前言初稿中采用了张家山汉墓是张苍墓的说法.我当即去信谈了我的看法.吴先生回信表示已将那几句话删去.又一次我去拜访吴先生.吴先生说那位先生说他的看法很难驳倒.我向吴先生转述了李先生“地心里有馅饼”的比喻,吴先生也大笑起来.
3.2 关于“方程”的释义
中国古代的“方程”就是现今的线性方程组,其“方程术”即线性方程组解法,“损益术”即移项列方程的方法,“正负术”即正负数加减法则,是《九章算术》的最高成就,超前其他文化传统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可是关于“方程”的本义,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刘徽说:
程,课程也.群物总杂,各列有数,总言其实.令每行为率,二物者再程,三物者三程,皆如物数程之,并列为行,故谓之方程.行之左右无所同存,且为有所据而言耳.[9]
唐李籍说:“方者,左右也.程者,课率也.左右课率,总统羣物,故曰方程.”[10]北宋贾宪说:“谓方者,数之形也.程者,量度之总名.”[11]明程大位说:“方,正也.程,数也.”[12]清梅文鼎说:“方,比方也;程,法程也;程,课也.数有难知者,据现在之数以比方而课程之,则不可知而知.”[13]近人钱宝琮说:“联立一次方程组各项未知数的系数用算筹表示时有如方阵,所以叫作‘方程’.”[14]
我在研究了刘徽关于率的理论[15]之后,认为刘徽“是把方程的每一行都作为一个整体,看成率”.“每行中,未知数系数和常数项的排列都有确定的顺序,就是说有方向性,应该说,它与今天方程组理论中行向量概念有某种类似之处”.进而认为刘徽对方程的理解实际上是将一个个带有方向性的数量关系并列起来,形成方程.因而认为这些看法中,只有刘徽最正确.明朝之后的理解,都偏离了方程的本义,而且有去古愈远,偏颇愈大的趋势.但是,我们一看到“方”,就想到数学上的正方形,或人品的正直,无法将“方”与“并”联系起来.我就这个问题请教李先生.李先生说:“方”的本义就是并.许慎《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像两舟,省总头形.”李先生陆续给我举了《诗经·汉广》《国语·齐语》《仪礼·乡射礼》等先秦古籍中使用“方”的例子,都表明“方”就是指用竹木合编成的筏,引申为并.根据李先生的教诲,我认识到,方程就是“并而程之”,刘徽关于方程的论述完全符合《九章算术》“方程”的本义.
3.3 关于“知”的训解
《九章算术》刘徽注和李淳风等注释中有许多“远而通体知”“近而殊形知”“凡所得率知”“合分知”之类的句型,在聚珍版、四库本中,戴震未作改动,然而在屈刻本、孔刻本中戴震开始将其中有的‘知’改作‘者’,后人又续有改动.钱校本则将这类“知”字连下读.对这些改动及钱老的句读,我总觉得有问题,便请教李学勤先生.与以往不同,李先生没有立即回答我.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认为这类句型中的“知”均应训“者”,不误,戴震等人的改动是没有必要的.古籍中“者”与“之”互训,用作指事之词.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九:“‘者’犹‘之’也.”又:“‘之’犹‘者’也.”自注:“‘之’与‘者’一声之转.故本书‘之’、‘者’互训.”而“知”作为语词,则与“之”相通.裴书卷六:“‘知’犹‘之’也.语助也.”故“知”也可用作指事之词,与“者”同义.接着,李先生列举了先秦典籍中的“之”、“者”互训,“知”与“之”相通,“知”与“者”同义的大量例句.李先生进而指出:乾嘉以来,古文大师未谈及“知”可训“者”,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九章算术》.李先生的教诲不仅使我拨云见日,解除了几年来的纠结,也解决了数学史界多年的疑惑.由此我想到,几年来我疑惑的传本刘徽注、李淳风等注释中以“知”结尾的句型时有作“者”者,而李籍《音义》引刘徽注、李淳风等注释同样的句子,均作“者”,实际上这些都可作为“知”、“者”同义的佐证.同时我由这类“知”训“者”,及古人读书常旁注同音同义词,而旁注的字常被后人衍入原字之上方,进而想到,传本刘徽若干以“者知”结尾的句型,如刘徽序中“故枝条虽分而同本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卷一减分术刘徽注“母互乘子者知,以齐其子也;以少减多者知,齐,故可相减也”,等等.“者”皆系后人注“知”字之音义,阑入正文.同时认识到,钱校本于“知”字上句读,“知”字连下读,是不妥的.我向李先生汇报这些想法,都得到他的首肯.
上面记述了李学勤先生对我帮助的几件事,是挂一漏万.社会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文史专家对理工科比较隔膜,而向李先生请教的过程中,他对《九章算术》的了解程度,使我吃惊.几十年来,我深深感到,他确实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追忆李先生的教诲,鞭策自己,在耄耋之年继续做好《九章算术》和中国数学史研究,为弘扬中华传统文明尽绵薄之力,是对李先生最好的纪念.
2019年3月20日于华严北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