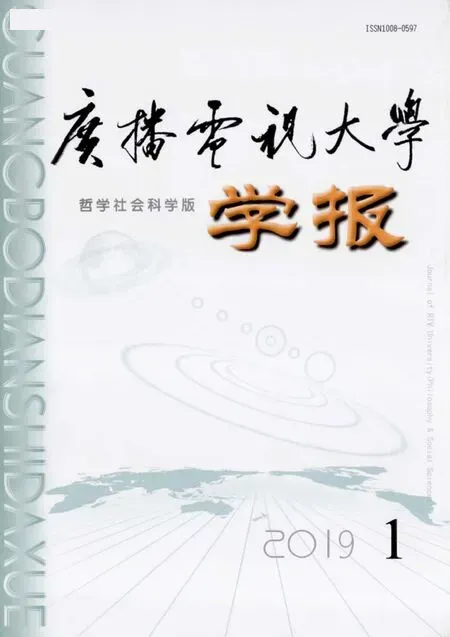象征主义诗歌写作的“暗示”手法
李文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象征主义是19世纪欧洲出现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文学观念特别是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突破可谓是颠覆性的。“象征”一词原本是指古希腊语里的一种木制的“信物”,将其一分为二,由誓约的双方各执一半,以为证明。由此引申出“象征”主义的文学观,即主客观世界的融合。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其 《应和》的诗中最先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自然是一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你注视。……”[1]P13在波德莱尔看来,人和自然是可以沟通的,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一体——客观的世界需要人的主观世界去发现,而人的主观世界,则是通过客观世界折射出来的。“自然”就仿佛一座“神庙”,这庙里的每一根柱子都是“活的”,都是充满着灵性的“象征的森林”,他们说出的模模糊糊的“话音”,和那“注视”你的“熟识的目光”,都可能是“神”的“暗示”。后来,这种“暗示”的观点,在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几位代表性诗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兰波提出了“通灵”论,主张诗人要去做“通灵人”;魏尔伦则强调诗的音乐性,极力剔除诗歌语言的所指性特征,通过突出语言的“韵律感”,去带给读者暗示;马拉美更是提出“纯诗”的概念,希望直接将诗歌作为主客观世界的“融合点”,呈现给读者。
其实,“暗示”作为一种手法,目的在于引发读者的想象,然而这并不是从象征主义诗歌才开始出现的,也并非为西方诗歌所独有。欧洲十九世纪前期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也曾普遍追求创作上的主观想象,而中国古代如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中那些朦朦胧胧的诗句也就是一种“暗示”的写法,但正如广义宽泛的“象征”,与象征主义的“象征”内涵不同,需要认真的界定、廓清。
象征主义的“象征”是有其哲学观念作为理论基础的。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主观世界的“投射物”, 强调直观高于理性,对于事物的本质性认识只能靠非理性的“直觉”“顿悟”的方法。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万物的本质归于“生存意志”,认为摆脱生存痛苦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在艺术活动(包括创作和欣赏)中通过“沉醉”的办法,来摆脱生存“意志”的困扰,从而达到暂时地远离痛苦;一个则是在宗教信仰中通过修炼而永久地摆脱生存的痛苦。而无论是“艺术活动”还是“宗教修炼”,都必须通过主观精神的“顿悟”来完成。尼采深受叔本华启发,却在其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权力意志”的概念,认为应该张扬“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通过释放“生命热情”,直抵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的深处,完成“生命的狂欢”。他说:“日神状态,酒神状态。艺术本身就像一种自然的强力一样,借这两种状态表现在人身上,支配着他,不管他是否愿意;或作为驱向幻觉之迫力,或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这两种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表现,只是比较弱些;在梦中,在醉中。但是,即使在梦和醉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对比,两者都在我们身上释放艺术的强力,各自所释放的却不相同:梦释放视觉、联想、诗意的强力,醉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的强力。”[2]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把万物的本质看作一场生命流动的过程,提出了“生命之流”(绵延)的概念,他说:“绵延是不可逆转之流。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实体。”[3]他认为通过神秘的“直觉”体验,人类在回忆与畅想中就可以抵达“绵延”的世界:“一种感觉,仅仅由于它被一直延长下去,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而成为不可忍受的。在这里,同一件东西不会始终不变,它被它的整个过去所加强和增大。简言之,机械学所谓的物质点永远处于现在这一刹那;但就一般生物而论,过去也许是真实的,就有意识的人类而论,则过去确实是真实的。……既然这样,如果有人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意识力或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认为这种力或意志受着时间的影响,并把绵延储藏起来,从而也不必遵守能量守恒律,那么这种假设难道不是有许多可取的地方吗?”[4]据此,象征主义的诗人和理论家们提出了文学上的“契合”理论,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交融。即是说诗人应该像巫师一般,在其诗中运用暗示的手法,去启发读者的想象力,从而带他们进入那神秘的彼岸世界,达到主客观世界的“契合”,如我国唐代诗人柳宗元所说的“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波德莱尔曾说:“想象力不是幻想,想象力也不是感受力,尽管难以设想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不是一个富有感受力的人。想象力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思辨的方法而首先察觉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应和的关系,相似的关系。”[1]P117显然,波德莱尔在这里把想象力看作一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直觉”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才真正沟通了“主观”和“客观”两个世界,使其融合。他坚定地说:“想象是真实的王后。”[1]P118于是,这派诗人们开始以瞬间的、模糊的、神秘的、直觉的“象征”,作为感知世界的方式,把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作为目的,表达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
那么,象征主义的诗歌是怎样进行“暗示”的呢?我们先来看波德莱尔的一首诗:
当低重的天空如大盖般压住
被长久的厌倦折磨着的精神;
当环抱着的天际向我们射出
比夜还要愁惨的黑色的黎明;
当大地变成一间潮湿的牢房,
在那里啊,希望如蝙蝠般飞去,
冲着墙壁鼓动着胆怯的翅膀,
又把脑袋向朽坏的屋顶撞击;
……
——送葬的长列,无鼓声也无音乐,
在我的灵魂里缓缓行进,希望
被打败,在哭泣,而暴虐的焦灼
在我低垂的头顶把黑旗插上。
《忧郁之四》[1]P96
这首诗的内容是诗人在诉说他忧郁的内心,如果按照传统诗的写法,很可能就是写实性的直接表达,诸如“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对愁情的抒发,在此已堪称“绝唱”,尽管是弦外有音,余音袅袅,但基本上还算是直接抒发出来的。或者如李煜的比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虽然有了“形象化”,而且也是化抽象为具象,比喻堪称精妙绝伦。但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表面化的,在现代主义诗人们看来仍算是“近取譬”。李煜的这首词表达“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所带来的无限“愁、恨”,文中大部分还是以写实的方法来表现其感情的,只是在最后一句中用了这样的比喻作为点睛之笔,形容其“愁与恨”的无边无际,贴切自然,形象生动,成为千古经典。
我们还可以将波德莱尔这首诗与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两首同样表达内心忧郁的诗比较一下:
…… ……
让琴曲的旋律深沉而激越,
欢快的调门请暂且躲开,
乐师啊,让我哭泣吧,否则,
沉重的心啊,会爆成碎块!
它原是悲哀所哺育,后来
长期在失眠中熬受痛楚,
命运给了它最坏的安排,
碎裂,——要么,被歌声收伏。
《我灵魂阴郁》[5]P62
…… ……
我爱过——所爱的人们已离去,
有朋友——早年的友谊已终结,
孤苦的心灵怎能不忧郁,
当原有的希望都黯然熄灭!
…………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5]P8
“沉重的心”需要深沉而激越的琴曲的配合,诗人恳求乐师“让我哭吧”,因为这心灵“原是悲哀所哺育”。“孤苦的心灵”因为“原有的希望黯然熄灭”,所以才强烈地渴求说:“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应该说,拜伦的表达是真挚而深沉的,他浓浓的情愫没有丝毫的掩饰,溢于言表,简单而直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是浪漫主义最明显的特点。浪漫主义强调主观自我,主张感情的自然宣泄,往往有着很强的抒情性,而这种抒情在诗中又是直接地表达出来的,一切跃然纸上,了然于外在。因此,读者很容易“知道”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领会理解就好了,并不需要运用更多的想象去找到和作者完全相同的“感觉”。
波德莱尔的诗也是在表达他这种痛苦的情感,亦或说全诗通篇都在写“忧郁”。但不同的是没有一字“直说”这种感情,而完全是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在抽象“忧郁”的主观世界与具象写实的客观世界之间穿越。通过现实中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客观事物(如“低重的天空”“黑色的黎明”)和现实的场景(缓缓行进的“送葬的长列”)以及“远取譬”所构成的“隐喻”(“如蝙蝠般飞去”的“希望”,变成“潮湿的牢房”的大地)等等意象来构成“暗示”,进而启发读者的想象,将其带入那神秘的“彼岸世界”,从而达到“主、客观世界的交融”。可以说,在象征主义的诗中,作者不会向你讲述他心灵痛苦产生的原委,也不会直接告诉你他“忧郁”的内心有多严重,只是通过一个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来“暗示”他的“忧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受着怎样的煎熬。因为充满“暗示”的语言是最能引发人的想象的,而只有在沉入想象之中,你彻底进入了诗中的世界,才会跟作者一样真正的“感同身受”。因此说,“暗示”手法的目的,或者说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理念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种作者与读者真正的“感同身受”。正是作者创作时的“心凝形释”,以及通过其作品的“暗示”作用,使读者阅读时达到的“感同身受”,这种由诗歌作品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便是象征主义所说的“主观世界的客观化,客观世界的主观化”,亦即“主客观世界的交融”或者说“契合”——所谓的“象征”就这样构成了。
“暗示”的手法在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中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英国诗人T·S·艾略特那里发挥到了极致。艾略特在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被称作“现代诗歌的里程碑”。“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白日梦”般的自由联想,戏剧化的场景,神话的结构,宗教的寓言,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式的“拼接”,纵横东西、穿越古今的“典故”,奇妙的隐喻、通感,各种语言甚至谁也不懂的自造的“语言”,诗歌的体式、“题记”、注释等等,都成为其主观精神的“客观对应物”,使其“思想感性化”,“暗示”给读者。其早期代表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全篇通过主人公普鲁弗鲁克在黄昏时分穿越英国小镇的街道,去跟情人约会的“戏剧场景”,展现其在路上的“意识流”,暗示出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感,有欲无情、迷惘彷徨的内心世界。而其代表作长诗《荒原》则更是充满着各种“暗示”的手法,全诗以东方印度的一个神话作为内在结构,以“荒原”上久旱无雨的现实暗示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以身背利剑的少年去寻找圣杯暗示荒原的拯救;以“雷霆的话”宣喻给人类的六字箴言:“舍予,同情,克制”,暗示只有通过信仰的回归才能挽救现代西方社会的堕落;全诗中使用了六种语言以及诗人自造的“语言”,四百多行的诗句包含至少六十本鸿篇巨制的内容,涵盖人类学,社会学,东、西方神话,哲学,宗教,文学,音乐等等各学科的知识,类比、对比的意象,戏剧化的场景片段,大量文学作品的拼接,奇妙的比喻,深奥的典故,全景展现与特写镜头,来自民间和文人创作的各种诗体的借用,等等。
总之,从象征主义开始,“暗示”的手法为西方现代派诗歌所广泛使用,其理论基础来自十九世纪西方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学理念,它颠覆的是传统文学流派整体上过于“写实”(表面现实)和“直白”(理性表白)的手法,而去追求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外在世界的高度“契合”。当然,传统文学不是说没有“暗示”,广义的“暗示”是始终存在,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但这里说的是狭义的“暗示”,是有着明确的哲学基础和文学理念的现代手法。仅就现代西方文学而言,从传统的表现形式到现代的表现方法,作家的写作策略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体验也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