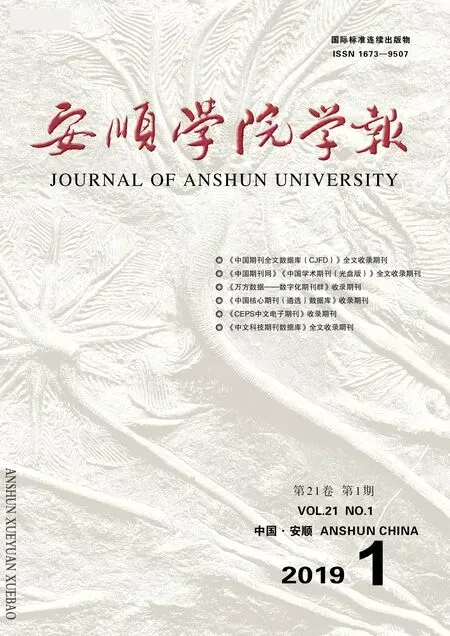论洪迈笔记的现实情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410003)
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饶州乐平(今江西省乐平市)人。历高、孝、光、宁四朝,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他天资聪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1]为官清廉,志节高雅。治学广博,著述丰富,其中积数十年之功而写就的学术随笔《容斋随笔》,凡五笔七十四卷,其书深于经史之学,旁及天文、民俗、地理等诸领域,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事实、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与沈存中《梦溪笔谈》、王伯厚《困学纪闻》等,后先并重于世,”[2]时人推重“为近世笔记之冠冕”[3]。学界多着眼于其史学思想、治史之法的发掘和研究与其小说观、诗学观的分析和探讨等。其笔记创作中充满着对时局的关念之情,所展现的现实情怀,则为时下关注甚少。鉴于此,论文在充分关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洪迈创作的旨意,呈现的旷达人生态度与济世情怀,以此揭示笔记对现实的关怀。
一、笔记创作的旨意
洪迈于宗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开始写作《容斋随笔》。此际时局有了南宋朝历史上最为凸出的两个倾向:一是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秦桧死后,宋高宗实行“更化”和“叙复”政策,大规模地清除弊政,尤其是为秦桧专权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进行平反。二是出现了与绍兴和议后完全不同的政治时局。金主完颜亮南侵失败,宋孝宗即位,签定了在宋金所有和议中最接近于平等的和议,并且不忘复仇,励精图治。此期,洪迈虽然于绍兴三十二(1162年)年因“奉使辱命”罢官归里,但翌年即又被起知泉州,并未沉沦。在这种背景下写作《容斋随笔》,自然直言无隐,敢于议论,“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4]书中多是作者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彰显了笔记创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由于洪迈多年的史官与文学侍从身份,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虽没有直接的评述,但从他所引述的李翱以及宋人张耒、吕南公的文论中,依然可以看出,他秉持的文与道的关系,实际上是偏向“文以明道”的,即认为道与文具有相同的地位,并进一步论述了“道”的广泛来源,指出庄子、列子、屈原、扬雄等先辈的文章都是有“道”之文,这就与狭窄的“文以载道”观念区别开来了,倾向于中唐韩愈的文道观。他既以史学家的立场肯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振兴古文的历史价值,又在通过对《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事”、“书法”的描写中,酝酿出了“风行水上”、“骏马下坡”的别出机杼的散文观。在《李习之论文》中,对李翱文论的引用,《书简循习》中对时人书简循习的批评,以《唐书载韩柳文》《蓝田丞壁记》中对柳宗元的微訾都可见出他这一文论观的具体体现。
于作者而言,文章不是“小伎”,而是人类文明制度、历史经验、至言要道得以流传的承载体,由此观文能“察时变”、“化成天下”,“彼后世为词章者……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他赞同苏东坡“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的作文之法,[5]强调诗文创作要有“志”、“意”、“旨趣”,有益风化。他在《容斋随笔》“张吕二公文论”条中强调作文应以理为主,表达心志:“张文潜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着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时学者,仰以为至言。予作史,采其语着于本传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6]从中亦可见出作者自身的文论观,主张只有尽心志的文章,方不会卑浅,如此才能立言。他还更为直接明了的指出:“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着,览者可以立决。”[7]
《容斋随笔》着意很多,但最根本的,且贯穿全书的还是其“忠义观”与“民本观”。“忠义”关系国家社稷的治乱兴亡,洪迈联系历史和现实,通过深入考察秦帝国灭亡的原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认识。《容斋初笔》卷五“晋之亡与秦隋异”条中,指出“得罪于民”是秦之所亡的原因,进而认为“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于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以此为出发点,思考现实,感慨靖康之难,指出北宋虽“虎旅云屯”,却“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8]士人忠义之气荡然无存,完全从精神上解除了武备装置,因此虽有“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却“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最终“端坐都城,束手就毙!”[9]他列举吴国侵略楚国时,楚昭王“国灭出亡”,以及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避乱幸蜀等八件历史事实,以此说明危急时刻以义感人的重要性,形势仓卒、急遽的时候,道义的力量甚至“竟以复国”[10],而如今“国家靖康、建炎之难极矣,不闻有此,何邪?[11]”在洪迈看来,为人尽忠切为重要,德高莫过于忠义,罪大莫过于不忠不义。他认为,危急时刻,“大义”可以鼓动人心,激励士气,化作巨大的力量。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分析中,辅之以丰富的史事,通过纵向、横向的对比,充分论证了忠义的极端重要性。
同时又主“民本”之说。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保证社会和谐运转、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的重要治国安邦理论,“民”乃为治政之本,为政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君”为本,其主要内涵分为保民、养民、富民、教民四个层次,“重民”是其中的核心层次。反映在两宋政治实践上,却出现了全然不同的景象,尊君而不重民,中央政权集权强化、君主专制盛行,奉行养兵之策,豢养了庞大的常备军,冗兵现象凸显;右文之策,供养了庞大的官僚士大夫食禄阶层,冗官现象空前,由此带来严重的冗费现象,财政负担沉重,由此导致横征暴敛的苛政与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势。因此,面对沉重社会危机,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挽救社稷民众,拯救社会危机,如何正确认识“君本”与“民本”问题,以采取正确的治国方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摆在两宋士大夫面前,成为了两宋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从《初笔》卷一《地险》到《五笔》卷十《农父田翁诗》,一以贯之民本思想,矢志不渝地坚持与弘扬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极力维护“民”在历史和国家中的根本地位,视爱民惠民为大德大义。他一方面充分肯定汉高祖、唐太宗、魏征等人的历史举措,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发抉历史“负面人物”的亲民善政之举,以表其事,以彰其德。《容斋初笔》卷一《地险》中以曹操、朱温均在缺乏地险的情况下兴起的史事,指出“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12],直接对理学家视曹朱为无德之人提出质疑,大加赞赏曹操以及五代朱温、孟昶、张全义、宋齐丘等人在乱离之季重建秩序、轻摇薄赋、利民安民的政治举措,认为他们的成功在于得民,由此不满于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这些史事的有意略去。洪迈运用这种被理学家定为“盗贼凶悖之人”的曹朱生平功业的用意在于,这样的人比其他历史人物更能说明:决定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根本原因是先秦儒家“政在得民”之德,而非宋代理学的纲常伦理之德的这一真理,由此批评“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毫无爱民之心,指出他们“有靦于偏闰之臣”[13]。洪迈这种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出发的识见,既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又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总结得出的。
二、旷达的人生态度
洪迈论士之处世,强调超脱、恬淡,体现独立不羁的人格与旷达的人生态度。不为名利所累,宠辱不惊,坦然处之,是其一以贯之的立身处世之道。在《容斋初笔》卷十四“士之处世”条中,他这样写道:“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棰,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14]条目中,作者以戏子、老人、小儿、醉汉之社会角色为参照对象,以此说明士人在进退之际应视富贵利禄如游戏,从容应对进退。这种不为世俗所羁绊的处世准则,体现着一种独立不羁的人格与旷达的人生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作者极力践行着这种人生态度。《容斋三笔》卷十二“人当知足”条写道:“予年过七十,法当致仕,绍熙之末,以新天子临御,未敢遂有请,故玉隆满秩,只以本官职居里。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赘食太仓为愧,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以为耿耿。予诵白乐天《初授拾遗》诗以语之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15]其安分知足之意,可见一斑。“因略考国朝以来,名卿伟人负一时重望而不跻大用者……皆不过尚书学士,或中年即世,或迁谪留落,或无田以食,或无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则予之忝窃亦已多矣。”[16]在作者看来,人应知足,应有一份超脱、恬淡之心。他因此强调人只有去其私心,方能去弊,“盖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丰以后,州县榷卖坊场,而收净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从而生。”[17]无私则少欲,可见他内心的淡泊,所追求的惟有以学明志,仰慕那些修己笃学,独善其身者:“士子修己笃学,独善其身,不求知于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无传。”[18]
他由此坚持“执中”的思想方法,反对“过”与“不及”的两种片面性,并着重反“过”。 “万事不可过”中写道:“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膏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懊亢。赏以劝善,过则为潜,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馅,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19]洪迈在通过对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展现的诸多事实中,反复论证了“过”的危害性,并着重说明“过”就是“偏”,“过”了就会造成片面性,酿成错误,酿成灾害,以此指出天下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过份了,过犹不及也。
正是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执中”的思维方式,作者的出处行藏,一切随缘,闲暇之时,他走向自然,乐其山水。乾道四年(1168年)六月,洪迈罢官归里,便在饶州建造亭园台榭,种植花草竹木。“予治圃于乡里……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数十本,其高仅四五寸,植之云壑石上,拥土以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过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势。”[20]《四朝闻见录》卷一“洪景卢”如此记载:“归番阳,与兄丞相适酬唱觞咏于林壑甚适。偶得史氏琼花,种之别墅,名曰‘琼野’,楼曰‘琼楼’,圃曰‘琼圃’,常“与兄丞相适酬唱觞咏于林壑甚适”[21]。怡然自得之状犹然可见,并与友人交游唱和。乾道元年与王嘉叟、王十朋、王秬、陈阜卿、张孝祥、何子应等人成立楚东诗社,结辑成《楚东酬唱集》。此外,还与方外人士交往,结识三教九流,甚至求神问卜。唱和交游,明月清风,山水林泉,宁静而澄明,他在《野处亭》诗中如此感怀这种情致:“莫厌攻台万杆声,芝亭入望得双声。快邀明月无余地,俯瞰澄江不碍城。花雨著人迷杖履,松风呼梦绕厢荣。弟兄丘壑平生事,付与鸣琴一再行。”[22]明月、澄江、花雨、松风、丘壑,清新自然,令人心旷神怡。在此种景致中,鸣琴赏乐,弹指五弦,心中的忧愁苦闷,日常琐事,皆飘散而去,仿若羽化而登仙,何乐至极,作者悠然淡泊且卓雅不凡的人生态度油然可鉴。
三、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
北宋积弱,屈辱而亡。南宋偏安,醉生梦死。历史的厄运,令洪迈扼腕悲叹;现实的苦难,更令其忧心忡忡。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始终以济民为己志,屡挫不改,进退皆忧。《容斋随笔》一些条目,以古鉴今,即史论政,可认为是其对当时政治的研判和建议。明代李瀚称其:“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23]黄濬指出“盖冀以感悟讽谏也。”[24]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洪迈忧念时局,始终以济民为己志,以理性的心理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时局作了多方面的辨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首先,笔记中多揭示战争的残酷,表达作者对普通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容斋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 条记述其父在英州目睹亡国之徒的悲惨境遇:“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猴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25]深刻地暴露了无数生命被杀戮的凄惨现实与宋金战争对南宋社会带来的深重破坏。作者始终忧虑百姓的苦难,时刻关心他们的命运。
其次,洪迈坚持民本思想,对官僚、军阀、恶霸残杀人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容斋随笔》中,作者重点剖析了北宋末年蔡京专权时,王黼、朱勔、童贯、李彦、梁师成等“六贼”结党营私、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贪赃枉法,以致祸害天下的罪行。笔记如此记载他们用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禁锢正士:“章惇、蔡京为政,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26]痛斥统治者任性随意而为地冗滥除官[27]。笔记中,他这样写道:“蔡京三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因而“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至十一月冬祀毕,大赦天下,仍复推恩。”[28]深感官员屡增,官俸亦与之俱增的可悲时局。洪迈回顾宋初州县官员俸入至薄,黄亚夫历任一府、三州,尚且有愧于其“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的俸禄,而“今之仕宦,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袛可禄一书吏小校耳!”[29]“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30]冗兵、冗官、冗费滋生沉重的赋税,官吏由此横征暴敛,百姓受尽其苦。洪迈对此感叹道:“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31]
洪迈精熟于有宋一代典章文物,“尤以博洽受知孝宗”[32]。韩淲《涧泉日记》中谓乾道、淳熙以来,熟悉“典章”,首推洪迈、周必[33]。李慈铭称《容斋随笔》“最留心官制”[34]。其南渡以后,官失其守,洪迈关于职官沿革、制度兴废之讨论,便有其现实意义。他看到了“台省胥吏旧人多不存,后生习学,加以省记,不复谙悉典章”(《三笔》卷九《司封失典故》)[35],“国家南渡以来,典章文物,多不与承平类”(《五笔》卷四《近世文物之殊》)[36]。《随笔》卷五《史馆玉碟所》,卷六《带职人转官》,卷九《三公改他官》《带职致仕》《高科得人》《翰苑故事》,卷十二《元丰官制》,卷十六《馆职名存》;《续笔》卷十一《祖宗朝宰辅》《百官避宰相》《百官见宰相》;《三笔》卷四《枢密称呼》《从官事体》《旧官衔冗赘》,卷五《枢密名称更易》,卷七《执政官转官》《宗室补官》《赵丞相除拜》,卷九《枢密两长官》《司封失典故》,卷十《司封赠典之失》;《四笔》卷七《考课之法废》等中,往往据故事考辨有司之得失。礼制方面,如省试官入院、政府呼召、从官立班随驾、百官骆从、朝服简削之类(《五笔》卷四《近世文物之殊》),在当时,这些典章制度皆事关大体。他往复引述商鉴于夏、周鉴于商、汉鉴于秦、唐鉴于隋的史事,并强调《诗》《书》的有关记载和汉唐诸多名臣的论述,认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37]从中可知,洪迈不仅批评了两宋以来史学中漫引古说,不着实际的倾向,并且指出了借鉴历史经验的正确途径。《容斋随笔》初集出版后,即受到孝宗的好评,《续笔序》曰:“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因复衷臆说缀于后,惧与前书相乱,故别以一二数而目曰续,亦十六卷云。”[38]所谈兴衰治乱、典章制度,或许正是以孝宗一朝君臣为其预设的读者对象。
《容斋随笔》对秦汉隋唐之兴衰治乱、帝王治国理政之成败得失着墨甚多,如《续笔》卷十《汉武留意郡守》论汉武留意郡守云:“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又举严助、吾丘寿王、汲黯为例:“观此三者,则知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39]。仿佛上孝宗言政事疏。洪迈又论“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40],于景帝多所批评。虽谈史事,实亦论今,都有“欲为圣明除弊事”“致君尧舜上”之深衷。《五笔》卷十《祖宗命相》中云“祖宗进用宰相,惟意所属,初不以内外高卑为主。”[41]谈的仍是“祖宗命相”严肃而重要的话题,从中不难看到其体国经野之识见,拳拳君国之忠心。
可以说,洪迈的笔记创作是其读书和思考在文字上的表达,尽管这些札记都是他兴有所致、意有所得的表现,但其议论是有所为而来的,是因其时局有感而发的。诸多条目中情理兼备,社会、历史、现实交响协奏,情中寓理,理中含情。既有个人处世态度的内在透视,又有关心民生疾苦、社会弊病的向外视野。不仅观照百姓的灾难与生存状态,也对官场黑暗、吏治腐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进行审视,体现出极为强烈的现实情怀。
——从《容斋随笔》所载宋人史学谈起
——以《容斋随笔》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