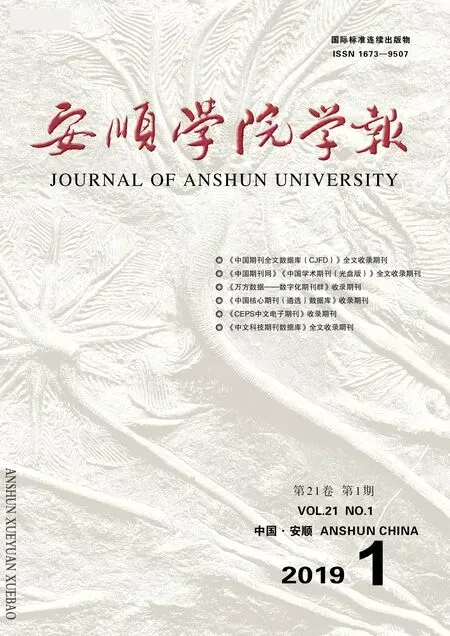中国志怪小说中人与异类之关系
——基于《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的人类学考察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401331)
中国志怪小说,是指以记录怪异之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其萌芽期产生于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进入繁荣期,清代志怪小说以《聊斋志异》为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涉病作品中共描写了人类与异类两大系统,其中有大量的异类致疾情节的描绘。异类致疾现象是指人类所患疾病不是出于自然生理状态的不适引起,而是由于异类的主动施与或者与异类接触致使人类患病,既包括生理疾病,也包括心理疾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既表现出人类对异类的恐惧、对异类空间的好奇与想象等复杂心理,又表现出人类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幻想自身拥有法术战胜异类的心态以及在实用主义理念影响下对善良异类的寻求。
一、《聊斋志异》中异类致疾现象内容呈现
异类致疾故事在中国志怪小说中是常见的母题,《神异经·中荒经》中就记载:“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人则病,名曰。”[1]《西京杂记·广川王发古冢》篇中,记录了一白狐击打人类,致使人脚肿痛生疮的故事。在《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中,这类异类致疾故事更是比比皆是。及至清代的《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吸取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也创作了大量的异类致疾作品。在对《聊斋志异》异类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异类女性的温婉可人、光彩艳丽出发,进而论述《聊斋志异》中人与异类关系的和谐与美好,“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2],而从疾病这一角度审视人与异类之关系,则会有不同的发现。所谓的异类,是指生命的非常态,即相对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个体,包括鬼物、神仙、狐妖、精怪、具有法术的术人等形象。笔者将异类划分的标准,需要说明几个概念,第一是“鬼物”的概念,《礼记·祭法》言“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3];《列子·天瑞》云“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4]“鬼物”是指人死之后的一种形体,地府的鬼卒、鬼吏等皆算作鬼物。第二是“神仙”的概念,“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5]刘向《说苑·修文》则曰:“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6]“仙”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长生仙去,从人从山。”[7]《释名》称:“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8]由此可见,“神”是创造繁育自然万物之母,而“仙”是指具有“长生不死”特征的形象。在道教的兴起与佛教的传入之后,神仙一词运用更为广泛,包括道教所供奉的土地神、城隍神、碧霞元君等,修道成仙者,民间信仰中崇拜的神祗如青蛙神等,只要享受民间的供奉,具有上述“神仙”之特征,这里统称为广义上的神仙。第三是“精怪”的概念。“精怪,本来是指各种自然物——山川土木、飞鸟潜鱼、走兽爬虫,老而成精,便能通灵变化”,“以后,又与自然界各种反常现象的总称妖怪汇聚在一起”[9],《论衡·自纪》曰:“诡于众而突出曰怪”[10],因此精怪是指超自然的动植物精灵和反常的无生命体。术人因具有寻常生命所不具备的法术力量,因此也将其列入异类的考察范围,具体内容已制成表格,如表1。

表1:《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力量所致疾病分类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知,致使人类有疾的异类以鬼物、精怪、狐妖、神仙篇目最多,因为先民们对这些异类的想象最为丰富,这些异类离人类的生活较远,多是人类思维幻想的产物,而异类致使人类有疾后,通过对表格2的病果分析可知,异类致使人类有疾,最终并不是病亡的结果大于病愈,反而是人类通过有疾后,病愈的结果较多。进一步进行考察,发现这样的结果与致病之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疾病描写能够对人类与异类的关系窥探一二,即在以疾为异的原始思维熏染之下,先民们随着对自然认知的进步,人的主体性的凸显,逐渐产生由对异类的崇拜祭祀到驱赶祓除的心理变化。

表2:《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力量所致疾病病果分析
二、致病之因——异类对人类的警示与规训
在原始先民心中,人类对除了自身以外的世界从未停止过思考,先民们幻想有超现实的异类存在,对于冥府、鬼卒的想象由来已久,中国志怪小说中记录的异类致疾现象就是这一想象的直接呈现。“原始社会极为低下的生产力、人们幼稚的思维能力和好奇心正是原始宗教和巫术产生的根源,鬼文化正是在这种极为低下的生产力和人们的原始宗教心理下产生的。”[11]而神仙的观念在东晋道教兴起后,也大肆流传开来。最开始疾病的出现,原始先民就认为是异类如鬼神等作祟致使,如《金枝》中记载:“如有一个收谷人在田里病了,就认为他是不知不觉中绊在谷精上了,是谷精惩罚亵渎不恭的冒犯者。”[12]“新不列颠的土人把疾病、旱灾、歉收,总之一切灾祸,都看作是妖精作怪。”[13]不仅西方典籍中记载了将疾病视为异类作祟,在中国典籍中,也有将疾病与异类相联系的记载,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述,“殷人把许多疾病都归咎于先人作祟和仇鬼缠身,故在卜辞中多有祈求神灵恩宠消灾,以达驱除鬼邪、护获平安的目的。”[14]因为异类拥有世间人类所不具有的法术力量,人类对异类多抱有恐惧心理,疾病多作为异类对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侵犯表现,要么表现为身体上的伤残疼痛,要么表现在精神上的痴狂呓语。
首先,人类若侵犯了异类,对异类不敬,没有服从异类的命令,包括侵入了异类所在的空间,异类将会通过致使人类有疾的方式达到对人类的警示与规训作用。有因对异类不敬者而致疾的情况,如卷三《狐妾》篇中,仆人私下所言对狐妾不敬,“明日,仆甫入城,头大痛,至署,抱首号呼”[15]。狐妾略施薄惩,等仆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方才痊愈。对异类不敬者,多体现为对神仙的不敬,神仙予以疾病告诫,只要诚心悔过,皆能痊愈,如卷十一《齐天大圣》一篇中,刚正鲠直的许盛嘲谑世人祝祷齐天大圣之盛况,“至夜,盛果病,头痛大作”,“未几,头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连足尽肿,寝食俱废”[16],不仅许盛遭受疾病折磨,兄长也大病,等神灵为其二人医治痊愈后,许盛对齐天大圣诚心信奉。卷十一《青蛙神》篇中,青蛙神将其女下嫁给昆生,自婚于神后,门前皆被青蛙围绕,昆生少年任性,对青蛙不敬,神女十娘怒其所为,而昆生不改其行,甚至将十娘赶走,果然昆生一家受到神灵的告诫,“至夜,母子俱病,郁冒不食”[17],后经由昆生之父殷切的祝祷,负荆请罪于青蛙祠堂后,母子二人疾病乃痊愈。但也有因不敬神灵而致使病卒者,如卷二《吴令》篇中,刚正耿介的吴县令因对敬奉城隍神之伤民劳财行为的不满,在城隍祠内公然怒骂神灵刮削民脂民膏,使得吴令“折股,寻卒”;卷十二《周生》篇中,周生代为祭奉神灵碧霞元君时,所作祷辞,颇多轻侮嬉戏之意,“未几,周生卒于署;既而仆亦死;徐夫人产后,亦病卒。”[18]未听从异类的命令而致疾者,如卷七《金姑父》篇中,神女梅姑挑选人间男子金生为夫婿,“族长恐玷其贞,以故不从。未几,一家俱病。”[19]卷九《乔女》篇中,乔女临终前的遗愿是将自己葬在穆家,而孟生之子乌头用金钱买通了穆生的儿子,让乔女与孟生合葬,已身为鬼的乔女对穆生之子进行训诫,“穆子忽仆,七窍血出,自言曰:‘不肖儿,何得遂卖汝母!’”[20]经由乌头祷祝后,按照乔女的遗愿下葬后,穆生之子方病愈。人类侵入异类所在空间范围而致病者,如卷十一《衢州三怪》篇,衢州之地,夜静之时若有人独行,钟楼上的鬼物听闻人行声即下,见到鬼物的人类就会生病,若人类在城中听到鸭鬼的叫声后,也会得病;如卷六《大人》篇中,人类误入大山深处,傍树休息之时,见到“大人至,以手攫马而食,六七匹顷刻都尽。既而折树上长条,捉人首穿腮,如贯鱼状”[21],令人惊恐的巨人对待擅闯入山的人类施与了惨重的训诫;卷七《郭秀才》篇中,郭秀才误入异类空间,饮用异类之酒水而病,郭生从友人处归来,“入山迷路,窜榛莽中”,看到有数十人席地饮酒,遂加入其中,“翼日,腹大痛;溺绿色,似铜青,着物能染,亦无溺气,三日乃已。”[22]
其次,异类主动来到人间,侵害人类,致使人类有疾。如卷二《庙鬼》篇中,城隍庙中的泥鬼主动来到人间迷惑王生而不得后,致使其得癫疾,王生“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数作,术药罔效”[23];卷三《刘海石》篇中,妖物作祟幻化成人形,来到人间吸食人体元气,致使刘沧客长子患脑痛病卒,妻子病卒,家人相继因病而亡;还有一些妖道,使用法术致使人类有疾,如卷五《小人》篇中,读书童子归家途中,“为术人所迷,复投以药,四体暴缩”[24],卷五《长治女子》篇中,亦是如此,长治女子绣于房中,“忽觉足麻痹,渐至股,又渐至腰腹;俄而晕然倾仆”[25],最终被道士剖心,魂魄被钉在木人之上,任其驱使。在异类侵扰人类的过程中,人类也会勇敢反抗,但在与异类搏斗的过程中,多数处于劣势,疾病是人类力量弱小的体现,如卷一《荍中怪》篇,长山安翁看到一大鬼在偷食荞麦,“大怖,不遑他计,踊身暴起,狠刺之”[26],暂时将鬼物打退,但在后来的时日中,鬼物频来,终龁翁额而去,安翁额骨如掌,已昏迷不知人事。即使人类在与异类的搏斗中能取得胜利,也是以人类的疾病反应作为代价,如卷一《咬鬼》篇中,记叙了某翁午睡之时,一鬼妇潜入,趁其不备某翁奋力咬至其颧骨,鬼妇逃走,而咬鬼之时的血迹“伏而嗅之,腥臭异常。翁乃大吐。过数日,口中尚有馀臭云”[27];卷一《斫蟒》一篇,巨蟒将兄长之头颅吞下,即将吞入腹中时,其弟用樵斧与巨蟒搏斗,力与蟒争,竟然将兄长拖曳而出,但兄长鼻耳俱化,气息微弱,医养半年方才痊愈。异类对人类的侵扰致疾,还表现在异类主动向人类靠拢,接触到异类而致疾,如卷七《鬼津》篇中,昼卧的李某见到一鬼妇,“妇猝然登床,力抱其首,便与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块,浸浸入喉”,致使李某“由此腹胀喘满,数十日不食”[28];人类与异类共处时间越久,也越容易生病,如卷六《冷生》一篇,狐主动前来与冷生友好相处,不多久,冷生就精神失常,忽然患上狂易病。
最后,异类与人类的交合也能致使人类有疾,这类描写颇多,既有异类为男性者,亦有异类为女性者,且以异类女性居多。《聊斋志异》中的异类,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主动来到人间,与人类的交合都能致使对方有疾。在异类为男性中,表现为对人类女性的侵扰,女性多是被迫从之,而且异类男性多被人类制服,甚至被人类杀死,如卷一《贾儿》一篇,妇人独居,其丈夫贾于外,因而妇人受狐所惑,精神恍惚,不能安寝,贾儿用毒酒杀死狐精后,“而妇瘠殊甚,心渐明了,但益之嗽,呕痰辄数升,寻愈”[29];卷四《泥书生》篇中妇人一日独宿,遇一书生,“妇骇惧,苦相拒”而未果,与其交合后,“月馀,形容枯瘁”,幸赖婆婆暗中以杖击中,“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堕地,案头泥巾犹存”[30]。而当异类为女性时,人间的男子对这些异类女性的到来是概而不拒,欣然接受,一旦人间的男性和异类女性产生了真正的情感,这些异类女性即使能致使人间男子有疾,也很少有被人类杀死的结局。异类女性为鬼者,《说文解字》曰:“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31],与鬼交合,损伤人体之元气,如卷二《莲香》一篇中,李氏为鬼,桑生夜晚独坐凝思之时,李氏飘然忽至,桑生大喜,两人遂相款昵,久之,桑生神气萧索,“因循数日,沉绵不可复起”[32],但因李氏与桑生皆彼此真心相待,桑生也被治愈,李氏也得以复生;异类女性为狐者,如卷五《荷花三娘子》,宗湘若惑于女色“数日,宗益沉绵,若将陨坠”[33],得番僧符咒相助,但因宗生追念以往情好,也不忍伤害狐女,遂放之;卷十一《狐女》中的伊衮,“夜有女来,相与寝处。心知为狐,而爱其美,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于是“久而形体支离”[34];异类女性为神者,如卷四《土地夫人》一篇,土地夫人与王炳极相悦爱,“因循半载,病惫不起”[3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异类致使人类有疾,一方面是侵入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显示出异类非凡强大的力量,比如上述中异类主动来到人间,表现出对人间的向往,侵扰人类社会的安宁;另一方面,异类致使人类有疾,是为了确立异类的绝对力量,能取得在人类心中的绝对地位,比如神灵会因为人类的不敬、没有服从神灵旨意的安排而致使人类有疾,异类与人类的交合因身份的不同也会致使人类有疾而不是异类有疾,更是凸显出这一点,这些皆体现出异类对人类社会的警示与规训。
三、救治之方——人类对异类的反抗与妥协
异类力量致使人类有疾后,病果多表现为病愈。人类通过示弱的方式向异类臣服,异类一旦受到人类的祝祷或者诚心悔过后,就会让人类痊愈,体现了人类对异类力量的一种妥协。如卷三《泥鬼》篇中,唐梦赉与表亲某见到庙中泥鬼之眼睛目光如炬,唐梦赉十分喜爱,将其眼睛摘下带走,“既抵家,某暴病,不语移时”[36],经过家人诚恳祝祷,且将眼眶放回后,方才痊愈;卷四《济南道人》篇中则是异类通过让人类自作自受的方式,认识到异类的强大,给予人类惩戒。济东观察因道士施法将自己的酒分给众人,不满其行为,令人笞之,“杖才加,公觉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虽声嘶阶下,观察已血殷坐上”[37]。其次,人类在自身走向穷途末路时,尤其是病重之际,皆会有善良的异类前来救治,这也是人类对异类力量妥协的一种表现,幻想善良的异类前来救助危急的人类,如卷二《莲香》篇中,在桑生生命垂危之际,狐女莲香以一药丸将桑生救愈;卷二《庙鬼》篇中,王生为鬼妇所缠,精神癫狂,意识不受自身所控,医药无效,一日忽有城隍神庙之泥鬼前来伏妖,于是病愈。
其三,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积极救治而病愈,体现了人类高超的医术和对异类的一种反抗。有因能人异士的救治而痊愈者,这些能人异士多为僧道,如卷一《画皮》篇中,道士为王生之妻的情义感动,救治了被鬼物剖心的王生;卷五《酒虫》一篇,刘氏体肥贪杯,腹中酒虫作祟,有异疾,番僧为其救治,取出酒虫。有因得到现实中他人的救治而痊愈者,如卷一《耳中人》篇中,谭晋玄见耳中有小人出没,于是得癫疾,号叫不得休止,医药半年后,病愈;卷三《连锁》篇中,杨于畏为了让连锁复生,将其精血渡给连锁,致使自身大疾,然经由人类的医师医治,“下恶物如泥,浃辰而愈”,体现了人世间医生医术的高超和精妙。也有因德义感天而病愈者,如卷一《斫蟒》一篇,兄长被巨蟒所吞其首,其弟拒不放弃兄长的性命,将兄长从巨蟒口中拖出,病重的兄长至今面目皆有瘢痕,但已将性命保住。
从以上文本来看,《聊斋志异》中异类力量所致疾病,一方面体现出人类对不可把控,不可感知异类的一种恐惧心理,对冥界鬼卒、神仙、狐妖等精怪的惧怕,鬼卒勾命皆以疾病的方式呈现,对神灵不敬也可遭致疾病的惩罚,致使身体受到规训,与异类的结合会受到身份的限制,致使人类有疾,种种现象都表明了人类对异类的一种畏惧心理;但在畏惧异类的同时,人类对这些主动侵害人类的异类也有反抗。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与异类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志怪小说中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的叙事。如《搜神记·戴侯祠》中戴氏女,“久病不差,见一小石,形像偶人”,遂祷告,“自后疾渐差。”[38]《殷芸小说》中,孙皓得一金像,未有侍奉,则身体疼痛不堪,“烧香忏悔,痛即便止。”[39]若有人敢怀疑和挑战鬼神等异类的力量,多以暴卒为代价。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认知,体现为想方设法寻求祛疾的方法,驱赶祓除作祟致疾的异类。及至唐代以后,这种思维体现更明显,如王度《古镜记》中,“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绩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40]王绩以宝镜照之,原来是公鸡作祟,以宝镜杀死公鸡。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古代其他的志怪小说,从人类对异类致疾的恐惧到对异类的反抗,事实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增强。
结 语
《聊斋志异》中通过疾病描写,展示了人类对待异类由崇拜祭祀到驱赶祓除、再到妥协的态度转变,也是中国志怪小说从先秦至明清发展过程中,人与异类关系的一种转变,这变化从深层次上来说是人的主体性觉醒与增强的一种表现。人类对于异类的想象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始,这一文化心理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先民们囿于认识自然的狭隘性,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将“疾病”与“异类”相联系,从而衍生出对拥有强大力量异类的臣服与崇拜心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从敬畏逐渐走向征服的一种文明进程,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人以一种不同的观念来想象自然以及他在自然中的地位了。对生命一体化的感情让位于一种新的更强烈的主旨——让位于对人的个体性的特有意识。”[41]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发展,进一步的体认世界后,人将自身摆放在世界的中心,试图运用自身的智慧与力量去征服自然和异类,这一思维的转变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凸显,由此显示出人类对异类的态度是驱赶祓除,但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多次的受挫,人类有可能转而至妥协。《聊斋志异》中的疾病描写即对人与异类的这一关系有着充分的展现,并在此基础上体现了人类主体性的觉醒,由此可以观照中国志怪小说中的人与异类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