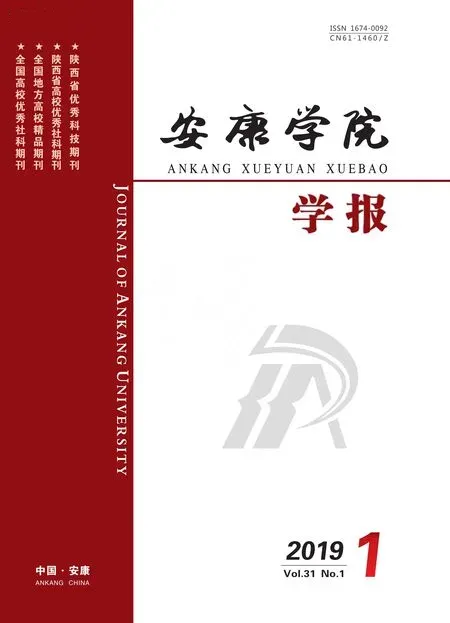对《说文解字》中“省形”“省声”现象的再认识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省形”“省声”是《说文解字》 (以下简称《说文》)中分析字形的一种补充条例,学界对这种体例的争议较多,主要集中在部分字说解的合理性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许书言“省”之字,曲说妄说者甚多,甚至有学者撰文全面否定“省声”[1]120,但多数学者对此都持辩证态度,认为其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哭”字下注解到:“按許書言省聲,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爲某字之省,若家之爲豭省,哭之从獄省,皆不可信。”[2]63他又在“家”字下面补充道:“此字爲一大疑案。豭省聲讀家,學者但見从豕而已,从豕之字多矣,安見其爲豭者耶。何以不云叚聲,而紆回至此耶。”[2]337王筠也与其有相似的观点:“哭下云獄省声,獄字会意自可省,然从犬何以知为獄省?凡此类者,皆字形失传而许君强为之解。”[3]之后,唐兰、裘锡圭等人在其著作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唐兰认为:“《说文》里常讲到省形或省声,但往往是错误的,因为凡可以称省,一定原来有不省的字,而《说文》里所说,大都不合这个原则。”[4]裘锡圭先生也认为:“虽然省声字是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我们对《说文》里关于省声的说法却不能随便相信。”[5]其后何九盈[6]4-18、冯玉涛[7]12-18等学者通过分析具体例子来说明《说文》中存在部分“省形”“省声”的分析错误。
虽然学界对《说文》中言“省”之字的批评质疑之声多于赞赏肯定之声,且都提出了相关的证据,但纵观以上学者的思路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站在许慎的对立面来批评许慎,鲜有人站在许慎的角度来思考,他以“省”来迂回解说小篆的动因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只有先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客观地看待《说文》中的“省形”“省声”现象。
一、从析字法的角度看《说文》中的“省形”“省声”现象
众所周知,《说文》是一部析字的书,而非造字的书,“《说文解字》的析字方法是‘构件分析法’,即首先将字形拆分成若干构件(包括独体构件),然后说明每个构件的功能,或者提出同形构件进行类比”[8],这就决定了许慎必须把他离析出的每个构件都赋予一个功能,但总有一些构件的功能在表面上看来不能牵合其字音或字义,所以许慎就曲为之说,比附《说文》中该构件的参构字,用“省形”“省声”来说明该构件的功能。
李敏辞曾说:“识别判明‘省声’的标准和方法:凡合体成字者,非会意即形声。无意可会者,则必为形声;既为形声而‘又不得其声’,是必为省声。”[9]38李氏虽是针对“省声”而言的,但同样也适用于“省形”字。一个合体字,拆分出的构件,不表义则表音,所以无论是直言其音或义,还是用“省”曲说其音或义,都只不过是赋予构件功能的手段罢了。
二、汉字构件与其功能“失联”的主要原因
造字之初,汉字都具有理据性,这种理据性表现在其结构的可分析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汉字的造字理据变得不可分析,构件与功能“失联”,而这种“失联”才是导致许慎言“省”的直接动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字形的变化导致出现“失联”现象
汉字从早期甲金文字到如今简化后的楷书,其形体从未停止过变化。而汉字所记录的语言虽也是不断发展的,但二者变化却并不是同步的。有些汉字,形体虽几经更迭,但其所记录的词语却从未发生过变化。如“日”这个汉字,自诞生至今,都专一地记录着“太阳”这个语义,而其形体却从最初的象形文字演变成如今的记号文字了。《说文》以小篆为基本形体,自有书面文字到小篆,期间也有千年的时间,汉字形体在此之间必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到许慎时代自然会出现不少汉字形体与其功能“失联”的现象。
(二)汉字职能的原因导致出现“失联”现象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个体汉字的原初构形都是以具体语词的音义为根据的,因而汉字的‘形’跟汉语的‘音义’是基本统一的。”[10]但随着所记之词语音与义的变化,字形构件与其功能之间就会出现“失联”现象。另外,也有些汉字基于假借等原因,其形体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约定俗成的,并不具有可分析性。如第一人称代词“我”,书面上是借用兵器意义的“我”这个形体来表达的。
(三)其他主观原因导致出现“失联”现象
主观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析字者个人的局限性。如《说文》以小篆为基本字形分析字义,虽也收录了一些籀文、古文,但数量较少,且其并未见过甲骨文等早期文字,所以“以形索义”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失误。当然,《说文》中也存在一些字形,或是许慎对其分析有误,或是后人篡改。二是文化上的要求,主要是避讳的要求。如古代为了避讳先祖或皇帝的名讳,都会在需要用到该字的地方缺笔写,由此也会导致字形与其功能之间的“失联”。
三、许慎建立“省形”“省声”的主要依据
“汉字形体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11],所以许慎以“省形”“省声”来说解文字,是符合汉字演变规律的。另外,《说文》中明确标有不省的原形的有35个,正是这些有明确的不省的原形启发了许慎用“省形”“省声”来析字。李润说:“正是由于古、籀、或、俗体字中不省之形,启发了许慎,使他能从古文字证明的二十多字推及其余二百七十余字,由‘省声’字的客观存在而推及‘六书’理论的不完备,于是建立了‘省声’条例。”[12]160所以,“省形”“省声”条例的建立是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的。
四、《说文》中“省形”“省声”现象的价值
对于《说文》中的“省形”“省声”现象,学界多数人认为给我们现代语言文字研究最大的启示就是“汉字简化”。李敏辞认为:“它一直在为创造与简化汉字服务着”[9]38;宋易麟也声援了这个观点,认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创‘省声’的体例,揭示了这种汉字简化法”[13];韩琳更是直接表示,“《说文解字》开创并系统应用了省形和省声这两种体例揭示了汉字的简化规律”[14]。以上学者都直接表达了“省形”“省声”对于汉字简化的借鉴意义,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汉字简化的前提一定是有不简的形体,而这种情况在《说文》中却只有寥寥几个,所以说“省形”“省声”“揭示了汉字的简化规律”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省声”在研究古音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炳祺认为:“这些‘省声’材料对我们研究汉字的谐声偏旁,特别是先秦至汉代的读音变化情况有一定作用”[15];李润也认为:“由‘省声’材料中,我们亦可探索字音的演变规律”[12]160。许慎不用“某声”而用“省声”,最重要的原因应是“省声”比“某声”更能反映当时的语音实际,因而也确实能反映古音的变化。
尽管“省形”“省声”确实存在“汉字简化”和“古音研究”方面的价值,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诟病《说文》中的“省形”“省声”现象,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许慎建立“省形”“省声”条例的初衷。《说文》是我国的第一部字典,其前身是《仓颉篇》 《训纂篇》等字书,所以《说文》如前代字书一样,都致力于蒙学教化和宣扬正统,故对于某些理据不明的字,为了不注“阙”,就模仿那些有原形的“省形”“省声”字,比附《说文》该构件的参构字,用“省”曲为之说。
五、《说文》中典型例子分析
《说文》中不可信的“省声”有158例[6]4,不可信的“省形”有67例[7]14,今选取争议较大的几例予以重新说明。
(一)家(从宀,豭省聲);哭(从吅,獄省聲)
许氏之所以分别将“家、哭”二字释为“豭省聲”和“獄省聲”,是因为许慎认为构件“豕”和“犬”与此二字的音义都联系不上,且《说文》中“豕”“犬”的参构字与两者之间的意义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和其读音却联系得起来。按,家、豭同为“见母鱼韵”字,两者同音;哭为“溪母屋韵”字,獄为“疑母屋韵”字,两者声近韵同。故许慎以“豭省聲”和“獄省聲”标注“家、哭”二字,只是为了说明两者的读音罢了。当然,书中符合音近或音同的参构字不止这两个,只是许慎在此选择了这两个参构字罢了,这种随意性才是段氏等人诟病其为“千古疑案”的最主要原因。
(二)从“熒”省的系列诸字
从“熒”省的系列诸字既涉及“省形”又涉及“省声”,包括从“瑩”“榮”“營”“勞”省在内,共涉及23例。这组言“省”之字,最为人诟病的就是“A从B省,B从C省,C从A省”这种循环解说,辗转相证的模式。到底何时该“从A省”,何时又“从B省”,让人摸不着头脑。李家祥对此更是直言:“各自省形相互为声……的等,更是混乱难析,随意性十分突出,它们不显现汉字的历史,不符合汉字固有的客观规律,是许氏在解字时的一种臆撰之说,非科学的理论。”[1]120这种解说方式确有随意之处,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反映汉字简化的客观历史,只是为了析字罢了。该组字的共同特点就是有共同的构件“”,而《说文》无此字,但金文有此字,许慎认为其不成字,所以比附《说文》中该构件的参构字,或言其“省形”或言其“省声”,只是为了不使其构件与功能“失联”罢了。类似的例子还有“贞、鼎”“伤、殤”等字,也是互相论证。
(三)利(从刀,从和省);埾(从土,从聚省)
利,析为“从和省”是为了牵合所引文献“《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的意义而作出的解释;埾,为了牵合所给出的“土積也”的意义而析为“从聚省”。两者之所以不解释为“从禾”“从取”只是因为“从和省”“从聚省”更符合字义解释的需要。
从以上典型例子可以看出,《说文》中大部分“省形”“省声”的例子都不是为了反映汉字减省的实际,而是为了汉字理据的重构,达到因形索其音义的目的,扫清字形与其音义之间的隔障,弥缝构件与其功能之间的疏离,是用来分析某些理据不明或理据丧失的字形的补救措施。
“省形”“省声”因其强大的字形说解能力使得后世学者对其一边批评一边却也有滥用的趋势。且不说《说文》中那些被人明确提出由后人增窜的例子[6]12,单就段玉裁、朱骏声这些《说文》大家注解《说文》的著作而言,“省形”“省声”字的数量也是大大超越了前代。这一方面说明了“省形”“省声”为字形解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汉字会逐渐记号化,变得不可分析。所以在因形释义或说音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为了教学识字,那“省形”“省声”体例,的确能调动人们联想记忆,是最快认知的有效途径。但如果是编纂字典辞书,就应该严格考证后再下决断,否则就会像许慎一样,留给后世诸多谜团,让研究的人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