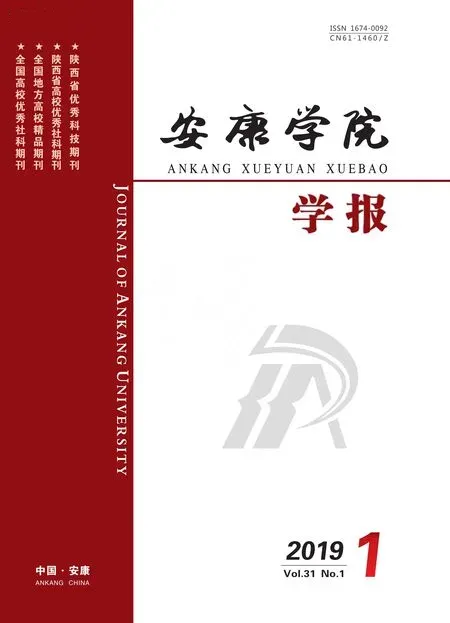有待乎内,无待乎外
——《童庆炳评传》札记
肖太云,阳惠芳
(1.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2.长江师范学院 图书馆,重庆 408100)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戏言,传的名目繁多,可以有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虽是小说中的一句调侃,却道出中国传记写作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多彩。当世的传记,一般分为自传、他传和评传三种。自传属于小传,用第一人称书写,给人以真切自然之感;他传用第三人称书写,往往客观允洽;评传属于一种特殊的他传,有传有评,丰富多元,要求作传者既熟悉传主的生平,又能洞察传主的思想,不容易写好,但也令读者解渴。吴子林的《童庆炳评传》就是一部精彩纷呈、大气朴素、让读者解渴的评传力作。他积七年之功,四易其稿,反复调整思路、完善结构、推敲语言,终成这部优秀之作。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吴子林有这样的学术诉求,也实现了这样的学术抱负。
吴子林是童先生的座下弟子,受其教,得其学,明其业。正如他在《后记》中的自述:“先生不仅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还赐予我理想、信念和勇气,点燃我的心灵之火,使我坚信精神的恒久力量。”[1]225他对童先生崇爱有加,童先生也喜欢他这个学生,有“毕竟同乡,毕竟师生,毕竟朋友”[1]224的知心之论。因此,《童庆炳评传》是一部有情感温度的书。首先,点缀于书页间的众多童先生儒雅可亲、风度翩翩的插图及童先生追悼会上莫言毕恭毕敬、庄重沉痛的哀悼画面,将一个蔼然有度、受人尊敬的长者形象直观地呈现了出来。其次,吴子林凭借对童先生的熟稔和洞悉,加上虔诚和尊恪,再现出了乃师的丰采和神韵。如对童先生“如佛”面相、“如佛”性格的刻画,对童先生“施恩如雨、温润如玉、挺拔如松、通达如桥、坚硬如钢”[1]70之学者人格的体认,对童先生“有待乎内,无待乎外”[1]60的研究境界的概括,都栩栩如生、呼之即出。当然,书中也有许多会心之笔,令人莞尔、受教。比如对童老师“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1]49的刻画和再现,形神俱备。一个善教、乐教的“老师”形象跃然纸上。纵览全书,从《自序》、正文、《结语》到《后记》,始终鼓荡着一股浓郁的激情。滚烫的写作,发烫的文字,灼热得阅读者脸发烫。内蕴着的感恩与怀念,流露出来的真情与不舍,让阅读者动容。热烈、诚挚而动情,是此书的第一大特点。
从传和评的次序与轻重来看,此书先为评,后为传;传为次,评为主。第一、二、三章为传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内容虽少,却不乏精彩。童先生的少年人生是一个励志故事。吴子林在第一章“农民之子”中,以轻松优美的文笔,将少年童庆炳写活了,朴实感人,又兼得趣味性,予人启迪。童庆炳出生于福建西部的连城山区,那里也是吴子林的老家。这片土地山美水美人纯净,给予少年童庆炳以审美的熏陶。按时下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家乡的怡人风物是童庆炳审美诗学的地理基因。“童庆炳的少年时代贫穷而又充满温情”[1]4,苦难的教育磨炼了他的心智,铸就了他的坚强;而祖母和母亲的温情又浇灌了他内心的柔软和善良。在艰苦的环境中爆发出来的“我要读书”的呐喊令人心酸又振聋发聩,其决心和意志令人动容。少年童庆炳的自立自强,与命运抗争的生命强力,在吴子林笔下得到了鲜活呈现。正如此章开首的题记:“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文精神,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1]1《童庆炳评传》是一部生命之书,不屈的命运之书,这是此书的第二个特点。
童庆炳先生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出身贫苦,为了读书历经坎坷。幸运的是龙岩师范学校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良好的氛围激发了青年童庆炳的求知欲,北京师范大学这座巍巍学府中的刘盼遂、李长之、钟敬文、黄药眠等名师的教益让他甘之如饴。更幸运的是在“社教”和“文革”的浪潮中,青年童庆炳获得了两次出国的机会,避开了那段动荡、混乱的岁月,在大使馆地下室的书库中饱览中外文史哲典籍,为他后来的人生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留校北师大任教更是为童庆炳先生提供了人生的舞台与展示自我的机会,从此他在宁静温馨的高校校园中游刃有余,达到人生和事业的巅峰。吴子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知人论世,有条不紊,语言清新自然,节奏收放自如,读来轻松愉悦,显示了作者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裁剪取舍编排方面的火候。这是一个在语言、叙述方面都很有特色的吴子林。叙述上的得心应手,叙事上的炉火纯青,这是此书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章至第九章是全书的重点和亮点,阐述的是童庆炳先生的学术思想。吴宓“恨不早十年遇白璧德师”[2],私心自誓“必当以耶稣所望于门徒者,躬行于吾身,以报本师,以殉真道”[3]。弟子对老师最好的纪念就是明其业,传其学。吴子林有这种明确的责任意识和学术自觉。他在《自序》中明言,研究童庆炳不仅是一个学术“薪火相传的过程”,而且可以“向世人展示中国学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昭示中国未来文学研究的路向”[1]6。他的这本评传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童庆炳先生是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一座高峰。如果说新中国第一代文艺理论家周扬、黄药眠等前辈学者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那么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文艺理论家则是立足于传统,在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对话与碰撞中创建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并建立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文艺理论界的范式及学科基础。吴子林完整展示了童先生自成体系的文艺学思想,写出了童先生为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做出自信自如的点评,这是此书的第四个特点。
拨乱反正之后的八十年代,中国文艺界需要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漩涡中摆脱出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亟需一次“审美的转向”。童庆炳先生应时而动,提出要创构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审美诗学”。这是一个回归文学本位、本质的提法,对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有深远影响。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诗学论是童庆炳先生文艺思想的核心和原点,他后来提出的各种理论都在此基础上生发而来。不管是以时间为序还是以重要性为序,吴子林理所当然先要交代清楚童先生的美学原点。他敏锐地抓住审美特征这个关键词,从“审美转向”“审美特征论”“文艺学第一原理”三个方面准确阐述了童先生的“审美诗学”观,并做出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颇具现实感的理论创构”[1]91的恰切点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极度弘扬。在此浪潮中,“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方兴未艾。童庆炳先生高瞻远瞩,从文艺心理学的论域来深入探析文学中的主体性问题,拓展出当代中国的“心理诗学”。他身体力行创作出《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等专著,并带领王一川、陶东风、李春青等一班弟子出版了“心理美学丛书”,提出审美研究要深入审美主体(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内心,探究审美主体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理机制的美学观点,引起极大反响。吴子林从理论的提出、发展与深化三个角度还原了童先生“心理诗学”观的理论历程,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各个理论阶段的核心观点。童先生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最新知识来系统阐述艺术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各种细腻、矛盾心理活动,并将创作主体的这一矛盾提升为文艺学的原理。吴子林对这一美学思想的把握、提炼和阐释尤见真章,极为精彩。他认为童先生的“心理诗学”是“纲举目张”,由此“把20世纪中国的文艺心理学从古典提到了现代的水平,使之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的界定也合情合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学出现新质,先锋文学关于文学形式的实验和探索执着而热闹。文学界的这一趋势需要文艺理论界做出及时应对与总结。童庆炳先生领时代之风骚,率先从文体层面做出思考和探索,建构出他文艺学思想的第三部曲——“文体诗学”。他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是其所有著作中被引次数最多的一部专著,与罗岗、王一川、陶东风、蒋原伦等门生一同出版的“文体学丛书”得到季羡林先生的肯定。吴子林从“文体三层面”“文体的功能”“文体的创造”三个角度切入,分门别类地评析了童先生的“文体诗学”思想,评价“其体系完备而又具有开放的态势”[1]131。“艺术作品中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逆反的相互征服运动”[1]126-127是童先生“文体诗学”的理论原创与精华之处。吴子林对这一理论闪光点做了充分阐析,评析透辟,直指鹄的,令人信服。
文艺理论家必须有开阔的眼界,比较的眼光,古今中外视野兼具,才能有大境界,成就大气象。无疑,在这方面,童庆炳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界的先行者、力促者和“戛戛独造者”[1]133。他兼收并蓄,开创一种“中西互证、古今沟通”的阐释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的吸收和转化,发展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比较诗学”理论。童先生主张古代文论的“转化”而不是“转换”。一字之差,显示出童先生的学术创见。他在历史优先、逻辑自洽、中西互为对话主体三原则的基础之上,重新解读了孔子、孟子、庄子、陆机、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李贽、王国维十大家的文论内涵及其现代意义,从而重新焕发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活力。童先生等人“在对话与沟通中改变西方现代文论独霸中国文学论坛的局面,进而为建设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做出贡献”[1]147-148。对此,吴子林有清醒的认知与准确的定性:“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研究实践,童庆炳有力地回答了在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如何保持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立品格和特色的重要问题”[1]148。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文学迅速边缘化,人文精神急剧衰落。有识之士发出呐喊,呼吁重建人文精神,重新确立价值、信仰对人的引导意义。有浓厚人文关怀的文化研究应运而生,成为当代的显学。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童庆炳先生持谨慎态度。在坚持审美论诗学的基本立场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审美主义的文化诗学”。他主张文化研究既要向微观的文本世界拓展,又要向宏观的文化视域拓展,强调文化研究的审美维度和诗学中心,反对“走火入魔”的“反诗意”的文化研究。在对“文化诗学”的不断探索和思考中,童先生又提出了颇富原创性的“历史—人文”张力说,认为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营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和平衡“应该是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理想”,并在他的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改编中重大问题研究”的课题中进行了研究实践。吴子林化繁为简、提纲挈领地对童先生的“文化诗学”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概述,特别是始终扣住童先生试图实现“文化诗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综合与超越这一基点进行评述,可谓精到扼要。
文学理论素养是大学文科生的必备素养,文学理论课程也是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童庆炳先生的可贵之处是使他的文学理论不只是藏于书阁之中、传播于同仁之间,而是使其转换成为大学的经典教材,走进千万学子的心间。童先生的文学理论教材通俗易懂又完整赅备,是文科学生不可多得的一本启蒙教材,注定要进入共和国的教材编撰史之中。它对莘莘学子文学理论的化育之功,确属功莫大焉。童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配得上任何赞誉。吴子林用专章来仔细梳理童先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修订过程,考究各个不同阶段教材的特点,用心良苦,是斟酌后的理性选择。在人民共和国文学理论教材流变史的整体视域中,以195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为参照背景,吴子林从《文学概论》的“初创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的“换代教材”到《文学理论新编》的“拓展教材”,一路细细道来,分析合理,定性准确,拿捏得恰到火候。对童先生文学理论教材的细致分析及对他在教材建设方面所作贡献的精确评述,形成了此书的第五个特点。
对童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解读与回望是此书的第六个特点。童先生对教育的思考及实践,构成了教育者童庆炳的一体两面。童先生不仅是一个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者,还是一个当代语文教育的思考与呼吁者。他对中国当代教育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他提出的“回归经典”、“赓续传统”、重视“文学教育”的语文教育新理念切中当下语文教育的症候。吴子林选用他人文字作为此章的内容,不失为一种灵活的处理策略,也体现出他对童先生进行“求全责备”评价的学术诉求。童先生作为一个教育者,不只是体现于对当下教育的观察与思考,更是体现于他的教育实践。吴子林以深情的笔墨,回忆他自己及众多同门在童门求学的情景,追叙莫言、余华、毕淑敏等作家听童先生在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讲授“创作美学”课程的往事,形成弟子眼中的“严师益友”与“作家眼中的理论家”两个序列,再加上对童先生“上课的感觉”的描述,构成“师魂永在”一章,颇见用心。本章之中,既有“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父亲’,备受学生热爱”[1]46的评价,也有对童先生研究心得的总结和分享。童先生将学术当宗教,他对学术研究过程的“进、出、进”,“无我、有我、证我”[1]52-53的简明扼要地概括,对任何一个研究者、阅读者都启发很大。读吴子林的书,无形之中就是在听童先生的课,受童先生的教。
“有待乎内,无待乎外”[1]60是童先生对自己学术追求的总结,也是他的学术境界、人格魅力之体现。吴子林的这本评传,将童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发扬光大,也将童先生的学术品格、人格魅力发扬光大。
当然,如果非得吹毛求疵的话,本书也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童庆炳评传》是于童先生在碧空如洗的金山岭长城驾鹤西去之后缮定、出版的。吴子林在平日对先生的敬爱、钦佩之中更增添了无限的怀念,使得评传的写作始终氤氲着一股浓郁、火烫的激情。如能拉开一点距离的话,此书也许会显得更为理性、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