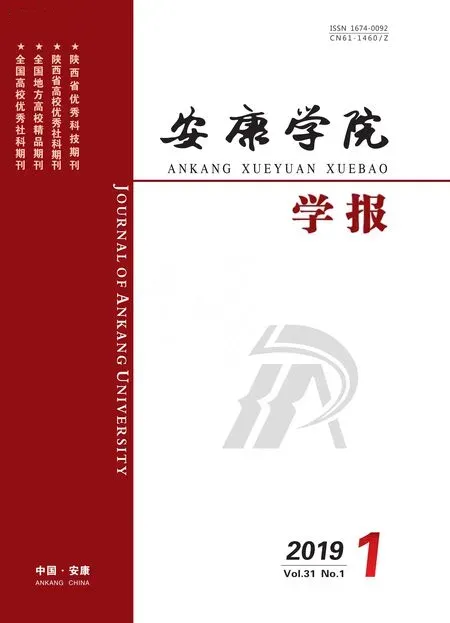《白噪音》中的死亡暗恐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 的长篇小说《白噪音》 (White Noise) 是一部闻名遐迩的后现代主义杰作,一经问世便获得美国文学大奖“全国图书奖”的殊荣。该书以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为背景,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工业污染、消费膨胀、阴谋诡计、家庭解体与重组、具有毁灭性的大众传媒以及人的堕落与恐惧等。在种种后现代危机之下,人类对死亡的思考贯穿了小说的始终。《白噪音》的中文版译者朱叶在译序中认为,唐·德里罗留给读者思索的重大问题就是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正“时时处处地笼罩在死亡恐惧的阴影之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白噪音》的研究多集中于小说中的生态意识、科技伦理、大众传媒、消费现象、后现代特征等,其中也有若干研究对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和死亡恐惧进行了探讨,但尚未有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出发研究小说中的死亡恐惧。在笔者看来,运用弗洛伊德的“暗恐(the uncanny)”理论能更加深入地分析小说中的死亡恐惧,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德里罗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
一、暗恐之表现
《白噪音》中的人物常常与幻觉相伴,比如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经常会瞥见彩色的光点,女儿斯泰菲(Steffie)在经历空中毒雾事件后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的症状。杰克的同事默里(Murray)有一套关于幻觉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会以为这些事情发生过?很简单。它们从前确实发生过,是在我们脑子里以未来的幻象出现的。因为这些事情是一些预想,我们无法按其目前的样子,将这些材料纳入我们的意识体系中。它本质上是超自然的玩意儿。我们展望未来,但是尚未学会分析这种经验。所以它藏而不露,直到预想成真,直到我们面对事件。现在,我们就尽可以记起它,将它当作熟悉的材料来体验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现幻觉情况呢?”
“因为死亡就在空气中。”他轻轻地说道,“它释放了被压制的材料。它使我们接近我们尚未了解的有关自身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见到过自己的死亡,但是不知道怎样使这素材显现。或许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说的头一桩事就是‘我知道这种感觉,我从前来过这儿’”。[1]166
这是杰克与默里的对话。在此之前,年过半百的杰克因为在毒雾中暴露了两分半钟而吸入了小剂量的尼奥丁,计算机的数据告诉他,这种物质的寿命是三十年,而且已经将死亡植入了他的体内,这意味着杰克已经走在了死亡的路上。得知自己的“死亡时间”后,杰克袒露自己从二十来岁开始就一直感到恐惧,而如今则是“果真应验了”[1]165。
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死亡恐惧恰好契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暗恐”的阐释。“暗恐”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于1906年提出的,弗洛伊德则在1919年的《暗恐》一文中对其进行了独到的阐述和发展。弗洛伊德认为,所谓“暗恐”,即“一种恐惧的情绪,它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就已认识且熟悉的事情”[2]220。他从词源的角度出发加以解释,指出暗恐的德文词“un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具有两种并存又相互矛盾的含义:“属于家的,不陌生的,熟悉的,受控制的,亲近的,友好的”[2]222,即“属家的”;“隐匿的,看不见的,他人无从得知或了解的”[2]223,即“非家的”。作为“heimlich”的反义词,“暗恐”既是属家的,又是非家的,是源于家(广义上)的非家恐惧。因此,童明先生提出,“非家幻觉”与“暗恐”这两种译法应当同时使用才能全面地理解这个概念的内涵,即“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上的某个源头”的“无以名状、突兀陌生”的恐惧体验[3]106。这恰恰是《白噪音》中的死亡恐惧所具有的特点,即熟悉与不熟悉并存,仿佛是过去死亡体验的重现。
这种过去的死亡体验并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小说中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感受,他们不可能亲历过死亡,但却目睹过死亡、认识过死亡。杰克曾提到他的妻子芭比特(Babette)在她母亲去世时崩溃,相比杰克,芭比特对死亡的抗拒尤为强烈,这才有了小说的第三部“戴乐儿闹剧”。而杰克作为一名希特勒的研究者,对现代历史上极为残忍的死亡事件一定非常熟悉。当他在某个夜晚错将自己的岳父认作“死神”时,他认为“死神”或者“死神”的听差“来自瘟疫时代、酷刑时代、无穷尽战争的时代”[1]265。另外,在小说中,杰克一家人常常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各种与死亡有关的报道,包括灾难、谋杀、犯罪等等。朱叶在译序中认为,这种“模拟”的死亡会麻醉观众,消解死亡的恐怖感,但笔者却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在他者的死亡中看到了自我的死亡。弗洛伊德的继承者、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在他的镜像阶段理论中提出,婴儿辨识出镜中的形象就是自己,并把它当作自己,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最初认同过程[4]。这一阶段需要“他者”的参与,对于镜像阶段的婴儿来说,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就是他者,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他者的死亡也成了自我死亡的镜像。每一次死亡事件不论是在史书上、电视中还是在身边复现,都会激起人的死亡暗恐。
杰克的女同事温妮(Winnie Richards)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件陌生和无所参照的事情[1]249。人们记得别人的死亡,他者的死亡是自我死亡的参照,这就是此后暗恐的种子。芭比特在服用治疗死亡恐惧的药物戴乐儿之后产生了记忆缺失的副作用,她觉得她的“记忆丧失是竭力抵制死亡恐惧的努力使然”[1]219,她也曾嫉妒和羡慕还是个婴儿的儿子怀尔德所具有的遗忘性[1]184。记忆中的死亡是熟悉的,它们被压抑在人的潜意识中,由此产生的恐惧情绪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的复现”,而所谓的“压抑的复现”正是“暗恐”的另一种表述[3]106。
弗洛伊德所解释的暗恐是以“double”的形式出现的,童明先生将其翻译为“复影”[3]110。所谓“复影”,它其实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心理阶段的创造物(creation)[2]236,与暗恐的出现如影随形。例如,《白噪音》中有一个故事之外的人物——希特勒,他是杰克的研究对象,小说中曾提到希特勒因为他的母亲死在圣诞树边而不能忍受待在任何圣诞节饰物的附近。圣诞饰物就是希特勒母亲之死的复影,当它出现的时候,暗恐就会袭来。对于书中的主要人物来说,作者多次提到的“身穿米莱克斯服、口戴呼吸面罩”的探测人员就是灾难和死亡的复影。第9章中,杰克的孩子所在的小学里有师生患了奇怪的病症,“孩子们头疼,眼睛发炎,嘴巴里还有一股金属的涩味。一个教师在地板上打滚,口中说着外国话”[1]37。调查员们认为这些毛病都是由建筑物引起的,于是这些探测人员就对整幢建筑物进行了扫描。第21章中,“空中毒雾事件”爆发,这些“穿戴着黄色米莱克斯服和防毒面具”的探测人员再次出现,并且在此后的故事中出现近十次。杰克说:“我们把这些装束与我们烦恼和恐惧的来源联系在一起。”[1]189准确地说,杰克的恐惧复影应该是这些探测人员的装束——看似全副武装、极具技术含量,却激起了人对现代化灾难的挥之不去的死亡恐惧。
二、暗恐之意义
作者德里罗曾在致读者信中表示,白噪音“泛指一切听不见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种声音”。书中的人物则将这样的声音与死亡相联系:
“假如死亡只不过是声音,那会怎么样?”
“电噪音。”
“你一直听得见它。四周全是声音。多么可怕。”
“始终如一,白色的。”[1]215
小说中的死亡暗恐在作者德里罗的笔下常常化作幽灵般的噪音,如孩子的哭泣声、垃圾压缩机的嘎吱声、电梯的嗡嗡声、车辆的鸣笛声、工厂的震动声等等,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在一切声音之上,或者在一切声音之下,还有一种无法判定来源的沉闷的吼声,好像出自人类感觉范围之外的某种形式的密集群居生物”[1]38。根据笔者在上文对暗恐之来源进行的阐释,这种给人类带来深深不安的未知“群居生物”极有可能是指已经死去的人。杰克曾在一块墓地边发出这样的感慨:“死者的力量在于我们认为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死者无时无处不在。是不是有一个层次的力完全来自死者?”[1]109而且,在小说的结尾,他重新定义了围绕在身边的各种声音:“这是波与辐射的语言,或者是死者向生者说话的方式”[1]358。
那么生者从死者那里都听到了什么呢?
首先,死亡的必然性。我们都会从已故的所有死者身上得出一个结论:人必有一死,无从反抗。小说中有一位非比寻常的死者,那就是希特勒,他是杰克的人生中“阴森森地忽隐忽现的史诗人物”[1]315。书中的人物默里曾说希特勒比死亡还要伟大,在笔者看来,这并非褒奖,而是在暗讽这个战争狂魔所犯下的累累死亡“业绩”。虽然杰克是一名连德语都不会说且不称职的希特勒研究员,但他的研究仍与战争和死亡密切相关。约翰·N·杜瓦尔曾指出,杰克的希特勒研究是他逃避死亡恐惧的一种途径[5]。默里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杰克“要把自己隐藏到希特勒和他的业绩中去”,同时利用他来增强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1]316。杰克曾提到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希特勒非常赞赏他的废墟价值理论(Theory of Ruin Value),想要以断壁残垣实现第三帝国的永恒,但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依然走向了终结。杰克依靠希特勒研究来反抗死亡恐惧的结局只会让他看到凡人必死的事实。
其次,死亡的新可能。杰克在毒雾事件中吸入尼奥丁后就走在了一条“新型”的死亡路上。这种致死的物质既不直接杀死他,又会使他活得更长,仿佛是给他判下了漫长、未知的死刑。随着社会的发展,死亡好像也在“发展”。“知识和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有死亡的一个新种类、新系统与之匹配。”[1]165飞机的轰鸣声、汽车的喇叭声、电视机的嗡嗡声等都在诉说着与原始死亡方式截然不同的新式死亡:死于空难、车祸或者波和辐射。人类很可能对此浑然不觉,但死亡却随时待命,“这就是现代死亡的特征”[1]164。二十世纪初期的死者和二十世纪末期的死者会向生者呈现多变、迥异的死亡方式,生者的死亡恐惧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古代人会畏惧雷电洪水,现代人则怕起了无处不在的白噪音。恐惧的感受还是原始的,但恐惧的来源则是陌生的。
于是,熟悉的死亡必然性和陌生的死亡可能性相互交织,“本该秘密、隐匿的东西暴露了出来”[1]225,形成了后现代背景下的死亡暗恐。《白噪音》就是作者对暗恐背后的科技公害、超速发展、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三、暗恐之负面美学
弗洛伊德认为,美学不仅仅是关于美的理论,还是关于情绪的理论。他在《暗恐》一文的开篇就直指传统美学的问题所在:偏爱美好的、有吸引力的、崇高的事物。但美学不只包含了积极正面的感受,还应关注厌恶、悲苦等截然不同的负面情绪[2]219。所谓负面美学,指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形成的美学,这“并非以前曾被简单斥为堕落、消极、反动的资产阶级美学倾向,恰恰相反,负面美学所强烈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反思能力”[3]111。《白噪音》中的死亡暗恐所反思的就是后现代背景下人的异化。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主人公的恐惧之源皆在于他者:他者的死亡像幽灵一样重复出现,时时刻刻都在构建着人物自我的死亡。自我里住进了他者,于是产生了陌生感,人对自己也失去了信任,继而对生命也失去了信任。默里建议杰克通过杀死他人来解除他自己的死亡恐惧,杰克采纳了他的方法,尝试杀死占有了他妻子、鼓吹戴乐儿药物的格雷先生。克里斯蒂娃(Kristeva) 在《陌生的自我》 (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书中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他者,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外人[6]。若是我们能反向运用这一逻辑,那么杰克杀死格雷的行为其实是他自己在杀死自己。芭比特曾将格雷先生称作一个“综合体”,他其实可以被看作杰克的另一面,他们在恐惧死亡这件事情上的差别只是反抗恐惧的方式不同——杰克选择在希特勒研究中躲避死亡恐惧,格雷选择用新式药物“治疗”死亡恐惧,而后者反抗死亡的方式却一直在折磨着杰克。格雷于杰克而言既是外在的他者也是内心的他者,这场谋杀的本质是自我伤害,这场谋杀的终极走向是人类的自相残杀,比如战争。克里斯蒂娃在解读弗洛伊德的暗恐时认为,能否消除人类内心的陌生感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内心的幽灵共处[6]191。也就是说,我们要直面内心中的他者,这不失为化解死亡暗恐的一种途径。
()()
杰克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时说道:“我们的恐惧带来了死亡。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害怕,我们就可以永生。”[1]310可见,书中的主人公十分渴望化解自己对死亡的暗恐。直面自己内心中的他者虽然需要个人在精神层面的努力,但一个生态凋零、科技异化的外部世界无疑是难以摆脱死亡噪音的,对后者的反思正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重要意图,对人类负面情绪的关注也是对当下社会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