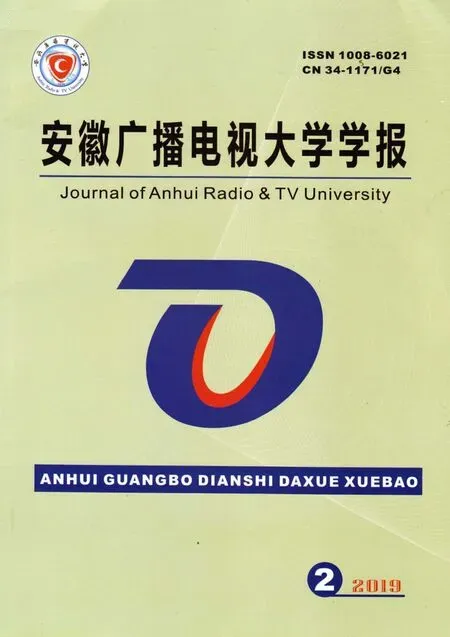《杀瓜》:犹豫不决的言说
——以小说原著为比照的解读
高 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高则豪导演的电影《杀瓜》改编自董立勃的同名短篇小说。电影在保留原著的人物设置和大致故事情节之余,做了别具匠心的改编,改编后的电影与原著相比呈现出了犹豫不决的面貌,而这背后又分明蕴含着一种新型叙事伦理。
一、复杂的乡村基层与虚弱的现实批判
电影《杀瓜》保留了小说原著的大概故事情节: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常年在公路边卖瓜的本分老实的瓜农陈草,有一天遇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买了他的瓜还在他的瓜棚里眯了一会,醒了给他付钱的时候丢了一百块在瓜棚里,他追出去还钱,没有追上。正在陈草返回瓜棚的时候,一辆失控的汽车撞塌了他的瓜棚,车主赔了钱离去,陈草则拿着钱不住说万幸,认为要不是那一百块,自己早已归西。不久有警察来询问那个摩托车男的行踪,陈草如实告知了。后来他才知道摩托车男名叫刘红国,他因为选举时没有投村长的票,被村长嫉恨,生活中处处遭到村长的报复打击,于是走上了反抗之路。最终刘红国被捕归案,陈草因举报有功,获奖一万块,村委会主任王大强也觉得脸上有光。但陈草却认为是自己害了刘红国,心理愧疚不已,并把奖金全数捐给了地震灾区。虽然电影《杀瓜》保留了同名小说的基本故事框架,但电影也在小说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调整和更改,正是这些改变清晰地显示出导演的犹豫与矛盾。
首先,小说中的王大强是一个霸道蛮横的村干部形象,他经常到陈草这里拉西瓜,每次都让陈草挑最大最甜的并开下空头欠条,并说“西瓜是村委会要用来招待上级来检查工作的干部的”“用陈草的西瓜招待上级领导,是看得起陈草是陈草的光荣”[1]。陈草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加之父亲生前是个老党员,一直教导他要听领导的话,所以陈草也就逆来顺受、不敢反对。小说塑造的这个村干部形象,分明指向了基层干部的强势、自私、欺凌百姓等现实黑暗面,是对乡村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的揭露与批判。与之不同,电影中的王大强尽管也有着爱慕功名的一面,如领导要来给陈草颁奖,电视台也要来采访时,他认为这是一个增光露脸的好时机,因此便仔细装扮陈草并训练他如何应答。但电影中的王大强更多的时候却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乡村干部形象,电影中的王大强不仅从来不欠陈草的西瓜钱,而且他还苦苦奔走在领导与村民两者之间,上下周旋应对、受尽委屈。比如,王大强为了招待领导到陈草那里买瓜时向其倾诉道,领导的秘书说不用太铺张浪费,只要四个菜一个汤,但王大强心里清楚必须得置办一桌好菜才能体现本村的热情,因此便忙着准备招待事宜,以至于屁股上起了火疖子。这样,本来对于乡村底层社会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批判被更改为对于乡村底层干部的同情。一为批判的言说,一为同情的观照,它们均折射了乡村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之一角。也就是说,乡村干部的权力滥用与其处于令人同情的左右为难的困局,都是乡村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它们的并存说明了乡村底层社会面貌的复杂性。电影之所以弱化小说对王大强这一角色的批判性,便是导演认识到乡村底层社会的复杂面貌后的犹豫之举。乡村干部既要面对上级的逼压,又得苦口婆心地与散漫的民众纠缠,这一夹层处境,使得导演很难对其作出坚决的批判。
其次,电影中的刘红国与小说相比,弱化了其反抗的决绝色彩。小说中的刘红国因为选举时没有投村长的票,还声称村长不够资格当村长,因而受到村长的嫉恨,不仅自己在生活中处处遭到村长的打击,其女儿也常常受到村长儿子的欺负,刘红国为此找村长论理和向上级告发均无果并被村长找人暴打一顿后,在一个黑夜用杀猪刀杀掉了村长一家八口。最终,小说中的刘红国被枪毙了。而电影中的刘红国遭受了同样的凌辱后,只是把村长家一头羊头剁下放到了村长媳妇的炕上,躲在门口的刘红国遇见村长回家便给其兜头一闷棍,村长当即昏倒,而刘红国误以为把村长打死了,所以才连夜逃跑。电影中的刘红国被捕后认罪态度良好,村民也联名为其求情,他最后也得以提前释放。与之相似,小说中的陈草在刘红国的感召下最终也走上了反抗之路,他在王大强又一次来拉瓜时举起手中的杀瓜刀,坚定地告知自此以后“不能欠账”并要求还钱。电影中的陈草则依旧安分守己,他老老实实地按照王大强称许的“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的规矩行事。“立住的人物形象”是电影的批判性“得以建立的支点”[2],电影《杀瓜》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刘红国和陈草与小说相比,均不那么坚挺,而是显出妥协的面影,这同样是缘于乡土底层社会复杂境况导致的现实批判的虚弱与犹豫。在导演看来,乡土底层社会压迫与反抗都不会那么惊心动魄,不是必须诉诸刀光剑影的决绝。更重要的是,乡土底层社会流传沿袭下来的一些规矩和准则,一方面是一种桎梏,但另一方面又的确有其合理性的价值。如此一来,面对乡村现实的批判只能走向犹豫。
二、利弊参半的规矩与前后矛盾的颂扬
尽管小说与电影中的刘红国均是陈草平静生活的“入侵者”,他的到来使陈草渐渐开始学会了思考,甚至走上了反抗之路。但是,与小说相比,电影中的刘红国带给陈草的冲击更为巨大,因为电影中刘红国给陈草讲了一段关于野生瓜和裂口瓜的道理。小说中的刘红国到陈草瓜棚里吃了西瓜后便匆匆离去,而电影中刘红国在陈草瓜棚里睡了一觉,醒来时还和陈草聊起了种瓜的经验之谈。陈草知道刘红国也种过瓜后便向其请教,自己该给瓜浇水就浇水,该施肥便施肥,一切都遵照规矩进行打理,可为何地里却长出那么多裂口瓜?刘红国回答,不同的瓜身处的土壤环境不同,因此不同的瓜需要不同对待,当你给每个瓜都一视同仁地浇水施肥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刘红国还和陈草讲起了野生西瓜,说野生西瓜个头小、味道不好,但野生西瓜结出的果子绝不会有裂口子。因为天地造化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好,但不会像人工种植的东西那样,规矩多了毛病也就多了。与野生瓜的道理类似,刘红国还讲起自己养过一头不同寻常的猪,它能模仿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各种声音,但就是不老老实实待在圈里做一只正经的肉猪,这最终给它带去了麻烦。刘红国口里的这头猪分明就是王小波笔下那头“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说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敢于无视对生活的设置”,并感叹“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3]总之,刘红国给陈草讲述的有关野生西瓜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蕴含着规矩与反抗、压迫与自由的道理,加之刘红国本人从被欺凌走上抗争之路的经历,凡此种种,均在陈草老实本分的平静生活中激起了波澜,它们提供了“一个反讽的透视角度,由此烛照其他人物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4],进而使得陈草这个一直处于安分守己状态的农民开始萌生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思。
刘红国的“闯入”不仅给陈草讲了有关野生瓜和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还给陈草揭示了关于“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规矩存在的弊病。王大强曾送给陈草一本红册子,里面就详细讲解了“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规矩,王大强认为只要村民都按照册子里古人说的话行事,“那样就天下太平,和谐社会”,陈草也觉得王大强说得有理。刘红国针对“君为臣纲”询问陈草假使你是大臣,而皇上要你去死,你怎么选择?陈草一下子陷入了茫然。然后又针对“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问陈草的妻子和孩子听话与否,陈草答说妻子倒是听自己的话,就是儿子不太听话,因此他觉得也该让儿子读读这本小册子。刘红国笑问陈草,如果你让自己的儿子去死,他该不该听话?陈草急了说再怎么老子也不可能让儿子去死的。刘红国退而求其次问道如果你儿子是大臣,现在皇上要让你儿子去死,又怎么办?陈草辩解说那可不行,他皇上凭什么无缘无故让自己儿子去死呢。刘红国沉默了一会儿紧接着讲到,这小本子上还有一句话“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经由这一番谈话,陈草渐渐领悟到刘红国的言下之意是皇上让自己去死,自己也不是非得去死。黑格尔说“完整的心灵在分化为他的个别性相之中,就须离开它的静穆,违反它自己而进入紊乱世界的矛盾对立。”[5]这段有关“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规矩的交流,是野生瓜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接着说”,它们都是打破陈草的“静穆”生存状态,将其引入“紊乱世界的矛盾对立”的助因,并起到了确立陈草独立自主的个体性的作用。
在刘红国的指教与感召下,陈草貌似就要变成了第二个刘红国,就要变成了一个“野生瓜”,他后来不是对妻子说“现在觉得,儿子不听我的话问题也不大,他终归是咱俩的儿子。儿子也不是什么事都得听老子的”嘛。然而,在导演看来要完全违背、舍弃延续已久的规矩并非理所当然,也不是万全之策。规矩的存在虽有束缚的危害,但若尽数忘却规矩,又会犹如负薪救火适得其反。因此陈草对刘红国说“种西瓜还得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你说野生西瓜不裂口,但你也说了这野生西瓜小而不甜,没人要不卖钱吗?”因此,陈草依然践行着“仁义礼智信”的规矩,他听闻刘红国出狱后,二话不说便前去寻找刘红国归还其一百块钱,并向王大强说:“这别人掉的钱多久都得还上。你不是跟我说过,仁义礼智信嘛,最后一条是信,我们做人必须要讲诚信。”影片结尾,当陈草最终骑着自行车前去还钱时,一轮落日斜挂天际,霞光射下,笼罩在陈草身上、铺满整个电影画面,而“色彩是电影中的下意识元素。它有强烈的情绪性,诉诸的不是意识和知性,而是表现性和气氛。”[6]故而柔和的落日余晖形构出极富诗意的场景,传达出温情而美好的气氛,这无疑是对卑微的陈草所信奉与持守的规矩的颂扬。
电影前半段一直在通过刘红国对陈草的宣讲来反思社会上种种规矩对人造成的禁锢、压抑和戕害,这时陈草是一个底层“傻瓜”形象,他身处被“杀”的境地却不自知,而刘红国的到来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无知。可到了电影后半段,当陈草反复且固执地寻求归还刘红国遗失的金钱,当陈草面对刘红国因自己的举报而锒铛入狱,自己却收到政府的奖金而惴惴不安并选择把奖金全部捐出时,我们又分明感到时刻按照规矩行事的陈草的高贵之处,分明感到导演对规矩与践行规矩的陈草的颂扬。一边在反思与解构规矩,一边又在表彰与颂扬践行规矩的人,这种矛盾实乃导演面对利弊皆备的规矩时的犹豫之举。规矩既会损害人的多元性又能保障社会有条不紊地运转,因此批判显得不那么毅然决然,而颂扬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这种在矛盾中生存挣扎的景象正是人类的真实处境:一方面我们努力寻求自由,竭力推翻一切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不断设置种种规矩以期将人类引向安全有序的道路。一方面是对自主性的呼唤与追逐,另一方面又是对蓬勃的自主性的呵斥与限制。在此意义上,所谓自主的主体性往往是值得怀疑的说法,因为我们时刻生活在种种关系网络之中,这些关系网络为我们设置了种种规矩,我们无法不受其引导。
三、犹豫背后的新型叙事伦理
高则豪的《杀瓜》与其《目击者》一样,都充满了戏剧张力,“也都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生命的思考”[7]。但与《目击者》不同的是,《杀瓜》的言说与表述处处充满了犹豫不决的况味。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情形,使其现实批判性与小说原著相比弱化不少;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规矩好坏皆备,又使其在人性高贵的张扬方面难以做到义无反顾。总之,《杀瓜》是一部面对复杂现实的犹豫不决的言说之作,其中缺乏斩钉截铁的说辞,鲜有界限分明的判断,随处可见的是纠缠不清、自相矛盾的表露。这不是电影《杀瓜》的缺陋,相反恰恰构成了电影《杀瓜》的独特价值,它的犹豫不决背后体现出了一种新型的叙事伦理。
一直以来醉心于乡土写作的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秦腔》的后记中深情诉说道:“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8]《秦腔》叙写了乡土中国在城镇化围困下的破败,写了乡土人在城镇生活的吸引下的逃离与眷念。面对这一切,贾平凹没有选择明确的赞颂或者诅咒,而是诉诸充满迷惘与矛盾的言说,借此为故乡“树碑立传”。因为贾平凹的矛盾与困惑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的诚实体会,“世道人心本是宽广、复杂、蕴藏着无穷可能性的,谁能保证自己对它们都是‘知道’的呢?”在学者谢有顺看来,贾平凹这种满怀矛盾的写作实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他的“不知道”非但没有影响作品的厚度,反而扩大了作品的精神格局,予人无限思索[9]。换言之,贾平凹的写作不拘囿于正反好坏、高低优劣的简单化价值判断,不惮于给人矛盾重重的感觉,宁愿舍弃鲜明直接且吸人眼球的断语,也要认真感悟、探查与呈现人间万象的夹缠共生性与复杂矛盾性。这一不黏滞于俗常道德准则与价值判断的新型叙事伦理,是“勇于探查灵魂究竟”[10]和直面世相本真的叙事维度,予人以超越而宽广的认知视野。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高则豪导演的电影虽然不像董立勃的小说原著那样态度分明,而是充满着犹豫,但这种犹豫是面对复杂现实与复杂生存处境的犹豫,它是一种真诚的坦露,不局限于现实经验和现世道德的泥淖,而是竭力通达有重量的精神世界,具备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是名副其实的新型叙事伦理。“电影导演旨在探索某个时刻的深度和多层意义”[6]310,很难设想如若高则豪在《杀瓜》中舍弃了犹豫不决的表达,选择了明晰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电影还能触及现实社会与生存真相的深度和多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