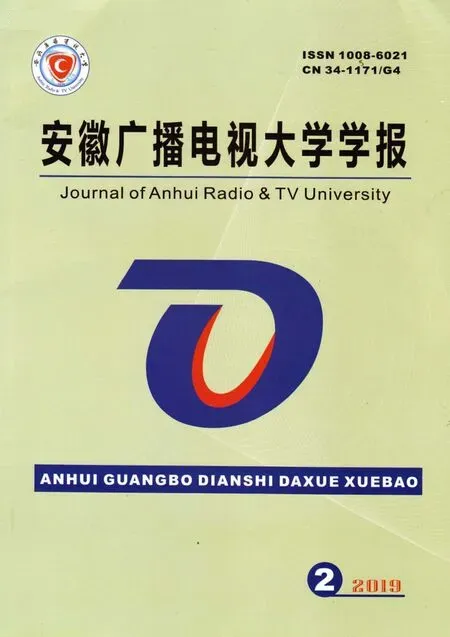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构造
简筱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武汉 430073)
一、问题的提出
以天津静海李文星案为契机,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打击非法传销活动的专项斗争。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在《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传销经营活动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坚决予以禁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要求将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以非法经营罪论处。非法传销行为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七》)在第224条之后增加一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实现对非法传销行为的特殊规制。以《修七》为转折点,刑法对非法传销行为的规制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修七》将刑法所规制之传销活动由原始型传销活动或经营性传销活动转变为诈骗型传销活动。其次,《修七》使非法传销行为的适用罪名由非法经营罪等边缘性罪名转变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专门性罪名。再次,刑法规制对象由非法传销活动本身转变为非法传销活动的组织与领导行为。最后,行为主体范围由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犯罪分子等缩减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1]。
适用罪名以及具体要件的变化也预示着非法传销活动相关罪名保护法益的变化。尽管作为兜底条款的非法经营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均位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一节,但是《修七》以前存在的规制非法传销活动的罪名并不局限于非法经营罪,而是包含集资诈骗罪、诈骗罪等侵害财产法益的罪名。即便《修七》新设立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也是以“骗取财物”作为其本质特征[2]。传销活动总是与财产利益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纠葛。此外,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中明确要求组织者、领导者的行为“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又与市场秩序之间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关联。所以,《修七》的变动并未使非法传销活动的规制“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处于一种扑朔迷离、飘忽不定的游离状态。为了肃清此种虚无缥缈之态,笔者拟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构造出发,探清其本质特征,以便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以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判断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二、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争
有学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组织参加者实施了传销行为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程度,无须造成一定程度的严重结果即可构成犯罪[3]。还有学者则认为,本罪是结果犯[4]。笔者认为,在进行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判断之前有两个前置性问题需要特别探讨:一,各论者所使用结果犯概念中危害结果为何?二,行为犯与结果犯之间的区分标准为何?如果不能站在统一的语境进行对话,上述学者的论述不过是自说自话。
(一)“危害结果”概念的厘清
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两组重要的“结果”概念,即构成要件结果和非构成要件结果以及物质性结果和非物质性结果。其中,构成要件结果与非构成要件结果的区别在于结果是不是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要求具备的要件。笔者认为,这组概念分类并不具有任何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构成要件结果与非构成要件结果分类的初始目的是提示危害结果构成要件的存在及其与量刑结果之间的区分意义。但是,对构成要件结果的提示以及对定罪结果与量刑结果的区分取决于刑法的明文规定,而不取决于刑法理论的事后归结。其次,构成要件结果与非构成要件结果的分类无法统摄现实案件中的所有危害结果类型。现实案件中的危害结果包括定罪结果、量刑结果和刑法不予关注的结果三类。构成要件结果与非构成要件结果的区分,只能划定定罪结果与后二结果之间的界限,却无法区辨量刑结果与刑法不予关注的结果。最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实质区别在于特定犯罪是否要求一定的损害结果作为成立要件,如果要求,就是结果犯,该结果就是构成要件结果;反之,则是行为犯,特定的结果就是非构成要件结果。本来要求一定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就是结果犯,但是此时构成要件结果的判断却更多地依赖结果犯的认定,有本末倒置之嫌。
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的区别则在于存在形态的差别。物质性结果是客观存在的、能够为人的感官所感知的,具有一定的时空维度的物质改变,例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死亡结果,盗窃罪中的财产损失;非物质性结果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果,但是其通常难以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并且不具有一定的时空维度,例如侮辱罪、诽谤罪中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损害。[注]物质性结果和非物质性结果与构成要件结果和非构成要件结果两组概念之间是交叉关系,构成要件结果与非构成要件结果中均可以存在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结果,两者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以侮辱罪为例,侮辱罪中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损害是典型的非物质性结果,但是我国《刑法》第246条仅仅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要件。根据理论通说,刑法对结果要件的规定往往是以“造成……结果”为范式,“情节严重”仅仅是对行为的方式、样态和程度的描述,侮辱罪是典型的行为犯。但是,既然肯定侮辱罪中的人格尊严与名誉损害的非物质性结果的存在,缘何对其置之不理而一意孤行地将其界定为行为犯?有一种可能是此处的非物质性结果并非从犯罪客观方面而是从犯罪客体方面来把握。然而根据通说对犯罪客体与危害结果之间征表与被征表关系的理解,两者之间显然不能简单混同。所以,只能在构成要件要素的意义上把握非物质性危害结果。
(二)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界分
通说认为,行为犯是只要求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即构成犯罪的犯罪,结果犯是除却实施一定的行为,只有发生一定的结果犯罪才告成立的犯罪[5]。张明楷教授则认为,法益侵害是现代犯罪的本质,任何行为要构成犯罪必须造成法益侵害或者侵害危险,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时空上的间隔[6]。笔者原则上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一方面,倘若坚持现代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犯,那么犯罪的成立便离不开法益侵害结果或者危险结果,即便是传统理论认为的行为犯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传统刑法理论语境下的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过于拘泥于危害结果的物质性。但是随着法益概念精神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否认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存在,会使刑法的精神化、伦理化加强,使得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因伦理性的欠缺而成为刑法的规制对象。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时空间隔的结果犯。首先,组织、领导行为的对象是传销组织,还是传销活动?有学者认为,组织、领导行为所针对的是诈骗型传销组织[7],有学者则认为,组织、领导行为所针对的是传销活动[8]。如果认为本罪的行为对象是传销组织,那么只有当传销活动实施到一定程度,团体发展到一定规模,满足刑法所打击的组织规模时,才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当传销团体发展到组织程度时,社会秩序被扰乱的危险已然存在,组织、领导行为与社会秩序被扰乱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传销组织的构成特征而无须另行判断。如果认为本罪的行为对象是传销活动,那么传销活动就存在一个由无害到有害再到危害重大的发展过程,组织、领导行为与传销活动之间的因果关联,传销活动与社会秩序扰乱结果之间的关联以及组织、领导行为与社会秩序扰乱结果之间的关联就成为需要特别判断的对象。依笔者之见,既然刑法规范文本中并未出现任何与“传销组织”相关联的词汇,并且多次使用“传销活动”的表述,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考虑,就不能恣意地将组织、领导行为的对象界定为传销组织。其次,组织、领导行为存在一个缓慢的形成过程。根据传统理论和2013年《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3年《意见》),组织、领导行为是指为成立某种组织而实施的发起、招募、雇佣拉拢人员的行为以及对组织及其活动的策划、指挥和布置行为。由于刑法对非法传销行为构成犯罪作出了人员和规模的要求,行为人的组织、领导行为必须满足“三十人以上、三级以上”的要件要求。因而在满足规模要件要求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存在切断因果流程的情形,如行为人在实施组织、领导行为的过程中,尚未满足上述量化要求,即被公安机关扫除。所以,行为与结果并非同时产生而没有另行判断的必要,反而由于存在多种介入因素需要对因果关系给予特殊关注。
三、危险犯与实害犯之辩
危险犯与实害犯是实质犯内部的分类。现代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那么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必须侵犯法益。其中,因为法益侵害结果而构成犯罪的,是实害犯;因为法益侵害危险而构成犯罪的,是危险犯。概念的界定本身并不存在十分重大的分歧,但是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存在形态却为学者们争论不休。即一种犯罪只能存在一种形态,还是可以同时兼顾危险犯与实害犯两种形态?
(一)实害犯与危险犯的存在形态
有学者认为,危险犯与实害犯作为相对应的犯罪概念不能在同一罪名的同一条款中并存。某种犯罪要么是危险犯,要么是实害犯,而不可能既是危险犯又是实害犯[9]。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危险犯与结果犯之间处于一种对应且对立的状态[10]。而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危险犯与实害犯的概念是相对于刑法所保护的具体的法益而言的,指称的是犯罪的具体形态而不是罪名,所以,针对保护复合法益的犯罪而言,其既可能是危险犯,也可能是实害犯[11]。笔者原则上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
首先,既然某种行为构成犯罪要么侵害法益,要么威胁法益,那么行为究竟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就必须在与法益相关联的意义上进行把握。所以,在以复合法益作为侵犯客体的犯罪中,完全可能对一法益是实害犯而对另一法益是危险犯。例如,在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中,行为人使用暴力等手段非法控制被害人后,在索取财物的目的实现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抓捕的,针对人身法益是实害犯,针对财产法益则是危险犯。其次,危险犯与实害犯针对的是具体犯罪的具体形态,而非罪名。例如,故意杀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既遂犯是实害犯,而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危险的未遂犯则是危险犯。再次,危险犯与结果犯之间并非对应关系。危险犯的对应概念是实害犯,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结果形态的差异;结果犯的对应概念是行为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间隔,因果关系是否需要单独判断。所以,在危险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意义上认定两者之间不可能在同一罪名或同一条款中共存疑问。最后,认为同一罪名或同一条款能否同时存在这两种形态,反映出论者不同的思维方式。认为只能是危险犯或实害犯的,是立足于对罪名性质的分析,以犯罪认定为视角;认为可以同时是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则立足于对法益侵害的分析,以犯罪发生为视角。而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分类本身就立足于对法益的侵害程度的区别,所以应当认为同一罪名可以同时存在实害犯和危险犯两种形态。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保护法益
既然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区辨在于法益受侵害的程度,那么在判断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构造之前,就有必要确证本罪的保护法益。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保护法益,学者们的观点颇为多样,大体上可以分为单一客体和复杂客体。主张单一客体的学者相对较少,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市场秩序[12]。主张复杂客体的学者则相对较多且观点不一,部分学者认为本罪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和社会管理秩序[13],部分学者认为本罪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1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本罪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15]。上述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众多弊端。
首先,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单一客体的观点过于狭隘。根据《刑法》第224条之一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一方面,侵害了财产法益和社会管理秩序;另一方面,很多被害人因为传销活动而精神失常或者自杀身亡,又侵犯了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其次,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所有权有待商榷。现代刑法理论通常认为权利与权利对象之间存在区别,作为权利对象的利益本身具有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权利作为刑法所规定之犯罪的保护法益会不当地限缩刑法的保护范围。再次,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和社会管理秩序忽略了刑法的罪名设置原则。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设置依据的是保护法益之间的关联,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置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说明了“市场秩序”是本罪的保护法益(之一)。最后,认定本罪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复合法益同样存在问题。因为该论点实际上是单一客体和复杂客体中第二种观点的简单结合,并未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所以,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财产法益、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生命健康安全符合论理和规范的要求。
(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形态类型
如上所述,危险犯与实害犯是针对具体法益的犯罪形态。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针对其所侵害的财产法益、市场经济秩序、生命健康安全等法益的不同可能呈现不同的状态,有必要分法益对行为构造形态进行具体分析。
就财产法益而言,只要行为人开始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不管是否骗取到财物,只要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成立犯罪(预备或未遂)。所以,行为人所实施的组织、领导传销行为既可能是针对财产法益的实害犯,也可能是针对财产法益的危险犯。
就市场经济秩序而言,本罪几乎不可能是针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实害犯。首先,虽然传销活动对市场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府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之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可能因为传销活动而市场失灵。其次,根据2013年《意见》,只要行为符合其所规定“情节严重”之情形,不管行为事实上是否威胁到市场经济秩序,均认为已经存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危险。这种法律推定或者立法拟制在我国刑法中并不罕见,比如近两年经常讨论的醉驾入刑问题,只要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并驾驶机动车的,就推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最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传销活动也可能存在。一方面,市场经济秩序不仅可以指全国经济秩序,也可以指区域经济秩序,影响区域经济秩序的非法传销活动完全可以存在。另一方面,非法传销活动之所以在当前形势下无法对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动摇,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强力调控。当国家的调控弱化,而完全由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时,市场秩序完全可能为非法传销活动所动摇。
就生命健康法益而言,行为人的组织、领导行为一般不会直接导致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但是却可能在高压“训练”“管制”之下导致被害人不堪重负精神失常。所以生命法益通常是以间接的方式被侵害,健康法益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侵害。应该说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是保护生命健康法益的专门罪名,生命健康法益受侵害只是2013年《意见》[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四、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对符合本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一)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三)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四)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所列举的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所以,如果以生命健康法益受到侵害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因素,侵害必须是现实发生的。即针对生命健康法益只能是实害犯。
四、小结
行为构造的研究主要包括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争以及危险犯与实害犯之辨。由于行为人在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过程中完全可能因为意志内外的原因导致因果流程中断,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时空间隔意义上的结果犯。危险犯与实害犯是针对具体法益的侵害形态而言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侵害法益包括财产法益、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生命健康安全。针对财产法益,其可能是实害犯或危险犯;针对市场经济秩序,其通常是危险犯;针对生命健康法益,其只能是实害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