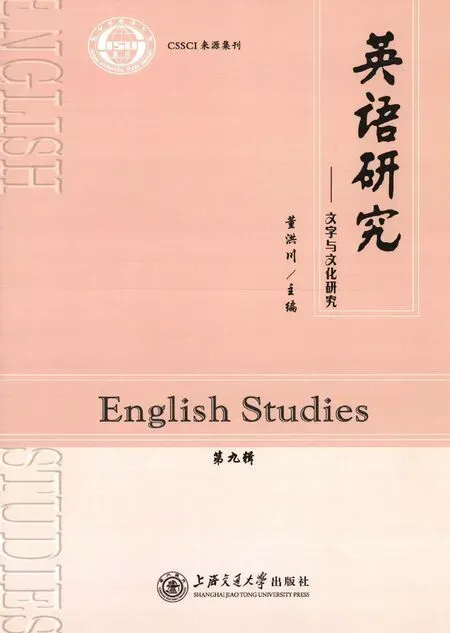美国非裔奴隶叙事文类研究
王 欣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0.引言
美国非裔奴隶叙事(以下简称为奴隶叙事)开始于18世纪,兴盛于美国内战前后,作为对残酷奴隶制的见证,为废除奴隶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760年,第一部黑人奴隶自传《黑人布列顿·哈蒙亲身经历的残酷折磨及侥幸脱险的故事,他原是新英格兰马氏菲尔德的温斯洛将军的仆人,在离家13年后重返波士顿》出版,这本由奴隶本人口述,白人作家执笔的传记开启了非裔奴隶叙事的文学历史。据斯大林 (Starling)(1981:331)统计,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大约有6000余名北美非裔,通过访谈、回忆录、论文、自传等,讲述过奴隶制中的个人和家庭的遭遇。评论家们一般将奴隶叙事归于自传的文类,斯大林(1981:331)指出:“奴隶叙事是由美国奴隶的自传或半自传构成的,或是以书的形式发表,或保存记录于法庭或教会,或在期刊发表中被发现,也有大多数存于没有发表的文集中。”不可否认,奴隶叙事诞生于美国特有的社会语境,起源于英美文学传统中的自传文类,但又具有独特的叙事组织原则和主题,其产生和创作都与美国内战前后的意识形态、废奴运动和奴隶的身份诉求密切相关。从文类的角度研究奴隶叙事,可以探索奴隶叙事和文学自传传统之间的异同,开拓奴隶叙事的研究空间,反映该领域研究的整体方向。
1.自传和奴隶叙事的文类研究
作为文类的一种,自传在西方传统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sofSaintAugustine)或卢梭的《忏悔录》(Confessions) 、歌德的《诗与真》(PoetryandTruth)以及华滋华尔斯的《序曲》(Prelude)等自传经典作品。帕斯卡尔在《自传中的计划和真理》(DesignandTruthinAutobiography)中指出,自传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自我知识。帕瑞尼认为,自传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以奥古斯丁和卢梭为代表的“忏悔录”(confession),作者暴露他内心的挣扎或喜悦——一种私人经验的记录。另一种是“回忆录”(memoir),作者提供外部事件的编年史:战争、政治斗争、商业冒险;个人在历史大舞台上成了主角。(Parini, 1999: 11) 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忏悔录及自传等文类的流行,标志着启蒙运动时期对个人生活的兴趣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写作成为一种了解自己和自我对话的方式。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自传“autobiography”一词最初来源于英国诗人罗伯特·萨尔西于1809年的一篇评论。从字面上看,autobiography 是由autos, bios, graphein 构成。 Autos指“自我”(self)或“他自己”(himself), bios 指“生活、生平”(life),graphein指“写作”(write),合起来“autos+bios+graphein”的意思是“自己写作自身的经历”。从词源构成来看,自传的文类特点也着重于作者、内容和写作三个方面。自传中的auto指“我”的叙事,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自传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或自述故事叙述(autodiegetic narrative),叙述者同时也是主人公,或是英雄人物;二是自传中的“我”,既是叙事行为的创作者和发起者,又是叙事行为的承担者。这就形成了真实作者和作者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之间的张力,叙事行为本身成为对自我的观察和剖析,自传也因此成为自我认识和自我成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叙事一经开始就表示着作者一段生活的结束,因为“传主总是知道他的结尾——或者说,在写作的那一刻,他就是故事的结尾” (Andrews, 1993:212)。所以当叙事开始的时候,“我”的视角就存在着经验自我和正在经历的自我之间的张力。前者对事件的发展和后果已经明晰,而后者却模拟了处于事件发生中的视角,对于事件的后果懵然不知。叙述主体和经验主体之间的这种张力也形成了读者阅读视野的视差,随着作者认知和经验的发展,读者也获得了相应的知识。
自传的bios是对个人历史的回顾,涉及自我认知、个人情感、自我认同、自我描写和自我身份塑造,在时间上常常呈现出线性发展的先后顺序,并在人格塑造上具有整体性。作者以“某时某事发生后的”经验视角进行书写,“将他或她的命运视作一个整体”,并努力去创造一个关于过去的统一的画面。 (Millim, 2013:15) 欧尼(James Olney)认为,自传,或是“回忆的叙事行为……不是中立的或被动的记录,而是创造性地积极的塑造者……记忆通过叙述事件而创造事件的意义”(Andrews, 1993:212)。由此可见,自传的内容通常指渉过去的历史,围绕着传主的个人生活,选择性地记录某一段重要的历史时刻,或者一生的经历。这种“我,我的灵魂”(“moi, moi seul”)的范式,要求自传主体应当如实记录个人的生平,把个人生活和情感秘密告知读者;另一方面,读者被迫作为见证人,见证作者的生活经历。莱日恩把读者与作品的这种关系称之为“自传的协定”(autobiographical contract):读者接受作者所说的话,且认为作者对自身生活的叙述是真实的;怀疑作者的真实性就是否定作品的自传身份。真实性成为检验自传的一个重要标准。
作为一种文类,自传在美国文学历史上源远流长,具有政治意义。路易斯·卡普兰编辑的《美国自传书刊目录》收集了1945年之前在美国出版的6377部自传,玛丽·布里斯克编辑的《美国自传:1945—1980》则收录了5008部自传。帕瑞尼(Parini)(1999:1)指出:“自传可以很容易被称为美国的基础文类,一种和我们国家自我意识紧密相连的写作形式。”在美国自传的文学传统影响下,非裔奴隶叙事采纳并改造了自传的文本体裁,从写作范式和社会话语领域两方面,发展成为一种具备美国特点的创新文类。富兰克林(Franklin)(1977:27)认为,奴隶叙事是“美国对文学世界所贡献的第一种文类”。 奴隶叙事也成为非裔文学的起源,查理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论文的标题说明了其对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奴隶叙事:一种黑人传统中萌生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Gates, 1982: 83)。欧尼呼应了戴维斯,指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在主题上同时也在内容和形式上,奴隶叙事都是非裔美国文学的传统起源”(Davis,1985:168)。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奴隶叙事有时也被称为“奴隶的叙事”(slave’s narrative),笔者认为,slave narrative更为准确一些: 前者的所有格形式容易让人误会作者的身份。应该指出,slave这里指代叙事的话题,而不是指作者的法律身份,因为它们通常是由逃跑的或已经自由的奴隶们写作或口述的,换句话说,当作者书写的时候,其身份已经不再是奴隶,只不过其书写的内容却集中在被奴役的经历上。另外,如果使用“slave’s narrative”,这个所有格形式意味着由某人拥有的叙事,具备个人化的色彩,而忽略了奴隶叙事的集体性和整体性特征。反之,去掉所有格“’s”,则标志着叙事的类型。
2.奴隶叙事的自觉性和自我书写
奴隶叙事的生产和流通和美国内战前后的意识形态斗争紧密相关,其书写具有显明的自觉性,传主的身份成为这一文类最重要的焦点。在《奴隶叙事》(TheSlaue’sNarrative)中,戴维斯和盖茨(Gates)这样定义道:“奴隶叙事仅指1865年前发表的书面文本,(因为)这之后奴隶制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他们这样解释道:“我们把1930年联邦作家项目收集的奴隶叙事口述编纂成论文。我们出于文学原因将这个时间作为结束之日:这种叙事的特殊结构……在他们写作的氛围……改变后,也极大地改变了。……一旦奴隶制正式停止了,也就没有需要让奴隶们通过第一人称叙事写作使自己被认同为人类群体。” (Davis et al, 1985: xii-xiii) 从盖茨等对奴隶叙事的定义可以看出,这一文类的时间性和传主的身份密切相关。不同于其他自传作者,非裔奴隶叙事的前奴隶身份注定了这一文类不仅是个人生平的记录,还是自我追求自由的方式,其书写本身即是非裔前奴隶对蓄奴制的控诉,表明他们具备人的天性、天赋和人的权利。
奴隶叙事的出发点是“彰显非裔作者的黑人性,证明他们自己是与别的人种,尤其与白人人种的平等存在,表明他们作为人所具备的特点和潜能,是欲与白人种族主义对抗的一种策略和方式” (赵宏维, 2011: 169)。也就是说,奴隶叙事的书写具有反抗白人话语并运用贬低化策略的自觉性。在蓄奴制的社会制度中,非裔黑人长期受到种族歧视,法律并不承认其公民权利,他们被视为“财产”,而不是作为“人”而存在。1850年,为了保障奴隶主的“财产”不受到损失,来自美国北方的妥协分子和南方蓄奴州联合起来,发布了《逃亡奴隶法》:允许所有居民抓捕逃亡奴隶,任何被发现向逃亡奴隶提供帮助的人都将面临高达1000美元的罚金或被判决监禁。1857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起诉桑福德》审理中,有七名赞同南方蓄奴制的法官支持这项判决,宣布任何有碍于奴隶制扩展的行为和意图都是违宪的。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Taney甚至还说,黑人“是如此低劣,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白人有必要尊重的权利;所有黑人都可以公正而合法地被贬为奴隶”(史托弗, 2011: 183)。就这位代表美国司法的最高行政官看来,黑人不是“美国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这意味着白人的司法话语体系中,黑人并不具备天赋人权,也没有公民的权利。
不仅法律上不能提供公义,文学上对黑人的再现也有扭曲。佛斯特(Francis Smith Foster)总结道:美国内战前文学中黑人形象只是“寓言家、忠诚的仆人、逗乐的小丑、悲剧的八分之一混血儿、高贵的野蛮人或造反者”。或者说,内战前黑人形象有五种原型:不幸者、自由民、小丑、满足的奴隶、受害者,或者后三种的综合体。 (Foster, 1979: 71) 这些固化的语言和人物模式,贬低黑人的智力,从而替奴隶制的合理性辩护。因此,为了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奴隶叙事有意识地借鉴了美国革命时期的自传,从中找到了黑人争取自由和读写能力的内在联系。作为美国自传的经典之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结合了忏悔录和回忆录的两种形式,构建了新大陆上“典范人生”的范式:即美国范式的自我依靠、自我素养和自我实现的新世界福音。以此为榜样,非裔叙事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传,吸取了富兰克林自传中的关于自我提升、自我塑造、个人主义等精神。和富兰克林一样,他通过模仿学习,通过自学阅读和写作,完成了“自我塑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道格拉斯的写作具有显明的作者意图,构筑了自觉的写作范式,从其自传标题《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由他本人亲自撰写》可以看出其两个关键词“一个奴隶”和“亲自撰写”,结合起来就说明了道格拉斯的经历——其过去是一个附属的奴隶,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作者。 (Douglass, 1846: 124) 标题本身就显示了一个前奴隶精神上的进步,说明了其独立自主的个体身份。事实上,几乎每一本奴隶叙述的标题都要加上“由他自己撰写”,以突出传主的读写能力。福尔曼指出:“对亲奴隶制辩论最有效的反击就是关于叙述者智力能力的证据——【他的】叙事。”(Furman, 1979: 140-41)叙事是黑人内在的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测试证明。在当时废奴运动的话语争锋中,这份证言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
不过,和西方传统自传相比,奴隶叙事虽然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但更多强调的是自我的转变,而不是传统自传中的自我成长和进步。这种转变甚至受到质疑。1845年,道格拉斯自传发表后,其前主人汤普森写给《达拉威尔共和国报》编辑的信中,质疑自传作者的身份:他指出“大约八年前,我认识这个怯懦的奴隶,他那时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贝利(而不是道格拉斯)”,“他那时和科威(道格拉斯提到的训奴专家)住,当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非常普通的黑奴,我很自信的肯定他那时没有能力写这里谈到的传记;他只不过是一个受过点教育的,懂得一些语法规则的人,不可能写得这么正确;尽管想做的令人称赞勉力而为,但写作者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写的平实,而这一点做作证明了整篇文章臭名昭著和不真实”。而道格拉斯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你很自信认为我写不出这本书,你的自信的原因在于,当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没多少文化且非常普通的黑奴。好吧,我必须正告你,你是在非常不利于我的情况下认识我的……即使有人七年前告诉我我可以念出这本自传叙事,还不要说写出这本书,我都不会相信这个预言。我那时受到压榨,科威毒打摧残我到如此境地,以至于我的精神已经被摧毁破裂。自由人弗雷德里克是完全不同于奴隶弗雷德里克的……自由给予了我新的生命。” (Andrews, 1991: 66) 道格拉斯的回答,对于前奴隶主人强调了自我转变:自由带来自我认知的转变,以及读写能力对自我的塑形。在奴隶制下,非裔奴隶无法拥有历史性的身份,如名字、出生地点或居住地、具体事件的时间等,部分原因是身份模糊,另外是不能对外公布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奴隶贩子追捕。而奴隶叙事的发表通常代表着获得自由,其解放和自由的标志在奴隶自传结尾处,体现为前奴隶拥有了一个新名字,并且能够将自己生活中的时间、地点和社会事件相联系,取得了个人身份所需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标记。因此,自传文类中“我”的因素对于奴隶叙事来说,具有自觉的主体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重要意义。
3.相似性和重复性:作为证言的奴隶叙事
相比于现代自传对于自我的定义和自我成长的回顾,奴隶叙事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相应的修辞策略。盖茨(1987: xii)在《奴隶叙事》的介绍中,将这一文类称之为“关于黑人奴隶状况的书面或口头的证词”。从1770到1807年,当奴隶贸易在英国和美国被禁止的时候,废奴运动组织就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奴隶自传,为奴隶叙事提供修辞策略,帮助打磨其政治焦点,这成为奴隶叙事话语产生和流通的重要语境。奴隶叙事在政治上为废奴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言:首先,作为对废奴运动的贡献,它们对于战前废奴的辩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奴隶叙事参与了战前美国发生的民主化进程,使“民主”成为国家政治,特别是1820中期之后的美国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修辞和实践;最后,奴隶叙事使美国公民反思自由的定义,重新思考人权的概念。奴隶叙事为废奴运动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来自非裔奴隶关于奴役和自由的经历及例证。 (Fisch, 2007: 28-29)
因此,前奴隶作为见证人,奴隶叙事作为证言的再现方式很快成为废奴主义者提倡的修辞模式。1838年,辉格诗人惠提尔在其编纂的奴隶叙事《詹姆斯·威廉姆斯叙事》(TheNarrativeofJamesWilliams)的前言中,提到“奴隶主的证词和看法仅仅是那些奴隶主所言,” 因此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他坚持“为了更完整地看到奴役的秘密,我们必须看看奴隶自己的(证词)”(Whittier, 1838: xvii)。1848年,沃森(Henry Wastson)(1848:38)他的叙事中应和道:“二十六年以来,我的人生的大部分,是在奴隶制中度过的,我见证了它的整个形式。”同样的,逃亡奴隶班克斯在他的1861年的叙事中,提到“我是美国奴隶制的反方证人,见证了它所有的恐怖”;而雅各布斯在她的《女奴叙事》(IncidentsintheLifeofaSlaveGirl)中表达她的愿望是,“为能写的笔增加一段证言,来让自由州的人们信服奴隶制的真实面目”(Jacobs, 1987:1-2)。因此,证言成为奴隶叙事一项特殊而重要的社会功能。
奴隶叙事作为证言,主要作用是提供知识:一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奴隶制下奴隶的悲惨遭遇,奴隶主的虚伪和残暴,为废奴运动提供经验性的和客观的证据;二是以个体的写作,来结构性地重塑黑人族裔的集体形象。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奴隶叙事不囿于传统自传对个人的特殊经历的写作范式;而是通过相似的个人故事,重复性地塑造集体叙事,构建集体记忆。欧尼在“‘我出生了’:奴隶叙事,作为自传和作为文类的情况”中总结了奴隶叙事形式上的几大相似的要素:
(1)一副版画,由作者签名;
(2)标题页,包括作为标题内部一部分的声明,“由他自己撰写或类似的:“基于他自己陈述的事实撰写”;或“由他的朋友、兄弟撰写”;
(3)一份手书的证明,或者几份前言或介绍,由叙述者的白人废奴主义者朋友撰写;或白人文书、编辑、实际的写作者撰写,在前言中读者会被告知,这个叙事是一个“平实、质朴的故事”,“没有放进去一丁点恶意,没有夸张,没有任何想象:实际上,这个故事,(仅仅是)保守地描述了奴隶制的恐怖”;
(4)一个诗意的名言;
(5)实际的叙事,包含了内容相似的12类要点;
(6)一份或多份附录,包含文件性质的买卖账单,奴隶被买卖的详情,新闻报道,关于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弥撒、演讲、诗歌等,呼吁读者投入资金和道义的支持,帮助反对奴隶制的战役。 (Davis, 1985: 153)
形式上的相似性,有助于加强读者对于奴隶叙事这一文类的证言作用的印象。除了在形式上的类同,奴隶叙事还保持了内容上的高度一致。戴维斯总结了奴隶叙事内容统一的组织原则,指出奴隶叙事的内容具有以下相似性:①奴隶制的野蛮和非人待遇;②奴隶逐渐认识到自由和社群的需要,认识到为了结束奴隶境况,需要掩饰自己增长的智慧;③奴隶能描绘(经历)的人物和地点以及能将自己的见解和事件结合;④读者意识;⑤主要讲述自身经历中重要的事件;⑥讲述一个特殊的黑人伙伴生平的故事;⑦讲述黑人的遭遇。(Davis, 1982: 83-119) 通过这些相似的内容,前奴隶从两方面完成了反对奴隶制的证词:一是自身经历,二是所见所闻。两者都以事实见证了奴隶制对传主自身、家庭、亲友的残酷剥削、虐待和残杀,造成了奴隶家庭破裂、骨肉分离,呼唤读者出于法律正义和宗教公义来支持废除奴隶制。同时,为了凸显其真实性,奴隶叙事通常在正文之后,附有大量的补录以及附录,包括作者生平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具有法律证词意义的报告,如路条,通信记录,被买卖的收据等,以证实文本中提到的一些事实。欧尼查证后指出:“附录通常是由文件式的内容构成—买卖的账单,从奴隶主手中购买(自由)的细节,新闻报纸……或关于奴隶制,弥撒,反奴隶制的演讲,诗歌的回忆记录等,(以)请求读者在反对奴隶制的战斗中提供经费和道义的支持。” (Davis, 1985: 153) 奴隶叙事通过这些事实证据,揭露和鞭挞蓄奴制的残酷和罪恶,从而为反对和废除奴隶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词。
奴隶叙事内容和结构上的相似性,并没有削弱其叙事功能,反而通过一再地重复,增强了其自传的真实感。欧尼认为,相比于自传autos+bios+graphein的组成要素,奴隶自传可以用“autophylography”来定义,“(自传)描绘的是个人的‘我’,其传主侧重自身独一无二的特别性,并想象他的经历是不可重复的和没有可重复性的;非裔叙述者们却不同,他们描绘的是‘我们和我们大家’,其生活经历是为一个集体——被一个种族——所共享。” (Andrews, 1993: 218) 正是因为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相似性,并通过重复的方式,证明了奴隶制度的残暴,从整体而言,实现了废奴运动将奴隶叙事作为证言的目的。斯通认为:
既然奴隶叙事和废奴运动紧密相连,而且主要出现在内战前的三十年前,现代读者会倾向于关心这些书的历史语境—它们的写作和出版,它们的接受和影响,以及他们对历史真实性和准确性的确认。道格拉斯等人的确为创造一种重要的反抗和宣传的文学做出了贡献,但不可否认,历史性从来不会和这些工作的文化价值无关——关系到文学风格、修辞策略、心理显现和动机。作为自传,道格拉斯的叙事和其他作品一样,占据了在历史和艺术,传记和小说,记忆和想象之间的位置。当前奴隶被问到这个其他传记作者也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写这个我生平的故事?”时,回答直接明了:描绘作为动产(奴隶)的经历,而不是一个白人读者要去摧毁的压迫机构的一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创造一种有说服力的历史真实和准确的印象。所以道格拉斯的编辑说,“读者们的注意力不是应邀在艺术作品上,而是在事实上。(Andrews, 1991: 63)
为了凸显证言的事实性和真实性,奴隶叙事的重复生产构筑了一个文本历史化的可能空间,体现为数量化生产,因而创造出前奴隶集体写作或者群体证言的盛况,“数量”成为废奴运动对奴隶叙事的需求。美国废奴组织(The AASS)编撰和出版的《美国奴隶如实录:一千份证人的证词》(AmericanSlaveryasItIs:TestimonyofaThousandWitnesses),其选材就来自超过两万份的新闻报纸剪辑。不仅如此,组织者还呼吁更多的人来作证,指出“所有在任何情况下了解这个国家中奴隶情况的人,都来提供他们的证词”;呼吁“不要让任何人因为其他人已经为同样的事实做过证就禁止他的发言。” 他们仔细地解释道:“证言的价值绝对不是靠它描述的可怕事实的新奇来衡量的”,强调“确凿的证据、事实,(即使)和那些已经证实的其他证言相同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Weld, 1969: 4)在这种数量的需求下,道格拉斯修改并扩充他的第二部自传《我的束缚和我的自由》(MyBondageandMyFreedom),以便提供更多的“事实”。斯托夫人用《打开汤姆叔叔小屋的钥匙;提供故事的原始文件事实》来增补《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内容;同样也促使所罗门·诺斯诺普在他的自传《逃奴十二年》(1853)中这样介绍道,“这是《汤姆叔叔小屋》的另一把钥匙” (Northup: 1968: xxvii)。这种集体写作意味着非裔奴隶们争取身份的自觉的斗争。盖茨认为,奴隶叙事“代表着黑人通过写作来证实存在的努力,” 因为“每一个作者都知道所有的黑奴都要靠里面的一页提供的公开的证据来被评判” (Davis, 1987: ix)。奴隶叙事不仅仅是个人的声音,也是一种集体的共有的事业,即“一种集体的发声,一个集体的故事” (Larson, 1998: 431)。据非裔学者查尔斯·尼克尔斯(Nichols)(1963:xii-xv)的统计,在1831—1865年期间,非裔奴隶叙事成为美国出版市场的重要读物,种数达到数千册,有的自传,如乔西亚·汉森自传累计印刷印数高达上万册(Nichols,1963:xii-xv)。正是通过数量繁多的奴隶叙事,通过重复的、相似的形式和内容,奴隶叙事成为美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记载了南北战争前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奴隶制下黑人的悲惨状况,刻画了一系列重要的非裔历史人物的形象,从而在美国文学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4.结语
“我们如果正视事实,就必须承认:尽管奴隶制残酷和不道德,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一千万黑人由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经历了美国奴隶制这个学校,因此与地球上任何一部分的同等数目的黑人相比,在物质上、知识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处于更坚强、更有希望的地位。” (McDowell, 1989: 66) 奴隶叙事为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种文类,奴隶叙事之间相似的结构方式和情节安排,以及重复性等生产特征,成为自传体系中独特的一种体裁。这种形式的特殊性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需求,构筑了一个文本历史化的可能空间,同时凸显了其作者的独特身份和特殊经历。由于非裔奴隶叙事的文类性质和特征,自传和奴隶叙事的文类差异其实也是一种话语差异,造成了不同的读者的期待视域。奴隶叙事具有显明的作者意图,并构造了自觉的写作模式,以见证和证言的方式,成为美国蓄奴制历史记忆的承载物,也成了非裔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