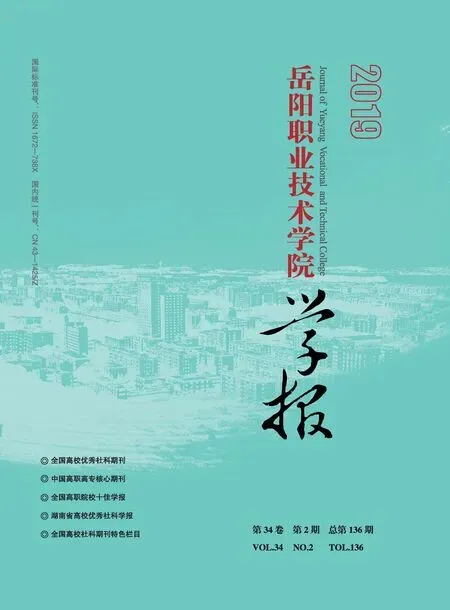论张竹坡《金瓶梅》批评中的“文笔之法”
张国栋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金瓶梅》为何被称为奇书?它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相比,《金瓶梅》将视角转向了社会市井和底层人民的生活,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金瓶梅》独创的网状叙事结构,打破了单线叙事的格局,张竹坡更评论其“人各有一传”“千百人合成一传”[1]的叙事结构实现了对《史记》的继承和超越。《金瓶梅》的行文,“文字如行云冉冉,流水潺潺,无一粘滞死住”[2]。《金瓶梅》的一奇在于其成功的人物刻画,一改以往“人物出场定性”的惯例,为人物赋予了鲜活的血肉,其人物描写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如在目前。更是将一群生活在一起的相似女性描绘出不同之处,潘金莲的淫、李瓶儿的痴、潘春梅的傲,人物特点各不相同,张竹坡亦评价道:“《金瓶梅》一书,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2]其文笔之妙令人叹为观止。
1 穿针引线之法
《金瓶梅》运用网状叙事结构,将众多的人物和情节包含在内,且条分缕析,清晰明了而不杂乱。它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片段和高潮,但前后脉络勾连,很难截然拆开,常常是故事中套故事,交互回环式推进[3]。张竹坡亦赞道:“然则《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2]《金瓶梅》将千针万线同为一线为枢纽,虽洋洋洒洒一百回,众多的人物、故事情节却相互贯通连接,互为架构,浑然天成。“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2]作者笔法高超,犹如穿针引线的高手,将众多如牛毛的细小末节贯穿起来,进行穿插夹叙、前伏后应、遥遥相照,行文起伏顿挫。众多情节丝线共同为主线服务,针线细密,天然相通。
1.1 细针密线
针细线密才可天衣无缝、浑然天成,彰显作者的文笔细腻之功底。“然丽丽洋洋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2]张竹坡在评点中十分赞赏《金瓶梅》的金针之细,在评点中予以着重说明。“若《金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只分别字句,细心者皆可为,欲随目成趣知文字细密者看下半部,亦何不可。”[2]“《金瓶梅》行世已久,予喜其文之整密,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2]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具有的豪迈气概不同,《金瓶梅》聚焦于生活中的琐粹事情,家长里短、饭后茶余均为其着重描写的对象。人物的每一个动作、表情,所说的每一句话、词汇,都可体现人物的心理、作者的意图,这对于书中情节的理解和主旨的把握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书中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杨姑娘气骂张四舅”中,竹坡评道:“是作者特借一月琴,将翡翠轩、葡萄架的文字,皆借入玉楼传中也。文字神妙处,谁谓是粗心人可解。”[2]此回中,翡翠轩对葡萄架,金莲弹琵琶相对于玉楼抚月琴,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相热处对于孟玉楼被冷处。仅此一回,作者巧妙构思,地点相对、乐器相对、冷热相对,且各个地点、乐器均有特殊的寓意。作者如此的文笔细腻、巧妙安排,提高了其文学价值。又如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一文中,“此回文字,最是难写。题虽两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笔写去,内却前前后后穿针递线,一丝不苟。真是龙门一手出来,不敢曰又一龙门也。”[2]此一回描写“瓶儿死去,办法事”,出场人物众多,如瓶儿、西门、伯爵、潘道士、吴银儿、王姑子、冯妈妈、如意、花子由等人物,而且众多人物之间的亲疏厚薄关系、浅深恩怨等亦有描写,一丝不苟,层层写出。每个人面对瓶儿死去的感情有所不同,“西门是痛,月娘是假,玉楼是淡,金莲是快。故西门之言,月娘便恼;西门之哭,玉楼不见;金莲之言,西门发怒也。情事如画。”[2]如此众多人物,作者亦将每个人的细微情感描绘栩栩如生,情事如眼前画面一般。作者心思细腻如此。情节的建构是一本书的骨骼,而细针密线的文字铺排则是一本书的血肉,血肉丰满才可以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1.2 穿插夹叙
穿插夹叙,即在顺序叙事的同时插入相近、或前或后的情节和人物,以达到情节波澜起伏、抑扬顿挫的效果。同时,使读者转移注意力,放松紧张的心情,使各处情节相互照应。在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读法》中,“《金瓶梅》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请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2]极尽能事的穿插夹叙之法,显示出作者的文笔高超、穿针引线能力的巧妙。每到事情发展到紧急的时候便转入另一件事情,在忙笔之中插入闲笔,一松一紧、一张一弛,令读者欣然神往。
张竹坡亦评“正写金莲,忽插入玉楼,奇矣。今又正写瓶儿,忽插敬济,绝妙章法。然此露敬济之来,下回遇金莲,方写敬济之事,则又对照中故为参差处。”[2]作者的穿插夹叙之法不是盲目、无目的的,在写作之前,作者早已将所有的人物和情节均了然于胸,某一情节的穿插,在下文中必然有文字对应这一情节。挖坑与填坑,作者写作一丝不差,如写金莲时,忽插入敬济,至下回写瓶儿时,必回写敬济一事,层层写出,一丝不苟。“上文自十四回至此,总是瓶儿文字。内穿插他人,如敬济等,皆是趁窝和泥。此犹娶瓶儿传内事,却接叙金莲、敬济一事。妙绝。”[2]《金瓶梅》中的一些穿插夹叙是“趁窝和泥”,在主线情节之外,加入一些辅助性的文字,无伤大雅,起到缓解紧张情节、舒缓读者情感的作用。穿插夹叙之法在《金瓶梅》中随处可见,作者运用此法十分自如,人物和情节参差不齐、错落有致,颇有文学结构的美感。张竹坡对作者的穿插夹叙之法颇为赞赏,认为即使太史公作《史记》的手法,也不过如此。
1.3 前伏后应
作者在写作本书,进行情节的穿针引线之时颇为细腻,常常设置悬念,前面种因,后面结果。作文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增加文学表达效果。竹坡评道:“文有写他处却照此处者,为顾盼照应伏线法。文有写此处却是写下文者,为脱卸影喻接入法。此回乃脱卸影喻接入法也。试思十日二十日,方知吾不尔欺。”[2]张竹坡将前后照应法分为两种,顾盼照应伏线法和脱卸影喻接入法。在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露阳惊爱月,李瓶儿睹物哭官哥”一回中,前伏后应之法体现得更为醇熟。“上文一路写官哥小胆,写猫,至此方一笔结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细。二句道尽,遂使推换猫上墙,打狗关门,早为今日打狗伤人,猫惊官哥之因,一丝不差。然后知其以前瓶儿打狗唤猫,后金莲打狗养猫,特特照应,使看者之官哥即子虚之化身也。”[2]此回,张竹坡详细解读“官哥为子虚化身”的前后照应,前写官哥胆小怕猫狗,瓶儿、金莲呼狗唤猫,后写官哥被猫所惊吓而死;官哥死时,瓶儿梦见花子虚来索债,知是官哥为花子虚的化身。作者文字细腻,穿针引线之中埋伏笔,前后照应,疏而不漏。
作者在运用“前伏后线”之法时,并不是简单地前埋伏线后照应的固定模式,有时亦写虚晃之笔以掩盖所埋的伏线。竹坡评道:“作者每于伏一线时,每恐为人看出,必用一笔遮盖之。一部《金瓶》,皆是如此。”[2]可见作者亦追求文学创作中悬念的效果,使读者表面看之无意识,等看过之后回味过来才觉得异常惊喜。如《金瓶梅》第二回“俏潘娘帘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说技”一文中,写潘金莲和武大吵闹了几次,便每天打开帘子,倚着窗子作样。至武大回来前,先收去帘子,关上大门。此处“落帘”便是伏笔,为以后“落帘打西门”提供了条件。但武大回来看到潘金莲如此守道,心中暗喜,认为“恁的却不好”[2]。此处便为遮盖文笔,用武大的“暗喜”来遮盖“落帘”这一伏笔,使读者不曾注意到“帘子”之一物件,等读到“落帘惊西门”时,才发觉“帘子”这一物件早在前文出现数次,使读者拥有满满的惊喜。
在《金瓶梅》这个庞大的网状结构中,作者穿针引线,运用巧妙的叙事技巧,将诸多琐碎的情节事件和人物有序地穿插起来,遥遥相照而有章法,共同服务于主线。“人各有一线,而千针万线同为一线”。
2 行文之法
章法结构的穿针引线建立了一个大间架,其行文之笔则填补其间的血脉和血肉。“白描”手法在《金瓶梅》中运用颇为成功,如情如画、毛发皆动,形象逼真。除了平铺直叙之外,曲笔和闲笔的运用更增添了《金瓶梅》的美感,文字跌宕起伏。“白描”的平铺直叙之中插入曲笔,增添了文学艺术性;“忙笔”之中插入“闲笔”,一松一紧,一张一弛,提高了可读性;写一是二,一笔用作千万笔,遥遥相映,奇妙笔法。
课堂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而课堂教学要素繁多,涉及面广,既包括教学方法的设计、教学手段的运用,又包括教学实践环节的安排、学生成绩的考核和教学效果的评价,这些都需要教师设计与优化。
2.1 曲笔
“凡人用曲笔处,一曲两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则?如本意欲出金莲,却不肯如寻常小说云‘按下此处不言,再表一个人,姓甚名谁’的恶套。乃何如下笔?因思从兄弟‘冷遇’处带出金莲;然则如何出此两兄弟?则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则用打虎。”[2]曲笔在《金瓶梅》中的应用已出神入化,随处可见,《金瓶梅》的曲笔之妙已至如此。《金瓶梅》为何为明朝“四大奇书”之首?在人物的设置和出场、情节的安排方面早已脱离俗套、不落窠臼,人物转换已不生硬。将众多人物的转换融入发展的情节之中,步步紧跟,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倒推而来,武松打虎引出武二,再出金莲,关系紧密,穿针引线,人物情节曲中有曲,读者读之不露破绽,仍觉文笔之妙。
作者将“曲笔”运用之高妙,其用笔不露痕迹,浑然天成,读者亦未发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用笔不露痕迹处也。其所以不露痕迹处,总之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2]张竹坡亦表明了曲笔运用之艰难。“夫此书头绪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数也。我执笔时,亦想用曲笔、逆笔,但不能如他曲得无迹、逆得不觉耳。”[2]可见“曲得无迹、逆不觉耳”是对作者曲笔运用的最高评价。文中曲笔之妙处处皆有,此不必一一展示,文字千曲百曲之妙,手写到此处,心思却到了另一处,穿插引用,遥遥相照。
2.2 闲笔
闲笔即消闲之笔,忙笔之中及时、合适地插入闲笔可以使行文更加流畅,避免情节过于紧张,舒缓人物情感。故作消闲之笔,如娶玉楼、嫁大姐、玉箫受约等都是极重要事件,但却在小说韵律节奏流动中,以极轻松、消闲的笔墨插入,使小说情节节奏避免平铺直叙,而是跌宕起伏,错落有致,这真正是大章法、大手笔[4]。
闲笔虽穿插于忙笔之中,但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为后文做铺垫,促进情节顺承发展,前后遥遥相照。“如买蒲甸等,皆闲笔映月娘之好佛也。读者不可忽此闲笔。千古稗官家不能及之者,总是此等闲笔难学也。”张竹坡亦分析了闲笔的重要性,《金瓶梅》的前半部中都在闲笔中提及月娘好佛,比如月娘买蒲甸,在闲笔穿插中描写月娘好佛要比花大笔墨着重描写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这种潜移默化的“闲笔”穿插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描写月娘好佛为后文中月娘去佛寺礼拜、孝哥遁入佛门做了铺垫。“文字不肯于忙处不着闲笔衬,已比比然矣。今看其于闲处,却又必不肯徒以闲笔放过。如看灯,闲事 也;写闹花灯,闲笔也。却即于此处出王三官。文字无一懈处可击。”[2]在忙笔之处插入闲笔,这在《金瓶梅》中已随处可见,但闲笔均为主线服务。看花灯、闹花灯都在为王三官的出场和其故事的发生做铺垫。故作者在穿针引线之中将忙笔和闲笔各得其所,忙中闲笔,闲中忙笔。
2.3 一笔作千万笔
一笔用作千万笔,是张竹坡对作者用笔之妙的赞誉。作者在写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时却能同时兼顾多个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变化,此所谓“一笔用作千万笔”。此种笔法对作者的文学修养要求极高,且不易把控,需要作者将众多的人物和情节条分缕析、了然于胸,同时作者要具有较高的文字掌控能力,才能手写此处,眼觑彼处,让多条针线齐头并进。在西门庆贪欲丧命一回中,张竹坡评道:“写伯爵,止用‘愕然’二字,写尽小人之心,已写尽后文趋承张二官之意,真是一笔当做千万笔用。”[2]西门庆死后,伯爵过来吊孝,闻知月娘刚生一孝哥,愕然道:“有这等事!也罢也罢,哥有了个后代,这家当有了主儿了。”[2]伯爵的嘴脸展露无疑,本想凭着“西门庆兄弟”身份捞一些好处,谁可想半路杀出一个孝哥,伯爵的夺财计划落空了,但他又没忘趋奉张二官之意。市井的嘴脸栩栩如生。
作者的“一笔两用、写一是二”的双写妙笔亦精彩无比,两相对照、遥遥相映。在《金瓶梅》第八回中,西门庆又要娶潘金莲,还要娶孟玉楼,两边踟蹰不前,遥相呼应,一处热闹便导致另一处冷落。竹坡评道:“则金莲处一分冷落,是玉楼处一分热闹。文字掩映之法,全在一笔是两笔用也。”[2]一笔两用,金莲对玉楼,热闹对冷落,相互衬托。又如潘金莲和庞春梅,两人一主一仆,相互照应,一笔用作千万笔,一处描写而多处的人物和情节均会受到影响,因此,读者读之需要细细品味。
3 人物描写之法
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为读者读完一本书后,能够回忆起来的便是一个个独特的典型人物。《金瓶梅》一改以往作品中“人物出场即定性”的固定模式,塑造出性格复杂多样的典型人物形象。《金瓶梅》成功地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达到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应该是属于哪一类,更应该是这一个[5]。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擅长塑造同种类型的人物,但又能避免这种同种类型的人物窠臼,达到共性和个性和统一[6]。无疑,《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西门庆的恶、李瓶儿的痴、孙雪娥的蠢等等都令人过目不忘,读后称颂。
3.1 犯而不犯之法
“犯笔”一词最先出现于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张竹坡继承并发展之,提出“犯而不犯之法”。张竹坡所提出的“犯笔”着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相同类型的人物中塑造出不同的人物特点,虽然同类相犯但绝对不同,于相同处写出不同,“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犯”。[7]
“《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2]伯爵和希大同为奴仆类型,金莲和瓶儿同为妻妾类型,但同中又各不相同。“《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镦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于春梅,纯用傲笔。此所以各各皆到也。”[2]作者根据人物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笔法。西门庆为一暴发户,没有文化,故不用文笔;潘金莲妖艳外放,尖锐深刻,故不用镦笔。由此可见作者的文笔慧心。
“写春梅,用影写法;写瓶儿,用遥写法;写金莲,用实写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泪’时,总用影写,金莲总用实写也。”[2]各人性格外貌不同,写作方法亦不同。潘金莲淫乐外放,用实写如在目前,感受其热情的冲击;瓶儿痴美,让人怜惜,用遥写法可以产生距离的美感,更加让人对其怜爱。对于一堆生活在一起的相似女性,作者用不同的文法、笔法令其展现出不同的性格魅力,可谓“特特犯手,却无一相犯”,见于作者“犯笔”的高妙。
3.2 旁见侧出法
旁见侧出法又名烘云托月,即互现法。最初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所创,意为在一个人的传记中主要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引入别人传记中去描写。在《金瓶梅》中,作者对太史公的互现法做了继承和创新,使其为人物性格塑造所服务,作者想要着重描写一个人,不是正面去描写,而是通过去描写其他人的言行来突出这个人。这种旁见侧出法笔在此而意在彼,隐含之意在其中,遥相照应,需要读者仔细阅读和揣摩以获得出其不意的阅读惊喜。张竹坡赞叹《金瓶梅》作者的笔法比史家笔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作《金瓶梅》者亦可作《史记》。
在《金瓶梅》第二回中,竹坡评道:“《水浒》中,此回文字,处处描金莲,却处处是武二,意在武二故也。《金瓶》内此回文字,处处写武二,却处处是金莲,意在金莲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见。”[2]自武松搬到武大家里一起住时,文笔便移至潘金莲,写潘金莲如何欢喜、如何打扮自己、如何遭拒心生怨气。如此便从侧面写出武二的英俊高大、正义不邪、心直口快。又如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一文中,武大和兄弟武二相见,“嫡亲兄弟”“是我一母同胞兄弟”“亲兄弟难比别人”[2]这些文字虽是描写武大和武二的兄弟情,却是处处敲击着西门十兄弟。从题目中“热结”对比“冷遇”则极具讽刺意味,通过描写武大、武二的“冷遇”兄弟情来旁敲侧出“十兄弟”的假情谊,文字奇妙,颇有指桑骂槐的味道。因此张竹坡所写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非常重要,读书要会读,不可盲读,枉费了作者的一番苦心。
3.3 白描
白描即通俗的顺序描写,是对事物最本质的描写,没有过多赘余的词汇,平白直叙,虽没有什么技巧,但却是文章写作的最基本方法。白描手法毋须技巧,简洁直观,最有力度地将一个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展现出来,直击心灵。张竹坡对《金瓶梅》中的人物白描手法很是赞扬,且有多处的分析和评价。在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时,竹坡评道“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向希大说:‘何如?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2]纯用白描手法来写伯爵,但如同追魂摄影一般将人物的形神、灵魂形象地描写出来。“伯爵伸着舌头道:‘爷不可折杀小人罢了!’”[2]将伯爵的小人嘴脸,讨好西门庆的形象一览无余地描写出来,其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样貌如同在我们身边,从骨髓中描出,溶成一片,不能为之字分句解。
“凡小说,必用画像。如此回凡《金瓶》内有名人物,皆已为之描神追影,读之固不必再画。而善画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影,以应其言语动作之态度也。”[2]作者将《金瓶梅》中的人物描神追影一般刻画出来,形成画面感,如对吴神仙的描写“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2]仅此一段描写则将吴神仙的画面在读者脑海中描绘出来,白描之法将人物的细节尽相绘出,人物如同画像一般出现在读者眼前。
3.4 阳秋笔法
“阳秋”一词出于“皮里阳秋”成语。“皮里阳秋”意思是心中有言论却不说出来,将意见藏在心中。亦有另一种说法是“阳秋”中的“阳”字避讳的“春”字,故“阳秋笔法”相似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一字寓褒贬,但行文曲折暗含褒贬。所以“阳秋笔法”和“春秋笔法”有一个共同点,即将褒贬性的文字隐含于曲折的文中,不易让读者发现,需要读者细细地品味。
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认为“阳秋笔法”主要运用在吴月娘身上。“故金莲敢于生事,此月娘之罪也。看他纯用阳秋之笔,写月娘出来。”[2]张竹坡认为作为西门家的正室,应负有管理“后宫”的职责,但西门后院内成天吵闹,春梅、雪娥吵闹一番,金莲、雪娥又闹一番,面对金莲的无理取闹,而月娘全若不闻,即使发生在她的面前,也就是云“我不管你”“由他两个”[2]直至后面发生大的祸患。由此观之,月娘有罪过,张竹坡认为作者运用“阳秋之笔”隐晦地表达月娘的过错。“总之,写金莲之恶,盖辱西门之恶;写月娘之无礼,盖罪西门之不读书也。纯是阳秋之笔。”[2]“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复归,且全不防闲门户,是又在作者阳秋之内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蕙莲公案至此又结。”[2]此后数回内,张竹坡均用“阳秋之法”分析作者对月娘的愤恨,月娘表面是一位好人,但却面对西门庆的奸淫好色、胡作非为置之不理,没有督促自己的丈夫走上正路,面对金莲和各位妻妾的斗争不闻不问,最终导致官哥、瓶儿和西门庆的惨死,从这一层面来看,月娘是一位奸险好人,作者亦未对月娘写有寓“褒贬”文字。笔者在此不讨论月娘的好与坏,仅从文笔法理论来探究,张竹坡的“阳秋笔法”确有意义。
4 结束语
张竹坡从章法结构、行文笔法、人物刻画等诸多角度对《金瓶梅》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文法理论。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使我们更加了解《金瓶梅》这部奇书的艺术价值。但《金瓶梅》这部书的宝藏远未开掘完成,需要今人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