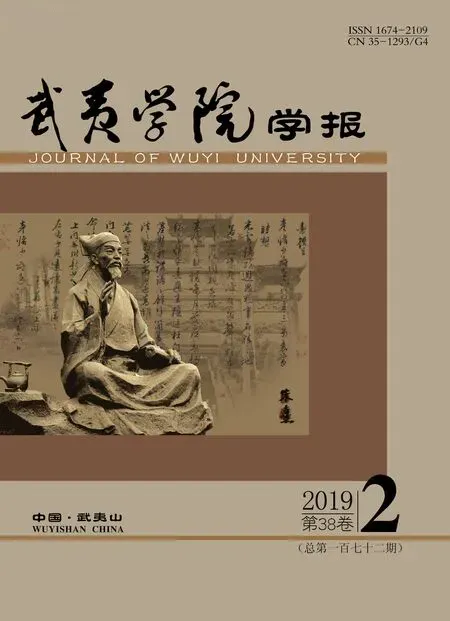近代化前夜中日政治结构比较
鞠月明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中国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大抵有:光绪缺乏实权,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抵制、满汉冲突、士人阶级的利益受损、新政缺乏整体统筹以及袁世凯的背叛。毋庸置疑,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处于同一时期的日本同样矛盾重重:天皇大权旁落,遵攘派与攘夷派之间、强藩与幕府之间、朝廷中公武合体派与尊攘派之间的多重争斗等,然而相似的改革背景,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其中原因不仅限于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本身,更是历史的、具体的变革背景之间的差异。对此刘金才指出:“在迄今有关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中,无论是将其视为外源性西化的产物还是视为内源性革命的结果,都几乎无争议地将其主要成因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变革。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无论从表象看是多么突发的变革,都必定是其内部事物的渐进解构,进而向前发展的结果……毫无疑问日本明治维新不是突发的,它应该是受被称为日本前近代的德川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使诸封建事物渐次解构,进而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果”[1]因此纵观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前的历史发展程度为改革提供了政策、体制及动力,两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这也恰恰解释了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差异导致了中日近代化道路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一、清朝君主专制政体与江户幕藩体制
君主专制政体是指在幅员辽阔的疆域内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类国家的特征是,中央政府通过划分地方政区,逐级设立由中央控制的地方政府,对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并通过地方政府对分散的民众进行间接统治。清朝中央通过增设机构加强对满人贵族、官僚和地方势力的控制,然而这些集权化的改革并不会提高政府的效率,同时因为缺乏制度性的监督,专制权力易于发生腐败,还会进一步加深官方与民间的裂痕,从而使国家很难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而沟通在中央与民间的地方势力由于受到中央集权下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又很难成长为可以与中央相抗衡的割据势力。
幕藩体制是日本江户时代所独有的政治结构,幕府通过分封给近270个大名土地,由其独立管理领地,进而对全国进行统治。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大阪之役德川家康消灭丰臣氏之后,立即制定《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从而牢固地掌握了幕府干预朝廷内部事务的手段。天皇和朝廷只享有任命官员、规定历法和改元等有名无实的权限,从此天皇成为独具神威而无实权的象征。而幕府通过对朝廷的垄断性控制达到了解释自身正统性的目的。除此之外幕府对各藩的统一是相对的,虽然大名的统治来自于将军的任命,但是作为各藩领主,大名是一种割据势力。各藩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因而幕藩体制下的各藩对幕府有一定的分权倾向。
二、从国家中央的政治权力横向分配来看两者的区别
清朝的国家治理并未发生大的改动,其常规官僚体制是以明代为范本而形成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持续已久的中央集权并未停滞。专制主义集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自宋代起,统治者就十分注意巩固中央集权制,明代以后,废相建阁,又把皇权专制推向新的阶段。到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尤为完善,雍正以后可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前期的主要中枢机构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期为内阁和军机处所取代。其中集权手段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设立军机处。19世纪中叶以前,清朝一直是以满族人的统治为核心的专制政权。关键性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这些权力包括官员的任免权、税收控制权和军队控制权。皇帝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将权力拆解成若干个要素,加强对满人贵族,官僚和地方的控制,雍正之后为了就西北用兵征讨准噶尔之事始设军机处。自军机处建立之时起,便成为掌握在皇帝手中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也是当时效率最高的中枢机构,虽然军机处职责重大,但其任命概由皇帝钦定,“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一切工作都处在皇帝严密的监督之下,没有任何决策权。有时某些强势的大臣即使能够对皇帝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的地位仍然是皇帝的臣仆,作用只是辅佐皇帝进行政治决策,而非与帝王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公职人员,因而不会对皇帝形成制约,更遑论威胁。因此君主专制政体中“分权”的基础是“主权在君”,程度仅限于官员层面,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力不在区分之列。管理如此泱泱大国,皇权的不断加强实系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之必然,但是凡事习之久则不觉非,西方世界的冲击方使我们意识到政治制度是国家的重要条件,倘若组织不健全,即使具备近代化的科学技术也于事无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固化,抑制地方力量的成长,一旦中央政权衰弱,而社会力量一时间无法成熟,就会使地方呈现碎片化,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根本做不到自上而下的改良。
同样被视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日本,在公元七世纪,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开始学习中国进行 “大化改新”。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从而建立起了以大唐为模本的律令国家。然而,在数百年之后,天皇经历了摄关政治、政院政治导致皇权开始走向衰微,直至以第一个武家统治机构——镰仓幕府的建立再经历室町幕府最后到德川幕府,天皇为首的朝廷大权旁论,从实际权力来看俨然沦为幕府统治下的一个藩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将军的统治与朝廷的权威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公武二元的政治结构始终存在,这在幕藩体制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留下了脆弱性的空间。对此福泽谕吉做出了准确的解释:“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与至强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人们身心,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日本”[2]。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天皇本身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格。虽然现实中天皇无力于政治,但是理论上却是一个不能被替代的 “神”。从这种意义上看将军的统治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能取而代之。是以当情况发生变化之时,当朝廷或各藩之中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力量,而突然崛起的力量又要拥立天皇的情况下,幕府就变得脆弱不堪。幕末时期,幕府因为开国的问题征求朝廷意见,幕府原本想从天皇处得到准许开国的命令,以此来压制反对开国的大名,但是事与愿违,孝明天皇明确表示反对开国,这引发了反对派对幕府统治的强烈批判,增加了天皇和朝廷的发言权。朝廷内部逐渐出现了具有浓厚藩幕府倾向的公家,他们与强藩联合,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幕力量。这也就不难解释近代天皇制何以成为维新变革唯一的制度选择。
三、从国家整体与部分的纵向分权来看
国家整体与部分的纵向权利关系是国家政治结构的核心内容,无论一个国家的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地实现治理社会。清朝虽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由于清朝地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问题复杂,加上交通技术条件的限制等原因难以直接进行管理。除去直接控制中央各个部门外,在地方上通过依靠督抚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因此国家想要将其力量扩展到官僚体系之外而直接控制地方的愿望如果得不到地方精英的合作是无法实现的。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处理上,皇帝不仅掌有选派督抚的全权,而且有一套严密监视和控制地方官员的制度。因此两者的关系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督抚绝无条件出现不服从中央、擅自为政的局面。除此之外,保甲制在地方基层组织建设中也相应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极度强化。保甲制是以保警为主的地方治安组织,为了适应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中央下令把保甲组织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在地方州县的控制下,直接对广大民众进行管理。中央重视保甲制的前提是保证政权的稳定而不是基层的创造力,对于中央来说权力下放并非为了鼓励地方自治和分权,恰恰相反,这不过是由于管理技术不成熟而无法事事过问地方事务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保甲制度非但没有整合地方势力,反而带来了隐患。“保甲制度不但在区位上破坏了原有的社区单位,使许多与民生所关事无法进行,而且在政治结构上破坏了传统的专制安全瓣,把基层的社会逼入了政治的死角。而事实上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去接收原有的自治机构来推行地方公务,旧的机构却失去了合法地位,无从正式活动。”[3]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衰败,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一批地方实力派充封疆大吏,成为清政府统治的重要支柱,但是始终未能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政府权力结构演变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呈现两难境地。传统集权体制由于自身弊端,加上时代环境的变迁,权力下移导致地方主义、军阀主义兴起,省界意识浓厚,国家走向分裂割据”。[4]在地缘广阔的中央帝国里,地方对于中央权力固有的限制,使得清朝的统治者难以进行社会变革,也使得这一制度适应变动中的社会力量。由戊戌维新为开端掀起的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失败,受到了封建势力,西洋国家和官僚阶层等不同力量的影响,但是就其本质而言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已经停滞不前,缺乏成熟的客观社会条件而无法复制明治维新的成功。
与19世纪的中国相比,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似乎与西洋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更为相似。幕府建立初期,为了加强武士阶层的统治,将军通过分封大名、建立附属藩国来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大名当中,在关原之战以前就归属于德川家族的称为“谱代大名”,在此之后归顺的称为“外样大名”。幕府通过经常性地改易和转封领地的办法挤垮了加藤、福岛等很多强有力的外样大名,同时为了监视外样大名,还把谱代大名转封到关东、东海道、中山道和畿内以外的全国要冲,又把外样大名改封到奥羽、四国、九州等偏僻地区。从而使得亲疏相间,互为掣肘。此外,在幕府体系下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中,重要的职位都由谱代大名选任,外样大名是不允许参与到政治统治中的。从表面上看,外样大名似乎已经臣服于这种主从关系,但实际上幕府对外样大名的打压正说明了德川家族的武力尚未强大到足以征服他们的程度。一旦时机成熟,这种隐忍,便会如雨后春笋般打破旧幕藩体制,成为一股来自幕府内部的新兴势力。“在幕末以领导权交替为中心的社会大变革中,不无来自西方势力的威胁与影响因素,但从整体而言,日本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分化、瓦解了幕藩制国家,并建立了能够对近代化加以领导的天皇制国家,外压仅是变革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5]。在天皇与幕府的戊辰战争中,充当主力反抗遵攘派的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都是在江户幕府中不能担任要职的外样大名,在江户时代不能进入权力中枢的愤懑不平,在幕末时期终于迎来了云开日出,重掌大权的时光。可见,幕藩政治结构本身就蕴含了自我更新的因素,它既能在两百余年内稳定阶级秩序,又能在受到外来势力的冲击时孕育新生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黑船来航后日本能够较为平稳而迅速的过度到现代化的进程。
四、总结
中日两国开启近代化的原因概由西方对东亚的入侵,因此时间上都处于近代化的末期了,两者缺乏完成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它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和制度上的特征以及在这种结构与制度下进行的变革和社会运动,仅为应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而采取的自保方式。两者的当务之急是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调动近代化所需要的资源要素,有效的整合社会力量,从而能够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的近代化变革。德川时代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精英阶层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呈现出不同的反应,通过内部协调的方式完成政权的更迭,转化成近代化的领导者,使社会产生较少的动荡,整合出现代化所需要的强而有力的天皇政府。亨廷顿认为“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化的参与体制的出现成为可能。”[6]以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来看确实如此。
清朝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又是中国走向现代的起点。面对外界的刺激,机构臃肿庞大的清王朝已然无法做出回应,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不过是墨守成规而已。地方政府的行政是高度集权,集权化向上延伸,从地方政府直到中央。由于中央权力过于集中,整个官僚机构管的过宽,社会力量无法成长,必然无法孕育出现代政治系统所需的民主要素。在历经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中国处于“国家政权衰落与社会力量薄弱并存的‘国家—社会’格局”。[7]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来领导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清末戊戌维新无法自上而下的进行变革的主要原因。我们一直强调不同的体制不是决定现代化的必然因素,不同的国家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中,制度性的因素确实扮演着制约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角色,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