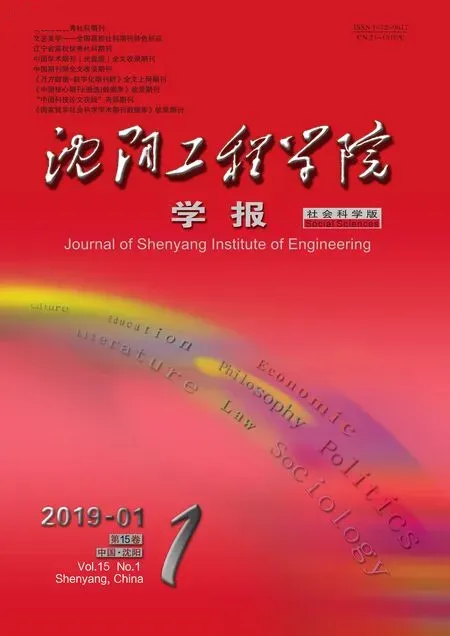“整体性”瓦解前的两道风景
--对“新乡土小说”的一种考察
孟芳芳,李庆勇
(沈阳师范大学a.文学院b.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新乡土文学”①这一定义是由孟繁华教授提出的,在孟教授的《百年中国的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现当代这百年文学中,乡土文学出现了两次转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发展到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次转折进入“乡村题材”阶段,到了八十年代,伴随“新乡土”文学的出现产生了第二次转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新乡土”文学主要指的就是“新乡土”小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贯穿始终。而到了20世纪,中国在西方现代化刺激下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所以,许多现当代作家都经历过乡村生活,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碰撞使他们对自身经历的乡村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并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孟繁华教授提到了不同阶段乡土文学发展的不同特色。但在同一阶段,乡土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色。莫言与汪曾祺的创作都根植于乡土社会,他们二人作品中所追寻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是高度一致的。然而,在同样的文化背景和主题之下,莫言与汪曾祺对于乡土世界的想象和叙述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接下来就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这两篇小说为例,对比这两位作家作品中语言的差异,以及他们对于乡土世界不同的想象与叙述,探究他们二者形成不同风格的思想资源。
一、矜持隽永与狂放乖张——乡土世界的不同声音
在文学的世界中,语言已经不仅仅作为一个传播介质而存在。它经过作家的精心雕琢与修饰、读者的体味与理解,甚至是经过作为媒介的不同样式的纸张的渲染都使其升华到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语言,并通过语言来获得存在的某种意义。因此,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世界观等。由此研究作品的语言,也就成为通向作家内心世界的桥梁。通过对作家语言的观照,也就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深刻意蕴。基于这样的理解,对于“新乡土”小说的创作,汪曾祺运用古朴清淡的诗性语言,矜持隽永,如潺潺小溪。而莫言对于乡土世界的书写,如大海一般波涛汹涌狂放乖张,似现代狂飙突进的命运交响曲。
1.文白相间与诗性语言
汪曾祺写作十分注重语言的锤炼,他写道: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1]366。这也就正体现出他对于语言的精致含蓄与隽永之美的追求。他对小说语言的使用力求准确,不仅仅是词语的准确,更是对于民间生活描写的准确,这也表现出他对于民间日常生活的欣赏与赞同。这里我们首先关注其用词的准确。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将语言表达的浅白易懂是每个作家创作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无论是景色描绘还是人物描写,其所运用的语言都是日常多见的。也曾有评论家评论他的语言每一句都很平淡,但不得不说却是十分准确的。如开篇第一节中对于四季的描绘,只是一些普通的景色描写。单看任何一词,任何一句都很平淡,但也就是这样平淡却准确的描写,让读者能够瞬间在头脑中勾勒出一幅四季变幻之图。简单,但又涵盖着层次之美。而层次之美本身就带有诗意,诗意隽永含蓄,这也就将文白统一在了一个四季变幻之中,其深意多么耐人寻味。而且汪曾祺对于景物的描绘、颜色的选择也是异常准确。除此之外还有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西边锡匠们打锡、练武、唱戏;东边挑夫们挑稻谷、砖石、石灰;还有主人公十一子和巧云在柳荫下织席化锡,一幅简单的男耕女织之图跃然纸上。尤其是这一句: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作伴。平淡中透露着温情。也许单看语言确实有些朴实无华,但是其语言中的表意功能却是落到实处,在小说的前三节汪曾祺把他心中的大淖景色和大淖人情实实在在地传达给了读者。他的语言也不失表现,即便没有富丽堂皇的辞藻,却也有其独到的匠心,简单三句,读出来却是朗朗上口,富有诗歌的内在韵律。而对于大淖四季的描写,如果是以一句一段的形式去感受就已然形成了一种散文诗的氛围。其实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不能说它是一个鲜明的完美的排比,但是其中的层次却是一目了然。而且这种诗性语言营造出了诗性意蕴,进而使得景色描写更加优美,气氛营造得更加隽永。《大淖记事》中语言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文化意境的营造,也就是前三节民俗风情人情的诗性描写。它超越了语言本身,字词本身的局限含义,彰显出作者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把人物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从环境中引出人物,不仅赋予了语言深刻的内蕴,也让整篇文章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这样日常生活与风俗人情描写的相结合,使语言文白相间,俗雅相见,诗性相生。
2.宏大叙事中的民间性
作为“新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即站在民间立场又不乏文学情怀。同时他也或多或少拥有着政治情怀,以至于他的创作不可或缺地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并且无论是创作的前期还是后期,莫言小说语言总有狂欢的烙印。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和营造出的“高密东北乡”神秘氛围,更是让其语言的狂放乖张发挥到了极致。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创造的一个民间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生意盎然,生机勃勃。那么怎么才能让其直观体现出呈现给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便得意于莫言语言的民间性,这种民间性表达方式其一便是对于民间生活以及民间人物的描写,其二便是人物自身的语言。如92岁的陶罐头老太太那段如歌谣般的历史,如戴凤莲回门时那段描写,莫言以其独特的语言表现能力让戴凤莲的哭声充满生机,日常词语加上独特的语言结构以及莫言对于民间事物的独特认识让戴凤莲此时的委屈活灵活现,让自然为之动容。莫言用语言将高粱地上的戴凤莲与漫山遍野的高粱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出了他语言的宏大,也表现了他想要让戴凤莲的无限生命力蓬勃而出的希冀,更加营造出一个狂放乖张的世界。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将语言的民间性与狂欢化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让狂欢真正成为了一件民间盛事,也就呈现出了一个越发激荡的世界,一个越发狂放乖张的世界。
二、桃花源与浮世绘——民间世界的不同想象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汪曾祺的高邮水乡是现当代文坛上极富特色的两个乡土世界,是作者自身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原因所创作的不同的世界,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民间世界的不同想象。八十年代前期,他们二者因自身经历的历史观念与意识形态,运用不同的话语方式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诉说与创作,并赋予了历史不同的意义与价值,这也就是他们二人对于民间世界的不同想象。汪曾祺和莫言都以一种回忆的笔触,天马行空的想象,重新描绘了一个他们曾经认识经历过的民间世界,并用一种虚实相见的态度把我们熟悉的世界再现出来。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陌生化了这个我们熟悉的世界,在主流的历史中,加入了不同种类的艺术再创作。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描绘的高密东北乡充满了生死与血泪,形成了一幅粗犷浪漫的浮世绘。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更多的是平静的普通人,是继承了民俗与艺术的手艺人,生活在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和谐恬淡的桃花源般的大淖中。
1.民俗风与手艺人
《大淖记事》为什么要以大淖开头,而不是巧云与十一子。而且小说的开篇也是先写大淖的景色,大淖的民俗风情,这当然源于作者汪曾祺的态度,可以说汪曾祺十分重视对民俗风情的诉说。汪曾祺自己也承认他喜欢看风俗画,以及讲风俗的书。《大淖记事》中的民俗风情描写不仅是对于传统的默默继承,也加入了汪曾祺自己对于生存方式的独特见解,也是他对于这一片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的怀念与向往。汪曾祺对于民俗的描写随意而又独到,他生于斯长于斯,所以笔下也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亲近之感,而汪曾祺本人一直追求一种含蓄隽永的诗性风格,这也就让《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充满了和谐与恬淡之风。汪曾祺将所向往的尽数写在了小说中,如烟波瀚渺的大淖、色彩斑斓的沙洲、浆过的衣服,又或者墙上的牛屎粑粑、比赛撒尿的小家伙。在这质朴、纯净的大淖中,来做生意的客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人和气,凡事忍让;锡匠们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这种世外桃源般的人间情景、民俗风情,在汪曾祺的笔下数不胜数,但无论是欢乐还是忧伤等情感,在他的笔下都趋于平和,总的来说他的民俗风情是平淡而乐观的民俗风情,他的高邮是平淡而乐观的高邮,这也是他对于生存方式的独特见解。
而对于这种民俗风情所包围下的大淖中的手艺人的人性美、人情美也就越发鲜明。小说最主要讲的是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的故事无论怎样平和,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情节矛盾的,只不过在这种民俗风情的背景下显得不那么激烈了而已。之前他们互相喜欢彼此爱慕,囿于现实,谁也不说穿,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但是当刘号长出现之后,巧云后悔了,然后她行动了,她与十一子互相爱慕,就该在一起,但是号长碍于面子必然要出面收拾十一子,十一子被打得半死,锡匠们用尿碱救了他,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锡匠们“顶香请愿”帮他们讨回公道,巧云照顾被打伤的十一子,找出她爹用过的箩筐,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钱去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小媳妇。从这些描述中不仅能看出锡匠和挑夫们正义坚贞,尤其是当他们像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一样在街上游行的时候,没有喧哗,没有呐喊,但是沉默中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那样浓烈,其中的人性闪亮,人情优美不言而喻,这种精神就像是他们打锡器的手艺一样,经久不衰。在汪曾祺的笔下,无论是乡土风俗,还是平常人生,无不散发出迷人的生活情趣和浓厚的诗情画意[2]302。这个平淡自由却又温情的世界,就是汪曾祺真正想给我们呈现出的他心中的具有人性美与人情美的世外桃源。
2.高粱地与江湖人
用江湖来形容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所创造的高粱世界再合适不过。有人的地方即是江湖,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英雄亦或枭雄;无论是怎样生活的人,流浪的隐士又或是本能的战士。《红高粱家族》中的生命和《大淖记事》中的生命一样富有人性美与人情美,他们都不在乎世俗道德、伦理纲常。他们和满口之乎者也的人不同。但是这些生命所存在的民间世界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差异的形成就来自于莫言对于民间世界的独特想象。汪曾祺笔下的水乡自然而然透露出诗意,而莫言的故事背景则是在一片高粱黑土地上。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3]115。这里善恶共生、美丑共存,莫言笔下的世界既可以高洁神圣又可以藏污纳垢,是一个浓烈丰富的民间世界。《红高粱家族》中有很多这样的描写: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4]31。月光圣洁,高粱伟岸,而接下来写的却是乡亲们尸陈遍野,一片狼藉。在紧张的行军中想的是孩提在墨河里抓鱼捕蟹,从人种优良,丰饶肥沃的黑土想到罗汉大爷零零碎碎的尸体。美丑相见,而小说中罪恶之丑,暴力之丑的巅峰也必然属于罗汉大爷被扒皮的描写,这里的扒皮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酷刑。小说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地把罗汉大爷被扒皮的整个过程记录了下来,而这样细致的描写也就给了读者更加直观的感受,所呈现的色彩更加浓重。
余占鳌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小说中的主角不同,他根本就不是纯粹的正义英雄。他是在这个色彩浓重的浮世绘中拼命挣扎的人,是江湖中的匪徒也是侠士,是不择手段、不畏伦理努力活下去的生命。江湖讲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余占鳌杀人越货,但他侠胆义肝,他从生命的枷锁下救了戴凤莲;他奋勇杀敌,给罗汉大爷报仇;他占山为匪,但也不忘家国大义,他与冷支队能够同仇敌忾,和江大队能够携手杀敌。就是这种亦匪亦雄的江湖人性格,构成了高密东北乡的彪悍民风,余占鳌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整个高密东北乡还有其他很多和他一样的生命,像罗汉大爷、曹县长、戴凤莲。戴凤莲是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形象的代表,陶罐头老太太说她是女中豪杰。戴凤莲是个小脚女人,可是她却一点都不像传统的小脚女人,她不娇柔、造作,豪迈飒爽,张扬不羁。她的血液里流淌着浓烈辛辣的高粱酒,她的灵魂里烙印着坚挺向上的高粱魂。这片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被莫言放在了一片虚幻的原始的旷野上,让他们共同绘成了一幅色彩鲜明、个性浓烈的浮世绘。
三、古典传统与西方美学——乡土书写的思想资源
在“新乡土”文学这个大背景下,作为同样着眼于部分,着眼于地域的作家,莫言和汪曾祺在《红高粱家族》和《大淖记事》中都歌颂了生命的蓬勃之力,传达了人性的美,人情的美。但是无论是他们创作运用的语言还是二者对于乡土世界的想象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差异的形成不仅在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更在于更深层次,即他们二者风格形成的思想渊源。
1.出世入世,儒道结合
文学,或者说是小说,到底应该拥有哪些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问题。而到了汪曾祺,到了《大淖记事》,就给了我们其中一个具体的回答,就是传承,对于传统思想的传承。汪曾祺曾说过: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4]38。儒家思想简单总结起来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而在《大淖记事》中体现着最多的思想渊源便是儒家的仁义思想。仁也就是仁爱,当然在汪曾祺的笔下,仁爱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天地君亲师,更多的是小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的仁爱,像是大淖里的生命们。做生意的客家人们在大淖和气忍让。锡匠们相互团结,相互友爱,师兄们悄悄给十一子留门。当十一子受到伤害时,锡匠们为他奔走,上街游行。这充分体现出了大淖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人与人之间友爱互助,患难与共,这种仁爱也丰富了大淖生命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大淖是个小地方,但是小地方的小人物却也拥有着不可磨灭的高尚品格,便是义以为上。锡匠们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他们为了给十一子讨公道上街游行,“顶香请愿”。挑夫们讲义气,无意间的男女分工,彼此互补,在十一子受伤后,杀了鸡,炖了人参汤,川流不息地来看十一子等行动都体现着大淖人的义。
当然,光是继承儒家思想是远远不足以形成汪曾祺这种浑圆天成的文学风格的,前文也提到比较来说,儒家思想影响最深。那么相对比的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中的其他两教,道教与佛教。佛教暂且不论,因为在《大淖记事》中佛教思想的蕴含远没有《受戒》及其他汪曾祺的作品中那么深刻。但是在《大淖记事》中,随处可见的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如道家的出世,超脱,旷达,随心意。开篇三部分描绘了大淖景色和民风质朴的手艺人们,画出了一幅世外桃源之景,同时也是一幅出世之图,远离街里的世俗气息,没有俗世的尔虞我诈。而这里的民风不受伦理道德约束,这里姑娘媳妇们像男人一样挑担赚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一样,走起来像一阵风超脱旷达。淖里的生命就是这样通达乐观,超脱旷达。儒家的仁义是一种入世意味,看似与道家的出世相对立,但是在汪曾祺的笔下二者却是妙不可言的统一在了《大淖记事》中,达到了一种和谐共生。大淖里的生命拥有着仁爱济民的思想,而当他们遇到挫折时,就转入世为出世。在这里儒家给他们以信念和努力,而道家则给他们自由与解脱。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汪曾祺的创作,但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2.“新乡土”中现代主义独特表现
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与五四文学的作家创作有着无法言说的内在关联,都处在社会剧烈转型期间的文学创作,是外来因素的刺激与作家乡土经验融合后的充分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学领域受到了外国文学风潮冲击,尤其是以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对于莫言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莫言从福克纳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表现领域,并获得了一个介入现实的精神立场,从马尔克斯那里更多地是学到一种表现现实的手段技巧[5]15。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出生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更是他文学创作的丰厚资源。因此,传统文化底蕴与文学表达对他有着深刻影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借鉴西方文学思想与自己乡土经验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学反应,体现在“新乡土”的文学想象中,这是现当代作家不可多得的创新意识。
福克纳是一个着眼于部分、着眼于地域的作家,他创造出了一个美国地图上无法找到但是却有真实存在感的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深受启发,高密东北乡便应运而生。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就创建了一个满地高粱,空气中弥漫着辛辣的高粱酒的味道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不是单纯的一个地理概念,需要符合常规常识,它是一个文化概念。莫言将他回忆中的高密表现出来的同时还加入了他想象中的东北乡,这也就让高密东北乡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含义。这也就让他跳出了传统的纪实乡土文学写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福克纳的地域写作,福克纳的世界里批判的声音最为强烈,而到了莫言,在批判的同时,因为对东北乡充满了主观的想象,所以他创造了许许多多自己向往和追求的充满了抗争精神的原始生命。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康普逊家族从繁盛走向衰微,同样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他用祖辈父辈的辉煌来对比衬托出今昔的失意与无奈,这不仅符合寻根文学的潮流,更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拘泥与僵化的强烈控诉。马尔克斯对莫言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莫言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如小说中豆官家的两匹黑骡子和罗汉大爷明明被日寇抓走了,豆官在家中梦里却能听见那两匹骡子清脆的鸣叫,这其实就是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艺术的表现出了豆官对于自家黑骡子和罗汉大爷超越时空的关心,充分体现出了人性美与人情美。当然莫言对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吸收与借鉴不止于此,莫言还是一名发展中的作家,但正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借鉴加以传统文化的建构莫言才形成了一个相对于稳定的文学风格。
四、结 语
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发展了百年之久,但具有自己独特地域文化的作品毕竟还占少数,所以研究莫言和汪曾祺的作品对于之后的地域乡土文学发展意义非凡,而同在“新乡土”文学的背景下,莫言与汪曾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乡土”文学。他们不仅是“新乡土”文学的两道靓丽的风景,更是之后作家创作的珍惜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