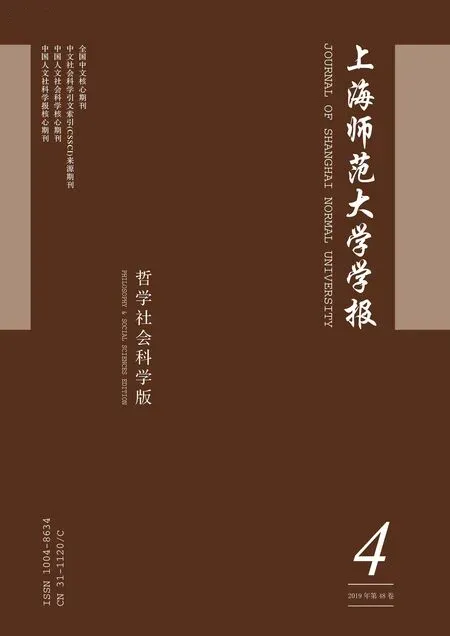从河东镇的政治处境论辛云京与仆固怀恩之乱
刘永强,张剑光
仆固怀恩之乱是紧接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再次遇到的重大危机,史言“为国大患,士不解甲,粮尽馈军”,[注]刘昫:《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89页。“不啻于禄山、思明之难”,[注]李昉:《文苑英华》,卷九三七《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926页。因此得到了学界颇多的关注。在研究仆固怀恩之乱时,学界多从唐廷与朔方军的互动关系、唐代宗的藩镇政策、仆固怀恩的民族性,乃至民族关系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阐释,[注]相关研究有林冠群:《仆固怀恩》,《中国边政》1982年第78期,第40—45页;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第七章“仆固怀恩与李怀光之反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281—291页;陈勇:《从仆固怀恩反唐看中唐的河朔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第26—27页;史秀连:《略论仆固怀恩》,《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42—45页;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第五章“朔方军地位的转变与仆固怀恩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84页;曾超:《试论仆固怀恩之乱》,《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45—49页;徐志斌:《仆固怀恩叛乱与代宗治国》,《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364—374页;吴晓红:《评析唐代民族将领仆固怀恩》,《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50—153页;陈翔:《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的重建》,《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第70—76页,等等。皆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不过,学界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时任河东节度使的辛云京,或者仅仅将其视为激反仆固怀恩之人而一笔带过。
事实上,辛云京在仆固怀恩之乱中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时人颜真卿就指出,“言怀恩反者,独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耳”,[注]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59—7160页。将辛云京视为仆固怀恩之乱的首要责任人。正是辛云京在仆固怀恩迎送回纥可汗时既拒绝仆固怀恩进入太原城又不犒军的举动,才导致仆固怀恩因愤怒而顿军汾州,在事实上已经叛乱的后果。而其他三人中,骆奉仙是在辛云京鼓动之下对仆固怀恩产生疑惧,进而力言其反叛的。李抱玉虽为泽潞镇主帅,但其本人在泽潞镇的时间并不多。至于鱼朝恩,检阅史籍,并未发现他与仆固怀恩有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因此,辛云京是仆固怀恩发动叛乱的关键角色。
那么,身为河东节度使的辛云京为什么会坚拒仆固怀恩入城?或者说,为什么辛云京会对仆固怀恩如此疑惧与戒备?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它关系到仆固怀恩之乱最为原始的面貌,也对理解唐代宗初期的政局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力图从河东镇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形势出发,整理挖掘相关史料,从辛云京的角度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回答。
一、辛云京对仆固怀恩奏置河北四镇的疑惧
宝应元年(762),唐廷向安史叛军发动总攻,“以(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条,第7136页。之后,在仆固怀恩、仆固玚父子的追击下,史朝义最终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在唐廷最终消灭史朝义的过程中,仆固怀恩父子居功至伟。作为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对河北之事具有合法的处置权。在仆固怀恩的奏请下,广德元年(763)唐廷下令“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闰月条,第7141页。
河北四镇的设立,史家多以为是仆固怀恩巩固权位之举,并指出河北呈分裂割据之势乃仆固怀恩所开启。此论有所偏颇。唐廷对待投降安史叛军的臣民多采取优容政策。在第一次收复东京洛阳时曾有主张处死陈希烈等投降安史之人,对此,李岘提出“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注]《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第3345页。得到采纳。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代宗时,“以二凶继乱,郡邑伤残,务在禁暴戢兵,屡行赦宥,凡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问”。[注]《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3837页。而给安史降将以优待,也是唐廷的一贯政策。如至德三年(758)二月,“贼将伪淄青节度能元皓以其地请降,用为河北招讨使,并其子昱并授官爵”。[注]《旧唐书》,卷十《肃宗纪》,第251页。上元二年(761)五月,令狐彰降唐,彼时令狐彰麾下仅有数百将士,“肃宗深奖之,礼甚优厚,赐甲第一区、名马数匹,并帷帐什器颇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毫、魏、博等六州节度,仍加银青光禄大夫,镇滑州,委平残寇”,[注]《旧唐书》,卷一二四《令狐彰传》,第3528页。仍然得到了唐廷超高的政治优待。宝应元年(762),张献诚“举州及所统兵归国,诏拜汴州刺史,充汴州节度使。逾年来朝,代宗宠赐甚厚”。[注]《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献诚传》,第3497页。因此,仆固怀恩奏请李宝臣等人分镇河北,与唐廷的政策并不冲突。对此,吕思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观能元皓、令狐彰、张献诚之降,朝廷皆授以元职,可知怀恩实承朝旨行事。”[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虽然仆固怀恩奏置河北四镇与唐廷调整河北藩镇的政策并不冲突,且作为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对河北安史降将有合法的处置权,但是,对辛云京及其所统领的河东镇将士而言,河北四镇的设置却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安史之乱爆发时,安禄山就派高邈擒获太原尹杨光翙。[注]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6页。在劫杨的过程中,河东“万兵追之不敢近”,[注]《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5页。从中可见安史之乱的爆发给河东镇将士的震撼犹如霹雳。安禄山南下进军的过程中,又“先杀太原尹杨光翙于博陵郡”,[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30页。无疑是给了河东镇将士一个难以忘却的下马威。叛军所要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东、西二京,由安禄山亲自统兵施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进攻太原。继而,如史思明所说,“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注]《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05页。在安禄山亲自率军南下的过程中,“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十万,寇太原”。[注]《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肃宗至德二载正月条,第7015页。此时的太原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李光弼所领导的太原保卫战也极为艰难:“时锐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满万……乃彻民屋为摞石车,车二百人挽之,……思明为飞楼,障以木幔,筑土山临城……思明宴城下,倡优居台上靳指天子……初,贼至,光弼设公幄城隅以止息,经府门不顾。围解,阅三昔乃归私寝。”[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85页。
在史思明降而复叛后,曾为安史叛军所属河东节度使的高秀岩又“帅其党叛”。[注]《旧唐书》,卷五十《刑法》,第2152页。河东镇北部、东部再次处于叛军的兵锋之下。直到上元初,河东镇所属的大同、衡野两军才为郭子仪所讨平。[注]《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进传》,第4217页。高秀岩是一名具有丰富履历的武将,开元年间曾在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王忠嗣属下任河东节度都虞候,“筹策无遗,攻战必取,前后大阵三十,小阵数百”。[注]同治《稷山县志》,卷八《艺文》,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24册,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872页。在安史叛军中他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而且对河东非常熟悉。也就是说,整个安史之乱期间,河东镇处于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杨光翙被杀的震动,太原保卫战的惨烈,大同、横野两军的直接威胁,在河东镇将士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对于从安史之乱就随李光弼作战的辛云京来说,这些不久之前的记忆必定会因河北四镇的重新设置而更加强烈。
除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记忆,以现实形势而言,河北四镇的设置对河东镇也有潜在的威胁。初置的河北四镇,除魏博外,其他三镇皆与河东镇接壤,而成德镇对河东镇的威胁最大。成德镇主帅李宝臣在安史之乱中是河东镇的劲敌,当年劫杨光翙事件中他便充当急先锋,“将骁骑十八人,劫太原尹杨光翙,挟以出,追兵万余不敢逼”。[注]《新唐书》,卷二一一《李宝臣传》,第5945页。而一直威胁河东镇的高秀岩,其子“齐皇,桓(应为恒)州别驾、试太常卿……霖皇,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充成德宣节度步军使兼都虞候经略副使”,[注]《稷山县志》,卷八《艺文》所载《渤海郡王高秀岩碑》中,高秀岩碑由其子高霖皇出资立于元和二年(807)。高齐皇、高霖皇分别为高秀岩第三子、第五子,碑载高秀岩死于上元二年(761),享年七十二,则此三子应早已成年,故在安史之乱中已经开始在田承嗣、李宝臣军中任职。不但有力地说明了高秀岩与李宝臣的关系匪浅,而且可知李宝臣对河东镇内部也相当熟悉。同时,成德镇的会府恒州的地理形势对太原尤其重要,如史书记载,“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北直五·真定府》,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89页。“常山(即恒州)地控燕﹑蓟,路通河﹑洛,有井陉之险,足以扼其咽喉”;[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七月条,第6989页。而其中的井陉关更是河东军东出的要道,“太行为控扼之要,井陉又当出入之冲”。[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北直一·井陉关》,第427页。李宝臣拥有恒州及井陉关,河东镇咽喉便为其所扼制,对河东镇的安危关系极大。
河北四镇主帅同为降将,利益息息相关,在面对政局变动时往往会相互配合。这从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与四镇频繁互动中可以看出:仆固怀恩“深结归命之帅,……虎据汾晋,寇於太原,乃分使河朔,连扇群帅,邀我(指魏博)同恶,示以师期”,[注]董诰:《全唐文》,卷四四四《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32页。“四帅相继来降,怀恩结为党助,奏复其职。至是拥众据汾上,子玚围太原,相、卫馈餫,以相掎角”;[注]《权德舆诗文集》,卷十九《故司徒兼侍中上柱国北平郡王赠太傅马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标点本,上册,第297页。而仆固怀恩“遗薛嵩自相、卫馈粮以绝河津”,[注]《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0页。“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注]《旧唐书》,卷一四一《李怀仙传》,第3895页。因此,河北四镇的设置对辛云京所统领的河东镇而言,几乎等同于再次相邻反叛之地。
且辛云京初掌河东镇,地位并未完全巩固,这从后来仆固怀恩发生叛乱时河东镇内部的异动中可以看出。在仆固怀恩父子追击史朝义时,“河东兵马使李竭诚、成德军将李令崇咸统精兵,亦革面来王,兢为掎角”,[注]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十六,代宗宝应元年十一月条,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3页。从此条史料中也可见仆固怀恩与李宝臣早有联系。而在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曾欲联合李竭诚谋取太原。而蔚州刺史曹楚玉“去顺效逆,与之连衡,更唱迭和,同为不道”,[注]《文苑英华》,卷五六七《贺仆固怀恩死并诸道破贼表》,第2908页。则可证明李竭诚、曹楚玉等人之前就已经与仆固怀恩暗通款曲。对此,作为河东镇主帅的辛云京不可能不知道。李竭诚所任的河东兵马使职位非常重要,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安史乱前此职已极为重要,盖实掌兵权故也。安史乱后,政局不宁,都掌兵马之任自更重要。”[注]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 第433页。辛云京在任代州刺史时亦任都知兵马使,由此为河东将士所推戴成为河东节度使。曹楚玉在《广德元年册尊号敕》里与仆固玚、李怀光等并列,“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加实封一百户。仍各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于凌烟之阁”,[注]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页。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且就蔚州的地理言,“州山川险固,关隘深严,控燕、晋之要冲,为边陲之屏蔽,飞狐形胜,实甲天下”,[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山西六·蔚州》,第2044页。为河东与幽州沟通之要地,彼时也是河东镇从北边防遏幽州的屏障。河东右厢兵马使张奉璋的墓志记载,河东镇其他地方的反应也与李竭诚、曹楚玉类似,“属仆固扇逆,晋人忷惧。东连涂水,南跨介山,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注]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页。总之,河东镇内部形势对辛云京而言也是很严峻的。
因此,在辛云京看来,河北四镇由仆固怀恩奏置,作为河北副元帅的仆固怀恩对四镇具有名义上的领导权,暗中又有勾连,若仆固怀恩有所举动,四镇必会响应,届时河东镇将很有可能会重复叛乱初期史思明等四路大军进攻的历史。加之河东镇内部的蜂拥而起,辛云京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辛云京不能不对仆固怀恩奏置河北四镇的动机产生强烈的疑惧。
二、仆固怀恩及河东镇南部形势对辛云京的压力
在安史之乱末期,仆固怀恩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其职衔有“太保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大副大都护、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六城水运使、兼河中副元帅、上柱国、大宁郡王”,[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招谕仆固怀恩诏》,第618页。是朔方军的当然领导者。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于广德元年七月“充朔方行营节度”,[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第273页。如吕思勉先生所说,“于是朔方兵权,尽入其手矣”。[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9页。安史之乱爆发后,朔方军势力迅速膨胀,所统辖的范围越来越广大,据严耕望先生研究,“朔方军统摄辽阔……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载台北历史语言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175—176页。即河东镇西部地区皆为朔方军的势力范围。尤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与河东镇会府太原关系最为直接的振武镇,形势也相当不利。严耕望先生指出,在唐代北边防御上,“即以振武为前线基地,西控天德军、三受降城,而太原又为振武之支援基地”。[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载台北历史语言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第1340页。在探讨太原北塞交通诸道问题时,严氏又指出,“云中、单于府地区,为塞北漠南最肥沃地区,北方少数民族渡碛南徙者常以此为中心根据地,故其地与中国北方重镇之太原关系尤切”。[注]《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第1340页。故而,振武镇对于太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振武节度使置于乾元元年,领镇北大都护府及麟、胜二州,但是直至大历十四年浑瑊任节度使,其间二十年并无人担任振武节度使。也就是说,振武镇实际上仍然在朔方节度使的统领之下,这从仆固怀恩“单于镇北大副大都护”的头衔中可以知晓。[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招谕仆固怀恩诏》,第618页。而这意味着,在辛云京尚未巩固对太原以北地区的领导权的同时,还要承受仆固怀恩所统领的振武镇所给予的重压,需要提防这些地区与振武镇联合威胁河东镇的安全。
在众多的职衔中,仆固怀恩又“兼绛州刺史”。[注]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七十八《帝王部·委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45页。当时朔方军兵力集中在绛州,兼河中副元帅、绛州刺史意味着仆固怀恩掌握了河中镇的朔方军。因此,对辛云京而言,河东镇西南部的形势对河东镇来说也很严峻。绛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州控带关、河,翼辅汾、晋,据河东之肘腋,为守战之要区”。[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山西三·绛州》,第1915页。若河中无事,则绛州可为河东镇的坚强奥援,但若仆固怀恩真的有所异动,那么绛州及所屯的朔方军就将成为河东镇的肘腋之患。而且作为河中副元帅,仆固怀恩统领整个河中镇所辖诸州的兵权。河中镇所辖诸州皆为重要地区,尤其是河中府与河东镇关系尤切,蒙古将领石天应谓河中“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注]脱脱:《元史》,卷一四九《石天应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27页。顾祖禹谓“有河中,则河东不能与长安相联络”。[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山西三·蒲州》,第1889页。因此在朔方军屯军绛州、控制河中府的情况下,若仆固怀恩发动叛乱,不但河东镇旁有肘腋之患,而且随时可以切断河东镇与长安的联络,届时河东镇将处于孤立无援之地。这不能不对辛云京产生巨大的压力。
河东镇东南的泽潞镇,形势也不容乐观。泽潞镇主帅李抱玉虽然也被颜真卿视为与仆固怀恩有矛盾之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河东、泽潞两镇可以互为奥援。乾元二年(759),李抱玉“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持节郑州诸军事兼郑州刺史、摄御史中丞、郑陈颍亳四州节度”。[注]《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第3645页。在史思明攻陷洛阳后,李抱玉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李光弼固守河阳。也就是说,在安史之乱期间,李抱玉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河南地区。在代宗即位后,他才被擢升为泽潞节度使。他与辛云京类似,也是新取得泽潞镇的领导权不久,对泽潞镇的掌控也并非稳固。仆固怀恩奏置的四镇中,如果说成德镇对河东镇威胁最大,那么薛嵩所领的相、卫、贝、邢、洺、磁六州对泽潞镇的威胁最大。在薛嵩所领的六州中,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河南四·彰德府》,第2316页。卫州“南滨大河,西控上党,称为冲要”。[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河南四·卫辉府》,第2303页。而邢、洺、磁州与泽潞镇关系最密切:邢州,“西带上党(潞州),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北直六·顺德府》,第658页。洺州,“邢、磁之中枢……攘夺洺州、邢,西逼上党,而河东兵势为之衰钝”;[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北直六·广平府》,第674—675页。磁州,“倚太行之险,控漳、滏之阻。……当太行之口,恒藉以联络邢、洺,为昭义之襟要”,[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河南四·磁州》,第2332—2333页。它们在地理上皆与泽潞镇的安危息息相关。在泽潞镇并未统辖邢、洺、磁三州时,薛嵩所领之地无疑在地理形势上对泽潞镇占据着优势。此外,薛嵩乃薛仁贵之后,在河朔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豫安禄山乱,晚为史朝义守相州”,[注]《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附薛嵩传》,第4144页。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皆为唐廷劲敌。安史之乱平定时,薛嵩又是以全军降唐,“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五月条,第7175页。与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等互为表里,实力强劲。因此,此时的泽潞镇,“兵所走集,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伍刁顽”,[注]《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真传》,第4621页。还未经李抱真整顿,实力并不强。同时,河中镇同样是泽潞镇西部的隐患。至于与泽潞镇相邻的河南地区,处在被唐廷抑制许久的李光弼统领之下,在代宗逃亡陕州时,近在咫尺的李光弼按兵不动,吐蕃退后又“欲收江南租赋以自给”。[注]《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11页。吕思勉先生评价道:“元振、朝恩诚非佳人,光弼亦非纯臣……当时朝廷经费,深赖江淮,果为光弼所擅,复何以自给邪?”[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19页。因此,在安史之乱期间曾经口出“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的李光弼,[注]《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04页。此时虽未明拒朝命,其实已非可靠之人。两相对比,薛嵩在政治、军事形势上对泽潞镇也呈绝对优势,因此,一旦形势有变,泽潞镇仅应对薛嵩就已经非常困难,能勉强自保就算不错的结果,根本不能为河东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仆固怀恩之乱发生时,被李抱玉委以军事的李抱真就迅速被擒获,足以证明以上所言并非凭空而断。因此,仆固怀恩及相关势力使河东镇东部、西部、南部皆有不安因素,作为河东镇主帅的辛云京无时无刻不处于压力之下,也就时时对仆固怀恩的所作所为极为敏感和戒备。
三、辛云京对仆固怀恩与回纥特殊关系的戒备
唐廷收复两京,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颇借回纥之力,唐廷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直至武宗时期,李德裕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谓:“彼蕃自忠义毗伽可汗以来,代为亲邻,连降爱主,恩礼特异,古今莫及。”[注]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诏书》,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56册,第34页。但回纥经常纵兵掳掠,在第一次收复洛阳时就“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略三日而止,财务不可胜计”,[注]《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9页。令唐廷头痛不已。但除了尽力抚慰之外,别无他法。代宗即位不久,遣宦官刘清潭出使回纥,欲再修旧好,回纥却为史朝义所诱,“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九月条,第7131页。纵兵南下,给唐廷造成极大震动。后在进至陕州时,又因时为雍王的德宗不对可汗拜舞,“引(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还营”,[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十月条,第7133页。使德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此,回纥留给唐廷君臣的印象极为恶劣。大历年间,出使回纥的萧昕就指出:“国家自平寇难,赏功无丝毫之遗……且仆固怀恩,我之叛臣,乃者尔助为乱,联西戎而犯郊畿……是回纥自绝,非我失信。”[注]《旧唐书》,卷一四六《萧昕传》,第3962页。由此更可见回纥在唐廷君臣心目中无疑是危险之众。
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仆固怀恩不但成为唐廷与回纥的关键联络人,而且与回纥可汗成为姻亲,又经常与回纥兵并肩作战,充当进攻叛军的前锋。在不断地交往和征战中他们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仆固怀恩对回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这种特殊关系之下,唐廷欲保持与回纥的和睦,仆固怀恩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反过来看,正是因为回纥对仆固怀恩的无比信任,会很容易为仆固怀恩所招诱,成为唐廷的隐患。
行文至此,需要阐明一个问题,即时人对仆固怀恩的观感。安禄山作为蕃将,深受唐玄宗信任并被委以统领三镇的重任,却最终发动叛乱,几乎置唐王朝于死地,使得时人对蕃将的观感极为恶劣。陈寅恪先生谓,“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叛逆,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0页。早在史思明再度反叛和相州兵败时,仆固怀恩就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与偏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条史料:“史思明自称燕王。牙前兵马使吴思礼曰:‘思明果反。盖蕃将也,安肯尽节于国家!’因目左武锋使仆固怀恩。怀恩色变,阴恨之。……还遇吴思礼于阵,射杀之,呼曰:‘吴思礼阵没。’其夕,收军,郭公疑怀恩为变,逐脱身先去。”[注]《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五《唐纪七》,第167页。
史思明复叛与仆固怀恩并无关系,而吴思礼以蕃将不肯尽忠于国家而直指仆固怀恩,几乎将其与史思明同等看待,当然会引起仆固怀恩的忿恨。仆固怀恩射杀吴思礼可谓纯属私人恩怨。虽说战场形势复杂,作为统帅的郭子仪之所为自有其考虑,但其中一个“疑”字却反映了仆固怀恩不但在诸军中,甚至在朔方军内部也一直不受信任的事实。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固然是一方面,[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二月条,第7105页。但是安史之乱期间官军恃功不法者非独仆固怀恩一人。实际上,“不法”在朔方军乃至神策军中皆为普遍现象。在收复洛阳时,朔方军、神策军“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十月条,第7135页。在所有的“不法”中,独仆固怀恩所受歧视最为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仆固怀恩的蕃将身份。在仆固怀恩之乱平定后,有大臣所上贺表中言:“逆贼怀恩者,毡裘杂种,出身微贱。陛下以其久经驱策,尝立功勋,任以枢机,升之上将。而豺狼其性,枭獍其心。连结西蕃,因依北虏,大为人患,二年于兹。谓旅拒可以偷生,猖狂可以集事,曾不知逆天暴物,其恶贯盈。故王师未加,而元凶自毙。”[注]《文苑英华》,卷五六七《贺仆固怀恩死并诸道破贼表》,第2908页。其中“毡裘杂种”“豺狼其性,枭獍其心”等词句,充满着“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的表达,代表了时人对仆固怀恩的最直接观感。因此,出身河西大族又曾为郭子仪“吏使”的辛云京,[注]李昉:《太平广记》,卷一七六《郭子仪》,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12页。自然对仆固怀恩先就有着不信任感。
更为重要的是,最初河东镇的设置就是为了配合朔方镇防御北边。安史之乱平定后,回纥成为不安定因素,因此北边防御的重心自然转为回纥。仆固怀恩作为朔方节度使与回纥的特殊关系,显然极大地淡化了朔方镇的防御功能。加之回纥在不久之前就曾为史朝义所招诱,意欲纵兵南下,不能不使辛云京及河东镇将士对仆固怀恩与回纥的交往极度敏感和戒备。这种敏感和戒备在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初,仆固怀恩受诏与回纥河汗相见于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以可汗乃怀恩婿,恐其合谋袭军府,闭城自守,亦不犒师。”[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条,第7147页。在安史之乱平定后,辛云京的敏感和戒备就更为强烈。此时仆固怀恩与回纥的特殊关系不得不使辛云京有这样一种更为强烈的担忧:如果出现仆固怀恩诱使,或回纥欲偷袭的情况,都会导致两者的联合,河东镇将处于东、南、西、北的包围之中,届时将会给河东镇尤其是太原带来最为直接的危险。因此,在仆固怀恩迎送回纥可汗时,辛云京的紧张与不安可想而知:
《邠志》曰:“宝应二年,河朔既平,诏太原节度辛云京及仆固怀恩各以其军送回纥还蕃。既出晋关,辛公率其轻兵先入太原。怀恩怒其不告,曰:‘辛君有虞于我也。’回纥至……见罗兵于诸街,蕃人大惊,辟易而去。”[注]《资治通鉴考异》,卷十六,代宗广德元年八月条,第174页。
同时,也应看到,仆固怀恩与回纥的交往虽是奉朝旨而行,但也不是完全光明正大的。在仆固怀恩顿军汾州后,“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纥还,怀恩先与可汗往来,恐翊泄其事,遂留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九月条,第7150页。仆固怀恩所害怕泄露之事,应当是为了自身考虑而与回纥私下所达成的某种协议。这种隐晦的交往被时为赵城尉的马燧所探知,并对李抱玉做了自己的解读:“燧因说抱玉曰:‘燧与回纥言,颇得其情。仆固怀恩恃功骄蹇,其子玚好勇而轻,今内树四帅,外交回纥,必有窥河东、泽潞之志,宜深备之。’抱玉然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闰月条,第7141—7142页。马燧所言可证明,仆固怀恩确实与回纥达成了某种共识。此种共识被马燧解读为仆固怀恩有意将河东镇、泽潞镇也控制在自己手中。
彼时河北四镇已置,与仆固怀恩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河东镇、泽潞镇互为掎角的河中镇在朔方军的控制之下,河东镇西部为朔方军的原始基地,河东镇的北部并不稳定,且对太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振武镇同样在仆固怀恩的统领之下,因此,河东镇可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而泽潞镇的处境虽非如河东镇那样被四面包围,但实力较弱,一旦形势有变,自保尚且困难。故而,马燧的解读是符合逻辑和现实形势的,因此李抱玉“然之”。那么,比李抱玉的处境更为复杂的辛云京就更是如此认识了:即使仆固怀恩不反,按照趋势,下一步也应该是取得河东、泽潞二镇的控制权。这对刚取得河东节度使之位的辛云京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的。于是,便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辛云京从历史记忆和现实局势出发,对仆固怀恩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并采取了相应的防备措施;而仆固怀恩作为平叛的功勋、河北副元帅及回纥的联络人,其所行之事皆与唐廷的朝旨相符合,在遭到辛云京的疑忌和防范时自然相当愤怒,出现了顿军汾州、不听朝命的事实反叛行为。
四、唐代宗对辛云京、仆固怀恩类似的情感和优待
仆固怀恩之乱给唐廷所带来的震动无须赘言,但对于仆固怀恩,唐代宗可谓宽容至极。在骆奉仙上告仆固怀恩谋反时,代宗“以功高容之,叱奉仙出,待怀恩如旧”。[注]《资治通鉴考异》,卷十六,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条,第174页。在仆固怀恩顿军汾州抗拒朝命时,他又“遣宰臣裴遵庆往宣抚之”。[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第273页。更在招谕仆固怀恩的诏书中言道:“朕以白日旌信,明神鉴心,若有负功臣,是大欺天下。为人君者,岂有此乎?……但当诣阙,更亦不疑,再三言提,庶早牵复。欲令方寸,悬示万邦,尔无我虞,朕言不再。久劳于外,必无成功,收之桑榆,殊未为晚。甘言之诱,王者不为,危而悔之,嗟何及矣。”[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招谕仆固怀恩诏》,第618页。
唐代宗一再表明,不会做出鸟尽弓藏之事,希望仆固怀恩回头是岸,可谓苦口婆心。在吐蕃撤军、收复长安后,他欲遣颜真卿宣慰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汾州兵败河东后,他又恩养其母,“给待甚厚,月余,以寿终,以礼葬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二月条,第7163页。此后,他仍然希望仆固怀恩能重新归朝,“朕惟务责已,情重旧勋,如能翻然来归,必从宽宥”。[注]《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永泰敕》,第24页。直至仆固怀恩死,代宗“犹为之隐,前后敕制未尝言其反”,[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九月条,第7177页。在听闻仆固怀恩死讯时为之恻然曰:“ 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注]《新唐书》,卷二二四《仆固怀恩传》,第6372页。因此,可以说,直到最后代宗仍然坚持认为仆固怀恩不是反臣。他在仆固怀恩死后又收养仆固怀恩的幼女,于大历四年(769)册封其为崇徽公主,“视同第十女,下嫁回纥可汗……诏宰臣以下百僚送至中渭桥”,[注]《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第11336页。其规格不可谓不高。在《册崇徽公主文》中,代宗在对仆固怀恩的小女夸奖一番后,言道:“割爱公功,嫔于绝域,尔其式是壶则,以成妇顺,服兹嘉命,可不慎欤。”[注]《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册崇徽公主文》,第207页。这完全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不舍与期望之情。
对激反仆固怀恩的首要责任者辛云京,唐代宗也有着几乎相同的态度。大历三年(768)辛云京去世后,代宗表现出了特殊的情感:“追悼发哀,为之流涕……后宰臣子仪、元载等见上,言及云京,泫然久之。”[注]《旧唐书》,卷一一〇《辛云京传》,第3314—3315页。辛云京的身后也得到了极高规格的待遇:“及葬,命中使吊祠,时将相祭者七十余幄,丧车移晷乃得去。德宗时,第至德以来将相,云京为次。”[注]《新唐书》,卷一四七《辛云京传》,弟4754页。不但其葬礼极尽哀荣,而且在其去世多年后仍然得到德宗的殊礼。代宗的态度还影响到了其他藩镇,“诸道节度使使人道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注]封演:《封氏见闻记校注》,卷六《道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1页。辛云京死后第二年,在代宗的授意之下,时任宰相的元载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注]陈思:《宝刻丛编》,卷八《陕西永兴路二·京兆府》,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2册,第332页。书中辛云京墓志及撰书者等内容题为:唐赠太尉辛云京碑,唐元载撰,史惟则分书并篆额,大历四年,京兆金石录。佚名:《宝刻类编》,卷三《名臣十三之二》,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2册,第629页。该书所载与《宝刻类编》大致相同,只是不载书者。不仅如此,代宗对辛云京的家人也给予了特别的关照。辛云京夫人于大历三年去世,而在十年后迁葬时,代宗给了高规格的礼遇:“圣慈轸念,诏赠肃国夫人,备物典策,及乎哀荣……圣上以相府有保乂之勋,以夫人有明哲之行,护问吊赙,用加恒制。”[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9页。辛云京之子辛浩则被任命为太常少卿,大历十三年去世时被赠予代州都督的头衔。[注]《宝刻丛编》,卷九《陕西永兴路三·京兆府下》,第358页。书中辛浩墓志及撰书者等内容题为:唐太常少卿辛浩墓志,唐成朝秀撰,韩秀实分书,大历十三年,京兆金石录。该书卷八《陕西永兴路二·京兆府》,辛浩墓志及撰书者等内容题为:唐赠代州都督辛浩墓志,唐成朝秀撰,韩秀实八分书,大历元年,京兆金石录。据此,辛浩死于大历元年。但《辛云京夫人墓志铭》中载辛浩犹在,则辛浩死于大历十三年无疑,《宝刻丛编》写为大历元年有误。
因此,代宗对两人几乎类似的情感和优待,堪称吊诡,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在安史之乱即将平定的大势下,唐廷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藩镇问题。唐廷对藩镇的调整遵循着一条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的路线,即:先罢诸州防御使,[注]《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第9页。收回一些重要州郡的控制权;接着废除京畿节度使、华州节度使,[注]《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一》,第1768页。将长安附近地区牢牢控制住;然后对长安附近的藩镇如河中、泽潞镇主帅进行措置,[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第272页。巩固长安的第二道防线,同时对河北降将予以优待,徐图后进。这其中,对朔方军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彼时郭子仪已经闲置已久,李光弼在河南郁郁不得志,仆固怀恩是朔方军的当然领导者,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即使没有辛云京、李抱玉等人的因素,唐廷也会对仆固怀恩采取措施,削弱并分化其权势。但是,仆固怀恩对巩固唐廷与回纥的联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使之如郭子仪那样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唐廷的藩镇、对外政策所服务是必然的趋势。既如此,仆固怀恩可以获得如郭子仪那样的政治荣宠,又不对唐廷产生实质性威胁,同时,能够有利于唐廷对朔方军的分化调整和助力唐廷联络回纥,并力西向,应对威胁日重的吐蕃,这对仆固怀恩而言自然是一种良好的政治归宿,对唐廷而言也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然而,这种双赢的局面最终由于仆固怀恩发动叛乱而不能实现。首先,仆固怀恩之乱导致了唐廷与回纥关系的再次恶化,使唐廷遭到回纥、吐蕃两大少数民族政权的同时威胁。其次,久为唐廷所闲置的郭子仪复出,对朔方军势力的分化削弱不得不再次搁置。最后,河北四镇乘机纠合旧部,各署文吏武将,并且互为掎角,渐成跋扈之势,使得唐廷重新恢复对地方的威权的努力宣告消散。这些连锁反应,对代宗而言无疑是一种无奈的失败。
仆固怀恩之乱初期,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即:仆固怀恩与回纥联合取得河东、泽潞二镇后,西联吐蕃。这对大乱之后的唐廷而言,不亚于再次处于生死存亡之地。河东、河北诸镇中,只有辛云京所领的河东镇、李抱玉所领的泽潞镇为唐廷所控制。而仆固怀恩之乱发生、吐蕃入寇长安后,李抱玉率兵赴凤翔节度使,本就实力弱小的泽潞镇根本无法应对。因此,唯一为唐廷坚守的便是辛云京。
辛云京的坚守,对唐廷的意义非常重大。河东三镇中,以河东镇实力最强、地位最为重要。在肃、代更迭之际,正是辛云京在河东推按谋害前节度使邓景山的举动,避免了河东镇以及同样发生动乱的河中镇与河北叛乱地区合纵的可能性,使“河东诸镇率皆奉法”。[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五月条,第7126页。因此,只要河东镇牢牢掌握在唐廷手中,则河中镇虽为朔方军所控制,却不能轻举妄动,而泽潞镇也就有了坚定的奥援,河东三镇皆能稳固并听命于唐廷。河东三镇稳固,对河北四镇则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相卫薛嵩在马燧的劝说下“绝怀恩从顺”,[注]《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0页。成德李宝臣“露布斩逆贼蔚州刺史曹楚玉,并破党项部落,收诸蕃官兵及百姓等三万余众”,[注]《文苑英华》,卷五六七《贺仆固怀恩死并诸道破贼表》,第2907—2908页。魏博田承嗣“率德相从,械系行人,显与之(仆固怀恩)绝,暨声问达于四境”。[注]《全唐文》,卷四四四《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第4532页。而从辛云京死时“范阳祭盘最为高大”的记载中也可以推测出,在辛云京的经营下,幽州最终与其他三镇保持了一致的举动。河东、河北局势稳定后,唐廷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组织各方力量进行反攻,仆固怀恩也就此走向失败之路。
就唐代宗对仆固怀恩的态度,吕思勉先生做出了精辟的分析:“禄山、思明,且皆无大略,而况怀恩?观其既叛之后,分崩离析,绝无能为,而知其本无叛志。此朝臣所以多明之,而代宗终信之欤?”[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12页。仆固怀恩的悲剧在于不识大势,或者说对形势有一定的感知,却要坚持抗争。而代宗对辛云京的态度,王夫之谓:“(仆固怀恩)叛之速,而祸止于太原与奉天,河北不与俱起,犹云京、抱玉之功也。”[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代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8页。辛云京之功也可谓力挽狂澜。因此,面对类似伍子胥、申包胥的仆固怀恩、辛云京,代宗的吊诡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余论
辛云京虽出身于河西大族,“有胆略,志气刚决,不畏强御”,[注]《旧唐书》,卷一一〇《辛云京传》,第3314页。但在任代州刺史时“屡为将校谗毁”,[注]《旧唐书》,卷一二七《张光晟传》,第4573页。遭到节度使王思礼的猜忌,为张光晟所救才免于祸,可见其在河东镇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同时,辛云京又是在河东镇发生动乱、前节度使邓景山被谋害时才被推为节度使,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对河东镇的控制自然不具有稳固性。故而,辛云京在大乱初定后的政局变动中,在事关河东镇安稳时显得格外敏感和警惕。
身处大变动中的政治人物,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会有一定的感知。如唐肃宗时,宋州刺史刘展面对唐廷提升自己为江淮都统的行为,谓:“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租赋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十一月条,第7098页。其已经隐约意识到唐廷要处置自己。同样的道理,作为安史之乱后期权势最重的仆固怀恩,其身处政局变动的最前沿,面对郭子仪、李光弼的被抑制,乃至来瑱的悲惨结局,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应当有着更为深刻的感知。仆固怀恩“为人雄毅寡言,应对舒缓,而刚决犯上”,[注]《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3479页。在政治上远不如郭子仪那般隐忍、退让和妥协,因此,面对时势时,选择的是直接对抗。他内树四镇,外交回纥,以其子仆固玚统领朔方军,虽皆有朝命,也暗含着在乱后政局中稳固自身地位的意图。
仆固怀恩的种种举动,皆与河东镇密切相关,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不能不令辛云京产生强烈的疑惧和戒备。仆固怀恩所谓“闭城不出祗迎,仍令潜行窃盗……闭关不出相看”,[注]《全唐文》,卷四三二《陈情书》,第4395页。正是辛云京结合自身处境,在疑惧和戒备之下所采取的直接应对措施。在辛云京看来,无论仆固怀恩是勾结回纥和河北四镇反叛,还是如马燧所说的窥视河东、泽潞,对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一种极大的危险。与普通人有所不同的是,像辛云京这样的政治人物在疑惧和戒备下的举动,对政局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极大。而我们从唐代宗对尖锐对立的两人有着近乎类似的情感和优待的“吊诡”态度,则可以对安史之乱平定后的政治局加以更为深刻和符合现实逻辑的解释。
后世史家在阐释仆固怀恩之乱时,往往把焦点放在郭子仪和仆固怀恩身上,而对辛云京经常一笔带过,似乎他只是仆固怀恩之乱的一个引子,之后的事情与他无关。事实上,虽然新、旧《唐书》的辛云京本传加起来不过寥寥数百字,在仆固怀恩之乱中的出场不多,其却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不能不做深入探讨。在政治史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与研究对象看似不相关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对政治人物所采取的种种行动进行符合当时形势和现实逻辑的探讨,才能接近历史事实的原貌,进而对政治史有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