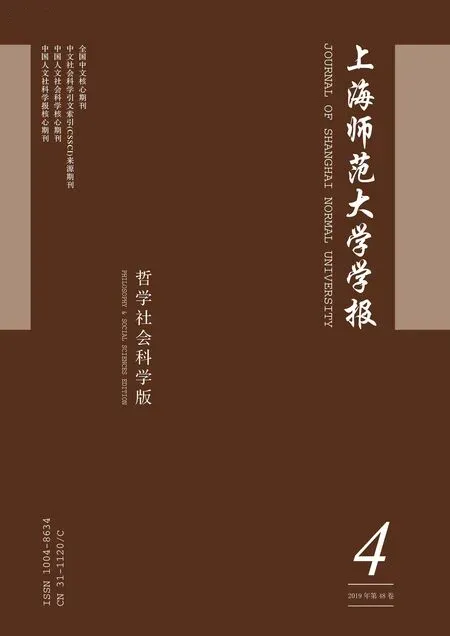孔子的文化责任和对于神话的责任
鲍鹏山,张 瑞
一、中国神话流传的面貌
神话的创造在文字产生之前,其流传依赖口耳相传,而神话的记录则须到文字产生之后。这样的时间差,就使得神话的流传后世有了一种危险:那些能够娴熟地使用文字来记录远古传说的后人,对神话的态度,包括是否尊重原貌的记录,抑或弃之不顾的弃置,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理性主义的改造,等等,都会影响神话的流传与否及其在后世的面貌。
我们今天见到的有关中国神话的记录,都不是最初的记录。于是,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有无最初的记录?或者是,有,但后来失传了?——便只好猜测。进而,孔子、司马迁到底有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古代文字记录?或者说,对于远古神话,他们也只是耳听(口头)而不是眼见(文字)?“好古”的、“述而不作”的孔子在删定六经的时候,绍圣孔子的司马迁在面对古代史料而撰述《史记》的时候,他们有无见过我们想象中的类似于希腊神话那样的文字?
其实,在先秦,比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记录有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的神奇经历;[注]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3—547页。《史记》的《殷本纪》《周本纪》及《秦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录,但这些有关民族始祖的神奇记录,严格意义上说不再是神话,而是传说。神话的主体是神,而传说的主体是人。神话是虚构一个世界或虚构一个对世界的解释;而传说是给现实世界一个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尊崇神灵,而是敬奉祖先,其源流,可以追溯到这里。
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逸周书》以及诸子之文如《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有一些零星的、散乱的、被实用主义理性精神改造过的神话记录。
更多的神话记录不是出现在先秦典籍中,而是出现在两汉的典籍中。即便如《山海经》,也是“秦汉增益之书”。[注]文清阁编:《历代山海经文献集成:第4卷》,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0页。今人认为《山海经》乃是战国初年至汉初的作品。袁行霈、袁珂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还在于,“《楚辞》《山海经》等书所述,不过是广大的神话世界的一小部分”。[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7页。
两汉记录有神话的著作中,西汉还有《淮南子》,东汉也有王充的《论衡》,等等。《淮南子》对神话的记录很有规模,是一部对神话传说的有心之作。但是,由于这都是二手改造过的资料,与神话的原貌应该有不少的差距。
这种差距就是:这些有关神话的记录,尽量让这些本来神奇的东西历史化、理性化、伦理化,然而失却了原来的面貌。
这种变化的一个巨大的推手,就是孔子,以及他开创的儒家学派。
其实,《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注]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和《史记》之《五帝本纪》中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注]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8页。则又暗示了“怪力乱神”之说以及百家有关黄帝的“不雅驯”之言,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在在皆是的。而“其文不雅驯”之评,既然说是“文”,似乎司马迁见到的应该是诸子百家对于黄帝的“文字”记录。当然,口耳相传的东西应该更多,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19页。可见,那时代神话传说还在民间保存着,并口耳相传着。但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六经,“《尚书》独载尧以来”[注]司马迁:《史记》,第18页。,黄帝的那些神话传说已然被删。到了汉代,连《孔子家语》中所载的“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注]司马迁:《史记》,第18页。了。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基本上也就是敷衍《孔子家语·五帝德》中孔子的话[注]《孔子家语》,第211—219页。(亦见《大戴礼记·五帝德》);除此之外,“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注]司马迁:《史记》,第19页。
这样“择雅”的结果,是原始的记录和当时尚在的民间传说被汰弃了,而留下来的都是经过删汰、弃置和改造的东西。如鲁迅所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那么,一个问题是:孔子为什么对神话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这就要考量孔子自我确立的文化责任,以及这种文化责任与神话之间的伦理冲突。
二、孔子对神话的态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及“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0页。袁珂认为:“以儒门正宗自居的卫道士,还是要竭力去遏阻和制止神话流传,……以为要这样才符合圣门的宗旨和心传。这就是使部分神话不得不散亡的原因之一,而其关键并不在于孔子本人。”[注]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显然,学者们都认识到孔子对于神话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
孔子对于鬼神,是有二重态度的,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重态度,是孔子并不在事实的层面上认同鬼神实有。
“子不语怪、力、乱、神”,其实,不语也是一种“语”,他是以此表明一种态度。为什么“不语”?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既然不相信,也就不愿意传布。我们知道,孔子的时代,传播的主要形式就是“说”和“听”,就是口头的“语”,而不是“写”和“读”。孔子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传授,不是以文章的形式实现的,《论语》乃是孔子去世之后,弟子对孔子口头之语的回忆和记录。如果孔子平时对鬼神“不语”,则弟子事后的记录——“论语”,也就无从“论”起。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24页。“祭如在”,应该是“祭鬼如鬼在”的简略式。鬼者,归也,祖宗所归往,子孙所归敬也。其全句意为:孔子祭祀祖先时,好像真有祖先在受祭;祭神时,好像真有神在受祭。既然是“如在”——就是假设在、好像在——则祭祀之时并非祖宗、神灵真实“在场”并受祭,而只是在祭祀时为了保持虔诚,心中默念祖宗、神灵“如(同)在”而已。可见,孔子这句话,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他不信鬼神真实物理性的存在,他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
所以,孔子对于鬼神的第二重态度,是孔子在价值层面上认同鬼神信念的社会道德功能。
《孔子家语·致思》曰:
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注]《孔子家语》,第81页。
子贡的问和孔子的答,其实不在一个逻辑层次上。子贡问的是事实层面的问题:鬼是否实有。孔子答的是价值层面的问题:对鬼之有无的认定,会影响人类的伦理选择。所以,对孔子而言,对于“死者有知无知”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关键不是去辨别事实,而是考量价值。
《礼记·表记》曰:
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注]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1页。
孔子实际上已经看出了鬼神信仰乃是出于一种价值考虑而不是事实认定。
其实,鬼神这种无稽之物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某种价值。后来的墨子看出了在孔子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鬼神实有,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反对孔子,反对儒家,力证鬼神实有。其实,他又哪里真的是有“科学”精神,究其实还是“伦理”的考量。在《墨子·明鬼下》里,墨子很卖力地证明鬼神的存在,他并非要“科学”地证明一个事实,而只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世界有无鬼神决定了人类的道德水平,决定了我们能否体面清白地做人。墨子批评“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墨子·公孟》),儒家对于鬼神“不明”之判决、“不神”之贬斥都是以实用理性判断为根据。
是故子墨子言曰: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见有鬼神视之。[注]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31页。
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241—242页。
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242页。
既然有鬼神在旁,鬼瞰其旁,我们哪敢胡作非为?
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242页。
墨子可能意识到,对绝大多数细民而言,“敬鬼神而远之”是高不可及的德性自觉。所以,鬼神的赏善罚恶功能,在圣贤眼里是伦理学功能,在细民眼里恰恰是利害计较:没有了鬼神,就没有了鬼神的赏善罚恶功能,没有了鬼神的赏善罚恶,细民就没有了利害计较,就没有了道德约束。所以,墨子必须坚持鬼神的实体和鬼神功能的不可分离: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56页。
作为儒家门徒、曾子的学生,公孟子的说法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但是墨子认为两者是体用不分的关系。
再看下面的对话: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子墨子曰:“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为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54—455页。
公孟子的说法,其实就是孔子的基本观点。孔子答子路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20页。实际上就可以看成是“有义不义,无祥不祥”。而下面这则更能说明:
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注]刘彬:《帛书〈要〉篇校释》,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也正是“有义不义,无祥不祥”思想的体现。
再看《论语·述而》: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80页。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天道无亲,唯德是辅。修养自己的德行,就是一直在祈祷。反之,“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24页。需要对人之祸福负责的,是人自己,而不是神;决定人之祸福的,是人行为的义不义,而不是时运的“祥不祥”。
还值得注意的是,公孟子的观点是一种伦理学的义理式表达,而且这种观念源远流长。但墨子的回答则并不从义理、学理和逻辑上来回复,而是以他认定的“事实”来回答。墨子可能觉得对方的观点有太强大的文化支撑,自觉无法在义理上战胜对方,所以,他只好选择用历史事实——当然是他认为的历史事实——来说话:相信鬼神的圣王,政治国安;不信鬼神的桀纣,政乱国危。
其实,墨子的思想也有历史的渊源。比如“神道设教”,《易·观》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注]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圣人确实有必要利用小人的“迷信”来实现道德的目标。因为迷信也是一种信,有信则有行,无信则无行;信行则忠良孝悌,无信则放辟邪侈。有信之民,胜过无信之民。
最能说明孔子对待鬼神的二重态度的,可见《论语·雍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62页。
既“敬”鬼神,为何又“远之”?因为“敬鬼神”,是为了敬一种价值;而“远之”,是因为不相信鬼神实有,不能沉迷于鬼神的执念。不知敬畏神秘力量,是没有信仰;迷信鬼神实有,是缺少理性精神。既有信仰,又有理性,这就叫智慧。
《礼记·表记》中所记孔子的话,对“敬鬼神而远之”这一态度有个对照说明: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注]王文锦:《礼记译解》,第813页。
作为对照组的殷人和周人中,殷人是“尊而不亲”,周人是“亲而不尊”,两者各有弊端。但细揣两者之弊,殷人的弊来自相信鬼神实有,故有“民免而无耻”之忧;而周人的弊似乎不在不相信鬼神实有而远之,而在于敬鬼神不够。如能在“远之”之时又能保持足够的敬,则“可谓知矣”。
综上所述,孔子对神话的态度,虽不能说就如袁珂所说的是“竭力遏阻和制止神话流传”,但是,对流传于民间口头的神话和或许存在的前人记录的神话,他应该是消极对待的:能够改造使之承担相应价值的,则加以改造;不能使之承担价值或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反的,就任其湮灭。这应是孔子的很正常的选择。
三、殷周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孔子的弃取
虽然孔子对夏商周三代之礼都表示过出于思想家的尊敬和出于史学家的兴趣,但是,相较而言,“周礼”所代表的周文化是他真正心仪之所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25页。这是孔子对三代文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弃取。孔子屡称文、武、周公,对文、武、周公之前的尧、舜、禹、汤也依据周文化的价值观予以形象重塑和定型;而他以传承周文化作为自己的天命之所在。《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92页。
殷周文化的大差别在哪里呢?
周文化轻鬼神祭祀,重人伦道德,重人道、轻天道,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都是对迷信鬼神的商文化的否定。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彭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国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殷周之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其基本特征就是:其一,由神(天道)向人(人事)的变革;其二,由重神权、重神事向重人事、重民事的变革。
殷人的精神信仰专在祖先神、自然神及上帝,而周人的精神生活则除了祖先神、自然神外,又添加了自我的德性,并凭借着这种优势战胜了大邦殷商,取而代之。对于自身道德的严格要求和自信,成为周人“天命转移理论”的核心内容,并由此解决了西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由于周人重视统治者的自我德性,并充分认识和评估自我德性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西周的统治思想特别注重“明德”和“敬德”,对美好德性的追慕和尊崇成为一时的贵族风范。而且,这种德性还不仅仅是一种自涉的个人修养以及自我的气质、行为和做派,更是一种涉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家风范。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家风范,也就是执政价值取向的“惠民”“保民”以及“慎刑”和“隆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0页。其实,这是对西周政治理念的遥望和追思。前引帛书《要》中孔子的话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注]刘彬:《帛书〈要〉篇校释》,第16页。孔子的自叙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而他的归结乃是“求其德”,这正是孔子于古代文化的弃取。
求其德,是指对人而言。而孔子之学,不仅如此,甚至更主要是求天下道义:
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注]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事实上,在先秦文献中,“德”字在《尚书》中频繁出现,有两百多次之多。从中我们看到,殷人在政治生活中也多次提到“德”字,并把它看作是政治的生命。但相较而言,殷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更多地沉迷于对帝与天道的迷信,而对人事、道德有意无意地轻忽。周人对“德”则有创造性的转换——对统治者个人德行品质的价值规定——并把它上升为天命的依据。 “有德”才有“天命”,明德、义德是膺受天命之德,而凶德、暴德为丧失天命之德。
而且,周人的德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政治政策中,《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注]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是对政治的深刻认知,从此政治的核心就是“德”。而“德”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民”的保护和蓄养。 “保民”即保有小民、爱护小民,《尚书·周书》中,“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乂”“惠康小民”“裕民”“民宁”“恤民”等说法比比皆是。[注]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第529—547页。《尚书·梓材》记周公的警告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注]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第567页。——想拥有万年江山,只有子子孙孙的统治者永远保民。“小邦周”战胜“大国殷”,其间民众之力量、民心之向背,一定给周初的周公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彭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国维卷》,第142页。由此,从道德的个人,到道德的政治,再到道德的社会,周的“德”文化涵盖了人生的一切方面,不仅体现为社会的文明、政治的清明,还体现为人格的贤明——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儒家安身立命的场所,也在“德”中。
四、孔子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感
孔子所心仪的,就是这样的“德”文化。他在历史上那些成就大功的人物身上也发现了“德”的因素,他甚至把“德”解释为这些人物成功的唯一因素。《论语·宪问》: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61页。
善射、善水,迷信神力,都将失败,只有德行战无不胜,终将拥有天下。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切非常态的东西,孔子都不谈,孔子只要我们懂常识。一切太玄妙、太神秘、缺乏根据的东西,孔子也不谈,孔子要我们有理性。孔子担心侈谈这类东西会让人走火入魔,不仅胡说八道,还会胡作非为;其结果是:不相信自己的命运由自我的德行决定,反而把它付之于一些不可知的东西,这不仅是道德卸责,还会引起道德堕落。
所以,孔子讨论常态的东西而不谈变异的东西:常态的东西是普遍适用的知识,我们必须掌握;变异的东西只是特例,不具备知识的普遍性。孔子只谈论人的品德而不谈论人的勇力:德行是根本的、可以养成的,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关键;勇力是末节的,且往往是天生的,与一个人的最终价值关系不大。孔子谈论合理的东西而不谈论混乱、有悖常理的东西:合理的东西是我们判断的依据和前提,是我们一切知识的基础;有悖常理的东西虽然在某时、某地偶然存在,但恰恰是反知识、反常识的,过多地谈这些东西会损害我们的正常思维。孔子谈论人力而不谈神奇:人的品行、行为、意向决定人的命运,而不是所谓的神奇、神力。人力实在而决定权在己;鬼神玄虚、无实据而决定权在他——不仅与人之幸福互不关涉,相信神力还有碍人类的道德自我提升。
在孔子看来,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才是智慧,甚至是智慧的起源。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弘扬的就是这样的智慧。
与不语怪、力、乱、神,与对神话人物非常隔膜、敬而远之相对的,是孔子对历史人物的亲近感。《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注]王文锦:《礼记译解》,第796页。孔子畅言尧、舜、文、武,而且全是从道德角度对他们进行表彰,以期成为人类尤其是人类中统治者的榜样。
在孔子看来,尧舜以德,神鬼以力。从价值的角度言,人德胜过神力。从古希腊神话以及中国的零星神话都可以看出,那些神祇在能力上是神,在德行上却是人,具备一般俗人的一切弱点和缺点,所以,神话中的人物不可能在德行上引导人类。这一点被孔子明显感受到了,所以,他有意识地拒绝谈论神话,而全力推崇人中的古代圣贤,因为这些圣贤具备了比神话中的神更加完美的品行,更有资格成为人类的膜拜对象。而“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射十日、杀猰貐、断修蛇、禽封豨”[注]刘安撰、许慎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的后羿等神祇,依靠的不是德行,而是神力。甚至,在后来的孟子看来,后羿甚至是有罪的:“逢蒙学射于羿, 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1页。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不是这些神力不伟大、不重要,尤其是当它用于正义事业的时候。问题在于,这种神力无法为人类所拥有,仰仗这样的神力不仅是虚幻的,还会导致人类的绝望,导致无力感,从而自暴自弃。所以,儒家文化对“力”的否定,是为了对“德”的肯定。人类不具备神话人物之“力”,但是,人类可以拥有超越神祇的“德”;这种“德”,比起神灵的“力”,更具有恒久的力量。由此,孔子也试图向人们展示人类自身的优势,建立人类自身的信心。
带着这样的认知,孔子自许的文化责任就是传承建立在人本基础上的姬周文化,弘扬推崇道德的尧、舜、文、武之道。《论语·宪问》: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76页。
孔子把“道之废行”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我的命运即道之命运,这样的文化担当意识相当显豁和强烈。
那么,哪些人可以称为“往圣”呢?孔子心目中的“往圣”,有七位。
尧、舜、禹三位,《论语》中皆有涉及。《论语·泰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88页。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89页。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89页。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90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语》中,“尧”出现6次,“舜”出现8次,“禹”出现5次,“周公”出现3次(另有一次似非指周公姬旦),“文王”“武王”“文武之道”出现4次,大致相当;但是,对比鲜明的是,黄帝、颛顼、帝喾等尧之前的三帝则一次也没有出现。这与司马迁说的“《尚书》独载尧以来”[注]司马迁:《史记》,第18页。是一致的。
《孔子家语·五帝德》: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有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注]《孔子家语》,第211—213页。
孔子对禹、汤、文、武及三王的推崇和对黄帝等五帝的冷淡,让我们不免揣测:是《尚书》有关黄帝内容的缺失导致了孔子对黄帝的生疏,还是孔子决定了《尚书》的这个现存样貌?
商汤、文、武、周公四位,《论语》中有如下记叙: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42页。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236页。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68页。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86页。
其他典籍中涉及的更多,随举几例于下: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注]《孔子家语》,第142页。
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昭假迟迟,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注]王文锦:《礼记译解》,第752页。
之所以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这七位,就是因为这七位体现了孔子心目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德”;体现在政治上,就是“道”;体现在社会秩序上,就是“礼”。《孔子家语·礼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未有不谨于礼。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注]《孔子家语》,第278页。
“礼”是什么?“礼”是相对于丛林野蛮时代和强权暴力时代的一种文明。从个人角度说,“礼”是一种个人面对他者时的文明相处方式;从政治角度说,是一种文明的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方式;从社会角度说,是一种文明的治理方式和和谐的秩序。简言之,“礼”是“道”的直观呈现,是“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实践和实现。
这种实践和实现,此前是由“王”——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来担当的,但是,王纲解纽之后,“王道”不存;曾几何时,甚至要靠“正而不谲”的霸主比如齐桓公来担当道义。“微管仲,披发左衽”[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68页。的意思,就是指,设若没有管仲,中原文化就会消亡,就会王道陵迟、礼乐文化绝灭。但是,孔子之时,王道、霸道俱已不存,孔子乃挺身而出,不仅自己以“士”的身份担当道义,而且创办私学,号召天下士人一起存亡继绝。“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注]钱穆:《孔子传》,第9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注]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9—150页。所谓“私名”,其实就是孔子所塑造的“君子儒”,其特征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所概括的:“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注]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6页。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则是出于《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注]王文锦:《礼记译解》,第796页。我们可以把这八个字看作是孔子自我赋予的文化责任。
于是,孔子开始对“士”进行重新定位,赋予他们重大的文化使命,那就是,担当起王和霸曾经担当的“道”。如《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33页。《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69页。《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87页。《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02页。《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92页。《论语·季氏》:“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202页。由上可见“道”在孔子生命中的分量。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33页。对“道”的认知和认同,成了生命的唯一价值;生命的对象化,就是道。这是孔子的绝大担当。后来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正是孔子的天命自许。而天地之心也好,生民之命也好,万世太平之根基也好,都是那些“往圣”身上体现出来的“德”。道德、道德,道即是德。《孔子家语·王言解》:“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注]《孔子家语》,第21页。
礼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礼是人间的秩序,孔子的历史使命就是致力于论证“礼”的价值,然后据此建立人间的秩序: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而后治其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其顺之也,而后言其丧祭之纪,宗庙之序。品其牺牲,设其豕腊,修其岁时,以敬其祭祀,别其亲疏,序其昭穆。而后宗族会燕,即安其居,以缀恩义。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注]《孔子家语》,第55页。
神话的世界是“无礼”的,神话的世界也是“无德”的,诸神的关系和秩序也不能给家国同构的人间人伦关系提供模范。孔子想在人间建立的秩序、人际的关系,是以人伦亲情为基础的。《周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注]周振甫:《周易译注》,第313页。从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儒家理解的秩序是基于人伦的;第二,虽然儒家把人伦的价值推之于先验的“天地”,但是,在天地万物中却没有神祇的踪影,在秩序的序列里也没有神祇的地位。
以人伦亲情为基础的人间秩序,维持的力量和价值的基础不是力而是德,所以,称德不称力是孔子评价现实人物和历史人物时的基本立场。连鬼神他都从“德”的角度来认知。《礼记·中庸》: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注]王文锦:《礼记译解》,第780—781页。
“鬼神之为德”,孔子直接就指明了鬼神的价值和功能在于“德”。甚至一匹马,他也觉得它的“德”更能体现它的价值。《论语·宪问》:“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75页。
称德不称力、崇德崇礼不崇力的孔子,对于崇力的神话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与神话,就是不相为谋而已。《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注]金良年:《论语译注》,第120页。“人”才是孔子关注的对象,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结穴处。
五、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孔子看来,尧舜以德,神鬼以力,而“德”比“力”对于社会、人间秩序更有恒久的力量。因此,孔子推崇人中的古代圣贤,而“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以此弃取殷周文化,以传承周代的“德”文化作为自己的天命,以弘扬尧、舜、文、武之道作为文化自觉,由此,对“士”进行重新定位,使其担当起“道”,并以“礼”建立人间的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的文化责任和他对于神话的责任,在价值层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是,孔子出色地履行了他的文化责任;而对于神话,他不仅没有尽到保护和传扬的责任,甚至,要对神话的零落负有相当的责任。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